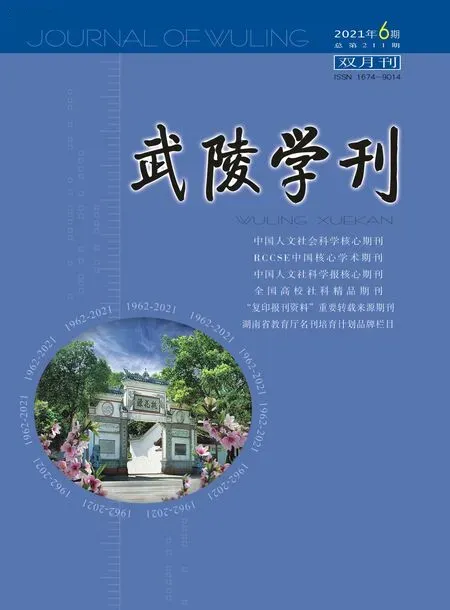颜钧忠孝思想钩沉
桑东辉
(1.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国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2.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0)
颜钧(1504—1596)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泰州学派的重要传人,其继承发扬了王艮的乐学思想,并将泰州学派的思想与民间教化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会讲、撰文和诗歌等多种形式,极大地宣扬了阳明心学,发展了泰州学派。作为传统的儒者,颜钧非常重视儒家的忠孝思想,大力宣扬忠孝思想,并将忠孝思想厚植于泰州学派的思想土壤中。
一、心性论:颜钧忠孝思想的理论基础
作为泰州学派的儒家学者,颜钧继承发扬了阳明心学特别是王汝止的“心是乐,乐是学”的乐学心性论,开显出忠孝乃人心性之衍发的义理,并将心性论作为其忠孝思想的理论基础。
如泰州学派的先驱王氏一样,颜钧也极其服膺阳明心学,高扬心的本体论价值。他从剖析“心”字的结构入手,来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指出:“先圣制‘心’字,以一阳自下,而湾向上,包涵三点,为三阳,将开泰以帝天地人物之父母也。是父母心,本能自湾,而竖立湾中,为佐以佩圭,为‘惟’者也。”[1]14颜钧从文字的结构入手,将心字的弯勾结构与三个点进行了心性道德哲学的阐析,认为古人造字已经将天地阴阳、父母之恩考虑在内。因此,人之忠孝道德也一样本于心性哲学。
在颜钧的著述中,心是出现频率颇高的概念。他赋予心以崇高的地位,所谓“窃谓天地之所贵者,人也;人之所贵者,心也。人为天地之心,心为人身之主”[1]1。也就是说,人为天地间之最尊贵者,而人最可宝贵的则是心。心是人之主,人是天地心。人心的根本在于道德,在于日用人伦。正如张载将儒家的道德责任定位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上一样,颜钧的道德哲学根本也在于发扬阳明心学特别是心斋乐学的泰州儒学精神,从拯救陷溺的人心入手,来建构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在颜钧看来,世道人心的陷溺主要是由于“圣学蓁芜,人心汩没”,从而造成“人人心火,忙里堪舆,各各心红,营为宇宙”[1]2。基于此,颜钧写了《急救心火榜文》,其所救之心火在于六急,其中包括“急救人心陷牿,生平不知存心养性”“急救人有亲长也,而火妒妻子,薄若秋云”“急救人有君臣也,而烈焰刑法,缓民欲恶”等[1]3。也就是说,君臣父子、忠孝仁义是世道人心的根本,一旦陷溺,儒家就要勇敢地担当起拯救世道人心的重任。
颜钧高扬了心学的心之主旨地位,一再宣称“精神心造”[1]11,以其改造《大学》《中庸》思想后得出的大中学庸思想来默契心印。颜钧提出了所谓“心印”说,其曰:“心之精神是为圣,圣不可知之谓神,不知其然而然之谓莫”,此“即是夫子五十知天命以后翊运精神成片之心印”[1]13-14。换句话说,颜钧主张“中庸大学兮心印猷”[1]66。通过“心印”说,颜钧将心性本体指向大中学庸。颜钧高度重视儒家的经典《大学》《中庸》,他将大学中庸阐析为“从心孕乐,率性鼓跃,学大为橐,庸中为籥”[1]35,“心之乐,性之跃,学以橐,庸为籥,日用流行”[1]51,也就是说,心性的活泼和生发在于学大和庸中。颜钧将大学和中庸组合成不同的序列,从而形成了自己关于大中学庸的一套思想理论,所谓“大中学庸,学大庸中,中学大庸,庸中学大,互发交乘乎心性,吻合造化乎时育”[1]49。在大中学庸的思想体系中,颜钧认为人伦日用要遵循中的原则,中正是天下的大本达道,所谓“身之中,涵以心、意、知、格,为时日运用之妙。是妙运也,皆心之自能在中也”,“夫是中也,主乎大之生。未是大也,家乎中之仁。……达乎中正之道”[1]17。黄宣民先生认为颜钧的心性之学体现的是一种自然主义心性论,而其倡导“大中学庸”的大中学则旨在构建一种“易知易行的宇宙和人生哲学”[1]前言4。通过将心学与大中学的结合杂糅,颜钧奠定了其道德哲学的基础,而其忠孝思想也都源于这一理论基点。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儒家的人伦日用,颜钧也从心性论的角度进行了剖析和阐发。他将日用析为两截,在颜钧看来,“日”就是天地之阳,所谓“体曰阳精,运行为昼,亘古今而悬旋,为白日之明,曝丽天地,万象万形之生生化化也”;至于“用”,颜钧将天道应用于心性道德领域,所谓“夫用也,言在人身天性之运动也。是动,从心率性;是性,聪明灵觉,自不虑不学……动乎喜怒哀乐之中节也,节乎孝弟辞让为子臣弟友之人也,故曰日用”[1]14。实际上,颜钧是想通过对“日用”的字义解析,重构日为天道尚中本体、用为孝悌忠信等儒家伦理。归根结底,颜钧强调“大道正学,中天下而立,立己立人,达己达人”[1]16和“孝弟辞让为子臣弟友之人”,其核心意蕴就在于重申其所谓的大中学庸之儒学大道。一方面,诚如张锡勤先生所指出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体现的是孔子所谓的忠之精神[2]。另一方面,孝悌辞让无疑体现的是儒家的孝道观。基于此,颜钧所说的“大道正学”其根本就在于忠孝之道,由此颜钧将凸显大中学庸和乐学主旨的心性论作为其宣扬忠孝思想的理论基石。
二、忠君·忠恕:颜钧忠德观的核心内容
作为封建社会的儒者,颜钧对“众德之基”的忠德自然也是十分重视的。在他的劝化诗歌中,专门著有《劝忠歌》和《自励忠怀》等篇什,不遗余力地宣扬忠德观。在古代社会,忠并非仅含有下对上的忠君一义,还有体现平等主体之间的忠恕、忠信、忠义等涵义。颜钧对忠德的阐析也是多侧面、多层次的。
一方面,颜钧大力宣扬维护君尊臣卑的忠君道德。颜钧的忠君思想是建立在君主专制的不平等君臣关系基础上的。他继承了传统的君为元首、臣为股肱的观念,认为“天下之戴大君,犹四体之供元首也。元首统四体以成形,形生必气血以周运”[1]5。颜钧除了从统治结构、秩序层级上认同于君尊臣卑的关系,还从君臣之义的角度明确了臣子忠君的道德义务。在颜钧看来,所谓“君养主义”[1]52,说白了,就是指臣子是靠君主的俸禄来生存的道理。因此,在这种“君以禄养臣”的逻辑下,臣子忠君成为“君臣之义”的最本质要求。基于“君养主义”,颜钧认可“君父之义,万古振振”[1]52的道德合法性和天然合理性。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颜钧大力宣扬臣子忠君的道德自觉,指斥、批驳那些为臣不忠者。在《劝忠歌》中,颜钧指出,做臣子的如果“视君如路人,视民如草木,但知全身躯,岂解识心腹。嗜欲骥奔泉,贪贿犬获肉。上不畏天宪,下不恤冤狱。苟便一己私,不顾一路哭”,则这种贪贿谀佞之徒,无疑是“尸素甘碌碌”的“欺罔”不忠之臣。他还列举了考父、晏婴、周公、夷齐、诸葛亮、胡铨、文天祥等历代忠臣的事迹,来弘扬忠君道德。颜钧鼓励臣子在危难时机要为君父和国家尽忠,所谓“古今忠与孝,开卷即在目。脱有不幸时,焉敢顾荣辱。挺身冒锋刃,安得恋罗縠”。反之,一旦忠节有失则魂神不安,所谓“一时节不全,千载魂亦忸”。而且他认为,不忠不仅会造成臣子内心的不安和自责,还会遭受来自天道和国法的双重制裁和惩处,所谓“天网虽恢恢,难容不忠族。明则有王诛,幽则有鬼戮”。因此,颜钧苦口婆心地反复劝告做臣子的,“嗟嗟食禄者,圣化久沐浴。此身既委贽,此心宜洗渌。置民衽席间,勿陷于沟渎。致君尧舜上,勿志于斗斛”。颜钧严厉批评了那些“时乎不堪用,板荡竟谁嘱。止为妻子谋,忍将君父鬻”[1]57的不忠之臣。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颜钧一再告诫臣子要忠君,但他的忠君思想并没有局限在忠于君主个人上,而更多地体现在忠于社稷的爱民利民上。这一点明显可以从其《劝忠歌》所反复强调的忠勤爱民思想中看出。而且颜钧的忠君观念还含有一定的君仁臣忠之双向度意味。也就是说,颜钧并非一味地强调愚忠,而是将君仁臣忠落实在爱民利民的社稷大业上,所谓“君臣仁义民安堵”[1]69。
另一方面,颜钧还大力提倡体现平等主体间人际关系和谐的忠恕之道。忠恕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提出,是先秦儒家人际交往的重要准则。曾参在概括孔子“一贯之道”时,指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自己也认为忠恕与道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所谓“忠恕违道不远”(《礼记·中庸》)。按照宋儒对孔门忠恕之道的解析,一般而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说的是忠;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说的是恕。忠恕之道是儒家对待社会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它的核心涵义是要求人们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积极助人、利人,而不要损害他人利益。
有研究者认为,孔子的“忠恕之道”与《大学》“挈矩之道”和《中庸》“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密切相关。“《中庸》由忠恕而申论诚身、明善,是在‘忠’的基本义上向前拓展了一大步。儒家由此而开出明善、诚身以致忠的义理”,并进而得到结论:忠恕之道与“古代君臣关系中所认定的忠德,显然异趣”[3]。实际上,孔子的忠恕之道体现的就是与政治伦理之忠相区别的人际交往之忠,其核心是践行一个“仁”字。“‘忠恕’是孔子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而‘忠恕’的内容则是仁义”[4]。由此可见,忠与恕是用来实践儒家“仁”的道德理念的,其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忠体现的是从积极方面来正向践行仁德,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则是从消极方面来反向防范不仁倾向和苗头。忠与恕合成为对仁的践行,体现了儒家“推己及人”的仁学道德实践哲学精髓。
如前所述,颜钧非常重视《大学》《中庸》的思想,开显出大中学庸的思想理路,并且他还将其与儒家的仁结合起来,认为“人为天地心,心帝造化仁”[1]16。在《论大学中庸》中,颜钧指出《大学》和《中庸》的主旨在于“中正之道”,在于“中之仁”,其核心意蕴则表现为“立达己人”的忠恕之道[1]17。在颜钧的论述中,反复强调立己达人(有时表述为“立达己人”或“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忠恕之道。他倡扬“立达己人之学”[1]9,并将忠恕之道作为大丈夫安身立命的根本,所谓“是在为男,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极止位育,毕天地之干秩也”[1]10。因此,颜钧毕生都服膺孔子的忠恕之道,所谓“立己达人宗孔业”[1]69。
此外,除了作为忠德核心内容的忠君、忠恕,颜钧也对忠信、忠义、忠贞等忠德特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发。就忠信而言,颜钧强调践约守信的“纳牖之忠”[1]5和“孚乡信友”[1]7的诚信精神,以及“言必可行兮行必酬”[1]66的践行忠信。就忠贞而言,颜钧提倡“顶天立地丈夫身,不淫不屈不移真”[1]73的坚贞不屈。就忠义而言,颜钧非常赞赏“忠义之交”[1]52的忠义精神。
三、孝道至上:颜钧孝道观的基本精神
相较而言,颜钧对孝的宣扬要多于忠。这主要是因为忠在那个时代主要是指忠君,主体是官吏,而颜钧是致力于民间教化的,他更多的是面对普通民众。尽管普通民众也有忠君的义务,但毕竟没有通过食禄委贽形式而与君主结成一种政治上的责任和义务关系,因此在忠君问题上的义务不像官员那么明显和具体。面对生活在宗法社会组织中的广大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颜钧将教化民众的重点放在了宣扬孝悌辞让上。故而,相对于忠、仁、义、礼、智等诸德而言,颜钧对孝的阐析和宣扬最多。孝是颜钧著述中的高频词,其不仅散见于颜钧的各种文字中,而且他的《箴言六章》的首章就是《孝顺父母》。此外,颜钧在写作《劝忠歌》的同时,也创作了《劝孝歌》①。
作为耕读治家的颜氏家族,孝是有传统的。据颜钧自云,其“家事耕读,世传孝友”[1]11,其小就“惯习孝弟和顺”[1]23。颜钧甚至将孝道的作用神圣化和神秘化,如他结合自身经历,将自己得到阳明心学要旨之传归因于自己的孝道感动天地。所谓“铎(即颜钧,因避君讳改为铎)惟知善养寡慈,将顺得欢心。有此孝行感天,得兄钥(颜钧兄颜钥)笔传道祖阳明阐揭良知,引掖人心四语”[1]23。在这种神道设教下,颜钧极力高扬“孝感求仁”[1]11的神通交感,认为“仁义养心”“孝友律身”[1]1。只有将仁义深植于内心,将孝道落实到自己日常生活中,才能使人的内在心性始终保持中正与和乐,实现一种家庭和社会的和谐有序,所谓“入孝出弟兮,蒸和丽”[1]63。
相对于“君养主义”而言,颜钧主张“亲生主恩”[1]52。也就是说,孝是基于子女为父母所生这一基本人伦事实,故而其道德基旨在于“报恩”,在于子女报答父母生养之恩。基于此,在颜钧看来,所谓的孝就是一种报答亲恩的自然道理。在《劝孝歌》中,颜钧主要从母子关系来切入,首先描绘了母亲生养孩子的艰辛。在未生之前,“百骸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饮母之血,饥飧母之肉”。临生产时,“儿身将欲生,母身如在狱。父为母含悲,妻对夫啼哭。惟恐生产时,身为鬼眷属”。此后,颜钧细数了养儿之艰辛,所谓“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抚鞠。母卧湿簟席,儿睡干裀褥。儿眠正安稳,母不敢伸缩。全身在臭秽,不暇思沐浴。横簪与倒冠,形容不顾渌。动步忧坑井,举足畏沟渎。乳哺经三年,汗血及几斛”。等到孩子长大点,又不好管教,让父母操碎了心,所谓“辛苦千万端,儿至十五六。性气渐刚强,行止难拘束”。不仅“日暮不归家”而且一旦出门远行,则“母心千里逐”。及至为儿娶妻,则“看母面如土,观妻颜如玉”,“母若责一言,含嗔怒双目”。反之,“妻若骂百句,陪笑不为辱”。而一旦父母老病则更为凄凉。“父母或鳏寡,长夜守孤独。健则与一饭,病则与一粥。袄裤甚单寒,衾枕不温燠。弃置在空房,犹如客寄宿”。等到父母一死,守孝期满,则“兄弟分财禄,不念二亲恩”。颜钧举了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的故事,说明孝亲报恩乃自然天理。他还劝告人们要多多学习古代孝子王祥、孟宗、郭巨、董黯等尽孝的古风美俗,反复规劝人们“勿以不孝头,枉戴人间屋。勿以不孝身,枉着人衣服。勿以不孝口,枉食人五谷”。最后,就像《劝忠歌》一样,颜钧在《劝孝歌》中也用神道设教的方式,来恫吓规劝人们要坚守孝道,所谓“天地虽广大,弗容忤逆族。早早悔前非,莫待天诛戮”[1]58。
在《箴言六章》的首章中,颜钧在点明“天地生民,人各有身。身从何来,父母精神”的道理后,再次重申孝顺父母乃为人之根本的主旨。从内容上看,该章主要仍是重复《劝孝歌》中所述及的生儿、养儿、教儿、成家的辛劳,指出“人有此身,谁不赖亲”“娶妻生子,何忍忘亲”?及至“父母衰老,舍儿谁亲?儿不孝顺,亲靠谁人”?与《劝孝歌》不同的是,在《箴言六章》之《孝顺父母》章中,颜钧不仅宣扬孝顺乃“报德报恩”的行为,而且还以“我若不孝,子孙效行。阳受忤逆,阴受零丁”的因果报应,来说明“我逆亲心,天逆我心”的道理。基于“孝顺父母,圣谕化民”的教化功能,颜钧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加之以人们所敬畏的鬼神思维,对孝道进行了更加深入地宣讲和普及,所谓“孝顺父母好到老,孝顺父母神鬼保。孝顺父母寿命长,孝顺父母穷也好”,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孝顺父母福禄加”[1]39的美好愿景。
四、会讲乐学:颜钧忠孝思想的民间教化
明代中期,自阳明开始,大兴讲学之风,儒家士人将会讲(亦称讲会)作为宣扬儒家伦理教化、参与社会治理的要津。阳明在世时,会讲之风已经在各地兴起。阳明死后,心学后人更是大力开展会讲,以阐扬阳明之学,立教化民众之功。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在会讲方面与其他阳明后学有所不同,其他学派的讲会对象多为地方生员,而泰州学派则表现出浓厚的“庶民性”特点。不仅会讲的对象多为下层民众,而且王艮弟子中也有很多平民[5]。这些平民出身的儒者担纲起民间教化的重任。颜钧就是泰州学派民间教化的佼佼者。
根据对颜钧生平经历的考索,颜钧早年在家乡就曾“为族党讲说孝弟,使人人感发”,而且他还在“里中立萃和会,雍然跻于仁让焉”。及至游学京师,访学名师后,更是“会讲豫章同仁祠,畅发学庸旨”,收到“士类景从”的效果[1]85。应该说,颜钧的民间讲学以及教化方式和效果都是非常成功的,这也被他的后学罗汝芳、何心隐所秉承。那么,颜钧是如何看待会讲的,其会讲核心与其忠孝思想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颜钧儒学核心在于一个心字,无论是他的《急救心火榜文》,还是会讲教化,其主旨都在于养心成人。所谓“参赞者知贵之所在,而立学以养心,立教以养人,人而囿于教,心闲乎学,斯得所贵”[1]1。因此,在颜钧看来,阐扬道德心性是会讲立学的根本,所谓“圣人因心以立学,因学而成会。会惟成学,学必立会”[1]30。“是故六道者,人为本,心为脉,志为根干,学为培植,德为枝叶,教为果实,成熟可用焉。”[1]32也就说,世间万物以人为贵,而人又是以心为脉。如果要培植心脉,则必须通过学,从而才能长出道德的枝叶,结出教化的果实。这个过程就是圣人所宣扬的人伦日用。基于这一理论逻辑,每逢会讲,颜钧则大力阐发其心学主旨和乐学精神,宣扬大中学庸的大中学,将心学与大中学庸打成一片,浑然一体,以陶冶人的性情,激发人的良知和道德心性。
关于会讲的核心内容,颜钧基于对象为底层民众这一现实,虽然也强调忠德,但更多的则是强调孝道。就忠德而言,颜钧虽然也强调忠君道德,但面对普罗大众,他强调得更多的是忠信、忠恕等人际交往之忠。如颜钧强调“孝弟忠信兮,住世耋前”[1]63,高扬“孝弟辞让兮臣友俦”[1]66的理念,希冀实现“亲亲长长兮,天下归”[1]65的理想世界。他在早年立“萃和之会”时就强调会讲的核心内容是:“讲作人先要孝弟,讲起俗急修诱善,急回良心,如童时系念父母,常得欢心,率合家中,外移耽好妻子之蒸蒸,奉养父母之老年,勤勤恳恳,不厌不倦。”[1]24在颜钧看来,通过会讲,最终收到了劝励忠孝、和睦乡里的教化效果,即“如此日新又新,如此五日十日,果见人人亲悦,家家协和”[1]24。如果把会讲作为一个道坛来看,则乡里宗族之间实现孝悌辞让和重义轻利,无疑是他立坛开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谓“孝弟谦和,修斩义利,此为道坛之德”[1]31。
总的看,颜钧道德教化的最高理想是达致一个“天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友朋交丽乎君仁臣敬”的“德馨道馥”[1]60之理想社会。用颜钧的话说,就是“仁义礼智根心坐,睟面盎背阳春和。举手揖让唐虞事,百战不用汤武戈”[1]61。也即“道在事亲与守身,躬行二者得吾真”[1]74。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颜钧继承了王艮的“人人君子,比屋而封”的“王道”政治理想,旨在构建一个不用刑罚而专用教化的“愚夫愚妇皆知所以为学”的“老安少怀”之理想社会[1]前言5。作为一位驰名儒学道统史上的著名“儒侠”和“布衣儒者”,颜钧以一个平民儒者的担当精神,以“负荷纲常只此身,险夷随寓乐天真”[1]73为己任,通过寓教于乐、施教于民的民间教化方式,践行着一个儒者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
综上所述,颜钧的忠孝思想通过会讲和诗歌、文章等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收到了良好的教化效果。据说他的教化影响力之大,乃至于听讲人动辄数千。但客观地说,颜钧的忠孝思想在理论贡献上要远逊色于其教化实践。除了在心性之学和大中学庸的大中学方面为其忠孝思想提出了有别于其他思想家的理论基础外,颜钧的忠孝思想无论是内涵的深度还是外延的广度上都没有超越前代学者,甚至远逊于很多同时代人。其忠德仍是重复传统的忠君、忠恕、忠信等道德精神,而其孝道思想也同样没有超越传统的报恩观念,其主要落脚点还在于养亲层面。颜钧还喜欢用神道设教的形式,来强化忠孝教化的效果。应该说,从理论上看,颜钧的忠孝思想理论是浅显的。以忠德而论,看不出颜钧对争臣谏诤精神的高扬,也没有详细展开阐述忠君、忠恕、忠信等概念的区别和关联。以孝道而论,颜钧不但没有超越先秦儒家的孝道观,甚至连先秦儒家的继承父志、匡父争子等合理内核也略而不论。从忠孝关系看,颜钧也没有系统分析忠与孝之间的关联,对忠孝两难境地更是没有触及。因此,从理论上讲,颜钧的忠孝思想是浅显的。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并非是颜钧缺乏理论建构和分析能力,而主要是由于其学术风格所致。颜钧作为“布衣理学”“平民儒者”,其毕生致力于民间讲学,致力于向下层民众宣讲儒家的人伦日用、道德精神。鉴于他宣讲的对象多为普通大众,颜钧更多地是用浅显明白的语言来阐释儒家义理,甚至用通俗易懂、直白朴质的诗歌谣谚来劝励忠孝。这就决定了颜钧在忠孝思想的理论建构和挖掘方面用力不多,而对如何宣讲、如何达到人人为善、个个君子的方式,反而用力尤勤。因此,我们今天在研究颜钧忠孝思想特别是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时,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以“同情的理解”态度,科学评价颜钧忠孝思想的理论不足和实践价值,既不刻意拔高,也不一味贬低,而是要还原到明代中后期的时代背景和泰州学派的讲学生活场景中,客观评价颜钧乃至整个泰州学派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注 释:
①尹继美在《颜山农先生遗集凡例》中曾提到“他书载《劝孝歌》为唐人所作,今并存疑”(见《颜钧集》第95页)。对于《劝孝歌》的作者问题,笔者采黄宣民先生的观点,将之归为颜钧名下。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