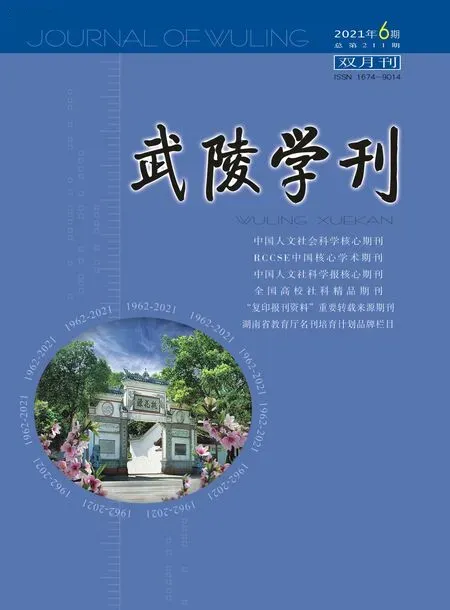学术破局与实践拥趸:泰州学派村治伦理的二元进路
郑文宝
(南京工程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7)
泰州学派是一个特殊性的存在,这从著名学人的著述中可管窥一斑: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对其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介绍,并给予了“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1]703的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却以极轻的笔墨一带而过,而且不置可否。这其中一定有着客观缘由,但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泰州学派以“平民、异端、禅学”的学术特色标显了自己的与众不同。泰州学派不但在伦理“思想”上以“平民、异端、禅学”独树一帜,在伦理“生活”中更是积极地投身于乡村伦理实践,在化风成俗、乡约濡化等乡村治理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树立了传统道德文化的践行典范,为中国传统伦理生活史涂抹了浓重的一笔。
一、泰州学派布衣儒化的学理缘起
有别于西方圣贤的理性思辨,儒家伦理一直以生活智慧、日常思考为核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思辨学说,但是历史上儒家学说一度很难真正进入大众的世俗生活,却是个不争的事实。精英定位以及教育文本化致使宋前的儒家学说多停留在贵族和知识分子层面,及宋虽然有平民贵族崛起,但是理学超经验性质的知识化体系,又将儒学推送至极端律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楼阁中,儒学虽一直致力于生活指导却从未真正地与基层社会良好结合。直到明代,儒学才真正意义上地融入到百姓的世俗生活之中,而泰州学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明显体现了儒学的这种道德文化取向。
儒学的传播和发展一直是依赖于国家体制的,即便是儒学伦理式微的魏晋隋唐时期,虽然佛道盛行,但是政治伦理仍然以儒学为主。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儒学的兴盛与发展都没有离开过对政治的体制性依赖。这种体制性依赖导致精英阶层的儒学观念与世俗层面的儒学需求出现了差异,朱熹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今人为经义者,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2],所以才有了朱熹的各种“集注”“集传”,也才有了朱熹对传统儒学的反思与批判,发展出了以理为核心的更为成熟的新儒学。但是朱熹并没有意识到,过往儒学乱象的本质性原因之一是体制依赖,所以程朱理学一直游离在政治意识形态边缘,没有从体制外寻求儒学发展的机会,以至于到了明代理学最终与科举制度结合,明初便明确规定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3]。至此,程朱理学开始正式借助政治体制的优势来指导、规范人们的伦常生活。但是,在程朱理学借助体制优势逐渐势盛的同时,它在体制束缚之下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的空间也越来越小,程朱理学本有的“内圣外王”“民胞物与”等思想也逐渐被士人冷落,它具有的慰藉心灵的良方灵剂功能逐渐丧失,成为人们谋取功名的手段和工具。这样,儒学发展虽然再次迎来了辉煌,但是人们生活中的世俗化伦理需求却依然无法从程朱理学这里得到满足,这就为阳明学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空间和舞台。
阳明学不同于程朱理学对体制的依赖,是以盛于民间著称的。经典作家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阳明学之所以能够在民间大行其道、普遍传播,说明其“心学”内容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也说明了程朱体制儒学的现实缺位。王阳明被尊为明300年间最为灿烂的思想者,其所创的心学一反当时程朱理学体制式的繁琐、僵化、支离,体现出真切、简易、直接的特色。即,在王阳明庞大又精致的心学体系中,有着十分丰富的儒学世俗化思想:认为“四民异业而同道”[5]941,给予工人、商人等民众以充分的平等地位;认为“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5]28,给予平民以成为圣人的希望;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5]42,给予平民世俗修炼的可能性……特别是《传习录》中记载一官员听王阳明讲学后,抱怨公事繁忙无暇格物致知时,王阳明着重强调道:“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5]95事上磨炼的简易修养工夫,体现出极强的生活实践特色,这对于跟随王阳明学习的王艮、王襞父子影响非常大。换言之,王艮之所以强调“百姓日用即道”[1]710,一是因为程朱理学体制化后离开了百姓日常生活变成了教条的文本,二是源于商品经济发展和市民阶层壮大后迫切伦理需求下的阳明学的出场。前者为儒学民间转向提供了可能和契机,后者为儒学世俗化的实现提供了现实条件和理论基石。虽然“阳明先生之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1]703,但是泰州学派也正是在阳明学派的这种学术创新背景之下才可能出现。实际上王艮的泰州学派是发轫、起始于阳明学的,王艮的教学对象多为目不识丁的农夫、陶匠、盐丁等,实际上就是对王阳明“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5]49观点的践行,只不过王艮单一地继承了王阳明的平民化儒学路向,并将之无限放大且践行,将儒学彻底引入了世俗化境界。
概言之,儒学摆脱体制依附世俗化是一种历史必然,同时也是儒学进行自我救赎、自我教化的过程,这个自我救赎、自我教化的世俗化起点在程朱理学世俗化的体制遗珠、阳明之学世俗化的开疆拓土,王艮创立的布衣儒者——泰州学派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对于泰州学派而言,这一学术背景为其产生既提供了必然性又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说此时产生泰州学派完全具备了充分且必要条件。
二、泰州学派村治伦理的学术表达
前文有述,儒学离开体制走近平民在王阳明处便已显现。但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只是“促使”儒学“平民化”,并没有“促成”儒学的“世俗化”,不然王阳明也不会震怒于王艮入京沿途“入山林、过市井”的讲学事件。进而言之,王艮思想来源于王阳明的儒学平民化,但是王艮比王阳明更为彻底,他彻底地将儒学平民化推进到世俗化的程度。泰州后学常出现惊世骇俗的“非名教之所能羁络”[1]703之人,也是继承了王艮这一叛逆的学术习性,而且泰州学派的这一世俗化的理论倾向为该学派乡村治理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一生拒绝入仕为官,但是却致力于地方政治与公益活动的道德伦理实践,因此在当时就拥有了极高的社会威望。嘉靖二年(1522),淮扬出现天灾,王艮“贷栗赈济”于真州商人;是年秋天发生瘟疫之时,王艮又“日煮药引广以调济”[6]71。王艮此类善举赢得了地方官员和百姓的信任,官员和地方百姓遇到困难时都会就教于王艮,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安丰场草荡分配”化解案例。经过这一事件后,王艮被推送至著名乡贤的位置。在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中,社会现象总是受其背后存在着的思想动机支配和指引的,王艮的种种村治善举也有着深邃的思想动机,即在王艮的思想深处实质上有着系统化的村治理论思考,他的种种善行是其治世理想的表征和践行,不是沽名钓誉也不是他的自我炫耀。因此,若要深刻理解王艮村治行为必先熟悉王艮的村治理论主张。
王艮师从王阳明,阳明心学以良知之学为重,良知之学按王畿的说法,在阳明之后分化为六种:“归寂、修证、已发、现成、体用、终始”[7]。王艮是非常典型的“现成”派,认为良知是先验式的现成的。在阳明学关于良知的文字表述中,虽没有“现成”二字,但是却有着非常明确的“现成”思想表达:“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5]105王艮是带艺拜师于王阳明的,在拜师王阳明之前他其实已经是盐场兴办的社学中的佼佼者,耳闻目睹了作为贫民的盐民的一切日常生活,拜王阳明为师后参悟良知学,得出了“良知天性,往古来今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措之耳”[6]47的“良知现成”的结论,这无疑是一种先验式的唯心主义观点。但是王艮独特的成长经历使得他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形上本体问题并不感兴趣,强调良知来自“人伦日用之间举措”[6]47,而且认为良知不用人力安排、不用进行思索,“良知之体,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要之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6]11。良知在王艮这里具备了先验性更具备了普遍性,同时王艮用“人伦日用之间举措之耳”[6]47指出了良知工夫的当下性,强调良知是在当下的人伦日用之中形成的,黄宗羲将之概括为“百姓日用即道”[1]710。“日用即道”在本体上肯定了日常世俗生活的意义,更简化了求道的繁琐工夫,认为良知在日常生活中“随感而应”,能保持这种随感而应的良知本体不失,任何人都可以得道成圣。但是,本体论层面道存在于百姓日用中,现实层面百姓日用也处处体现着所谓的道,可是王艮清晰地明白百姓对道是知之甚少的,因为百姓不似圣人,大多没有接受过教育开化,所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6]10。换言之,因为百姓日用中处处存有道,所以在百姓日用中修炼良知才有可能。可是又因为“百姓不知”[6]10,所以在百姓日用中修炼良知才有必要。这样,王艮便将道德的超验性、绝对性和神圣性消除,由此将百姓日用提升到道德哲学的高度,并将百姓日用合理化为本体,把脱离体制依附的儒学彻底平民化到世俗的地步,把程朱理学中的儒学本体从形上的理返璞归真到世俗日用。
概言之,在泰州学派创立之初,创始人王艮虽从阳明学出发,但又不局限于阳明学,勾勒了一幅较为清晰的儒学世俗化图景,并在世俗儒学指导下进行了“贷粟赈济”“均分安丰草荡”等村治实践,从理论到实践为泰州学派奠定了村治基调。
三、泰州学派村治伦理的践行范式
泰州学派最为可贵的地方不在于其惊世骇俗的理论主张,而在于其货真价实的村治实践,在中国伦理学史上像泰州学派这样能真正深入最基层的百姓之间,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实践的学者、学派少之又少。由于王艮叛逆的学术习性,致使泰州诸学没有循规蹈矩,泰州诸学的村治路向各不相同,大体可分为“讲会治村”“宗族治村”“乡约治村”等几个范式。
(一)泰州学派的讲会治村
众所周知,传统社会中平民百姓接受教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尤其是对山野村夫而言,更是难上加难。事实上,山野村夫在传统社会是被教育系统忽视的一个群体,但是泰州学派却致力于山野村夫的启蒙教育,试图通过乡村启蒙教育实现“遵圣道天地弗违,致良知鬼神莫测”[6]71的目的。泰州学派就是通过乡村讲会来实现乡村启蒙教育的。
讲会顾名思义就是讲学的聚会,兴起于两宋理学家的讲学活动,但是宋代的讲学局限于知识分子之间的学问交流。虽然明中叶王阳明提倡“良知之教”,主张“有教无类”,但是王阳明的讲会对象还主要局限在士人层面。到了泰州学派时却完全向平民开放了,明代著名“异人”邓豁渠曾这样描绘泰州学派的讲学盛况:“是会也,四众俱集,虽衙门书手,街上卖钱、卖酒、脚子之徒,皆与席听讲。乡之耆旧,率子弟雅观云集”[8],“街上卖钱、卖酒、脚子之徒,皆与席听讲”足以说明泰州学派的讲会真正实现了“有教无类”,完全向平民百姓开放。泰州学派的这种平民讲会始自王艮,当年王艮在北上入京沿途宣讲师道,就是“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6]71。虽然王艮的讲学遭到了王阳明的阻止,被召回稽山,但是这次事件却奠定了泰州学派“入山林”“启愚蒙”的讲学宗旨和讲学路向。在王阳明去世之后,王艮便经营起自己最为重视的讲学事业,在家乡泰州面向社会所有阶层开门授徒,“入山林”“启愚蒙”的讲学宗旨和讲学路向就这样被宣传和推广下去,一直被泰州后学所传承。
在王艮的世界观中,讲学之事是所有事功中最为重要之事,他曾反复强调“经世之业,莫先于讲学以兴起人才”[6]18。这样,王艮所开创的泰州学派也一直以讲学之事为要,以至于王襞一生以讲学为主业,甚至在临终之时也不忘叮嘱门人“惟有讲学一事付托之”[9]211。王艮的另一弟子王栋不但坚持讲会,还强烈主张讲会必须“集布衣为会”,极力将讲会深入到一邑一乡以移风易俗,认为“苟得移风易俗,化及一邑一乡,虽成功不多,却原是圣贤经世家法,原是天地生物之心”[10],即在泰州学派的思想世界中,不存在着卑贱之身与尊贵之身的讲学之别,认为讲学“入山林”“启愚蒙”才是真正体现了“天地生物之心”,彰显了真正的“圣贤经世家法”。在“淮南三王”的教育理念支配下,泰州后学讲会活动都直接面向平民百姓。虽然颜钧讲会具有宗教色彩,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其讲会受众的广泛性;罗汝芳则更是延伸、拓展了泰州学派“入山林”“启愚蒙”讲会的形式,盛世鹤鸣的滕王阁、幽深道观灵济宫、家乡偏偶的乡会组织都有罗汝芳讲学的身影。泰州学派真正实现了讲会的通俗化、大众化。
概言之,泰州学派的讲会没有场所的限制,书院可讲、寺院可讲,甚至秋天的打谷场都可以讲;也没有僵化的形式限制,童子捧茶、穿衣吃饭都可以是讲学的素材;在讲学对象上也没有任何等级限制。泰州后学知名弟子朱恕原本是一樵夫、韩贞原本是一陶匠,泰州学派最大限度地突破了书院讲学的各种限制,突破了地缘与血缘社会关系的限制,形成了开放式的社会教化关系格局,对于“山林”百姓而言具有“启愚蒙”的教化意义,对于乡村道德个体的道德人格构建有着重要意义。
(二)泰州学派的宗族治村
钱穆先生针对中国之治曾强调道:“欲通中国之社会史,则必先究中国之宗法史。”[11]可见宗族制度、宗族现象在传统社会的重要作用。由于宗族的血缘限制,泰州学派的宗族建设只能在自己的宗族内部进行,但是仍然可以从淮南王氏宗族建设中管窥泰州学派的村治伦理路向。
泰州学派兴起于明中叶后期,千户万人义庄频现,王艮家族就是如此。王艮家族自姑苏迁至东台,发展到嘉靖元年(1522)已有160多年的历史,拥有了超千户的家族规模,是名副其实的大家族,但是这个大家族却一直是“灶籍”,苦于徭役以设灶煎盐为生。明中叶以后,江南一带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经济活动已经出现。王氏家族也有人从事自煎自卖私盐的活动,家族内部因此出现了贫富不均、莨莠不等的分化现象,宗族开始变得不再稳定。而此时的王氏家族却一直没有宗族祠堂,也没有宗会组织,宗族人口众多却如散沙游存。王艮之子王襞目睹此等现象,不禁疾呼:“夫一家之亲,散为群族,虽门户分裂,盖亦同根于祖宗一脉。而枝分者,故血气流贯痛痒相属,而君子有联宗统族之睦焉!”[9]235王襞遂将其父王艮的讲学之所改成祠堂,并捐己田为祭田,且于嘉靖三十年(1551)“立宗会于钦差巡监御史胡所建高士心斋父之祠”[9]235,促成了王氏宗族组织体系的健全。王襞热衷于宗族组织建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同族之人有着共同的祖先,所谓“同根于祖宗一脉”。建宗祠、立宗会可以使族群的情感回归、守望相助有一个良好的平台,利于族群一体、手足相亲。当然,这是所有族群进行宗族建设的共同缘由,并不是泰州学派的特殊性所在。泰州学派热衷于宗族建设的特殊原因,在于他们“良知天性,往古来今人人具足”[6]47的伦理认知。换言之,泰州学派认为人人是平等的,三代圣世是最为美好的社会,自己宗族的人自然不能贫富不等而门户分裂,所以面对宗族日益壮大却“气数不齐,才品稍异,富贫莫均,贤愚劣等”[9]235,泰州学人自然不能坐以待视,希望搭建一个组织平台来强化宗族内部联系,以促进宗族的团结与兴旺。
在泰州学派宗族建设的伦理实践中,除王襞之外,颜钧创办的“萃和会”、何心隐所立的“聚合堂”也是著名的宗族组织,只是聚合堂相对而言较萃和会更为规范,因此笔者仅以聚合堂为例进行阐述。何心隐传承的泰州学派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在讲学上何心隐虽然有着宗教色彩,但是在宗族建设上他却实实在在地体现着泰州学派的乡治进路。嘉靖三十二年(1553),何心隐创办了“聚合堂”,并撰写了宗族规约《聚合老老文》《聚合率养谕族俚语》等。何心隐创办聚合堂时,江西盛行“私馆”,很多族人之子接受教育是在私馆中完成的。“私馆之聚,私念之所由起”[12],族群社会因此出现分化过度、空间割裂现象:上族子弟因上族之馆而只知上族之亲、中族子弟因中族之馆而只知中族之亲、下族子弟因下族之馆而只知下族之亲。这无疑拆散了宗族,更为主要的是在宗族内部出现了不平等的差等区分,这是泰州学派思想主旨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何心隐创聚合堂,期待能以“本族乡学”替代各家私馆,而且聚合堂在学子身份、衣食等各方面对富人子弟都做了严格限制,充分体现了泰州学派平民、平等的教育理念。何心隐的聚合堂在践行泰州学派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思想的同时,更将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1]710的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聚合堂设“征粮理事会”,监督地主将税赋转嫁给平民,聚合堂内充分尊重宗族的老年人、照顾弱者,并通过日常税赋缴纳、养老敬老等百姓日用杂事彰显道义。
(三)泰州学派的乡约治村
乡约是传统社会进行乡村治理的有效手段和方法,在宋、明、清时期大为流行。在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颁布了指向乡村建设的“圣谕六言”,所以明代时的乡约多由民间“勉为善而耻为不善”[13]转向演绎圣谕的官方“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5]600之乡村治理。泰州学派一直致力于乡村的化风成俗,并在乡约工作方面结合自己学术思想特点演绎圣谕,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泰州学派风格。
在泰州学派以前,乡约多以蓝田《吕氏乡约》和阳明先生的《南赣乡约》最为著名,只是《吕氏乡约》是纯粹的民间乡约,而《南赣乡约》带有官方色彩。在明嘉靖(1522)之前,中国的所有乡约大多效仿《吕氏乡约》以村治实际为核心内容,而嘉靖之后大多以演绎圣谕为核心内容,乡约建设具有了当时的“核心价值”的意蕴。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乡约文本体现了规范化、体系化的特点,而广大村民由于没有太多的文化,甚至是目不识丁,因此这些形式上越来越趋于完美的乡约,实际效果却越来越差。换言之,过于正规化、官方化的乡约,在乡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效果不佳。泰州学派一直致力于百姓的世俗教化,崇尚“不学不虑之旨,转而标之曰‘自然’,曰‘学乐’,末流衍蔓,浸为小人之无忌惮”[1]12的理念,在乡约上也采取了“乐即学、学即乐”教化理念。因此王栋、颜钧等人用诗歌等形式来演绎圣谕,出现《乡约谕俗诗六首》《又乡约六歌》等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乡约规范。颜钧结合自己的风格,将圣谕内容融合进民间关于善恶因果的逻辑中进行讲解,虽然具有宗教或迷信色彩,但是由于根植于百姓心理习惯,道德教化效果反而非常显著。
泰州学派体系庞杂,泰州学人大都从实际出发,进行布衣儒化。王栋、颜钧都是平民①,与底层百姓接触最多,所以他们在乡约建设中,都采用了自己最擅长、也最能让百姓接受的方式。但是在泰州后学之中,有些人已不是平民百姓而是一方官吏,这些人则积极利用自己身份进行乡约建设,已有别于王栋、颜钧等人,其中以罗汝芳为典型代表。罗汝芳虽然官运多舛,但他在任期间积极推进乡约建设。他在云南的腾越州和江南的宁国府、里仁等地,大力推进乡约建设,曾规定“木铎老人每月六次……乡下各村,俱择宽广寺观为约所,设立圣谕牌案,令老人振铎宣读,以警众听”[14],因此罗汝芳被称为泰州学人中最热衷乡约践履的人。为保证乡约的受众面,罗汝芳还将保甲制度融入乡约建设中,保证乡约的宣讲落实到人、到户,充分体现了泰州学派勤勉、务实的学派气象。
总而言之,泰州学派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是一个特殊性的存在,是儒学摆脱体制依附进行自我救赎的一次重要尝试,它不但在伦理思想史上独树一帜,更在伦理生活史上创造了辉煌——在中国伦理生活史上以学派的身份出现的伦理践行是极为罕见的②,泰州学派也因此成为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践行典范。
注 释:
①王栋近耳顺之年才做官,颜钧也一直以讲学为主。
②张锡勤、陈瑛、唐凯麟等先生开中国伦理生活史研究先河,分别出版了专门性的伦理生活史著述,从中可见以学派身份出现的伦理生活践行是极为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