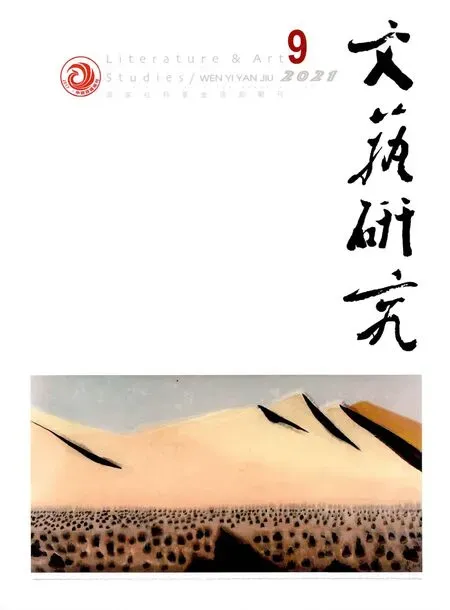汉乐府《薤露》本事及演变考论
冷卫国 董方伯
《薤露》是汉乐府名篇,历来不乏研究者。《乐府诗集》题解称:
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泣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谓之挽歌。”谯周《法训》曰:“挽歌者,汉高帝召田横,至尸乡自杀。从者不敢哭而不胜哀,故为挽歌以寄哀音。”《乐府解题》曰:“《左传》云:‘齐将与吴战于艾陵,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杜预云:‘送死。’《薤露》歌即丧歌,不自田横始也。”按蒿里,山名,在泰山南。魏武帝《薤露行》曰:“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曹植又作《惟汉行》。①
《薤露》的本事当是田横自杀、门人送葬。由于上引文献层次较为复杂,历来学者的相关探究有两种不同的追溯路径:一是根据《乐府诗集》题解,将《薤露》出现的时间追溯到《左传》“齐将与吴战于艾陵”一事②;二是根据宋玉《对楚王问》,将《薤露》出现的时间追溯到宋玉生活的时代③。这两种追溯方式都值得商榷。迄今为止,人们多将《薤露》置于《乐府诗集》“挽歌”类或“三曹”乐府(已经是拟作而非古辞)的框架下进行研究④,较为粗略。近年来兴起的现代民俗学田野调查的方法⑤,又未将考察成果与《薤露》古辞相结合。本文拟从《薤露》的古辞本事、雅化路径、民间传唱三个方面入手,考察《薤露》的源流,分析其音乐形式特点,探究古代社会各阶层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丰富对乐府诗歌的认识。
一、本事辨正:《薤露》题解的误读与正解
由于相关文献层次复杂,学界对《薤露》本事的看法歧出,甚至存在不少误读。那么,厘清文献层次,对确定《薤露》本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先对《薤露》本事出自《左传》说和出自宋玉《对楚王问》说加以辨析。
其一,《薤露》出自《左传》说。这一说法始于后人对《薤露》起源的误读。如果按照《乐府诗集》题解所引崔豹《古今注》的说法,这首古辞当出自田横门人无疑,但郭茂倩随后又引了《乐府解题》(一般认为此处的《乐府解题》,就是唐代吴兢撰写的《乐府古题要解》)的说法,认为“不自田横始”。若将《乐府解题》所引《左传》的《虞殡》和《薤露》混同为一,那么《乐府诗集》题解所引《薤露》本事“本出田横门人”与“不自田横始”无疑互相矛盾。《乐府古题要解》载:
旧曲本出于田横门人,歌以葬横……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亦呼为《挽柩歌》。《左氏春秋》:“齐将与吴战于艾陵,公孙夏使其徒歌《虞殡》。”杜预注:“送葬歌也。”即丧歌不自田横始矣。复有《泰山吟行》,亦言人死精魄归于泰山,《薤露》《蒿里》之类也。⑥
然而,通检《左传》全书,不见“薤露”二字。由此可证,《薤露》与《左传》绝不相涉。《乐府诗集》所引“齐将与吴战于艾陵,公孙夏使其徒歌《虞殡》”并非《左传》原文,而是对《左传·哀公十一年》如下内容的概括:“为郊战故,公会吴子伐齐。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军从王,胥门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展如将右军。齐国书将中军,高无丕将上军,宗楼将下军。陈僖子谓其弟书:‘尔死,我必得志。’宗子阳与闾丘明相厉也。桑掩胥御国子,公孙夏曰:‘二子必死。’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⑦杜预注:“《虞殡》,送葬歌曲,示必死。”⑧《乐府古题要解》所表达的意思为:《薤露》虽有丧歌之用,但并非丧歌之祖,丧歌(挽歌)如《虞殡》之类早已存在。由此可见,《乐府古题要解》称引《左传》,意在追溯丧歌的始源,强调其来有自,即最早的挽歌并非《薤露》,亦不是始于田横门人。
又《春秋左传正义》云:“贾逵云‘《虞殡》,遣殡歌诗’,杜云‘送葬歌曲’,并不解‘虞殡’之名。礼,启殡而葬,葬即下棺,反日中而虞。盖以启殡将虞之歌,谓之‘虞殡’。歌者,乐也。丧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盖挽引之人为歌声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旧说挽歌,汉初田横之臣为之。据此,挽歌之有久矣。”⑨根据《虞殡》“反日中而虞”的题名意义,可知《虞殡》《薤露》应是完全不同的两首曲子。唐代成书的《初学记》将“虞殡田歌”与“松云薤露”两条事类并列⑩,可见二者并非一事。至此可以断定,将《薤露》上溯到《左传》的时代,是对文献的误读。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厘清《薤露》与挽歌的关系。由于《乐府诗集》题解言及《薤露》又被称为“挽歌”,似乎混淆了概念,遂导致后世把《薤露》等同于挽歌的看法,这就把《薤露》可能的源头进一步泛化。其实,广义的挽歌应指一大类歌曲的总称,这已成为学界共识,“汉代挽歌歌辞在汉乐府中相和歌辞类目下尚保留一部分,具体曲目有《薤露》《蒿里》《梁父吟行》《东武吟行》等”⑪。因此,《薤露》《蒿里》和“挽歌”并非等同的概念。挽歌的概念有广、狭之分:广义的挽歌应指包括《薤露》《蒿里》等一批以挽棺时所唱的怀念死者、感叹世事的哀歌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歌曲;狭义的挽歌是指直接以“挽歌”为篇名的作品,《文选》《乐府诗集》等均有收录。《薤露》题解所谓“使挽柩者歌之,亦谓之挽歌”,实际是讲“挽歌”的词源问题。《礼记·曲礼上》:“适墓不登垄,助葬必执绋。”⑫送葬时帮助牵引棺材或灵车的动作就是“挽”,挽者所唱的送葬歌亦即“挽歌”。这当然是所有挽歌共同具有的原初意义,不唯《薤露》一曲。只是《薤露》在流传中似乎还有“挽歌”的别号,这在名称上造成一定的含混。因此,《薤露》的源头并不等于挽歌的源头。
其二,《薤露》出自宋玉《对楚王问》说。宋玉《对楚王问》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有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⑬这则材料易被认为是《薤露》早于田横一事存在的证据。这个说法如若成立,必须考虑到《蒿里》的情况。为何在宋玉的叙述中始终没有出现《蒿里》?换言之,《薤露》怎么会与之分离?关于这一点,支持者多受闻一多《乐府诗笺》启发:“《汉书·韩延寿传》:‘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注引张晏曰:‘下里,(伪)(物),地下蒿里伪物也。’《酷吏田延年传》:‘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注引孟康曰:‘死者归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案《对楚王问》又曰:‘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下里当即《蒿里》之曲。”⑭他们试图证明《下里》就是《蒿里》,从而推论出此《薤露》便是彼《薤露》。对此,笔者以为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方面,《下里》就是《蒿里》的说法并非确凿之论。吴阌平《下里正诂》一文就提出反对意见。第一,宋玉《对楚王问》这段文字存在异文,如西汉刘向《新序·杂事》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陵》《采薇》,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而已。”⑮无论异文如何变化,《下里》和《巴人》都是确定并联系在一起的。第二,从语音上说,乐府古辞“少与战国楚骚巴调方枘圆凿,钅且铻难符”⑯。
另一方面,按照《乐府古题要解》《乐府诗集》之记载,如果把李延年“分为二曲”的语义理解为将一曲分开,那么《薤露》《蒿里》本为一曲,至汉武帝时期才呈现新的形式,在此之前必以一整首曲子的形式流传,只有一个篇目的名字。如果宋玉《对楚王问》中所记录的《下里》确为《蒿里》、楚《薤露》乃是乐府古辞《薤露》,那么意味着《薤露》《蒿里》最晚在战国时代就已分为两曲,这与汉代李延年将其分为二曲的记载是矛盾的。
笔者认为,两首《薤露》可能是同题异曲的作品,并无密切联系。仅仅根据歌曲名称一致,就认定两首《薤露》是同一首曲子,未免过于武断。“薤露”一词,本来就容易引导人们联想到逝去、死亡的话题。《正字通》卷九:“古人言薤露,以其光滑,露易坠也。”⑰薤是原产于我国的多年生草本植物,适应性较强,多地可见。“薤露”一词自魏晋以后,成为与“死亡”“挽歌”“墓地”相关的意象。齐地田横门人完全可能仅仅取“薤露”一词的普遍意义,或自己创制曲词,或借鉴当时流传的民俗歌曲进行二次创作。他们创作的《薤露》与宋玉《对楚王问》中所言的《薤露》,未必是同一作品。
总之,将《薤露》出现的时间追溯到《左传》或宋玉《对楚王问》的时代,都不妥当。而将汉初田横门人视为《薤露》一诗的作者,将田横自杀、门人送葬视为此曲的本事,则比较合理。元稹《故中书令赠太尉沂国公墓志铭》云:“送横之客歌《薤露》,于嗟沂公今已乎。”⑱张岱《夜航船》更是直称:“田横从者始为《薤露》《蒿里》歌。”⑲一个“始”字,表明张岱对田横门人原创《薤露》一曲的肯定。
二、演变考述:《薤露》的异代雅化路径
《薤露》自汉初产生以后,在后世不断演变。概言之,可分为两个宏观的方向:一是进入宫廷音乐和文人拟作的雅化路径,二是在民间传唱不衰的俗化过程。就第一个方向而言,音乐雅化表征了《薤露》音乐地位的升沉,甚至从侧面反映出汉唐以来审美风尚的变迁;文人拟作则体现了《薤露》从作为哀乐的挽歌到进入文人创作视野的发展轨迹。
其一,《薤露》在音乐方面存在由俗至雅的宫廷接受历程。《薤露》最初为俗乐,属于《乐府诗集》引《晋书》所言“凡乐章古辞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⑳之类。这些俗乐是被统治者收集而来的,在汉代由少府所掌,与雅乐相对,其作用是观地方风俗、察政治得失,如《汉书·艺文志》所言:“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㉑
《薤露》雅化的第一个节点是汉武帝时期的李延年。“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㉒汉初田横门人所作的《薤露》古辞较为质朴,在音乐编排上也应比较简单,本是一种代替哭嚎、寄托哀思的手段。李延年作为宫廷乐师,对民间音乐予以一定的加工,亦属情理之中。自此,《薤露》《蒿里》为上层社会所接纳,用于送葬之时,并赋予一定的等级属性。这是《薤露》被宫廷进一步接受、使用的基础。
《薤露》雅化的第二个节点是魏晋时期的曹氏三祖。汉末战乱导致汉乐零落,而曹氏三祖对汉乐府的整理和保存功不可没。包括《薤露》在内的相和乐,在汉代已渐被于弦管,“魏晋之世,相承用之”,“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㉓。曹操和曹植还分别拟作《薤露》,配魏乐演奏,郭茂倩因此转引王僧虔的话评价道:“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㉔说明魏时的宫廷已广泛使用《薤露》。
《薤露》雅化的第三个节点是晋以后的清商乐。西晋荀勖利用相和旧曲,积极建构清商乐:“荀勖又采旧辞施用于世,谓之清商三调歌诗,即沈约所谓‘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㉕南北朝时期的情况是:“承嘉之乱,五都沦覆,中朝旧音,散落江左。后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清商乐,相和诸曲,亦皆在焉。所谓清商正声,相和五调伎也。”㉖简言之,清商乐在南北朝时期代表着华夏正声,是有源可溯的一切中原音乐的总称。虽然理论上的华夏正声应当追溯到九代之遗声,但实际上最早能追溯到的还是汉魏旧曲,故晋人承汉魏旧曲以实现恢复华夏正声之目的。《薤露》等相和曲在汉初产生时,仅仅是寻常巷陌讴歌的作品,然而在南北朝乃至以后的朝代,却被视为古老的雅正之乐。至此,《薤露》借由清商乐的建构,完成了在后世宫廷中的雅化过程。
随着《薤露》由俗乐变为雅乐的过程,宫廷、士人中渐渐产生一种倾向,即利用《薤露》进行娱乐、表演。《后汉书·周举传》记载了东汉外戚大臣梁商的一次宴会:“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举时称疾不往。商与亲匿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太仆张种时亦在焉,会还,以事告举。举叹曰:‘此所谓哀乐失时,非其所也。殃将及乎!’”㉗在宴会倡乐之后演唱《薤露》,显然是一种娱乐行为。《薤露》虽是丧葬所用歌曲,但也可在平时演唱,主要用来抒发歌者的哀伤。唐代《李娃传》中有一段两家丧器店铺互相比试争胜的情节,其中一家公然搭台令男主人公唱《薤露》以较高下,“曲度未终,闻者歔欷掩泣”㉘。可见,用《薤露》进行表演的现象是真实存在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汉唐以来以悲为美的时代风尚。
其二,《薤露》在文本方面逐渐文人化、个人化。《薤露》的文人拟作可粗略分为两个时期:唐前的定型期和唐后的式微期。定型期的作品以《乐府诗集》所录《薤露》拟作五篇为代表,它们遵循汉魏以来的音乐体制,不过抒发的感情越来越具体化、个人化。
《薤露》最早的文人拟作当数曹操“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㉙一篇,又称《惟汉行》。此诗直写时事,抒发己怀,回溯汉朝自建国到当世已历二十二世,现在所重任的人却是等闲之辈;诗人讽刺外戚何进心量狭窄、犹豫不决而导致国破家亡,控诉董卓杀害君主、焚烧东京洛阳而使百姓流离失所的种种罪行;最后写自己瞻望洛阳城内的惨状,就像当年微子面对殷墟那样悲伤不已。曹操大力拟作乐府,开创了文人拟乐府诗歌创作的全盛局面。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称:“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三祖陈王,所作皆多至数十篇,文人乐府,斯为极盛。”㉚具体来说,曹操打破了原有拟乐府的写作方式,直接叙写现世生活题材。较之《薤露》乐府古辞,他有意将文辞修饰齐整,并且一改古辞中较为宽泛的抒情,以旧臣身份抒发黍离之悲,使情感更加具体化。
曹植绍承乃父,拟《薤露》为“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㉛一篇。这首拟作已然是文人个体抒情言志的作品,开篇便是“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㉜这样关于人生的感慨。此诗作于魏明帝时期,时值曹植晚年,参与政治、建功立业对他来说已希望渺茫,可以视为曹植对自己人生所谱的一曲挽歌。
今存曹植的另一篇《薤露》拟作“太极定二仪,清浊始以形”一篇,题为“惟汉行”㉝,取自曹操拟《薤露》的诗句“惟汉二十二世”。此诗创作时间应早于上篇,抒发了曹植参与政治的热情。他怀念上古的英明君主,告诫当今的君主要实行仁德,尊重贤者。在曹植的两篇拟作中,都涉及到“怀”的意思,尚未完全脱离“薤露”古题之意,但个人化的倾向无疑更为显著,不仅用典等艺术手法的使用更加纯熟,而且抒写的都是诗人自身的境遇和心绪。
迨至晋朝,傅玄有拟作《惟汉行》叙述楚汉旧事:“危哉鸿门会,沛公几不还。”㉞此篇实际是以诗歌形式叙述鸿门宴故事,就内容而言,视为咏史诗亦无不可。诗歌先是交代历史背景,营造紧张的氛围,然后主体部分赞颂主人公樊哙,最终发表议论,认为英雄应不问出身,讽刺腐儒着实可笑。这首拟作已难以读出《薤露》的挽歌意味。
前凉张骏拟《薤露》为“在晋之二世,皇道昧不明”㉟一篇。在写法上,诗人毫不避讳地模仿了曹氏父子,甚至可以说就是以曹操《薤露行》为模板,且与曹植《惟汉行》同韵。诗歌回顾晋朝历史,揭示朝政之昏暗,叙述了西晋时期宫廷之变、藩王之乱、胡族入侵等历史事件,展示了西晋必然灭亡的历史轨迹,最后从个人视角抒发感慨。东晋十六国是一个连年战乱的时代,建安时期拟作的精神内核在张骏的诗作中得到继承。张骏和曹操的经历有相似之处,他对曹操拟作心有戚戚不足为奇。不过,两首诗的情感存在微妙差异:曹操终究还是贴合“薤露”题意,表达微子式的黍离之悲,尚未丢失挽歌的意蕴;张骏则直接痛斥晋朝,表达的主题是“义士扼素腕,感慨怀愤盈”,“誓心荡众狄,积诚彻昊灵”㊱,已毫无挽歌的意味,反而更见一种激荡的心怀。
总之,唐以前的《薤露》明显经历了一个从抒发普遍情感意义的挽歌,到曹操感发时事、哀叹战乱,再到曹植对人生志向的抒发与感慨,最后到张骏倾吐不平、愤懑之情的文人化、个人化的过程。其创作范式可以概括为“借题发挥”,即以曹操开创的五言乐府体制为基准,用于抒发文人的惋惜、哀伤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情感、思想。
进入唐以后,《薤露》的文人拟作逐渐式微,之所以缺乏名篇,是因为挽歌的创作范式发生了变化。元代吴莱《渊颖集》:“如古挽歌辞,《左氏传》所载歌虞殡者虽不可考,汉魏之间歌《薤露》《蒿里》,则犹古也。自唐至今之为挽歌者必以今体,五、七言四韵。”㊲唐以后的文人不再大力拟作《薤露》,即使有以“薤露”为题的零星作品,也不再遵循唐前的旧制,抒写较为随意,甚至能否被认定为拟作都成问题。如明代刘基《薤露歌》:“蜀琴且勿弹,齐竽且莫吹。四筵并寂听,听我薤露诗……”㊳此诗虽以“薤露”为题,却又以“薤露诗”“薤露歌”等字眼入诗,无法认定为《薤露》拟作。又如明末清初王夫之《管大兄弓伯挽歌二首》:“薤上露,光油油。日出曈曈,其光易收。乐日之匿得久留……”㊴这类作品有的保留了汉魏古辞的句式,主要是对巷陌歌谣意趣的模仿而非文人诗,说明至此阶段,文人拟作已经表现出式微的倾向。
三、遗存探究:《薤露》的当代传唱样貌
除雅化路径之外,《薤露》作为丧歌,在民间一直传唱不衰。唐代张籍《北邙行》云:“洛阳北门北邙道,丧车辚辚入秋草。车前齐唱《薤露歌》,高坟新起日峨峨。”㊵明代王维桢《思惠张翁挽诗序》曰:“以送之曰《薤露》者,言人命促迫也;曰《蒿里》者,言贤愚同一坏也。至今丧家传习之,号为挽歌,历千百祀未之有易也。”㊶清代《永绥厅志》称:“歌谣:农民每莳插收获之时,往往互相歌唱以为娱乐,亦有牧竖信口编成互相酬唱者,又凡遇有丧之家,虽素不相识,邀约多人在于丧次,击鼓唱歌,达旦不歇,曰唱孝歌,丧家仅以殽馔酬之。乡里愚民大抵如此,此亦田横资从歌《薤露》之遗风也。”㊷这些材料说明,《薤露》在民间传唱有序,甚至在今天仍有遗存。祝红梅、费庆华《古歌〈薤露〉的历史探秘》一文记录了楚地阳新(今属黄石市)山区一带的《薤露》歌——作为农事歌使用的《薤露珠》和作为丧歌使用的《薤上露》——的歌词和曲谱㊸。这显示民间传唱的《薤露》歌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传承力,堪称民间音乐文学中的“活化石”。
《薤露》歌在如今的楚地还有遗留,从文献记载看,明人陈钢与有功焉。《明史·循吏列传》载:“陈钢,字坚远,应天人。举成化元年乡试,授黔阳知县。楚俗,居丧好击鼓歌舞。钢教以歌古哀词,民俗渐变。”㊹《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二:“楚俗居丧击鼓夷歌,乃谕歌古哀词如《蒿里》《薤露》等歌,民知向风。”㊺陈钢此举促成了《薤露》歌在楚地民间的流传。
遗憾的是,现代民俗学研究者虽从民俗学和音乐学角度详实考察了《薤露》歌的当代遗存,但没有将今天仍在传唱的《薤露》歌同《乐府诗集》中收录的《薤露》古辞古曲相联系,忽略了《薤露》在民间传唱的历史演变轨迹。有鉴于此,笔者试析之如下。
其一,文本的改造与互动。今天仍作为丧歌使用的《薤上露》,其功能是缅怀死者而抚慰生者,使丧主获得安慰,驱走恐惧。这个功能与《乐府诗集》题解中的相关记录一致。今天作为丧歌使用的《薤上露》歌词,除却语气词,同乐府古辞差异很小。
《薤露》歌在如今的民间又被作为农事劳歌使用。从根本上讲,挽歌与劳动密不可分。“执绋”首先是一种艰苦的体力劳动。《礼记·杂记下》:“吊,非从主人也。四十者执綍。”郑玄注:“言吊者必助主人之事。从,犹随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壮时。”㊻挽柩需要年轻力壮的人参与。王莉《汉乐府挽歌歌辞考论》认为:“挽歌最初是挽柩人用以整齐步伐哼唱的简单曲调,后来配以歌词,形成固定的葬礼歌曲。”㊼也有学者从“挽”和“绋”的本义入手,认为劳歌是挽歌的最原始形态㊽。不论此说是否可靠,挽歌与劳动的关系不容忽视,且挽歌与劳歌互相转化,也是符合情理的。古辞《薤露》是否由最为原始的劳歌转化而来,已不得而知。但今之农事歌《薤露珠》应是由作为挽歌的古辞《薤露》转化而来。根据上文所述,田横门人应为《薤露》的首创者,后世所有以“薤上露,何易晞”为核心的表述,皆应出自他们创作的古辞《薤露》。
大概在民间从事不同种类的劳动,有不同的鼓点节奏。《薤露珠》采用的是“挖地鼓”,即播种前垦荒时所用的鼓点,其词为:
引:[客哟啊]
领:打起单鼓拜地祇,
合:薤上露,露见稀,
领:拜地堡,请地祇,
合:人生一去何时归?
领:薤上露,露见稀,
合:拜地堡,请地祇。
引:[客哟哎]
领:单鼓声声响地旁,
合:薤上露,露见阳,
领:雷公不打种田郎,
合:地神送福送吉祥,
领:薤上露,露见阳,
合:雷公不打种田郎……㊾
这首农事歌与乐府古辞《薤露》整体上非常相近,但又有一定的改动和增扩。第一,《薤露珠》省略了古辞第一个七字句“露晞明朝更复落”,删除了原本的隐喻和递进的艺术手法,只保留了最核心的诗意;第二,“拜地堡,请地祇”等添加的表述反映了民间信仰,后文“雷公不打种田郎,地神送福送吉祥”,也体现出明显的民间文学特点;第三,歌词多用俗字俗语,琅琅上口,便于劳动人民记忆和传唱。这样改造过的歌词,一方面适应了田间劳动的需要,以便劳动人民在农忙时用歌曲互相呼应;另一方面也抒发出劳动人民对辛苦劳作的叹息,以及对朝露易晞的人生境遇的唏嘘。这与挽歌所传达的哀伤精神内核相通,因此挽歌与劳歌可以互相转化。
《薤露》古辞经过民间传唱和改造之后,呈现出复杂的样貌。农事歌《薤露珠》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古代社会各阶层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及机制。古代社会各阶层文学之间并非毫无关联,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当影响力巨大的文学作品出现时(如田横自杀而门人作《薤露》),作品有可能被上层采集,走上由俗至雅的道路,也有可能在民间广泛流传,被人民大众有选择地吸收、改造和使用。上层社会也可通过自上而下的施压,对民间流行文学进行干预。不过,最终民间文学呈现的样貌,仍具有鲜明的地方生活特征。
其二,音乐的追溯与复原。《薤露》歌的歌词文本与乐府古辞相比,可谓变化甚微,这印证了上引“至今丧家传习之,号为挽歌,历千百祀未之有易也”的判断。据此可以推断,今天民间遗存的《薤露》歌在曲调上亦与古歌存在密切的继承关系。下面,笔者拟利用《古歌〈薤露〉的历史探秘》采录的两首《薤上露》和《薤露珠》之曲谱㊿,结合歌词分析其音乐文学特征。
今天作为丧歌使用的《薤露珠》,节拍为4/4拍,速度为每分钟72拍,属于行板,比较舒缓,用以充分地抒发情绪、寄托哀思、宽慰生人。《薤上露》和《薤露珠》两首曲子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前者与后者相似,但在节奏上稍慢一些,往往将多个音节转化为一个音节。全曲最高音出现在“薤上露”的“露”字、“露易稀”的“稀”字(作者采录时记作“稀”字)、“人生一去何时归”的“去”字。换言之,旋律正是围绕歌词部分起伏,在歌唱正文部分时达到情绪的顶峰,而在其他地方或升或降,咏叹多为“哎哎嘿哎嘿”,凄厉悠长,给人以凄婉悲痛的感觉。不过,曲调的旋律都控制在一个八度的范围之内,没有很大跳跃,由此也可窥见中国古人“哀而不伤”的音乐观。
今天作为农事歌使用的《薤露珠》,曲子总体上欢快洒脱、张弛有度。节拍为6/4拍,歌曲速度为每分钟104拍,接近“小快板”,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劳动人民如火如荼的劳作过程。鼓点的节奏是固定的,鼓者只需要重复相同的敲击动作,在“嘿吼嘿哟伙”号子的应和下,显示出强烈的力量感。从音乐形态的角度考量,乐曲的节拍变化较少,旋律较为简单质朴,便于人们接受和传唱。结合歌词不难发现,《薤露珠》整体上切分节奏稍少,在出现全曲最高音的句子上,达到整首曲子的高潮,而这也是歌词文本所强调的部分,即“拜地堡,请地祇”和“人生一去何时归”。对神灵的敬畏、对人生不知归向何处的迷惘,是整首曲子的核心思想。
总之,通过今天仍在演唱的《薤露》歌,我们尚可窥见《薤露》古曲的模糊样态。基于民间传唱的需求,《薤露》古曲的旋律不会过于复杂,但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作为丧歌的凄厉哀伤的情绪,这与其古辞抒写的情感是和谐一致的。
结 语
关于汉乐府名篇《薤露》之本事,历来说法不一,存在不少误解。这与《乐府诗集》题解所引文献的层次复杂有很大关系。经过层层剥笋式的梳理、考辨,笔者认为,《薤露》出自《左传》说和宋玉《对楚王问》说均不能成立;《薤露》的本事当是汉代初年田横自杀、门人送葬。《薤露》产生之后,沿着两个方向演变:一是进入宫廷音乐和文人拟作的雅化路径,二是依然在民间传唱的俗化过程。就雅化路径而言,《薤露》在音乐方面经过汉武帝时期的李延年、魏时期的曹氏三祖、西晋的荀勖等人的建构,逐渐向朝廷雅乐靠近;在文本方面经过曹操、曹植、傅玄、张骏的拟作,逐渐呈现文人化、个人化的特点,而唐以后的相关文人拟作逐步消歇,渐失古意。除雅化路径之外,《薤露》作为丧歌,在民间一直传唱不衰。在今天的楚地阳新山区一带,仍流传着作为农事歌使用的《薤露珠》和作为丧歌使用的《薤上露》。考察《薤露》本事和演变,有助于深化古代社会各阶层文学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从而丰富学界对乐府音乐、乐府文学的认识。
①⑳㉒㉓㉔㉕㉖㉙㉛㉜㉝㉞㉟㊱㊵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578页,第549页,第578页,第549页,第929页,第549页,第549页,第578页,第579页,第579页,第579页,第581页,第580页,第580页,第1922页。
② 参见巫东攀:《〈薤露〉考》,《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祝红梅、费庆华:《古歌〈薤露〉的历史探秘》,《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③ 闻一多《乐府诗笺》:“案《文选·宋玉对楚王问》曰:‘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薤露》之名首见于此。”(朱自清等编:《闻一多全集》第4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2页)
④ 参见顾农:《曹操〈薤露行〉〈蒿里行〉新诠》,《天津师大学报》1993年第5期;梁海燕:《〈乐府诗集·挽歌〉考论》,《国学学刊》2017年第2期。
⑤㊸㊾㊿ 祝红梅、费庆华:《古歌〈薤露〉的历史探秘》。
⑥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页。
⑦⑧⑨ 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黄侃经文句读:《春秋左传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7页,第1017页,第1017页。
⑩ 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63页。
⑪㊼ 王莉:《汉乐府挽歌歌辞考论》,《安徽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⑫㊻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04页,第3389页。
⑬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28页。
⑭ 朱自清等编:《闻一多全集》第4册,第113页。
⑮ 刘向撰,赵仲邑注:《新序详注》,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5页。
⑯ 吴阌平:《下里正诂》,《吉首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⑰ 张自烈:《正字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039页。
⑱ 冀勤点校:《元稹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66页。
⑲ 张岱撰,刘耀林校注:《夜航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页。
㉑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6页。
㉗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28页。
㉘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988页。
㉚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㊲ 吴莱:《渊颖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㊳ 林家骊点校:《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
㊴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25页。
㊶ 王维桢:《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二,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3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㊷ 杨翰主修:《(宣统)永绥厅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7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13页。
㊹ 《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10页。
㊺ 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二,《续修四库全书》第533册,第264页。
㊽ 杜瑞平:《挽歌考》,《中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