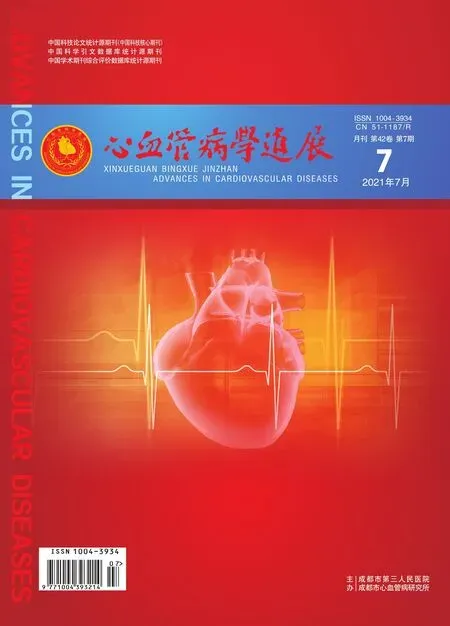体-肺动脉分流术在建立先天性心脏病动物模型中的应用进展
周玲梅 张文倩 张智伟
(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儿科 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080)
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是人类常见的先天性疾病类型,发生率为0.7%~0.8%,是婴儿和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1]。CHD可分为心脏和大血管的形态和功能异常,以外科或介入治疗纠正解剖畸形或改善症状,延缓继发性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PH)及心力衰竭的进展是治疗CHD的根本手段。因此,为研究CHD的病理生理,优化治疗手段,建立稳定可靠的动物模型就至关重要。体-肺动脉分流术(systemic pulmonary arterial shunt,SPAS)是指通过建立体循环动脉或静脉与肺动脉的连接,使血流改变走向,继而改变心脏压力及负荷。这种血流改变导致的肺循环血流及压力改变适合CHD所致的PH的模型制作。传统上,该技术多采用外科手术方法实现,创伤较大,动物模型围手术期护理难度大,死亡风险高。介入方式建立SPAS具有创伤小和恢复快等特点,但其稳定性仍待评估。随着技术发展、经验积累和研究需要,建立SPAS的方式不断得到改进,现就SPAS在多种CHD动物模型中的应用和发展进行综述。
1 SPAS的提出和发展
SPAS最早应用于紫绀型CHD的姑息治疗。1944年,Helen Taussig和Alfred Blalock为治疗法洛四联症,外科手术建立了锁骨下动脉(或无名动脉)与肺动脉的端侧吻合,即所谓的Blalock-Taussig分流术,该手术旨在通过增加肺循环血流,改善氧饱和度和促进肺动脉发育,为后续的根治手术创造条件。类似的Ports分流术(降主动脉和左肺动脉)、Waterson分流术(升主动脉和主肺动脉)、Cooley分流术(升主动脉和右肺动脉)等[2]基于不同血管间的吻合术式也随之出现,相继应用于各种复杂CHD的治疗。因经典Blalock-Taussig分流术游离了锁骨下动脉,部分患儿出现上肢缺血,而其他术式也因分流管道堵塞,分流量难以控制等不足,均已鲜有应用。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为改良Blalock-Taussig分流术,是利用聚四氟乙烯血管在锁骨下动脉和肺动脉之间建立分流,避免了锁骨下动脉的游离,较好地控制了肺血流量,降低了充血性心力衰竭和PH的风险[2]。该血管孔径较小,限制了组织内生,而纤维母细胞能将其固定到周围结构上,使血管稳定并降低堵塞风险。临床上,SPAS的建立也给难治性PH带来了福音。缺乏右向左分流通道的PH患者最终会发展至右心衰竭,预后明显比艾森曼格综合征更差,经SPAS产生的右向左的血流缓解了过高的肺循环压力,减轻了右心室后负荷,从而避免了右心衰竭。与房间隔造口术相比,动脉水平建立的分流容易控制分流量,避免了心房压力的骤升[3]。虽然该分流带来的低血氧饱和度会引起血细胞代偿性增多,易导致血液瘀滞和血栓栓塞,然而通过选取降主动脉与左肺动脉的吻合,能保证一侧肺血流量,在维持足够血氧饱和度的同时降低右心室后负荷,另一方面将血栓的危险局限于下半身,维持了大脑等重要器官的氧供[4]。
2 SPAS用于建立PH模型
传统的PH模型多以药物或低压低氧条件下诱发为主[5]。注射野百合碱(monocrotaline,MCT)的方法因其操作简便,诱导速度快,且多采用大鼠建模,被研究人员广泛接受,虽机制尚不明确,但MCT的内皮损伤作用能表现出明显的肺血管重塑和内膜增生,这有助于PH的血管重塑机制的研究[6]。然而MCT可同时引起心肌炎,累及心室,难以准确地反映严重PH相关的右心室肥大或右心衰竭[7]。此外,该模型以一个急性或亚急性病程诱发的PH可在多种药物实验中得到明显改善,具有可逆性,这也与临床上PH治疗效果大相径庭[6,8]。慢性缺氧条件下诱发的PH模型易预测且可重复性强,模型简单,常可见非肌性血管肌化增厚及右心室肥大等,但不同物种对慢性缺氧的反应各异,且病变可逆,很少发展至右心衰竭[7,9],这与临床上PH晚期血管的不可逆病变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的机制[6]。严格意义上,该模型更类似肺部疾病导致的PH,与直接影响肺循环的其他类型的PH不同。
上述两种模型都着眼于肺血管重塑的病理改变,但从病因上讲,都缺乏类似CHD-PH的左向右分流的血流动力学变化,且模型的肺血管病变无明显致死性[5],与临床上CHD-PH导致的右心衰竭和死亡结局相异[7],因此这两种模型都不适合用于CHD-PH的研究。SPAS在建立左向右分流的PH模型上已有多年的应用[10],Heath等[11]于1959年就在犬身上建立了Ports分流和Blalock-Taussig分流,20个月后活检观察到了肺血管增厚和阻塞等病变。Rendas等[12]通过对4~12周龄的猪进行主动脉与肺动脉干吻合,术后1~3个月发现4周龄猪PH更加严重,认为幼猪更适合用于模型。Black等[13]则在妊娠晚期的胎儿羔羊中建立了主-肺动脉分流,羔羊分娩后1个月表现出PH和肺血管重塑,他们认为在胎儿循环的肺血管压力下降之前建立分流能减轻对实验动物的影响,使模型能耐受血流变化,也更符合CHD的病程。为方便自身对照,Schnader等[14]和Bousamra等[15]分别选择了羊和猪作为模型,把左侧肺动脉分支和主动脉之间端端吻合,在单侧肺叶动脉中也发现了新生内膜病变和管腔狭窄。Rondelet等[16]还利用类似的模型产生持续过度循环,引起右心衰竭。除了研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机制,以上模型在药物实验中也多有应用,如吸入性NO、波生坦和前列环素等[17],可靠地证明了药物的有效性。
然而,分流并不等同于压力升高,升高的肺动脉压力可使肺血管收缩,加速肺血管重塑,发展出与PH患者相当的复杂的新生内膜病变。临床上房间隔缺损患者,肺血流量增加而压力不增加,小部分(10%~17%)会进展到PH。而来自高压腔(如左心室和主动脉)分流的CHD,肺循环远端血管的阻塞性病变出现较早,PH可能在2~3年内发展至晚期且不可逆转[5,8]。因此,主动脉-肺动脉之间分流的建立更适合用于PH模型。当分流口过大时实验动物常因急性右心衰竭而死亡[18],而分流量过小则无法诱发PH,因此分流口的大小设计也需考虑。Heath等[11]证实犬模型中3~5 mm大小的分流口是合适的,但仅依靠建立分流的动物模型是否有机会发展出晚期肺血管重塑和新生内膜病变仍未可知,且耗时耗力。
临床上,PH常隐匿性发病多年,症状出现时多已有复杂的病理改变,难以通过单因素诱导的模型重现。针对CHD-PH,分流模型所产生的肺血流变化不可或缺,晚期血管重塑病变的缺乏限制了其应用。因此,多种手段结合构建的模型可能更符合人的病理生理[6],有助于进一步研究PH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方案。Tanaka等[19]通过改变肺动脉的血流动力学状况,证实增加的肺血流会促进MCT对肺血管的影响,在分流动物模型中,MCT仅5周就在肺动脉中诱导出更严重的内膜变化。而缺乏内皮细胞损伤时,5周内仅肺血管压力升高不会引起肺血管重塑。van Albada等[20]也结合了主动脉-腔静脉分流和MCT诱导模型,4~5周后诱导出严重的右心衰竭。由于形成肺血管闭塞性病变及更为严重的PH和右心室肥大,且诱导出PH的时间更短,这类模型随后被用来研究病因和逆转病变的可能性[18,21]。
3 介入方法建立SPAS
目前肺动脉和体循环血管的吻合通常通过外科手术来完成,因需要胸骨切开和体外循环,术后恢复期长,护理和治疗更为困难,临床上常伴随着高死亡率,尤其是在高危患者中[22-23]。就长期结果而言,人工血管和吻合口易扭曲、狭窄和堵塞等,部分患者还需多次手术,无疑使手术的复杂程度和风险进一步上升[24]。相比之下,介入的并发症发生率更低,术后监护时间更短,具有创伤小和恢复快等特点。在心血管介入治疗中,在相邻的两条血管壁上穿孔并放置支架可创建各种血管间通道[25],常用于紫绀型CHD和难治性PH的姑息治疗[26]。作为体-肺循环连接的通道,肺动脉、主动脉以及上腔静脉在某些部位距离相近,因此使用穿隔针、硬导丝末端或射频能量结合支架建立通道,具有理论可行性[27]。这种安全有效的方法能减轻这类患者的手术负荷,使不能耐受外科手术的重症患儿有机会延长生存期,还具有能通过放置合适大小的支架调节流向和血流量的优势,且方便按需再次扩张[28]。
介入方式建立SPAS已在动物实验中证实了其可行性。Chigogidze等[29]在犬模型中经导管分别构建了腹主动脉与下腔静脉、升主动脉与肺动脉干、降主动脉与左肺动脉之间的吻合,通过磁铁拉近血管间距并穿刺植入内膜支架,提高穿刺的安全性。Levi等[30]首次报道了使用磁性导管介导的射频打孔技术在猪体内建立了降主动脉-左肺动脉分流的模型,提高了穿刺定位的准确性和稳定性。Sabi等则直接通过射频消融的方式在猪体内分别建立了主动脉-肺动脉干分流[31]和上腔静脉-右肺动脉分流[32]。Ratnayaka等[33]则在磁共振成像实时引导下穿刺小猪血管建立分流,认为比起X射线下磁铁引导,此方法无需在肺动脉放置目标导管。对于存在右心室出口闭塞或狭窄的患者,导管不易抵达肺动脉,因此磁共振成像引导下的穿刺更为安全,但目前大多器械并不适用于磁共振成像,相应设备仍需研发和普及。在临床应用上,Esch等[26]于2013年首次将介入建立分流的技术应用于难治性PH患者,使用穿刺针连接降主动脉和左肺动脉并置入支架,虽然有1例患者术中因纵膈出血而死亡,其余3例均远期预后良好。Sayadpour Zanjani[34]则认为射频能量能使组织凝固,减少出血,提高建立这种分流的安全性,但目前还无临床应用。
在模型成功建立的基础上,支架是影响模型稳定性的关键。临床上的支架主要为金属裸支架和药物涂层支架[35]。人工建立的新通道与原有血管不同,炎症损伤反应更为复杂,需额外评估支架置入后的反应[36]。Sabi等[31]所建的模型中,6个支架出现了4例自发性闭塞,这可能是射频能量的局部刺激导致的组织内生和血栓形成。这就需要支架有抗炎和抗血栓作用,理论上支架还应能紧附血管壁,保持稳定,易于人为再次扩张或堵闭,不影响到进一步的手术治疗[36]。针对以上要求,应用生物可降解材料(如聚左旋乳酸、镁合金和铁合金等)设计支架,可能是很好的解决方案[37]。其中金属可吸收支架能保证足够的支撑强度,且在降解过程中未发现对人体有毒性损害,不影响狭窄血管的自行重塑和发育,降解后不妨碍后续手术或其他操作治疗[38]。然而目前金属可吸收支架的降解速度和残留降解产物仍需进一步改进,有待更多实验进一步研究验证其远期安全性及有效性。
4 总结
综上所述,体循环和肺循环之间的交通已成为治疗某些复杂CHD和难治性PH的关键,SPAS技术也是模拟左向右分流型CHD及其所致PH的重要手段。当前以介入建立SPAS的技术仍在不断改进,使得构建动物模型的方式更加简便,实用性更强。而如何解决以介入建立SPAS的稳定性的问题,仍是需突破的技术难题。更多介入器械的研制和改良,可降解支架的改进以期得到更加稳定和可靠的动物模型,最终为临床患者带去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