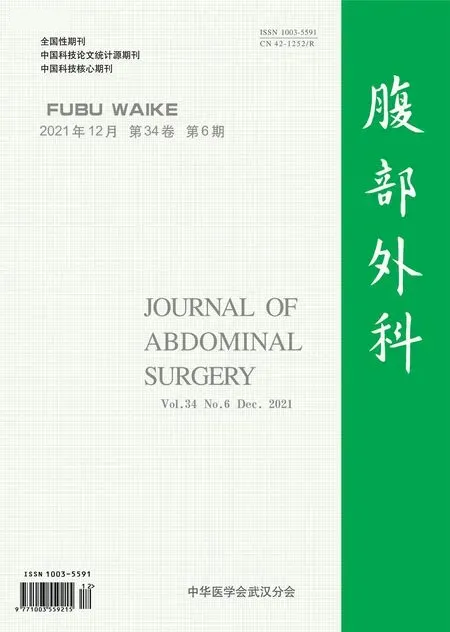肝门部胆管癌的诊断与手术进展
崔云甫,夏浩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肝胆胰外科,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
胆管癌是起源于胆管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根据肿瘤组织沿胆道树的不同分布,胆管癌可被分为肝内胆管癌、肝门部胆管癌和胆总管中下段癌[1]。肝门部胆管癌自胆囊管的开口处延伸至左、右肝管,毗邻肝门区的脉管网络与神经淋巴组织,解剖位置深在且复杂[2]。既往将肝门部胆管癌与胆总管下端癌统一归为肝外胆管癌,二者虽以胆囊管的插入点作为解剖界限,但发病机制与分子病理学特征方面的诸多异质性使得这一分类方式被逐渐摒弃。
肝门部胆管癌高度的分子异质性使其尚无标准的姑息治疗方案,根治性切除术是病人获得长期生存获益的唯一选择。肝门部胆管癌毗邻肝组织,且其纵向黏膜扩散、辐向透壁浸润的生长模式使得肝周血管极易受侵,局限性胆道切除似乎难以满足R0切除的手术目标,因此联合肝切除术成为中晚期肝门部胆管癌的外科治疗共识。然而,肝脏具体切除范围的选择以及权衡病人的生存获益与围手术期风险等问题构成了当今肝门部胆管癌外科治疗的主要矛盾。本文概述肝门部胆管癌的当今外科诊治进展,综合性分析各治疗方案的潜在裨益,以期为制定更合理的肝门部胆管癌手术决策提供参考。
一、肝门部胆管癌的术前诊断
高分辨率CT能够准确地评估肝门部胆管癌的局部扩散范围、血管侵犯与转移情况,还可以于扩张胆管内更好地预测肿瘤组织的胆管内扩散。磁共振胰胆管成像(MRCP)通过无创胆道显影在识别肝门部胆管癌的方面具备理想的敏感性和准确性(分别为92%和76%),但缺乏血管侵犯的评估信息[3-4]。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CT(PET-CT)在肝门部胆管癌分期中的作用很小,但可用于识别转移性淋巴结、远处转移或进行鉴别诊断。直接胆道造影[经内镜逆行胆胰管造影(ERCP)或经皮肝穿刺胆管造影(PTC)]可提供胆道树的解剖信息,常用于鉴别胆道狭窄的性质或行胆道引流,然而有创性检查势必会伴随感染、出血、胆瘘等风险。ERCP与PTC还可取材局部组织,但肿瘤的促纤维增生性质使得该方法虽特异性可达100%,敏感性却低(5%~40%)[5]。内镜超声(EUS)可提供肝门部胆管癌定位、淋巴结与肝血管侵犯的准确信息,结合细针穿刺取样适用于非侵入性技术无法确诊的病例,总体特异性为92%~100%[6-7]。然而穿刺针穿过十二指肠球和腹膜腔进行采样可增加肿瘤播散的风险,因此应仅用于无法行根治性手术的病人。随着内镜技术的不断革新,SpyGlass DS胆道镜直视化系统的问世还为肝门部胆管癌的术前鉴别诊断提供了胆道成像、直视下活检的技术选择。术者通过直视化技术对肿瘤的侵袭性边界的划定也有利于术前肿瘤分型与手术方案的制定[8]。光学干涉断层扫描(OCT)是目前分辨率最高的腔内影像学技术[9],相关应用现多局限于心内科的冠状动脉斑块评估。笔者提出并着手准备胆道肿瘤早期诊断方面的OCT临床研究,其精细的三维成像可洞悉胆道黏膜的病理性改变,将对胆道肿瘤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实验室检查中,癌胚抗原(CEA)和糖类抗原(CA)19-9等肿瘤标志物应作为常规评估指标,然而针对肝门部胆管癌而言缺乏足够特异性,其他原因所致的胆道梗阻亦可增加。值得注意的是,IgG4是IgG4相关性胆管病病人产生的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在诊断不明确的胆道狭窄病例中应评估血清IgG4水平,以与肝门部胆管癌相鉴别[10]。
二、肝门部胆管癌的分型与围手术期准备
(一)分型、改良分型与分期
Bismuth-Corlette分型[11]基于胆管树的解剖结构,描述了肝门部胆管癌对胆总管、左右肝管汇合部及双侧肝管的纵向侵袭程度,对肿瘤的R0切除与重建胆道连续性具有指导性意义。然而缺乏对肿瘤辐向血管侵犯、肝叶萎缩与转移等情况的评估也体现了该分型方式在肿瘤可切除性与病人预后评估方面的局限性。董家鸿等[12]在段肝管水平对Bismuth-Corlette分型予以补充优化,在Bismuth Ⅲ型、Ⅳ型的基础上参照肝门部胆管癌侵犯双侧肝管二级分支的不同细化为Bismuth Ⅲ a/b/c/d型、Ⅳ a/b/c型和Ⅴ型,提升了术者制定肝门部胆管癌精准肝段切除手术决策的个体化与精准性。Blumgart T分期[13]与其改良版MSKCC T分期[14]纳入了肿瘤侵袭范围、门脉受侵及肝叶萎缩情况作为评估标准,可辅助肝门部胆管癌的术前可切除性评估,然而缺乏动脉侵袭与肿瘤转移因素的评估,使得上述两种分期尚存不足。2007年召开的欧洲肝胆胰协会专家会议强调了制定完善的新型肝门部胆管癌分期系统的重要性,与会成员DeOliveira等[15]结合多种分期系统,构建了一套涉及胆管树侵袭范围(B)、TNM分期、肿瘤宏观形态(F)、血管受侵(PV/HA)、剩余残肝体积(V)和基础肝脏疾病(D)的多参数分期方案。该方案系统化地提供了肿瘤进展的详细信息,协助术者制定外科决策与评估病人预后,也为肝移植的应用指征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该分期系统因其自身复杂性目前尚未得到广泛推广,Bismuth-Corlette分型现仍被视为肝门部胆管癌临床应用最广泛的分型系统。
(二)剩余残肝体积(future liver remnant, FLR)评估与优化方案
FLR是肿瘤可切除性评估与病人术后肝功能不全风险的关键组分,尚未达到FLR必需值(黄疸病人<40%,正常肝病人<30%[16])的病人术后肝衰竭与死亡风险显著增加[17]。门静脉栓塞术(portal vein embolization, PVE)可通过术前栓塞拟切除侧肝脏的门静脉,诱导肝脏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和生长因子重新分布,实现保留肝脏肥大的目的。相关研究表明PVE治疗后FLR平均增加8%~27%[18],降低手术风险的同时也为术前FLR过低的病人保留了手术机会。然而自PVE施行至FLR增大至满足手术需求常需3~8周,较长的术前等待所导致的潜在肿瘤进展使得PVE尚存争议。联合肝脏分割和门静脉结扎的分阶段肝切除术(ALPPS)可诱导预留肝脏的迅速肥大,一期手术后7~10 d可实现肝脏体积增加60%~80%[19-20],体现出PVE无法比拟的效率优势,但一期手术所致的术后感染、出血等并发症及短时间内的二次手术冲击使得病人并发症发生率与死亡率居高不下。Olthof等[21]比较了肝门部胆管癌病人于肝切除术前是否行ALPPS的预后差异,结果表明ALPPS组病人的死亡率为肝脏体积相似但未接受ALPPS病人的2倍(48%比24%),中位生存期也存在明显劣势(6个月比29个月)。故ALPPS的安全性与病人生存获益状况仍需进一步的临床研究观测,即使针对进展期FLR不足的肝门部胆管癌病人仍需谨慎施行。
肝门部胆管癌病人多伴随胆道梗阻症状,肝内胆汁淤积可损伤肝细胞再生能力,有研究指出其与病人术后死亡率增加密切相关[22],然而术前是否需行胆道引流及减压方式的选择现尚无统一定论。胆道减压虽可缓解黄疸并改善肝功能,但仍伴随感染并发症、恶性肿瘤播散及延迟治疗等诸多潜在风险,权衡胆道减压获益和与之伴行的围手术期风险是术者面临的两难抉择。考虑到肝门部胆管癌病人常需联合大范围肝切除术,Kennedy等[23]和Wiggers等[24]的研究将FLR视为术前引流的评估因素:胆道引流可明显降低术前FLR不足病人的术后肝衰竭发生率与死亡风险;但相对于FLR充足病人,因胆道引流所伴行的感染风险反而增加了病人的术后死亡率,生存获益难以体现。现一般认为胆管炎病人、高胆红素血症引起的营养不良病人、肝功能不全病人和接受PVE的黄疸病人需行胆道减压。除上述指征外,也有诸多学者建议术前常规行胆道减压,以获得低于2~3 mg/dL(34~51 μmol/L)的基线胆红素水平[25-27]。笔者也提倡常规的术前胆道减压,以改善病人术前的肝功能储备状态,降低术中出血量。此外,肝门部胆管癌病人术前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PTCD)引流后的胆汁可经口服用,或经鼻肠营养管回注消化道内吸收再利用,对改善病人围手术期营养状态、降低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等存在积极影响[28-29]。
三、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术
(一)联合肝切除的根治术
病人的术后生存率与切缘状态高度相关,R0切除是肝门部胆管癌病人取得长期生存获益的唯一方式,其中位生存期和5年生存率显著高于R1切除病人。鉴于肝门部胆管癌纵向黏膜扩散、辐向透壁浸润的生长模式,显微镜下所视的病理纵向扩展边界常超过术中或胆道镜下肉眼所见的肿瘤边缘,单纯的肝外胆管切除常难以实现根治性切除目的,因此联合肝部分切除术现已成为外科治疗的常规理念[30]。尾状叶的胆管开口位于双侧肝管分叉部,极易受到毗邻肿瘤组织侵犯,且相关病理数据支持40%的肝门部胆管癌累及尾状叶[31],故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术中行尾状叶切除术现已成为常识性问题。近期研究证实未联合尾状叶切除术的肝门部胆管癌病人切缘处残留肿瘤组织风险明显更高[32],而联合尾状叶切除可显著增加肝门部胆管癌的R0切除比(59%~87%),同时使病人5年生存率由33%提升至44%[33-34]。
Bismuth Ⅰ型和Ⅱ型肝门部胆管癌需行围肝门联合尾状叶切除术或左、右半肝联合尾状叶切除术。针对右肝管或右前叶胆管和右后叶胆管(B5、B6、B7、B8)受累的Bismuth Ⅲ型肝门部胆管癌,应实施右半肝联合尾状叶切除术;若针对右侧的肿瘤组织同时向左侧波及,明显浸润了左内叶胆管(B4)根部的Bismuth Ⅳ型肝门部胆管癌,则原则上应实施右三肝联合尾状叶切除术。值得注意的是,右半肝+尾状叶的体积占比达65%~70%,附加左内叶则可达到80%,因此如何在术前保证病人肝功能状态稳定并提高FLR是病人顺利度过围手术期的关键。肿瘤浸润左肝管的Bismuth Ⅲ型肝门部胆管癌应实施左半肝联合尾状叶切除术;若肿瘤组织向右波及至右前叶上段胆管(B8)和右前叶下段胆管(B5),原则上应实施左三肝联合尾状叶切除术。不同于左半肝+尾状叶仅为30%的体积占比,属于左三肝切除范围的左半肝+右前叶+尾状叶体积占比可达全肝的65%~70%,接近于右半肝+尾状叶,故仍需术前考虑病人FLR的充足性与肝功能储备。值得注意的是,肿瘤自身对血管及胆管分支的侵袭可引发对应肝段的体积改变,因此术中可根据术者的经验更改计划术式,体现了肝门部胆管癌的个性化手术策略。
根据上述Bismuth Ⅲ型、Ⅳ型肝门部胆管癌的术式讨论,半肝或肝三叶联合尾状叶切除所致的大范围肝切除常面临FLR不足的问题,结合梗阻性黄疸病人普遍存在的肝功受损情况,术前优化肝脏体积及肝功能状态至关重要。PVE或胆道引流均局限于术前等待时间过长,ALPPS技术也未能在病人生存获益方面取得理想效果。因此在联合肝切除方面,如何通过合理规划手术方案以取缔盲目的大范围肝切除术是胆道外科未来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精准外科时代的个体化治疗
现如今,基于薄层CT数据的计算机辅助系统已实现了对肝门脉管结构及病灶侵袭维度的三维化重建和各肝段体积的几何测算,有助于术者精确评估各解剖结构的毗邻关系,判断伴行血管是否受侵及其侵袭范围,实现肿瘤可切除性的精准化评估与手术的个体化设计。同时外科手术技术的进步也逐步打破原先固有的手术瓶颈,外科术者更多地敢于挑战传统术式的局限性,转而建设性地提出诸多改良术式,无不体现当今医学精准化、个体化的核心理念。陈孝平等[35]提出肝切除范围≤3个肝段,通常以肝门区的肝段或亚肝段切除为主的小范围肝切除术。该术式摒弃盲目地大范围肝切除,以保留未受侵的功能性肝实质为目的,可降低病人术后的肝衰竭发生率。同时该团队认为手术切缘>1 cm即可实现完整的R0切除,故盲目的大范围肝切除术尚无充分理论依据。董家鸿等[36]结合肝门区的脉管解剖结构,设计并提出了节约肝实质的围肝门联合选择性肝段切除术,范围包括肝门区胆管、肝外胆管、尾状叶及肝门板周围实质及受侵肝段切除,并将肝门板周围实质切除范围设定在肝门板周围1.5 cm。该术式同样取缔大范围肝切除术,实现了最大化地保留功能性肝实质。针对严重黄疸难以耐受半肝切除术的病人,Wang等[37]设计并实施了肝脏1段+4b段及部分5段的“哑铃型”肝切除术。病人FLR显著提高,且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明显优于半肝切除组,然而两种术式在病人术后生存率和复发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Jonas等[38]通过保留部分4段的右三肝切除术以代替传统右三肝切除术,将FLR由23.9%提升至38.3%,为无法耐受大范围肝切除的病人创造了手术机会。然而部分术式的设计理念虽为节约功能性肝组织,但忽略肝脏自身脉管走行的“非解剖性肝切除”常易带来尾状叶切除不全、残余肝组织胆汁引流不畅与血供缺乏等缺陷,符合完整肝段切除理念的中肝(1段+4段+5段+8段)切除术可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上述情况。1段+4段+5段+8段/1段+4段/1段+5段+8段切除术均属于中肝切除范畴,主要适用于肝脏右后叶与左外叶尚未侵及的肝门部胆管癌病人,可在兼顾R0根治效果的前提下保留充足的功能性肝组织(FLR为45%~50%[39]),有相关文献记载其术后肝衰竭发生率明显低于右三肝切除术[40]。然而相对于半肝切除术或左、右三肝切除术的单一肝断面与固定清晰的离断结构,以上肝门部胆管癌的节约肝组织切除术均面临两个或多个肝断面、多点吻合的技术难题,以及随之伴行的术后出血与胆瘘风险;“非解剖性肝切除术”的非常规手术切割线使得肿瘤的术中切除范围往往依赖于术者的临床经验与自身判断,一定程度上增加了R0切除的风险;中肝切除术在手术技术上等同于左、右三肝切除术的组合,涉及两个断面与四个肝门,充分体现了该手术的复杂性,较长手术耗时对病人带来的潜在冲击也值得考虑。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手术因较高的技术难度对术者提出了极高要求,仅局限性地实施于少数大规模临床中心,因此缺乏可观的临床样本量与标准肝切除术形成有效的病人预后对比,且术式的普适性也面临诸多问题。笔者认为,以Bismuth Ⅲ型、Ⅳ型为主的肝门部胆管癌的外科治疗显然不存在完美的方案,FLR与肝功能状态、术前的等待时长、手术的技术难题与伴行的围手术期风险等问题均无法于同一手术中得到兼顾,故仍需综合评估病人的自身因素,结合术者的临床经验与多学科团队制定个体化的手术方案与治疗决策。
(三)联合血管切除重建术
肝门部血管受侵既往因过高的切除风险被视为肝门部胆管癌外科根治的相对禁忌,然而随着外科显微操作的进步与肝移植经验的增加,门静脉与肝动脉的切除重建逐步取得业内学者的认可,肝门部胆管癌的可切除指征被不断拓宽。门静脉切除重建现已成为众多肝胆系统恶性肿瘤的既定做法,尽管技术的复杂性可能会增加病人的围手术期风险,但几个大规模临床中心均报道了可期的预后结果:联合门静脉切除可提高肝门部胆管癌的R0切除术率,但尚未与病人不良预后存在明显相关性[41]。肝动脉切除重建现仍处于临床实践阶段,因高达56%的死亡率而饱受争议[42]。Abbas等[43]对24项临床研究的荟萃分析评估了肝门部胆管癌血管切除术对病人的预后影响:门静脉切除术未对病人术后死亡率产生明显影响;肝动脉切除术显著增加了病人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与死亡率,没有体现生存获益。然而Nagino团队[44]对既往50例联合门静脉和肝动脉切除重建的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术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表明仅1例发生围手术期死亡,病人1年、3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79%、36%和30%,明显优于既往临床报告。笔者认为,R0切除对保障病人的长期生存至关重要,仅针对门静脉受侵的肝门部胆管癌应联合门静脉切除重建术;而施行肝动脉切除术应严格选择特定病人,尽可能地降低病人术后高死亡风险。
(四)腹腔镜与机器人技术的应用
腹腔镜下或机器人辅助的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术目前业已在国内外诸多临床中心开展,但案例有限且多针对术前诊断明确的早期肝门部胆管癌。鉴于术前CT及三维重建等影像学评估有时难以精确捕捉肿瘤的具体侵袭范围及毗邻血管有无受累,术者往往需要术中的二次评估以制定进一步的外科决策。腹腔镜器械和机器人的机械臂有时无法提供精准的触觉反馈,在术中评估血管及胆道侵犯时略显不足,且操作时长相比于开腹手术显著增加,对病人的耐受能力提出了进一步考验。笔者认为,考虑到该类手术较高的技术难度与复杂性,应在对疾病充分认知的基础上,以及严格选择病人的前提下由经验丰富的临床中心开展,并在术后密切随访病人的预后情况,以统计、评估病人的远期疗效。
(五)肝移植
肝移植为部分失去根治性切除机会的肝门部胆管癌病人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然而早期关于肝门部胆管癌的移植治疗效果不甚理想:病人5年生存率仅为28%,肿瘤复发率高达51%[45]。梅奥诊所的移植团队开创性地提出了结合术前新辅助放化疗的多模式治疗方案,并通过术前评估区域淋巴结受累和远处转移情况,严格筛选入组病人,该治疗方案使病人获得了相对理想的临床预后。然而考虑到目前有限的供者资源及R0根治性切除病人可接受的长期预后,笔者认为根治性切除术仍将作为肝门部胆管癌治疗的标准策略;肝移植治疗已展现曙光,但仍需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进行进一步评估,目前尚未作为肝门部胆管癌外科治疗的主流。
四、姑息性手术
针对部分无法实现R0切除的肝门部胆管癌,姑息性的胆肠吻合术可实现减黄目的,一定程度上改善病人的生存质量,然而该手术实施的必要性尚存较大争议。相比于胆道内支架植入和PTCD,姑息性手术的减黄有效率、并发症发生率及病人术后生存时间均未体现出优势性[46-47],胆道支架相比而言更适合晚期肝门部胆管癌病人的姑息治疗[46,48]。针对部分病例,单纯PTCD或胆道内支架植入因未对局部肿瘤组织实施针对性治疗,短时间内再发胆道阻塞概率较高。胆道射频消融术可通过射频电极于胆管狭窄处的产热效应使局部肿瘤细胞坏死脱落,以实现胆管再通的目的,然而该技术的安全性与消融范围评估有待进一步的临床深入研究。光动力疗法依赖于肿瘤组织对光敏剂的高浓度聚集效应,在特定波长下激发光敏剂的细胞毒性反应而杀伤肿瘤细胞。该技术虽于部分文献报道中展现出延缓肿瘤生长与延长胆道通畅时长的治疗效果,但受限于高昂的治疗成本而尚未于临床中广泛应用。笔者认为射频消融术和光动力疗法目前均不是肝门部胆管癌的主流治疗策略,期待在未来更多的临床实践与对照实验下进一步评估其裨益与应用前景。
五、结语
我国肝门部胆管癌的外科治疗现已步入精准化和个体化时代,随着手术技艺的不断突破与手术理念的不断革新,病人的临床预后得到明显改善,然而仍需更多的临床数据支持以进行更多治疗方案间的病人预后对比。笔者认为以肝段为基础的解剖性肝切除虽存在较高的技术要求,但手术技艺的瓶颈相对于病人自身状态的约束更易突破,可通过反复的临床实践而日臻成熟,且医学影像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帮助术者合理规划手术方案,规避术中可能的潜在风险,以控制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与死亡率,因此个体化设计的肝段切除术有可能成为未来肝门部胆管癌外科治疗的主流理念。腹腔镜、机器人辅助下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术与肝移植技术的兴起拓宽了外科治疗决策,射频消融术或光动力疗法等治疗手段也为部分无法行根治性切除术的病人提供了姑息治疗选择,但均需未来大样本量的临床对照研究进一步评估对病人的远期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