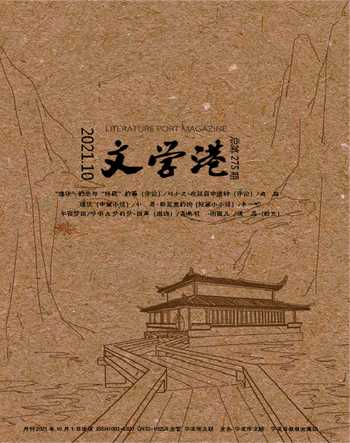日常的神性:小年夜
张远伦
1
小年夜,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夜晚,超过了中秋之夜。天空中不再有月亮自称天意,洒到人间来。它们跨越星球的光抵达,其实是毫无内容的白色侵略;大地上没有木樨空气添加剂般的混合,刻意的香气释放扰乱了暮晚之后的所有宁静。而今晚,戊戌年腊月廿四的酉时,中山四路的老街上,我正在为每一种可能的命题作答。
今天再次传来武汉疫情的消息。我们都隐约有一些不安。
但是,作为诗歌的命名者,我需要把一些尚未厘清的眼下物象作出准确的诠释。用诗的语言,对那些动态的或者静态的符号作出所指的扩散。我是笨拙的,但此刻是灵敏的,中枢神经对电脑文字的支配欲,已经变成对迟钝的声音文字的把控。我干得并不游刃有余,但是勉强可算及格。
群星占领天幕时,黯淡是我的能力
同样坐在寂静中,失明的那枚才是黑暗的知己
——《小年夜》
在整个戊戌年,我都是黯淡的。写作处于瓶颈期,没有一首诗或者一两个句子能让我自己记住,群星灿烂,而我独自无光。我和我的星球都坐在宇宙无垠的寂静之中,我像是消失的人,存在却又被黑暗吞噬,只有那颗逐渐失去光泽的星辰,那颗逐渐近于失明的星辰,才像是我,像是我的知己,理解了我的孤独和自失。
然而,中四路上翩然而至的鹊羽,白色的绒毛,在我的身旁轻轻零落,黏在我的肩头,带着人类的体温,予我抚慰。它们是无意落入农历小年夜的小段公历时间,是错入城市南方的小片北方。它们来自公历五月,却一不小心掉进了农历腊月,这一段时间的穿越,带有浓厚的玄幻色彩。羽毛就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形象化的时间。它们在叶间飘落的时候,时间也在旋转,虚化的事物突然全有了具体的形状。时间是羽毛状的,时间是所有飞翔的态势;时间是黑夜中的所有白色,不耀眼,但是足够穿破迷障,所以时间是七种颜色调配的,最后具有了单纯的同色调。羽毛来自嘉陵江之北,是一个空间概念。它婉转地落在我的头上,轻轻地触摸了我的前额。像是飘渺而又瓷实的一片空间,贴在我的思想之上了。我显然尚未完全做好迎接浩大空间的准备,显得有些慌乱。我的一生,随便一处小小的缝隙就可以容纳和拘留我,我对太大的宽阔没有要求,也没有清醒的认识。我的辽远来源于灵魂,只有诗歌撑开我的心胸,我才意识到自己其实也是天空一样有容量的孩子。就像现在,我在老街上,这些圆拱门太敞亮了,以至于我随身的黑暗具有绝对的小,轻轻一坐,就能把自己插入夜色,楔子一般,找到孤独感中的撕裂,而作为自己得以生存几秒的空间。羽毛来了,它用细小和柔软,反衬了空间的恢宏和坚实。空间无形,然而有形。空间也是羽毛状的,肉眼可见的光源,是江之北的起点,然而它本身又是江之南的终点。它来到我的额头,巧遇我、抵牾我、紧贴我、深入我,似乎已经用锐利的空间,刺透我的想象,进入我的骨髓。我感觉到身体被打开,一片羽毛在心室找到自己的位置。小小的空间逼开了我诗歌中巨大的空间,我感到膨胀,血脉贲张,似在全身心地飞翔,就要在老街上迷乱地扑腾。
2
手机信息弹出的武汉现状,已经不很乐观。人们正在大量储备口罩,已经有人出城。
一些古旧的人则准备返回乡村。
我也是古旧的人,茫然不知有华彩的现代,这点呓语,是我十年语音的合成。这个世界是有很多隐患的,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万物都是先验,却拒绝向我们告知”。只有当万物中的某一物以敌对的姿态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才会事后诸葛亮般说:又错了。我们本该认识到每一种弱小存在的价值和巨大的破坏力,但是依旧认为它们是弱小的,是我们的附庸,我们只需要享用这种霸凌感和控制欲就行了。当我们在时空中越来越强大,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宇宙中越来越孤立。古老和现代这对词语,在我身上有着奇妙的守恒,但是我还是时常觉得惶惑不安。时间要抛弃我们太容易了,没有谁能逃脱这些无形的惩罚。当羽毛滑向嘴唇,我感觉到某种神秘的力量又要來惩罚我了,不是疫情,那些语焉不详的病毒并不是我最害怕的。我感到恐惧的是时间和空间本身的无限,而我们是如此短暂和脆弱。我还对时间和空间的具象——一片羽毛突然地莅临,感到忧惧。任何碰撞都是命定的,即使是老街上的迎面触动,也是命定的。我仰着头,迎迓这片羽毛,它像纯净的病毒,迅速感染全身。我呓语,口齿不清,不知道病毒所为何来。
我在这里,解答内心关于诗歌的问题。而羽毛是一个对我进行访谈的问号。
北滨路和嘉陵江的关系是什么?一条河运送着灯火,光影参与形成。将军府外的修竹有怎样的此情此景?一排栅栏围着民国,小院便是独自承欢。树根何以一排密布在墙壁上?
那是线条化的时间,老去的生命伸出触须。诗是不是特异功能?那么,语言就是迷信,是神的终将垂怜……
羽毛的问句没有这么具体,它进行着抽象的谜之问。当它问出“关系”的时候,我的诗歌是结构主义的,是我对罗兰·巴特的微调:“你是突然降临于我的脑中,而不是我召唤得来的。”一条河把你运送到我这里,江与滨江的关系得以生成。“羽毛创造了意义,意义创造了生命。”我们的关系,就是诗歌的生长关系,是一种不断创造的过程,我的生命因此得以完善。
当它问出“情景”的时候,我的诗歌是中国古典主义的,它讲究了“情景交融”和“触景生情”。它去了东方以东,便是无尽的“物哀”;它去了西方以西,便是无限深度的“意象”,是一群人的影子,诸如勃莱、赖特、帕斯、豪格等。我看到的小栅栏围着民国,而不是围着现代主义,是小院独自承欢,羽毛独自优雅。
当它问出“诗”本身,我的诗歌是存在主义的,是老树根被时间派到墙壁上一网千年;我存在,成为语言的迷信,成为被一片羽毛怜爱的古旧之人。我因此得以对抗虚无。
3
这片羽毛一直在小年夜里舞动,从民生银行迷离的光圈中走出来,经过桂园、求精中学、德精小学、圆拱门、三闲堂、周公馆,到曾家岩的悬崖边,它一直有着雀跃之美。天空的流量中,你是全部,别人不是。候鸟的奔袭,留鸟的沉静,都在羽毛上。你如果继续白着,云朵就不敢再白,你如果深一些,气流层都尽数避开。落地时那对大地的颠扑,颤抖的波动,让大量梦境惊觉。此后,久久的静止,像生命为我留出巨大的默契,在人世喧嚣中。
疫情在继续发酵,一些恐慌溢出,我们对于生命的思索又多了些。有一本书叫《神秘的生命灵光》,说的是濒临死亡,从死亡线上回来的人,大多感觉过灵魂出窍,然后经过一个隧道,看到一片灵光,这个过程自然而然,没有恐惧,没有痛苦。有人说,这是因为人在死亡边缘会分泌某一种物质,对人进行最后的生理性的安慰。人在对抗死亡的过程中,最需要的安慰是自我安慰。自我安慰主要来源于精神层面,告诉自己,死亡并不是那么恐怖,并不是那么痛苦。那种身体抵达极限的时候,自我的生理性安慰,投射到灵魂层面,让人会走得轻松。我想这是人对自己最后的最高礼遇吧。
而当我们得知疫情的扩大时,曾经笃定的认识——“死亡并不可怕”——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我开始觉得死亡是可怕的,尤其是“非正常的死亡”,是不能接受的。那么,疫情中的死亡,显然就是内心动摇的源头。我对于信仰和艺术的追求,便是为了抵制死亡和虚无。但是我感到了这种努力的不可信。隐约的警惕感让我觉得:其实我们更需要另外一些东西。
死亡是孤独的,是一个人的事情,绝无可能结伴而行。所以死亡不仅仅是对生命消逝的恐惧,还在于对虚无、对巨大的孤单的恐惧。我想,如果要让濒临死亡的人减轻这种恐惧,就要尽可能地减轻弥留前夕的孤独,让他们感受到爱。这种爱不仅是亲人的爱,还有来自男女之间的灵魂之爱,如一个人被巨大的深刻的爱包围,一定会走得轻松很多。因此一个人生前最大的财富之一,便是拥有爱情。同时,这个人还会很深刻地爱别人。《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上帝把一切丑陋给了他,但他有对爱斯梅拉达高贵、圣洁的爱,最后他死在少女的尸体旁,他殉道于爱。司汤达的墓志铭也说道“米兰人亨利·贝尔,活过、写过、爱过。”司汤达的一生并不长,不到六十年,他爱得奋不顾身,却无一例外,全都无果而终,终生未婚,但他的确是“爱过”的,他有资格说出这句话。所以,他很坦然地在自己的墓碑上写下“爱过”两个字。这两字得以让他更坦然赴死。
4
这个小年夜显然不同于我经历过的43个小年夜。当我们遥远地向着武汉祝福的时候,也是在祝福自身。或许我们的城市,已经有了疫情的苗头。或许我应该明天就佩戴口罩了,或许我应该回到村子里去,躲避厄运。
城市有个阳台,就在中四路的尽头,从悬崖边凸出去。我的心灵有些延伸,这凸出的部分用于通风和呼吸。站在这悬空里,江岸线也柔顺了些,北滨路的灯饰变幻,一会天蓝一会火红。嘉陵江就在情节里流淌,逆水的游船满载灯火,拖着倒叙的光芒。曾家岩边,设计师的美学,是重庆的虚和实,是人们的镜与像,那微风沿着悬崖上来,仿佛来自一条大河的抚慰,吹拂着我。
鹊羽也被吹动了,我看见了它灵魂的翻卷。
这是一片年幼的羽毛还是年长的羽毛,还是和我一样,是一片中年的羽毛?如是,那么也就和我一样并未参透生死,并未身心通透,并未对诗歌作出未来的判断,并未对即将袭来的灾难做好迎击的准备。然而我错了,这是一片悠然自得的羽毛,它的飞行路线封闭而又自足,开放而又主动,有些来自林间荫翳的羞涩和不谙世事,也有些独悬城市中央的骄傲和舍我其谁。
我对它说话,用眼睛的凝视说话,我没有更多的声音表述。
我对羽毛说:死亡是价值的一部分、是生的一部分、是爱的一部分、是这个星球乃至于整个宇宙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小年夜的语言系统中,起到结构作用的那一部分;当然,也是对少年的我和青年的我进行解构的那一部分。
一部分什么?我尝试着回答。
人对抗死亡最好的方式,是追求人生价值,实现人生价值,这样,会走得少一些遗憾。当一个将死的人觉得自己一辈子很值了,那么,我相信死亡也不那么可怕。有精神追求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后会更加積极面对死亡,因为他们获得了精神的满足,比如文学艺术、科学研究等。而一味追求金钱的人,往往会不断陷入新一轮的虚空,最终会觉得没有实现价值,没有填补内心那巨大的黑洞。很多平凡的人,会有平凡的价值观,但是不影响达到的效果,和看似伟大的价值观一样,都能在对抗死亡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匠人的手艺达到精湛,造出满意的产品;农民的稼穑获得丰收;打工仔赚到钱回家修好了房子,都是一样的。当然总有很多人最后觉得人生充满遗憾,价值没有实现,这时候,他们往往会寄托于亲近的人,希望他们的价值得到最大化。比如子女对父母临终前最好的安慰是儿女的成功,无微不至的照顾固然重要,但是儿女不断走向新的境地,更让他们觉得安慰。
我无声地絮絮叨叨,不知道羽毛有没有听进去。我看见它飘动得更快了,也许是某种来自量子的呼应和纠缠,也许只是因为嘉陵江又起风了。
5
我把整条街道走了一遍,重复昨天,一群人变成一人,像收脚印的灵魂。灯光迷离,人用低语译出了竹和树的交谈,导出了城市阳台和民国警局,像在用诗拍一部纪录片,我有拙劣又陈旧的解说词。近春了,红灯笼正在树上悬着,影子却紧紧抱着影子。我在播放自己,分成一帧一帧,每秒都令我窒息。老街的今夜如此空旷,一点光落地的声音都没有。一片树叶睡着了,一片羽毛醒了过来。此时,我看见了人们的飘逸和卷曲,中山四路,正进入城市的浅睡之中。
嘉陵江走在夜行列车的前面去了,它尊重了暮色,并预祝了人们晚安。这里的高楼,与南岸的大厦一样,在用顶层扫天空。天空有什么不干净的?落地窗明亮无比,有人坐在光圈里,从我的角度看过去,也是坐在浪纹里。共同想起的人们,定然就在春阳那边吧?像辽阔的江水那样,吃倒影,听船鸣。现在我要向老街献上最灿烂的温柔了,我从候鸟那里找到它,群鹊纷纷避让。它在空中缓慢了些,像是要祝戊戌年小年夜晚安,祝武汉晚安、祝中国晚安、祝人间晚安、祝万物晚安。
安好。最朴素又最深情的词语。
我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夜晚之后,我们的医疗机构经受到了非典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武汉的疫情,向周遭渗透,我的重庆也在劫难逃。在这个晚上,一片羽毛导引着我想了许多。
有人说医疗机构做好了人“生的准备”,没有做好人“死的准备”,对病人的关怀,需要更完善更人性化。就是整个社会,大都是做好了人“生的准备”,没有做好人“死的准备”。对每一个人必然的死亡,缺乏教育和疏导。孩子小时候总是爱问:爸爸妈妈,人会死吗?你们会死吗?我会死吗?这时候,我们总是企图捂住他们的嘴,让他们别乌鸦嘴,好像死亡是一个禁区。
记得我的大女儿进幼儿园后,听说了“死”这个词,回家后就忧心忡忡地问我:“爸爸,你会死吗?”
“不会的。”
我在回答这一句问话的时候,甚至有点相信自己会永生。那时候不知道永生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是一直活着。多年后,人到中年,才知道永生就是向世界低头认输,承认自我局限,承认必死,承认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只是为了在死亡前获得另一种永生的理由。所以我写诗。
显然,那时候的女儿是相信“爸爸不死”的答案的。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回来问:“爸爸,你们会死吗?“
“不会的,宝贝。”
她的眼里有了犹疑,内心有了动摇,她已经获得了人都要死的信息。但是她不再问话,不再戳穿一个美丽的谎言,不再对她的至亲进行逼问乃至最终伤害自己。
她只是过了一段时间自言自语似地对我说:“人会死的。”这句话的潜台词令我几乎潸然泪下。
6
同样,我们也坐在寂静中
你像白羽凌虚,我像孤星落实
——《小年夜》
当我在小年夜如水的清凉中,和一片羽毛对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孤星一样落实了。
而那片羽毛,凌虚而行,把寂静当成了食物。
它像是我的诗歌的眼睛。
在今夜,我的诗歌突然间超越了俗世情感,进入了哲学的领域。我有些担心,当哲学和诗歌交合,我会不会被更多的柏拉图逐出“理想国”,会不会因为成为“无限的少数人”而羞耻,会不会对哲学的零碎理解而妄断诗歌的前途,会不会因为一片羽毛的三种落地方式而放弃自我生命的终极之美?
羽毛落地太美了。美到一切诗歌和哲学都是对它的阐释。
第一种落地方式是:預习死亡。羽毛中最睿智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哲学就是,预习死亡。”显然,羽毛的诗歌节奏已经练习千万遍了,从我写下的众多句子来看,预习死亡就是获得某种语言节奏,进而从容面对死亡,做好了人死诗歌不亡的准备。实际上,每一个人都需要预习死亡、思考死亡、应对死亡,有一个成熟理性的死亡观念。那么,人就不会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那么消沉、沮丧,甚至恐惧。我的诗歌在宗教意义上是成立的,它们是我内心的经卷、是自我复述和自我预谋、是自我燃烧也是自我消弭。因此,羽毛看到我喃喃自语,那是我在反复训练,准备好迎迓死亡之光。羽毛于小年夜落地的时候,是惯性的,是流畅的,是驾轻就熟的,是得到万千祷辞和祝词的。所以它落下来,并未惊惶,灿若星辰。
第二种落地方式是:亲吻死亡。羽毛中最超脱的哲学家蒙田说:“死亡说不定在什么地方等候我们,那让我们到处等候它吧。”羽毛说出了死亡的本质是“等候”,而且是互相等候。就像我在等候羽毛,羽毛也在等候我。我们在小年夜相遇了。这几乎就是胜过了一次死亡的小小奇迹。对我这样的诗人个体来说,它甚至超越了“死亡”,而得到了上天的“神助攻”,羽毛对我的临幸,像一场亲吻。它在我的额头上久久不落,像是代替天意,对我进行长吻。我们互相用“死亡”致意。用“窒息”致意、用“惊厥”致意、用“休克”致意、用病毒般的“关照”致意、用灾难般的“席卷”致意。羽毛落地是轻柔的,温润的,是得到宠溺之爱的、是享受到天光摩挲的、是得到无数词语的光斑洗涤的。所以它落下来,仿若意愿已了,无声无息。
第三种落地方式是:死之不死。羽毛中最圣洁的器官捐献者周老师说:“死亡是一个人最好的精神发育。”周老师的女儿捐出了遗体的五处器官。拯救了五个陌生人。相当于女儿还活着,活在五个地方,母亲能真切地感受到。周老师不仅不觉得是自己和女儿拯救了别人,反而觉得是别人成全了自己。这就是天使般的温暖,是善良的极致。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更为超脱。一个人无论财富多寡,身份高低,最后都要面对死亡,人生最后的课题就是如何与死神握手。人最后的衰老和死亡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发育,是人生最后的也是最高层次的发育。发育得好,就会正视死亡,拥抱生命。在诗歌的意义上,这种发育的结局就是“死之不死”。是永恒性,是生命圆满的标志。所以羽毛落地了,《道德经》和《诗经》一样轻盈地落地了,《逍遥游》和《论语》一般愉悦地落地了。羽毛获得了人世的赞美诗和唱经声,它起落天然,挣脱星球引力,大自在,如是观。
7
父亲告诉我,按照神灵的旨意,小年夜要进行献祭。
然而我没有美酒和佳肴,没有诗歌中的名句,没有生命中的至纯,来进行一场献祭。
最终,羽毛悠游天际,我将独自献祭。
我向天空献出自我,一个迷思的自我。天收否?不收,则我将继续苍凉下去,老旧下去,病痛下去。
自我隔离下去,自我否定下去,自我消除下去。我将献祭给自己,给诗歌,给一切有为法和无为法。
阿图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中讲了一个故事:托马斯为了帮老年人抵抗疗养院的厌倦感、孤独感和无助感,建立了新的疗养模式,在里面养了2条狗、4只猫和100只鹦鹉。护士因增加了工作量而拒绝照顾这些动物。但是老人们主动认养,并从中获得了快乐和满足,从而大大抵消了身体和心理的负能量。
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消失。消失的意义是为了“最好的告别”。
托马斯的老人们需要动物的灵性来拯救内心,我需要一片羽毛来拯救诗歌。
我独自在中山四路逡巡,试图从阶梯的分行中找到断句的方法,从老树盘根中找到语言的梳理方法,从城市阳台的人造光影中找到物理性和心理性的融会,从嘉陵江的不舍昼夜中找到词语的运动轨迹。最关键的是:从一片羽毛的消失中,找到死亡的提点。
我相信任何一种存在都是要告诉我“存在之道”。
“小道救我”“大道利他”,所有“道”是为了向无形的无垠还债。我的诗歌拙劣,还债缓慢,不知道能否救赎我的最终。
荷尔德林希望自己写出伟大的诗歌,即使只有短暂的时间活着,也要像神那样生活,就没有更高的要求了。
权威的命运啊,只要给我一个夏天,
加一个能让我的诗歌成熟的秋天,
让我的心尝够这甜蜜的游戏,
那时,我就死而无憾。
——荷尔德林《致命运之神》
诗人不在乎生命的长度,而在乎生命的高度,在乎那种巅峰水平的价值体现,而不需要永生,不需要多长时间。这是一种生命价值或者说死亡观念的极端。诗人相信自己虽然人生短暂,但是作品会永生。当人的生命具有巅峰水平的高度时,当然是时间越长越好。生命的长度和高度、广度和深度结合,才是最好的。
然而,谢利卡根在《死亡哲学》中认为:像这种代替活下去的方式,实际上不是永生,是一种半永生和准永生。就像伍迪·艾伦所说:我不想通过我的作品变得不朽,我想要通过不死来活着。所以一片羽毛告诉我:“你的诗还写得不好,不死之死的境界还远着。你的诗小气,耽溺于自我。”所以我在小年夜实在拿不出可以献祭的东西了。
有一个命题是:你是选择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还是选择做一头快乐的猪?哲学家长期思考人的深层次问题,比如说“预习死亡”。另一种观点是,要“无视死亡”,活在当下。实际上这两者都没有问题。思考死亡并正视死亡,才会拥抱生命。无视死亡而超越死亡,也是在拥抱生命。殊途同归。但是有一点,无论哪一种方式,都有自己的价值在其中。痛苦的哲学家有深度的心灵体验,而快乐的猪有深度的感官体验。说实在的,我们不能说快乐的猪就是一种享乐主义,可能那也是很好的对抗死亡的方式。
小年夜,我向河流注视很久,它的平静像一场冥想,没有主题,巨大的杯盏里空空如也,神灵正在辟谷。先祖和我都空腹许久了,月亮投宿江北,它将收受我的献祭过夜。大河开始丰盛的烹饪,小区贴出停水通知,新闻中播出疫情专家“不要恐慌”的劝慰,河面上,一蓝一红的航标灯仿佛是永远亮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