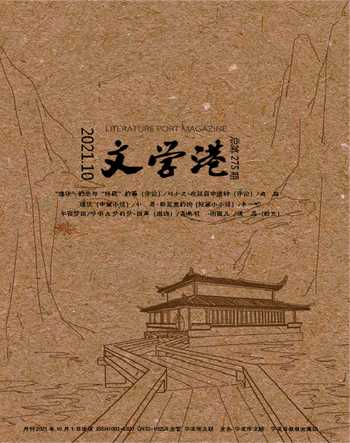那些昭和年间的事
张烦烦
1
喜欢周作人译的小林一茶的俳句,便寻源去了解这只下蛋鸡的日常,总也不太能如俳句般爱得起来。又不甘心,偏要耐心去探寻他的过人之处。好在最终不失所望,得着了一些,遂一边读一边零星记下。
周作人和鲁迅不同,总是努力平和,避免甚至杜绝激动,仿佛要极力使血压平稳下来。摔酒瓶子破口大骂的事情是断然做不出的。
蔑视微小,想要割裂掉作为人的某一部分。从感情上来讲和旧传统中的假大空是一脉的,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奄奄一息的错觉。实际上是懒得与你交流,反正我说了写了,你爱听不听。
有时候又流氓一样,不要指着我的口吻,失了自己的园地也不见得怎样可惜。三十几岁便一副活了好久的腔调,让人不悦。但他三十几岁的积累是我们所不具备的,所以他作文的好处没有一定的积累便不能懂。
偶尔也会用力。但他的力用得隐讳,你不觉得他在使劲。或者说他把这个作为一种修养贯穿在行为中。着意要省些力,以养长生之基,平常人或许不易做到,但他可以。避免多言,以“不语”为美德。
至于其他不妙的地方,自不必多言,随他去好了。不过于作者来说,对于旁人对自己的评论无法认同或反驳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无论他分析得多么头头是道,褒扬的还是贬斥的,或者是臆想,甚至是肢解的,撕裂的。
2
晴天屐其实在雨天也可以穿用的,趾前覆履。永井荷风的一本散文集子用它作了名,陈德文把它译作《晴日木屐》,但深谙日本文化又娶了日本妻子的周作人却把它译作《日和下驮》,听起来更符合日文的习惯。下驮的发音是“足桁”的音变,始用于室町时代,更古一些的时候叫“足驮”或“木履”。
永井荷风常穿了晴天屐,手执蝙蝠伞行走于街巷,甭管多好的晴天,不穿木屐,不带蝙蝠伞就安不下心来,对一年到头湿气浓重的东京天气完全信不过,穿了木屐,就可以防备突然间的降雨。荷风怀揣了嘉永版的江户区划图,四无目的地行走,并把见到的祠、寺、小巷、悬崖、坂坡、闲地、树、水、渡船、夕阳、富士山统统写下来,且给穿了木屐拄了伞杖的自己画了一幅画,画中飒然的荷风踩着足有五英寸高的木屐,简直高过了富士山。
清寂的横街里,常有清贫度日的老年人,开了带住家的小小门店,夫妻两人或者谁单独一个人经营,进去贴着窄窄的条桌坐下,照墙上简单的菜谱点了餐——菜式只是那么几种——或者不点店主人亦了解每位客人的口味,互相鞠躬客气自然是免不了的。场面温情,暗淡,缺乏色彩,于同情之外,又常常泛起些尊敬来。
有人在练唱《清元曲》,这种哀婉不健全的江户音仍然可以保存它的命脉。荷风把自己当作他人,对无可把控的现实感到讽刺,越是想用力抓住自己投进去,越发觉得痛楚,踉跄中同时看到了得意与悲哀。
穿了木屐像是分别把一座移动的小木桥随时踩在左右脚底。木屐不能打弯,这样五个脚趾头要使出更大的力来贴附它。来自广西的张武媛同学入学时带来了木底的屐,远远地就听到她“呱哒呱哒”的声音,木底的屐敲着俄式建筑的木地板格外响。
3
读是很深入的一个参与过程,唯有投入才能得它的好。如同爱一个人。不能匆匆掠过。再得有感觉逐步清晰化的过程。读过了,放下书本转身去做别的事时,它的好才逐渐明晰起来。如同爱一个人,天天腻在一起不觉得,稍稍离开些,才明白她的好来。
高村光太郎讲他去海拔高的山间温泉泡澡时,定会带上绳索,万一遭遇火灾,随身携带的绳索便成了救命的稻草——难道火灾会常常发生的么?温泉别墅的门框上可以随心作画,高村光太郎在上面画了很多素描。西铅温泉更深处有座名为“丰泽”的小村庄,那里有很多有名的猎熊人,被人们称为“叉鬼”,如果请他们帮忙的话,甚至可以吃到熊的胃。丰泽村的蘑菇产量极高,有滑菇、伊野菇、马哈菇、毛钉菇。采菇人对蘑菇生长地绝口不提,即使对自己的家人也严格保密。
山居生活清新、自然,哪怕早餐只有冷饭。佐一些越瓜、赤苏、绿紫苏或者腌制的蕨菜都是好的。蔬菜都是高村自己种出来的。镇上的阿布博先生送一些苹果给他,一种被称为“祝”的青苹果,还有一种被称为“旭”的红苹果。本地的井水虽然清冽,但高村从来不喝,只用来漱口,因为如果饮用了井水他会全身冒汗,因此增加出来的洗衣工作虽然很清爽,但又太费时。
山口村里的孩童们对山外来客诚挚地行礼,或道“再会”,或者说“感谢您”。高村初始避居此地时,总疑心自己是否会显得特立独行。村民们得知他被疏散到此,对他的处境格外忧心,或提米而至、或冒寒踏雪前来看望。他想要修建小屋时,又和他一起从一里地以外拆除另一个工棚,把柱子和房梁扛回,原样把小屋搭建起来,并掘井于屋外,对他说放心吧,村庄能养活你。
雪期未过时,村里会进行祈福,届时会请来传统舞者跳起插秧舞,人们齐聚一堂,击打着太鼓。上元节,村里的孩童会蜂拥而聚,跳起欢乐的稼舞,长长的队列绕行于各家各户。
白日里,小屋会有许多访客,或放暑假的老师和学生、或打算在田园中野炊的游客、或久违的故友,高村便和访客们如往昔在東京那般畅快地饮起酒来。有时候,高村同村民们一起被邀请了去村长家吃荞面,妇人们一大早便带了食材去村长家准备餐食,一小碗一小碗的荞面会不断地从厨房端出,摆到餐桌上,然后哧溜哧溜地进了村民的肚子。村民一点都不浮躁,连烦恼都是沉着的,扎下去的。他们自是知道心在哪里自己才会安稳,自会趋向散发出光亮的地方。
后来高村还是得了肺病,咯血是常有的事,尽管很注意营养。他喜欢吃动物的内脏,认为它们不仅美味,且廉价。得肺病的日本作家真是多呀,樋口一叶、夏目漱石、太宰治,统统得了肺病。好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可以从容一点的,看周作人在文中提及自己在西山碧云寺里养病,好生让人羡慕,他们的生活节奏是有时间休养、调理自己的,而如今的人连生病都不敢,不可以有任何的意外和闪失,不然会被淘汰。
日本人的姓名很素朴,常常是自然里原有的事物,你看,比如高村、村上、大江、田中、北野、永井荷风、三岛、川端、渡边、东野等,像是顺手拈来浑然天成般,就像高村为文,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写就怎样写,如此就很好。
4
日本有许多从事手作、坚持自由创作的人,遵从心中理想打造生活器物。他们执着于素材的细致感,配合人心摇摆不定的功能化使用需求和情绪性欣赏需求,设计出简单且让人眷恋的东西。他们需要同时具有创作之手和判断之眼,尽量去除个人风格中过于强烈的部分,没有扭曲,不带偏见,创作出处处渗透着生活感的器物来。日本有许多这样让人不忍失去的好物,因为感受到物品孕育出来的爱而买回来,器物的意义就不只停留在表面。
设计师深泽直人说,不要羞于谈论美这件事。应该以积极又诚实的态度看待美。“一件纺织品为何如此有魅力”这样的事情是重要的,不必动不动就想把类似的物品集结起来加以归类。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深具各自特色的器物。
可以确立自己的喜好机制,感受色彩的微妙差异。可以直接去铸铁店和铸铁师傅面对面交流,用传统方法造一把修剪枝条用的剪刀。铸铁师傅将铁放入炉中烧得通红,再取出放到铁床上敲打,一边敲打一边问:“如何?这样可以吗?”你可以回答“麻烦这里再弯一点——好了,就这样,太棒了。”也许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即便如此,还是想要。这样的感觉特别美妙。
“祭”是一个很好的字眼。有宗教般的虔诚在里面,也有面对美好事物时常会产生的悲哀和无奈在里面。那些崭新的、低质的、浅薄的奢华,同“祭”体现出的内心严肃的遵从必然是相悖的。
高山市所属的香川县知事金子正则被称为“设计知事”,他说“政治和艺术追根究底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丰富人心而存在”。金子正则生长在一个美学意识早已融入生活的城镇,他的父亲曾是制作团扇的工匠,不过说到底是一位艺术家偶然做了知事,在他担纲指挥下做出香川县厅舍这种明明是现代主义建筑,却让人强烈感受到传统和风的奇妙建筑来。金子正则有关政治和艺术的相关主张仅凭书中简单的表述并不能使读者充分理解并认同,但可能他有最终不为人所知的道理。
《器物的足迹》这册书不好的一点是纸质厚,且涩,总疑心是不是把两页合一起了没分开,但翻过去看时两个页号却是相连的,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钝。钝是不好的,作为一册书却没有灵气,呆头呆脑的。纸质生了也不好,少了一个步骤,还没做完就集合起来裁好了,装订起来便不随,不妥帖,似乎每一页纸都挣扎着各自朝了自己认准的方向。你说捧在手里读一册这样的书可怎么好。如果哪一天自己再做一本书,一定要选轻而韧的纸,绝不可同样费了时间和精力做一册蠢笨的书出来。
读这册书时生出一个念头,想要把家里用的竹制案板侧面也照着书里的创意,用铁筷子烧红了烫一个自己想要的图案出来。一定有一些人对美有着更强烈的需求,就像我比常人需要更多的光亮一样。也总会有人喜欢另一些东西,比如彩色和纸糊成的人偶,比如重叠起来烧成的瓷碗,也不必去骂他们,在尊重的基础上悄悄嫌弃就可以了。
对于我来说,写字即是手作,其认真,耐心,还有等待新事物一点一点生成的情形是一样的。文字也有很多种花样,两者很相似。
5
蓝染职人。从江户时代开始起,蓝师栽培蓼蓝,每年九月砍下蓼蓝,阴干后便现出浓浓的户部蓝来,接着裁成一小段一小段,洒水,捣制,做成二十五厘米左右的蓝靛,再把蓝靛送到蓝染职人处。蓝染职人也被称作染匠,他们把蓝靛放入深埋在土中的蓝瓮中发酵,再投入要染的丝线和布匹,十分钟后取出,如此重复多次,直到把它們染成喜欢的色度。蓼蓝的种子是从德岛县来的,日本关东地区将具有高超蓝染技术的人尊称为“瓮之上”。
卖眼泪的。也是一种行当,在日本战败后到昭和三十年间最为活跃,靠哭闹、装可怜来推销商品,一边哭喊着“我的工厂倒闭啦”,或者“没有电车钱,回不了家啦”,一边售卖物品,能不能把戏做足,演技是否有爆发力和感染力,直接决定着他们的收入。假哭卖钢笔的用“工匠骗术”,谎称家里着火的用“失火骗术”,统统算作“卖眼泪的”。
三明治人。昭和年间移动着的活体广告人,身体前后都挂着宣传广告,在商店门口、车站、广场等人口稠密处进行非常有喜感的推销,因为身体如三明治般被广告牌夹在中间,所以被称为“三明治人”。三明治人只要向辖区的警署递交道路使用许可证就可以开展活动。有的三明治人背了水桶,水顺着管子流到木屐底部的毛毡活字上,这样一边走一边就有一个湿漉漉的广告印在路面上。后来三明治人被卡通人物所取代。
门边艺人。过年的时候穿戴好行头挨家挨户上门表演,有的带了盲女,弹着三味线说唱一些祝福的吉祥话语。即便是乞讨,也是以才艺赚取生活费,算是以劳取酬,相较之下可恶的是那些假扮的槛外人,借了神圣的名义明目张胆上门求索,眼珠子骨碌碌地转,利用人们的良善,给食物不要,给钱少了也不走。
还有一种最不可思议的行当——拾发女,属于行商的一种(行商是走街串巷做小商品生意的人),她们行走在京都的街衢上,一边走一边喊“头发掉了哟,头发掉了哟”,一边将地上的头发捡起来,积少成多,然后攒起来卖给批发商做成假发——简直太不可思议,有这样的可能吗?
《消失的行当》(日本泽宫优著)一书记录了许多“昭和的行当”,均为昭和时代常见的庶民从事的职业,如今有的已经消失,有的仍作为一种地区文化活动存在于特定的时间和场合,比如纸芝居屋。
在那个时代,一些行当以简单的形式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樵夫需要上山伐木,人们从头顶柴火的大原女手里买来上等的木柴。人们可以把用坏的铁锅和雨伞请人修补好。可以点对点地请信鸽送去私密的信息,不必担心网络监控和大数据信息收集。街上是热闹的,有卖冰棍的、有街头评书的、有拉洋片的、有表演水艺的,孩子们可以到处追着跑。蓝染职人认为蓝靛是有生命的,他们每次工作时都要念唱“南无爱染明王”。人和人之间频繁交流,面对面接触,少有人感到孤独。几十年坚持用心做好一件事,比如制作一件趁手的农具。
一位叫高木护的流浪诗人做过一百二十多种工作。他出生于昭和第二年,在不同的阶段分别做过黑市看守、算卦先生、破布分选工、浊酒铺职员、山中找矿人、剧团经理、见习乞讨、出入证发放人等。他讲算卦先生其实是假的,只是在宽慰人,主要帮客人做些人生咨询——一个潦倒的人为他人做人生咨询也够滑稽的。做乞讨也是有诀窍的,服装要百年如一日,言语要含糊不清,不能在意时间早晚。后来他在昭和三十八年来到东京成为诗人,以自己的经验为素材,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
如果我生在那个年代,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摆渡船的船老大,摆渡身穿白无垢的新娘和她的家人,即使生病也不许请假。或者灯塔看守人,安静地几十年呆在一处安静的海上,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读书、写东西。或者腰封文案作者,像阿部次郎一样写下“快读”这样雷人的话。可以肯定的是有些事情一定不会去做的,需要坚持的内容必定不可妥协,这是一定的。
6
夏济安谈鲁迅谈得特别起劲,完全不像他个人日记里恋起爱来也缩头缩脑的一个人,盖或是实际生活中缺乏勇气,便在文章中使劲补偿。
我觉得某些部分他不能自圆其说,有些理解不到位,比如对死的理解,对梦境和鬼魂的理解。一旦发现不太合理的地方就有点读不下去了,得再拣一个时间才能仔细读完后面的部分。
他和兄弟夏志清书信来往可以出好几卷。不知两个男人间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