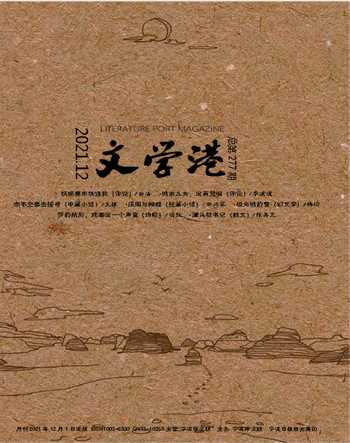城市儿女,出离荒诞
李潇潇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城市故事。主人公是两个货真价实的都市青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脱离乡村关照而独立存在的城市故事开始生长。随着乡土寓言(抑或童话)的走失,城市上空的绚烂荒诞摇摇欲坠。
一、城市儿女
狼性的程小晋和佛性的吉波不愧为当代都市代言人。他们彼此如此相异,却不妨碍读者一一指认。因为雖然程小晋像打了鸡血一样“想出人头地”,为了成功上蹿下跳,内外兼修,他用着爱马仕钱包,却不得不对中央空调的费用耿耿于怀。结交着各路精英,将本职工作视如鸡肋,却根本不敢辞职,并且和你一样,陷入白天越辛苦,晚上越失眠的怪圈。同住的吉波性格恬淡,与世无争,只要他想,就可以一直靠刷刷网页打打游戏过着不用花钱就丰富多彩的好日子。这般掐头去尾的躺平姿态,你一定也认得。
当代都市青年狼性或佛性的进化方向,都足以让我们为自己惊叹。我们确实是爹娘生养的真实人类啊,但眼下的我们,为什么可以如此孤独,如此坚强!我们何止坚强,我们比任何一代青年都更为“人间清醒”。我们拒绝蒙蔽、询唤,我们如饥似渴,必要时茹毛饮血。我们心胸旷阔,自律,坚韧,瑞思拜极致理性,也赶国际神秘主义的时髦。那个需要呐喊的铁屋早已灰飞烟灭,城市儿女,极目远眺,独立自主,不成“狼”便成“佛”。我们识相,懂事,我们愈发孤独。我们早已甘心情愿地吞服那剂“绝望”的蜜符。况且只消打开电脑,世界性的蛛网呵护和缠绕着我们,夫复何求?无非是赤手空拳,破涕一笑。
“我想发财,想成为大明星,我很努力,比你们这些稀里糊涂过日子的人付出几百倍的努力,我在人前压制我的臭脾气,我像个婊子一样被别人随叫随到,我到处赔笑脸,我不找女朋友……我失眠,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我学习一切值得学习的东西,我努力提高情商,用四十六岁的要求来要求二十三岁的我……我多么努力啊,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与生俱来云树遥隔的人物性格在城市化进程中被消解,广谱平庸的成功学照耀下,应对高额房价,程小晋父母赠与的三十万和吉波的一文不名似乎没有太大的差距。于是当吉波被千载难逢的机遇砸中,他又随即成为文学长河里最为镇定的一名幸运星。因为城市的幸运与焦虑如影随形,为了五年后的两百万差价,需要三天筹集一百万的首付。吉波“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生活惯性让他下意识首选了放弃。
而城市儿女的要义才刚刚体现:个人主义如浮萍不堪一击。无论是自我张牙舞爪的程小晋,还是自我低进尘埃的吉波,一旦被这“唾手可得”的诱惑洪流灌入,一念起落,旋生旋灭的情绪挣扎,我们眼见他们无一幸免。短短几小时间,这个“两百万”的涡轮不断撩拨着程小晋,激动、嫉妒、焦急、愤怒、感动、沮丧……鞭挞着他着魔一般地涌进。从网贷到众筹到诈捐,他疯狂构想着成功法则,几乎就要变成魔鬼。与此同时,吉波的恋爱情绪也像植入了一个悬疑病毒,无时无刻不在悸动着购房的成败。
在这股庞大情绪袭击之下,他们忽而满腹希冀,视险若夷,忽如槁木死灰,一触即溃。善恶美丑一览无余,欲望席卷一切堂皇修饰,只剩真实。
城市分化,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城市日新月异。程小晋生于斯、长于斯,却常常对它感到陌生,更有甚者,对这城市里的自我感到陌生。王棵催命鬼般的语速同频共振着当下的城市儿女,却不打算硬着脖颈斜睨他们。王棵收起了炫技的惯性,叫停了嘲讽或批判。两个青年如醉酒一般疯癫了一阵,又如醒酒一般恢复理智。这显示着作者难能可贵的真诚。也许唯有这个品格,才能造就货真价实的城市文学。
“对!先去吃饭。吃完饭,继续战斗!”
二、出离荒诞
天池妖姬如果加入这场摇号购房的故事之中,或许那个熟悉的荒诞气味就会扑面而来。金钱摧毁爱情?然而以她为代表的传统亲密关系,将在这个彻头彻尾的崭新城市故事中黯然失色。这一定是王棵胸有成竹的精心安排,因为他理解真正的城市,他知道城市的荒诞是一堵墙,而我们并没有走到终点。
荒诞如一场病毒,人类与其胶着缠斗多年。它像是渐渐被我们咀嚼,消化,而后甘之如饴地吞噬。或者说,我们的价值基因早已被荒诞悄然篡改。但毋庸置疑的是,警钟长鸣的古典价值犹在耳际,却不止影影绰绰,几乎脉微如缕;作为“一种理想主义的痛心疾首,一种天真而锐利的失望”的荒诞初生之时的刀刃也随之不复存在。俯拾皆是的荒诞,无聊得不值一提,平凡到失去意义。再也不存在圆溜溜的荒诞,它已经流泻弥散到四处。
或者说,现实早已比荒诞更荒诞,我们于是不得不出离荒诞,返身进入最为具体的现实,去体察变化,寻找答案。新的业态,新的潮流,新新人类,精彩绝伦,沸反盈天。城市即将成为人类新的乡愁,我们无法也不该视而不见。
例如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城中的亲密关系已经悄然改变。传统牢固坚实的关系纽带,家庭、爱情,同僚等,在城中都显得望梅止渴。吉波的父母十七年前离婚后各自组建新的家庭对他视若累赘,程小晋华丽丽的朋友圈里借不来半毛钱。当然,这些疏离状态作为老牌城市病,已经广泛出现在小说中。难能可贵的是,王棵关注的不只是拆卸,而是某种建立。
吉波和程小晋以一种性情互补的方式生存在同一屋檐下,携手应付昂贵的房租和更为昂贵的梦想。吉波一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模样,程小晋则自诩为心机boy,他们各自的日常生活邋遢或浮夸,但在真正的挫折或危机之时(程小晋被下药,吉波摇号中签),他们竟然确实是可以相互支撑的。是城市生活的重压带来的阶层认同,还是殊途同归的空洞更容易随机地在对方身上看见自己?如果将这一次摇号中签事件作为一个观察切片,至少我们毫不费力地心随其动。直到我们追随程小晋的情绪风暴,听见他声嘶力竭地呼喊:“我累了,我怕我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么拼了。以前,我那么拼,也没能出头,不拼,能出头?绝不可能。我想,我这辈子恐怕都没法跳出穷窝了。你是我朋友,我助你一臂之力,让你出头,对我来说也是个安慰。”我们和吉波一样目瞪口呆。
“我自己出不了头,但我朋友能出头,那也行啊。”
这番充满“正能量”的夸张言论,我们似乎就这么信了。程小晋需要这些天赐的兴奋和沮丧,这些不可思议的可能性,像是对他遵循成功学法则兢兢业业却一事无成的一次有力报复。共同对抗憋闷的城市气压,他和吉波是战友,更是亲人。吉波和程小晋的亲密关系,展示了一种新型的人类纯粹之爱。莫名却真实。算作一次有益的尝试。
也是同样的缘故,吉波那些近乎弱智的网恋,那种莫名的迷恋和付出,也正在这具冷漠的城市形体上秘密潜行。人类亲密的欲望有增无减,甚至更磅礴而疯狂。
城市儿女的境遇被现实逼进窄门,互联网时代却能让同理心冲出藩篱。我们同时拥有空前的桎梏和自由。简单地赞美或批判都不再奏效,书写城市的新真实需要作家拥有更具想象力的人文精神。
对当代作家来说,中国的城市小说极具挑战。曾几何时,王棵不再是躲在家里自怨自艾的小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他没有成瘾上头的怀旧病,气质大方坦率。“破帽遮颜过闹市”,他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去探探情况,凑凑热闹。他可以和城市里大展拳脚或头破血流的年轻人共情。因为无论如何,他是一名都市青年,这是他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