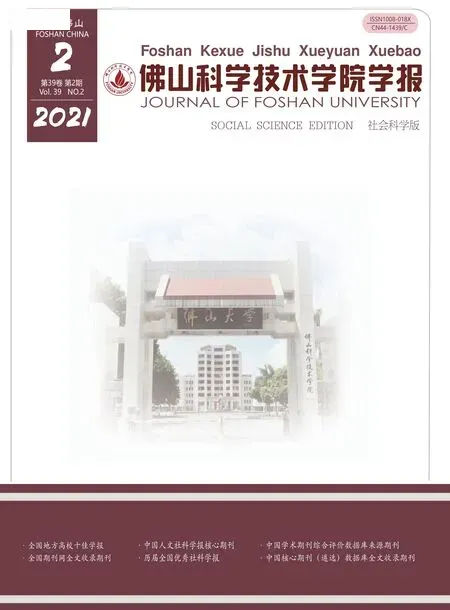民国时期佛山铸镬作坊运营情况探析
——以《铸造铁镬行例》为中心
陈君娜
(佛山市禅城区博物馆,广东 佛山528000)
明清佛山的冶铁业为当时的支柱产业,其主打产品铁锅、铁钟远销海内外,是佛山成为“天下四大名镇”“天下四大聚”的重要经济动因。关于佛山冶铁业历史的研究,已有多位学者深入研究,并形成了多篇论文和相关专著,他们从行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模式、生产技术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述。[1]但因为佛山冶铁业没有留下如石湾陶业《花盆行历例工阶例》和《陶艺花盆行规》那样的商业档案、契约文书等文献,导致关于佛山冶铁业的论述中缺乏细节描述,如冶铁作坊的运作模式、雇佣关系等,这对一个曾经红火数百年的重要行业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因此,在明清佛山冶铁业的相关论述基础上,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仍有必要。2018 年,佛山市禅城区博物馆征集了一份文献《铸造铁镬行例》(1936 年纸本手写),从名称来看,是整个行业的制度规范,但细读文献,却发现它只是一个铸锅作坊的内部制度汇编,主要包括《铸造铁镬行规》《雇铸造铁镬工人规章》《铸造铁镬材料》《铸镬器具》《本厂铁镬之种类》《拟定雇铸造论镬计工规条解析》等[2],较为详细地规定了一个小型铸镬作坊的运营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是此书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注明明确的地域,这就给研究者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因此,考证其地域性是首先面临的问题。
一、《铸造铁镬行例》地域考
明清佛山冶铁业中,铁镬是其中主打产品。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佛山素善鼓铸,其为镬,大者曰糖围、深七、深六、牛一、牛二……”[3]《佛山忠义乡志》又记“铁镬行。向为本乡特有工业,官准专利,制作精良,他处不及。”[4]明确的文献记载使得一些学者认为以“铁镬”就是佛山的产品,其实不然。镬为古语,《周礼》有记:“掌共鼎镬”。颜师古对镬注解为:所以煮肉及鱼腊之器。因此在历史的流变中,铁镬并不是佛山的专有名词,浙江宁波、温州一带也称锅为“镬”,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补铁镬技艺》一项[5],可见单纯以“铁镬”来判断是否佛山的产品,是不合理的。
那么如何界定地域,还需细读文献本身。在《铸造铁镬行例》(以下简称《行例》)中有一条规定颇具地方特色:“订明每逢初二、十六日祃期日,猪肉四斤、鸡一只……若无鸡补豕肉一斤以代之,另酒菜银四毫,每逢时节照祃期办法。”[2]9关于“祃期”,《澳门大辞典》解释为:“澳门商界流行的习俗,广州、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地区亦曾流行。俗语称做牙,即打牙祭。该习俗何时形成已不可考。据古书称“师出必祭,谓之祃。”又称“祃,师祭也,为兵祷。”古代所祭的是军前大旗,称为牙旗;祭品是大猪。商界沿袭此习俗,让伙计饱餐一顿,目的是鼓励大家做好生意。祃期是农历的每月初二和十六,年初二时每年的第一个“祃”,叫开祃;农历十二月十六是该年的最后一个祃,叫“尾祃”。这两个祃都要大打牙祭,商号往往聚餐加菜,吃得比平日都好。[6]
香港书法家陈荆鸿在《海桑忆语》中对“祃期”也有过回忆:“旧式商店,有所谓‘做祃’那一回事的,每月两次,在上旬的初二日和中旬的十六日。做祃多数是宰鸡作馔的。至于每月初一日和十五日,则是煲猪肉。这大概因为日常菜肴,都是清淡居多,所以选取三几天比较丰富些,以示对伙伴一点慰劳之意。劳资双方,和衷共济,是应该的。”陈荆鸿是广东顺德人,后长期居住在香港,他的回忆大多记述顺德、香港的往事。由此上述两则材料可见,祃期大致是珠三角地区或者广府地区的商业习俗。那么由此推定《铸造铁镬行例》也是该区域的产物,但是否佛山,还待进一步考证。
从《行例》文本信息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地域考证。
首先,从民俗活动角度,可大致判断《行例》所产的地域。《行例》中写明“订明九月廿八日华光诞日东家补酒菜银壹拾元正一概在内,限以停工两天(或停工四天亦有)。若不停工,此二天内工银另照给足,倘要开工,任由东家注意,不得执拗不铸。”[2]10这条资料说明此地对华光诞这一神诞非常重视,特意放假并发放节日补助。那么广府地区何地对华光诞如此重视,很多资料指向佛山。《佛山忠义乡志》记载“二十八日华光神诞,神为南方赤帝,火之司命,乡人事黑帝天后以祈求水泽,事赤帝以消火灾,是月,各坊建火清以答神贶,务极奢侈,互相夸尚,用绸绫结成享殿,缀以玻璃之镜,衬以翡翠之毛,曲槛雕栏、锦天绣地、瑰奇错列、龙凤交飞。召巫作法事凡三、四昼夜。醮将毕,赴各庙烧香,日行香,购古器、罗珍果耄,备水陆之精素,擅雕镂之巧,集伶人百余,分作十队,与拈香捧物者相间而行,璀璨夺目,弦管纷喧,复饰彩童数架以随其后,金鼓震动,艳丽照人,所费盖不资矣,而以汾流大街之肆为首。”[4]
《广东民俗大观》中对“华光诞”的介绍更为直接地将此习俗的地域范围界定为佛山。“华光是南方火神,佛山祀华光十分隆重。佛山人忌水患,故祀奉华光火神以消灾。农历九月廿三华光诞期,镇内各坊都建‘火星礁’,由所属街巷店户捐款,选出代表(称为值理)搭醮棚,悬挂五色铜枝彩灯,‘建醮景色’。建礁前,值事们前往低街(今莲花路)华光庙,迎华光塑像供奉在醮前,开坛通经祭拜,街内各店户到坛参神;次日午,由一人敲响高边锣开道,道士们各持法器,为首的平持法剑,沿途通经、舞剑,并用剑尖施洒净水,俗称‘送火星’,随后是十队‘八音’,飘色彩童数队。历时三、四日,华光神像回庙,火星礁才告结束。”[7]
如果说《佛山忠义乡志》的记载还是偏于一隅,不具有代表性。《广东民俗大观》作为全省民俗资料的集大成者,则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全省范围内,“佛山祀华光十分隆重”,基本将佛山与华光诞之间画上了等号。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行例》规定华光诞要停工两到四日,是因为华光诞要历时三至四日,各家各户要捐款建“火星礁”,到各神坛参拜,迎接华光神像巡游,是一场遍及全镇、包含祈福娱乐多重意义的盛会。因此,从华光诞民俗活动角度,可大致判断《行例》出自佛山。
其次,从产品种类规格角度,也可进行大致推断地域范围。《行例》记载该厂生产铁镬的种类有:“吉星镬每担拾六个,每重例□(字迹残缺)斤;一尺二镬每担壹拾四个,每重例五斤;一尺四镬每担壹拾弍只,每重例五斤半;一尺六镬每担壹拾个,每只例重六斤半;一尺八镬每担八个,每个例重八斤半……”[2]21而民国时期佛山生源镬厂的产品种类规格也是1.5 尺至2 尺(大镬)、1.2 尺至1.4 尺(中镬)、1 尺至1.2 尺(小镬)。与《行例》所在的厂家产品基本一致。[8]94
最后,从产品的生产过程的一些细节,也可推断出《行例》为佛山所出。佛山铁镬铸造有其独特的工序,《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曾专门收录了佛山铁锅的铸造工序图,组图共十张,分为:舂泥、筛泥;造模坯、车上模;上色、车下模;合模、探模;落模、烧模;模红、出模;收破旧铁镬(锅)料;落铁水;去模拣铁锅;修补下货。[9]其中舂泥、筛泥部分的工序,据铸镬工人回忆主要为“首先用稻秆、田泥(黄泥、细沙泥、烟泥等)、谷糠、水砂等按一定比例倒进先行挖好的大池内,工人用双脚踩练至有一定韧性,才开始制模。”[8]94而车模时,“要把炼好的胶泥拿上来做成1 个内模、1 个外模,用炭火烘干,然后用白泥浆拌和焦炭粒加在泥模的表面,再烘干,再涂白泥浆拌焦炭粒,如是者3 次,便可以用来铸镬了。”[8]58而《行例》中也有关于造模和车模所需材料的记载:“造模需用泥(要坚结无沙)、十月禾草(要舂烂取禾根)。车模(车模工作归铸造师责任)用车刀、细沙(用捞斗筛过)、煤碎(即炉内清出碎碳,因经过铁水故坚硬)。”[2]17两相对比,可以发现,《行例》中有关泥模的程序,与佛山铁镬泥模的相关程序是一致的,都需要对泥进行去沙处理,禾草与稻秆是同一物,焦炭粒与煤碎只是称呼不同。同时,对泥模数量的要求体现出“佛镬”的特点。《行例》中规定“每种泥模须备足三盒并要陆续制造,方不致有不敷至虞。因造模费时太久,方能得干也。”[2]11文中“三盒”还不确定是多少数量,但文字意思显示,对泥模的数量有很大要求,要源源不断地提供才可满足生产。而佛镬不同于四会镬、惠州镬的冷漠铸造,它的生产工艺为红模铸造法,其特点就是“一模一镬”,每铸一镬便耗费一个泥模,因此需要大量泥模。《行例》的规定恰好符合佛山铁镬生产工艺。此外,《行例》中关于“炉门石”的记载,也符合佛山铁炉的特色。在《行例》中有《铸造铁镬材料》一项,炉门石是其中之一,作者对其进行了注解:“塞炉口,□(字迹残缺)有此铁生乃溶。”[2]18而佛山传统铁炉中,有种普遍使用的铁炉——点头炉,在其方形的出水口放一块砖堵住,出铁水停风时把它夹开,送风时把它放上,这块砖其实就是炉门石。[8]107
综上所述,《铸造铁镬行例》应是出自佛山的铸镬作坊。证明此点,就可以据此探究民国时期佛山铸镬作坊的发展情况,包括运营情况、雇佣关系与劳资权利、生产情况等。这也是《行例》的学术价值所在。
二、从《铸造铁镬行列》看民国佛山铸镬作坊的运营情况
因文献缺乏,学术界对佛山铸镬作坊的运营管理情况一直语焉不详。目前最为详细介绍民国佛山铸镬作坊经营管理的文章要属黄慧根《近代佛山私营铸造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载《佛山文史资料》第11辑),该文以民国后期佛山最大的铸造厂——德记铸造厂为例,介绍了佛山铸造行业在吸取现代管理经验之后的新发展。德记铸造厂规模大,人员多,技术先进,其经营方式虽是标杆,但并不具备代表性。该文结语也谈道:“基于各经营者素质上的差异,不‘肯于用功夫,舍得落本钱’的多,故德记整套的经营管理方法并没有为全行业所普遍采用。”而《铸造铁镬行例》背后的铸镬作坊,因人员少,规模小,是佛山铸镬作坊的缩影。因此,以《行例》探究民国佛山铸镬作坊的经营管理情况,比较符合历史的普遍性。
根据学者研究,民国时期佛山铸镬作坊经营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资本家独资或合资经营,资金最多的一两万,少则几百元;二是家庭手工业,纯由父子兄弟做工,规模小,产量低;三是铸造工人合作经营,共同投资、自己做工、共同分红;四是“搭水”方式,即有技术无场地,有生意去租同行场地开工生产,交纳一定搭水费后,赚取利润。[8]9-10
《行例》规定显示,此铸镬作坊属于第一种,有店有厂,店面负责存货、销售,工厂负责具体生产铁镬。作坊人数不多,但分工明晰,设正司理一人,司柜一人,造模师一人,杂役若干,伙头一名,铸造工人八名。除铸造工人外,其他人员都在店面工作。司柜则负责记账和货物进出记录。杂役主要负责检查铁镬安全质量、发现残次品进行修补、寄送货物等。造模师傅是镬厂的技术骨干,因为泥模的质量直接关系铁镬的成型和光洁度,所以造模师傅的工资饭食不在铸造工人范畴,由店面负责。他除了造模之外,还包括清点生产铁镬之数量、运输铁镬时的安放工作并在闲时修补铁镬,与杂役的工作职责有交集,但地位高于杂役。伙头只负责店面人员的膳务工作,铸造工人的膳食则自己负责。铸镬工人负责熔铁浇铸工作。铸造工人每天分早中晚三次将所铸的锅拿到店面,杂役清点后由司柜记录入库(存镬总部)。司柜记录时分为入库、出库,出库包括:现沽(现买现卖)、客贷(按当时商业习俗,可以赊购,以后按季度或端午节、中秋节、冬至、春节时结账付款)、回炉(残次品无法修补,只能回炉重铸)。最后月终清点账目,做到出入相符。[2]4
总体来说,店面负责销售,技术含量不高,且人员相对固定。因此,作坊对店面的要求不高,对铸造工人则有较高的要求,如《雇铸造铁镬工人规章》及《拟定雇铸造论镬计工规条》中有详细条款规定雇佣方式、生产要求、工资福利、奖惩标准等,是我们了解民国中后期佛山铸镬作坊生产方式的重要凭借。
(一)雇佣方式
《行例》显示,该作坊主在招雇铸镬工人时,并没有采取单个招聘的方式,而是通过承包项目的方式与整个团队签订合约。合约后面必须附上说明:“凡雇铸镬师傅时关于其职责内之工作与规条及一切例外之事务要当面与其订明,并一一书入工作合约内,于交定银时须(上夜)即师傅签名于合约内,以照慎重。”[2]13由此可见,上夜师傅即是整个团队的带头人,负责与作坊主签订合约,承揽铸镬业务。那么,何为“上夜”,《行例》规定铸镬工人八名分为:上夜、下夜、接石、看炉、替班(兼轩风)、轩风(三名,负责送风)。八个人分两班,每班工作日夜各六小时。[2]7,8顾名思义,上夜即是负责上半夜铸镬工作的师傅,因为开炉一般是在晚上,所以上夜即是整个团队的带头人,也是第一班工作的负责人。在雇佣时间方面,以月为单位,订明时段。如期满仍有工作任务,工人工食按日计算,铸工不得以期满为由拒绝工作。这种雇佣方式对雇主非常有利,根据市场灵活运作,无须承担过多无用的人力成本。同时,被雇佣方因为是团队协作,更能发挥各自专长,轻车熟路,能够保证产品质量。
(二)生产要求
在原料方面,要尽量节省,“由开工之日起,要续日将店内所存之碎铁及广生铁兼用铸去,不得留存不铸,要在此工作期内铸清。如期满收工之日业觉有此两种之铁留存,则扣工银拾元正,倘能依期将碎铁铸完则赏奖银拾元正。”[2]28在产量方面,采取计件工资法,“每日例规铸镬五担为额”“每月满日计算以三十天为壹个月共计应出镬除回炉外限以一百五十担为额。”[2]29每多一担,增加工银若干,以此类推。在质量方面,佛镬以轻薄著称,因此雇主对重量非常重视,“每担镬限重以六十四斤为额,以轻不以重。不得过重,如有七十斤重者,工食银减半计算支给。”[2]27在炉具修理方面,佛山化铁炉是用黏土砖砌成,外面用竹木铁皮捆住,内膛用白泥混合石灰黏土做成土方,干燥后成为炉衬。用过一段时间,炉衬受损,如不修理,将影响炉内温度的稳定性。因此,《行例》规定“凡开铸之后每拾日须修炉一次(或不足或不止)。须看炉火如何而决之,不可任其借口十日之例,每次费时间一天停工修理,越日即须照常开工铸造,例不许延迟。”[2]15,16由此可见,该作坊对产品的质量、数量、成本等项目管理非常细致,虽达不到现代管理的要求,但对于一家铸镬作坊来说,已经抓住了管理的大方向,为我们提供了民国佛山作坊经营的一种面相。
(三)工资福利
铸镬工人因工种不同,工资也有区别。不过可惜的是,《行例》没有明确规定上夜、下夜、接石、看炉四位师傅的工资。只写明替班每月五元,轩风每月四元[2]6,可以推测上夜等四位师傅有与雇主议价的空间,而替班等四名属于辅助工种,技术含量低,可以明确工资水平。轩风工人有时也要兼任洗沙任务,工资为每百斤三毫。除工资外,八人每日的餐食也由雇主提供,在一些重要日子,雇主要加菜或提供费用,如开工当晚需要举行开炉仪式,晚膳很丰富,“要购猪肉四斤,鸡一只,小菜任便,以飨工人。”晚膳之后还要给猪肉一斤或菜数斤,供其早上食用。[2]15
此外,神诞节庆祃期等日更是如此。每年华光诞(农历九月二十八日)“东家补酒菜银壹拾元正一概在内,限以停工两天(或停工四天亦有)。若不停工,此二天内工银另照给足”。[2]10而祃期(每月初二、初十六日)也是雇主加餐的重要时日,当天雇主要提供“猪肉四斤、鸡一只……若无鸡补豕肉一斤以代之,另酒菜银四毫。”[2]9其他重要节日,也参照祃期的规格提升餐食标准。
总体来说,《行例》背后的铸镬作坊,虽然达不到行业标杆——德记铸造厂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但在运用协作关系和用人策略方面,还是尽量向先进看齐。德记的工人工资分甲乙丙几个等级,技术骨干更是高人一等;除了祃期、华光诞、开炉日要杀鸡煮肉外,每月还请工人到酒楼吃饭或订席由酒楼送酒菜来厂,劳资共叙一次,每桌8 人花15 块银圆,以此保持工人积极性并取得较别厂为高的生产效率。[8]78两相对比,可看出两家铸造厂对待工人的相似性,这在当时佛山整体经营环境中还是较为难得的。不过《行列》的要求过于以雇主为本位,在生产要求、雇佣期限等方面,工人无任何选择权,即使雇佣期满,“仍须续铸,工食按日照计,任由东家主意,不得借口期满为词。”[2]5同时,对工人劳动保障等方面无任何条款,这与当时逐步流行的现代管理理念是背道而驰的。以同时期由佛山人梁日盛在上海开办的梁新记兄弟牙刷公司为例,该厂工人的工资,依照他们生活的负担决定。而他们的生活状况,由厂房特高薪聘请大学毕业生进行调查,以示重视。在教育医疗方面,工人子弟可以在厂中附设的工人夜校中免费读书,夜校每逢周一即举行学术讲座,聘请上海各界知名专家学者到校演讲,传播各方面的文化知识。工人免费享受体检,如身体有恙,不仅厂方负责提供特殊饮食,还给医疗补贴,实在不够还提供借款。在文化娱乐方面,厂内设立图书室,并鼓励工人自己办理板报,以增进工人的读写能力。同时成立球队、音乐会、戏剧社等,每逢重要节日便举行音乐会或戏曲演出。如有值得看的大戏或电影,厂方也会购票请工人去看,以丰富工人的文娱生活。[10]由此也看出佛山当时工商业发展与上海的差距,在这种大环境下,佛山铸镬业在当时慢慢衰落也是必然的。
三、结语
作为以工商业著称的岭南重镇,佛山虽然具有浓厚的商业文化,但成系列成规模的商业文献并未留存,这为我们探究这座商业重镇内部运营的细节,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铸造铁镬行例》的发现,对研究民国铸镬行业的运营情况,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笔者通过文献中记载的民俗资料、生产工艺等细节,最终证明该《行列》为佛山铸镬作坊的制度汇编。通过这些制度要求,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完整地了解到民国佛山铸镬作坊的运营情况,包括人员构成、管理架构、生产程序、工资福利等,弥补了此前佛山铸造研究中的细节空白,同时也为我们了解佛山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一扇窗口。当然,《铸造铁镬行例》中所展现的雇佣契约,过于保护雇主的权利,在权责要求方面没有体现现代契约中的公正平等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看,佛山铸造在民国时期为何不能延续此前的辉煌,此正是背后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