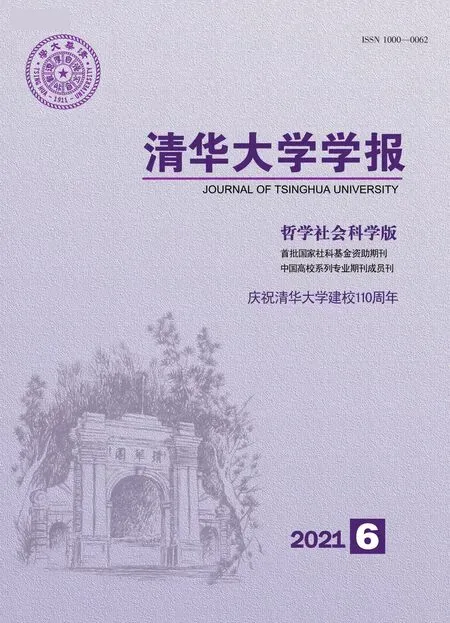啤酒与麦酒:舶来品译名的东亚视角
刘群艺
从19世纪至今,啤酒在东亚区域内从一种舶来品变为日常消费品,中国与日本等国家也成为全球啤酒生产与消费的佼佼者。虽然是相同的产品,也具有较为类似的消费体验,同为汉字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却选择了不同的译名。为什么“beer”(或bier)在中国与日本有各自独立的译名?中国的“啤酒”与日本的“麦酒”又有怎样的定名过程?
在全球物质史的研究中,对舶来品的命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这种命名过程包含文化遭遇、共同的消费体验、产品的流动以及消费网络的形成等关键因素,①R.Grew ed.,Food in Global History,Boulder:Westview Press,1999,pp.8-11.可以完整还原传播过程。啤酒在东亚各国的命名过程就表现出以上诸因素的相互作用。
在之前的研究中,仲伟民揭示了成瘾性消费品的全球传播与近代化的关系,认为在近代世界即将形成的时期,成瘾性消费品可以成为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催化剂,将全球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②仲伟民:《全球化、成瘾性消费品与近代世界的形成》,《学术界》2019年第3期,第89—97页。这就明确了啤酒传播史研究的全球化与近代化价值。林采成则从东亚区域角度考察了食物的传播史,描绘了食物帝国网络形成过程中出现的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③林采成『飲食朝鮮.帝国の中の「食」経濟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9年。这在啤酒本地化生产开始时也有表现,对译名的选择也有所影响。田野村忠温考证了中国近代语言教材与词典中众多食物名称的来源,在展现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梳理了译名研究所需的一手史料。对于啤酒的中文译名,田野村认为存在从广东、上海到北京的南传北过程,在此过程中,译名发生了与外文词汇发音的背离。④田野村忠温「コーヒーを表す中国語名称の変遷」、『或問』第37巻、2020年、41-60頁;同氏「カレーを表す中国語名称の変遷」、『或問』第38巻、2020年、15-25頁;同氏「啤酒の謎の解─この不可解な名称の成立過程」、関西大学第10回東西学術研究所研究例会「文化交渉と言語接触」、2021年2月19日。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先从全球史以及东亚史角度来简述啤酒的传入,再以啤酒的汉语译名为起点,对比啤酒的日语译名,结合韩国与台湾地区的译名,来探究全球化的传入环节对译词选择的影响。
一、啤酒来到东亚
作为饮料的啤酒已经具有至少5000年的历史。啤酒起源于两河流域与古埃及,又从埃及传入希腊与罗马。但是从现代消费习惯来看,南欧人似乎更喜欢喝葡萄酒,更热衷于酿造和饮用啤酒的是西欧和北欧人,可能是因为欧洲西部和北部地区位于葡萄种植线以北,不太适于种葡萄。这些早期的啤酒并没有使用啤酒花,大概到12世纪,啤酒匠才开始在酿酒时添加酒花。直到今天,是否使用酒花也就成为了划分啤酒产品的一个重要标准。
啤酒的种类多种多样,按照发酵技术可以大致划分为爱尔啤酒(ale)和拉格啤酒(lager)两类。爱尔啤酒起源于英国,发酵温度较高,酵母浮在麦汁表面,为上发酵啤酒;拉格啤酒则最早多见于德国南部,发酵温度低,酵母沉在麦汁底部,因此被称为下发酵啤酒。早期的英国啤酒多为上发酵方式,包括同为英国出身的波特啤酒(porter)。但在工业革命之后,由于低温发酵、大规模生产和长途运输技术都有了突破,下发酵啤酒显示出明显的优势,拉格啤酒也因此成为了工业时代的宠儿。早期英国与荷兰殖民者都曾将爱尔啤酒带到东亚,但在19世纪晚期以后,东亚消费者接触到的就以拉格啤酒为主了。
中国考古发现以及史料记载中的“醴”是类似于现代啤酒的谷芽酒,也与远古时代的啤酒一样,没有添加啤酒花。这种醴酒也见于古代日本与韩国,多用于祭祀。这种酒的度数较低,后被较高度数的酒所取代,也就没有在东亚普及。近代,当谷芽酒以啤酒的形式再次进入东亚区域时,人们对于其味道和工艺还是比较陌生的,尤其不适应啤酒花的苦味。①M.Pilcher,“Tastes Like Horse Piss”Asian Encounters with European Beer,Gastronomica:The Journal of Critical Food Studies,Vol.16,No.1,2016,pp.28-40.
在认定啤酒进入东亚的渠道时,“开国”或者“开港”会被作为一个方便的切入点,即以鸦片战争或黑船来航作为考察的起点。确实,舶来品在东亚的传播具有沿开放口岸逐步扩散的特点,但如果想追溯啤酒的初次现身,这个时间点应该再往前推,因为早在锁国之前就有西方殖民者来到东亚。考虑到欧洲人消费啤酒的地域特征,可能最早是荷兰人或英国人把啤酒带到了东亚。②传教士将啤酒带入东亚的可能性比较小。在记录早期葡萄牙、西班牙与意大利传教士在中国生活的《拜客训示》中,我们看到的酒类消费就只有葡萄酒,没有啤酒。李毓中等:《〈拜客训示〉点校并加注》,《东亚海域交流史研究》2015年创刊号,第133—168页。
在《热兰遮城日志》中,荷兰殖民者记录了17世纪来往于台海两岸船只的货物装载情况,其中就有啤酒。另外,日记中也出现了“日本啤酒”和“中国啤酒”的说法,显示出荷兰殖民者用“啤酒”来命名一切当地酒类的倾向。③曹永和:《热兰遮城日志》,江树生译注,台南:台南市政府,2011年。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熱蘭遮城日誌/I-A/1630-01-02,2019年8月13日。
荷兰人的啤酒不仅出现在台海两岸,也同时出现在日本长崎的商馆中。1631年3月23日,长崎的荷兰商馆馆长给我国台湾地区的同行写信,要求提供酿造啤酒用的瓶子。④谢明良『热兰遮城遗址出土的十七世纪欧洲、日本和东南亚陶瓷』、『金沢大学考古学紀要』第30巻、2009年、3-16頁。
除了荷兰殖民者,英国人也将啤酒带到了日本。在平户开港时期(1550—1641),英国人跟随荷兰人的步伐,在当地开设了商馆。1613年,初次来航的英国船只“格鲁普号”(Groub)就载有啤酒。⑤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東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第3巻、2頁。
可惜的是,以上啤酒传入过程并没有相应的中文或日文史料,也就不知道这些啤酒是否存在译名,之后的闭关锁国似乎限制了啤酒的进一步传入。这些在开国开港之前的传入经历有助于丰富舶来品在区域内的交流途径,也提醒研究者注意啤酒的非英文词源。
啤酒的日文和中文文献要分别在18世纪和19世纪才集中出现,这说明当地人开始接触到啤酒了。因为有了接触,才有必要用本国语言来称呼这种物品。这些最初的史料主要来源于外国人聚居地,即沿海沿江的港口城市,包括中国的澳门、广州、厦门、上海、哈尔滨和青岛,日本的长崎、横滨与东京等。啤酒在区域内的最初消费者还是这些来到“大门口的陌生人”。但因为传入渠道的多样化,啤酒开始从最初较为单一的译名变为五花八门的多个译名。这种现象在中国尤其明显,因为先后开放的门户城市较多,各地的方言差别较大,而统一性的词典又出现的较晚。同时,那些走出国门看世界的外交官与知识分子又从另一个渠道增加了对啤酒的见识以及相应的译名。
在这些中文和日文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爱尔和拉格啤酒在内的各种啤酒,这是因为离拉格啤酒占主流的19世纪晚期还有一段时间,随之呈现的也是更为多样化的译名。
东亚区域内啤酒译名的单一化与全球范围内拉格啤酒的大规模生产几乎同步,这种工业化热潮也催生了东亚本地的啤酒产业。也与工业化的先后顺序相同,日本的啤酒业要早于中国的本土产业,译名的统一过程也更早。在外来词单一化与啤酒生产标准化的同步演进中,日本也开始影响东亚其他区域。但正如最终的译名所示,日本并没有成为东亚啤酒译词与产业区域化的标杆,中国的啤酒译名确定过程足以为证。
二、“啤酒”与“皮酒”
根据译名的形式,啤酒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9世纪70年代前为啤酒引入阶段。啤酒的消费群体主要还是驻地外国人,啤酒的最初译名源于与洋人打交道的国人。译名多出现在语言教材中,也同时出现在海内外见闻中,译名的多样性是多传入渠道的一个必然结果。“啤酒”一词出现在这一阶段,广东以及沿海城市为主要传播区域。(2)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啤酒进口与外国厂商本地生产阶段。“皮酒”一词出现,先以上海及周边地区为中心,后流传到其他区域。(3)20世纪20年代之后:啤酒的本地生产逐渐展开,啤酒的译名也开始统一,市场偏好受到厂商与媒体的左右,其影响力超过书籍以及政府的宣传。啤酒逐渐得到消费者认可,但市场还主要分布在全国各大口岸城市。
“啤酒”是由两个固有汉字组成的复合词,“啤”取西文对应词的发音,“酒”则指物品种类,两个字的结合兼有全球化与地方化的效果。虽然“啤”字早就运用于书面语中,①王赛波:《大型字典“啤”字音义补释》,《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1期,第123—124页但“啤酒”这个译名确实是从口语中产生的,较早的文字资料也显示出选字的过程。“啤酒”更可能是最早接触这一舶来品的广东人采用的译名。也因为这种日常用语渊源,“啤酒”的译名先是出现在口语教材中,之后才被收入词典中。
迄今所知最早出现“啤酒”一词的资料是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这是一本粤语口语教材,1828年在澳门地区出版。书中的有关词条是:“啤酒,中国并不存在;中国人称之为‘卑酒’,就是啤酒,‘细卑’,低度啤酒;‘大卑’,高度啤酒,就是波特。”这里用的是“卑”字,但在另一处关于“Sei pay”的解释中,作者使用了“啤”这个字,即:“细啤,广东话中的低度啤酒,或者是对啤酒的总称。他们称波特啤酒为高度啤酒。”②R.Morrison,A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ingsley Bolton),早期粤语口语文献资料库(Early Cantonese Colloquial Texts:A Database),http://143.89.108.109/Candbase/,2019年3月20日。马礼逊强调了啤酒的外来性,并混用了“卑”与“啤”字。书中所提到的波特啤酒确实主要来源于英国,而根据酒精度来划分啤酒的方法也多见于英国,这可能是“啤酒”一词英文渊源的一个证明。
几乎同时,出现了关于中国人喝啤酒的记载。当然,国人对啤酒的最初评价是负面的。1830年,就职于广州旗昌洋行的美国人在商馆举行宴会,邀请当地盐商罗家的儿子来吃“番鬼”餐,同行的还有一位叫罗永(音译)的中国人。事后,罗永在给北京亲戚的信里描述了这次宴会,提到了啤酒:
乳酪(Che-Sze),用来就着一种浑浑的红色的液体吃,这种液体会冒着泡浸出杯子来,弄脏人的衣服,其名称叫做啤酒(Pe-Urh)。①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原信已经被翻译成英文,其中啤酒一词用的是广东英语,基本特征是将单音节的外文词汇分解,加入辅助音节,以适应当地人的发音习惯。根据信中的描述,宴会中喝的应该是一种爱尔啤酒。
当时,普通人喝啤酒的体验还是非常少见的,与啤酒接触更多的还是来自在洋人家庭里做佣人的中国人,之后出现的多本口语教材收录的也多是主仆之间的对话。丹尼斯在《初学阶》中就指出啤酒一词源于中国仆人,是音译加物品种类的复合词:
“啤酒”,如同其它复合词一样……是用来说明外国物品的混合词,就是用来指代物品名称的发音。练习中会不可避免的遇到这些词,因为这些词都是在中国仆人中使用的。②N.Dennys,AHandbook of the Canton Vernacul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Hong Kong:China Mall Office,1874,p.16.
如上,早期广州或澳门地区的粤语教材中,多使用“啤酒”这个单一译名。期间,少有的“大麦酒”名称则来自曾在中国各地生活过的英国翻译官罗伯聃,他在1843年的《华英通用杂话》中将“beer”注成“大麦酒 必而切”。③R.Thom,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1843,p.29,https://nla.gov.au:443/tarkine/nla.obj-49757619,2021年2月1日。
上海开埠以后,啤酒也随着外国人的脚步来到这个日后最大的贸易中心,国内最早的啤酒酿造记录也出现在上海。④Great Fermentation in China,22 Feb.1868,p.245.19th Century UK Periodicals,http://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5PV850,accessed 27 Oct.2017.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外贸易量的猛增催生了上海的洋泾浜英语。与广州英语类似,国人最初是使用当地方言的发音来给外语注音的;但与早期的粤语英文教材不同,很多教材出自国人之手,可以看出国人对于中外交流越来越热衷了。其中,杨勋以吴音编著的《英字指南》记录了啤酒在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译名,即“皮酒”,采取“皮酒Beer皮挨”的译名-英文词汇-注音形式。⑤转引自田野村忠温「啤酒の謎の解─この不可解な名称の成立過程」、2021年2月19日。而在这些外语教材出版前后面世的吴地小说和媒体中也多采用“皮酒”的译名,并描绘了上海人吃洋餐、喝啤酒的场面,显示出啤酒在这些开埠的城市中已经有了相当的接受程度。由于上海在中西文化与经济交流中的引领作用,“皮酒”这一译名还曾经后来居上,在20世纪初超过了“啤酒”的使用率。⑥在20世纪上半期,上海的啤酒运销量也居各大城市之首。刘群艺:《中国酿造学社与近代企业网络组织的初步考察》,《企业史评论》2020年第1期,第108—136页。
随着参与中西交流的人越来越多,对啤酒的命名也逐渐开始多样化了,特别是那些睁眼看世界的知识人,使用了多个译名。魏源参考了马礼逊的文献,在《海国图志》中使用了“啤酒”一词,比如提到德国与荷兰的酿酒状况,“荷兰薯更多,即每年用千三百五十万石,以蒸酒二万万樽,所造之啤酒过其数”。⑦魏源:《海国图志》第3册卷五七,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594页。而在《欧游随笔 使德日记》中,作者就用“皮酒”来描述德国的饮酒盛况了,这可能与李凤苞出身于上海有关。⑧钱德培、李凤苞:《欧游随笔 使德日记》,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184页。知识人的创造力是超乎想象的,在《近现代辞源》一书中收录的啤酒译名就有近20种,除了上述译名之外,还有啤儿、比耳、比而、皮卤等等。①黄河清编著:《近现代辞源》,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575页。
随着国内开放口岸的增加,啤酒也出现在越来越多的方言以及多语种教材中。席雷格编纂的《荷华文语类参》为荷兰语“bier”提供了“酠”“麦利”“麦酒”和“啤酒”四个译名。②“麦利”是一个字,麦加利,音为“lī”。G.Schlegel,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met de transcriptie der chineesche karakters in het Tsiang-tsiu Dialekt Hoofdzakelijk ten behoeve der Tolken voor de Chineesche Taal in Nederlandsch-Indiëbewerkt door Gust,1886,https://bildsuche.digitale-sammlungen.de/index.html?c=viewer&l=ro&bandnummer=bsb00073491&pimage=00110&v=100&nav=,accessed Aug.13 2019.杜嘉德编纂的《厦英大辞典》(1873年)将“麦”的厦门发音标的是/beh/,相应的啤酒发音就是/beh-a-chiu/,使得“麦酒”不仅具有意译,而且兼有音译的特征。在法汉词典或语言教材中,多出现与“大麦”的组合,如《法汉常谈》中的“大麦酒”和《法华字汇》中的“大麦水”。港口城市宁波则贡献了“苦酒”的叫法。③W.Morrison,An Anglo 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on Press,1876,p.39.
表1列举了各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英文字典。这些字典虽然只列英文单词,但却包含了几乎上述所有的译名,反映了当时中国开放区域的文化和经济交往热度。其中第一阶段的词典都来自洋人作者,既有广东早期的单译名,也有多语种和多语言环境贡献的不同译名;到第二阶段,国人开始积极编纂外语词典。来自广东的邝其照和来自上海的颜惠庆确实采用了更具有地域特征的译名,也收录了beer一词的灵活运用,并将渐显优势的拉格单列出来;第三阶段则开始出现统一译名的趋势,有些许官方背景的词典《官话》选择的是“啤酒”与“麦酒”。

表119世纪—20世纪初主要英汉字典中的啤酒译名
从区域角度来看,“啤酒”与“皮酒”仅在我国有普遍的使用记录,可以确定两者的国内语源,但“麦酒”虽为汉籍词,因为有对应的日语词汇,难于明确其产生区域。啤酒与麦酒在我国并用的时间较长,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两国都没有选择这一译名,而只有曾受日本殖民的韩国以“麦酒”为译名。
三、“麦酒”与“ビール”
正如前述,17世纪的驻日荷兰与英国商馆并没有留下关于啤酒消费的日文记载。直到18世纪初,史料中才有了啤酒的日语名称,这也同样是初次体验啤酒的日本人留下来的。
1724年,驻日的荷兰商馆馆长赴江户幕府询问通商事宜,同行的日本翻译记录了这些荷兰人的衣食起居,辑为《和兰问答》,其中一条提到啤酒:
酒用葡萄做,也用麦子做。我喝到麦酒时,感觉不怎么好喝,就问(“荷兰人”——作者注)这是什么酒,说是啤酒。①今村明恒『蘭学の祖今村英生』、朝日新聞社、1942年、337頁。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得知,品尝啤酒的日本人知道啤酒是用麦子原料酿制的,就使用了麦酒一词,以表明酒的原料,而段末的“啤酒”一词实际上是用片假名标出的荷兰语发音(ヒイル,音/hi-i-ru/)。这种同时标注意译词与音译词的习惯也延续到了之后出现的外语词典中,例如1798年出版的荷日词典《蛮语笺》中的词条就是“bier:麦酒,ビール”,②キリンビール『ビールと日本人—明治?大正?昭和ビール普及史』、河出書房新社、1988年、第40頁。1814年英日词典《谙厄利亚语林大成》则是“beer:べール 麦酒”等。③本木庄左衛門『諳厄利亜語林大成』、1814年、国文学研究資料館、ht t p://base1.nij l.ac.j p/iview/Fr ame.j sp?DB_ID=G0003917KTM&C_CODE=0091-027502、2019年8月24日。
啤酒在日语中的英语音译最初为“ベール”(音be-i-ru),而非“ビール”(bi-i-ru)。这是因为日本模仿荷兰(1770—1860)在先,后又开始模仿英国(1860—19世纪末),日语啤酒的音译名也首先来自荷兰语,这一语源影响到了之后的英语译名。荷兰语的“ee”发/ei/音而非/yi/音,在看到英语“beer”一词时,日本人也就想当然的先按照荷兰语的发音规则来标记了。
当时英国啤酒在日本留下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迹莫过于爱尔啤酒的译名(エール)了。英国产的巴斯牌(bass)爱尔啤酒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盛行日本,其商标“赤△印”(红色三角标)甚至成了爱尔啤酒的一个代名词。但这爱尔啤酒的热潮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从19世纪末期以后,日本又开始转向模仿德国体制,民众原本对英国啤酒的热衷也转向了德国啤酒,特别是当时更为普遍的拉格啤酒(ラガー)。
因此,日本人较早区分了爱尔啤酒和拉格啤酒,并分别以两者的音译词来称呼,而以“麦酒”或“ビール”来作为啤酒的总称。但与我国类似,由于爱尔啤酒较早进入日本市场,早期的麦酒更多指称爱尔。在爱尔啤酒近乎消失之后,“麦酒”和“ビール”都基本专指拉格啤酒了。
从18世纪起,日文词典就将啤酒词条收录其中,这就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译名选择。开港后周游世界的日本外交官与知识分子也就没有贡献更多的译名,而仅仅停留在“麦酒”或“ビール”的各种音译变形上。④例如“麦酒”存在“バクシュ”的音读与“ムギサケ”的训读等差别,见キリンビール『ビールと日本人—明治?大正?昭和ビール普及史』、3-37頁。啤酒译名最终定为“ビール”则取决于产业、市场与媒体的影响力了。
日本啤酒产业的展开有民间与官方两个途径。早在1872年,野口正章和涩谷庄三郎就分别在甲府和大阪开始酿造啤酒,以“ビール”为名。
相比之下,官方背景的啤酒产业多采用“麦酒”译名,如建于札幌的官方啤酒厂——开拓使麦酒酿造所。主持这个项目的是曾在普鲁士学习酿造技术的中川清兵卫,他在1877年成功酿出适合日本人口味的“冷制麦酒”,其实就是清爽的下发酵拉格啤酒。1877年9月,在日本各大报纸上刊载了“札幌制麦酒”的广告。日本的啤酒官方研究机构与啤酒立法也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出现。例如1901年的《麦酒税法》第一条称:“依据本法对麦酒(ビール)征收麦酒税。”①「麦酒税法」、内閣官報局、『法令全書.明治34年』、23-25頁、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788021/21、2019年8月19日访问。其中麦酒采取了括号中加注“ビール”的做法,但1908年《麦酒税法改正法律》取消了这一加注,只采用“麦酒”的名称。可见,日本官方以“麦酒”为首选译名。
早期创立的日本啤酒公司多采用“麦酒会社”的名称,这也与其官方背景有关。辞官下海的涩泽荣一就先后参与了多家麦酒产业的经营,包括直接起源于开拓使麦酒酿造所的札幌麦酒,市场整合后的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以及分立后的日本麦酒与朝日麦酒公司。而另一家啤酒巨头麒麟麦酒公司,虽然起源于外国人建立的天沼酿酒公司(Spring Valley Brewery),但后来也被日本人接手,并在经营中受到涩泽的影响。可以看到,这些啤酒巨头们在创立和发展期都采用“麦酒”作为公司名称,之后才改用国民更熟悉的音译名称,改名的时间有的在战后,有的则迟至20世纪80年代(见图1)。

图1 日本啤酒企业变迁图
但是,日本媒体并没有跟随官方的选择。在《朝日新闻》历史数据库所显示的标题与关键词中,“ビール”的使用量要明显多于“麦酒”。只是在二战期间,“麦酒”曾经逆风上升,有取代“ビール”的趋势,显示出政府在战争期间的强大影响力。但随着战争的结束,“麦酒”的使用量骤减,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基本不见踪影。
“ビール”胜过“麦酒”的一个原因还应该归于民间的去汉字化倾向。这个倾向从明治维新开始,到二战后更得到占日美军的支持。②秀茹『日中両言語における外来語の対照研究』、博士学位論文、広島市立大学大学院国際学研究科、2013年。直至今日,连“麦酒”的日语发音也改为“ビール”了。
麦酒译名虽然在日本国内没有保留,但在日殖的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却有所保留。韩国直到今天仍采用“麦酒”译名,台湾地区则是先并用“麦酒”和“啤酒”,在光复之后恢复了“啤酒”名称。两地在被殖民期间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比如都是先为当地的日本人进口啤酒,后改为本地生产。1919年日本人安部幸之助在我国台湾地区建立高砂麦酒公司,1933年大日本麦酒在韩国建立朝鲜麦酒公司。所不同的是,台湾地区与大陆的中文联系更紧密。
在我国台湾地区被殖民期间,虽然在中文或日语新闻媒体中普遍使用麦酒一词,但在知识人日记中出现的啤酒一词要多于麦酒,甚至出现了日语词加啤酒的台式组合用法。①例如黄旺成日记中出现的“カブト啤酒”,1914年7月30日,台湾日记知识库,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2019年8月24日。这种源自民间的坚持也直接影响了译名的更迭。殖民期结束后,使用啤酒一词的转换过程迅速而彻底。根据啤酒专卖制度的官方文件,由“麦酒”到“啤酒”的转换发生在1946年,②“民国三十五年啤酒配给关系”,台北“总督府专卖局”,档案典藏号00112793001,册号12793。被派去接收啤酒厂的朱梅也记录了这一变化。③朱梅:《为官一年》,《世界月刊》1948年第2卷第9期,第40—48页。
相较于我国台湾地区,韩国采用麦酒一词的时间更早,因为早在甲午更张之前,韩国就开始模仿日本的近代化制度。许多韩国的知识人或官僚去日本考察,留下了包含麦酒一词的考察记录。④(韩末韩国人日本观光团研究),2005→107,,2005.从本土来源来看,现在可见较早用“麦酒”指称啤酒的新闻报道来自1883年12月20日的《汉城旬报》,其中登载的“海关税则”显示:“红白葡萄酒、麦酒的关税率为价格的10%”,⑤(大韩民国新闻数据库),http://www.nl.go.kr/newspaper/.说明当时已经开始进口啤酒。但在20世纪之前,“麦酒”在新闻中的使用量较少。在甲午更张之后,使用量才有一个骤然的增加。一战期间,新闻媒体中麦酒一词的使用量又有大幅下滑,显示出使用频率与贸易量的直接相关性。一战后,麦酒一词又开始频频出现在报纸中,特别是在朝鲜麦酒公司建立之后。二战后,麦酒一词在媒体中基本消失,直到20世纪70年代本土啤酒公司建立,“麦酒”的使用量才逐渐增加。可见,“麦酒”在日本吞并韩国之前就已经在韩国本土成为一个固定译名,使用频率取决于贸易或者本地生产的数量。直到今天,啤酒在韩国仍被称为“”,即麦酒的韩语发音词,日本的殖民统治在韩国留下了深深的啤酒印记。
四、“啤酒”“皮酒”和“麦酒”
1868年2月22日,路透社发布一条名为“中国伟大的发酵事业”(The Great Fermentation in China)的快讯,宣布在上海成功酿造出啤酒,还同时附上一首小诗,慨叹原来盛茶的杯子里装上了啤酒。⑥Great FermentationinChina,22Feb.1868,p.245.19thCenturyUKPeriodicals,http://tinyurl.gal egroup.com/tinyurl/5PV850,accessed27Oct.2017.这首诗在赞美外国人酿造啤酒这一行为的同时,还不忘嘲笑一下中国人,满是殖民者居高临下的姿态。这是因为当时确实还没有一家中国人的啤酒厂。殖民者的这种姿态延续至了20世纪20年代,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国人投资的啤酒厂开始形成气候,啤酒也在同一时期进入普及阶段。⑦马树华:《啤酒认知与近代中国都市日常》,《城市史研究》2016年第35辑,第163—196页。同时,啤酒的译名开始逐渐向“啤酒”集中,舍弃了同为本土语源的“皮酒”和日本使用的“麦酒”译名,这种集中的动力也同样来自市场与媒体。
“麦酒”其实是取自汉籍的一个词语,指用麦类做原料酿造的酒。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出了麦酒的语源:
麦酒者,以大麦为主要原料。酿制之酒,又名啤酒,亦称皮酒……后汉范冉与王奂善。奂选汉阳太守,将行,冉与弟协步赍麦酒,于道侧设坛以待之。是麦酒之名,我国古已有之。蒋观云大令智由在沪,每入酒楼,辄饮之。①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饮食类·麦酒”,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325—6326页。
在文中,徐珂引用了《后汉书》中提到的麦酒事例,并以麦酒为啤酒的首选名称,而且也没有点明啤酒的舶来品性质。这与他在前一个词条“葡萄酒”中的介绍形成鲜明对比,似乎将麦酒作为一种非舶来品了。文中还提到蒋智由喜欢在酒楼喝啤酒,显示出民国初年上海消费者对于啤酒的认可度,加深了啤酒源自本土的印象。
由于中国开始称“啤酒”为“麦酒”的时间晚于日本,很难说这个译词是国人的发明还是借鉴于日本。但可以确知的是,当时游历日本的中国知识人普遍将在日本看到的啤酒称为“麦酒”。这些指称有的是由于直接引用日本麦酒公司的名称所致,例如刘学询《考察商务日记》、沈翊清《东游日记》、吴汝纶《东游丛录》、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等。而另外的应用,则是在记叙日本见闻时,把啤酒作为新事物进行介绍,例如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的介绍:“欧洲中有一种葎草,制麦酒者用之为味”,“酒则葡萄酒、麦酒、花酒、果酒、香迸酒”。②黄遵宪:《日本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577、2543页。甚至也有人把“麦酒”的名称用于描述欧洲的啤酒与啤酒厂,例如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所述:“观麦酒公司。此公司极大,欧洲推为麦酒公司中第一家”,又“询知丹国以农、牧为立国之本……又有麦酒酿造所、瓷器公司,麦酒常运至中国,此皆其国之名产云”。③蔡尔康、戴鸿慈、载泽:《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出使九国日记·考察政治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443、439页。
就连对日语译名颇有微辞的严复也多次使用了麦酒一词。④亚当·斯密:《严译名著丛刊 原富下》,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68页。看来麦酒在知识人圈中耳熟能详,也因为其汉籍来源,并不被认为与日本有瓜葛。
与日本政府类似,清末的官方也多采用“麦酒”一词。1909年,清政府下设的学部设立编订名词馆,由严复任总纂,其成果大部分收入赫美玲的《官话》之中。《官话》将“黄啤酒”加注“新”,并列举“麦酒”为同义(见表1)。另外,《大清光绪新法令》的“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细目”,其中使用的就是“麦酒”,为“三十七、酿造物及饮料:酱油、醋、葡萄酒、麦酒等”。
但是,知识人与官方采用的“麦酒”一词并没有在媒体中占主流,反而先是“皮酒”、后为“啤酒”更多出现在媒体中。
根据表2所列《申报》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啤酒”和“皮酒”的使用量要远远多于“麦酒”。⑤为了防止《申报》发行地域与新闻来源地有限所导致的偏向性,作者也对《全国报刊索引》进行了检索,结果与《申报》的结果类似,但因为给出的结果不如《申报》的年份更为具体和连续,所以此处采用《申报》的结果。这其中有“啤酒”和“麦酒”同时使用的记录,集中于1914年—1915年与1920年—1936年间。例如1935年4月5日“工部局审核酒馆请照事件”,提到“售卖啤酒麦酒之营业执照,每年须行审核一次……啤酒麦酒售卖者,有南京路二十号、福煦路八四六号、静安寺路九九零号、成都路四九零弄三号、威海卫路一六六号各家”。还有“皮酒”与“麦酒”同时使用的记录,较为分散,但都在1932年之前。值得注意的是,“啤酒”与“皮酒”共同使用的记录较少,因为两者是明显的替代关系。对这两个词的选择则主要是由厂商与广告商来决定的。最初常用的是“皮酒”,而非“啤酒”,⑥例如入乡随俗的日商在1914年以“太阳皮酒总厂”注册,后在1920年改为“太阳啤酒公司”。《上海指南》卷六“实业丁各类店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但从20世纪初开始,产品的普遍认知与译名的统一开始同步。新进国产啤酒商开始频繁刊登“啤酒”为名的广告,最终使得“啤酒”代替“皮酒”而站稳脚跟。之后,“啤酒”一词不仅仅限于广告用语,也成为新闻的首选译名。

表2 《申报》中皮酒、啤酒与麦酒等词汇的使用量
对于这一趋势,也可以从《皇朝续文献通考》中得见:
啤酒又称皮酒或麦酒,种类亦多,制法亦歧,主要不外麦芽、蛇麻及水三者。我国之酿造啤酒始于光绪二十七年俄德两国商人在东三省所合办之哈尔滨啤酒公司。至光绪三十年,英德两国商人在青岛合办之啤酒酿造股分[份]公司亦告成立。见在东三省、天津、北京、上海、青岛均有啤酒酿造厂,为数虽不少,而国人以习惯关系需要有限,加以外国输入从中相竞,故此业今尚在幼稚时代。①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五《实业八》,见《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8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与《清稗类钞》不同,这里是把“啤酒”作为主要名称,使用顺序优于皮酒和麦酒,原因可能就在于同时列举的这些啤酒厂。这些啤酒企业,如果使用中文名称,都多以“啤酒”为名,除了上文提到的外资酒厂之外,还有1914年创立的北京双合盛啤酒公司、1920年烟台醴泉啤酒公司以及1935年广州五羊啤酒厂等。也由于拉格啤酒在全球啤酒业中的优势地位,这些啤酒公司都以拉格产品为主,极少生产爱尔,“啤酒”一词多泛指拉格。
当然,“麦酒”也还是有影响力的。按照表2中的《申报》使用量统计,最多的时段是在一战期间,因为当时日本麦酒株式会社收购了青岛啤酒,在《申报》上刊登了大量的广告,导致“麦酒”的使用量增加。另外,日本在一·二八事变后对上海的占领也使“麦酒”与“啤酒”同时使用的数量增加,出现前文所述的工部局管理规定等并用的实例。日本啤酒商也同样以拉格为主营产品,与国人经营的啤酒厂形成竞争,就如同“啤酒”与“麦酒”译名并用的局面。
“啤酒”与“麦酒”两个译名并存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在1949年出版的英华字典中,“beer”词条仍为“啤酒、麦酒”的形式。②辞典编译委员会:《英汉新医辞典》,杭州:新医书局,1949年,第150页。1949年之后,随着众多啤酒厂的改制,以及《青岛啤酒生产法》等技术手册在全国的推广,麦酒才逐渐不再指称啤酒了。
五、结 语
从“啤酒”译名的形成过程来看,这种舶来品的全球史可以归纳为传播过程中物与名的联动过程。随着“物”由外而入内,名称的实施者与承载文体也随之变化,即从单纯进入(殖民者,日记/游记)→进口(殖民者商人与本地商人,语言教材/字典)→本地生产(在地外国生产者与本地厂商,新闻)→出口(在地外国、本地厂商与本国政府,技术指南与法规)。这一传播过程与抽象名词的定名过程有所不同,以生产为最终环节,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市场比知识人对其译名更有影响力。
从现知的资料来看,中文译名“啤酒”源于广州十三行贸易期间的英语语境,之后开埠的上海地区贡献了“皮酒”这一名称,两者都属于音译加意译的复合词。在啤酒传播过程中,多渠道以及多语言环境也催生了众多译名,但都多以音译为主,意译为辅。“麦酒”一词的使用有知识人和官方背景,而本地啤酒厂商以及新闻媒体最终选择的还是“啤酒”。
日本先兰学、后英学、再德学的西学史,也同样投射在啤酒译名的选择过程中,“ビール”的语源是荷兰语。日本人对啤酒的认知较早,也就避免了海外出行的知识人贡献五花八门的啤酒名称,外语词典中的词条也只是列举了有微小差别的音译名以及“麦酒”的不同读音,之后市场的力量加上去汉字化的倾向将“麦酒”这个意译名直接剔除了,最终集中于“ビール”。
日本的殖民过程与汉字文化圈身份确实将东亚的啤酒史联系到了一起,但并没有藉此促成译名的统一化。韩国将“麦酒”而不是“啤酒”收入囊中,但我国台湾地区并没有偏向“麦酒”,选择“啤酒”具有克服殖民影响的意义,克服的动力还是源自民间的力量。日本对于中国近代啤酒业的参与也影响了啤酒的译名,但“麦酒”的存在是暂时的。
之所以能在众多酒精饮料中取得一席之地,啤酒的吸引力不可小觑。从东亚的传播过程来看,东亚消费者从对啤酒的排斥到形成消费习惯大概用了百年的时间。沿海沿江地区的变化较快,海岛国家日本接受啤酒的速度快于中国。在啤酒业完成工业化之后,拉格啤酒也席卷了东亚,并促成了啤酒译名的最终确立。这种全球化的力量也以区域流动的形式存在于东亚,表现为区域市场与文化要素的互动。正如全球化要面临地方化的反动一样,舶来品的译名也说明先行工业化国家在某些领域并不能施加绝对影响,因为在全球和区域消费网络之中,每个地方都是联结网络的纽带。
衷心感谢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内田庆市与沈国威、关西大学文学研究科一濑雄一、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周呈奇、伯尔尼大学毛新愿提供的观点启发与研究资料协助。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毛泽东主席关怀清华
-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与对策建议
-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新公共治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