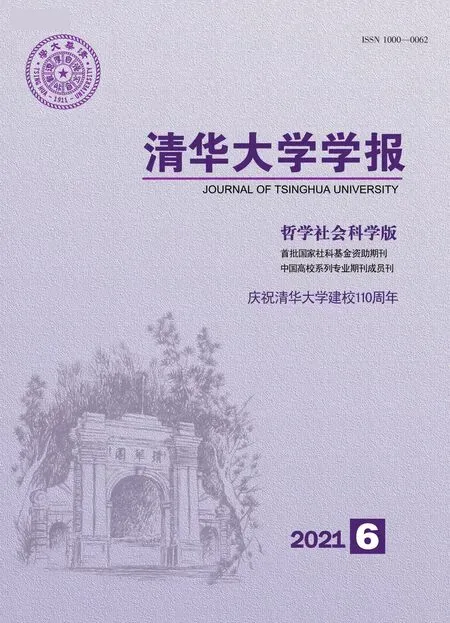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新公共治理原则
蓝志勇
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意涵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由“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y Forum)创办人和执行董事长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2016年1月15日开始的达沃斯(Davos)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①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以基金会形式成立的非营利组织,成立于1971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州科洛尼,创始人就是克劳斯·马丁·施瓦布,德国籍但久居瑞士的工程师和经济学家。他拥有弗里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工程学博士学位以及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学位。1972年,他成为日内瓦大学年轻的教授,荣获多项国内外荣誉。他的论坛根据“瑞士东道国法”于2015年1月获得正式地位,被确认为国际公私合作机构,每年冬季在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举办的年会,聚集全球工商、政治、学术、媒体等领域的领袖,讨论世界所面临最紧迫问题。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提法,在这个会议上提出,自然会受到媒体、工商领袖、学者和政治领导人的关注。他的新书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会议前几天的1月11日出版(Schwab,K.,2017)。他不拘泥于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的划分(Toffler,A.和Alvin,T.,1980),只关注工业革命后的分期。这一提法,在短短的时间内,风靡全球,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克劳斯·施瓦布认为,从1760年到19世纪初这一段时间内,欧洲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工场、②当时不少地方还不叫工厂,是沿袭下来的工作坊改造而成的有一定动力的集体工作场地(works or work place),后逐渐过渡到组织完善的工厂(factory)。纺织厂、轮船、火车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19世纪,工业革命的中心移到了美国。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钢铁、石油、电、电灯、电话、内燃机等新技术和流水作业线管理等现象大批涌现,时代创新的代表人物是爱迪生。这些技术推动了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被认为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表现。第三次工业革命被认为始于20世纪60年代。核心技术是数字革命、半导体、芯片技术、计算机、互联网等的发明和运用。进入21世纪,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始了。这次革命的核心是数字革命、生命科学革命和物理产品革命的齐头并进,数字世界与物质世界和生命世界深度融合,从信息化走向智能化,进而形成以数字算法驱动的、高度灵活的、人性化的产品生产与服务模式。物理技术、数字技术和生命技术的融合,不但改变了人们的客观世界(产品和生产工具),还在改变生命的组成和人本身(基因复制和器官再造)。表征的技术现象是:物联网(IOT)、大数据、区块链(Block Chain)、人工智能(AI)、自动驾驶(AV)、声音指令驱动(Voice Activated Assistance)、人脸识别(Facial ID)、纳米技术(Nano)、生物技术、材料科学、能源技术、量子计算健康跟踪(Health Sensor),基因修复(Human Geno Restructuring),3D打印(可以器官再造)等等。这些过去难以想象的新产品和新方法,开始更加迅猛和深入地改变人们的生活,甚至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Schwab,K.,2017)。
这几次工业革命,一次比一次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间,有100多年的时间。从电话的发明到电话拥有一亿用户,用了75年。而“脸书“(Facebook)的一个在线图片和视频分享软件“线上分享”(Intagram),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拥有了同样多的用户。精灵宝可梦(Pokemon Go),一个全球性的免费手机游戏,在2016年6月发行一个月后,就有了一亿用户,遍及五大洲。再比如3D打印机,2015年投产年只卖出了200台,到2020年,卖出的产品是240万台。3D打印已经可以打印牙齿和人体骨骼的替代品,更不用说打印建筑器材,也包括可回收民宅本身,市场发展前景广阔(Elizabeth,2016)。国内外,网络直销,抖音小视频,传播的速度也令家长防不胜防。
虽然很多新技术目前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但在信息技术大发展,物理、数字和生物技术深度融合、相互激励和推动的条件下,所有的行业都受到了冲击。新商业模式、生产运输模式、消费模式、交易模式、支付和投融资模式、学习和教育模式、医疗模式、交通模式等等,都开始显现出被颠覆性重塑的迹象,全方位给人类的未来带来难以确定的影响。
二、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当前公共治理的挑战
人类的夙敌有自然灾患,饥饿,瘟疫和战争。农耕技术和医药卫生的发展,特别是国家组织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战胜这些夙敌的能力和机会。二次大战后世界在雅尔塔体系下建立了联合国,人类大规模死于灾患、饥饿、瘟疫和战争的概率已经大大减少了,是文明和治理的结果。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被解决,战争、瘟疫、垄断市场和强权政治导致的分配不均与饥饿的风险依然存在,在协调不好的情况下时有发生。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就是一个协同不足的鲜明案例。有些作者甚至感到悲观,认为人类文明能够在21世纪后继续生存下来的概率只有50%,恐怖主义、生态环境退化、全球升温、技术变化,都是潜在的威胁(Rees,M.,2004)。全球畅销书《未来简史》作者尤瓦尔也说,21世纪的人类世界依然必须面对几大严重的挑战:核战争、地球生态的持续恶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事实上,前两项都是第三项发展的结果。科学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也带来了更大的潜在性风险。他说道,如果人类在掌握今天的高科技的条件下,还按历史上强者为王的丛林之法巧取豪夺,进行战争,那么,人类是有能力毁灭地球,毁灭自己的(尤瓦尔·赫拉利,2017)。
今天的世界与死伤过亿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已经久远,①二战死亡者近9千多万。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World_War_II_casualties。战后下定决心要走出传统的意识也逐渐减弱。在全球化的今天,又出现大国领袖往后看,运用传统封闭性思维,搞单边霸权主义,强化传统地缘政治,推动造墙、退群、高壁垒、内卷等逆全球化的运动的现象。原因其实很清楚,他们学习不足,对历史没有正确的了解,②当年小布什对伊拉克展开反恐袭击时,竟然提出要像千年以前的十字军东征一样去攻打伊拉克。特别是,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带来的社会变化和全球治理的挑战不能理解,并怀有深深的恐惧:这么多好的技术,被偷窃了怎么办?这么广泛的文化交流和意识形态冲突,输了怎么办?全世界都在学习和进步,超过了自己怎么办?核武器、战争机器人、基因改造等等,我不做,别人会做,那我必须做得更好,才有安全感。如何妥善应对这些恐惧感,是未来人类安全的关键所在。有哲人表示,除了霍金所说的难以遏制的陨石坠落,人类最大的威胁或许还是自己的愚昧,缺乏合作共赢的包容心,缺乏应对自己内心恐慌的合适方法。
科学技术是重要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生产力的改变,必然要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变,进而带来上层建筑的改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1995:32— 33)因为这一发现,使马克思走出困惑,人类走出困惑,能更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正确把握人类社会及各阶段变动及依次更替的运动规律。
马克思的这一段经典论述,清楚说明,人们的意识由存在决定,而存在中不断变化和能动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变化,必然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但旧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在变化中失去原有的优势地位,会努力抵制、操纵、引领或者异化这样的改变,从中获利或得到新的好处。这两股力量的博弈就是全球治理改革博弈的最前线。
新技术在带来巨大生产力提升的同时,对未来文明社会的威胁也越来越清晰。有数据显示,当前顶尖的40项颠覆性新技术中的80% 是由少于人口1%的亿万富翁们投资获得的,他们已经手握全人类50%以上的财富。如果说对未来技术专利的拥有会决定未来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那么,掌握新技术的阶层,必然是新时代的主宰。英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了过去一个世纪工业化过程中的财富分配情况后指出,按照过去的国家治理和市场运行方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内,贫富悬殊一直在加大,只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财富的分配有过短暂的趋平现象(Piketty,T.,2013)。而新技术革命,更有扩大这种差异的趋势。具体来说,人工智能提高了生产力,但会带来大规模的就业替代,机器人战士会带来规模性的战争杀戮、而基因技术更会带来生命的不公,这些都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被很好认识的问题。未来的世界,被机器替代的人中很大一部分人或许会成为不相干的“无用之人”,或不值得长寿的无足轻重的人,他们的意见甚至生命权,还值得被关注吗?如何关注?而谁将是做出这些决定的人呢?
特别是,新的感知技术带来的对人的私密空间的侵犯和行为控制,如视频监控、植入跟踪、穿戴设备和无所不在的区块链留痕等方法,使得个人的隐私权和隐私能力荡然全无。同时,在个人生命信息、家庭信息、情感信息、交易信息、消费信息、阅读和偏好信息及财务信息全部数字化的技术背景下,个人隐私被大企业、财团强权侵犯和全面控制的可能也越来越成为可能。信息该被谁掌握?如何使用?是新工业时代重中之中的问题。它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是人类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组织、组织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公共治理、国家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的治理问题。
在微观层面,新技术也在不断加大治理的难度。比如说,人脸识别技术的出现,在短期内提高了刑事案的侦破率,但很快又成为犯罪分子侵夺个人身份的新手段之一,成为高科技犯罪的工具;智能电子产品的涌现,让国家消费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和监管疲于跟踪;智能学习工具的出现,完全可能增大数字鸿沟;网络交易的规模和跨地区交易,让传统的属地管理方法变得束手无策……
总结起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给公共治理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一种挑战是现有生产和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和描述的物理环境变化带来的社会生产、生活和组织结构变化的挑战,如产品更新、市场结构改变、产业升级、就业替代、武器更新等等。这些属于需要适应技术带来的物质基础变化的挑战使得人们必须适应新产品、新技术、新生产组织方式和生活形态,如使用手机、穿戴产品、群居在密集的城区、适应远程但全息屏显的会议和工作环境、员工管理方式、组织文化塑造等等。这中间有一部分可以用技术解决,如强大的机器人战士可以用更强大的机器人或其他技术应对,人脸识别犯罪可以用更高级的防伪技术和侦察技术防患。但技术和物质环境变化永远是双刃剑,有利有弊,没有止境。人类还是需要用非技术和非物质的方法来解决技术变化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第二个层次的治理挑战——上层建筑必须相应变化、适应新技术条件的挑战,是人们意识到的技术带来的物质基础变化对原有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挑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生产方式与社会分配和社会福利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教育与创新的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构建新的法律条文,甚至改变对文化和生命意义的认知。第四次工业革命之所以说是史无前例,因为这革命中的物理技术、数据技术和生命技术结合产生的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巨大的仿真效果,或者说是“以假乱真,以假替真,使假成真”的效果。这一技术能够改变人的智慧、器官,甚至人本身,在能力、智慧和生命的长度上带来过去想象不到的变化,冲击人类已有的认知、法理和生命观,进入未来学家尤瓦尔所描述的从追求幸福到追求永生和直接成神的一种全新的生命形态(Harari,Y.N.,2014)。在过去,人类生命的产生是自然界的偶然,一旦存在,生命可贵,人人平等。而未来世界注重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自身自觉的生命意义。那么,是否不能有效参与生产和创新的人就不必存在?不懂得对生命意义追求者就不值得生活得长久或被进行基因修复?这对于推翻了奴隶制和阶级、种族的现代社会来说,又是一个颠覆性的新问题。如何应对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化的躁动,认识技术、管理技术、规范技术、掌控技术、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处理好技术带来的再分配问题、技术的有和无的关系、公民和社会权益问题、国内发展与全球化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是现代国家治理必须面对的刻不容缓的重大挑战。
三、第四次工业革命呼唤理论创新
传统国家治理理论基于组织结构功能理论,强调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科层结构的重要性和行政官僚的工具性(Weber,M.,2009)。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强调阶级斗争,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替代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用阶级压迫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当然,有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提出完整的国家理论,但他们对国家的本质,一直是有所关注并作出过精辟的分析的(列菲弗尔,1993:122)。他们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13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提到了国家阶级统治的本质:“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274)因此,当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首要任务是阶级专政,但最终的目标还是解放全人类,解放自己。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解决饥饿和贫困的能力逐步增强,阶级间你死我活的矛盾也由于物质生产能力的提升和物质需要的丰富得到缓解。在这样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成为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最爱,认为国家的目标是保护人权和自由,保护产权和维护自由的市场经济(Jefferson,T.,1952)。管得最好的国家,是对市场干预最少的国家(Reagan,R.,1986)。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推动政府改革,管理主义(Lan,Z.和Rosenbloom,D.H.,1992:535-537),新公共管理(Hood,C.,1995:93-109),新公共服务(Denhardt,J.V.和Denhardt,R.B.,2015:664-672),和去中心化的治理理论,甚嚣尘上,盛极一时。到现在为止,依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是由世界银行提倡的治理理论,提倡用公民和民间组织的力量,参与协作治理,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问责,强调以效率、效益、参与民主、法制、开放、透明、回应、问责、公众舆论、公平公正、有战略目标等为治理标准,追求民主、效率和高尚道德标准的善治(蓝志勇和魏明,2014:1—9)。事实上,治理的核心意义是“统治与控制”,从中文字面意思看,就是“统治和理顺”各种关系。但在过去30多年的行政改革中,西方改革的理论家们给“治理”一词赋予了新的含义——即推动社会各界的不同力量共同关心和参与本属于统治者(国家领导或组织领导)职责范围的工作,甚至提出要去中心化,强调社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协同治理(蓝志勇,2014:31—35)。
这一理论,虽然有广泛的认同,但由于其“后现代”和“去中心”的倾向,并不能被所有的政体广泛接受。治理理论的基础是经济社会高度发达、政治文化和规则有良好认同、群体自主意识和法制意识很高的社会环境。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发展的方向性、国内政治文化和政治规则都还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思想水平不同,政治认同感不足、不少经济生活还没有自由的人群,并没有时间、精力、知识、信息等参与国家治理,治理的提法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空中楼阁。因而,不同国家在运用治理这个概念的时候,内涵是十分不一样的(蓝志勇和魏明,2014:1—9)。在这种条件下谈论平等、透明、去中心的治理,是在构建难以实现的海市蜃楼。第四次工业革命,内涵是涌现性的新技术,潜在的危险是更大程度和规模的贫富差距、个人能力、发展机遇、甚至生存权利的差异,是传统的指令性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都没有解决、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新技术涌现提出的问题包括: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人工智能造成的对传统就业机会的替代,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在高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做到社会公平、公正与发展机遇平等?在技术创新为新常态的情况下,国家管理和技术规制能够如何跟上形势,有不会抑制技术创新的热情?在技术涌现的情景下,如何平衡社会的变化与稳定?在技术推动的生产力高速变化的过程中,如何迅速调整生产关系,乃至进行国家治理的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和适应性变化,未雨绸缪,超前思考和设计,迎接新技术时代的新挑战?新技术也会造成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技术拥有国和创新大国有赢者通吃的优势,而创新不足和技术落后的国家则越来越失去平等竞争、公平发展的机会。
总体来说,不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1975)还是新自由主义的放任经济理论,还是后来提出的后现代版治理理论(或者说治理模式),在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涌现型的技术环境条件下,都有力不从心之感。不论经典社会主义理论还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和模式的基础都是物质缺乏条件下的治理,或许这一现象还会由于上层建筑难以改变而继续存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但事实上,已有的技术,加上未来的技术,完全有可能让人类超越原有的治理基础,寻求新的突破。新技术条件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有能力消灭阶级,常态化的涌现性创新使得计划赶不上变化,而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难以解决的社会分配问题和公平发展问题在新技术条件下却更加难以得到妥善的解决。在技术优势集中在大财团或少数权利运行者手中的条件下,在有人能成神而有人可以变成无用之人的可能的条件下,谁来治理、如何治理、治理目标都需要全新的思考。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总结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治理的经验,以党的领导为基石,满足人民对美好幸福的追求为目标,五大发展理念和八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文化,灵活能动的行政改革为方法,推动新时代的新治理。与现代西方的前沿治理理论相比较,就是公共价值导向的新治理(Bozeman,B.,1987)。但这一构建新型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努力,还依然在改革的路上,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中国刚刚完成了全面脱贫的世纪工程,走在高质量发展的小康道路上,民生需求的压力、生态环境保护、创新需求、产业升级、国际竞争与责任的挑战,依然巨大。
中国自古有天下为公的大道之行的理想,①戴圣《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王文锦:《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但每每在朝代的更替和变化之中付诸流水。在两千多年文明史的岁月中,人们饱受贫困、战争、颠沛流离之苦的时间要长于享受富足、和平和稳定生活的时间。一方面,当然是生产技术能力低下原因,土地依赖性强;而更多的,则是王朝更替、强权兼并、内忧外患带来的困苦,是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冲突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末期,西蒙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一系列讲座,讨论“人为设计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认为工程、医疗、建筑和管理等学科都是人为设计和创造的学科,与传统自然科学学科有很大的区别,但他们往往又不得不遵循科学的思维范式,进行模式化的研究和思考。结果是,无法从一些迥异的场景条件下提出有普遍意义的因果关系的假设(Shangraw Jr,R.F.,Crow,M.M.和Overman,E.S.,1989:153-160)。
公共管理学者,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校长克罗博士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概念。他认为,公共管理应该是“设计科学”。需要根据变化的条件、情势描述,设计和重塑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就需要远见、敏感度、理念、原则和技巧。需要有一系列的设计原则,如,有求变的倾向,有灵活性,能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系统性地回应性思维、跨学科性、适应性(Shangraw Jr,R.F.、Crow,M.M.和Overman,E.S.,1989:153-160)。他还将他的理念运用在新型的大学设计上,将他任校长的大学按照几大原则重新设计:(1)拥抱地方文化、社会经济条件和物理环境,用好所在地的优势。(2)致力让每一个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成功。(3)通过与社会的链接催化社会的变革。(4)跨学科和超学科研究创造知识、推动知识力量的融合。(5)以知识为基础推动和鼓励创新,重视企业家精神。(6)与社区协同合作,嵌入社会。(7)从事能对社会和使用者产生影响的研究。(8)推动和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所有的机构设置、运行方法,都按照这样的设计理念来推动。②ASU Web.https://asu.edu.
将制度设计、或者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设计作为新时期治理改革的目标,寻求和制定国家治理的设计原则,不断调整和创新体制机制,设计国家的功能,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应对新技术时代的到来,是新时期治理理论创新的要求。
四、广义相对论的启示——不忘初心的新公共治理
“设计治理”需要有对事实、历史、人类自己的深刻了解。身处于复杂多元和变化的世界中,人类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当代著名作家和哲学家尤瓦尔认为,从物理世界的角度来看,智人的存在,就像生物世界里的其他物种一样,并没有必然的原因。但对于人类自己来说,存在的目的有二,一是生存和繁衍,按生物的本能延续自己的物种;二是追求意识赋予的感觉,避免痛苦,追求快乐(Harari,Y.N.,2014)。由于人是高阶动物,在意识的基础上,还发展出了理性,用积累的知识和逻辑方法,指导自己的行为,追求生命的价值。当然,这个价值,是人类自我赋予的,是人类在组织起来与大自然博弈的过程中,为自己创造出来故事和愿景,以激励自己的努力。
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包括至少几个重要的维度:
个体与集体的关系(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
没有个体,就没有集体。个体的存在是基础性的根本,但人同时又是群居动物,很早就懂得要和集体一起,共同合作,与天灾人祸博弈,以赢得生存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在特定的情况下,以少数个体的牺牲,换来集体的生存和机会。人类的组织,包括家庭、氏族和国家,一直在用各种方法,协调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探讨如何在追求个体的利益的同时,增进公共利益(自由资本主义);或者在推动公共利益的同时,提升个体福利(社会主义)。
智慧与感知(intelligence and consciousness)
智慧与感知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性与感性的关系问题,是另一个重要的维度。在科学和哲学不发达的时代,人类没有系统思维的习惯,意识就是对已有知识的概括,凭直观的感觉行为,似乎感觉就是智慧。但在哲学、伦理科学和自然科学高度发达的时代,人类注重知识的积累和务实的行为结果,了解了更多更复杂的因果关系,趋于将理性智慧与简单的意识和感知区别开来,更多地依靠智慧—知识和理性原则指导的思维来主宰人类的行为,以满足感知的需求。在很大的程度上,甚至用理性来训练和规范感知,就是我们常说的进行价值和理想教育。这一对关系如何处理,中间大有学问。
狭义与广义(specific and general)
追求福祉的过程中,人类的合作需要有集体主义的精神,也就是身份的认同和对所在群体的忠诚。这两个概念都有哲学意义上的狭义和广义之分。
一个人常常可以有不同的身份认同。如驾驶员,医生,工程师,科学家,知识分子,团体会员,宗教信仰者;或者说,老乡,同学,业余活动爱好者;可以同时是消费者和生产者,食客和服务员,公民和公务员;可以同时是家庭成员、社区成员、地区成员和国家公民、世界公民。错综复杂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需要个人和国家的智慧才能理清楚和处理好。也有两难的可能,比如说家国情怀——在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有冲突的时候,对与错、情与理的价值判断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同样的道理,人们在工作岗位上,也可以有不同层次的责任忠诚。有对国家宪法精神的忠诚,有对具体工作单位的忠诚,也有对顶头上司的部门领导人的忠诚。如果这些责任忠诚是可以统一的,就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常常是,这些忠诚的目标并不完全一样,有阶段性和长期性,地方性和国家性,个人性和组织性的区别,常常还会产生冲突,比如顶头上司是贪官或部门领导以小单位利益为重,这就需要个体来进行识别和妥善处理这些冲突。
扩展到国家层面,本土理念与全球理念也有同样的张力。它们可能有冲突,也可能不应该有冲突但被认为有冲突。如原子能的使用、气候升温和生态退化、瘟疫、生命基因工程之类的科技能力,都会带来全球性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国家本身的规制和治理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比如碳排放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拒绝谈判还是讨价还价讨论碳排放标准,是同意碳排放交易权安排还是勇当带头人,以榜样、甚至自我牺牲来争取信任,引领变化,是几个不同层次的行为方式。各个国家,如何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实力,关注和提供解决这些具有共性的问题,对国家和全球都是同时有益的努力。但其中依然有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狭义本土利益与广义全人类利益的矛盾。当前风行的逆全球化思潮,受的就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这一思潮只关注眼前和狭义的单一标准,忽略全景和长远,努力的目标往往与应该追求的目标相反,使得人们在全球利益关联性越来越强的今天,倒行逆施,思想混乱,无所适从,害人害己。
阶段性目标与终极目标(temporal and ultimate pourpose)
阶段性目标和终极目标是许多个人和国家都很难处理好的问题。一般来说,终极目标属于美好理想型。古往今来,人们对人类的终极目标都有很美好的描述,有的甚至浪漫化了。现代世界对终极目标有完整描述的当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和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如果我们认真研读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里面提到的反对压迫和剥削,改变世界,解放全人类,让人们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论述,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中提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理想,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现代人文主义和思想革命的产物。它们的重要区别在于达标路径的选择:如何到达社会的终极目标?是通过个人主义的奋斗,还是集体主义的努力;通过资本家精英的引领,还是国家精英的引领;通过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等等。过去一个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和自由资本主义阵营的竞争,让我们对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有了具体的认识,知道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能仅仅简单依靠宏大的叙事,也要靠不辞劳苦的对细节的关注和努力(Dahl,R.A.和Lindblom,C.E.,1953)。
理想和目标十分重要,但阶段性努力也必不可少,关键点之一要让阶段性目标与终极目标有兼容性、一致性,让工具服务于而不是替代目标。如果只说不做,或者南辕北辙,或者停留在工具理性带来的阶段性目标上,就永远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终极目标。
变化与稳定
公共治理作为一种设计科学,也需要处理好变化与稳定的关系。变化与稳定是古希腊哲学家就开始讨论的命题(Boas,G.,2019)。斗转星移,季节变换,灾害、瘟疫、战争、交替出现,让人们生活在动荡、变化和不确定的社会之中,具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人们组成族群和国家,抵御变化,追求稳定和安全。但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最大的稳定来自于因时、因环境的改变。如果不变,则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变化是永恒的,最大的不变就是变化本身。只有与时俱进,才能达到动态的平衡,保证安全和稳定。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必须要能够适应变化,学习变化,推动变化,在创新和变化中求得稳定。
根据以上讨论的治理需要关注的维度,可以列出一个总结性的表格,将不同理论在操作过程中的核心原则提炼出来,审视新治理需要的新原则和发展方向(见表1)。

表1 不同时代的治理理论的操作性特点示意图
结 语
设计新公共治理理论,需要一个坚实的底座原则。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看,在变化的世界中,有一种秩序,是客观存在的永恒,也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基本前设。广义相对论力图显示,充满暗物质的宇宙空间,是一个平面。但加上了物体(星球)重力,就形成了时空的扭曲和变化,形成了新的引力场,形成了我们通常认为的万有引力。万事万物,就开始按照引力场作用力的规律运行。所有的运动,万变不离其宗,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有序运行。
人类的文明,也处于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多种力量共存和博弈。第四次工业革命风起云涌,将给我们未来的世界带来难以想象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也可能是万变不离其宗,依然遵循“道”的规律。《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的依据就是自然及其规律。而宇宙自然的奥秘,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理解其万一。爱因斯坦相对论所解释的自然规律,以及其在人类社会对自我规律的认识方面的延伸,启示我们要关注探索终极世界和终极理想目标的思考,那就是什么是人类的终极理想的追求?如何将终极理想追求与阶段性追求有效结合?
最新的医学科学和行医实践不断发现生命的奇妙,也催生了新的医学原则:就是人类不必带着疼苦生活并以为那是生命规律中的必然存在。医学可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脑出了问题就医脑,心脏出了问题就解决心脏问题,牙疼就换牙,眼睛看不见就换晶体或者角膜或修补视网膜。手术过程中不再让患者咬着牙接受刮骨疗毒的痛苦,①古代麻沸散和针灸效果不稳定。而是打麻药、用止痛片、甚至吗啡以减轻痛苦。这些进步,也给了现代治理设计新的启示。即在治理过程中,可以努力将理想与现实结合,变化与稳定结合,运用智慧与感知,解决好变化与稳定、狭义与广义的人生意义、手段与目的、阶段性目标与终极目标等种种矛盾,追求灵与肉的统一。在新技术条件和财富分区的条件下,克服狭隘,克服无能,克服被动,让人民做正义的人,幸福的人,有尊严的人,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在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断涌现的同时,每一个人都是被国家保护和接受国家服务的公民,也同时是保护国家利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奉献者、卫士和原动力。国家一方面要大力提倡和推动新技术的创新,但也同时要关注好新技术带来的社会福祉的合理分配。新的治理逻辑、理论和方法,必须要围绕这样的理念展开,新时代的新公共治理,需要超越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私有制、民主透明、官僚行政等工具理性之争,构建直指人类理想的终极目标制度体系和行为方式,追求行动与结果、阶段性与终极目标的统一,在走向未来的征程中,时刻不忘为人民谋福利的“初心”。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啤酒与麦酒:舶来品译名的东亚视角
- 毛泽东主席关怀清华
-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与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