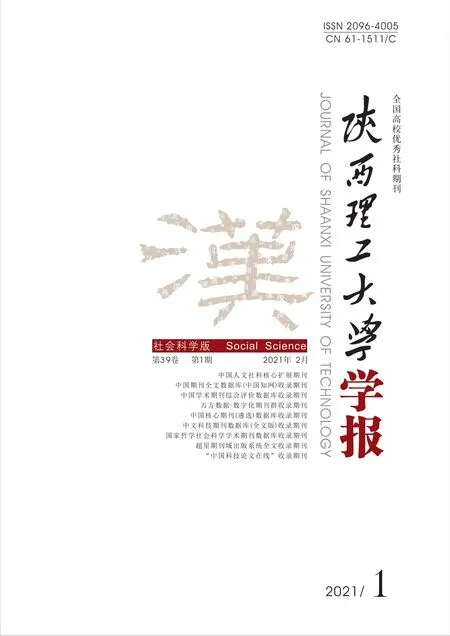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农民工称谓的嬗变
张 军
(1.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2.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710119)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群体迅速发展壮大,截至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超2.9亿。该群体的名称几经更迭,曾经使用或正在使用的指称形式多达数十种。这些称谓折射出所指对象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其兴替和流变昭示着社会演进的步伐。
目前对农民工(1)虽然我们不赞同“农民工”这个称呼,但为了称说方便,还是采用了该名称。称谓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语言学及传播学方面也有零星的探讨。主要涉及两大方面:一是“农民工”称谓的存废问题,包括造成“农民工”称谓歧视的原因分析与更名有无必要的争论;二是关于引发农民工称谓变迁的社会环境因素的讨论。研究的主流是透过“农民工”称谓关注其背后的社会问题。我们认为农民工称谓毕竟是以一系列词语的形式呈现的,是社会现象,同时也是语言现象。但作为特殊群体的指称形式,农民工称谓经过了怎样的发展演变轨迹?有何特点?促使其演进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这些都是必须厘清的问题。因此,我们拟从社会语言学视角进行考察,探讨农民工称谓的演化历程、特点以及促使农民工称谓更替的决定性因素。
一、 农民工称谓的演化历程
农民工称谓数量庞大,这里选取有代表性的一些称谓如:“盲流”“打工仔”“打工妹”“民工”“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新市民”“城市建设者”进行探讨,以揭示农民工群体称谓的变化轨迹和兴替过程。
1.盲流、打工仔、打工妹
“盲流”是“盲目流动”的减缩,本是动词,指农民在未被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私自进入城市。1952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社会司的文章《应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首次提出“盲目流动”的概念。1958年1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管理登记条例》,以法律的形式明文限制农民流入城市。此后,未经允许进入城市的农民即被视为“盲流”。20世纪80年代末,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形成“民工潮”,给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这一背景下,“盲流”一词频繁出现在政府文件和媒体中,并迅速扩散开来。1992年之后开始不再指称农民工,直到2003以后,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盲流”意味着非理性、无目的、无序化流动,是对既有经济、社会秩序的破坏,是“麻烦制造者”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盲流”反映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以国家政府为中心的不允许农民自由流动的强制性政策安排,是“国家中心主义”的体现,忽视了农民的实际需求和流动意愿。“盲流”贬斥意味浓厚,歧视色彩鲜明,一般只用于背称,面称则具有高度的侮辱性。
“打工仔”“打工妹”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深圳特区及珠三角一带的三资企业里,用来称呼受雇佣的外来青年。两词都是三音节偏正式合成词,“打工”描述劳动性质,受他人雇佣,具有临时性;在粤语中“仔”“妹”分别是男孩和女孩的意思,标示性别、年龄特征。“打工仔”“打工妹”原本是指二十岁以下及二十几岁的外来打工人员,后来,随着使用中的泛化,年纪较大的,比如四五十岁的也称“打工仔”“打工妹”。有时,“打工仔”还可涵盖“打工妹”的意义,泛指打工者。
跟“盲流”相比,“打工仔”“打工妹”的负面意蕴有所弱化,但仍然包含一定的歧视色彩。一方面,虽然“打工”本是个宽泛的概念,除了国家工作人员和私营业主之外的都可算作打工者。而实际上,“打工仔”“打工妹”当时主要指基本不具备知识技能,只能出卖劳动力的底层打工者,反映出对底层劳动者的鄙视与排斥。另一方面,这两个词是当地人对外来打工的年轻人的口语化称呼,透露着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对外来务工者的疏离与不屑,包含地域歧视、身份歧视和职业歧视的意味。在北方话中,“仔”同“崽”,常作为骂人话,这也加剧了“打工仔”“打工妹”的负面情感倾向。所以,浓厚的方言口语特征及与生俱来的歧视色彩,使这两个词难以成为全国性的称谓形式。
2.民工、农民工
“民工”一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用来称呼支前群众。解放后,这一称谓被沿用下来,《现代汉语词典》将其概括为“在政府动员或号召下参加修筑公路、堤坝或帮助军队运输等工作的人”。改革开放促使农民进入到城市谋生,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民工”的意义有所延伸,开始指自发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逐渐成为农村转移劳动者的主要指称形式。21世纪伊始,随着“农民工”的快速崛起并占据主导地位,“民工”成为其简称形式。
与“盲流”“打工仔”“打工妹”自带贬义不同,“民工”一开始是作为一个中性词,用来指称农村转移劳动者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今在某些文学作品或口语化(包括网络语言)语境中“民工”也出现了贬义。如:
例1:外媒镜头下的千玺被嘲很民工,吴亦凡好吓人,……(2)星珠娱乐,《外媒镜头下的千玺被嘲很民工,吴亦凡好吓人,ab居然都能顶得住!》,https://m.sohu.com/a/2/9623575_371652.
例2:耳朵里听出茧子的有:装备很民兵,纪律超民主,待遇很民工。(3)邸长鹏,《华盛顿》, 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
例3:因为我的长相很“民工”,夜晚出去吃宵夜.还经常被联防队员盘查有没有证件。(4)河流,《城市理想 东莞城市文明肖像》,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上述例句中的“民工”都可以换成“农民工”。可见,“民工”是在与“农民工”同指的意义上衍生出负面意蕴的。
“农民工”这个词早在1980年已经在《人民日报》中用来表示进城务工的农业户籍人口了,2002年后逐渐取代“民工”成为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群体的最常见的指称方式[1],进入政府文件、学术论著、大众媒体和普通民众的话语中。在2006年3月27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农民工”作为官方正式称呼出现,并获得了权威解释:“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工”是“农民”加“工”构成的偏正式复合词,中心语素是“工”,工人,代表职业,“农民”修饰“工”,表示户籍身份。从词语构造看,“农民工”应该属于工人范畴。但现实语境中,“农民工”却往往被划归农民之列,《现代汉语词典》就将其定义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政府文件中农民工问题也属于“三农问题”。结构与意义的龃龉却正是当下农民工尴尬处境的写照:亦工亦农,又非工非农,既区别于留守农民,也跟城市居民格格难入。在城乡户籍身份壁垒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户籍身份是首要的,而职业则居其次,所以,他们干着工人的活儿,身份却还是农民。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阶段性称呼,“农民工”带有一定的歧视性。用“农民”修饰“工”,将本不该出现的城乡身份隔阂固化下来,在户籍身份上将农村转移劳动者跟一般的城市工人分隔开,进而使这个群体在附属的劳动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都难以享受与“城里人”同等的权益。所以说,该称呼带有旧的门第观念和等级观念的烙印,导致“农民工”低人一等的社会偏见,使他们在许多方面受到歧视。[2]
现在,“农民工”是政府、媒体和民间语境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称谓。但有调查表明农民工群体自身对这个称谓的认同率较低,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明显不能接受这种称谓,已经开始质疑户籍本上的“农民”身份,他们感到“农民工”这个称谓刺耳。[3]189
3.进城务工人员、新市民
“进城务工人员,是指那些户口仍在农村但已完全脱离或基本脱离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以在城镇各类所有制企业打工、经商以及从事其他服务行业为生的一类人群。”[4]3这一叫法出现于20世纪末,通行于当下,是一个正式称谓,主要为官方和媒体使用,民间很少使用。
丢掉了“盲”“打工”“农民”等字样,“进城务工人员”明显减轻了排斥、歧视的意味,也淡化了农民工与市民的区别。但“进城”仍含有外来的、并非城市里的意思,依然暗示“进城务工人员”不是市民并与之有一定区别。[5]
用“新市民”指称农民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出现,通行主要是在当下。如2003年江苏常州钟鼓区开办“新市民夜校”;2006年2月青岛市将外来务工人员改称为“新市民”,其子女称为“新市民子女”;2006年8月,西安市雁塔区发文将外来人口、外来务工人员、打工者、农民工等统一称为“新市民”。“所谓新市民,是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名词,是城市社会对外来务工的、有相对稳定职业的劳动者的尊称。”[6]34因此,“新市民”不仅仅是一个称呼,也代表城市人对农民工态度的转变。
4.城市建设者
“城市建设者”原本指从事城市基本设施建设的城市居民,本世纪初衍生出新用法,指称进城的农民。葛建雄将城市建设者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除了不具备工作能力,已经退休,或少数社会救助的对象外,城市的居民和外来的劳动者(含管理者)都是建设者。狭义上,则是指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人员,既有本地居民,也有外来劳动者。[7]32目前,“城市建设者”一般有特定的所指——农民工群体中从事建筑、环卫等公共建设的人员,并不是所有农民工都被称为“城市建设者”。也就是说“城市建设者”的外延往往小于“进城农民工”,仅指其中的一部分。如:
例4:外来务工者,你们辛苦了!20位外来的城市美容师、城市建设者昨受表彰(5)《外来务工者,你们辛苦了!20位外来的城市美容师、城市建设者昨受表彰》,宁波日报,2005年12月5日,第2版。
例5:坐在离舞台最近的观众席A区。当晚,观众席上全市困难家庭、“低保”户、残疾人、退休职工、城市建设者、外来务工创业人员等群体的代表有2000多人。(6)《杭州:西博会上看新风》,人民日报,2004年11月4日,第2版。
例4“外来务工者”涵盖了“城市美容师”和“城市建设者”,“城市美容师”指环卫工人,“城市建设者”则特指从事建筑业的人员。例5“外来务工创业人员”与“城市建设者”并列,而他们又与“困难家庭”“低保户”“残疾人”“退休职工”同属一个更大的范畴——弱势群体。这里的“城市建设者”是指从事建筑、环卫工作的人员,包括进城农民,而“外来务工创业人员”则是指进城的农业户籍人口中从事其他职业的人。
有时“城市建设者”又相当于“进城农民工”,如中新网题为《城市因他们而生动——致敬那些城市建设者》的文章:
例6:城市因人而生动,尤其因它的建设者而生动。他们是快递小哥、环卫保洁、物业保安、家政人员,还有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无论是城市运行,还是日常生活,都离不开他们的辛勤劳动与付出。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称谓——“老乡”,统计学上叫农民工,在工作报告中叫扶贫对象,进了城叫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理应被善待,因为他们为这座城市贡献出了青春和汗水。(7)本刊编辑部,《城市建设者》,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48期。
“城市建设者”这个称呼,极具包容性,凡是对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人,都可囊括其中,既包括城市户籍居民也包括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户籍人口。它拉平了市民和农村转移劳动者之间的差距,符合当前国家建立和谐社会的基调。更重要的是,用它称呼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劳动者,肯定了他们对城市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表明城市对该群体一种积极的态度,这跟以往的“盲流”“打工仔”“打工妹”“流动人口”“外来务工人员”相比,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转移劳动者的称谓演变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轨迹:盲流、打工仔、打工妹→民工、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新市民→城市建设者。每个称谓形式都是特定历史阶段农民工生存状况的写照和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缩影。
二、 农民工称谓演变的特点
农民工称谓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称谓,其兴替变化有其独特性,我们归纳为多样化、阶段性,渐进性、并存性和去贬化。
1.多样化、阶段性
多样化指进城农业户籍人口的称呼异常丰富,包含历时层面的新旧更替,从“盲流”“打工仔(妹)”到“民工”“农民工”,再到“进城务工人员”“新市民”以及“城市建设者”;也包括共时层面的异形同指。目前除了“盲流”外,其他几个称呼都还存在于我们的交际中,另外,还有众多的替代形式。这当中有政府、媒体书面语的正式名称,也有民间随意性叫法;有立足于输入地的指称,也有立足于输出地的称呼;有包含歧视色彩的贬称,也有充满敬意和尊重的尊称。如此之多的能指形式,从不同侧面反映农业户籍务工者的特征,承载各类命名者的态度、情感和评价。
农民工称谓的多样化是诸多因素促成的:其一,农民工群体历经四十余年,其成员来源不一、就业形式复杂,不同时期的称谓各有特色,从而累积了相当庞大的量;其二,当前农民工群体的壮大,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力量,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命名主体多元化导致名称不统一;其三,各方对农民工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官方“高大上”的称呼与民间通俗的叫法并行;其四,称谓具有主观性,体现命名者对被命名者身份、地位、特征的认识,也包含态度情感倾向,命名时选择的角度、提取的特征各异,造就了农民工称谓形式的纷繁复杂。
称谓的阶段性表现在不同时期有其独特的称谓形式。从历时变化看,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民工潮”期间,“盲流”流行;而东南沿海外资企业兴起的时候,“打工仔““打工妹”频频出现;世纪之交国家开始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时候,“民工”“农民工”活跃起来;当农民工改名呼声不断、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时候,“进城务工人员”“新市民”“新……人”等纷纷亮相;当建设和谐社会作为主旋律的时候,“城市建设者”及时登场。

表1 改革开放后农民工称谓的时间分布
农民工称谓的某种形式,往往有其特定的使用周期,一个时代结束了,旧称谓也随之退出,由新时代的名称来接替。就未来的发展而言,“民工”“农民工”这两个词本身就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性称谓,带有身份歧视印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农民工群体将不复存在,这两个称谓必将走向消亡。“进城务工人员”和“新市民”作为“民工”“农民工”的替代形式出现,客观上淡化了对进城就业的农业户籍人口的不公平对待,但也隐含城乡二元分割的思维模式,同样也会随着城乡差距的缩小和城乡户籍壁垒的打破而隐退。
称谓的阶段性还表现在,即使同一个称呼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也会衍生出迥异的附加内容。“民工”指农村转移人口,是其原义的延伸,本是中性词,如今在某些市民的观念中却增添了负面意蕴,将它与“贫穷、落后、邋遢、粗俗”等字眼联系在一起,跟“农民工”一道变成市民歧视农业户籍务工者的符号。这种附加意义主要是社会环境赋予的,是特定历史时期农民工群体不利的生存境遇的反映。现实中,农民工文化水平总体比较低,所从事的往往是城里人不愿干的脏、苦、累、险、重工作,收入有限,还常常成为被剥削、排挤和欺压的对象。这种现实状况决定了人们关于农民工的认知经验中累积了太多的负面信息,而这严重制约着对农民工的客观认知。另外,21世纪以来,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大幅度增加,但报道多把农民工定位于社会的弱势群体,需要被关怀救助的对象。这种模式化描述使得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多地在社会成员心里形成负面的刻板印象,影响了现实生活中对这一群体的正确认知。[8]
2.渐进性、并存性
渐进性是指农民工称谓的更迭是个漫长的过程,短期内难以见到明显变化。当代一个称谓词语从产生到通行再到隐退,通常需要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的时间,新形式完全取代旧形式也至少需要数年。比如“盲流”,改革开放初复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流行,直到21世纪头十年才基本消失(在一些文学、纪实作品中还有保留)。而“打工仔、打工妹”之类的称呼,直到现在还有使用。目前的农民工更名问题也是如此,虽然近年来已经开始有淡化“农民工”称谓的提法,并已经出现了“进城务工人员”“城市建设者”“新市民”等替代称谓。但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经过反复研讨斟酌,征求多方意见,最终还是采用了“农民工”这一称谓。此后,取消“农民工”称谓的呼声不绝,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这个话题又被提起。对此,人社部给出的答复是目前不宜取消。因为,在农民工问题被根本解决之前,农民工群体还将存在一段时期,因此需要有特定称谓,以便实行有针对性的政策,逐步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除“农民工”外,很难找出一个准确、简洁、各方认可的称谓,来指称户籍仍在农村但从事非农产业的群体;此外,“农民工”称谓已经约定俗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9]可见,农民工称谓的更替将是一场持久战,要想短时间内剔除“民工”“农民工”之类的带有不平等印记的称呼是不现实的。但质变需要量的积累,目前新称谓形式的渐进发展都在为将来彻底摒弃农民工的歧视性名称做准备。
并存性指在新旧称谓交替的过程中,两种或多种形式会共存并用,形成竞争关系,更多时候是各有侧重点,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如现阶段,“民工”“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新市民”“新……人”“城市建设者”“农业转移人口”“外来务工人员”等指向同一群体。这当中,意义基本相同的“民工”和“农民工”,构成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据统计,从1995年到2004年,在《人民日报》网络版全文数据库中,“民工”占优势,2005年之后,“农民工”成功逆袭[10],而现在“农民工”的使用范围在萎缩,而“民工”却相对平稳。大多数称谓都有一定差别,适用于不同的语境,如“进城务工人员”突出输入地和职业属性,“新市民”“新……人”显示其新的城市身份,“城市建设者”体现功能角色。有的是语体特征存在差异,如“民工”“农民工”是通俗的说法,官方、民间均有使用,而“新市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市建设者”则多见于官方文件和报道中,民间口头交际几乎不用。
3.去贬化
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农民称谓变迁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去贬义化。称谓不仅仅是指称符号,也代表着命名者的主观情感倾向和思想认识。所以,称谓总是附着着一定的感情色彩,表现为褒义、贬义和中性三类。从“盲流”明显的侮辱歧视,到“打工仔”“打工妹”的部分歧视,再到“民工”“农民工”的逐渐“变味”,接着到“进城务工人员”贬义大大减轻,而到了“新市民”“城市建设者”则体现出认同与尊重。在这个称谓演变链条上,贬义逐渐递减,而褒扬意味渐次上升。
盲流、打工仔(妹)→民工、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新市民→城市建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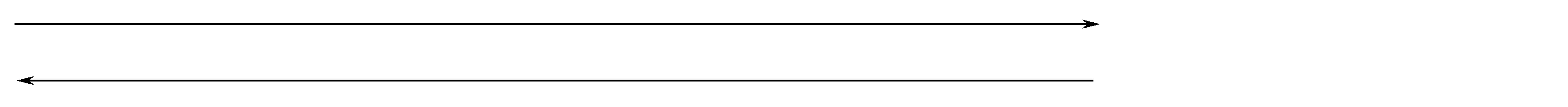
褒义
贬义
现在,“盲流”已然退出,“打工仔”“打工妹”的使用有限,“民工”“农民工”依然高频,但已经受到自身歧视色彩的影响和新生称谓的挑战,而“进城务工人员”“新市民”“城市建设者”等发展势头正劲。农村转移人口的称谓更替过程,同时也是摒弃消极称谓形式而转用积极肯定称谓的过程。反映了政府对农业转移劳动者的日益重视和认识的转变:即由麻烦制造者到正常流动现象再到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折射出市民态度的改变,少了些排斥、鄙视,多了些接纳、认可。
这种去贬化,主要是人为干预的结果。1993年8月国务院在文件中提出不要给出来打工的农民戴什么“盲流”的帽子。以此为拐点,在《人民日报》中“盲流”不再指称农民工,政府文件和其他媒体也立即响应。21世纪初,不断有各界人士质疑“民工”“农民工”称呼,建议更名。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率先行动,2005年江苏昆山市“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改名为“新昆山人建设委员会”;2011年河南省取消农民工称谓;2012年1月初,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广东将加快研究并适时出台取消“农民工”称谓的政策措施;2019年3月,格力董事长董明珠发声,禁止格力内部使用“农民工”和“打工仔”的称呼。权威者的话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限制了歧视性称谓的使用,转而采用让农村转移劳动者感觉更有尊严的称呼形式。
三、 促使农民工称谓更替的决定性因素
农民工称谓的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语言系统自身的调整、社会环境、大众心理、媒体的参与等等。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基于城乡二元分割户籍制度的农民工政策的变化,它是农民工称谓指称对象产生和存在的前提,也制约着农民工群体指称形式更迭的方向。
1.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决定了农民工称谓指称对象的产生和存在
农民工称谓是为了指称农民工群体而存在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是农民工称谓出现的客观依据。在我国,农民工群体的形成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制度的产物。1958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规定了居民常住、暂住、出生、迁入、迁出变更等人口登记制度,以法律的形式严格限制了户口的流动。它将公民划分为农村户籍居民和城市户籍居民,二者在住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等制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别。此后20年间,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只能通过升学、当兵、招工等有限的正规途径实现,其他通道均被堵塞。改革开放使农村生产力提高,富余劳动力增多,而城市的迅速发展导致用工需求大幅增加,在二者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开始进入城市谋生,这就诞生了农民工群体,也催生了农民工称谓。农民工从产生之日起就面临着身份归属的尴尬:从职业看,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与一般的城市居民没有差别;从户籍看,他们又是农村户籍人口,不同于城市户籍居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待遇和保障等。在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面前,农民工成为处于城乡夹缝中的“边缘人”,负载着多元的社会政治文化信息,这也为其不同称谓形式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2.农民工政策的变革制约着农民工群体指称形式更迭的方向
农民工称谓是一种政策性话语,反映着政府对该群体的认识和态度,它受制于农民工政策。农民工政策的更革指引着农民工称谓向何方向变化,如何变化。
我国农民工政策及其演变大致分为五个阶段:控制流动阶段(1979—1983)、允许流动阶段(1984—1988)、控制盲目流动阶段(1989—1991)、规范流动阶段(1992—2000)、公平流动阶段(2000年之后)。[11]29-381989年春节后,“民工潮”汹涌而至,给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带来空前的压力,“盲流”一词活跃起来,伴随而来的是国家的农民工政策由允许流动转变为控制盲目流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大提速,对劳动力的需求猛增。国家对流动人口的管理由“控制盲目流动”转向“鼓励”“引导”“有序流动”。农民工成为一种常态,不宜再称为“盲流”,于是,其他称呼竞相出现,最终,“民工”胜出。对《人民日报》的统计显示,在1995年到2001年,相对于“农民工”,“民工”占据绝对优势。2002年之后,农民工问题已作为重要的社会问题提升到国家制度解决层面。在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中,开始使用“农民工”一词。尤其是200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对“农民工”给出了官方定义,全面系统地阐释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所以,从2002年开始,“农民工”一路走高,并迅速超越“民工”成为政府、媒体和民间最常用的指称形式。这一时期,从“民工”“农民工”以及并存的“进城务工人员”“暂住人口”“外来务工者”“新工人”“外来青年”“外来工”等可以看出,社会总体上还是将农民工视为外来者、城市过客。与此相对应,当时的户籍制度虽有松动,但未有大的改变,农民进城落户仍然不具有普遍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农民工政策进入通过推动大规模的、实质性的农民工“市民化”而走向“农民工终结”的新阶段。[12]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工”“农民工”等基于户籍壁垒、有失公平正义的称谓已经不合时宜。所以,在2012前后,“新市民”“新……人”“城市建设者”“异地务工人员”等名称纷纷亮相,带动了农村转移劳动者称谓形式的新一轮竞争。各类替代名称都从一定程度上剔除了带有城乡分割意味的歧视性字眼,肯定农村转移劳动者对城市发展做出的贡献,促进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农民工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特定时代的产物,各个称谓形式均与独特的时代背景相联系,记录着该群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存状态和奋斗求索,也反映出转型期我国城市社会生态的演进。农民工称谓的更替过程漫长而复杂,既是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艰辛史,也是新时期我国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史。这背后的强大动力来自于我国农民工政策的调整与变革。目前,关于农民工称谓的争论还在继续,但随着国家对农民工问题的重视和相关改革的推进,相信未来这个群体会获得真正的公平,包括称呼上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