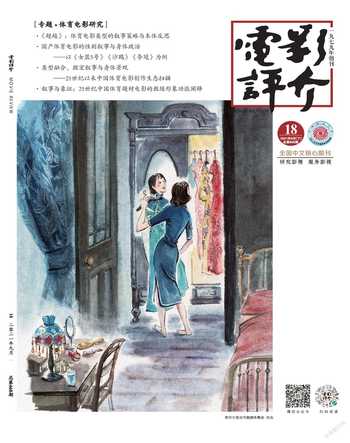再现、表现与表征:“西游”题材影像的旨归嬗变考索
杨璟 袁智忠
《西游记》作为中华优秀古典文化中的瑰宝,是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取之不尽的“超级IP”。自1926年第一部《西游记》衍生电影《孙行者大战金钱豹》以来,“两岸三地”拍摄了100余部取材于《西游记》的电影。这些电影“不仅促进了《西游记》的广泛传播,也丰富了对《西游记》多样化的诠释和接受。”[1]
“representation”一词自20世纪50年代西方文化研究兴起以来,其内涵逐渐由“再现”“表现”演变为“表征”。在文化研究学者看来,“表征”是文化生产意义上的符号性意指,世界观、价值观正是在文化系统中被生产出来的,在“言说”中包含着各种“权力关系”。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如今进入了新时代,每个时期《西游记》衍生电影的“表征”各异。本文主要从《西游记》衍生电影对时代精神的诠释与再现出发,分析其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近代、现代及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嬗变之中,并以“表征”的方式影射时代话语。
一、革命与斗争的政治隐喻
如果说现存最早的《西游记》衍生电影《盘丝洞》(1927)只是在商业类型片中表达创作者的人生思考,而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长动画片《铁扇公主》(1941)是现存最早的高度配合时代伦理精神的《西游记》衍生电影。《铁扇公主》产生于全面抗战时期上海“孤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华民族需建立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于此,《铁扇公主》在原著的基础上做了一定修改,讲述了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三人分头借芭蕉扇的失败,最后在唐僧的教导下,三位徒弟发动火焰山群众合力击败牛魔王和铁扇公主,夺得芭蕉扇,熄灭了火焰山大火的故事。正如该片导演万籁鸣所言,“在《铁扇公主》中,我们有意曲折地用打倒牛魔王作为借喻,反映出影片的主题,那就是‘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对付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2]从某种意义上讲,《铁扇公主》开创了将《西游记》故事作为政治伦理隐喻文本的先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怎样解放”“如何解放”是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重要思想表达诉求。“歌颂光明与胜利的活力和乐观主义色调成为时代美学的要求,中国人的审美生活开始呈现出崭新的时代面貌。”[3]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在叙述革命历史时,或直接呈现革命英雄形象,或利用中国传统故事来诠释革命思想,而作为中国古典名著中的“超级英雄”形象的孙悟空,很自然地被选为表达革命思想的代表。
绍剧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960)是最早被纳入新中国建设时期的时代话语,成为革命伦理精神代言的《西游记》衍生电影。这部以原著中“三打白骨精”故事为主体,融合了“波月洞”和“莲花洞”元素的戏曲电影,实际上只是更加强化了原著的戏剧冲突性,通过将原著中故事情节的疊加,强化了白骨精的阴险狡诈,突出了唐僧不辨忠奸的“现世报”。由于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同志观看了浙江省绍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之后,完成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将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定性为“借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个神话故事,歌颂无产阶级反修战士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英雄形象。”[4]从而,使绍剧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政治伦理思想由“隐”变为“显”。
1961年和1964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电影《大闹天宫》(上、下集)主动地进行革命叙事,其只是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稍作改动便实现了特殊的效果。一方面,电影的结局表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全面胜利,删除孙悟空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这一段情节;另一方面,在人物塑造上,它建立了天宫众神和孙悟空的二元对立关系,突出了天宫众神的傲慢、无能与孙悟空的斗争精神。原著中“大闹天宫”体现的“这种反抗精神是作品能够启发读者联想、激发封建时代人们的反抗斗志的思想基础。”[5]而为了进一步突出表现孙悟空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伦理,动画电影《大闹天宫》(1961)中,将原著里孙悟空那些“无理取闹”的性格特征也剔除了,留下一个高尚、纯粹的革命者形象,突出了孙悟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斗争精神。
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将原著所蕴含的主题与时代精神极好地结合起来,开创了“齐天大圣”革命英雄形象的模式,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新时代。例如,同样是大闹天宫题材,根据《西游记》衍生小说《悟空传》(2000)改编的电影《悟空传》(2017),在基本剔除了原著中主要人物的消极情绪基础上,歌颂了转世孙悟空坚持不懈地对抗黑暗的天庭,打破“天机仪”控制人类命运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时也表达了英雄人物为人类的生存与尊严而奋斗、保卫家乡及百姓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天庭为维护所谓“秩序”所做出的种种恶行,是转世孙悟空“偏执”复仇的诱因,其彻底的革命精神带动了阿紫、天蓬、杨戬和卷帘等诸神走上了反叛之路,最终个人英雄战胜了强大而等级森严的天庭势力,转世孙悟空打碎了控制人类命运的“天机仪”。可见,50年后,作为革命英雄的“齐天大圣”形象依然具有生命力。
二、自我与责任的伦理冲突
“‘大同’、‘太平’、‘天下为公’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为之不懈奋斗的信念和社会理想。”[6]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个人的最高伦理要求就是“天下为公”。同时,“中土佛教伦理的思想和规范具有自身的济世品格和人世风格。”[7]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游记》原著中师徒四人的取经过程,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儒家伦理与中国佛教精神的深度结合,此精神内涵影响了《西游记》衍生电影。如,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地区生产的《西游记》衍生电影,《红孩儿水晶救母》(1959)、《铁扇公主神火破天门》(1959)、《红孩儿》(1962)以及由邵氏公司出品的何梦华《西游记》系列电影:《西游记》(1966)、《铁扇公主》(1966)、《盘丝洞》(1967)、《女儿国》(1968)等,都将《西游记》原著中的“救赎”精神贯穿到电影主题中,歌颂了唐僧师徒为实现“救赎”人类的目标,不畏艰险、坚忍不拔地远赴万里之外的“取经精神”。
20世纪70年代,香港跻身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中国率先富起来的地区。“一百多年的发展,使香港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业金融贸易社会,这其中物质利益原则、等价交换原则、消费原则成为社会各领域公认的准则。”[8]同时,西方后现代文化进入香港后对其传统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中西文化逐渐融合。西方后现代思想中的反主流、反传统、绝对自由、快乐至上等精神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责任意识、仁爱精神共同作用于当时的香港电影。
20世纪90年代,由内地和香港合作拍摄的《西游记》衍生电影《大话西游》(1995),在当年的票房并不佳,而且“当‘大话’文化在1995年进入内地时,对于整个内地的文化生态来说,还是略显操之过急。”[9]但随后几年,其进入录像市场后却深受内地青年人的青睐,《大话西游》是《西游记》衍生电影产生剧变的标志,也同其他香港“无厘头”电影一同折射出经济繁荣背景下传统与现代伦理价值观的冲突。
《大话西游》讲述了孙悟空因背叛取经大业而被上天惩罚托生为落魄的强盗头目至尊宝,并与白骨精、紫霞仙子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最终逃不过“天命”,重新踏上取经之路的故事。在影片中,命运决定了孙悟空必须抛开凡人的一切情感,默默地去完成取经任务。“片子结尾,孙悟空对自我的回归,也是对自我的超越,因为他已不是那个为所欲为的‘孙猴子’了,而成了一个主动背负宏大使命的‘取经人’,狂野的生命力量,爱情至上的个性主义,乃至救赎的激情背后,是深刻的怀疑主义。”[10]影片建立起了自我/责任的二元对立,突出人的选择性悲剧。在影片中,至尊宝反复利用月光宝盒想要去改变命运,但始终无效,表达了人的力量在命运面前的渺小。
经济繁荣、文化市场的发达以及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传统伦理价值观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市场经济所体现出的利益至上原则对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的“义利观”产生了冲击,“于是一些与传统道德、伦理迥然背离的众生相纷纷发生。”[1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解构蕴含传统伦理精神的文学文本成为当时文化市场的可能性选择。《大话西游》流行后,个人主义与责任意识相融的当代青年伦理价值观开始影响《西游记》题材电影的主题表达。如《情癫大圣》(2005)中,唐僧为了爱情宁可放弃取经事业,但又因为爱情,他继续踏上取经之路。又如,网络电影《大梦西游》(2016)系列的每一部影片中孙悟空都会在取经路上经受女妖们的爱情考验,但最终,在留下深深的遗憾后,孙悟空重踏取经之路。可见,《大话西游》中自由与责任的伦理冲突主题的深远影响力。
三、崛起与复兴的国族寓言
进入21世纪,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上谋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进一步将西方意识形态包装在高科技的视听盛宴中。这其中,以“漫威”超级英雄电影为代表的如《蜘蛛侠》系列、《钢铁侠》系列、《美国队长》系列等很巧妙地将美国国家精神融入到人物独特有趣、情节跌宕起伏、视觉冲击力超强的电影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观众的价值认同感。在新时代,各国之间依然进行着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竞争,其中“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之一。国际话语权的大小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和尊严。”[12]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中国将会自觉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保证国家的文化安全,坚持文化自信,另一方面要打破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妖魔化”塑造所造成的文化偏见,寻求更进一步的国际文化认同,突显大国形象与气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中华文化,不仅自己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借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13]而作为已经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西游记》文化是承载中国当代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
2015年出品的中国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无疑是新时代以来《西游记》衍生电影开发的成功的案例。“影片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国产电视动画的粗糙复制模式,又突破唯技术的视觉表象诱惑,重回商业电影叙事法则,回到富有人性光彩的故事自身,这对中国动画电影乃至真人电影都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14]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演绎了英雄责任回归的过程。电影讲述了齐天大圣敢于反抗天庭的英雄事迹影响了四百年,小和尚江流儿就是齐天大圣的忠实崇拜者。此时山妖横行,直接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机缘巧合下江流儿解除了孙悟空的封印,将孙悟空放出五行山,然而,孙悟空由于手腕上的封印尚未解开,无法恢复法力,变成了一只普通“猴子”。孙悟空“从一名失落、排斥他人的迟暮英雄,被江流儿的救人壮举打动,最后与混沌展开决战,完成了一次人格的蜕变,在自我救赎中重新归来。”[15]这样的设计,是将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艺术形象象征性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心态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的齐天大圣经历了从盖世英雄到平凡神猴再到超级英雄的人生之路,正是中华民族古代、近代和当代民族地位变化的寓言。又如,另一部《西游记》衍生动画电影《小悟空》(2018)故事发生在美国纽约。讲述了自认为是孙悟空转世的大森本是四川动物园中一只普通的金丝猴,为救被牛魔王绑架的管理员观观来到纽约,在“八戒大師”的引导下恢复前世的超能力,最终战胜了邪恶的牛魔王的故事。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和《小悟空》都是有关自信恢复的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的孙悟空是因为手腕封印未解,无法使用超能力而失去信心;《小悟空》中的大森也是因为没有超能力而缺乏信心。在这两部电影中,获得超能力的途径正是来自内心的自信力,是勇敢、无畏、仁爱、侠义及大无畏牺牲精神。有趣的是,《小悟空》作为以少年儿童为主要目标受众的电影,把中国古代的超级英雄故事放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将时代精神编入电影之中,可谓用心良苦。
总之,从《西游记》衍生电影的创作历史来看,一方面,其继承了《西游记》原著中所蕴涵的反抗精神和救赎精神,又在历史语境中被改装和重新演绎。现当代中国各个时期的时代伦理精神也显在地被植入到电影之中,这是对中华传统伦理精神的传承,也是一种现代化转换。可以说,《西游记》是具有极大影响力中国文化品牌,如何把握用好它、改好它、传承好它,对重塑中华传统伦理精神,建构现代中国伦理精神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简介】 杨 璟,男,重庆人,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教授,西南大学美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影视伦理、艺术美学研究;
袁智忠,男,重庆人,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影视传播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影视伦理、影视批评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重庆人文科技学院2017年度人文社科项目“《西游记》衍生魔幻电影的伦理价值研究”(编号:CRKXJ201727)、西南大学2020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创新团队项目“中国电影伦理思想研究”(编号:SWU2009111)的中期成果。
参考文献:
[1]赵敏.《西游记》改编研究的进展与思考[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53-61.
[2]万籁鸣.我与孙悟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90.
[3]黄会林,王宜文.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美学探论[ J ].当代电影,1999(9):65-73.
[4]林飞.学习毛主席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3):32-35.
[5]朱式平.试论《西游记》的思想政治倾向[ J ].山东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6):53-61.
[6]吴来苏,安云凤.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评介[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76.
[7]王月清.中国佛教伦理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243.
[8]王瑾.互文性:名著改写的后现代文本策略——《大话西游》再思考[ J ].中国比较文学,2004(2):62-73.
[9]姚爱斌.“大话”文化与青年亚文化资本——对《大话西游》现象的一项社会学考察[ J ].文藝理论与批评,2005(3):73-77.
[10]房伟.文化悖论时空与后现代主义——电影《大话西游》的时空文化研究[ 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82-86.
[11]袁智忠.光影艺术与道德扫描——新时期影视作品道德价值取向及其对青少年的影响研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144.
[12]许门友,许旸.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的逻辑理路及其实践[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1):37-47.
[13]习近平谈文化自信[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7-13.
[14]陈可红.《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叙事回归与人性情怀[ J ].电影艺术,2015(6):59-61.
[15]蒲剑.用普世的手法讲好中国故事——《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启示[ J ].当代电影,2015(9):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