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碑刻文研究成果分类及其评析
——以1982—2017年藏文论文为对象
吉加本
(四川民族学院藏学学院,四川 康定 626001)
自1982年新中国藏学学术类刊物(藏文版)创刊至今,吐蕃碑刻文研究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其研究对象涉及我国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份和巴基斯坦境内。此期间,国内藏文学术刊物上有关吐蕃碑刻文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这些成果为吐蕃时期相关历史议题的考释、拓宽新的研究方法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因此,笔者以1982年为起点,梳理分析了1982—2017年间,吐蕃碑刻文的研究成果及其分类,并对相关问题展开了评述与探讨,以期全面呈现35年来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和丰富吐蕃碑刻文的研究。
一、1982—2000年间的吐蕃碑刻文研究
从研究成果来看,1982—2000年间,撰写吐蕃碑刻文相关论文的是恰白·次旦平措、巴桑旺堆、加央和高瑞等学者,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多为西藏自治区内发现的吐蕃碑刻文。
1982年巴桑旺堆发表《新见吐蕃摩崖石刻》[1]一文,以山南洛扎县境内发现同一内容的两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内容为依据,提出此碑文属于赞普赤德松赞为大臣得乌穷颁赏的盟誓碑文。1984年加央的《探讨桑耶寺碑和钟》[2],考察了桑耶寺碑所建年代、造型、文字以及寺内钟的现存状况。1985年恰白·次旦平措的《工布第穆地区石刻文》[3],对工布第穆摩崖上的古藏文作了较为详细的解读。1988年,他又发表《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4]一文,对丹玛摩崖石刻文字的特征、内容、具体方位及年代等进行了论述与考证。1991年索南切加的《西藏古代石碑、石刻文字、钟铭的考释》[5],分别就雪石碑、唐蕃会盟碑等五种碑刻文字进行考释,另外还对叶尔巴寺钟铭文、昌珠寺钟铭文做了简要介绍。1994年次旦格列的《考察古遗址——噶迥寺》[6],以拉玛岗镇的释迦寺作为调查对象,提出释迦寺周围发现的残存石碑为噶迥拉康门前石碑的看法,并对石碑上的古藏文作了详细的注释和解读。

二、2000—2017年间的吐蕃碑刻文研究
随着藏学研究逐渐成为热点,2000年以后吐蕃碑刻研究的范围逐渐从整体宏观的视角落实到细节研究,学术视野亦从国内延伸到了国外,并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
2001年卡岗·华青太的《略述南诏德化碑》[13],指出南诏德化碑建于766年赞普赤德祖赞时期,它对研究唐朝、吐蕃及南诏的民族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2002年江央达吉的《浅谈吐蕃时期碑文内容》[14],认为吐蕃时期碑文的内容分为以佛教为主的宗教类碑文和以政治为主的政策类碑文两大类。夏吾索南的《藏文碑文内容述略》[15],通过对吐蕃石刻文的研究,提出噶琼寺碑与桑耶寺碑属于佛教发展为主的石碑,赤德松赞墓碑与雪石碑属于记录君臣功勋为主的记功碑,而唐蕃会盟碑则是记录汉、藏民族关系为主的和盟碑。2004年扎西达娃对贡布雍仲赞石刻文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发表了系列文章,其中第一篇是《贡布雍仲赞石刻文及其位置探析》[16],他在文章中提出雍仲赞石刻文是赞普赤德松赞在位时与工嘎布王缔结的盟约,该石碑立于林芝县门日区广久乡雍仲赞村,故命名为工布雍仲赞石刻。随后他的第二篇论文——《贡布雍仲赞石刻文字及其几部摹本比较研究》[17],通过比较研究对工布雍仲增摩崖刻碑原抄本中出现的错误部分进行了校勘和阐释。第三篇论文发表于2006年[18],作者在对前两篇论文作了补充的同时,将工布雍仲增摩崖刻碑文中出现的部分难解或争议较大的古词语部分以宗教源流及新的研究成果为依据进行了全新的解析。贡仲美郎尊的《卫堆夏拉康碑文略考》[19],分别就夏拉康的历史、碑文内容、语法作了简要讨论。为方便读者,文章结尾作者附有夏拉康的全部碑刻抄录。久美的《略谈吐蕃时期碑文内容》[20],以约十座石碑作为研究对象,指出石碑内容可分为记载赞普功勋为主的碑文;记载佛法昌盛不灭而君臣间所立的盟约碑文;赞普颁发的为纪录有功勋之将臣的伟业的特殊碑文;汉藏民族友好关系内容的碑文等四大类。热贡·强巴的《甥舅会盟碑文语法特点初探》[21],通过文献比较研究法,认为藏文二次厘定时藏文的形态并未出现较大的变化。索南才让的《敦煌古藏文文献、碑文藏文语法与吞弥·桑布扎藏文语法之比较研究》[22],以敦煌文献和石碑、钟铭、简牍为依据,对藏文语法理论《三十颂》《音势论》为吞弥桑布扎所著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并提出《三十颂》《音势论》的注释是随着藏语文的发展而被后世学者们不断完善并形成的集体性成果这一观点(1)对此,多丹和恰白·次旦平措就这一争论各自撰写了一篇论文(可参考多丹:《初论〈三十颂〉、〈音势论〉两部藏文语法书是否为公元七世纪作品?》,载《中国藏学》(藏文版)2003年第3期);恰白·次旦平措:《藏文语法理论发展历史阶段初探》,载《中国藏学》(藏文版)2006年第1期。据恰白·次旦平措所言,他的这篇论文主要是作为对前一论文的回应而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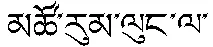

2014年江琼·索朗次仁的《对雪碑最初立碑位置的几点质疑》[33],则依据奥地利人类学研究员恭特朗·哈佐德(Hazod Guntram)和巴桑旺堆的研究成果,通过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雪石碑最初位置的问题进行了考证,他认为雪石碑最初立于卫茹禁卫军千户府所属蔡公堂齐(艋)之地,到了17世纪末,迁移至布达拉宫“雪”之地(3)经整理分析相关文献发现,最初质疑雪石碑位置的学者为奥地利恭特朗·哈佐德(Hazod Guntram)研究员,他在2007年根据布达拉宫壁画及汉藏文献,提出雪石碑最初应位于拉萨附近的蔡公堂。。巴顿的《试探谐拉康碑来源及其立碑位置》[34],以当地传说为主要线索,介绍了两座石碑的来源、立碑的方位,进而提出两座石碑最初位于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北侧的索扎岩(糍B跬B糨B)。阿贵的《洛扎摩崖石刻中的吐蕃历史人物考察》[35],主要探讨了洛扎摩崖石刻中出现的德曼德琼忠心于赞普赤德松赞,其后裔执掌特殊权利的历史信息。夏吾卡先的《琼结桥碑相关问题探析》[36],考察琼结桥头碑文时,发现其有被修正过的可能性,并指出该石碑是17世纪从赤松德赞墓前迁移至今琼结雪之地。古格·次仁加布的《略述西藏昌都芒康县新近发现的吐蕃时期大日如来石刻像》[37],对芒康县境内发现的大日如来石刻像作了论述,进而提出该石刻是典型的吐蕃时期石窟艺术,它的发现对研究唐蕃时期的历史、宗教、文化和石刻艺术具有重要价值。桑吉苏奴的《浅谈唐蕃会盟碑中的汉藏音译》[38],以唐蕃会盟碑为例,主要探讨了吐蕃时期的汉藏音译的方法和实践,并期望后人从事翻译工作时能遵循和传承前贤译者的宝贵经验。由陈庆英、马丽华、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等撰写并由加央平措和呷南翻译的《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时期的藏文碑刻》[39],对巴基斯坦索卡杜境内发现的吐蕃时期碑文进行了解读与校译,提出该石碑是当地民众为见证菩提节而举行供佛法会和祈愿功德回向于赞普王室而建立的,对研究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吐蕃时期的佛教活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文是加央平措和呷南从事古代吐火罗与象雄、吐蕃之间的佛苯宗教文化交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普玛吉的《拉萨雪碑与桑耶兴佛证盟碑的社会背景考析》[40],通过拉萨雪碑和桑耶石碑比较,分别探讨了碑文的语法特征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三、简要评述与探讨的问题
综上所述,以上学术成果不仅推动了吐蕃碑刻文的研究进程,而且还对后人继续研究吐蕃时期的各类文献以及社会文化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参考史料。下面笔者对这些研究成果予以简要评述并对存在的问题略加探讨。
(一)研究成果评述
1.根据近35年来发表的论文增长趋势不难看出,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吐蕃碑刻文的整理和学术研究。据笔者粗略统计,自1982年藏文学术类刊物创刊以来,用藏文撰写的相关学术论文有50余篇,其中1982—2000年之间发表过12篇,2000—2017年之间发表过38篇。笔者在搜集过程中由于条件受限、资源短缺等原因仅收集到以上的这些论文,可能对于相关研究成果收集方面出现涉足不全或遗漏的现象,这亦是本研究后续需要努力补充的地方。
2.在以往研究中,吐蕃碑刻研究领域对各地新发现的有关碑刻文的整理和研究比较多,其中有些论文对石碑原文进行抄录和释读,这对于处理吐蕃碑文中的疑难词汇和解读原文极有帮助;而有些学者探讨了藏语文的发展历程,其研究成果对藏文语法的某些问题起到了校正作用。但同时,学者们也对《三十颂》《音势论》的作者归属问题出现了争论,这样既方便读者全面了解语法的演变规律,也为后人在这一方面继续研究提供了方便。
3.藏传佛教后弘期,建于吐蕃时期的部分石碑被迁移至其他地方,导致后人在研究考证石碑最初所立的位置、历史地名的真实性等方面遇到了诸多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有学者以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式对其进行考证和研究,这一研究还原了现有石碑的最初所立位置,纠正了混乱记述,更充分挖掘了吐蕃时期石碑的研究价值。
4.敦煌古藏文文献以及在我国藏族地区乃至我国毗邻的外国境内发现的碑刻文献,都为研究吐蕃时期的历史人物和社会文化方面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譬如,有些学者对青海都兰县吐蕃墓的主人做了考证;有些学者对协拉康北面发现的墓碑进行反复考证后,认为该墓碑是为了纪念董氏家族的丰功伟绩而建立。这一系列考证与考究,对真实还原历史真相和深入了解吐蕃时期的社会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5.“喜马拉雅西部地区”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我国乃至喜马拉雅西部地区对吐蕃时期藏族文化的研究内容,而且为吐蕃碑刻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开拓了新的视野。
6.以往研究中除了云南丽江格子吐蕃碑之外,其余如青海都兰3号吐蕃墓石刻文和琛妃墓刻文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都是学界不曾关注的对象,这两块墓碑是多麦地区最早出土发掘的吐蕃时期的碑刻,对考究吐蕃势力如何扩张到多麦地区的历史问题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7.从研究方式来看,学者们都比较侧重于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吐蕃时期石碑原文的解读和各种历史问题的考证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助于深入了解吐蕃碑文的历史信息。
(二)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1.就吐蕃碑文研究的整体现状而言,有很多学者仅仅把碑文的原文抄录和解读以及历史价值作为研究的关注点,反而对碑刻图案的演变历程、佛像图案的刻写方式,还有对佛塔、狮子和龙的图案特征等艺术价值方面和相关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稍显不足。
2.就研究者而言,吐蕃碑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布雍仲增摩崖刻碑、唐蕃会盟碑、雪石碑、谐拉康碑、玉树贝纳沟摩崖刻碑、噶迥拉康碑、洛扎摩崖刻碑等碑刻上,而且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相对而言,学者们对桑耶寺碑、芒康大日如来石刻、南诏德化碑等碑刻的研究较少,尤其勃律碑、工布朗嘎碑、扎耶巴石刻的关注度和研究论文则非常稀少。
3.以往研究中,单篇文章的成果较多,但对吐蕃碑刻文献有集中性、专题性的研究并形成专著的则较少(4)目前,研究吐蕃石刻方面已出版的专著为《甥舅石碑与吐蕃和唐朝之间的关系》一书,此书系学者高瑞在西北民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的毕业论文,1986年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4.喜马拉雅西部地区石刻研究近几年才开始,还有许多研究范畴未开垦,由此,笔者认为喜马拉雅西部地区遗存的吐蕃碑刻文字进行抄录、整理研究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上述尽是笔者个人愚见,其实吐蕃碑刻文献的研究价值远不止于此,还有其他更多历史信息的挖掘需要学者们继续探索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