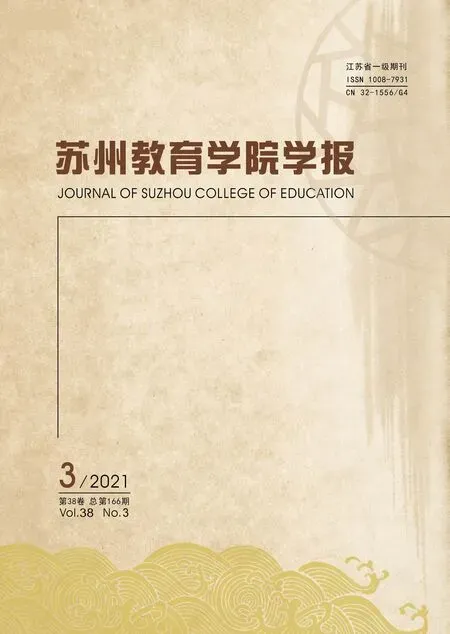“义侠”与“游民”:霍桑与明智小五郎比较研究
张子康
(关西大学 东亚文化研究科,日本 大阪府 564-8680)
侦探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如同一颗流星,虽有耀眼的光芒,却终究一闪而过,消逝在黑夜中。然而,侦探小说①日语中的“推理”与“侦探”本为同一个意思。把“侦探小说”改称为“推理小说”,是日本小说家木木高太郎首先提出的,当时文坛对此反应冷淡。后来日本实行文字改革,“侦”字被废止,文艺界这才用“推理小说”替代“侦探小说”之称。却在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生根发芽,蓬勃发展,日本成为了当今侦探文学最为兴盛的国家之一。这巨大的差别是由复杂的内、外因素造成的。在当下中国本土的侦探小说创作再度起步的背景下,回溯历史,希望能从中日两国文学中的名侦探形象那里获得启迪、助益。
从范伯群、陈平原等学者开始,对以往被忽略的中国通俗文学的发现和研究逐渐深入,然而对属于舶来品的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的比较研究工作还尚未完全展开。没有这部分的工作,就不能发现这些由西方引进的文学类型的本土化创作在世界范围处于何种位置,更不能全面了解创作的得失。除了与发源地欧美的比较以外,也不应该忽略同为接受者的日本这个重要的参照对象。就侦探小说而言,除了柯南·道尔和他的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其他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少有深入研究,日本侦探小说更是被忽视,以致不少研究者将江户川乱步归为“本格推理派”,这是不准确的②常大利的《世界侦探小说漫谈》(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出版)将江户川乱步归为“本格派”,而江户川乱步在《推理小说今昔》一文中提到日本本格作品很少:“我自己也是如此,只写了《心理测验》等几篇本格作品,其他作品大都是怪奇小说路线。”参见江户川乱步:《幻影城主》,新星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144页。。因而,在对世界侦探小说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将中国侦探小说放入其中进行比较研究,是必要且有意义的。
本文选取程小青和江户川乱步这两位极具代表性的侦探小说作家,探析其笔下的霍桑与明智小五郎这两个名侦探形象的异同之处,在比较中进一步明晰霍桑形象塑造的优劣得失与文学地位,并进而探究近代中日两国侦探小说为何走向不同的发展路径及其对当下的启示。
一、东方脸的西洋侦探:霍桑与明智小五郎的共性
侦探小说虽以破案情节为核心,但名侦探形象却往往比设计巧妙的诡计和精彩的推理过程更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欧美侦探小说大师的成功往往离不开对名侦探形象的成功塑造,杜宾、福尔摩斯这些大侦探形象在系列小说作品中被逐渐强化和完善,也将一个个单独的作品串联起来。尤其是福尔摩斯形象获得的巨大成功,使之后的侦探小说家们无不懂得创造一位名侦探的意义。中日作家们与侦探小说第二个黄金时期的莫里斯·勒勃朗、阿加莎·克里斯蒂、艾勒里·奎因、切斯特顿这些大师一起精心塑造了属于本国的名侦探,在亚森·罗宾、波洛、奎因父子、布朗神父等这些登场的后起之秀中,终于出现了亚洲面孔。
1914年,程小青以处女作《灯光人影》参加上海《新闻报》副刊举办的小说征文大赛并获奖,霍桑由此登场,并且在接下来的50多部作品中被塑造成中国侦探小说史上最为成功的名侦探形象。而日本第一位名侦探形象——明智小五郎——在10年后才出现。被称为“日本推理小说之父”的江户川乱步在1923年发表《二钱铜币》后获得成功,并开始创作侦探小说,在次年发表的《D坂杀人事件》[1]中,日后日本家喻户晓的名侦探明智小五郎初次登场。霍桑与明智小五郎在接下来的20年间活跃在中日侦探文学中,作为各自国度的第一个名侦探形象,除了观察力强、思维敏捷、拥有打斗能力等显而易见的共同特征外,霍桑与明智小五郎最大的共性在于——他们都带有明显的西化特征,是超脱于现实的理想中的文学形象。
霍桑具备的逻辑推理能力及科学知识无一不是西方的舶来品,并且还有着拉小提琴这样在当时中国少见且高雅的爱好。从一开始,程小青就有意让霍桑与助手包朗不那么“中国”,这从他们颇为西式的姓名上就可见一斑,程小青在《霍桑和包朗的命意》一文中解释了为这对搭档起名的用意:
我以为“王福宝”、“李德胜”等名字,一进人家的耳朵,随俗固然随俗得多,但同时脑室中,不能不发生一种挺胸、凸肚、歪戴帽子、衔雪茄烟、翘大拇指等可怕的现状。若使说这种模样的人物,乃是守公理、论是非、治科学、讲卫生的新侦探家,那就牛头不对马嘴,未免要教人笑歪嘴了。原来我理想中的人物,虽然都子虚乌有,却也希望我国未来的少年,把他们俩当作模范,养成几个真正的新侦探。[2]
可见程小青有意将霍桑与传统公案小说中的官老爷、判官区别开来,创造出当时中国并不存在的“新侦探”,目的就是更好地展现和传播西方的科学、理性、法制、卫生等精神。
江户川乱步笔下的明智小五郎则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①笔者所见到的研究中,福田裕子将明智小五郎的变化分为“初期”“移行期”“安定期”,考虑得更为充分、合理,但是本文并非以此为重点,所以将明智小五郎的形象分为前、后期更便于比较研究。此外,在江户川乱步1955年发表的《化人幻戏》中,已经50岁的明智小五郎回归到最初运用心理分析方法解密的“安乐椅侦探”,但这不在本文考察的时间范围内。,但始终是一位“洋”侦探。在《D坂杀人事件》中初次登场的这位名侦探被认为是典型的“高级游民”,所谓“高级游民”,指的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一定的财产、没有固定职业、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一类人。文中的“我”在介绍明智小五郎时就明确地说:“他的经历、谋生手段、人生理想目标等等,我一概不知。不过有一点我倒是可以确定,他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游民。”[1]31另外,这时的明智小五郎颇有日本浪人的风采,“明智和我年纪相仿,不超过二十五岁。体形偏瘦。如前所述,他走路时有个甩动肩膀的怪毛病……明智的头发较长,蓬乱毛躁纠结成团,跟人说话时,他还会习惯性地用手指把那原本乱糟糟的毛发抓得更乱。至于服装,他向来不讲究,棉质和服上系一条皱巴巴的兵儿带”[1]31。其后发表于大正年间(1912——1926)的《心理测验》《黑手组》《幽灵》等短篇小说中,明智小五郎基本维持这种外在形象和偏好运用心理分析的探案手法。然而,在192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蜘蛛男》中再次登场的明智小五郎,已经彻底变了样子:
白色立领西装配上白皮鞋,雪白的遮阳帽,形状奇特的手杖,帽子底下是晒得黝黑的脸孔,鼻梁高挺。手指上戴着一枚约一寸宽、充满异国风情的大戒指,缀在上面如黄豆大小的宝石闪闪发亮。他身材颀长,一眼看过去以为是来自于非洲或印度殖民地的英国绅士,又有点儿像久居欧洲的印度绅士。[3]
此时的明智小五郎虽然外表上变成一副“洋绅士”的模样,与之前截然不同,但其内核依然还是所谓的“高级游民”,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不受物质的束缚,寻求智力上的挑战与精神上的刺激。这种“高级游民”本身就是日本在西方物质与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快速蔓延的城市化、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等多方面社会经济文化的产物。早期的明智小五郎虽然一副日式装束,但是他在西洋书堆得满满的房间中沉迷于阅读和研究,具备了完全的西式思维,因此他能自如地运用心理分析的推理方式,更不要说后期他从内到外已经完全变为“洋绅士”。
作为中日侦探小说的先行者,程小青与江户川乱步都自觉地将笔下的侦探与社会中的官老爷、探子划清界限,突出其“西化”的一面。他们与东方拉开距离,努力接近西方,这正表现出在东西方文化碰撞时期的知识分子所作出的选择。
二、惩恶扬善与以解谜为乐:中日“福尔摩斯”的异质
假使霍桑与明智小五郎相会,共同侦破案件,霍桑一定会皱起眉头,明智小五郎想必也会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两人在破案手法、为人处世上,都迥然相异,合作必然会不欢而散。
在破案手法上,霍桑和明智小五郎各有偏重。霍桑是通过典型的福尔摩斯式观察推理来破案的。程小青在《从“视而不见”到侦探小说》中提出,我们的观察力薄弱到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的地步,而侦探小说就是治疗这个“病症”的“药膏”,因为“侦探小说中的侦探,自然个个都有精密的观察力的。我们读得多了,若能耳濡目染,我们的观察力自然也可以增进”[4]228。然而在《D坂杀人事件》中初次登场的明智小五郎就驳斥了“我”利用观察力进行的推理,并指出“人类的观察力与记忆力其实相当不可靠”,而明智小五郎运用“心理式地看透人的内心”的方法找到了真凶。[1]40-41导致这种差别的一大原因是程小青和江户川乱步的创作时间相差十余年,这期间,侦探小说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快速发展和传播,柯南·道尔之后,又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侦探小说作家,他们笔下的侦探们的探案手法也在“更新迭代”,这使得以江户川乱步为代表的日本作家有了更多的模仿对象和学习经验。“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就将心理分析的方法运用在侦探小说中,她笔下的波洛是满脑子“灰色细胞”的心理大师,常常能够不紧不慢地将犯人揪出来,这类新的侦探形象与早期的明智小五郎是比较接近的,包括江户川乱步在内的不少日本侦探小说作家也的确受到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影响。
在具体的人物设定上,霍桑与明治小五郎也有诸多差异。相较于霍桑,明智小五郎身上没有“福尔摩斯”式大侦探的经典设定,比如明智身旁没有华生这样的助手兼搭档,直到后期才有了小林秀雄这位不那么典型的少年助手(实际上在一系列的少年侦探故事中小林秀雄才是主角);明智也不像那些名侦探般不近女色,在《魔术师》中,明智就倾心于委托人妙子,之后又与杀人犯的女儿文代结婚;后期的明智几乎难以用“侦探”去定义,他在“冒险动作剧”中大显身手,少有精密的推理,更多展现的是其神乎其技的变装和打斗能力。从以上列举的三点来看,明智就与“东方福尔摩斯”霍桑有明显的区别。明治小五郎后期形象中越来越少有福尔摩斯的影子,这是由于江户川乱步逐渐走向了所谓“变格派”侦探小说的路径,“变格派”是日本侦探小说的独创,从艺术追求、故事情节、人物设计等各方面与西方侦探小说渐渐拉开了距离。
霍桑与明智小五郎迥异的性格特质使他们对推理破案的目的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一深层次的差别来源于各自的创作者截然相反的侦探小说理念,并受到两国的文学观念、社会环境的综合影响。
作为中国文学中的首位侦探,霍桑所表现出来的侠肝义胆、忧国忧民的性格特征是本土化的鲜明表现,也是这个文学形象最具价值的地方。在程小青的第二部作品《江南燕》的开篇,借包朗之口对霍桑进行了介绍,尤其强调其“性格顽强,智睿机警,记忆力特别强,推理力更是超人,而且最善解人意,揣度人情”[5]243等能够成为侦探的过人之处,并且着重说明了霍桑“痛恨罪恶,痛恨为非作歹,见义勇为,扶助贫困压制强权的品格”[5]244。关于霍桑的性格特征,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归纳得很充分了,在这里将着重分析原因。第一,常常名列“鸳鸯蝴蝶派”中的程小青实际上是近代“新小说”的继承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实践者。他在《谈侦探小说》一文中明确表明自己“为人生的艺术”的观念,肯定侦探小说的功利作用。他认为,侦探小说不仅有助于激发国人的“好奇心”与“观察力”,这于社会的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还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建立有所助益。[4]220-224程小青还在《侦探小说在文学上之位置》一文中否定了西方将侦探小说斥为不入流,排斥在文学之外的做法,认为“侦探小说于诉诸情感之外,兼含智的意味,其推理论情,既须合于逻辑,而情节之演述更须有科学之依据。往往于无形中助长读者之思考力及社会之经验”[4]225。秉持这样的创作观念,程小青将鄙视名利、乐于助人、除暴安良、服务社会等品质赋予一个私家侦探,有着明显的理想化色彩,更是希望可以感染读者,使社会风气能有些许改善。第二,公案小说对程小青的创作有所影响,比较明显的是霍桑并不完全遵循法律,有时采取更符合人民意愿的“情判”方式,甚至亲自对为非作歹之人予以惩罚,如在《乌骨鸡》中他“敲诈”了身为小官僚的委托人一笔,并将之捐赠给民众团体。第三,一直以来,文学功利观为主流,文章乃“经国之大业”(曹丕《典论·论文》)的说法被传统文人奉为圭臬,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更将小说与诗歌等量齐观,大力宣扬小说开启民智的社会功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是程小青赋予霍桑更多功利色彩的外在原因。
反观明智小五郎,在严肃、认真、充满社会责任感的霍桑面前,他更像是以破解谜题为乐,追求惊险刺激,自由无羁的孩童,这正是所谓“高级游民”的精神表征。最重要的是,江户川乱步所持的侦探小说观与程小青的是相反的。他在《一名芭蕉的问题》《再论侦探小说之宿命》《评侦探小说纯文学论》①需要说明的是,“文学”一词在江户川乱步的论述中比较混乱,在这里,按照他的说法,“文学”应该是创造典型性的现实主义文学,有时也指“变格派”猎奇、惊险、刺激但缺乏谜团和推理的创作,当然不论是指哪一种,江户川乱步对侦探小说的功利观都是不赞同的。等文章中专论自己对文学与侦探小说的看法,他认为,侦探小说最重要的是趣味性,“我当然并不排斥文学,但我认为不管具有多么出色的文学性,若是在谜团和逻辑的趣味上不够出类拔萃,那么以侦探小说来看就是无趣的”,“想要接触人生机敏细微之处时,我不会从侦探小说中寻求,而是亲近普通文学”,“所追求的中心主题是巧妙建构的谜团,以及抽丝剥茧时逻辑的乐趣”,“很早以前,我骨子里就是个侦探小说游戏论者”。[6]156-174因此,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的明智小五郎,在侦破案件时都绝无惩奸除恶的想法,对于死者也无怜悯之情,甚至经常给罪犯设下圈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羞辱对手。文学传统的差别在两位作家身上有着深刻的体现,相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学功利观,日本文学有一种鲜明的“脱政治性”,即追求文学本身的价值。“日本的传统文学向近代文学的转型,是明治维新这一政治运动的结果,但日本近代文学依然保持了与政治疏离的姿态。”[7]另外,江户川乱步还深受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等人的影响,在其侦探小说中表现出一种对病态、变态的美感的追求。明智小五郎身上就表现了作家的这种欲望和特征,他对血腥而残酷的“人体艺术品”表现出兴奋和激动之情,对于变装甚至是女装的热衷,这些癖好使这个艺术形象更加复杂。
综上所言,由于作者的创作观念、模仿对象乃至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霍桑与明智小五郎两位侦探在探案手法、人际关系、性格特征诸多方面的差异。
三、成熟与僵化:比较视野下的霍桑
(一)本土化创造的成熟侦探形象
西式侦探霍桑的出现为中国文学人物长廊中增添了从未有过的新形象,科学、法制、理性等新思想是组成这位名侦探的精神要素,但他的精神内核依然是中国式的侠义,这使霍桑这一形象得以立足中华大地,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侦探。程小青自觉地将侦探小说与社会现实相联系,霍桑为了拯救劳苦大众、医治社会弊病不辞辛苦地奔波,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已经超越了福尔摩斯式的侦探,与大洋彼岸的美国在1920年代兴起的“硬派侦探”、日本在“二战”后大为兴盛的“社会派推理”遥相呼应。霍桑不仅仅是中国最早的侦探形象,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社会派”侦探形象之一。程小青所作的本土化改造不仅是一种适应,更是一种创新,这种创造性是在考察霍桑形象时最应该肯定的价值所在。
与明智小五郎相比,霍桑形象更为成熟稳定。明智小五郎的形象不断变化,后期越来越单薄,他最后出现在少年侦探系列中时已不具备在《D坂杀人事件》中的风采。笔力的欠缺是江户川乱步的一大缺陷,后期被称为“冒险动作剧”的通俗推理小说中的侦探和罪犯,都如同皮影戏中的人物般轻飘。除了效仿福尔摩斯这个经典形象作支撑外,程小青早年翻译外国侦探小说所练就的文笔,在刻画霍桑这一形象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异常勤奋的程小青为了追求精益求精,对原来的小说进行数次修改,因而几十篇侦探小说中的霍桑形象一以贯之,日臻完善。
(二)形类有余,趣味不足
人们常道日本人善于模仿,却忽略了他们学习借鉴后的创新,他们的创新精神开拓了日本侦探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疆域。江户川乱步在《论日本侦探小说的多样性》中说:“我们才短短十多年历史的侦探小说界,与拥有数十年历史的英美侦探小说界相较起来,也可以说绝不逊色。”[6]114“本格派”“变格派”“社会派”“新本格派”“温情派”“日常派”等类型接连出现,江户川乱步的创作就涉及广义的侦探小说中的多种类型,这种尝试精神是其留下的财富之一。就侦探形象而言,除了鼎鼎大名的明智小五郎,还有同样深受欢迎的少年侦探小林秀雄,以第一人称登场的身份各异的业余侦探,这些侦探形象无一例外都是江户川乱步的自创。
就侦探形象的艺术水准和成熟度来说,霍桑超过了江户川乱步笔下的所有侦探形象,但是,他始终没有摆脱福尔摩斯的影响,并且在30余年的时间中,程小青也未能为霍桑增添新的要素,这的确是巨大的缺憾。程小青在广泛阅读当时的侦探小说后,选定福尔摩斯为模仿的对象,可谓独具慧眼,效仿世上最为成功与著名的侦探形象是起步阶段的一条捷径。但这种模仿在某些方面太过“细致入微”,反而损害了其价值。如福尔摩斯喜爱小提琴,霍桑也爱小提琴,并同样在事件进展不顺利时作调整思路之用;福尔摩斯擅长格斗,霍桑就习中国传统技击;福尔摩斯好卖关子,霍桑常常给代替读者询问的包朗吃“闭门羹”。凡此种种,就连搭档的形象和作用也是大同小异,不得不说程小青的人物创作没有迈开步子,甚至于在接下来的30余年创作中,霍桑还是遵循着古典侦探小说的传统,缺乏变化,对世界侦探文学的风云变化也有些“视而不见”。
霍桑的形象也过于单纯,如他的身边只有助手包朗。福尔摩斯有一个比他还要聪明的哥哥,对艾琳·艾德勒抱有特别的情愫,莫里亚蒂教授是他的死敌;明智小五郎则有爱人文代、助手小林、其他朋友及死敌二十面相。这里暂且不论霍桑作为主角功能化和符号化太过严重的问题,过于单纯的形象使其趣味性大大降低,没有爱情、亲情,也无棋逢对手的对决,作为通俗文学的主人公来说丢失了太多必要的元素。
当然,霍桑绝不是没有变化和发展的,池田智惠认为,在程小青1940年后创作及重新改写的作品中,霍桑的形象越来越接近警官而非侦探。当司法问题逐渐成为小说关注的重心时,霍桑也演变成一个科学理性的司法执行者和改革者的形象。如此,霍桑不再是一位“都市游侠”,而变得更加严肃认真,这种变化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小说中原本就比较缺乏的趣味性变得更少了。正如池田智惠所说的:“侦探小说是以破解谜题为中心的娱乐小说,阅读的乐趣在于解密的过程,犯人是否受到法律的惩罚并不是小说的关键。”[8]侦探小说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种供读者消遣的通俗小说,程小青让霍桑承担了过多的社会教化责任,忽视了推理,将重心转移到法律、社会等问题上,从而损害了其娱乐性。而江户川乱步则一直宣扬趣味性是侦探小说的正道,因而他在理论上和实际创作中都难以成就杰出的纯文学,这是侦探小说的宿命,他说道:“可是我并不为这个‘宿命’感到悲伤,我无条件地爱着拥有此般‘宿命’的侦探小说。因为这当中有着侦探小说的特异性,有着其他任何文学都无法类比的独特世界。”[6]163江户川乱步在“二战”后转向成为日本侦探文学界的组织者,鼓励创作者更专注于本格的谜团设计和推理的趣味性。
(三)价值与地位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首位侦探形象,霍桑不仅没有水土不服,反而扎根中国土地,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艺术魅力;他形象完整,个性鲜明,堪称中西合璧的典范。1914年出现的霍桑形象,超越了同时代的鸳蝴小说中媚俗的旧人物,呈现出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新人”形象,比现代文学中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早出现了好几年,又比那些往往空有抱负的新青年更具行动力。从世界侦探小说史来看,模仿福尔摩斯的霍桑的确不能与同在黄金时期的亚森·罗宾、波洛、布朗神父、奎因父子等相提并论,然而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平民意识、侠义精神、社会责任感则是上述大侦探们所不具备的,可以说,这方面的创造为霍桑在世界侦探人物长廊中争取到了一席之地。
通过与明智小五郎的对比可以发现,霍桑不仅早出现整整10年,而且人物形象更成熟,文学性也更胜一筹,虽然在创新性和趣味性上有所不如,但二者都是杰出的文学形象。然而与明智小五郎相比,霍桑在中国的影响力与地位还远未被充分认识,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侦探文学在程小青之后并未充分发展,大部分作家都是乘兴而作,兴尽而止,1949年后侦探小说更是逐渐沉寂,如今少有读者关注到近代中国的侦探小说①最新版本的《霍桑探案集》是群众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市面上已经难以找到。;另一方面,近代侦探小说又常被归于鸳鸯蝴蝶派,一并被批判打压,使霍桑这一文学形象的地位和价值长期被漠视。
四、早熟与早衰:近代中国侦探小说的缺陷
缺乏创新性和趣味性并非仅仅是程小青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侦探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侦探小说虽然在模仿阶段成熟得很快,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一条自己的发展之路,代表中国侦探小说创作高峰的程小青与孙了红,一个模仿柯南·道尔,另一个则是模仿莫里斯·勒勃朗。中国本土的侦探小说一直被译介的外国侦探小说所压制,范烟桥曾评价说:“中国的侦探小说创作并不甚盛……市上流行的仍以翻译的为多。”[9]当时主要刊载原创作品的《侦探世界》杂志的主编赵苕狂在停刊时说:“就把这半月中,全国侦探小说作家所产出来的作品,一齐收了拢来,有时还恐不敷一期之用。”[10]虽然程小青和孙了红通过模仿的“捷径”,获得了成功,但是放眼整个侦探小说界,这种创作方式对本土化的进一步发展助益不大,大部分作家创作困难,读者更青睐于翻译作品。缺乏创新是中国近代侦探小说失败的重要原因。
另外,以程小青为代表的作家在创作侦探小说时,背负了太多社会功用的“包袱”,未能处理好社会性与艺术性、趋俗与趋雅的关系。当然,在当时也有娱乐性比较强但未成气候的惊奇冒险类与滑稽类的侦探小说,不过依然缺少侦探小说最应具有的趣味——诡计的设计与推理的过程。纵观近代中国的侦探小说未见有令人拍案叫绝的谜团设计和推理情节,这种趣味性的缺乏使得中国侦探小说失去了灵魂。在侦探小说史上,不论是“变格派”“硬派侦探”,还是“社会派”,都被认为是异类,江户川乱步就批评包括自己的作品在内的“变格派”,缺乏侦探小说的趣味,应该发展本格推理。松本清张引领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之后被推理小说界认为是严重影响了日本本格推理小说发展的“清张魔咒”②“清张魔咒”是指松本清张发表《点与线》之后的30年间,日本推理小说界被“社会派”所统治,本格推理式微的状况。1970年代“新本格派”的崛起终于打破了“社会派”一家独大的情况。松本清张、森村诚一自然是将推理与社会揭露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家,然而在当时上百名“社会派”作者中能二者兼得的人少之又少。,因为这些作品相对缺乏侦探小说的特异性,远离了巧妙建构谜团并破解谜团的中心。
改革开放后,中国本土的侦探小说创作再度起步,然而理论界对于通俗文学的关注点还停留在肯定作品的社会功能方面:谈及侦探小说必强调其普法的作用,科幻小说必谈科普的功效,官场小说就是揭露腐败,武侠小说也和宣扬传统文化联系到一起,等等。这一类论调实际上是不了解通俗文学的特性,是将严肃文学、纯文学的标准套用在通俗文学上的错误偏差。1996年,公安部政治部宣传局、公安部报刊图书出版社、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联合召开了“中国侦探小说发展前景”研讨会,这样的举办方组合着实难以让侦探小说与政治脱钩。1998年,全国首届侦探小说大赛举办,评奖标准将“弘扬法制精神”“弘扬科学精神”“弘扬人文精神”放在首位,可以看出其中的社会功利偏向。一些研究者依然秉持着“文以载道”的观点,对这些条条框框大声喝彩。应该看到,在这套理论观点指导下的20余年间,中国也没有产生有分量的侦探小说作品,这些理论指导是否符合侦探小说的创作发展规律,值得深思。我们要吸取近代侦探小说失败的教训,借鉴日本侦探小说成功的经验,把当下中国的侦探小说与公安小说相分离,自主发展,在谜团和推理等以往被研究者所忽视的“智力游戏”上多下功夫,从人物设置到推理过程都需要增强小说的趣味性,同时坚持本土化创作,走出中国特色的侦探小说创作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