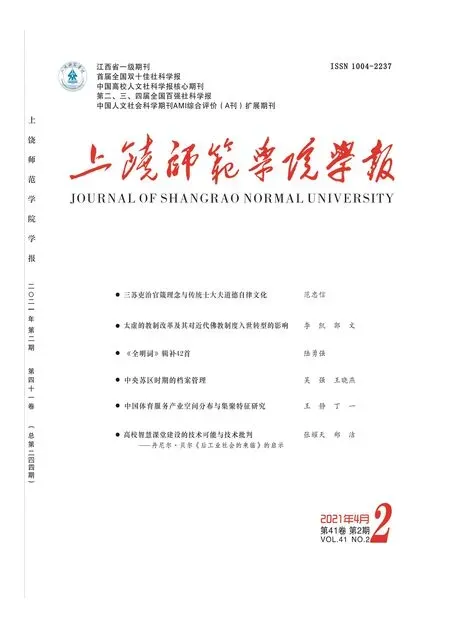欧阳竟无的孔学研究
袁芳林
(上饶师范学院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西分中心,江西 上饶334001)
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的晚年研究开始转向孔学,他最终认为孔子和佛陀都是圣人,而孔学和佛学俱为圣学。他引用陆九渊的语录说:“东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1]631但他也认为,传世儒学中更多的是假孔学,所以他弃“儒学”一词而用“孔学”,表示以恢复真孔学为旨趣。欧阳竟无孔学研究的主要成果都结集于《孔学杂著》和《中庸传》,除了概论和一些书信之外,其余都是关于《四书》的讲解和编次,所以欧阳竟无的儒学研究主要是四书学。对欧阳竟无孔学的已有研究,主要包括程恭让《欧阳竟无佛学思想研究》中的《孔佛究竟会通说》一章、肖平的《欧阳竟无对儒学的贡献》、韩焕忠的《欧阳渐的四书学》,以及胡伟希的《欧阳竟无与〈孔学杂著〉》等。以上研究都认为,欧阳竟无孔学的旨趣在于以佛法融摄孔学,最终达到孔佛会通,最终目的是为了阐明孔学在其佛学体系中的补充作用。欧阳竟无的孔学思想对于我们理解熊十力、牟宗三这一系新儒家思想的开端具有重要的意义。熊十力曾问学于欧阳竟无,而且亦由佛入孔、亲近宋明心学、重视精神阐发、疑经惑古,等等,可以说,新儒学的种种气质和特征都和欧阳竟无的孔学研究有着直接联系。本文立足于儒学本身来阐发欧阳竟无的孔学研究,将之视为儒学自身发展的一个部分。
一、重建道统
欧阳竟无早年曾学儒,对儒家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但终究服膺佛学,两相对比之下他认为:“佛学渊而广,孔学简而晦”[1]616。研究孔学的首要困难是缺乏系统,传世的儒学文献大多是经汉儒整理而恢复成型的,但欧阳竟无认为其中缺乏真孔学的精神,因为汉儒去孔子已远,孔子思想并没有经过真正的结集而得以传承。欧阳竟无感慨道:
道之不明也,于此数千年,究其原始,乃在孔子既没,无结集大儒,缺毗昙大教,秦火汉仪,安知道之攸寄,如阿难、迦叶之于佛教者?故佛学尚有典型,而孔学湮没无绪,可胜叹哉![1]655
欧阳竟无认为孔子之后的大儒只有孟子,而“中国自孟子后数千年来,曾无豪杰”[1]660。虽然荀子的学说影响也很大,但欧阳竟无认为孟、荀之学根本不同,所谓:“数千余年,学之衰弊,害于荀子,若必兴孔,端在孟子。”[1]657综合来看,欧阳竟无的儒学史观有两个特点:一是参照佛教而梳理统绪,二是认孟子之学为唯一正宗。
显然这是儒家道统说的又一版本。自韩愈提出道统之说以来,各种版本的道统说几乎都有这两个特点。道统说的核心是排斥异端和判定正统,二者是一体两面的,正如孟子所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2]276。孟子尽管提出了道统精神和儒家圣人的传道谱系,但道统论成为一个明确的问题还需要特定的历史机缘。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韩愈的道统论是模仿禅宗而得的,他说:“退之自述其道统传授渊源固由孟子卒章所启发,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3]320佛学的刺激使韩愈感受到了为儒学建立道统的迫切性,此后的道统论都是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正的,道统论的修正者都将自己这一系视为孟子之后的正统传人。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4],韩愈的这一感慨代有回响。朱熹说,“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2]15,这是将韩愈排除在了道统之外,而以二程接续孔孟之道。王阳明却认为:“有象山陆氏,虽其纯粹和平若不逮于二子(周、程),而简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传。……故吾尝断以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5]这是说,陆九渊才是孟子的直接传人,周程诸子还可以讨论,但完全不提朱熹。欧阳竟无说:“应知孔子之道晦数千年,当继孟子后大启昌明也。”[1]480他明确强调:“自孟子外,宋明儒者谁足知孔?”[1]479“宋明诸儒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敬告十力:万万不可举宋明儒者以设教也。”[1]480由于后人不断将前人从道统中剔除出去,所以儒家的道统建构始终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道统论以儒家圣人传承的历史叙事作为形式,但各版本道统论之间的巨大差异说明,这不是一个历史考据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孔孟真精神的问题。用欧阳竟无的话说,道统的核心就是如何“知孔”和“继孟”。后儒不能“知孔”“继孟”是蔽于荀学的乡愿流毒,而重建道统就是廓清流毒和重振孔孟的真精神。尽管欧阳竟无在总体上是否定宋明儒学的,但一定程度上对象山和阳明表示了认可。因为陆王心学要求学者以本心去契合圣人之心,个人意志成为把握圣人之意的根本和唯一依据。欧阳竟无用佛学术语也提出了这一要求:“不可宥于世间见,而必超于不思议也。”[1]617如何达到这一境界,他举了两个例子:
临济观佛有鼻有口,曰:我可作佛,他日竟作祖开宗。象山幼时思天际不得,读古往今来,悟无穷无尽,遂为南宋大儒。[1]617
用孟子的话语来解释,临济观佛的意涵可说是“践形”,象山思天际的结论则是“万物皆备于我”[2]357。前者说的是身心关系,后者是天人关系,二者又是一体的。孟子说:“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2]368人以实现人身的潜能为目的,这就是人的“天性”,所以人的目的就是天的目的,这里人心与人身、天地在目的因上是同构的。邵雍说:“天地之本其起于中乎?……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6]。天人、身心最终都归于一心之中,人作为意义世界之中心的价值能挺立起来,无穷无尽的宇宙时空才随之赋有价值。象山在这一感悟下提炼出个人意志的重要性、精神的绝对性,说出了这一名言:“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7]要做一个笼统的区分,可以说朱熹重视知识,而陆九渊强调意志,心学的传统是一种围绕着意志而展开的哲学。万物皆是精神的自我开显,宇宙与人身都归结于人的意志。所以阳明说象山之学就是孟子之学,直接将朱熹排斥在了道统之外。
孟子生活在从宗法社会转向专制社会的时代,但孟子之学却表达了对专制社会的批评和抵触。到荀子的时代专制社会已成事实,荀子虽然继承了儒家学说,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出对专制社会的接受和认同。而韩非之学则完全将荀学中认可专制的这一面发挥了出来,彻底走向了孟子之学的对立面。其中的根本差别在于,孟子以个人意志作为根本价值,而专制主义却主张抹杀个人意志。作为二者之间的过渡,荀子思想的核心特征就是“乡愿”。“乡愿”虽然还不到抹杀个人意志的程度,却表现出轻视个人意志的态度。《荀子·荣辱》篇云:“孝弟原悫,车句录疾力,以敦比其事业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暖衣饱食,长生久视以免于刑戮也。”[8]荀子这里认为道德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衣食和安全,这不正是孔子批评的“民免而无耻”[2]54的状态吗?荀子的“孝弟原悫”完全是工具性的,站在孔子的立场上看这简直不能称之为“道德”,而只是专制社会中的驭民之术,所以欧阳竟无将孟子之后的儒学统称为“乡愿伪儒”。清末到民国的时代,在西方观念的参照下,专制时代的弊端暴露得非常充分,清算传统文化中的专制因素成为时代的声音。欧阳竟无总结道:
新周故宋王鲁,革命之义出于《公羊》,而伪儒以为说经义齐驳,岂是鲁纯?民为贵,君为轻,民权之义出于《孟子》,而伪儒专制之奴,谓孟子泰山岩岩,英气甚是害事。大同出于《礼运》,而伪儒竟谓《礼运》大同之说非孔子之言。[1]647
汉代公羊家将孔子奉为“素王”,试图通过公羊学阐发隐匿在《春秋》经中的孔子学说。清末公羊学复兴,康有为等学者又以“真孔学”的阐释者自居,试图为改制、变法的主张提供合法性依据。欧阳竟无受到公羊家的影响,将“革命”“民权”这些近代政治观念尽归于孔孟,可能有牵强比附之嫌,但孔孟之学尊重个人的价值,商韩之学毁灭人性而彻底服务于专制,其中的分别和对立是确定无疑的。萧公权指出:“宋明诸儒不知儒法二家同道尊君而其旨根本有别。大唱‘三纲’之教,自命承统于洙泗。实则暗张慎韩,‘认贼作父’。且又不能谨守家法,复以尊德贵民之微言与专制之说相混淆。”[9]229荀子之学混淆其中的分别,后儒阳奉阴违“认贼作父”,这也是事实。
在这样一个民族危机深重、民族情绪低落的历史阶段,为了彻底唤醒国人的意志,欧阳竟无大倡孟子的狂狷精神,他说:“沉渊溺淖,至矣极矣!疾雷破山风振海,十日并出,金石流,土山焦,振聋聩于今日者,其唯《孟子》乎?”[1]635压抑的直接原因固然是内忧外患的政局,但深层的原因则是民族文化之主体性的危机,这一危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专制社会对个人意志的贬抑而导致的人格扭曲,二是西方强势文明的威胁而导致的自卑。欧阳竟无坚信传统文化中的真精神可以应对这一危机:
宋明节义之士,如文、史诸人,皆有造于国家,乃至今日抗日犹能长时,无非赖是。……真孔既分别,人皆知孔矣。孔义不但于抗战非常,多可权借,尤于抗战建国非常非常,足以经宗。盖中国哲匠,蝟起林立,于我大本,唯孔相符,同则取之,俾我大本之通于国中也。[1]648欧阳竟无认为真孔学精神是国之大本,这是他晚年转向孔学的根本原因,盖佛学虽然义理广博却毕竟非我民族所固有。在晚清民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际,孔学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这正揭示出道统论的又一历史价值,即陈寅恪总结的韩愈的第四条功绩:“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3]328韩愈强调儒行和佛道有别,这种强烈的分别意识是中华文明主体性的一种自觉。主体总是要对应“他者”而确立,韩愈的主要工作是将佛教思想描述为“他者”。韩愈把佛教称作“夷狄之法”,将之与中华固有的“先王之教”对立了起来,把夷夏之辨作为儒教复兴的首要意识,从历史背景上看,“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3]329。东晋以来长期的民族信心不振是韩愈提出道统说的重要动机,而民国时候更为严重的危机意识则促使欧阳竟无从民族文化的根源处再次要求“知孔”和“继孟”。
当然欧阳竟无对韩愈排佛的立场耿耿于怀:“韩愈误清净寂灭,遂恶清净寂灭,并使千载至今,张冠李戴,岂不冤哉!”[1]660他鄙薄道:“韩愈文人,乌足知道,更何论清净寂灭!”[1]482但是,他对于韩愈的气节却是极为推崇的,认为韩愈之文足以和《孟子》七篇一样被称为“夏声”:
《孟子》七篇,……下而至于韩之文,杜甫、陆游之诗,辛弃疾之词,史可法之疏,乃至忠肝义胆,片言舒郁,莫不皆夏声之所寄。[1]639
“夏声”就是道统的一种表达,欧阳竟无说:“孔子之道不著,轲之死不得其传,夏声乃不得不发。”[1]637因为道统中绝,人心中的郁结之气不得不发,发而为文章,就是“夏声”。尽管韩愈排佛,和欧阳竟无的学术立场不同,但欧阳竟无认为他和韩愈有共同的郁结之气。他们各自在具体时代下面对着同样的道统危机,这是民族主体性不能伸张的共同压抑。
道统论在学术史上的影响不全是正面的,宋明儒的门户之见也往往由道统之争而起。因为道统的确立就内含着对离经叛道者和似是而非者的排斥,道统的正统性正是以排他性作为前提的。这一点尤为欧阳竟无所厌弃,他指出:“愚者不然,曰此禅也、非圣也,死于门户之拘,一任众芳芜秽,天下不知务者又如此也。”[1]631学者将欧阳竟无的立场归结为“会通孔佛”,它不完全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同时也表达了一种民族主义立场。在民族文化面对生死存亡的深重危机时,从其内部发掘道统精神的普遍性而不是自我消解于门户之争,应该是欧阳竟无参照佛学重建道统的心理动机。
二、结集经典
佛学思维特别重视逻辑和系统性,这是中国传统比较欠缺的。建立儒学的系统有不同的维度,汉代经师专注于经典传承的脉络,韩愈道统论梳理儒家宗师的谱系,宋明儒学更关注义理的贯通,三者分别是文献的系统化、历史叙事的系统化和义理的系统化。因为欧阳竟无认为只有孟子得到了孔学真传,后儒诸家大多不被他认可,所以儒家宗师的谱系终结在了孟子这里,问题转换成为如何“知孔”和“继孟”。如此剩下的重要任务就是经典和义理的系统化。
儒学传统本身极重视经典的传承,如陈寅恪所言:“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盖非此不足以征信于人,观两汉经学传授之记载,即可知也。”[3]319但这是史料学或文献学的系统,欧阳竟无所谓的“系统”与此不同。欧阳竟无是从为学的角度来理解经典系统的,圈定核心篇目,说明为学次第,才是他所说的经典系统。他认为,汉人的经学未能真正传承道统:
佛学有结集,有毗昙,三藏浩汗,循其统绪而可读。孔学无是,既扼秦火,又复年堙,于是老师宿儒,曾不能答具体之求,而世无真孔。世既不得真孔,尊亦何益于尊,谤亦乌乎云谤?[1]631
佛学有其统绪,而孔学没有。孔学原本自有系统,但是被破坏掉了,所谓“秦火汉仪,安知道之攸寄”[1]655。“秦火”首先是指商鞅韩非主张的文化专制政策对儒家经典的毁禁,其次秦汉之间的战乱本身也毁损了很多先秦文献。但“秦火”的破坏显而易见,“汉仪”的破坏却在暗处,后者的危害更为深远。汉朝号称儒学复兴,被司马迁讥讽为“汉家儒宗”[10]2726的叔孙通正是“汉仪”的创制者。对于“汉仪”的本质,司马迁说得非常清楚:“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10]1159“汉仪”仍是秦法的延续,朱熹也指出过这一点:“叔孙通为绵蕝之仪,其效至于群臣震恐,无敢失礼者。比之三代燕享,君臣气象,便大不同。盖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11]西汉儒家以董仲舒最著名,但在政治实践上却是公孙弘最重要,后者被汉武帝委以重任完成了“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建设。司马迁却为公孙弘专门创制了“曲学阿世”一词:“固(辕固生)之徵也,薛人公孙弘亦徵,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10]3124公孙弘以儒术干禄,正是孔子“无为小人儒”[2]88一语要批评的对象,也是欧阳竟无所痛恶的“乡愿伪儒”。欧阳竟无感慨道:
二千余年,孔子之道废,乡愿之教行。孔子谋道不谋食,乡愿则同流而合污;孟子舍生而取义,乡愿则曲学以阿世。[1]644
所以恢复孔学的首要工作就是恢复孔子之教,申明君子小人之义、严判义利之辨应该成为核心问题。欧阳竟无认为传世的《论语》《孟子》版本都未能突出这一主题,所以无系统可言。而儒家的传世经典中只有《中庸》是有系统的,所以需要阐明《中庸》的系统,重新编次《论语》《孟子》。为了帮助后辈学习孔学,他自编了《论语》《孟子》的读本。他说:
孙辈读经,苦无课本,类而聚之,曰《论语十一篇读》也。仓卒应求,粗疏无当,若必组织成统绪谈,须萃群经,大其结集,然后有济。[1]632
传世的《论语》分20篇,每一篇取首二三字为题,其实是无题。各篇的内容也并非按照特定主题来编排,所以确实缺乏系统性而略显杂乱。欧阳竟无重新将其编排为11篇,为各篇加上题目,按照为学次第结为系统:“始之集《劝学》、《君子小人篇》而读,以定其趣也。终之集《群弟子》、《古今人篇》而读,以博其义也。”[1]632
编排《论语》是为了突出君子小人之辨,编排《孟子》则着重于乡愿的批评以及义利之辨。他说:
人之所以为人者,气也,节也;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也;是三者、天下之大本也,如是读《气第一》、《士第二》、《民第三》。仲尼之徒,崇本而黜末,如是读《义利王霸第四》。[1]635
欧阳竟无将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规定为气节,即不屈服于专制压迫的自由意志。因此,他裒辑孟子语录,以关于“气”的内容作为开篇,接以“士”的尊严作为次篇,第三篇突出“贵民”为目的的政治理想,第四篇的义利王霸之辨包含着对专制思想的批评,第五篇以后讲仁政、孝悌等具体节目。中国哲学一向被诬为不讲逻辑和缺乏体系,但经过欧阳竟无编次的《孟子十篇读》竟隐然有了类似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般的结构:从自由意志和人的尊严讲起,落实为民权为本位的社会结构,再进一步到设计具体的政治结构。
如前文所述,欧阳竟无将批评乡愿作为认识真孔的前提。“乡愿”就是以“乡人皆好之”[2]148而自居的一种状态,表现为对习俗和外在评价的完全认同,实质上是以彻底丧失自身立场来实现的。孟子非常痛恨这种人,认为他们“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因为正面的挑战(杨朱墨翟之言)是可以直接回应的,而“乡愿”者则保持着似是而非的含混样貌,所以“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2]384。反之,狂狷精神之所以可贵,因为狂者不惜以遭受习俗批评为代价而表达个人意志。士的气节首先就表现为坚持个人的道德信念而不屈服于政治压力,孟子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2]358而在商鞅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中,君主之“势”是压制其他一切原则的,所以尊君是法家的政治目的。萧公权说:“儒家贵民,法家尊君。儒家以人民为政治之本体,法家以君主为政治之本体。……尊君至极,遂认人民为富强之资,其本身不复具有绝对之价值。”[9]191法家思想中君主是目的,而“民”只是手段或质料。孟子“民贵君轻”的主张正是为了批评法家的专制思想,完全扭转这一关系,指出“民”才是目的,这一政治主张就是所谓“仁政”。所以“仁政”的本质是以人为目的,而“仁政”思想的起点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肯定。正因为如此,“乡愿”者身上那种浑浑噩噩和麻木不仁的气质,在欧阳竟无看来就是甘于放弃个人意志而沦为专制之具的人格表现。
儒家经典中,欧阳竟无对《中庸》的研究最为完整,他认为《中庸》一书最具系统,可以作为孔学的概论:“学有概论,乃有系统,虽不得全,犹知其概。孔学有系统谈,止是《中庸》一书,《大学》犹所不及。”[1]658欧阳竟无非常重视对学说系统的提炼,于是创作《〈中庸〉传》来揭示其系统。和传统儒学注疏经典的工作不同,欧阳竟无不太注重具体文义的训释,在需要讲解的地方常常直接引用朱熹的解释。《〈中庸〉传》虽然也是对《中庸》全文的逐段讲解,但主要是通过阐述各段落之间的关联来显示孔学的系统性。所以,《〈中庸〉传》的核心工作是利用《中庸》的文本建立一个结构,文义解释都是为这个结构服务的。
为了方便讨论《中庸》的结构,我们仍然沿用朱熹的传统分章。朱熹将《中庸》分为33章,从文本形态上可以分成两部分:前20章大量引用“子曰”的语录,集中讨论“中庸”之德,朱熹认为这是孔子的思想;后面13章集中讨论“诚”的问题,朱熹认为这是子思的阐发[2]33。用儒家经学的术语说,前半部分是经,后半部分则是传。
欧阳竟无抛弃了这一传统结构,他按照佛教的讲法将《中庸》分为三个部分,即所谓“文诠三义,为三科:曰略论,曰广论,曰结论”[1]660。原来的第一章为第一科略论,原第二章至第三十二章为第二科广论,原第三十三章为第三科结论。第一科略论分三层讲明“《中庸》三大义”;第二科广论有31章之多,欧阳竟无将其分为六段,成为“三大义”的具体论证;第三科结论则重申“三大义”以“结而论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精致的结构,首尾各一章用来树立观点前后呼应,中间31章则具体阐发。和经学家将之分为两个部分的做法不同,他将《中庸》阐释为一个精心布局首尾一贯的义理整体。
欧阳竟无虽然非常重视系统性,但他认为系统不是一个空的结构。系统必须落实为真实本心,真实本心的开显即为系统,所以他说:“万变唯心,组成绪统,如何非学!”[1]463前文提到,朱熹重视知识而陆九渊强调意志,这是传统宋明儒学的理学、心学两大系。在这个问题上,欧阳竟无是认同陆王心学的,他指责朱熹的知识建构缺乏真实本体。佛学中这个本体称作“寂灭寂静”,欧阳竟无认为孔学的本体也应如是:
孔道概于《学》、《庸》,《大学》之道又纲领于
“在止于至善”一句,至善即寂灭寂静是也。[1]618
孔学中没有“寂灭”之语,欧阳竟无用《易传》中的“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诸语去比附。为学的根柢在于本体,欧阳竟无认为《中庸》中的“素隐”一词最能表达这一实在。
三、发挥素隐
按照欧阳竟无的梳理,《中庸》义理结构的核心是“三大义,曰修道,曰素隐,曰不已”[1]660,《中庸》全文都是为了开示这“三大义”而展开的。欧阳竟无又说:“隐,道也;素隐,修道也,素隐而不已,修之成也。”[1]660可知这“三大义”根本就是一义,所以他说:“中庸三大义,根依惟在素隐”[1]665,“诚哉!中庸之为书也,素隐之书也”[1]680。
“素隐”一词出于《中庸》第十一章:“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2]21欧阳竟无解释说:“素隐之名立于此。素之为言本也,隐之为言寂也,不言本寂而言素隐,则中庸之言也。”[1]664这里将“素隐”解释为“本寂”,连同前文提到的“修道”解释,都是说人生的根据立于这隐微之道。这种解释很难说符合《中庸》的文本原意。
对于这一章,郑玄的解释是:“傃,犹乡也。言方乡辟害隐身,而行诡谲以作后世名也。”[12]1668孔颖达在此基础上进行疏解,认为:“谓无道之世,身乡幽隐之处,应须静默。若行怪异之事,求立功名,使后世有所述焉。……如此之事,我不能为之,以其身虽隐遁而名欲彰也。”[12]1669我们知道,《中庸》后文紧接着说:“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2]22因此,孔颖达的解释是有根据的。简单地说,“素隐”就是向隐、归隐,是圣人在“无道之世”的选择,本身无可厚非,而“行怪”则是为了欺世盗名,所以圣人“弗为之”。
朱熹的解释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素,按汉书当作索,盖字之误也。索隐行怪,言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盗名,故后世或有称述之者。”[2]21由于《汉书·艺文志》里写成“索隐行怪”,所以朱熹将“素隐”解释为“索隐”,意思是“深求隐僻之理”。显然,朱熹将“素隐”和“行怪”解释成了一个连带的行为,都是圣人“弗为之”的对象,因此圣人是不赞成“素隐”的。
上述二者分别代表了儒家汉宋经学的经典解释,欧阳竟无都不接受。欧阳竟无说的“素隐”显然不是回乡隐居,而更接近朱熹的解释——“求理”,但两者存在极大差异。朱熹根据文义将“索隐”解释成应当予以否定的“过分深求”的“求理”,他认为过分深求违背“中庸”。欧阳竟无将“素隐”视为《中庸》的根本大义,赋予“素隐”和“行怪”完全相反的价值。他说:“君子居素隐之名而行离道之怪,不诚非知也。”[1]664意思是说,“素隐”本身是好的,但“不诚”的“素隐”就是“行怪”,是应该避免的。
欧阳竟无和朱熹的解释存在根本的分歧。朱熹认为,不偏不倚就是“中庸”,如果过分深求就违背了中庸,因此这只是一个度的问题。欧阳竟无则认为,“中庸”不是一个度,而是本质,只在度上讲就架空了这个本质。他特别反对程颐、朱熹的解释,认为:“中不在过、不及上求,亦不在非过非不及上求,扪烛扣盘,盲焉得日?髻珠怀宝,不悟终贫。”[1]663在他看来,程朱的解释拘泥于知识和文义,只是在本体之外描摹,却根本不见本体。他说:
道之不明也,一言中庸,而一切过不及之名、平常之名以至。何者过不及,何者平常?但是空言,都无实事。[1]620
所以,只讲“不偏不倚”的“中庸”,是一种没有根柢的虚无,欧阳竟无甚至将其痛斥为“乡愿中庸”,认为“天下乱于乡愿中庸”[1]653。与之相对,真孔学的精神则是“素隐中庸”:“君子本素隐之中庸,而行于素位,乡愿则创素位之中庸,而不言素隐。”[1]667欧阳竟无认“素隐”为根柢,在他看来,讲不讲“素隐”是真孔学与伪孔学的分界。
欧阳竟无将“素隐”和“素位”合起来讲,出处在《中庸》第十四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2]24
郑玄解释说:“傃皆读为素。‘不愿乎其外’,谓思不出其位也。‘自得’,谓所乡不失其道。”[12]1672孔颖达疏曰:“素,乡也。乡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行之事,不愿行在位外之事。……言君子所入之处,皆守善道。”[12]1673总之,他们都将“素隐”解释为归隐,将“素位”解释为安于其位。欧阳竟无引申了一步,将“素隐”解释为修道,将“素位”解释为行道。由“素隐”而“素位”,欧阳竟无以此来解释未发至已发的过程。他将原文改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庸。”[1]660这样,“中庸”二字就被解释成了未发与已发。欧阳竟无认为“《中庸》是素隐之书”,根本上是为了说明孔学本体也是“无余涅槃”。他用唯识宗“宗趣唯一、法门三次”[1]478的结构来说本体与修行的关系,正好和未发、已发对应起来。“《中庸》之素隐不已与修道,语语皆与涅槃寂静相符”[1]655,这样,“素隐”的含义同于唯识宗本体“涅槃寂静”,成了孔学之本体,“素位”则是真孔学精神的实行。
四、结语
欧阳竟无转向孔学研究与民国时期的民族危机有直接关联,所以其孔学并非传统经学的延续,而带着浓厚的个人体验和实行的意味。发挥真孔学的精神是其主旨,清算后儒标榜的虚假道统成为第一项工作。他结集经典重构儒学系统,将《中庸》奉为孔学核心,重新解释《中庸》的篇章结构,为这部分工作提供文献依据。欧阳竟无阐发“素隐”的含义,将孔学本体解释为寂灭,这里固然借用了佛学名相,但实质上对儒学传统缺乏真实本体统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欧阳竟无将传统文明的危机归罪于“乡愿伪儒”,认为这正是长期专制社会历史的帮凶,重建孔学道统,要求真正“知孔”和“继孟”,这是在专制社会之前的先秦思想中寻找人的尊严和价值。欧阳竟无认为,孔孟真精神要求“革命”呼吁“民权”,正是应对时代危机的“国中大本”,是民族能够自我存续并走向未来的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