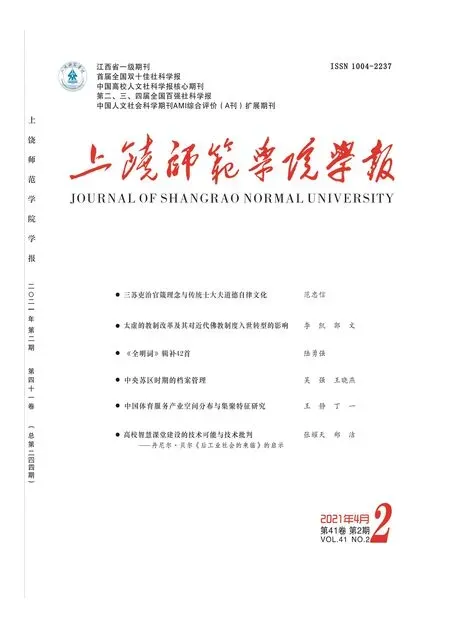清初经典考据下的学理之辩
——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为中心
王新杰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在清初渐兴的儒家经典考据、辨伪之潮中,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可谓是一部标志性作品。阎氏从《古文尚书》之篇名、篇数、典制、文法等方面罗列证据128条,以严谨之考据得出《古文尚书》乃晋人伪作的结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十三经注疏·尚书·引言》中论及《尚书古文疏证》《古文尚书》之真伪曰:“自朱子以来递有辩论。至国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其事愈明”[1]322。清代以降,学人多以此书考定了自宋以来关于《古文尚书》真伪的学术公案。江藩《汉学师承记》对《尚书古文疏证》考据之价值评断曰:“读阎若璩《古文疏证》乃知古文及孔传皆晋时人伪作。”[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有“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1]409的赞誉。《尚书古文疏证》成书于清初考经证史蔚然而兴的学术氛围之下,阎氏的考据之功为其时学人所重,自在情理之中。然而,细考阎氏著述之旨,《尚书古文疏证》绝非单纯的考据之作,而是有学术思想寄寓其间。仅就阎氏其以《古文尚书》这一儒家经典为考辨对象的著述行为而言,其学术意义非同小可。此书剥去儒家经典不容置喙之外衣,“四书五经”由以往仅可被崇拜、诵习变为可以被研究甚至质疑的对象。在其之后,考订儒家元典之作相继而出。从此层面而言,阎若璩的考据工作不啻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诚如梁启超针对《尚书古文疏证》所发议论道:“两千余年来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它。忽焉真赃实证,发现出全部是假造……自此以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的开拓出来了。”[3]然而梁氏此论仅道出《尚书古文疏证》于思想史的客观理论价值,并未抉发阎氏之主观著述动机。
承梁启超之遗意,余英时在《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一文中深入讨论阎若璩撰作《尚书古文疏证》之主观动机,认为“在纯考证的兴趣之外,百诗也还有另一层哲学的动机”[4]。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第二卷第三十一条考证理学的重要理论来源“虞廷心传”为伪,其乃荀子援引道经而成[19]144-149。余英时认为:“这十六字心传是陆、王心学的一个重要据点,但是对程、朱的理学而言,却最多只有边缘的价值”[4]。加之阎若璩尊程朱而贬陆王的一贯学术立场,断定阎若璩的考证旨在推翻陆王心学之理论依据,有着超乎考证以上的哲学动机。此后,故宫博物院赵刚发表《论阎若璩“虞廷十六字”辨伪的客观意义》[5]一文,从“十六字心传”于理学两派之地位,阎氏本人对“十六字心传”之认识,黄宗羲、毛奇龄等同时代学者以及四库馆臣对阎氏著作之评价等方面同余英时商榷,得出阎若璩的考据辨伪并无哲学动机之结论。然而细绎两位先生之叙述,中有部分观点殊堪再作商兑。
一、“虞廷心传”于朱陆二派之价值
余、赵二位先生关于“虞廷心传”在程朱、陆王两派的理论体系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的看法,存在较大差异,并认为此系判断阎若璩的考据有无哲学动机的关键。“虞廷心传”源于《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6]十六字。“虞廷心传”在理学中最先由二程发掘,经由朱熹发挥,将其地位提升至尧、舜、禹万世相传之心法。此后无论是程朱一派抑或陆王一派,皆从不同角度对此“十六字心传”加以抉发、诠释,最终成为宋明理学在形上层面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余英时先生以朱熹尝怀疑《古文尚书》的真实性及其一贯的辟佛立场,推测“十六字心传”出自《古文尚书》,又与禅宗“单传心印”说法颇相类似,故难以为朱熹所重,因此其在程朱一派中最多只有“边缘价值”。其实此一推论似是而非。事实上,二程最先借此阐发理学中经典的人心道心、天理人欲之分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自明。”[7]朱熹虽尝疑《古文尚书》为伪,然而对《大禹谟》一篇,尤其对“虞廷心传”深信不疑,可谓阐发不遗余力。他首先以“虞廷心传”为经典依据构建、诠释儒家道统观:“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8]14朱熹借此确立了上自尧舜、下至二程的理学道统谱系,使儒学在与佛、老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其次,“人心”“道心”二分之说又是朱熹将“天理”“人欲”对立并提出“存理去欲”修养方法的理论根源:“至若论其本然之妙,则惟有天理,而无人欲,是以圣人之教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于形体之私,则固不能无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于天地之正,则又不能无道心矣。……是以欲其择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杂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流于人欲。”[9]职是之故,与阎若璩先后考据《古文尚书》的李绂指出:“(《古文尚书》)朱子亦尝疑之,而卒尊之不敢废者,以人心、道心数语为帝王传授心法,而宋以来理学诸儒所宗仰之者也。”[10]由此看来,“虞廷心传”实亦为程朱一派的“重要据点”,而不独于陆王心学为然。
与余英时先生认为的“虞廷心传”乃陆王心学的重要据点不同,赵刚先生则以陆九渊、王阳明对“虞廷心传”无多直接阐释为据,认为其对心学才只具有“边缘价值”。然而,细察各派学者对“虞廷心传”的评价,“虞廷心传”之于心学的价值实有悖于赵刚先生所断言。
以心学中人为例,陆九渊在《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讲义中对“虞廷心传”给予正面评价:“知所可畏而后能致力于中,知所可必而后能收效于中。夫大中之道,故人君所当执也。……则舜、禹之所以相授受者岂苟而已哉!”[11]有明一代,“十六字心传”对于心学一派的地位论述颇多。章潢有言“心学传自虞廷”[12],湛若水曾说:“(十六字心传)此乃帝舜传授大禹以心学也。”[13]心学殿军刘宗周同样认为:“虞廷十六字有功于万世心学大矣”“虞廷十六字为万世心学之祖”[14]。黄宗羲亦每每论及“虞廷心传”:“虞廷以道心别人心,千古而下更动不得。阳明独得此意,故以良知释致知,亦虞廷之意、孟子之意。”[15]“虞廷之训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万世心学之源也。”[16]明末东林士人领袖、以程朱理学为宗的高攀龙则直言:“虞廷十六字万古以为心学宗祖矣。”[17]此外,不拘于门户、主张调和程朱、陆王之学的冯徒吾也认为“心学之传始自虞廷”[18]。具体到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而言,其本人对于“虞廷心传”的认识同样如此,在书中阎氏曾自述:“或难余曰:虞廷十六字为万世心学之祖。”[19]246可见在阎氏看来,自己考据所面临的非难主要还是来自陆王一派。可引为佐证的是,即使为《尚书古文疏证》作序的黄宗羲,起初也并不同意“虞廷心传”为伪的说法:“圣人之言不在文词,而在义理,义理无疵,则文词不害。其为异如大禹谟人心道心之言,此岂其三代以下可伪为者哉?”[19]1179另一位陆王学者毛奇龄在读完《尚书古文疏证》后,乃作《尚书古文冤词》与阎若璩针锋相对,力证“虞廷心传”之非为伪。毛奇龄考辨的严谨性和说服力姑置不论,但以其不遗余力为《古文尚书》及“虞廷心传”辩护,“十六字心传”之于心学一派的地位亦隐然可见。
毋庸置疑,“虞廷心传”对于程朱抑或陆王之理论价值并无明显高下之分,实为程朱、陆王两派共同的“重要的理论立足点”。因此,余、赵二先生以“虞廷心传”之于程朱、陆王价值的孰轻孰重,来判断阎若璩的考据是否具有哲学动机,显然有失严谨。进而言之,清初辨伪《古文尚书》之学者,顾炎武、朱尊彝等尊程朱,而黄宗羲、李绂等奉陆王;同样,为《古文尚书》辩护者,李光地、陆陇其等为程朱一派,毛奇龄、李塨等则属陆王一系。其中黄宗羲的态度变化最为耐人寻味,他深知“虞廷心传”在陆王心学中的地位,故起初对阎若璩的考据并不赞同,认为圣人之言“岂其三代以下可伪为者哉?”[19]1178然而在读到阎氏《尚书古文疏证》之后,态度陡然生变,不仅欣然为之作序,甚至还直斥道:“然则此十六字者,其为理学之蠹甚矣!”[19]5可见并不能简单地以学术门户为先决条件,而断言其辨伪是否具有哲学动机。
二、《尚书古文疏证》尊朱贬陆立场之体现
尽管余英时先生关于《尚书古文疏证》“对于程朱理学最多只具有边缘的价值”的判断,有失偏颇,但其对阎氏著述动机的抉发,却言之成理;而赵刚先生之论则断难成立。细绎《尚书古文疏证》,阎氏实有“尊程朱而贬陆王”的哲学动机横亘心间。
以尊程朱而言,以程朱为宗乃阎若璩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在其文集《潜邱札记》中,尊朱贬王之言,所在多有,如其自言“守朱说尊若金科玉律”,将友人推崇陆王心学喻为“跳上陆子静贼船”[20]。而在《尚书古文疏证》中,尊朱之意更是昭然可见。其子阎咏为《尚书古文疏证》所作后序中提及,阎若璩曾多次表露心迹,明确体现尊朱立场[19]7-8。《尚书古文疏证》书成后,阎若璩面对宗程朱者“怪且非之者亦复不少”之情势时乃感到“意不自安”,于是申辩道:“吾为此书不过从朱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耳,初何敢显背紫阳以蹈大不韪之罪?”又说:“孔子者,万世取信一人而已。余则谓朱子者孔子后取信一人而已。今取朱子之所疑告天下,天下人闻之自不必尽笃其信。”[19]7强调其尊孔崇朱立场之余,将考据《古文尚书》说成是“从朱子引而伸之”以回应他人之非难。对于自己的考据可能导致的孔、孟、程、朱道统传承谱系的崩解,阎氏则辩解道:“徒以‘道经’二字而辄轻议历圣相传之道统,则一病狂之人而已。”[19]247此语含义有二:其一,阎若璩认为道统乃“历圣相传”,不可轻议;其二,对于未经严谨考据便以“道经”妄议程朱之道统观者,阎氏一概以“病狂之人”斥之。
“虞廷心传”本由朱熹极力推崇,方确立为“帝王心法”及“万世道统”所在,而今被证明为伪,朱熹无疑难辞其咎。然而《尚书古文疏证》并未对朱子有何微词,且多为之开脱。首先将矛头直指荀子,认为正是荀子“不得儒之醇”,将源自道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引入《大禹谟》中,致使后来“有宋程朱辈出,始取而推明演绎,日以加详殆真。以为上承尧统,下启孔教者在此……孰料其乃为伪也乎!”[19]248其次,强调朱熹亦曾疑《古文尚书》之真伪,然而“虞廷十六字”对理学道统观的建构具有相当之价值,致使朱熹阐发不遗余力,“子与其疑也,宁信”[19]248。最后,阎若璩关于“虞廷心传”还有一段自己的见解:“尧曰:‘咨尔舜,允执其中’。传心之要尽于此矣”[19]246对比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所说“‘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8]14,阎若璩在此效仿朱熹将“虞廷心传”区分为尧授舜、舜授禹的两个版本,朱熹认为“允执厥中”乃十六字之精华;阎若璩则强调“允执其中”乃“传心之要尽于此”,暗含批驳荀子援引道经,将其演变为十六字纯属节外生枝。
从贬陆王看,在《尚书古文疏证》第八卷第一百二十八条中,阎若璩总体品评了历代孔庙从祀对象,并提出一个理应罢祀名单,从西汉到晚明一共三人,即王阳明、陆象山、陈白沙。若联系阎若璩一贯尊朱贬陆的学术立场,他所提出的罢祀名单,正是其考据有无哲学动机的直接体现。阎若璩罢祀王阳明之理由有二,一是认为王阳明与荀子类似,在心性之说上立异孟子。阎氏评价荀子为“生平无可以,仅以议论曰性恶是也”,而王阳明则是“亦仅以议论曰无善无恶是也”,晚明儒门“辨无善无恶者众矣,而莫善于万历间顾、高二公”[19]1245,故以其对儒学并无突出贡献,理应罢祀。二是指斥王阳明援佛入儒。在此条中,阎若璩以冗长的篇幅批判王阳明袭用禅宗对儒学带来的危害:“(无善无恶)辨四字于佛氏易,辨四字于阳明难。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则阴坏实教也。”又说:“依凭此语如服鸩毒,未有不杀人者。”[19]1246同时大量援引顾宪成、高攀龙批判阳明心学的辟佛言论作为旁证。阎若璩在这段论述中从形上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方面,对王阳明之援佛入儒大肆挞伐,则已完全脱离了纯考据之范畴。
紧接王阳明之后,阎若璩又指出陆象山同样应该罢祀,其因同样有二。一是“阳明之学出于象山,象山生平亦无可以,亦当以其议论曰颜子为不善学是也”,二为“(陆象山)此语果是,则孔子为非;孔子不非,则此语殆无忌惮”[19]1252。阎若璩认为,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背道而驰,这是其被罢祀的根本原因;而陆象山之议论更有悖反孔、孟之嫌,岂有不罢之理,是故“不罢象山亦无以服荀卿之心”[19]1253。
心学一脉中处于象山和阳明之间的陈白沙,阎若璩同样以其学近佛为由,认为理应罢祀。陈白沙有诗云:“起凭香几读《楞严》”“天涯放逐浑消事,消得《金刚》一部经”[19]1259。阎若璩便据此认定陈白沙不守儒、释之藩篱,“陆与陈与王,虽深,却阴坏儒之壸奥,故一在莫敢废,一在必当罢”[19]1260。
此名单及罢祀理由一出,阎若璩以“辟佛”为由将陆王心学彻底革出儒门道统的哲学动机,便昭然若揭。然以阎若璩之学识,何尝不知若以此厘清儒、释门庭,势必令同样援佛入儒的二程、朱熹难辞其咎。故阎氏在《尚书古文疏证》中,不仅为朱子开脱,辩称朱子阐发“虞廷心传”是在不知其为伪的情况下所为,同时把“杂入道经”的责任归咎荀子。即便阎氏深知“虞廷心传”之于心学的重要价值,为避免将抉发、阐释“虞廷心传”的二程、朱熹亦置于同样境地,并未将“虞廷心传”为伪作为罢祀陆、王的论据。及至最后提出的罢祀名单,陆象山、陈白沙、王阳明等心学一派重要人物皆因非孔、近禅、援佛等理由名列其中,而对于程朱一派的援佛入儒则避而不谈。这种明显的态度差异,正是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重申程朱道统地位之学术意图的直接体现。
三、清初经典辨伪思潮的理学背景
清初学界在反思明亡之时,无不将学术思想层面的原因归咎于晚明以来禅学化的阳明心学所导致的束书不观、空言心性的空疏学风。承接晚明东林士子严守儒、释疆界,“远宗孔圣,不参二氏”[21]之风,清初诸儒大多对阳明心学之援佛入儒严加批判。顾炎武将晚明王学空谈比作魏晋玄学清谈,称王阳明与王衍、王安石一样,皆是“以一人而易天下”,其误国之罪“深于桀纣”[22];王夫之痛斥“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23];费密批评王学之致良知说乃“达摩面壁、司马承祯坐忘、天台止观同一门庭”,无疑应为“学术蛊坏,世道偏废”[24]的结果负主要责任。即使属于王学阵营的黄宗羲,也不得不承认阳明心学袭用佛氏之事实:“先生(王阳明)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久之。”[25]180但又为阳明非禅辩解,强调王学与禅学的差异:“禅则先生固尝逃之,后乃觉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诚也,天之道也。诚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诚,以人合天之谓圣,禅有乎哉?”[25]6清初学界也因此呈现出由王返朱之大势,李光地、张履祥、陆陇其等人之学术皆为先王后朱,实“学术流变,与时消息”[26]有以致之。
在清初学界“辟异端”为共识的环境下,禅与非禅成为评判学术思想的唯一标准,禅学化的阳明心学因此遭到摒弃。诚如毛奇龄在《与阎潜邱论尚书疏证书》中所言:“(阎若璩)误以《尚书》为伪书耳,其与朱陆异同则风马不及,而忽诟金溪并及姚江,则又借断作横枝矣。……今人以圣门忠恕,毫厘不讲,而沾沾于德性、问学,硬树门户,此在孩提稚子,亦皆有一诋陆辟王之见存于胸中。”[27]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成书于如此背景之下,自然于学理层面上带有尊朱斥王之倾向。而阎若璩与毛奇龄关于《尚书古文疏证》真伪性的辩论,皮锡瑞则认为不过门户之争:“学者各有所据,蔽所不见,遂至相攻,有据孔传以攻蔡传者,如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是也,有据蔡传攻孔传者,如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是也。”[28]《尚书古文疏证》若抛开第八卷不论,确也足当一部纯考据著作。及至阎氏之罢祀名单一出,不仅毛奇龄认为此乃节外生枝、硬树门户,四库馆臣也揣测此系阎若璩“盖虑所著《潜邱札记》或不传,故附见于此,究为枝蔓”[1]409。阎氏甘冒削弱此书学术价值之风险,也要将罢祀名单列于《尚书古文疏证》这一生平最为得意的著作之中,其哲学动机则不言而喻。
而随着“辟异端”思潮由针对禅学化的阳明心学转变为扩展到整个理学范畴,程朱理学同样被置于该标准下加以审视。尤其是程朱建构理学的经典来源四书以及五经中的《易》受到的质疑最多。以被朱熹列为四书之首的《大学》为例,陈确作《大学辨》,先从文迹上考证《大学》很少引用孔孟的言论,再论“大学”二字孔门中人从未提及,甚至在《大学》文本中有抄袭并改动《尧典》之痕迹,认定《大学》并非如程朱所言为孔子之书。而后在文理上,陈确对《大学》中“知止”概念提出质疑,认为“惟禅学之诞有之,圣学则无是也”[29]554。因此,朱熹因“知止”所阐释的“格物致知”方法论“亦为虚设”,实乃“空寂之学”[29]573。陈确据此判断程朱理学不仅在形而上的认识论、方法论上袭用禅宗,在形而下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等方面也与传统儒学并非一致,乃半杂禅门:“《大学》其言似圣而其旨实窜于禅,其词游而无根,其趋罔而终困,支离虚诞,此游、夏之徒所不道,决非秦以前儒者所作可知。”[29]552陈确系心学殿军刘宗周弟子,其《大学辨》证《大学》并非如二程、朱熹所言乃圣人之书,主张将《大学》黜还于《礼记》,以此解构凭《大学》而巩固的程朱一派道统地位。而张履祥在《答陈乾初一》中以《大学》修、齐、治、平所体现的践履性,证明《大学》与佛氏并无关联,以此为程朱辩护:“《大学》之书俱在,自篇首至末简,何一章之不及行乎?即以知论,禅之言知,说顿、说渐,总不致知者也。今之儒名而禅实者,言致知而不及格物者也。且自诚意而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何一而非行之事乎?……谓《大学》为非孔、曾亲笔之书,则固然已;谓《大学》为非孔氏之道、曾氏之学,则必不可。”[30]
至于《易经》,梁启超有言:“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31]集易学之大成的朱熹,其易学思想倾向于图书一派,将邵雍的九图冠以其所著《周易本义》之卷首。及至清初,出自道士陈抟的图书派自然被易学界口诛笔伐,朱熹同样成为被批判的焦点。清初考证辨伪《易》的作品,前期主要有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黄宗炎的《图书辨惑》、毛奇龄的《图书原舛编》,均属浙东王学,主要考证朱熹所推崇的太极诸图实传自道教,暗含对朱熹的批驳之意。顾炎武则在《日知录》中指出,现在看到的《周易本义》并非朱熹订正的原本,为朱熹开脱:“洪武初,颁五经天下儒学,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为书,永乐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传之后,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殽乱。”“《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颁,不敢辄改,遂即监版传义之本刊,去程传而以程之次序为朱之次序,相传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书,竟不得见于世,岂非此经之不幸也夫。”他进而提出“复程朱之书以存《易》”的思想[32]。而较顾炎武稍晚的胡渭,在其《易图明辨》中除了继续完善对《易经》的考证辨伪外,亦将矛头直指朱熹,其曰:“河图之象不传,故《周易》古经及注疏,未有列图书于其前者,有之,自朱子《本义》始。……学者溺于所闻,不务观象玩辞,而惟汲汲于图书,岂非易道之一厄乎?”[33]2又谓:“间有涉于老庄者,亦千百之一二,未尝以文王、周公、孔子之辞为不足贵而糟粕视之也。独为先天学者,欲尽废周孔之言,而专从羲皇心地上寻求,是其罪更甚于何、王矣!”[33]266尽管未点明,但胡渭这段议论无疑是针对于易学上尊伏羲而贬周孔的朱熹而发,直言朱熹败坏学风之罪更胜魏晋之清谈。此论既出,王懋竑撰《易本义九图论》替朱熹辩白,说辞与顾炎武类似:“九图断断非朱子所作,而数百年以来未有觉其误者。盖自朱子既殁,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义,流传既久,有所篡入,亦不复辨。”[34]
由此可见,清初兴起的经典考据辨伪之风,实基于浓厚的理学背景而发。阎若璩、陈确、胡渭等人的考据决非单纯的为考据而考据,而是在“辟异端”的思潮下对转移学风、净化经典的诉求,同时又体现出理学内部在学理上的分歧与门户之争。
——论《江格尔》重要问题的研究方法
——以“能不我知”考据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