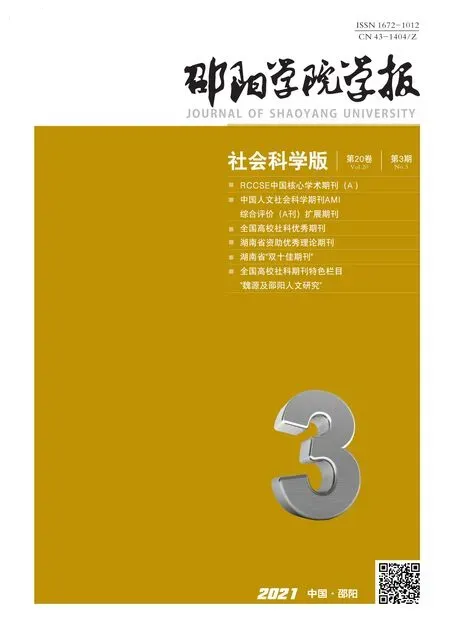《白鹿原》的方言运用探析
孙雅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488)
《白鹿原》开篇引述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1]这部50余万字的巨著,宏伟壮阔地描述了清朝末年到20世纪70、80年代白鹿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白鹿村是关中地区的风土人情和乡村社会的缩影,上演着白鹿两家祖孙三代的明争暗斗,将中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目前学界关于《白鹿原》文学价值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而对于具体作品的语言分析甚少。在这部小说中,方言独具魅力。分析文本的遣词造句,有助于全面了解作品的艺术特征,深切体会关中文化。本文着眼于《白鹿原》中独具特色的关中方言和浓重的乡土气息,探讨方言词的巧妙运用及表达效果。
一、《白鹿原》中方言词的巧妙运用
(一)名词
名词表示人或事物和时地的名称[2]8。作品中出现的方言,名词类可以分为表示人和事物、表示时间、表示处所三种。
1.表示人和事物
(1)“尻子”
①黄牛正在坎下的土壕里,腹下正有一只紫红皮毛的小牛犊撅着尻子在吮奶。[1]25
②白嘉轩跪在主祭坛位上祭祀祖宗的时候,总是由不得心里发慌尻子发松。[1]63
粗略统计,《白鹿原》中“尻”字的出现有十余次。方言“尻子”是臀部的意思,可以指人、牛、狼、猪等的屁股。“尻子”也可被称为“沟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称“尻”今俗云沟子是也,作家多次使用“尻子”,蕴含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例②背景是白嘉轩在父亲过世之后,顺理成章地继任组长,需要领头祭祀祖先。每逢祭祀,他不寒而栗的神态,如同动物被人类捕捉后恐惧的样子。“尻子发松”表现了白嘉轩浑身无力、身体发软、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样子,叙述手法极为独特。
(2)“(你)/(他)大”
③小娥羞怯地叫:“大——”鹿子霖嘻嘻地嗔怒:“甭叫大甭叫大,再叫大大就羞得弄不成了!”[1]256
“他大”亦称“他爹”,是指孩子的父亲。“大”这一称谓,最早见于秦汉时期的陕西、山西地区,各地县志皆有记载。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古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北方作家的作品,善于运用“大”这一称谓,便于贴近原汁原味的生活,塑造典型而复杂的人物性格。例③中鹿子霖夜间找小娥寻乐,因违背传统伦理道德心中不安,故不让她称“大大”,其老奸巨猾的形象跃然纸上。在黑娃离开小娥后,面对孤立无助的小娥,他自称为“大”,目的是抚慰小娥的情绪,让其不再害怕并对自己产生依赖。称呼上精细入微的变化,生动地展现出丰富多样的人性特征,可见方言词汇的微妙与神奇。
(3)“乡党”
④婚后半个多月,饱尝口福的乡党还在回味无穷地谈说宴席的丰盛。[1]148
⑤“乡党们,我今日对着日头赌咒,我说田总乡约加码征地丁银的话全是假的……”[1]231
“乡党”指同乡、乡亲的意思,是关中人对老乡的称呼,其他地域不常使用。柳青《创业史》第一部题叙:“但愿你两口,白头到老,俺乡党们也顺心……”[3]7“党”是古代地方组织,据《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记载:“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释名》解释“五百家是一党”,党正是聚集之地的最为尊长者。
(4)“麻达”
⑥“我向冷大哥自荐想从中撮合,八字也都掐了,没麻达。”[1]113
⑦鹿兆鹏解释说,“他们接受培训提高了觉悟,就会改掉自己的麻达。”[1]200
“麻达”表示问题、事故。村民喜欢用“没麻达”做口头语,表示身处困境时的从容自若。有些时候,这是在别人寻求帮助时的热情回应,语调高昂,语气肯定,凸显关中人豪爽的性格。在特定语境里,“麻达”也指缺点、不足。例句⑦中,田福贤听闻黑娃将要去城里接受培训,担心其身上毛病太多,会惹是非,于是鹿兆鹏为黑娃做解释。有时“麻达”也能名词用作形容词,是麻烦、闹心的意思。可见,方言的含义要结合具体语境去分析。
除了上述极具陕西关中方言特征的名词之外,我们还注意到文中一些深具地方色彩的食物。关中地区主产小麦,人们的饮食通常离不开种类齐全的面食,如“罐罐馍”“臊子面”“羊肉泡馍”“麻食”“麻花馓子”“荞面”“饸饹”“油饼”“搅团儿”“老鸹头”“荠菜水饭”“锅盔”等。此外,还有“水晶柿”“葫芦鸡”“苞谷糁子”等独具风味的陕西特产。关中人在穿着上的称谓也别具一格:“褡裢”(一种长形布袋)、“汗褟儿”(夏天贴身穿的中式小褂)、“棉窝窝”(特指棉鞋)。可见,陈忠实先生的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2.表示时间
(1)“后晌”
⑧儿子鹿子霖说:“后晌先种这地的苞谷。”[1]38
⑨这年新年前夕的腊月三十后晌,白嘉轩研了墨,裁了红纸,让孝文孝武白灵三人各写一副对联:“谁写得好就把谁的贴到大门上。”[1]120
《篇海类编·日部》指出:“晌,午也。”“晌”,本义为正午或者午时的前后,“后晌”便是下午或晚上。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河北、内蒙古等地还保持着这一方言的使用。此外,“晌”在贾平凹、周大新、陈忠实等北方作家的一些作品中常常出现。
(2)“黑间”
⑩孝文媳妇说:“我天天黑间劝他少念会儿书少熬点儿眼……”[1]154
“黑间”即夜晚。杨朔的《春子姑娘》使用了这一方言词:“你看春子,夜来黑间又跑回她婆婆家来了——这不是灯蛾扑火,甘心找死么?”[4]“黑间”一词,其后可以加儿化,山西大同、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地区还保留方言“黑间儿”的用法,每到傍晚,常能听到妇女叮嘱自家孩子“黑间儿天凉,要多加衣”。
3.表示处所:“厦屋”
在现代汉语中,“厦屋”通常是指较为高大的房屋,然而在陕西关中地区,其专指一边施椽,而且前低后高的偏房和厢房。平房上面架有木头,在人字形房梁的最高处铺瓦,没有屋脊,便于流水,夏天太阳不宜晒透,可谓冬暖夏凉。“陕西八大怪”当中的“房子半边盖”指的就是这样的屋型。“厦屋”一般建在正房之后,紧靠院墙,用以支撑着房顶,省却梁柱,节约地基与木料的成本。“厦屋”的设计,体现了关中人巧妙的智慧和简朴的生活作风。长辈通常居住在关中人的“上房”,即正房,而儿孙和小辈通常住在“厦屋”。《白鹿原》中提到,母亲一个人住在上房,白嘉轩住在厦屋,此处彰显了白嘉轩的善良孝顺,也可见忠孝文化影响之深远。
(二)动词
动词表示动作、行为、心理活动或存在、变化、消失等[2]9。小说《白鹿原》的方言中有不少极具代表性的动词,贴近生活,妙趣横生。
(1)“咥”
“咥”,陕西关中、河西走廊一带的方言土音,最常说的就是“咥饭”“咥面”。秦人生性豪爽,农忙时节,人们三五成群,或蹲在土墙根,或站在树下,或依靠石碓,就着辣椒或大蒜匆匆吃面。农民没有时间细嚼慢咽,面条一半下咽,一半还在碗中的场景比比皆是。大碗干面在火急火燎中吃出了激情,馍馍在大口吞咽下“咥”出了豪迈。“咥”,自然而然成为了秦人生活的真实写照。特别在深秋之际,为了御寒,面条里会放更多辣子,加上大蒜的刺激,不过多久,吃面的人就会汗流满面。进食时若能发出令人垂涎的声音,才是秦人最为标准的“咥”。原生态的秦风秦韵是秦人数千年的积淀,它豪放、高亢、激昂、厚重,不可比拟。“咥”如同秦腔中的吼一样,去掉“吼”便不是秦腔了,不用“咥”便难以反映秦人的豪迈。
(2)“弹嫌”
“弹嫌”表示挑剔、计较、找麻烦。《白鹿原》中多次出现“不弹嫌”,也是关中人豪放不羁,随性洒脱的一种表现。
(3)“熬活”
“熬活”指做苦工。同“做苦力”“扛活”这些近义词相比,“熬活”一词,更能凸显出农民使出浑身解数才能谋生的艰辛,这一表达贴合语境,真实再现了当时关中百姓的生活状态,还体现出农民吃苦耐劳的典型性格特征。
(4)“试火”
“试火”即试一试。白嘉轩在被黑娃打折了腰以后,想要犁地,心痒难耐,卧床的三个多月让他烦躁郁闷。他说:“我不怯吃苦不怯出力也不怯迟睡早起,我最怯最怕的事……就是死僵僵躺在炕上,让人伺候熬汤煎药端吃端喝倒屎倒尿。”[1]288于是,白嘉轩起身在田地里“大显身手”,充分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正因为他勤恳善良、淳朴仁义的品质,白嘉轩才能成为让人信服的族长。
(三)形容词
形容词表示形状、性质等[2]11。作为现代汉语中较为复杂的一个词类,形容词的标准及语法特征的描述分析至今仍旧争议不断。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提出:“凡词之表示实物的德性者,叫做形容词。”[5]17朱德熙《语法讲义》从语法特点的角度对动词、形容词做了区别:“凡受‘很’修饰而不能带宾语的谓词是形容词,凡不受‘很’修饰或能带宾语的谓词是动词。”[6]55他还明确提出:“形容词可以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两类。”[6]73笔者注意到《白鹿原》方言中这两大类形容词存在着具体的、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表示心理活动的形容词以及带有后缀成分的形容词,需要做出具体分析。
1.性质形容词
(1)“秀溜”
“秀溜”是北方方言,指体态轻盈,身姿灵活,苗条秀气。“秀”指“秀气”,“溜”有“线条顺畅、顺溜”之意,多形容女性身段优美,也指外貌秀气、打扮整洁、仪表得体。例句用“秀溜”一词形容小娥小脚的灵活,将她不轻不重、不胖不瘦的体态形容得恰到好处。
(2)“骚情”
甘肃、陕西等西北地区经常使用的“骚情”,是指男女调情、谈情说爱时的热情过火,形容男性的献媚之意,用在女性身上通常指风骚之情。例句是鹿子霖在惩罚白孝文的当晚,因为心情愉悦而喝得酣畅淋漓,借着酒劲迫不及待地去见小娥。鹿子霖处处与白嘉轩针锋相对,设圈套来陷害白氏家族——诱导“臭名远扬”的田小娥去勾引白孝文。田小娥不可避免地成了白、鹿两大家族斗争的牺牲品,其最终死在阿公梭镖下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陈忠实笔下的田小娥极具悲剧色彩,她的一生,是20世纪初期许多悲惨女性的缩影。柳青的文学作品也常出现这一方言词,如《创业史》第一部第六章:“于是,改霞她妈吞吞吐吐地说:‘梁生宝不是人,胡骚情……’”[3]93
(3)“嫽”
“嫽”,有美、好的意思。《说文》:“嫽,女字也。从女,尞声。洛萧切。“嫽”表示美好,所以才会被女人用作表字。西汉扬雄《方言》卷二:“嫽,好也。”“嫽”的使用范围不限于陕西,我国山东、江苏一带也把好叫作“嫽”。陕西话中的“嫽得太”,就是指非常好,上文的“嫽得很”也是如此。被鹿子霖陷害后的白孝文一蹶不振,为买鸦片倾家荡产、精神萎靡、瘦骨嶙峋,甚至为寻求残羹冷炙,被恶狗追咬。白孝文吃舍饭,实则放下了他作为“人”的全部尊严,其曾受人尊崇的伟岸形象消失殆尽。鹿三嘲讽孝文将人活成了狗的模样,白孝文矢口否认,说当下的光景正让他感到“嫽得很”。白孝文每一次性格的重大转变都推进着小说趋向高潮。
2.状态形容词
(1)“黄不拉叽”
“黄不拉叽”用来形容庄稼,指黄色的麦苗。
(2)“霉朽污黑”
“霉朽污黑”形容麦秸秆污黑且呈霉状。
3.表示心理活动的形容词
(1)“受活”
豫西人最常使用“受活”,意即享乐、享受、快活、痛快淋漓。在耙耧山脉,“受活”也暗含有苦中之乐、苦中作乐之意[7]4。例句是鹿子霖与白小娥偷情后的得意发问。
(2)“瞀乱”
“瞀乱”是指不适、昏乱,精神烦乱。
关于形容词的分类,少有学者提及反映人类心理情绪变化的形容词分类。本文参照赵家新的意义聚类法,将反映心理情绪变化的形容词分为性质形容词、情态形容词、判断形容词这三大类[8]。情态形容词中包含表示心理活动的形容词和感官形容词。因此,可以将上述方言“受活”“瞀乱”等表示心理活动的形容词归为情态类性质形容词一类。
4.带后加成分的形容词
有趣的是,《白鹿原》的形容词方言当中有不少后加成分,分双音节和三音节两类。三音节的后加成分,包括“A不BC”式,如:“灰不溜秋、黄不拉叽”等,即上述的状态形容词;双音节的后加成分,通常是两个同音的音节,多为“ABB”式,如:“绿油油、硬邦邦”等,朱德熙在1956年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一文中,将其称为“状态形容词”。这里仅列举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词语,从动静两维度、状态及感觉两层面进行归纳和整理。
(1)动态
a.形容人(状态):
愣实实的样子圆嘟嘟的尻蛋子气冲冲捞起蘸了泥浆的笤帚颤怯怯坐下去直溜溜的眼睛死僵僵瘫痪炕头的废物毛茸茸的嘴巴痛快快咥了一顿毛楂楂的阔大的嘴巴 白嘉轩心痒痒腿脚痒痒 小娥从炕墙根下颤悠悠羞怯怯直起身来
b.表示感官(感觉):
笋瓜也脆蹦蹦的(触觉) 关于男盗女娼的酸溜溜故事(味觉)酸滋滋臭烘烘的气味(味觉、嗅觉) 喷出热骚骚的烧酒气味(嗅觉) 脸颊顿时烧骚骚热辣辣的(触觉) 拔掉瓶塞儿咕嘟嘟灌下一口烧酒(听觉)
(2)静态
a.形容物(状态):
那一坨湿漉漉的土地稀溜溜的苞谷糁子鲜嫩嫩的羊奶奶 全是平展展的水浇地热烘烘的血流和火流湿漉漉的草料 露出一根嫩乎乎的同样粉白的秆儿 用棒槌捶打得硬邦邦的衣服湿漉漉黏糊糊的麦穗绵茸茸的被攘践倒地的麦子的青秆绿穗儿
b.表示颜色(感觉,主要指视觉):
红扑扑的脸膛绿油油的小蓟青苍苍的柏树绿莹莹的豌豆粒儿光亮亮的眼睛黑乌乌的头发黑乌乌的眼睛黄蜡蜡的新鲜眼屎清幽幽的香气绿葱葱的麦田白亮亮的屁股黄灿灿的新缰绳蓝幽幽的潭水黄澄澄的麦子黑沉沉的夜空黄亮亮的米粥黑漆漆的戏台绿油油的壮苗黑溜溜的头发白花花当啷啷的银元黄蜡蜡的冰块黄灿灿的小米黑黢黢的丑陋而又无用的东西
二、《白鹿原》方言的表达效果
(一)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白鹿原》的方言运用是小说的一大特色。韦勒克和沃伦认为:“语言是文学艺术的材料。我们可以说,每一件文学作品都只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语汇的选择,正如一件雕塑是一块削去了某些部分的大理石一样。”[9]163陈忠实在典型环境中合理运用方言,尽力塑造典型人物的性格,这种字斟句酌的态度为人所肯定,他说:“我对每一个重要人物在书中的出场和在生活的每一步演进中的命运转折,竭尽所能地斟酌只能属于这一个人的行动,包括一句对话。”[10]
黑娃拒绝给白家做长工时,一家三口精彩的对话值得回味:
黑娃说:“我嫌……嘉轩叔的腰……挺得太硬太直……”[1]124
鹿三听了轻松地笑了:“哈呀,我的娃呀!我当是什么大事不得开交!咱熬活挣咱的粮食,只要人家不克扣咱不下看咱就对咧!咱管人家腰弯腰直做啥?”[1]124
母亲帮黑娃说话了:“他大,你就依了娃吧!娃不悦意就甭去了。娃说的也还在理。”[1]124
鹿三说:“也好也好!你出去闯荡二年,经见几家财东心里就有数了,不走高山不显平地嘛!到那会你就不会弹嫌……腰直腰硬的屁话了!”[1]124
鹿三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为白嘉轩家做长工,“熬活”挣粮食,从不会“弹嫌”,是勤劳淳朴的农民形象的典型代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子承父业。鹿三虽为长工,但却懂得礼义廉耻,始终将白嘉轩关照鹿家的点点滴滴铭记于心,卖力干活去报答白家的恩情;当白孝文吸食鸦片堕落时,表现出对他败家行为的嘲讽和惋惜。黑娃自幼具有反叛精神,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初尝冰糖和水晶饼,他感到可口的同时又倍感痛苦,出身的卑微强烈地刺痛他敏感的内心。惧怕白嘉轩酷似神像的脸,折射出黑娃潜意识中渴望平等和寻求超越的性格特征。于是那句“我嫌……嘉轩叔的腰……挺得太硬太直……”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为他后来投靠土匪闹革命以及打折白嘉轩的腰埋下了伏笔。他母亲是传统农村妇女的代表,平和善良,勤俭持家,尊重丈夫(凡事都和“他大”鹿三商量),疼爱孩子,有着柔软的内心,黑娃不愿意去白家干活,她便为孩子求情。
陈忠实十分注重从遣词造句的角度把握人物性格,关照的是历史长河中性格各异的个体。如,白嘉轩有着勤恳淳朴、仁慈宽厚的美好品质,即便被土匪打折了腰,还叫嚷着做事:“我是个罪人我也没法儿,我爱受罪我由不得出力下苦是生就的,我干着活儿浑身都痛快;我要是两天手不捉把儿不干活儿,胳膊软了腿也软了心也瞀乱烦焦了……”[1] 288又如,小说第十章仅凭一句“小娥一双秀溜的小脚轻快地点着地,细腰扭着手臂甩着圆嘟嘟的尻蛋子摆着”[1]160,便写尽了田小娥婀娜、妩媚、风骚的身姿。
陈忠实善于选用极具特色的方言展开对人物的描写,凸显人物的形象特点。此外,行文有意凸显方言的节奏与味道,常使用高密度长句型、排比句式,营造厚重大气、不拘小节的感觉。比较经典的例子有《白鹿原》第十八章鹿三辞工,白嘉轩的好言相劝:“三哥你听着,从今往后你再甭提这个话!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吃稠的你吃稠的,我吃稀的你也吃稀的;万一有一天断顿了揭不开锅了,咱兄弟们出门要饭搭个伙结个伴儿……”[1]312这句话读来琅琅上口,句式整齐,语调铿锵有力、气贯长虹,一个“甭”字体现出白嘉轩态度的坚决,加重了想挽留鹿三的表达效果。白嘉轩是地道的关中人,还是一族之长,却没有半点儿主仆观念,称鹿三为“三哥”,下决心与他同甘共苦,不希望鹿三辞工,便再三相劝:“没活儿干了你就歇着睡着,歇够了睡腻了你就逛去浪去!逢集了逛集没集时到人多的地方去谝……你甭瞪眼!兄弟我不是给你撇凉腔是说正经话:天杀人人不能自杀。年馑大心也就要放大。年馑大心要小了就更遭罪了。”[1]312白嘉轩的这段话是由几个连动句组成,“歇着”“睡着”“歇够”“睡腻”“逢集逛集”“没集去谝”这些动词短语互不作成分,共同作谓语,中间可以不用语音停顿,给人一气呵成的感觉,这与秦人以及关中方言的豪爽、干脆有着内在一致性。鹿三热泪盈眶,因为他心知肚明,白嘉轩说这些并不是给他“撇凉腔”,而是真心相待。可见,正是因为白嘉轩兢兢业业的精神以及忠孝仁义的性格特点,他才能深受村民的爱戴,他“品行端正,刚直忠良,公正无私,明察秋毫,他身上凝聚着几乎全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11]549。
白鹿两家恩恩怨怨斗争一辈子,让人始料未及的是鹿子霖晚年的失智。狡猾奸诈的鹿子霖归于本真,白鹿两家的爱恨情仇走向终结,轰轰烈烈的历史就此土崩瓦解。鹿子霖能做的,唯有把鲜灵灵的“羊奶奶”递到白嘉轩眼前:“给你吃,你吃吧,咱俩好!”[1]680陈忠实成功地将自身经验与生命感悟运用到小说当中,结合方言的恰当使用,将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跃然纸上。“倘与另一部政治文化色彩浓厚的长篇《古船》相比,可以说:《古船》写的是人道,《白鹿原》写的是人格……《白鹿原》有多少充满魅力的人格啊,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黑娃、白孝文、田小娥、鹿兆海、鹿三……,哪一个不是陌生而复杂!”[12]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与在劫难逃的命运息息相关,典型人物的逐个退场,可以说是顺其自然,也可以说是陈忠实刻意为之,“他们任何一个的结局都是一个伟大生命的终结,他们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压力,经历了那么多的欢乐或灾难而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死亡的悲哀远远超过了诞生的无意识哭叫。几个人物的死亡既有生活的启示,也是刻意的设计”[10]。
(二)成就小说的艺术价值
《白鹿原》早已成为文学经典,获得了广泛好评。北大中文系陈晓明教授指出:“不管从哪方面来看,《白鹿原》都是20世纪90年代初最重要的作品,我把它的出版看作90年代初文学的、也是思想文化的具有标志性的事件。”[13]著名评论家雷达说:“我从未像读《白鹿原》这样强烈地体验到,静与动、稳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12]他还进一步强调“《白鹿原》终究是一部重新发现人,重新发掘民族灵魂的书”[12]。朱寨将《白鹿原》称为“扛鼎之作”[14]。这部著作的闪光之处,还在于语言上的精雕细琢,特别是方言词语的运用,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域色彩。
小说对景物的描写较为简约,多用重叠词,展现一望无际的原野风景,如:“黑沉沉的夜空”“绿油油的壮苗”“黄灿灿的小米”“那一坨湿漉漉的土地”“稀溜溜的苞谷糁子”“鲜嫩嫩的羊奶奶”“绿油油的小蓟”“青苍苍的柏树”“清幽幽的香气”“绿葱葱的麦田”“蓝幽幽的潭水”“黄澄澄的麦子”。这些重叠词跃动在读者眼前,组成一幅幅动人的图景,仿佛令人能看到花草树木、感受到阳光和嗅到脚下的黄土地的气息。同时,我们通过“没麻达”“不弹嫌”“嫽得很”“秀溜”“受活”“甭”等这些形象生动的方言,也能领略质朴豪放的关中风情,还能被关中人豁达乐观的天性所感染。
《白鹿原》的创作,正如陈忠实曾写过的名为《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的小册子一样,着实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他说:“我越来越相信创作是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过程。每个作家对正在经历着的生活(现实)和已经过去的生活(即历史)的生命体验和对艺术不断扩展着的体验,便构成了他的创作历程。”[10]土生土长的他用原汁原味的方言将关中的地域习俗复活再现,塑造了生动、鲜活、典型的人物形象,使得作品呈现出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
《白鹿原》问世近三十年,如今仍在畅销,还通过诸多艺术形式展现,例如话剧、秦腔、电影、舞剧等。它的语言通俗、有趣,增强了人们对地域文化的兴趣和关注度,对今后地域文学的创新和发展有所启迪。关注《白鹿原》中的方言运用现象,对于运用方言进行文学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