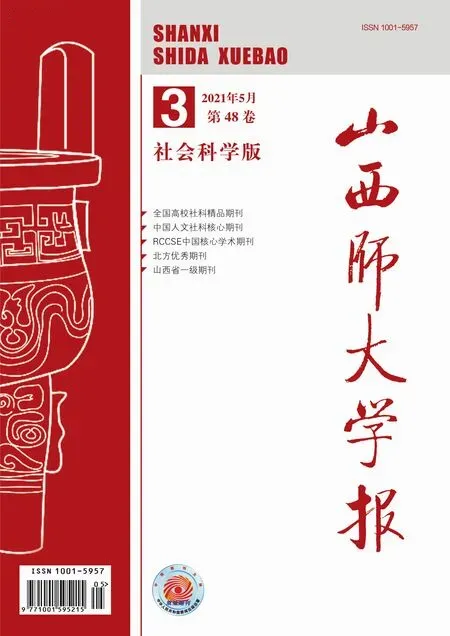“禁书”政治:清末北洋时期的《推背图》与社会治理
李 俊 领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中国谶纬文化源远流长,蔚为大观,对历朝政局皆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近代海通以来,由于西方印刷技术的引入,诗谶、图谶、占卜、命理等具有谶纬色彩的书籍得以大量印行。其中,《推背图》一书对社会各阶层心态的影响较为显著。该书是一部唐代问世的预言国家治乱兴衰的图谶之书,宋以降屡遭官方查禁。清末,该书在社会上秘密传播,禁而不止。民国时期,由上海出版商倾力营销的新编本《推背图》流行于城乡民众的日常阅读世界,成为当时最为典型的“图谶”文本。
清末北洋时期,禁书《推背图》一直是参与塑造不同群体之社会心态的重要“图谶”文本。在当时社会失范、信息极不对称的情况下,底层民众难以了解高层政治的动向,较多通过《推背图》等预言书猜测政局走势与国家命运,同时吐露他们的社会期待。无论是新知识人借助《推背图》展示其赞同辛亥革命的立场,还是袁世凯的臣属通过《推背图》等预言为洪宪王朝拟定年号,抑或是一般民众依据《推背图》猜测蒋介石是符合“天意”的政治强人,都可见该书对各界民众心态的深远影响。诚然,该书之所以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与上海出版商的营销密不可分。
据学者王学泰回忆,陆定一曾表示,“从马克思主义到《推背图》都要研究”。(1)王学泰:《〈推背图〉·图谶·〈红楼梦〉》,《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98页。不过,1960至1980年代,大陆学界因其荒诞不经的内容而甚少论及该书。史学家唐德刚则注意到该书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曾言:“我们写中国近代史,连《推背图》都要容忍三分。”(2)唐德刚:《晚清七十年》,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123—124页。近年有学者提出,“《推背图》的流传史堪称‘图谶版’的中国历代兴衰史,实不宜将其归类为迷信伪妄之书,而不予深究其流传背后的意义与价值”。(3)黄秀政:《〈推背图〉研究的集大成》,翁常锋:《〈推背图〉研究》上册(潘美月、杜洁祥主编《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十六编第23册),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序言第1页。近30年来,学界对近代《推背图》的文本及其传播已有一定的探讨(4)近30年来,学界已从文学、哲学与史学等不同学科角度讨论《推背图》,相关成果较为丰富。从史学角度探讨该书的主要论著情况如下:a.王硕认为,所谓金批本《推背图》“编成必在近代,绝非清初金圣叹所批”。见王硕:《〈推背图〉的流传及其历史观点》,《历史文献研究》新三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168页。b.陈学霖认为,1911年在日本东京问世的《推背图说》与滞留该地的中国革命党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见陈学霖:《刘伯温“烧饼歌”新考》,《罗香林教授纪念论文集》(下),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第1380页。c.台湾学者翁常锋系统考察了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荷兰等国图书馆所藏的40余种版本的《推背图》,初步梳理了该书在民国知识界的流传过程;另,其对德国慕尼黑大学鲍尔(Pro. Bauer. Wolfgang)教授、日本国学院中野达(Nakano Toru)教授等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亦作说明与辨析。见翁常锋:《〈推背图〉研究》(潘美月、杜洁祥主编《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十六编第23册,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d.许明、田野经过考证,认为大英图书馆等西方主流图书馆收存的英译本《推背图》的译者为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见许明、田野:《华夏有奇图,沧海现遗珠——〈推背图〉李提摩太英译本的发现与考证》,《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4期。,但对该书与近代中国社会治理之关系的探索尚不多见。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报刊、日记、档案、回忆录等资料,呈现清末北洋时期《推背图》的文本生成、信息传播、政治境遇及其对民众心态的影响,进而展示当时社会心态演进的复杂性与多面性,透视这一时期国家文化政策与社会治理的关联及成效微弱的深层原因。
一、清末《推背图》的流传与查禁
晚清时期,《推背图》虽仍为官方禁书,但在民间不乏秘藏、流传者。这一时期朝野流传的《推背图》版本数量尚难细究,但至少有数种。从图的数量看,可分为六十图本、六十一图本、六十四图本、六十五图本、六十七图本与六十八图本等;从流传的阶层看,有宫廷秘藏本与民间的抄绘本、石印本、铅印本等。(5)参见翁常锋:《〈推背图〉研究》上册,(潘美月、杜洁祥主编《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十六编第23册),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75—87页;三和君:《〈推背图〉版本考》,《读者欣赏》2013年第2期;王见川、宋军、范纯武主编《中国救劫预言书汇编》第一、二、三、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收录了20余种版本的《推背图》。晚清皇室熟悉《推背图》一书,如同治帝之嫔西林觉罗氏即依据该书的预言,将牛视为清朝的象征。(6)按:西林觉罗氏或是依据清代旧本《推背图》第42象的图像(“黄牛背上一绿头鸭”),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下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4—1495页。另,20世纪20年代初,溥仪喜欢看群狗和公牛打架,不时在宫内上演群狗追逐公牛的闹剧。荣惠皇贵太妃闻听此事后甚为担忧,认为这是关系爱新觉罗家族前途命运的大事。她依据《推背图》的预言,将牛视为清朝的象征,而群狗追逐、甚至咬伤公牛之事似为爱新觉罗家族的不祥之兆。不得已,她请来老福晋刘佳氏,托其劝说溥仪放弃群狗追牛的游戏。见贾英华:《老太妃从〈推背图〉算出皇城末日》,《你所不知道的溥仪》,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15页。光绪时期,六十七图本《推背图》在民间流传较广,甚至出现在德国的一家刊物上。历史学者李世瑜先生最先将德国刊物上的《推背图》介绍至国内,并认为这极可能是最接近该书历史原貌的版本。(7)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下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16页。实际上,该版《推背图》已经过清人改编,其第40象云:“红李中间一眼睛,长驱跃马入神京。无端恼了三公桂,—旦乾坤属大清。”(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下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2页)这显然是清人在影射满族得吴三桂之助而入主中原。本文姑且将六十七图本《推背图》称为“旧本《推背图》”。
庚子国变时,人们更为关注《推背图》《烧饼歌》与《黄蘗禅师诗》等预言诗文对时局的判断。进驻京城的义和团民众不乏熟悉前述预言者,他们以“扶清灭洋”为旗号,视外国人为“鬼”,并借用《黄蘗禅师诗》中“红鸡啼后鬼生愁”(8)《黄蘗禅师诗》,朱肖琴补注:《中国预言八种》,上海:广益书局,1947年,第100页。按:民国时期的图书将黄蘗禅师之名也写作黄蘖禅师、黄檗禅师、黄櫱禅师。本文统一写其名为黄蘗禅师。一语,将法、日、美、德等国使馆所在的北京东交民巷称为“鸡鸣街”。清人复侬氏、杞庐氏对义和团的这一行为解释说:“团众改交民巷为鸡鸣街,因《推背图》中有‘金鸡啼后鬼生愁’一语也。”(9)复侬、杞庐:《都门纪变百咏词》,杨米人等著,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9页。不过,目前所见清代多种版本的《推背图》中并无此句,应是他们将该书与《黄蘗禅师诗》混为一谈。这也表明当时士人阶层对《推背图》一书并不陌生。
清末,一些官员对《推背图》不无兴趣,但困惑于其背后的推演方式。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以博学著称的工部官员孙宝瑄未能参透前人预见时局走向的本领与路数,禁不住在日记中叹息道:“今日于天下万理,皆可勘透,惟先知之理不能明其故。……若夫谶纬家能预推千百年后事,相传之《推背图》《烧饼歌》,皆甚奇不可解。”(10)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93—594页。像孙氏这样了解《推背图》的官宦、儒士的确大有人在,其好友黄益斋甚至认为《推背图》源于孔子的《闭房记》。只是他们难窥该书的推演之术。
宣统时期,民间书坊私印的《推背图》传播渐广,人们借此表达对时局走向的期待。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相继离世后,清末政局愈发动荡,民间甚至出现了以《推背图》预言清廷气数将尽的舆论。学者萨孟武回忆称,大约在宣统元年(1909),《烧饼歌》与《推背图》“在市上都可以秘密买到”,其中《推背图》影响甚大,“时人均深信清室必亡”。(11)萨孟武:《〈烧饼歌〉与〈推背图〉》,《学生时代》,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第53—54页。当时有人称,中国“每逢国家将亡,及有大乱发生之时”往往会出现关于时局的预言,“而李淳风《推背图》、刘青田之《烧饼歌》、黄蘗禅师之《汉中语录》,竟至畅销于南方者,亦此类也”。(12)雷震:《京师谶纬之言》,《新燕语》(卷下),陆保璿编《满清稗史》下册,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第17页。南通“工商业受苛捐杂税的压榨,……极不公平,工商业者怨恨极了,大骂亡国政府,且有附会《推背图》《黄蘗诗》各种谶言,以决定清朝必然复〔覆〕灭”。(13)费范九:《南通光复记》,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第217—218页。作家张恨水回忆说:“在辛亥的前夕,扬子江一带城市,疯狂的传看着《推背图》《烧饼歌》这种文件,先是大家传抄,后来就有印本可买。”(14)张恨水:《看〈推背图〉的悲哀》,北平《新民报》1948年10月10日。他还注意到,当时人们对《推背图》那些奇奇怪怪的画像和似是而非的诗歌都感到莫大的兴趣,在茶余饭后互相交流,分析该书某句是影射时事的哪一点,甚至认为哪几句诗的预言马上就要实现。清末时人乐于谈论《推背图》,既是在乱局中互通声气,调适各自的焦虑心理,也为寻求世事变化的“天意”。在民间视野中,“天意”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政治观念,意即王朝的鼎革与循环在冥冥之中由上天预定,非人力可以左右。另外,“天意”并非秘不可测,一些具有特殊本领的人通过占卜手段可以探知其某种预定的可数量化的确定性,故而“天意”可具体化为“天数”。这种观念经过中国历代王朝兴衰之周期律的验证,加之《水浒传》等“历史感颇强的民间戏曲小说的熏染以及《推背图》、《烧饼歌》之类的谶书的影响”,有力塑造了清末民众对中国历史演进与人事代谢的认知。(15)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46页。在内忧外患日重且民不聊生的现实压力下,人们自然认为社会演进又到了王朝鼎革之时。
清末《推背图》在民间广泛流传,实与上海出版业的进步密切相关,这种现象引起清廷的恐慌,遂令巡警部明令查禁。宣统三年(1911)六月,巡警部向江苏省发出通令,要求查禁《推背图》等书籍。江苏巡抚程德全依据该地巡警道的相关禀告,向上海道饬称“(《推背图》)此等邪说实为淆人心之大患,亟宜严行禁止,以免妨碍治安”,同时要求该道“严禁各书坊出版”此书。(16)《江苏抚院程札上海道据巡警道禀奉部札饬严禁〈推背图〉等项书籍一案文》,《南洋官报》第178期,宣统三年七月,第6页。此时,清廷已查明上海是印行《推背图》的主要地点,试图从源头上进行治理。
然而,这种查禁举措实则难以奏效。清末上海的书局有400余家,不乏以印行《推背图》获利者,而上海巡警总局与各分局警力有限,在实际执行巡警部的查禁之策时难免力不从心,查不胜查。光绪三十年(1904),军机处将《革命军》《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等宣传革命的书刊列为禁书。然而,在清廷对社会的管控力度大为削弱的情况下,这些书刊一经查禁,反而销路更广。禁书《推背图》与革命党人的书刊一样,因查禁更受大众的关注。令清廷意想不到的是,一些新知识人开始在上海筹备出版新编本《推背图》。
武昌起义期间,一些乡绅也难以判断时局走向,不乏借《推背图》解闷者。浙江台州的乡绅黄秉义忧虑国事,在日记中称:“人云无定数,余则曰诸事均在于数,不可与其强求可也”;“今黎元洪于鄂省起事,以致数省未与战斗,能得如是俯首听命,乃国家大数。后事如何结局,人虽不知,早定于数也”。(17)周兴禄整理:《黄秉义日记》(第三册第三十六章)宣统三年九月廿五日(1911年11月15日),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1312页。他相信世事变迁皆有“定数”,不可违背,但又不能预知此“定数”。1911年11月18日,他从友人陈少山那里借来《推背图》,尝试从中一窥天机。当时像黄秉义这样既眷恋清廷又想顺从“天意”的乡绅为数甚众,而《推背图》这类谶书成为其选择政治立场的重要参考。
清末《推背图》虽仍为官方禁书,但已成为参与塑造社会心态的特殊文本。这种图文兼备的预言书蕴含着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循环历史观,在政治信息极不对称的社会环境中更容易引起普通民众的兴趣。清廷的查禁政策反而促使民众确信该书预言的真实性与可验性。作家张恨水对于《推背图》“那种毫无凭借的推测”不以为然,但对于清末民众议论该书的行为却予以理解和同情。他说:“一个人在苦闷中,往往就是用自骗的办法,来求得安慰的。在满清末年,国人眼见外侮频来,而满清官场还是那样腐败与无能,谁都想国家能找到一条出路。这出路,去问谁呢?在帝制时代是不可胡问的,而《推背图》这类东西,就以先知先觉的身份出现,而给予苦闷者一种摸索。问不到人,暗中摸索,不也比不摸索强吗?这正是当年乡党自好者一种悲哀。平心而论,讥笑他们无知是过分的,因为,我也是读《推背图》的过来人,所以我能作这种恕词。”(18)张恨水:《看〈推背图〉的悲哀》,北平《新民报》1948年10月10日。张以过来人的身份肯定普通民众借助《推背图》摸索未来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揭示帝制时代的政治言论管控造成的“愚民”现象。事实上,清末禁书《推背图》的广泛传播是民众对清廷离心离德的反映,而这种反映经过“禁书”政令的刺激与放大,又进一步消解了清廷“天命”的神圣性。
二、辛亥革命中的《推背图》编创及其短暂解禁
《推背图》虽不能带来革命,但可以成为革命党人的舆论工具。宣统三年(1911)三月,同盟会会员范鸿仙在《民立报》上发文,借用旧本《推背图》预言中的“金凤”与“五色云”赞颂湖北新军,期待中国出现领导革命的“华盛顿”。他说,自己崇拜英雄而不得,遂冒着“迷信图谶”的忌讳,以《推背图》“寄其思伤”。(19)南京市档案馆编:《铁血忠魂:辛亥先烈范鸿仙纪念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72页。范氏选择《推背图》作为其寄托心意的文本,正是看中了该书及其隐含的“天意”观念在民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其对《推背图》的解读代表了部分革命党人与普通民众对政治变革前景的期待。这种运用“图谶”的宣传策略促使人们关注湖北革命形势的进展,甚至比三民主义的革命宣传文字更能触动人心。江南地区的民众从《推背图》等谶书中推断革命党人排满行为及其旗帜颜色的“天意”所在。宣统三年(1911)秋,像浙江德清的严家衖这样偏僻的村庄也流传起“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反满口号。夏衍回忆当时这里的情景说:“我记得那时流传得最广的一本书是《推背图》,老百姓说,那是‘明朝的诸葛亮’刘伯温写的。我没有看到过这本书,但是我每次走过邬家店门前,都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议论《推背图》上说的‘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这两句话。他们说九十九就是一百缺一,百字去了一,就是白,因此革命军挂的是白旗。”(20)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2页。在这些民众看来,明代的刘伯温像诸葛亮一样能够洞察“天机”,其所作《推背图》准确预言了革命军在宣统三年(1911)推翻清廷的政治事件,而且革命军旗帜的白色符合谶言“手执钢刀九十九”的暗示。这种观念意味着革命军对清廷的政治斗争符合“天意”,且清廷覆亡自有定数,难以改变。因此,这些民众倾向于同情甚至支持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其实,“手执钢刀九十九”一句出自《烧饼歌》,夏衍错将其当成《推背图》中的内容,但他所言该书在社会上的流行情况较为可信。
由于民众普遍敬畏人格化的“天”,革命党人重视运用《烧饼歌》与《推背图》向民众宣传革命符合“天心”的正当性。1906年,革命党人在湖南发动萍浏醴起义时的一则公告宣称:“今日天心属我,体天伐罪吊民。”(21)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二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143页。1911年10月17日,湖北军政府在阅马场举行祭祀天地的仪式,黎元洪主祭后宣读《祭告天地文》,表示自己在克复武昌之际“投袂而起,以承天庥”;革命党人“用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22)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112页。。前述两份文告特意使用了“天心”与“天庥”两词,强调“天”对革命的肯定与支持。这里的“天”可以视为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另外,革命党人还利用《烧饼歌》《推背图》等预言宣传其革命的正义。湖北军政府成立后,革命党人在其大门口右侧贴有标语,其文云:“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斯其时矣。”(23)傅国涌:《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6页。10月27日,同盟会元老谭人凤为首批援鄂湘军所写的《军歌》云:“湖南子弟善攻取,手执钢刀九十九,电扫中原定北京,杀尽胡人方罢手。”(24)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二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151页。他对《烧饼歌》中的“手执钢刀九十九”一句做了新的解释,称:“革字九笔,党〔黨〕字十九笔,这句话,本来是谶讳(纬)家的预言,却应在我们革命党身上。”(25)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二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151页。紧随湖北军政府成立,革命党人印制了《秘本详解推背图说》(26)《秘本详解推背图说》,1911年印行,出版地不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藏。,其封面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出版”字样,对应的公元纪年为1911年。革命党人对《推背图》的利用,不仅促使普通民众接受革命者受“天心”支持的舆论宣传,而且强化了革命党人自身对这场革命的政治认同。
“辛亥革命时,刘伯温《烧饼歌》及《推背图》传诵一时。”(27)张延祥:《钢刀九十九》,《申报》1932 年4月9日。而《推背图》已成为此时人们表达政治期待的公共文本。1911年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成立,革命党人推举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随后,黎元洪成为军政府首领的信息很快传到北京、天津等城市。有人回忆称,其当时在京津旅行,注意到一同乘船的两位商人的闲谈,甲说:“《推背图》中未见有黎元洪,恐不能成事。”乙反驳道:“不然,黎元洪者,即大元朝朱洪武之后人也,必继其祖业无疑。”甲笑曰:“我们且不管,但预备看新皇帝耳。”(28)心潮:《革命纪念京津旧游记》,《申报》1920年10月8日。这位旅行者又注意到,几位商人于舱外席地而谈,一人问革命党是否与李自成一样,一人曰:“否,瞎李是贼,这是争皇帝。鞑子坐了二百多年,也该还我们了。”(29)心潮:《革命纪念京津旧游记》,《申报》1920年10月8日。他们仍以臣民的心态议论时局,认为掌握湖北新军的黎元洪或是改朝换代的真命天子;又从汉族的本位出发,认为应该轮到汉族人当皇帝了。对于一般民众而言,革命是别人的信仰和事业,自己只是旁观者,而非主动的参与者,至多是被动员的跟随者。当然,他们最希望在皇帝的治下过升斗小民的太平日子,至于谁当皇帝并不是他们可以置喙的事情。
民国肇兴,原本属于清代禁书的《推背图》得以暂时解禁,上海一些出版机构抓住商机,遂公开印行该书。1912年1月2日,位于上海四马路的新汉印书馆在《申报》上发布广告,称其出售西洋印装的“禁书”《推背图》。(30)《禁书十九种减价出售(广告)》,《申报》1912年1月2日。不久又发布广告称,洋装《推背图》等“前清禁书”现在政府又将禁售,“欲购从速”,极力刺激消费者的好奇心与消费欲望。(31)《满清禁书》(广告),《太平洋报》1912年6月19日。其所售洋装《推背图》当为明治四十五年日本东京秘库本的精装版《推背图说》。
除出版清旧本《推背图》外,上海的出版机构还印行新编本《推背图说》,其中1912年艺海书店版《推背图说》(32)《推背图说》,上海:艺海书店,1912年。另,《推背图说》(明治四十五年刊本)为每一象加了卦名、卦辞和按语,但未加谶语。颇具代表性。该书共有60象(每幅图及所配文字为一象),除第30象系自创之外,其余59象均取自清旧本《推背图》。其具有一个开创性的特色,即在60象的图像后面增加了干支、卦名、谶语与按语,借助“易理”的占卜形式,抬高其预言的权威性。(33)翁常锋:《〈推背图〉研究》,(潘美月、杜洁祥主编《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十六编第23册),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6页。在图像改编上,该书不顾史实,将多数“胡人”的着装均改为清代官员或士兵衣装,如第26象中宋代金人的衣帽竟然是顶戴花翎、长袍和对襟马褂(34)《推背图说》,上海:艺海书店,1912年,第10页。。又将第47象说明文字中的“胡儿”二字改为“夷人”,并为其配了近代欧洲男子常用的礼帽、领带、风衣与文明棍。(35)《推背图说》,上海:艺海书店,1912年,第23页。绘图者似未意识到这种“夷人”的衣装绝非唐代李淳风、袁天罡所能预知。不过,新编本《推背图》作者的具体姓名目前仍无线索可查。
辛亥革命前后,无论是旧本《推背图》的秘密流传,还是新编本《推背图》的悄然改编,都显示民众借助这些“图谶”文本表达其政治倾向性的社会心态。庚子国变以后,有识之士开始盼望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能为清末政治困局开出一条新路。普通民众在庚子赔款与外债的沉重压力下,再难承受新政的改革成本,纷纷希望清廷倒台,代之而起的新生政权能给他们一个喘息的机会。他们基本不了解革命的意义,大体视之为恢复汉族姓氏的江山。虽然他们对革命的认同和接受,不能直接左右革命者与清廷的对决,但客观上为革命者一方增加了权重。“老百姓的态度实际上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刺激着官吏和乡绅,日积月累地销蚀和瓦解着上流社会对王朝的信心和忠诚。”(36)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59页。《推背图》《黄蘗禅师诗》等谶书无形中动摇了官员对于清廷统治的认同感。1912年2月,曾任学部主事、军机章京的许宝蘅对于清帝逊位并不伤感,他原以为《黄蘗禅师诗》中“继统偏安三十六”一句预言宣统朝会有偏安36年的运数,未料不过36个月而已;在其看来,清廷国祚终结的过程几无纷扰,如此容易,既是“天心已厌乱”(37)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一册,1912年2月12日,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94页。的结果,也是天数不可违的宿命。当社会秩序严重紊乱,革命行为得到普遍同情的时候,乡绅阶层与各级官吏也会因为“民心已失”而有意另谋出路。尤其在清末内忧外患并发的重压之下,民众的社会心态在无形中加速了清廷国祚的终结。对于辛亥鼎革之际的政治走向而言,《推背图》可谓一种特殊的社会风向标。
三、北洋时期《推背图》的遭禁与民众的社会期待
民初传统谶书得以解禁的好景不长,北洋政府很快恢复了“禁书”政策。1914年,京师警察厅开始依规查禁《推背图》。是年3月,北洋政府颁布《治安警察条例》。依照该条例,警察、官吏对于民众在通衢大道及其他公众场所粘贴、散布、朗读文书图画的所有行为,如果认为其有“扰乱安宁秩序”或“妨害善良风俗”的情形,就必须“禁止并扣留其印写物品”。(38)《治安警察条例》(教令第二十八号三年三月二日公布),《内务公报》1914年第7期,第7页。同月,京师警察厅内左三区的巡警在街头发现山西平顺县人崔歧祥售卖《推背图》等书,认定该书为有害于社会秩序与善良风俗的禁书,遂将崔氏带到警署。崔氏供称,自己是山西平顺县人,现年65岁,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居住,以卖书为生;近期从一位过路人手中购得《推背图》与滑稽小说4本,在街售卖,并不知《推背图》系禁书。相关办案巡警称该书“语多迷信,足以惑人观听”(39)《京师警察厅内左三区区署关于崔歧祥售卖禁书的送案表》(1914年3月1日),档号:J181-019-07083,北京市档案馆藏。,随后将其扣留销毁,但没有解释该书究竟“迷信”在何处。他们在处理崔歧祥案的判决书中明确称其“本属乡愚,估〔姑〕予从宽省释”。(40)《京师警察厅内左三区区署关于崔歧祥售卖禁书的送案表》(1914年3月1日),档号:J181-019-07083,北京市档案馆藏。这“乡愚”二字的定性可见京师警察厅对普通民众的俯视姿态。其实,旧本《推背图》与民国元年出版的新编本《推背图》对清康熙帝之后的中国历史虽有预言,但相关图文十分模糊,实难比附袁氏当国的政局。当时京师警察厅将《推背图》列为禁书,可能沿用了宣统三年(1911)巡警部的相关政令,唯恐有人借《推背图》预言制造社会舆论,聚结反对北洋政府的力量。当时高层政治信息并不透明,普通民众也没有可以问询的正规渠道。他们在苦闷中也只能以《推背图》等预言聊以自慰,远未意识到自己的国民身份与自由权利。
在京师之外的地区,警察对《推背图》的查禁并不严格,而上海的出版机构继续发行新编本《推背图》。1915年5月,《圣叹手批中国预言》(一名《中国二千年前之预言》)由上海文明书局与中华书局共同出版。其中收录的“金圣叹手批本《推背图》”即后世所称“金批本《推背图》”。该书借鉴了艺海书店版《推背图说》增加干支、卦名、卦辞与按语的做法,所录60象的图文与此前各版本《推背图》大不一样,至少有26象的图文属于新创。(41)这些新创图像较为明确地对应了晚清与民初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其具体预言如下:第34象谶曰:“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颂曰:“太平又见血花飞,五色章成里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非。”此象指太平天国运动,甚至将“洪秀全”三个字嵌入诗句中。第35象谶曰:“西方有人,足踏神京。帝出不还,叁台扶倾。”颂曰:“黑云黯黯自西来,帝子临河筑金台。南有兵戎北有火,中兴曾见有奇才。”此象指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仓皇逃亡热河。第36象谶曰:“纤纤女子,赤手御敌。不分祸福,灯光蔽日。”颂曰:“双拳旋转乾坤,海内无瑞不靖。母子不分先后,西望长安入觐。”此象指庚子国变中,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逃亡西安。第37象谶曰:“汉水茫茫,不统继统。南北不分,和衷与共。”颂曰:“水清终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内竟无王,半凶还半吉。”此象指辛亥年武昌起义,清廷国祚将亡,由帝制改为共和制。见《推背图》,《圣叹手批中国预言》,王见川、宋军、范纯武编《中国预言救劫书汇编》第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不过,二者存在一个相同的局限,即大多数图像中的“胡人”均配用清代官员的衣装。金批本《推背图》自创图像部分的推演方式“应该与旧图所用方式非常类似,是一种混用几种占法的演算”。(42)劳思光:《“绝倒芳时虚度”——我以术数自娱》,《解咒与立法》,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240页。其图文相互配合,采用了拆字、嵌字、藏头、类象、比喻、谐音等表达方式。虽然目前仍难以考证金批本《推背图》的作者,但该书“似与南社诗社颇有关联,举凡个人著作与金圣叹批注《推背图》有关人士,皆有参与南社诗社之共同背景渊源”。(43)翁常锋:《〈推背图〉研究》,(潘美月、杜洁祥主编《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十六编第23册),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92页。如该社成员徐珂与胡怀琛等人均探讨过金批本《推背图》。民国初年,南社的多数成员积极反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其通过改编《推背图》的方式表达政治立场也确有可能。另外,文明书局的创始人之一廉泉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曾任该书局经理后又创立中华书局的陆费逵亦赞同革命。在编创者的精心策划下,金批本《推背图》问世后很快赢得读者们的青睐。
金批本《推背图》一经问世,就引起北洋政府的重视。1915年7月,《圣叹手批中国预言》出版不过两月,袁世凯总统府内史监致函内务部要求查禁该书。其在函文中称,由进步书局印刷、文明书局与中华书局发行的金批本《推背图》在各省中华书局分售,“此等妖言历来即在禁止之列。今该书又加裒集,并有改造之处。若任其流播,殊足蛊惑人心,于治安甚有妨碍。希电沪禁止该书局发行,并通饬各省一律禁止售购,以息构煽而定人心”(44)《江苏巡按使公署饬第四千一百六十一号》(遵照内务部咨禁售〈圣叹手批中国预言〉),《江苏省公报》第585号,1915年7月23日,第9—10页。。在其看来,传统的《推背图》《烧饼歌》之类的图谶实为“妖言”,特别是经过“改造”后的金批本《推背图》,更有“蛊惑人心”之害。按照1914年颁行的《出版法》第四条规定,《圣叹手批中国预言》一书出版之前,文明书局与中华书局须禀报当地警察官署,并由该官署将一份样书“送内务部备案”。(45)《出版法》(1914年12月5日),蔡鸿源编《民国法规集成》第2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16页。从事后发生的情况看,两书局很可能未向警察机关报备,否则,内务部会依据《出版法》第十一条有关文书图画不得“妨害治安”与“败坏风俗”之规定(46)《出版法》(1914年12月5日),蔡鸿源编《民国法规集成》第2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17页。,禁止该书出版。
不过,内史监对这类图谶如何“鼓惑人心”未做解释,判断标准也不明确,仅凭一己之见而饬令内务部执行。内务部依照此函指示,遂电令各省行政长官督办此事。但这一查禁政策显然有悖于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第二章第五条第四款有关国民“言论、著作刊行”(47)《中华民国约法》(1914年5月),蔡鸿源编《民国法规集成》第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9页。及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的规定。
北洋政府查禁《推背图》的通令引起革命党人何海鸣的注意。何氏于1911年参加文学社,后在上海任《民权报》主笔;二次革命时,何氏在南京策动讨袁,并自任讨袁总司令,失败后潜居香港,但仍坚持反袁立场。他原本认为《推背图》的预言不过是“荒唐之说”,但因政府突然查禁该书,心生好奇,于是特地购置一册《圣叹手批中国预言》。不过,他从中没有看出“袁家天下的好处来”(48)何海鸣:《求幸福斋随笔初集》,上海:华商出版社,1915年,第84页。,也没有看出袁世凯查禁该书的根据。相反,他认为,为该书作序的清溪散人所言“民国时代例无忌讳”(49)《推背图》“清溪散人序”,《圣叹手批中国预言》,王见川、宋军、范纯武编《中国预言救劫书汇编》第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50页。的话很有道理;只有君主时代的当政者因为“个人之天下”而患得患失,难免担忧《推背图》的预言为敌对者所利用;在五族共和的民国时代,《推背图》的政治预言无关个人得失,只关国运盛衰,无需查禁。(50)何海鸣:《求幸福斋随笔初集》,上海:华商出版社,1915年,第88页。因此,他猜测袁氏查禁该书的动机是出于个人政治得失的考虑。
不过,何海鸣对金批本《推背图》确有兴趣,并将其研读后的心得收入《求幸福斋随笔初集》一书。其中涉及近代中国历史的内容如下:第34象指“洪秀全太平天国之革命”,第35象指“咸丰出狩热河,英军火焚圆明园之事”,第36象指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逃至长安,第37象指清朝灭亡、武昌首义与袁氏当权后的时局,第38象指欧洲战争,第39象预示东邻日本对中国的祸害,第40象似暗示某个日本人或孙中山于1915年去世,不能确定,第41象可能预示“亡清死灰尚有在西安复燃”的一天,第42象可能指美国的干预促使中日交涉后和平相处的“可喜之兆”,第43象与第44象所指不明,第45象可能指日本遭到了“教训”。(51)何海鸣:《求幸福斋随笔初集》,上海:华商出版社,1915年,第84—88页。以目前所见资料,何氏在民初较早解读了金批本《推背图》,领一时之风气。商务印书馆编辑徐珂在其所编《清稗类钞》中介绍了该书,并承袭了何氏的相关解读。(52)《推背图》,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3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第3—5页。
《求幸福斋随笔初集》于1915年9月由华商印书馆付梓。当时政局波诡云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声势持续高涨,而普通民众无从知晓高层政治纷争的信息,只好从《推背图》中猜测国运的起伏。
吊诡的是,金批本《推背图》竟影响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后的年号选拟。曾任参议院议员的刘成禺称,袁氏恢复君主立宪制,在年号拟定时受到该书的影响。当时有提议用“武定”者,有建议用“文功”者,结果主张“符应图谶”(53)《洪宪年号》,刘成禺著,宁志荣点校:《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三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00页。的提出者占了上风。其依据《推背图》与《黄蘖山人禅诗》,认为二者均符合《周易》卦理和“五行”观念;其中《推背图》“小小天罡[垂]拱而治”一条云:“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元向汉中看。”《黄蘖山人禅诗》云:“继统偏安三址〔十〕六,洪荒古国泰阶平。”因而,其建议年号先确定第一个字为“洪”字,再拟第二字。袁世凯认可此说,遂纳其言。(54)《洪宪年号》,刘成禺著,宁志荣点校:《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三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00页。由此可见袁氏的幕僚中确有人借金批本《推背图》并杂合民间预言迎合袁氏寻求“天命”之心(55)按:曾任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员的徐兆玮在1937年7月的日记中提到刘成禺关于洪宪年号议定之事。他发现,在袁世凯年号问题上主张“符应图谶”者依据的所谓德国图书馆影印的《推背图》与传钞本不相符,而《黄蘖山人禅诗》与其父的手录本也不一样。徐氏因而感叹道,这类图谶预言的“礻几祥小数”并无标准文本,大家说法不一,是非难辨。(清)徐兆玮著,李向东、包岐峰、苏醒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六册(1937年7月24日),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4085页。,而袁氏迷信命理与“图谶”也是事实。(56)袁世凯之女袁静雪回忆称:“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听得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主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也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见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27页。
洪宪帝制失败后,《求幸福斋随笔初集》于1916年6月又由民权出版部印行,在全国发售。这自然引起人们更多关注《推背图》对时局的预言。翌年5月,《申报》广告称,某江南名士精研该书10余年,“豁然领悟”其中奥妙,认为《推背图》对过去有准确无疑的预示,对现在有蛛丝马迹的暗示,对未来有人定胜天的警示,进而撰成《推背图索隐》一书。(57)《推背图索隐》(广告),《申报》1917年5月27日。经过出版商的营销,《推背图》及相关谶书在各大城市热销。当时,《益世报》的一位记者注意到北京的茶楼戏馆总有人兜售《推背图》,禁不住慨叹:这种书“迷信无理,惑世害人有最大的关系”;现在茶楼戏馆大卖特卖,“也没人问,也没人管,难道说这算出版自由吗?”(58)亦我:《推背图》,《益世报》(增刊)(北京)1917年5月2日。其从开通民智的角度主张“非把此等邪书一火焚净不可”。(59)亦我:《推背图》,《益世报》(增刊)(北京)1917年5月2日。在一些新知识人看来,《推背图》这类预言书以“迷信”蛊惑人心,必去之而后快。
或许因为《益世报》等社会媒体的呼吁,京师地方政府加紧查禁《推背图》等谶书。1917年10月7日,京师警察厅左一区的巡警伊荣贵发现有人在街头兜售《推背图》与《宪书》,随即将其带到警署。(60)《京师警察厅内左一区区署关于蕴德隆售卖〈推背图〉等书一案的呈》(1918年1月1日),档号:J181-019-22244,北京市档案馆藏。随后,这位书贩供称,自己名为蕴德隆,是河北香河县人,现年36岁,在前门外校尉营居住,以售卖《宪书》为生;这次花7500文钱从打磨厂学古堂的文成斋书铺购得20册《推背图》,每册卖铜板五六枚。经过警察训诫,蕴氏表示其家境贫困,不知《推背图》系禁书,保证以后不再贩卖此类禁书。随后,蕴氏在保证书上签字画押后被释放。京师警察厅左一区区署并未就此结案,而是传讯学古堂的铺掌,要求其将剩余的《推背图》一并送案。后因该铺掌有事回籍,追查学古堂库存《推背图》之事暂停办理。其实,像蕴氏这样的普通民众整日为温饱奔波,几乎没有法律意识,也难以理解《推背图》究竟因何犯禁。他们的臣民心态和迷信心理的改变有待于社会的整体进步。
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界对《推背图》的看法并不一致。一方面,批评该书以“迷信”害人。有人认为,《推背图》《烧饼歌》之类的预谶之说“识者不道”;如果事后偶得一个巧合的谶语,用作闲谈,则有趣味,但泥于“迷信”,则显得不够明智。(61)定夷:《戊午随笔·预谶》,《小说新报》第4卷第9期,1918年9月,第3页。钱玄同表示他在1903年之前还相信《推背图》《烧饼歌》确有灵验,现在这种“荒谬程度略略减少”。(62)钱玄同:《答陈大齐〈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第626页。陈独秀也认为《推背图》所言并无根据,说想要了解千年万年后的社会制度如何,“只待富于神秘性的玄学大家重造新《推背图》”。(63)陈独秀:《答张君劢及梁任公》,《新青年》1924年第3期,第4页。同年,李翰忱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批评说,“最能使社会陷于迷离惝怳之中” 的预言书是《推背图》,该书“现在所传的本,也不[是]一种,其中的语调,若明若昧,闪闪灼灼,类乎骑墙语,令人难凭;这就是他惑世的伎俩处”。(64)李瀚〔幹〕忱:《破除迷信全书》,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317页。在他们看来,《推背图》不过是民间“迷信”之书,不可受其蒙蔽。另一方面,肯定该书预言准确。有署名为“枫隐”的作者撰文称,童谣和《推背图》《烧饼歌》之类的图谶一样,乍听“似费解可笑”,实际“与后世时局颇有关系”。只是不到其时,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些谶言的真实寓意。(65)枫隐:《童歌新释》,《大公报》(天津版)1922年7月29日。曾任江苏都督府顾问的严伟表示,《推背图》多奇验,“汉水滔滔”一节确指辛亥八月武昌发难。(66)严伟:《心太平斋笔记》(续),《礼拜六》第168期,1923年,第10页。知识界对于《推背图》的批评与肯定各有长短,一时间难以形成有利于开启民智的主导观念。像严复、钱穆、梁启超、蒋梦麟、穆藕初等新知识人相信占卜,并未明确反对《推背图》,大致默认了这种属于占卜的图谶。
事实上,北洋政府的查禁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都未能真正改变民众对《推背图》的兴趣与需求。因为有利可图,上海一家书店不顾北洋政府的禁令,于1921年8月公开在报纸刊登广告售卖《推背图》。(67)《广告》,《申报》1921年8月18日。1924年,有人指出,《推背图》流传数百年不绝的原因在于“政府有禁令”,这让“好事者反以为秘书而藏之”。(68)老圃:《推背图跋》,《申报》1924年4月15日。可以说,北洋政府的查禁在很大程度上为《推背图》做了免费广告。
在战火频燃的乱世,普通民众深盼着能够统一中国的强势人物应运而生。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因此大失民心。7月,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共讨北洋政府。一时间,国内政坛风云激荡,南北硝烟四起,呈群雄逐鹿之势。1927年1月,有人对国民党的新秀蒋介石大加赞赏,称中国古书《推背图》有“将军头上一丛草,二人立在石头上”一句,前半句“寓蒋一字”,后半句“寓介石二字”。(69)逸庵:《蒋介石考》,《申报》1927年1月23日。其由此论称《推背图》“言之恰合”,隐喻蒋介石掌管国民革命军符合“天意”。其实这两句话不过是民间流传的谜语,并非当时各版《推背图》中的文句。这种宣传手法似乎意在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营造社会舆论。虽然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但诸多民众却仍保持着“天子”观念,希望有“真主”建立一个新的朝廷,使社会秩序恢复常态。他们也不一定拥护皇帝,而是从自身的安全出发,“感觉强人可以给人一种安定的生活”。(70)李怀宇:《余英时:开启共和之梦》,《思想人:当代文化二十家》,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9页。即使如此,借《推背图》称赞蒋介石的社会舆论也反映出一些民众不再认同北洋政府的正当性,转而期待有实力、有政治理想的国民革命军为中国政治进步带来新的机遇。
四、余论
清末北洋时期的普通民众对《推背图》半信半疑者居多,毕竟当时并没有解释该书预言的标准答案。他们对《推背图》的阅读、推测与谈论,重在寻求心理安慰,克服社会恐慌,表达由某位政治强人现世并重建社会秩序的愿望。这种阅读和谈论多少带有一些迷信和娱乐的成分。相对于民众借助《推背图》克服恐慌心理与表达社会期待的积极作用而言,其“迷信”问题居于次要地位。这也正体现了该书之社会影响的多面性与矛盾性。
《推背图》的预言很容易被普通民众附会成某些具体人事变化的“天意”。他们仍旧保持着传统的“臣民”心态,在对《推背图》的津津乐道中,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位“真命天子”身上。革命党人有意利用《推背图》等预言宣传革命事业的正当性,在政治话语上特意使用了民众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天心”观念,因为当时民众仍将“天”视为一切政治秩序安排及其正当性的最终决定者。在社会革命滞后的情势下,普通民众尚不能理性看待中国古代历史的演进,容易将其视为由“天意”决定的治乱兴衰的周期循环与王朝宿命。退而言之,即使中国历史像《推背图》预言的剧本那样一幕幕演出,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那就是一种宿命,因为“已经发生了的历史,未必就是必然要发生的历史”。(71)胡文辉:《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个预言》,《洛城论学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1页。
诚然,《推背图》依托的占卜思想与“命理”观念具有久远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社会根基。即使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严复、梁启超、蒋梦麟等诸多新知识人依旧相信占卜和命理,因为“科学并不能为人们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是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个人的命运问题,人文学科在这方面又没有发挥足够大的作用”。(72)熊月之:《近代中国读书人的命理世界》,《学术月刊》2015年第9期。这就给蕴含占卜思想和“命理”观念的《推背图》等预言书留下存在和传播的空间。尤其在中国古代信息极不对称的社会环境中,各类“图谶”和扶乩、看相、堪舆、算命等推演人事的术数共同构建出一套应对生活不确定性的办法。其在实际生活实践中的部分灵验性,表明社会变化确有某些可以预知的趋势。因此,不少人相信以“易理”可以推算“命理”,并将其适用范围从个人命运延伸至国家命运。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占卜这种“小道”存在着“致远恐泥”(《论语·子张》)的局限。
清末北洋时期,新旧《推背图》毕竟被列为官方禁书。清廷查禁《推背图》,实系维护其一姓之天下的私心使然。不过,在民心思变之际,清廷查禁此类“图谶”书籍的效能颇显微弱。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指出,清廷禁书、禁报的政策是最拙劣的“操术”,因为“书愈禁则求之者愈切,读之者愈熟,而感受者愈深”。(73)梁启超:《敬告当道者》,《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67页。尤其在清末朝廷对民间社会的管控大为衰弱的情势下,新式印刷业与出版业迅速崛起,“禁书”之令几如螳臂当车,不可能再现雍正、乾隆时期相关政令的成效。只是清廷不谙世道人心之变,终使《推背图》流传更广。北洋政府视《推背图》为“迷信”“妖言”,将其连同其他预言书一并查禁,且不加解释。这表明威权人物仍秉持王朝时代的“治教一体”模式,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变相剥夺了《中华民国约法》赋予国民的相关自由权利。然而,像蕴德隆、崔歧祥等因售卖《推背图》而被查禁的底层民众却不知维护其国民权利。所谓该书“妖言惑众”的重心并不在“妖言”,而在于“众”能够被“惑”的民智问题。以开启民智而言,查禁《推背图》的策略与举措实无多少意义,反而刺激人们更多地传播该书。因此,北洋政府关注和尊重《推背图》反映的社会心态,远比查禁该书更为重要。在信息传播多元化的新社会环境中,禁书之令只能成为所禁之书的免费广告。
清末北洋时期,新旧文化并存与信息传播多元化已成为社会的新常态,当政者有智“不如乘势”(《孟子·公孙丑》),实不必以信息封锁的方式管控公共舆论与风俗人心。查禁《推背图》之举实为逆势而行,既无助于国民意识的觉醒,也销蚀了其政治正当性的“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