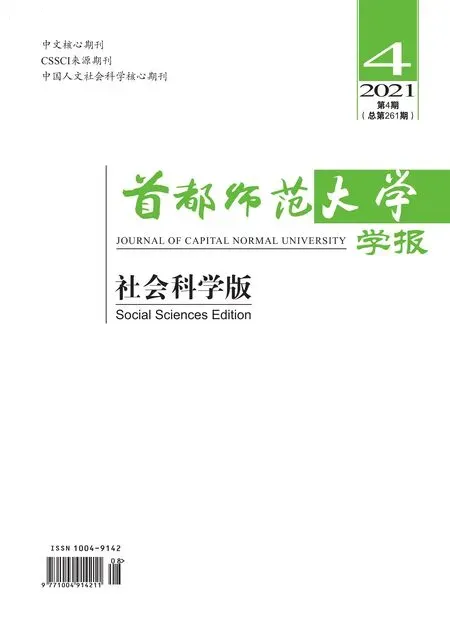新浪漫主义的中国旅行与实践困境
龙扬志
引 言
从新文学百年历史维度回望外国诗学理论的输入,20世纪20年代前后兴起的新浪漫主义理论译介是不应忽视的一个环节,其引进初衷是给新诗提供一条参照途径,通过诗歌内容与形式的改良和完善回应诗质缺失的质疑。作为一种推动文学发展的积极方案,新浪漫主义的译介自有历史与现实价值,但在当代学术场域中,相关话题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因“茅盾研究”浮出地表。事实上,学界对新浪漫主义的理解与定位迄今仍较为模糊,有学者将新浪漫主义视为阐释世纪末思潮的一种文学观念,强调新浪漫主义并不等于早期现代主义,原因是“现代主义思潮在当时西方尚在初创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界对其是相当隔膜,态度也是很谨慎的,他们眼里的欧洲新思潮主要是一种世纪末文艺思潮”①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有学者指出现代作家经常混淆“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两个概念②吴晓东:《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有时甚至是相互指涉的(如谢六逸),“尽管在具体估价象征主义的地位方面论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大都把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西方最为晚近的新艺术潮流,代表了文学发展的取向。这反映了20年代初之所以形成介绍象征主义的一个高潮的基本成因”①吴晓东:《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正因如此,作者将新浪漫主义视为一个派生出象征主义诗学的早期形态。
与此相对照,早期倡导新浪漫主义的核心人物沈雁冰在20世纪50年代回顾新浪漫主义时,认为它就是“现代派”:“‘新浪漫主义’这个术语,二十年代后不见再有人用它了,但实质上,它的阴魂是不散的。现在我们总称为‘现代派’的半打多的‘主义’,就是这个东西。这半打多的主义中间,有一个名为‘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事实上是逃避现实,歪曲现实,亦即是反现实。因此,我以为‘超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倒可大体上概括了‘现代派’的精神实质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派’和五十多年前人们曾一度使用过的‘新浪漫主义’,稍稍有点区别;当时使用‘新浪漫主义’这个术语的人们把初期象征派和罗曼·罗兰的早期作品都作为‘新浪漫主义’一律看待的。”②茅盾:《夜读偶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参与20世纪40年代新诗理论译介的代表袁可嘉在回顾现代主义源流时则指出,五四时期所称的“新浪漫主义”其实就是广义的现代主义,包括唯美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③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如果去掉特定历史语境的批判话语,沈雁冰与袁可嘉对新浪漫主义的理解相当接近,概念和内涵皆涉及现代主义的多重特征。④持这一观点的著作还有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34页)、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等。海外学者认为新浪漫主义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线性时间的热情采纳,“对于一些中国作家和批评家来说,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新浪漫主义体现了文学的最新发展,新浪漫主义是当时最为先进和最为现代的文学潮流。作家和批评家们将这一现代主义写作潮流看成是进步过程的最后一阶,又将对新浪漫主义的认知和加入看成是自身文学现代性的完成标志”⑤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其观点是新浪漫主义在新文学发展观念中扮演着实践现代性的终极模式,在基于进化论建立的共和国文学史叙述中,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现代性话语被排斥于理论体系之外。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沈雁冰对新浪漫主义的倡导初衷并非是文学层面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以“新理想主义”哲学为骨子,包含着“人类爱”这一特殊色彩的“人道主义”文学。⑥潘正文:《沈雁冰提倡“新浪漫主义”新考》,《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
中国学界对于新浪漫主义的概念、内涵及其相关问题产生的不同看法,尤其是源自当事人与后来者的差异化理解,说明不同处境和视野可能产生很大的分歧。从理论旅行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梳理,清理其传播背景、途径、过程等具体历史问题,反思西方理论在移入中国文学空间时提供的参照作用,审视外来资源转化为中国诗学资源所面临的挑战,不论是重识文学观念演变,还是着眼当下理论话语的建构,都有切实之意义。
一、新浪漫主义与日本资源
尽管新浪漫主义源于欧洲,但在进入中国文学视野的过程中,日本作为独特的桥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由日本文坛转译到中国的西方文学观念,虽然经过日本学界的重新消化和理解,甚至与原本内涵产生歧义,却不能忽视译者选择译介对象的文化立场。⑦陈方竞在探讨《苦闷的象征》对中国新文学的参照意义时指出:“如果说厨川的《苦闷的象征》立足于东亚,从日本文学发展出发,对柏格森、弗洛伊德的这些‘舶来品’剥离中的汲取,使文学艺术真正从本民族学院派‘科学家似的专断和哲学家似的玄虚’中独立出来,以实现对社会文化变革中人的生命意识和精神现象的审美表现的理论建构,那么,中国新文学发生在北京大学这座高等学府中,这带来中国新文学更为突出的学院文化特征,这一特征的负面意义更是在‘五四’后呈现出来的,是新文学作家愈益突出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艰难中表现出来,是新文学无法承担‘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职责的根源之一。因此,中国新文学面临的就更是一个人的生命意识觉醒和精神发展要求的问题,《苦闷的象征》在这个背景下进入中国新文学,是新文学挣脱学院文化束缚,从主观意志论、生命哲学、精神分析学出发寻求文学发展的表现,同时,这也是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真正获得独立,并得到独立发展的表现。”(陈方竞:《〈苦闷的象征〉与中国新文学关系考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这种变异的理论无疑不同于理论本身,所以有必要以谨慎态度重新清理日本学界对新浪漫主义的译介与改造。
据考证,“新浪漫主义”概念在日本文坛出现的时间比中国早近30年:
“新浪漫主义”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日本文坛是明治24年(按,即1891年)6月《栅草纸》第20号上刊登的森鸥外对罗赛蒂的批评。明治34至35年间,“新浪漫主义”这一术语在德国近代文学的冲击下重新流行于日本文学界。大塚保治《论浪漫主义及吾国文艺之现状》一文首先使用了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①肖霞:《浪漫主义:日本之桥与“五四”文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明治40年之后,以文学团体“牧羊神会”中的北原白秋、木下圶太郎、吉井勇、长田秀雄等人为代表,围绕《昂星》《屋上庭园》《三田文学》《新思潮》等文学平台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异国情趣的作品,日本文坛和学术界关注并阐释新浪漫主义的理论家逐渐增多。在“现代主义”作为一个特指名词出现之前,“新浪漫主义”用来描述那些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和思潮。比如生田长江(《象征主义》,1907;《从自然主义到象征主义》,1908)、本间久雄(《最近欧洲文艺思潮史》)、宫岛新三郎(《现代日本文学评论》)等人都对此有深入讨论。日本高校采用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如温彻斯特的《文学批评原理》、莫尔顿的《文学的近代研究》、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坪内逍遥的《近世文学思潮之研究》《小说神髓》等,它们成为中国青年留学生接触现代文学的重要来源。其中,厨川白村和升曙梦关于新浪漫主义理论的阐释对中国影响尤其广泛(二者在田汉1920年4月写给友人的信中被提及)。
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第九讲“非物质主义的文艺”)对“新浪漫主义”进行了详细介绍,此书1912年出版,1921年8月罗迪先译成中文由上海学术研究会丛书部出版,厨川白村解释了这一流派产生的原因:虽然新浪漫主义不能囊括欧洲文艺新潮流,但代表了一种主要倾向,书写从“科学万能的迷梦中醒来”的精神状态,即“灵的觉醒”。厨川白村如此总结新浪漫主义的基本特点:“晚近的新文艺,主要的是取那样人生之神秘的梦幻的方面文学。换言来说:暗示人生隐藏的一面,在自然的眼看不见的真相,由具象的东西来表现,是把这个结晶了象征了的东西。”②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下卷,罗迪先译,学术研究会丛书部1934年版,第118页。与现实主义比较,新浪漫主义的“进步”表现在对表象的超越:“新浪漫派常喜欢用神秘的色彩象征的笔致,也不过为着暗示潜在实人生里面。某种的方便或手段罢了。自然派的物质之描写到底是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现实主义的文艺,专描写接触耳目的实生活里面为能事相反;而新浪漫派的作家,在实生活中,人我都要感受耳不得闻,目不得见的某物更有进一层的努力。”③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下卷,罗迪先译,学术研究会丛书部1934年版,第122页。尽管罗迪先的译文相当粗劣,不过仍可传达出作者的大概意思。
相比之下,升曙梦关于新浪漫主义的解释要更全面。升曙梦是日本明治、大正年间公认的俄国文学研究专家,对中国新文学理论的影响深远,特别是中国接受俄国文学的相关环节。升曙梦的新浪漫主义研究建立在强烈的认同基础之上,他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谈道:
从明治四十年(按,即1907年)光景开始,注意到当时在俄国文坛也是刚在开放花朵的新浪漫派、象征派、新写实派底新的艺术,不断地拿到手边贪婪地读了下去。这样,那每一句对于我都像是发现新大陆,这正可以说是一种惊异之感罢,感觉到全然像是重生一般的兴味,而立刻翻译了那其中的一、二篇。④升曙梦:《翻译与研究五十年》,文之译,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第24页。原题为“研究和翻译五十年”,1950年发表于东京新星社出版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译者认为翻译谈得更多,因此重新调整了标题。参见该书“译后记”,第73页。
大正10年8月(1921年8月),升曙梦与生田长江、野上臼川、森田草平共著的《近代文学十二讲》由日本新潮社出版,不知什么原因,汪馥泉后来翻译此书并没有署其他三人的名字,结果在中国就成了升曙梦的“专著”。可能同为“讲义”的缘故,关于新浪漫主义的讨论明显借鉴了厨川白村,比如新浪漫主义与旧浪漫主义的区别,升曙梦说:
旧罗曼主义,只是忘我地歌咏,只是沉醉于梦幻空想的境地中,全然和现实游离的。但是新罗曼主义,是曾由于自然主义受了现实底洗礼,阅历怀疑底苦闷,为科学的精神所陶冶,而后显现的文学;同是神秘,旧罗曼主义底神秘,只是从梦幻中酿出的,新罗曼主义底神秘,是从痛切的怀疑思想出发而更进一步的。①升曙梦:《现代文学十二讲》,汪馥泉译,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版,第248—249页。
这一段描述和此前厨川白村的基本相同,从罗迪先的翻译中可以看出:
虽说是神秘梦幻的文学,但决不是像前世纪初的浪漫派,只管迷惑在梦幻空想的境地,理想憧憬时代的文学。其中已经是经过一回实现的经验,被科学的精神陶冶后的文学。经过自然主义怀疑思潮这种痛烈的人生经验和修练之后,表现出来的文学。所以一样说是神秘,决不是从旧时梦幻空想出来的神秘;新浪漫派是出生在近代的怀疑更深进一步的东西。②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下卷,罗迪先译,学术研究会丛书部1934年版,第118—119页。此部分翻译比较混乱,可参考昔尘:《现代文学上底新浪漫主义》,《东方杂志》第17卷第12号,1920年6月25日,第71页。
值得注意的是,升曙梦等人在厨川白村的基础上加入了不少自己的思考。本书对新浪漫主义的理论定位,是通过与其他文学思潮的严格区分实现的,如前所述及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此外,升曙梦特别提到新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区分,认为印象主义是自然主义加入主观因素发展而来:
虽则笼统地说自然主义艺术是客观的艺术,但这只是比较上的事;只有本来自然主义,可以说客观的艺术罢,但印象派的自然主义,是客观的,同时是主观的。就是,是成立于主观客观融会的境地的艺术,立在所谓物心如一的境地。换句话讲,是在自然主义(本来自然主义)底物质的倾向与非物质的倾向,——心灵的倾向,正好合一的状态中的艺术;这稍稍增加一点主观的量,便立即离开自然主义的领域,进了新罗曼主义的境地。在这意义上,印象主义(印象派的自然主义),成了自然主义与新罗曼主义底过渡的东西。③升曙梦:《现代文学十二讲》,汪馥泉译,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版,第255—256页。
印象主义文学加入更多的主观因素,进一步发展为象征主义文学,这就决定印象主义具有过渡性质。升曙梦抓住主观成分这一关键情感因素,从理论上界定了印象主义与新浪漫主义文学的区别。
升曙梦在本讲第三节重点讨论Decadent(颓废派)艺术,汤鹤逸将标题译为“颓废派的艺术与象征主义”,汪馥泉则直接音译为“丹加旦的艺术与象征主义”,这一处理体现出译者的深意,把原本包含“颓废”含义的词译成专有名词,以消解负面的道德倾向。④“颓废”在20年代还有一个更加形象的音译:“颓加荡。”李欧梵认为这个译名更好,因为它“音义兼收,颇为传神”。参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1页。升曙梦认为象征主义与颓废派的文学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他分析“颓废”这一名词在1882—1883年的偶然性来源,说明颓废派文学的审美趣味并不具有道德含义。为了消除望文生义的误解,莫里斯等一部分人后来将这一命名改为“Symbolism”(象征主义),这是象征主义的来源,而另一部分人则沿用“颓废派的艺术”。因此,虽然后来的发展各有侧重(比如颓废派对“异常”的渴求),二者在本质上却是相通的。升曙梦在“新罗曼主义文艺底勃兴”这一讲还分析了神秘主义、享乐主义、新理想主义等文学思潮,把它们当成新浪漫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
“新浪漫主义”在英国19世纪末主要指史蒂文森、康拉德等人的小说作品,它们的特点主要是写离奇的冒险故事,表达人物具有不同寻常的个人冒险和开拓精神,在德国则指霍夫曼斯塔尔、霍普特曼等剧作家,他们通常于现实之外寻找写作题材。新浪漫主义通常被作为后期浪漫主义的替代词而出现。⑤参见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7—88页。可见新浪漫主义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欧洲概念,与后期浪漫主义相互通用,并不具有“现代主义”的内涵。新浪漫主义从欧洲旅行到日本文化场域后已经发生变异,日本文坛对新浪漫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加入了新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新浪漫主义的现代性面貌塑造在日本近代文学场域完成,经过明治时期的“脱亚入欧”引发概念内涵的变化,这种悖谬体现了世界主义与民族语境的差异性转化,当它被移植到现代观念与文化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必然要经历落地生根和适应生长的困难过程。
二、新浪漫主义的中国旅行
“新浪漫主义”出现于中国现代报刊,最早可能是在田汉的诗歌中。赵英若《现代新浪漫主义之戏曲》刊于1919年9月出版的《新中国》第1卷第5号,则应该是在理论文章中最早的正式表达。1919年8月15日,田汉散文诗《梅雨》在《少年中国》第2期发表,根据他次年4月8日回复给黄日葵的长信《新罗曼主义及其他》来看,此诗是春天所作,在这封信里田汉再次将该诗与新浪漫主义联系起来:
还有一些意志强固些的人,也不肯自杀,也不肯咒生,也不肯遁世,偏偏的孜孜的要求一样什么自救的东西,于是这种要求表现于文学的,便是欣慕新世界的文学,便是新罗曼主义的文学!我去年春上做了那首“梅雨”诗。末了的几句说:
我虽不懂什么世事,也害过许多世纪病,
受过许多世界苦,——
在这“古神已死,新神未生的黄昏”中,
孜孜地要求那片新罗曼谛的乐土!
也就是这样意思。①田汉:《新罗曼主义及其他——覆黄日葵兄一封长信》,《少年中国》第1卷第12期,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6月15日出版,第47页。《梅雨》原诗最后一节是:“我虽然不甚懂世事,也受了许多世纪病Tin-de-siècle,经了许多世界苦(Welt-schmes),在这‘古神已死,新神未生的黄昏’中,孜孜的要!要!求那片Neo-Romantism的乐土!”参见田汉:《梅雨》,《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出版,第18页。其中法语“Tin-de-siècle”(世纪末)后来修改为“Finde siècle”,德语“Welt-schmes”(世界苦)修改为“Weltschmerz”。
田汉对新浪漫主义的推崇,是通过多种文学思潮综合比较而逐渐形成的,当时他同日本的重要文学家如佐藤春夫、石川啄木等人有直接或间接交往,通过他们广泛结识了一批日本文学界、出版界和戏剧界人士,这对于田汉体会日本文学的发展情况和方向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就交往对于田汉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形成而言,首先应该提及的是厨川白村。田汉向黄日葵介绍新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来自厨川白村,并复述了拜访厨川的经过:“上月(三月)中旬我游京都四天,在伯奇兄那儿住。我到九州去的前晚(即十八日晚),曾偕伯奇访问白村先生于冈崎公园侧之广道,畅谈至九时半才回来,我曾问他三四个重要的问题,都给了很满足的答复。他对我国的新文坛,希望很殷,并且希望我们‘少年中国’的新艺术家多事创作,心中若是想要写什么,便马上要写出来,莫管他好和歹。因为思想不同别物,若莫用他他便要臭起来。又说,翻译事业,固然要紧,在建筑自然主义,最好多译易卜生的。尤推荐我们译俄国Dostoievsky(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说日日言社会改造,毕竟是要从个人改造起,他的艺术能令人为深刻的反省啊!”②田汉:《新罗曼主义及其他——覆黄日葵兄一封长信》,《少年中国》第1卷第12期,1920年6月15日,第39—40页。肖霞认为这是厨川白村与中国作家之间直接见面的唯一记录(《浪漫主义:日本之桥与“五四”文学》,第275页),实际上郑伯奇后来还去见过一次,“从此,我和厨川总算认识了,以后,我为给《少年世界》写一篇有关日本妇女运动的稿子,还访问过他和他的夫人”。参见《忆创造社》,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41页。田汉对厨川白村把文艺思潮与人生相对应起来分为三期的主张深为感佩,他以简明的方式列出一个表格,第三行:“新浪漫主义——四十岁前后的圆熟时代(求可以有的对象)”,“圆熟”是“静”的体现,代表文艺的成熟,这都是厨川白村的描述。田汉认为中国新文学将来的趋势就要沿着这条道路向前发展,他明确标明《梵珴璘与蔷薇》(VIOLIN and ROSE)是一部“新浪漫主义的悲剧(A Neo-Romantic Tragedy in Four Acts)”③田汉:《梵珴璘与蔷薇》,《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15日,第41页。该剧连载至第6期登完。。
田汉接受日本文艺观念并应用于欧洲文艺问题分析,意在获得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参照。《俄罗斯文艺思潮之一瞥》(1919)、《诗人与劳动问题》(1920)与《新罗曼主义及其他》(1920)之间清晰的逻辑关联,大致反映出认知的转换。《俄罗斯文艺思潮之一瞥》刊于《民铎》第6期“现代思潮号”,主编李石岑加了热情洋溢的介绍:
吾友田寿昌君,夙究心于文学,近年于俄罗斯文学思潮,研讨尤力。余编现代思潮号,以俄国文学思想与现代思潮关系最切,特以此托之。田君此文全编约五万余言,亟欲全登,维后半尚须改削,本期登至近代写实主义(realism)之爱他主义(altruism)为止。后此为俄罗斯马克思主义(Russian Marxism)时代与现今文学象征主义(Symbolism)时代,此时代中以象征主义为经,以社会思潮为纬,篇幅颇长。最后结论,综合现代各国思潮以说明俄国思潮,并述过激主义(Bolshevism)与文学思潮之关系,甚具真价。愿阅者待之,下期定当续刊也。①参见《民铎》第6期第85页,1919年5月出版。
实际上,续刊(第7期,1919年12月)时仅谈到虚无主义,未涉及马克思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1919年11月动笔、历时3月完成的《诗人与劳动问题》则提供了一个与以往文学理论不同的视角,从现实生活与艺术关系来阐释文学的互动发展,用田汉本人的话说,是“由文学向社会”②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1920年2月15日,第1页。。田汉采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分析文学与社会阶层的关系,意在揭示出文学随生产方式进化而呈现出“时代文学”色彩。他将诗歌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拟古典主义与资本主义”“罗曼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然主义与社会主义”“新浪漫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③原文为英文,参见《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第13—14页。文章洋洋洒洒两万多字,却因时间安排限制,仍未谈到新浪漫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④田汉在文章后面附有简要说明:“又本章之后本拟再加一章介绍象征主义与主观经济学的体系也因为时间关系,不能不待下回介绍,而照本论讲至此也大可收束了,缺漏之处单于出单本时补入,且译诗中有太草率的,读者不能不谅我偷空执笔之苦。二月十日晚八时田汉识。”参见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1920年3月15日,第104页。《少年中国》第8期为“诗学研究号”,出版时间是2月15日。不过,他附在文后的发生学背景阐释了《新罗曼主义及其他》的起源,亦可定位出新浪漫主义在田汉心目中的位置,他是把它当成一种先进的西方方案来理解的,该观点随田汉与郭沫若、宗白华三人通信集《三叶集》的出版而扩散。
沈雁冰是继田汉介绍新浪漫主义之后响应积极的一位,由于沈氏担任《小说月报》编辑的有利地位,在其推动下,新浪漫主义成为国内文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问题。
1919年,商务印书馆受到陈独秀、罗家伦等人的公开批评而“声誉一落千丈”,被寄予革新厚望的沈雁冰作为王蕴章的助手加入《小说月报》编辑部,旋即增设“小说新潮”栏,沈雁冰明确表示以前的翻译小说(主要指林译)都“不合时代”,介绍“新派小说”已很迫切:“况且西洋的小说已经由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进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表象主义(symbolicism)、新浪漫主义(new romanticism),我国却还是停留在写实以前,这个又显然是步人后尘。所以新派小说的介绍,于今实在是很急切的了。”⑤参见《“小说新潮”栏宣言》,《小说月报》第11卷第1号,1920年1月25日出版。在有关新浪漫主义的文学理论中,象征主义被定义为写实(自然主义)到新浪漫主义的中间环节,新文学要达到与世界思潮接轨的水平,象征主义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阶段,因此沈雁冰在《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一文中,采用问答方式就“表象主义”提倡的意义进行了解释:
问:写实主义对于恶社会的腐败根极力抨击,是一种有实力的革命文学,表象主义办不到这层,所以应该提倡写实,不是表象。
答:这些话我通通承认,但我们提倡写实一年多了,社会的恶根发露尽了,有什么反应呢?可知现在的社会人心的迷溺,不是一味药所可医好,我们该并时走几条路,所以表象该提倡了。
问:然则提倡表象之后立刻有多大效验么?
答:自然不敢必。但我们要晓得:写实文学的缺点,使人心灰,使人失望,而且太刺戟人的感情,精神上太无调剂,我们提倡表象,便是想得到调剂的缘故,况且新浪漫派的声势日盛,他们的确可以指人到正路,使人不失望的能力。我们定要走这条路的。但要走路先要预备,我们该预备了。表象主义是承接写实之后,到新浪漫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得不先提倡。①雁冰:《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小说月报》第11卷第2号,第6页,1920年2月10日。原刊目录的标题为“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字么”。
正如问答体暗示了自我诘辩的过程一样,沈雁冰给出表象主义必须提倡的理由其实很不充分,他没有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趋势进行思考,大概意识到写实主义在文坛占据一统天下的局面,而表象主义可以为这种单调增添多样性,用他的话来说表象主义相当于调味品,这跟后来周作人对新诗“没有一点朦胧”表示不满、期盼欧化的趣味是一致的。当然,也说明沈氏对于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的了解还比较简单。
沈雁冰的理论缺陷引起谢六逸的注意,《小说月报》第11卷第5号、第6号连载了谢氏寄自日本的文章《文学上的表象主义是什么?》,有学者认为这是沈雁冰“组织谢六逸等人对文学上的表象主义进行讨论”②董丽敏:《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根据作者回忆,应是谢氏的主动投稿。③茅盾在《新文学史料》连载的回忆录中说:“同期(11卷第5期)‘小说新潮’栏又登载了谢六逸的《文学上的表象主义(象征主义)是什么?》这大概是见了第二期我写的《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引出来的。谢六逸当时尚在日本,可见这局促一隅的‘小说新潮’栏竟也引起身居海外者的注意。”茅盾:《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辑,第69页。谢六逸的阐释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他说:“就吾国说:还没有经过实写主义的文学,骤然间来谈表象主义,不免有‘躐等’之弊;但是表象主义是什么,我们却不可不研究。”④谢六逸:《文学上的表象主义是什么?》,《小说月报》第11卷第5号,1920年5月10日,第1页。该文先谈何为表象,然后根据所分类别依次介绍“本来表象”“比喻与寓言”“高级表象”和“情调表象”,“情调表象”与前三种的不同表现在以“锐敏的神经官能的作用为基础,而表现情调”,谢氏指出“挽近颓废的艺术(Decadent Art)的表象派著作,多属是种。”他说:“表象主义,不外是以暗示(Suggestion)为根本的文艺。这派的文艺,以诗歌最占势力。”⑤谢六逸:《文学上的表象主义是什么?(续)》,《小说月报》第11卷第6号,1920年6月10日,第3页。谢六逸标明了该文的理论参考书,其中“日人厨川辰夫《近代文学》”就是指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按,厨川名辰夫,号白村),在介绍表象主义诗歌特点之后,分析了“晦涩难解,很不易使人欢迎”的原因:“其实表象诗之所以难解,乃其本质所致。因为注重情调;而情调就不如像思想感情之分明,是茫漠的;不可捉摸的。……唯其当作谜语;所以难解了。这是一部分。此外有不很注重形式,专写人生的种种相和生命中的几微,用表象方法表现作者的感情的。”在比较新浪漫派与浪漫派之间的差异时,谢六逸显然参考了《近代文学十讲》,也加入了个人的理解:“以前的浪漫派只求美于幻境;自然派又只注重地上的现实生活,专寻出丑来。到了晚近的新艺术——新浪漫派——便能由清新强劲的主观,参加实写主义精微的观察力,团练调和一过,艺术的趣味也就达到最高的境界。开拓‘诗美的新领土,就算这派。’”⑥谢六逸:《文学上的表象主义是什么?(续)》,《小说月报》第11卷第6号,1920年6月10日,第7页。谢氏对于在中国提倡表象主义文学持否定态度,他的依据是中国还没有经过“实写主义”,“没有经过实写主义特色——科学的制作法,描写兽性,描写人生;周围;个性;印象;作短篇小说及戏剧等——的滋味,不由这些阶段通过。便要一蹴而学表象主义的文艺,那就未免不自量,仍然要跌到旧浪漫主义(传奇派)去。因为没有受过科学的洗礼,便要倾向神秘;没有通过实写;就要到表象,简直是幻想罢了。”⑦谢六逸:《文学上的表象主义是什么?(续)》,《小说月报》第11卷第6号,1920年6月10日,第7页。谢六逸“浇冷水”或许带着几分情绪化色彩,不过也多了几分旁观者的清醒。就新文学发展短暂的历史而言,除了鲁迅等为数甚少的几位中年作家之外,基本上还没有产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新诗则仍然还在为生存合法性与旧派文人展开激烈论争。
作为一种理想型的文学图景,新浪漫主义所展示的现代诱惑无法抗拒。虽然遭受谢六逸“棒喝”,沈雁冰在此后不久的《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中坚持“非自然主义的文学”,理由是“新文学要拿新思潮做泉源,新思潮要借新文学做宣传”,文坛现状是“新文学追不上新思想”。沈氏为了解新浪漫主义的知识背景花了相当精力,他此时尚不通日语,获取信息主要借助欧美书刊。这篇文章也显示了这样的特点,凡是有助于证明新浪漫主义比自然主义优越的观点,皆被悉数罗列,并辅以相关作家作品加以说明。
但是,新浪漫主义在欧洲并不具有现代主义的内涵,即如沈雁冰所说:“所谓新浪漫主义起初是反抗自然主义的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发生极早,在自然主义初生的时候,已经有了。”①雁冰:《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第3卷第1期,1920年9月15日。与日本文学理论家们提出的表象主义构成自然主义过渡到新浪漫主义的中间环节相冲突,也不符合沈氏自己描绘的文学进化路线。在这种有意误读下,他得出的结论是:“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能引我们到真确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所以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②雁冰:《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第3卷第1期,1920年9月15日。这一观点也是此前《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的延续。
有人指出沈雁冰的理论过于“冒进”,智荪认为中国新文学在写实主义与新浪漫主义之间犯了一个程序错误,建设新文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以欧洲文学作为学习范本,则有必要将近代文学的渊源和过程进行深入学习,不能仅限于自然主义与新浪漫主义之间来取夺。③智荪:《对于谈新文学者之意见》,《改造》第3卷第10期,北京新学会编,1921年6月15日,第73页。按;“智荪”可能是张东荪的笔名,张东荪是《解放与改造》(后来改名为《改造》)自始至终的重要撰稿人,主要使用“张东荪”“东荪”等名字发表文章。智荪强调文学的“沉酣”,因为欧洲不同时代的文学各有特点,值得中国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学习,不宜偏废,唯有“沉酣”才能领会精髓,如他此前认同的,“艺术之道,莫先于求忠实”。沈雁冰迅速回应智荪的质疑,认为提倡更先进的文学潮流是“我们现在所能做而且必需做的”:“这两问题底新旧两方面底争,自然是很剧烈,却是同属于新的,彼此也有许多歧异,因而生出许多闲话。譬如新近有位朋友做了一篇《对于谈新文学者之意见》,之乎者也,说了半天,总是一个‘现在做的东西都不好,还是不要做好’,这种消极的求进步办法,真和骂古代人为什么要造出后世人要不用的独木船来渡河一样的有趣!”④冰:《我们现在所能做而且必需做的》,《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6月30日。在他看来,更有力量的回应是用实践证明新浪漫主义文学的价值。《小说月报》革新之后,外国文学翻译占居了很大份量,如编者所说:“本刊自改革以来,最注重者是介绍西洋文学。”⑤参见《最后一页》,《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1922年6月10日。选择对象也不限于新浪漫主义,以俄国文学为例,有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爱罗先珂、安德列夫、高尔基、蒲宁等作家被译介,包括了19世纪至20世纪以来的大批重要作家,新浪漫主义代表如波德莱尔、梅特林克、王尔德、戈尔蒙等更是反复被译介。沈雁冰曾说:“我们如果承认现在的世界文学必要影响到中国将来的新文学——换言之,就是中国的新文学一定要加入世界文学的路上——那么西洋文学进化途中已演过的主义,我们也有演一过的必要。”⑥沈雁冰:《文学作品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论》,《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从文学观念看,作者坚持中国文学必须与世界文学踏入同一条河,才会获得站立的根基,这是沈雁冰将新浪漫主义视为文学发展理想形态的根源。⑦当代学者潘正文认为沈雁冰提倡“新浪漫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于社会启蒙价值,因此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学范畴指向并不完全重合:“沈雁冰与‘新浪漫主义’的关系,沈雁冰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虽然两者之间不无关联,但实际上它们基本上属于两个命题,不能简单等同。沈雁冰虽然译介过许多现代派的作家、作品,但这只是出于普及知识的需要;而他明确提出要倡导的‘新浪漫主义’(这代表着沈雁冰心目中的文学方向),实质上是指以‘新理想主义’哲学为骨子,包含着‘人类爱’这一特殊色彩的‘人道主义’文学。文学研究会的‘爱’与‘美’文学,正是与之相呼应的文学种类,或者可视为是某种变形。”参见潘正文:《沈雁冰提倡“新浪漫主义”新考》,《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不论是“冒进”,还是追上世界浪潮,说明这样一种理论新形态当时具有超前性,理解与消化的困难不仅存在于读者群体那里,甚至也存在于译介者本身,相比于前者,后者需要更长的实践机制提供反馈。
三、观念挪用与实践困境
新浪漫主义通过有意提倡受到广泛关注,很快进入到接受的具体操作层面,一些理论介绍文章通过不同渠道发表,不过它们主要是从日本著作中摘译出来。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标准知识”作为文化启蒙和普及的一部分受到重视,郑振铎、沈雁冰等提出统一外国人名地名翻译的倡议,对文学词条进行释义,意在通过标准化实现对外来文学概念的知识化定型。
比如李达在《民国日报·觉悟》“文学小辞典”栏目介绍了“神秘”“神秘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词的定义,其中“新浪漫主义”的定义是:
描写人生神秘的梦幻的方面,暗示人生隐蔽的方面,把人所不能见到的真相,用具体的方法表现出来,叫做新浪漫主义。(古典主义,代表古代文艺思潮;浪漫主义,代表中世纪文艺思潮;自然主义,代表19世纪前后的文艺思潮;新浪漫主义,代表最近的文艺思潮。)①李达:“文学小辞典”,《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6月6日。
不久,夏丏尊选出“描写”“暗面描写”“周围描写”“象征”“高级象征”“情调象征”等“新词”再解释,比如新浪漫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情调象征”是这样定义的:“把用普通的说法所表示不出来的情调,用别的事物来暗示的,叫做情调象征。音乐底能以声音底高低长短,表示种种情味的,就是情调象征底一个好例。”②丏尊:“文学小辞典”,《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6月15日。这些新浪漫主义诗学范畴的名词被纳入“辞典”,说明与新浪漫主义相关的知识已经获得被阐释的地位。
此外,《民国日报》还大量刊载了厨川白村、升曙梦等人的文学理论译稿,汪馥泉算是用力最勤的一位,译文质量也很高。仅就新浪漫主义相关的译作来说,有揭载于1921年10月4日的《灵肉合一观》(厨川白村);厨川的《文艺思潮论》连载于1922年2月21日至3月28日计26次;汪氏和张闻天合译的《王尔德介绍》从4月3日载至18日计12次;汪、张二人合译的王尔德代表作《狱中记》又从20日开始登载至5月14日计14次。该年7月,汪馥泉写出介绍性短文《文艺上的新罗曼派》:“新浪漫派是暗示人生隐着的一面,把眼睛所不能看到的自然真相用了具体的东西来表现,并使这东西结晶且象征化”,“新浪漫派因为能观察到人生的深奥处,能透视事物的底里,所以能从丑的表面发现美,从有毒的花里吸出甜蜜的汁”。③汪馥泉:《文艺上的新罗曼派》,《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7月9日。此后,汪馥泉还译出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觉悟》1924年6月1日—24日连载计23次)。凭借《民国日报》这一影响广泛的媒体平台,新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先锋性理论逐渐流行。
关于新浪漫主义的大众传播,颇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是黄忏华在一本有教材色彩的著作中对“新浪漫主义”作专门介绍④黄忏华:《学术丛话》,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版,第122—124页。,他在引言中甚至明确表示对这一文学的“感情”:“就作者个人说,文学方面,顶醉心的,是新浪漫主义当中的近代神秘主义;哲学方面,顶醉心的,是东方哲学当中的印度哲学。”⑤黄忏华:《学术丛话》,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版,第1页。不过,新浪漫主义经过日本改造而获得丰富的现代内涵,由于移入中国缺乏相应的时代土壤,导致相关观念停留在翻译“挪用”的层次,无法得到作品的及时确证。比如,讨论新浪漫主义通常会引用昔尘《现代文学上底新浪漫主义》(《东方杂志》第17卷第12期,1920)与汤鹤逸《新浪漫主义之勃兴》(《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1924)的文章,但它们皆为译作而非原创,不能与田汉当年的阐释相提并论。⑥昔尘的《现代文学上底新浪漫主义》刊发时没有任何说明,但它确实是从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第九讲第一节摘译出来的,可以对照厨川《十讲》罗迪先译本第115—132页。汤鹤逸的《新浪漫主义文艺之勃兴》译自升曙梦和另外三人合著的《近代文学十二讲》第五讲,文后有译者附记:“右作系根据生田长江,野上白川,升曙梦,森田草平共著的《近代文艺十二讲》之第五讲。惟原著有行文过于冗长之处,因取便读者,略加删节,附此声明。1924年12月6日,译者识。”可以对照汪馥泉译本第243—298页。只有移译而无创作实践融会贯通的理论挪用,说明在倡导与理解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
理论挪用往往造成望文生义的生吞活剥,一位叫洪瑞钊的作者指出,象征派文学关系到中国文学的前途,但其列举的作品却是冰心的《超人》《月光》、叶绍钧的《潜隐的爱》《低能儿》《一课》、李之常的《金丹》、许地山的《命命鸟》。⑦洪瑞钊:《中国新兴的象征主义文学》,《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7月9日第4张第2版。洪氏对象征主义的概括和理解相当混乱,可能因为象征主义与此前倡导的新浪漫主义有密切关系,沈雁冰以《文学批评的效力》回应洪氏“实在误会已极”,指出“文学批评者不但要对于文学有彻底的研究,广博的知识,还须了解时代思潮,如果没有这样的修养便批评,结果反引人进了迷途了”,其实也从一个角度指出了理论挪用的条件。
作为一个重要的旁证,简单挪用导致的低级错误曾引起鲁迅强烈不满,给西山养病的周作人通报文坛动态时仍难掩愤懑:“《时事新报》有某君(忘其名)一文,大骂自然主义而欣幸中国已有象征主义作品之发生。然而他之所谓象征作品者,曰冰心女士的《超人》、《月光》,叶圣陶的《低能儿》,许地山的《命命鸟》之类,这真教人不知所云,痛杀我辈者也。我本也想抗议,既而思之则‘何必’,所以大约作罢耳。”①鲁迅:《致周作人》,参见《鲁迅书信集》(上卷)第34号函,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20天之后,鲁迅又在信中谈到沈雁冰“太骛新了”,实际上对沈氏专挑新题材、新作家作为约稿限制很不满。②鲁迅:《致周作人》,参见《鲁迅书信集》(上卷)第37号函,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他认为新东西需要消化的过程,“唯新是慕”不一定会有理想的收获。
身为鼓吹新文学的主将,胡适在1921年7月22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对《小说月报》部分文章的看法,向新浪漫主义的鼓吹者沈雁冰提出劝告:
我昨日读《小说月报》第七期的论创作诸文,颇有点意见,故与振铎及雁冰谈此事。我劝他们要慎重,不可滥收。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作底子。我又劝雁冰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现代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有写实主义作手段,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如梅特林克,如辛兀(Meterlinck,Synge),都是极能运用写实主义方法的人,不过他们的意境高,故能免去自然主义的病境。③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页。
虽然鲁迅与胡适对沈雁冰提倡新浪漫主义不满,但是二人的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鲁迅认为“骛新”,新浪漫主义对照中国文学发展实际仍是一个超前的话题。胡适表示不可“滥唱”,强调文学首先要立足于现实,反映现实,至于是否要发展到新浪漫主义,未必是新文学的必然结果。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胡适的态度显示出“意见领袖”对文学发展的某种期待与忧虑,而沈雁冰对于胡适的批评也不像回应谢六逸、智荪、洪瑞钊等人一样忙于自我辩护,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表态要“期期提倡自然主义”,并准备出专号,译介福楼拜、莫泊桑的作品。④沈雁冰:《沈雁冰信四通》,《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62页。意味着他重新理解新浪漫主义译介与新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新理论既呈现了文学现代性问题面对的现实诉求,促使观念与实际保持合理的差距,又隐喻了一种“现代性困境”,想象的理论脱离历史势必构成观念的空转。
作为国内引介与力推新浪漫主义的新文学骨干,沈雁冰从1922年开始转向对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倡导,到1925年“五卅”前后,完成了以反映阶级斗争的“新唯实主义”文学转向。随着这位坚定信徒的“出走”,寓示着新浪漫主义理论的中国旅行划上阶段性的休止符。
不过,作为丰富文学观念与创作手法的尝试,在后续的文学实践中获得回响。由田汉对新浪漫主义率先进行的译介,就推动了早期象征主义和颓废派文学理论的传播。他在《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续)》(1921年12月1日)一文中,将波德莱尔描述的经验定义为近代主义、象征主义的条件,并将“Decadent Symbolism”音译为“醴卡妉象征主义”。汤鹤逸将升曙梦的第三节讨论的标题译为“颓废派的艺术与象征主义”,汪馥泉则采用音译的方式,译为“丹加旦的艺术与象征主义”,把原本包含“颓废”含义的词当成一个专有名词翻译,意在淡化其道德倾向。早期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等人的诗歌体现出鲜明的颓废色彩,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新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穆木天曾说“贵族的浪漫诗人,世界末的象征诗人,是我的先生”⑤穆木天:《我主张多学习》,郑振铎、傅东华编:《我与文学》,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318页。,比如《泪滴》《我愿作一点小小的微光》等作品体现出浓厚的颓废情绪。颓废风格在1926年后的创造社诗人中表现得相当明显,除穆木天的诗集《旅心》(1927)之外,王独清的《在圣母像前》(1926)、冯乃超的《红纱灯》(1928)也有类似的倾向,他们当时对于颓废美学的理解是与象征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将其视为象征主义诗歌的一种特质。颓废与象征在中国新诗语境中之所以混杂难分,原因还是二者发生学背景相同,其皆源于新浪漫主义中国化改造。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曾对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的象征主义风格进行比较:“后期创造社三个诗人,也是倾向于法国象征派的。但王独清氏所作,还是拜伦式的雨果式的为多;就是他自认为仿象征派的诗,也似乎豪胜于幽,显胜于晦。穆木天氏托情于幽微远渺之中,音节也颇求整齐,却不致力于表现色彩感。冯乃超氏利用铿锵的音节,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咏的是颓废,阴影,梦幻,仙乡。他诗中的色彩感是丰富的。”①朱自清:《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8页。所谓“拜伦式”“雨果式”,实际上指诗歌的感伤倾向,对应了新浪漫主义向内转的美学追求:“同是神秘,旧罗曼主义底神秘,只是从梦幻中酿出的,新罗曼主义底神秘,是从痛切的怀疑思想出发而更进一步的。”②升曙梦:《现代文学十二讲》,汪馥泉译,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版,第248—249页。
穆木天的人生道路在“九一八”事件前后发生巨大转变,他加入“左联”,并与杨骚、蒲风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诗歌创作彻底偏向现实主义。他在回顾艺术观念与人生信念的关系时这样说:“象征主义的手法,我们是可以相当地应用的,但我们不能作一个颓废的象征主义者。而到象征主义中去寻蔷薇美酒之陶醉,去找伽蓝钟声之怀乡病,则是大不可以的。”③穆木天:《我主张多学习》,郑振铎、傅东华编:《我与文学》,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319页。事实上,创造社同仁基本上都经历了类似的告别,革命时代的价值追求必然导致同过去生活与艺术方式的断然决裂。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因日本全面侵华而导致民族危机空前激化,文学的艺术探索让位于救亡图存课题,体现出新浪漫主义内涵的颓废主义、象征主义文学在大众启蒙话语中逐渐走向没落,意味着新浪漫主义中国旅行的终结。类似新诗“诗质”缺失的困境,成为更年轻的后来者所直面的问题。
结 论
从历史的“后见之明”审视新浪漫主义的译介和传播,它在早期新文学尤其是新诗的发展脉络中并没有起到落地生根的效果,因为作为文学出路之一的方案探讨主要仅限于观念层面,但客观地说,新浪漫主义的译介凝聚了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向世界文学寻找新参照的诸种因素,内在地响应了新文学进一步完善自身的历史诉求。新浪漫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新诗欧化讨论、象征派诗歌的互动与延展看似偶然,其实说明理论旅行有其必然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而它未能成为有效解决新诗“诗质”缺失的方案,说明民族文化与时间层面的落差,构成了域外资源及其诗学经验本土化的根本性困难。
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始终困扰中国作家的问题是如何与世界对话,这样一种冲动其实还是由民族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弱势处境造成的认同困境,并且自然延伸为文化/文学的自信问题,后果之一就是中国文学不断面临追随世界文学潮流的焦虑,不少文学理论的译介就在此背景下发生,但最终因为无法找到契合中国诗学传统、让文学呼应现实的途径而昙花一现。不能忽视部分新浪漫主义诗学观念在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和纯诗写作中的继承与发展,然而更重要的问题还是如何立足于民族文化与美学土壤,开拓既契合时代变革潮流又能丰富文学自身的诗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