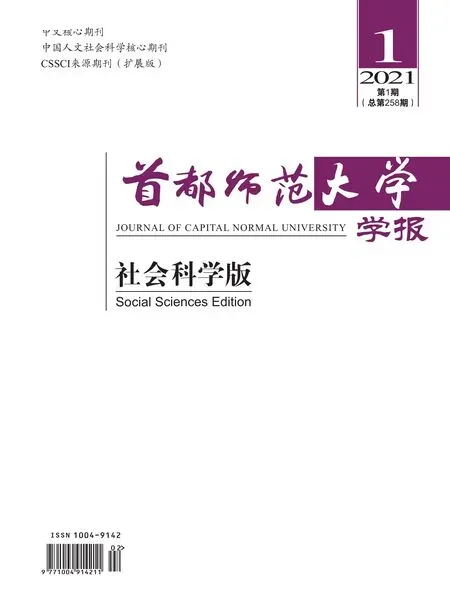互文叙事与被解构的“作者”
——《纽约三部曲》中的互文叙事研究
王立新 王跃博
一、《纽约三部曲》的互文叙事
作为一位久负盛名的美国当代作家,保罗·奥斯特一直以其对后现代都市人主体性问题的深刻洞察著称。学界对其代表作《纽约三部曲》(TheNewYorkTrilogy)的研究可分为三部分:1.叙事分析:多以文本中的反侦探叙事、不稳定叙事、迷宫叙事等文本特质为视点进行分析,如马德琳将作者身份失效的主题与《纽约三部曲》中所呈现出的反侦探叙事相联系①Madeleine Sorapure,The Detective and the Author:City ofGlass,in Dennis Barone(eds.),Beyond the Red Notebook:Essays on Paul Auster,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5,p.71.;2.形而上学阐释:多以法国当代哲学家的理论为工具对奥斯特的文本进行阐释,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命题,如尼克尔认为《纽约三部曲》是将《文学空间》(TheSpaceofLiterature)中布朗肖的思想具象化和戏剧化的实践②Bran Nicol,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Postmodern Fi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82.,而罗素则认为《纽约三部曲》和德里达一样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文本中侦探所寻找的其实是“存在”③Alison Russell,Deconstructing The New York Trilogy:Paul Auster′s Anti-Detective Fiction,in Harold Bloom(eds.)Paul Auster,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4,p.98.;3.话语阐释:此类研究多将文本置于某种当代理论体系或话语体系中进行综合性的阐释,如马丁研究其后现代性的《保罗·奥斯特的后现代性》(PaulAuster′sPostmodernity),布朗以空间理论为视角的《保罗·奥斯特》(PaulAuster)。由于奥斯特的创作中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思辨性,学者们多将其文本视为一个哲学阐释的对象,甚至默认其为一种改头换面的后现代哲学读本。但《纽约三部曲》并非一部纯粹的理论著作,它具有文学文本所独有的特质而有别于哲学文本——在《纽约三部曲》中,互文叙事(Intertextual Narrative)成了文本中最为核心的文学特质:这部作品几乎是用互文性建构而成的一部文本迷宫,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元叙事,文本夹杂和指涉着其他文本,这导致每一文本都在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中形成意涵。奥斯特非常关注人、文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正如阿里奇所说:“奥斯特的自传《穷途、墨路》佐证了他的兴趣在于世界与文字之间的关系。”①Aliki Varvogli,TheWorld that is the Book:Paul Auster’s Fiction,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1,P.2.本文认为,在《纽约三部曲》频繁的互文叙事中,保罗·奥斯特其实探讨了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他解构了传统的作者观念。
《纽约三部曲》中充满了对全书主题构成重要隐喻的互文叙事。伯恩斯坦认为,奥斯特以两种方式使用互文性:其一,使用互文性创造新的文本;其二,将互文性预设为存在与经验的决定性因素②Stephen Bernstein,The Question is the Story Itself,in Patricia Merivale and Susan Elizabeth Sweeney(eds.)Detecting Texts:The Metaphysical Detective Story from Poe to Postmodernis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9,P.135.,也即,互文性之于奥斯特首先是一种构造情节的方法,其次是一种世界观。基于此,本文认为《纽约三部曲》中的互文叙事既体现于其情节、主题、人物身份之上,也体现在其所呈现的世界观中。在情节方面,《纽约三部曲》由《玻璃城》(CityofGlass)、《幽灵》(Ghosts)和《锁闭的房间》(TheLockedRoom)三个具有互文关系的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由一位侦探或作者主人公去探求有关另一个人身世的真相,却最终失败。在此过程中,主人公的主体性发生了异化,文本中本应揭示的真相始终悬置,却都在结尾留下一个无法正确释读的文本。在主题方面,奥斯特热衷于在作品中谈论自己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使其文本与其他文本形成互证、互涉与互文的关系,以此扩大其作品阐释和表现的空间。③奥斯特热衷于以互文性将其作品联系起来,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他的《密室中的旅行》(Travels in the Scriptonium)中的情节:主人公不断地遇到奥斯特其他小说中的人物,这些人物还不断谈起那些小说中的情节。阿里奇就认为:《纽约三部曲》无论在哲学立场、叙事策略,还是关于表达的本质、理解的危险性等问题的探讨,都与19世纪美国文学传统存在互文关系。④Aliki Varvogli,TheWorld that is the Book:Paul Auster’s Fiction,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1,p.19.在《玻璃城》中,斯蒂尔曼谈到了《圣经》中的巴别塔故事,“作家保罗·奥斯特”提到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DonQuixote),这些文本以及奥斯特对其实施的二度阐释,都与《纽约三部曲》的主题构成重要的隐喻关系;而在《幽灵》中,布莱克和布鲁每天阅读《瓦尔登湖》(Walden),他们之间的对话又围绕霍桑、梭罗和惠特曼等作家展开,这都使得《幽灵》主题的外延不断被推向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中。在人物方面,《纽约三部曲》的每位主人公都在自身的行为中与他者构成模仿和对照关系,这使得其主体性不再稳定,成了多重身份和他者的影子人。有的主人公更穿越文本的虚实界限进入其他文本,如《玻璃城》的主角奎恩和斯蒂尔曼同样出现在《锁闭的房间》中,而奎恩既在《玻璃城》中监视斯蒂尔曼,又在《锁闭的房间》中追逐范肖。以上情节、主题与人物身份的互文性,又全部统摄于互文性的世界观中:在《纽约三部曲》的世界中,词、物与意义是相互分离的,因此写作行为创造了一个与物分离的能指世界,这个能指世界不断通过“延异”(Defferance)和互文性产生新的意义、指涉新的文本,这使得无论情节、主题还是人物身份都处于互文性中。
奥斯特有意使用互文叙事去构造故事情节,使得《纽约三部曲》不断地将主题和阐释引向与其他文本的关系。戴维·洛奇认为文本互涉有时是构思和写作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⑤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当代互文性理论将文本置于一种无限繁殖的互文网络中去理解,这使得文本如克里斯蒂娃所说,成为一种“生产力”⑥Julia Kristeva,Desire in Language: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Thomas Gora,Alice Jardine,and Leon S.Roudiez(tra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36.,在文本内部各种因素和话语始终在进行对话,文本外部的诸多社会因素以及其他文本也始终在与它发生关系。于是,阅读和阐释文本成了一个追踪文际关系和文本间性的过程,意义则生成于文本与其指涉和关联的复杂互文网络之间。①Graham Allen,Intertextual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1.本文认为,整部《纽约三部曲》可以被视为一部使用互文叙事方法写成的、探讨互文性语境中“作者身份”的文本。换言之,经由对《堂吉诃德》《范肖》(Fanshawe)等文本所进行的互文叙事,奥斯特通过隐晦地探讨作者、文本与读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达致了这一目的:《玻璃城》有关文本中作者身份的生成与分裂;《幽灵》观察了写作过程中作者的状态;而《锁闭的房间》则把目光投射到写作过程完结以后,作者的消失和文本对读者的控制。
二、《堂吉诃德》与“作者虚化”
在《玻璃城》与《堂吉诃德》的互文指涉中,奥斯特解构了西方文学传统认知中的“作者”这一身份。他不仅区分了封面作者与数个虚构作者的不同表现维度,更虚化了一直以来被认为具有稳定控制作用的“作者”功能。
在《玻璃城》中,主人公丹尼尔·奎恩是一名侦探小说家,他以威廉姆·威尔逊②直接出自艾伦·坡的小说《威廉姆·威尔逊》。该作品的内容是威廉姆·威尔逊与他的影子人兼死敌之间的生死较量,整个小说透出宿命论的恐怖意味。之名撰写侦探马克思·沃克系列小说。在监视斯蒂尔曼途中,他使用沃克的侦探方法,感觉到自己正在成为虚构人物沃克——与此同时,他又在扮演“侦探保罗·奥斯特”这一被委托者。在遇到“作家保罗·奥斯特”之后,他发现后者的儿子也叫丹尼尔·奎恩。此后,奎恩的自我身份异化了,他进入小彼得·斯蒂尔曼的房间,成为了他的替身。奎恩的经历印证了被他监视的老彼得·斯蒂尔曼的说法:在现代人类社会中,词与物的关系是分裂的。斯蒂尔曼的书里写到,《圣经》中的伊甸园故事和巴别塔故事都与人类语言的堕落有关,语言从“上帝意旨的传达者”退化为“某种随心所欲的符号集合”③保罗·奥斯特:《纽约三部曲》,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那么,物、词与意义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破裂,词不再能够恰切地表象物,意义也无法在词中直接获取,如福柯所说:“文本不再是符号和真理形式的组成部分;语言不再是世界的形式之一,也不是有史以来就强加在事物上面的记号……词不再有权被当作真理的标记。语言已从存在物本身中间隐退了,以进入其透明和中立时期。”④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59页。因此,语言只是浮在物之上的一个存在,人无法通过语言直接认知物;充斥着无数词与无数物的纽约,实为一座“玻璃城”。在“玻璃城”中,人可以通过“词”一览无余地看到所有物,却无法对其产生影响——相反,词与词聚合成文本,文本与文本产生互文,它们又不断地增生更多与物无关的意义,这使得人通过语言与文本对世界的解释成了一种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那么,文本的生产过程——写作行为——就变成了一个写作主体(作者)与新的意义不断发生关系的动态过程,这些新的意义不断影响着作者的主体性。据此,萨尔门托认为奥斯特表现了一种独特的“写作宇宙生成论”:奥斯特认为人的精神活动(写作)创造了一个独立于物的区域或宇宙,这个宇宙重新将意义赋予与词相分离的物质世界,人的行为只不过是这个独立宇宙的延伸:“这幅图景描绘了写作宇宙生成论的生效过程,其真正本质其实是作者身份的想象的产物,缺少了它这个宇宙就不会存在。”⑤Clara Sarmento,Paul Auster’s“The New York Trilogy”: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an Imaginary Universe,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2002,Vol.3,No.2,p.86.因此,作者身份的意义实际上有赖于通过写作建构的能指世界,而能指世界中的人物就成了作者身份的不同形式的投射,作者身份通过虚构人物获取意义。在能指世界中,符号与意义的任意关系使得任何词与任何物都能够随意建立起联系,而任何词、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可以被随意打破——这就是奥斯特的创作中充满了偶然性和互文性的原因。按照德里达的观点:“无论在口头话语还是在文字话语的范围内,每个要素作为符号起作用没有不指涉另一个自身并非简单在场的要素。这一符号链就导致每一‘要素’(语音素或文字素)是建立在符号链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踪迹之上的。这一符号链,这一织品是只在另一文本的变化中产生出来的。”①德里达:《多重立场》,佘碧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1页。那么,能指世界中的词将只有在符号链和文本场中才能够生效,词将永远指向其他词汇。举例来说,当奎恩以威廉姆·威尔逊之名撰写马克思·沃克系列小说时,他究竟是谁呢?显然这三个名字都可以指向他的实存,又都无法完全诠释他。果不其然,随着情节发展,奎恩(Daniel Quinn)又成了“侦探保罗·奥斯特”,后来又发现自己名字的缩写D.Q和堂吉诃德(Don Quixote)一样。如此一来,奎恩的主体身份便可以无限制地与任何词对应生效,而这些词又可能随意地与任何其他词产生互文关系——这是奎恩主体性异化的根本原因。从这一点来说,奥斯特的创作的确体现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与物之间关系的判断:“如果把‘意义’这个词用来表示与这个词相对应的东西,那就是把它用错了。就是把名称的意义同名称的承担者混为一谈了。”②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0页。这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即作者身份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在传统文论和认识论中,“作者”往往被认为是那个控制文本内容和意义的人,甚至如韦恩·布思所说,作者对文本和读者的干预和控制无处不在。③参见韦恩·布思《小说修辞学》第一章,华明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作者被认为是具有最终控制权力的主体,而文本及读者则是被控制的客体。在英语中,author一词的意思是“作者”,然而与author同属一个词根的则是authentic(真实的)和authority(权威)。很显然,作者往往被认为对文本和事件具有权威解释权,也与真实性相关。早在古希腊时期,史诗作者如荷马,就被认为具有通神的能力,其创作源于一种“神感”④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页。。福柯认为“作者”是一种话语控制,具有其功能性作用:“作者的名字不只是一个词类成分。它的存在是功能性的,因为它用作一种分类的方式。一个名字可以把许多文本聚焦在一起,从而把它们与其他文本区分开来。一个名字还在文本中间确立不同的形式关系。”⑤Michel Foucault,What Is an Author?,in Paul Rabinow(eds.)The Foucault Reader,New York:Pantheon Books,p.107.不仅如此,萨特甚至明确指出散文作家就是介入作家,散文写作就是一种作者介入世界的行为:“我每多说一个词,我就更进一步介入世界,同时我也进一步从这个世界冒出来,因为我超越它,趋向未来”,因此语言文字只是“装了子弹的手枪”,“说话就是开枪”。⑥让-保罗·萨特:《什么是文学?》,施康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页。这些,不仅是一种“作者中心论”的表述,而且是一种“作者控制权力”的表述,即作者身份对文本和读者具有稳定和确定的控制权力。但是,正如奥斯特于1992年接受的那场访谈中所说,一本书封面上的作者,和埋藏于字里行间的作者恐怕根本不是同一个人。⑦Larry McCaffery,Sinda Gregory and Paul Auster,An Interview with Paul Auster,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92,Vol.33,p.14.关于这一观点的复杂表述,隐藏于“作家保罗·奥斯特”对《堂吉诃德》的互文叙事中。
在《玻璃城》中,失去斯蒂尔曼踪迹的奎恩找到了“作家保罗·奥斯特”,后者给他讲了自己最近正在撰写的有关《堂吉诃德》的评论文章:作者塞万提斯在第一部第九章中宣称全书的作者是希德·阿迈特·贝嫩赫里,而非塞万提斯,奥斯特则认为这个希德其实是书中的四个人物:学士、理发师、神父和桑丘,这四个人各司其职。全书的缘起,只不过是堂吉诃德本人装疯做出的一个圈套,利用了以上的几个人以及塞万提斯本人。也即,塞万提斯不过是《堂吉诃德》的封面作者,而这四个虚构的人物才是全书隐含的真正作者。塞万提斯虽然作为图书封面上具有现实合法性的作者,然而实际上他只不过起到了转述和遭遇《堂吉诃德》文本的作用,而书中的虚构人物,疯癫的堂吉诃德才是控制着整个书写行为的人。与此相关,塞万提斯在第一部第一章中以一位真实的作者身份出现,神甫还宣称认识他⑧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下),张广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这使得塞万提斯作为现实作者的身份被虚构化,文本中的虚构与现实的关系被颠覆——这与堂吉诃德无法区分骑士小说文本中的虚构与现实具有同质性。在1987年的一次访谈中,奥斯特直陈《玻璃城》的主题和故事直接喻指《堂吉诃德》。①Joseph Mallia,Interview with Paul Auster,in James M.Hutchisson (eds.)Conversationswith Paul Auster,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13,p.9.将以上“作家保罗·奥斯特”的解读与《玻璃城》做互文分析,不难发现:封面作者保罗·奥斯特同样以一位虚构的作家身份出现于《玻璃城》的情节中,这使得他作为现实中的作者身份虚化,既写作文本也进入文本的能指世界;而在能指世界中,《玻璃城》的真正作者则是奎恩、“作家保罗·奥斯特”、无名转述者(这个转述者对文本的处理非常可疑)以及彼得·斯蒂尔曼等几个虚构人物,这些人物实际上都可以被看作奥斯特的“作者身份”在能指世界中不同形式的投射,他们共同承担起真实作者的身份。可见,奥斯特对《玻璃城》中的作者身份所进行的虚化处理,完全是对照《堂吉诃德》进行的。
奥斯特并非单纯地引用《堂吉诃德》,而是使用互文叙事将其纳入自己的叙事空间中,对其进行重新阐释,并通过重新阐释使其获得与《玻璃城》在主题上的文本互证与对话。借此对《堂吉诃德》的互文叙事,奥斯特将长期以来起到控制作用的、稳定的作者身份解构成了几个非常不稳定的、无法独自起作用的虚构身份。很显然,奥斯特并未止步于罗兰·巴特等人所宣称的“作者已死”,更不承认作者身份对文本和读者有着如韦恩·布思等人的叙事学理论所宣称的控制功能;相反,奥斯特认为作者一旦进入书写这个行为之中,就会逐渐掏空自己原来的身份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自己所书写的文本和人物所控制,作者自身则化身成了其他身份潜入自己的文本中。以《玻璃城》来说,偶然性与互文性共同促生了作者和人物身份的不稳定性,那么奎恩就既能成为威廉姆·威尔逊、马克思·沃克、堂吉诃德,也能成为“保罗·奥斯特”,那么任何虚构的人物都能成为作者;因此封面作者保罗·奥斯特自然也能够变换身份,潜入文本书写的空间中成为某个虚构人物。而在《幽灵》中,奥斯特甚至直接借布莱克之口说出:“我们总是谈起试图探索一个作家的内在之物,从而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可是你真要这么做,你会发现那里面并没有很多内容——至少不比你看到的任何一个普通人更多。”②保罗·奥斯特:《纽约三部曲》,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尤其需要予以澄清的,是奥斯特的作者观念与韦恩·布思等叙事学学者关于“隐含作者”的阐述。布思认为作者在写作时会创造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这个“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不同,在每一部作品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③韦恩·布思:《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66-67页。很显然,布思的“隐含作者”其实是一种叙事身份,也就是作者在书写时会自动形成的介于真实作者和文本之间的作者形象,可以说作者通过“隐含作者”完成对文本的控制。正如申丹教授所说:“隐含作者”“并不是写作文本的人创造了另一个实体,而是指此人以特定的方式来写作”。④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因此,“隐含作者”并非对作者功能的解构,相反却是使稳定的作者控制权力得以实现的叙事工具,这与奥斯特的作者观念南辕北辙。拉文德使用叙事学学者查特曼的“隐含作者”图式进行分析后,发现《玻璃城》的作者图式相当复杂:
奥斯特0—奥斯特1—奎恩—威尔逊—沃克—奥斯特2—“我”⑤William Lavender&Paul Auster,The Novel of Critical Engagement:Paul Auster′s“City of Glass”,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34,No.2,pp.223-224.
因此,他认为《玻璃城》其实正是对这种叙事学作者理论进行的一场戏仿。从这一点来说,本文并不认同齐尔科斯基所谓“奥斯特通过小说来彰显自己的作者地位”⑥John Zilcosky,The Revenge of the Author,in Harold Bloom(eds.)Paul Auster.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4,p.65.的观点。
三、《范肖》与“作者死亡”
在《锁闭的房间》结尾处,无名叙述者声称《纽约三部曲》是同一回事的不同阶段。在结构、主题和情节等方面,《锁闭的房间》始终与霍桑的《范肖》构成互文叙事,在这种互文性中奥斯特宣判了书写行为完成后作者的死亡。
在1987年的访谈中,奥斯特指出“范肖”对霍桑的处女作《范肖》有直接指涉关系,还特别谈到霍桑与《范肖》之间的特殊关系:年轻的霍桑在出版《范肖》之后不久,希望将其全部销毁。①Joseph Mallia,Interview with Paul Auster,in James M.Hutchisson(eds.)Conversations with Paul Auster,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13,p.10.而在《巴黎评论》的一次访谈中,奥斯特直陈对霍桑的钟爱:“在所有过去的作家里,他(霍桑)是我感觉最接近的一个,他最深刻地对我讲话。”②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I》,黄昱宁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页。《范肖》的内容是两名知识分子争夺一位女士的芳心,其中也有些勾心斗角的角逐,结局则是范肖出于自身的意愿放弃了爱情。显而易见,在情节上,《锁闭的房间》与霍桑的《范肖》构成互文关系,沿用了其双男主对决、男主主动放弃爱情的模式。然而,《锁闭的房间》对《范肖》的互文叙事又并不止于情节。泰里曾指出,《范肖》在出版时并非匿名,而是一本完全没有作者的作品,只有“范肖”一个标题。在某种程度上,范肖成了霍桑本人在文本中的化身。因此,《范肖》是一个作者不在场的文本,但作者却想将其全部销毁。泰里认为:霍桑躲在虚构的范肖身后并拒绝承认其存在;奥斯特的范肖则躲在叙事者身后,远距离控制着叙述者并通过他创造一个公共文学身份。③J.M.Tyree,Fanshawe′s Ghost,New England Review,2003,Vol.24,No.3,p.78,p.83.泰里的这段分析也许不尽完美,但为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奥斯特在互文叙事中有意使用《范肖》的目的在于这个文本与作者霍桑的关系,即作者的不在场和未知状态,以及他与自己所创作的文本之间复杂的关系。
在《锁闭的房间》中,无名叙述者“我”是一位文学评论家,而范肖是一位小说家。一直以来范肖对“我”施加一种不在场的控制,“我”感到“范肖一直在那里”。之后,“我”成了范肖的替代品,不仅读者误以为“我”就是范肖,范肖太太也在和“我”的性行为中将“我”当作范肖进行报复。范肖这种不在场的控制,当“我”在巴黎被人误认为范肖时达至顶点,“我”的自我身份异化,意识到任何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本质都是偶然性和互文性。但奇怪的是:从始至终,范肖始终不在场、不可知、无法触及,一直到故事的结尾。对“我”来说,范肖始终是一个无法解读的谜题,一个无法阐释的文本。皮科克认为“锁闭的房间”其实“不仅仅是作者的头脑;同时也是范肖秘密的核心,更是每个人都希望隐藏的神秘中心”④James Peacock,Understanding Paul Auster,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10,p.74.。然而,这只是小说的表层内涵。如果引入泰里对霍桑和奥斯特文本的互文性分析,那么奥斯特在《锁闭的房间》中想要处理的其实正是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范肖在完成自己的写作后离开,暗指一位作者在完成写作行为以后就退场了,或者说“死亡”了,与其文本彻底割裂——这与《范肖》文本中缺失的作者霍桑相一致。在这之后,作者是完全消失的,他无法对自己的作品或文本构成影响,而作品则如前文所述,成了一个独立的能指世界;在写作行为完成以后,作为作者身份的范肖就已经死亡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结尾处范肖严禁“我”叫他“范肖”。这种作者身份缺失的处理,暗合了布朗肖的观点:“任何一个已完成作品的人都不可能生活在、停留在作品旁边。作品就是决定本身,它把作家打发走,把他删除,把作家变成劫后余生者,变成百般无聊、无所事事者,变成无生气的、艺术并不依赖的人。”⑤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页。
而“我”作为一位评论家,一直在尝试通过文本解读作者范肖的秘密,暗喻读者或评论家企图通过阐释行为理解作者和文本的真相。但是,在小说结尾处出现的“锁闭的房间”作为一个喻体,实际上否认了读者对文本进行有效阐释的可能性。从“我”与范肖在锁闭的房间内外的对话可以看出,在作者死亡以后,读者只能在“锁闭的房间”之外打转。借此,奥斯特不仅如上文所述消解掉了作者作为控制权力的权威性,他同时也消解掉了读者和批评家企图对文本施加的诸多阐释的暴力。因此,奥斯特对作者完成书写行为后的死亡宣判与罗兰·巴特著名的“作者已死”理论并不一致。巴特宣称:“为使写作有其未来,就必须把写作的神话翻倒过来: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①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301页。他认为作者的死亡其实是将作品的控制权和阐释空间让位给了读者和批评家,这使得“关闭的写作”被不断地编织进新的意义,拒绝“秘密”。而奥斯特恰恰是保守秘密,他拒绝承认读者通过阐释获取真相的可能性。
我国学者李玉平将当代互文性理论区分为意识形态路径和诗学路径两种②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页。。从其意识形态路径来说,本文认为当代互文性理论至少具有三种理论向度:1.以德里达的“延异”观念为代表,试图确定符号与意义之间、符号与符号之间、符号与物之间的不确定性和任意性,这使得文本成了一个人与意义不断错失的场所;2.以克里斯蒂娃为代表,旨在改变看待文本的传统方式,将文本置于历史、社会、心理和符号意义的交汇中心重新审视,使得文本成为不断与某个更大的话语场进行交流、互通的意义生成体;3.以巴特的“作者已死”理论为核心,他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而所有的互文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不断增生的、人可以随意进入的互文网络(能指世界),因此并没有单纯的文本,只有无限的互文——作者也就不再是传统认为的意义生产者,他的传统作者功能失效了,文本反而是由社会中诸多话语的互文本生成的。毫无疑问,这三种趋向都在试图弱化作者对文本的控制权力,而将文本视为一个不断膨胀的、人无法完全控制的能指世界,这使得人、文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庞大而复杂的互文网络面前,人(作者)的主体性失效了。在《纽约三部曲》中,奥斯特的创作不仅涉及了以上当代互文性理论的趋向,更以其互文叙事对作者权力的失效做出了独特的回应:通过对《堂吉诃德》进行的二度阐释和互文叙事,奥斯特将书写行为中的作者身份做虚化处理,使其对文本的控制功能失效,成为被互文性符号“延异”而成的多重身份;作者身份又进而与他者、其他文本产生互相观照和对话的张力;最后,通过对《范肖》进行的互文叙事,奥斯特描述了书写行为完成后作者身份的退场,文本成为具有控制力的、封闭的能指世界——其封闭性既体现于作者对解释的拒绝,更体现于读者不可能通过文本抵达作者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