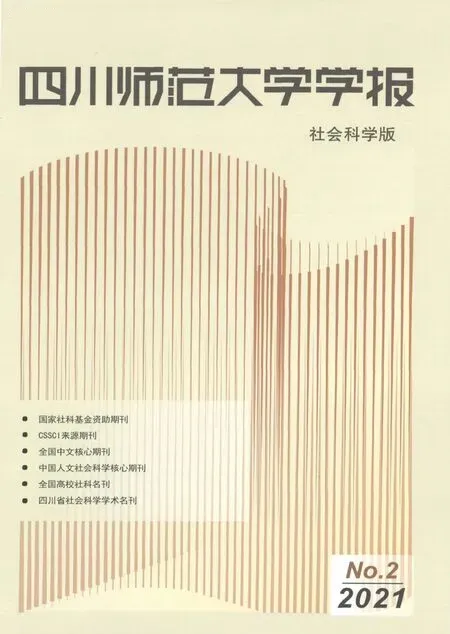礼乐制度与楚汉辞赋的演变
安生 许结
论楚汉辞赋之相承与相异者甚多,相承者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言“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页。,后世传说,已然定论;而辨异者却言说纷纭,其中清人刘熙载《艺概·赋概》直以“楚辞,赋之《乐》;汉赋,赋之《礼》。历代赋体,只须本此辨之”言“楚辞、汉赋之别”(2)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37页。。何谓“赋乐”与“赋礼”?今人论赋,似有未发覆之义。
考其义源,第一层思考首先是文体宗经观的确立。《礼》《乐》为经,《乐》又通《诗》,汉人称赋为“古诗之流”,尔后刘勰“始以各体分配诸经,指为源流所自”(3)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46页。,如《文心雕龙·宗经》“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2-23页。,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更是开宗明义:“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5)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7页。由于早期的文学文本如诗、楚辞、赋沿着“《诗》-楚辞-诸诗体”与“《诗》-楚辞-诸赋体”两种差异化的隆替轨迹流衍,其经源、经辨批评构成某种独特样态,凸显于以《乐》《礼》别画骚、赋的现象。例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灵均唱《骚》,始广声貌”(6)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34页。,胡致堂《向芗林酒编集后序》“《离骚》者,变风变雅之音,怨而迫、哀而伤者也。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则异”(7)王应麟著、翁元圻辑注、孙海通点校《困学纪闻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112页。,袁栋《诗赋仿六经》“诗赋等文事略仿六经……诗余温柔敦厚似《诗》,赋体恭俭庄敬似《礼》”(8)袁栋《书隐丛说》,《续修四库全书》第113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45页。,甚或以“礼法”为赋体立“格”,即如陆葇《历朝赋格·凡例》:“《礼》云:‘言有物而行有格。’格,法也。前人创之以为体,后人循之以为式。”(9)陆葇评选《历朝赋格》,《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74页。因为落实到文体,这又引出另一层思考,就是“赋乐”与“赋礼”与礼乐制度的关联。明人胡应麟就骚、赋二体的风貌加以判别,但礼、乐批评的因子却隐寓其间,如《诗薮》谓“骚与赋句语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同。骚复杂无伦(情感),赋整蔚有序(秩序);骚以含蓄深婉为尚(尚情),赋以夸张宏钜为工(尚辞)”(10)胡应麟《诗薮》,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6页。。《礼记·乐记》云:“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11)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87-1009页。如果绾合《礼记·乐记》此处阐释礼乐教义与政治功用的区别,缘此反观楚骚于“乐”与汉赋于“礼”的制度化特征,并从礼乐政治的离合衰振而于六义溯源流别中深觇骚赋之体变的理路,或能为重新省察楚汉辞赋的演变提供新的启思。
可以说,文体宗经是辞赋与礼乐关联的学术背景,而礼乐制度的变迁对辞赋创作的影响,以及呈现于文本书写的异同,才是深入探究这一问题的重要视点。
一 礼崩乐坏与楚辞赋乐
在辞赋批评史上,唐代出现了一股强烈的以“诗教”否定“辞赋”的思潮。这在初唐王勃到中唐古文家笔下常见,如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云:“诗不作,则王泽竭矣。至于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国之音也。至于西汉,扬、马以降,置其盛明之代,而习亡国之音,所失岂不大哉?”(12)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54页。其说虽然偏激,然“亡国之音”之于古代王朝“制礼作乐”的开平世道而言,却对楚辞的“赋乐”不无以反彰正的启迪意义。
考楚人立国,既以“蛮夷”自居,彰显武功,又致力于摆脱文化上的“蛮夷”烙印,强调文治,所谓共王勋业:“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13)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02页。,已隐然折射出楚国文化的糅合肌质。近年《性自命出》《缁衣》《孔子诗论》《采风曲目》等简牍文字的出土,儒家“六艺”文献在楚地均有所见(14)杨华《楚礼研究刍议》,《华中国学》2014年第1期,第62-70页。。而秦末被目之“瓦合適(谪)戍”的楚人陈胜、吴广,竟能吸引一代儒嗣正脉愿持孔氏礼器往投,即《史记·儒林列传》所载“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1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16页。,恐非偶然。由此考察楚辞与礼乐的关联,主要落实在两个层面。
一是礼崩乐坏下的楚乐糅合肌质。礼乐崩坏致使“王官失业,雅颂相错”(16)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42页。,乐官抱器往奔诸侯,如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等(17)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30页。,《通典·乐典》“历代沿革条”载:“周道始衰,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乐官师瞽,抱其器而奔散于诸侯,益坏缺矣。”(18)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92页。从政教经义的角度看楚乐的糅合,实际内含渎用专制之乐的“僭乐”与杂陈各地俗乐的“淫乐”。前者如混用军、燕之乐,《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楚厉王有警鼓,与百姓为戒。饮酒醉,过而击,民大惊。使人止之……居数月,有警,击鼓而民不赴。”(19)王先慎撰、锺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87页。邵伦评曰:“楚厉王以军鼓为酒鼓,可谓渎乐矣。”(20)董说《七国考·楚音乐》,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35页。再如送别之乐配入祭祀之乐,《淮南子·泰族训》载:“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瞋目裂眦,发植穿冠。因以此声为乐而入宗庙。”(21)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25页。后者已杂陈吴歈、蔡讴、郑卫之音,如《楚辞·招魂》有云:“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宫庭震惊,发《激楚》些。吴歈蔡讴,奏大吕些。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放敶组缨,班其相纷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激楚》之结,独秀先些。”(22)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9-211页。《采菱》《涉江》《扬荷》《激楚》等楚地歌乐,与郑卫淫声等新乐潜合默契,较周代雅乐迥异。胡文英《屈骚指掌·凡例》云“屈骚之音,楚音也”(23)胡文英《屈骚指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楚音尚悲,以清激(急)凄怨称闻,又与雅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声乐相悖。王逸注楚曲《劳商》“劳,绞也。以楚声绞商音,为之清激也”(24)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221页。,扬雄《方言》释“茕、激,清也。……清、蹑,急也”(25)钱绎撰集,李发瞬、黄建中点校《方言笺疏》,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19-420页。。又,《宋书·乐志》谓清商曲调:“务在噍危,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典正,崇长烦淫。”(26)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53页。其楚乐与清商乐的渊系甚密(27)按:《乐府诗集》卷二十六引《唐书·乐志》将楚调及其由此变化而来的侧调,与平调、清调、瑟调“总谓之相和调”,卷四十四又引《魏书·乐志》而谓“《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见: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6、638页。,也可证楚乐的糅合肌质。而在这种肌质中,既有乐曲杂错,也有乐教思想的渐滋暗长。
二是楚地“因情制礼”的礼乐思想。品读楚化了的战国楚简《性自命出》(28)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181页。,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楚地的礼乐观念,与周礼尊奉“以礼节情”的象德论异趣,彰显了楚乐中崇尚“因情制礼”的至情论:“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后之舍则义道也”,“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29)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179、181页。。第论楚化之义,略有三端:一者出于对教化之“性”的反正以及对天赋之性的呵护,所言“道”“情”“性”关系亦与儒家思想不侔:“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30)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179页。;一者出于对声、乐作用人心之力量的速效认知:“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以乐之速也”(31)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180页。;一者“至乐必悲,皆至其情”的尚悲观念实乃出自楚音声悲的文化土壤,陆长庚将楚人善怨归于天性,《重锓楚辞序》谓:“大夫之《离骚》,自怨生也。喟然惨怛,怨而不怒。嗟嗟,楚人之善怨,其天性哉!”(32)崔富章编著《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可以说,“因情制礼”的表述彻底颠覆了“以礼节情”的政教逻辑基础。由此来看《汉书·艺文志》言屈赋所由作,知其兴于“聘问礼废”之际,然仍具“古诗之义”,则可于中窥探楚地乐论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复杂渊系。
楚辞就其乐属,虽不能一一确指乐章之名,但因赋文卒篇往往系之以歌,如“乱曰”“重曰”“少歌曰”“倡曰”之类,可于“词未申发其意为‘倡’;独倡无和,总篇终为‘乱’”(33)沈德潜著、霍松林校注《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故被定为“古乐章之流”(34)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第469页。。先秦楚歌如《沧浪歌》《越人歌》与《九歌》等皆合乐可歌;《离骚》《九章》《天问》等在楚地民歌基础上扩衍发展,亦有“离骚”与“劳商”旁纽通转,两者乃异名一物,为楚曲说(35)游国恩《楚辞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24页。;有《九章》亦为武功之乐名说(36)周拱辰《离骚拾细》,《丛书集成》(三编)第35册,第738页。按:刘永济《屈赋通笺》亦承其说。。纵或不再配以管弦,至少仍是讲求节奏乐律的徒歌韵语。就其内容,则莫不以情实为本而悲怨哀思系之,如陆时雍以句例论楚骚“三情”之旨:“‘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此情语也;‘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此情境也;‘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此情事也。”(37)陆时雍《楚辞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8页。楚骚反复陈情,其情实(38)唐枢《叙》曰:“言者心之声也,言之发而可歌者,则谓之辞。屈子心乎公室,以忠见废,其抑郁无聊、怨慕不平之意无所于泄,而假辞焉发之,犹之穷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盖有出于情实。”见:朱熹撰、蒋立甫校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306页。,故“字字性灵,言言心极”(39)黄姬水《楚辞协韵叙》,屠本畯《楚骚协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72页。,其《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被推誉为“千古情语之祖”(40)王世贞著,陆洁栋、周明初批注《艺苑卮言》,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其音“噭咷”,故发辞悲怨急切,诚乃楚乐崇情尚悲思想的实践者。是故《文选》独标“骚”体以彰其功,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与曹植《洛神赋》,皆因缘情而被置入“情”赋类。
弥纶以上诸面,重审班固“露才扬己”“狂狷之士”(41)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49页。、刘勰“狷狭之志”“荒淫之意”(4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47页。、朱熹“语冥婚而越礼,摅怨愤而失中”“《风》、《雅》之再变矣”(43)朱熹撰、蒋立甫校点《楚辞集注》,第6页。等经式批评话语,其内在理路无不是就“以礼节情”的诗义观来衡裁“因情制礼”的楚辞创作。由于汉以后人多持经义批评,《诗》“志”成为对待楚辞续作的一个重要标尺,黄伯思痛慨近世拟楚之作“失其指”,《新校楚辞序》云:“屈、宋之文与后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陈说之以为唯屈原所著则谓之《离骚》,后人效而继之,则曰《楚辞》,非也。……自汉以还,去古未远,犹有先贤风概,而近世文士但赋其体,韵其语,言杂燕、粤,事兼夷、夏,而亦谓之《楚辞》,失其指矣。”(44)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06页。晁补之《续楚辞序》亦言:“后世奈何独窃取其辞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类而无愧。而续楚辞、变离骚,亦奈何徒以其辞之似而取之。”(45)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景上海涵芬楼藏明刊本,第1030册。其论皆在诗志,而不及楚乐。回到“楚辞”定谓,黄伯思的“纪楚”说与陆时雍的楚人、楚情、楚音之“三楚”说皆中肯綮,《楚辞条例》:“自屈原感愤陈情,而沅、湘之音,创为特体。其人楚,其情楚,而其音复楚,谓之《楚辞》。”(46)陆时雍《楚辞疏》,第372页。故后世拟骚诸作唯淮南小山《招隐士》,节短音长,迥出常格,独入《文选》,而得“古今莫迨”(47)胡应麟《诗薮》,第4页。的“真骚”(48)乔亿《剑溪说诗》:“汉之骚皆赋也,惟淮南小山《招隐士》,节短而音长,迥出常格,乃真骚也。”见: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6页。崇誉。
二 礼乐争辉与汉赋赋礼
辞赋发展至汉,隐然有二分之势,一是向以楚声为乐基的汉乐府等后起诸诗体演变,一是向“关系国家制作”(49)于光华辑《重订文选集评》引何焯《两都赋》评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的汉大赋等后起诸赋体演变。这与武帝朝重稽姬周典制以建构汉家制度直接相关。《汉书·礼乐志》因史论文,已申明其义:
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50)班固《汉书》,第1045页。
倘从汉代礼乐制度层面,探究汉代辞赋的历史演变,其要有三。
其一,乐府制度下歌诗与汉赋的渐趋分离。近人谢无量认为:“汉之灭秦,凭故楚之壮气;文学所肇,则亦楚音是先。《大风》之歌、《安世》之乐,不可谓非汉代兴国文学之根本也。”(51)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三,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2页。意指楚音对汉代文学尤其是汉乐府的奠基作用,高祖刘邦所制《大风歌》《房中乐》(后改称《安世乐》)十七章、《鸿鹄》等乐歌皆在相当程度上袭用先秦楚歌形式,并纯用楚声乐曲,被定性为“乐府楚声”(52)许学夷《诗源辨体》,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册,第6089页。。到汉武帝朝,扩大乐府规模,定立乐府制歌、采诗制度,作为汉天子郊庙礼的重要表现形式,司马相如等奉制的《郊祀歌》十九章,基本上保留了楚骚的风貌。郝敬《艺圃伧谈》认为“汉《郊祀》等歌,大抵仿楚辞《九歌》而变其体”(53)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6册,第5922页。,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亦云:“汉《郊祀词》幽音峻旨,典奥绝伦,体裁实本《离骚》。”(54)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952页。刘勰《文心雕龙·乐府》叙写史事,以为“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范文澜注“骚体制歌”引陈伯弢语“朱马或疑为司马之误,非是。按朱或是朱买臣。《汉书》本传言买臣疾歌讴道中,后召见,言《楚辞》,帝甚说之。又《艺文志》有买臣赋三篇,盖亦有歌诗,志不详耳”,作评云:“谨案师说极精。买臣善言《楚辞》,彦和谓以骚体制歌,必有所见而云然。”(5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01、108页。将其与《汉志》对读,应该是整体上指向乐府歌诗,且“感于哀乐”的指认亦深明乐府与楚声悲怨的乐属渊源。就“郊祀”一端,其创作也先于以扬雄“四赋”为代表的兼具游猎与郊祀性质的郊祀大赋的造作。楚声、楚辞在《乐府诗集》十二分类中的“郊庙歌辞”“相和歌辞”“琴曲歌辞”与“杂歌谣辞”里大量保留,且楚辞中的一些篇目与早期楚声乐府古题又不断孕育出后起乐府新题,成为乐府形成的基础(56)郭建勋、张伟《楚声与乐府诗》,《乐府学》第3辑,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200页。。缘此,费锡璜《汉诗总说》认为“《楚辞》尤为汉诗祖祢”(57)王夫之等撰、丁福保编《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45页。,日人青木正儿亦言:“楚声——楚歌从汉初到武帝时甚流行,……故当时的乐府不少《楚辞》底诗形的。”(58)青木正儿《中国文学发凡》,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据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所载后起诸诗体,则五言古诗“广于《离骚》”、七言古诗“既多乐府”、杂言古诗“大略与乐府歌行相似”、近体歌行“有声有词者,乐府所载诸歌是也”(歌、行、吟、辞等类“多与乐府同”)、绝句“原于乐府”等,莫不导源于楚辞、汉乐府(59)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108页。。
其二,王朝礼制下赋家身份的转变。倘以武、宣盛世为汉赋兴隆的历史坐标,则此前创作主要含括两类。一是以渊承战国楚辞体系为主的拟骚之作,如贾谊《吊屈原赋》等,属“贤人失志之赋”的嗣响,其身份职属为“行人之职”,刘师培传述《汉志》之意作论:“《汉志》所载诗赋,首列屈原,而唐勒、宋玉次之,其学皆源于古诗,虽体格与《三百篇》渐异,然屈原数人,皆长于辞令,有行人应对之才。西汉诗赋,其见于《汉志》者,如陆贾、严助之流,并以辩论见称,受命出使。是诗赋虽别为一略,不与纵横同科,而夷考作者之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职。”(60)刘师培著、舒芜点校《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7-128页。一是战国末至汉初的邦国赋,如《西京杂记》所载“梁王宾客”赋,乃战国纵横家之残梦,所以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篇》说:“纵横者,赋之本。”(61)章炳麟撰、陈平原导读《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后人虽并称“屈宋”,但考其身份从属却又有“学《诗》之士”与宫廷文学侍从的差别而旨趣各异(62)许结《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91页。,故陈第视宋玉赋为“楚辞之变体,汉赋之权舆”(63)陈第《屈宋古音考》,《丛书集成初编》第1215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47页。。到西汉盛世,行人淡退,纵横家与辞赋家同被纳入王朝建制而变换为礼职身份,汉大赋继踵诗志传统,与“大汉继周”思想称行,《汉书·礼乐志》:“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64)班固《汉书》,第1075页。落实到文学的视域,宫廷礼职赋家的群体崛起与宫廷大赋的影写礼制成为汉赋赋礼的两个重要面向。
首先,赋家献赋的礼职身份。班固《两都赋序》昭示了赋家身份与兴盛史迹: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65)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汉代赋家的身份职属,有“时时间作”的太常蓼侯与孔臧(赋二十篇)、大鸿胪冯衍等身居要职的礼官,有在汉代同属礼官的博士员如杜参等,但更多的是“日月献纳”的从属于中朝官系的郎官,其主要职能是随侍行礼,献赋待诏。黄本骥《历代职官表》记述汉代的郎官系统:“汉代有一种无职务、无官署、无员额的官名,不在正规编制之内,而直接与皇帝接近,能起相当的政治作用。这都属于郎的一类,郎是殿廷侍从的意思,其任务是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66)黄本骥《历代职官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兹以前后《汉书》明例,胪举如次。西汉东方朔“上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67)班固《汉书》,第2845页。;枚皋“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68)班固《汉书》,第2366页。;常侍郎庄怱奇赋十一篇(69)班固《汉书》,第1748页。;侍郎谢多赋十篇(70)班固《汉书》,第1751页。;司马相如奏赋,“天子以为郎”(71)班固《汉书》,第2575页。,而终拜孝文园令(亦属礼官);吾丘寿王曾“迁侍中中郎”,遭免后又“复召为郎”(72)班固《汉书》,第2794页。;郎中臣婴齐赋十篇(73)班固《汉书》,第1749页。;刘向“以父德任为辇郎”,子歆“为黄门郎”(74)班固《汉书》,第1928、1967页。;扬雄因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75)班固《汉书》,第3583页。;给事黄门郎李息赋九篇(76)班固《汉书》,第1749页。;车郎张丰赋三篇(77)班固《汉书》,第1750页。;东汉则班固“自为郎后,遂见亲近。……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78)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5页。;马融“拜为校书郎中”(79)范晔《后汉书》,第1954页。;张衡“征拜郎中”(80)范晔《后汉书》,第1897页。;李尤“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81)范晔《后汉书》,第2616页。;李胜“亦有文才,为东观郎,著赋”(82)范晔《后汉书》,第2616页。。郎官在汉代礼乐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传统延及唐宋,郎官有署,多为礼职(83)许结《汉赋与礼学》,《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1-6页。。考郎官设立之由,实与武帝的中朝官制改革相连。《汉书·严助传》载:“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庄)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84)班固《汉书》,第2775页。钱穆据此析断武帝内外廷的职别,言:“故武帝外廷所立博士,虽独尊经术,而内朝所用侍从,则尽贵辞赋。”(85)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2页。于是以汉初藩国纵横家之流的宾客与文学侍从作为中朝侍从的构成要员,就与赋家一同被纳进郎官系统而身兼献赋娱戏与敷政讽颂的双重功用。
其次,汉赋对礼仪礼事展开集中敷陈与颂赞。一是大批事关礼仪礼事的专题大赋出现,如刘向《请雨华山赋》、杜笃《祓禊赋》、李尤《平乐观赋》《辟雍赋》《东观赋》、廉品《大傩赋》、邓耽《郊祀赋》等,虽仅剩残文,却可见其规模。二是形成以隆赞“天子礼”为中心的创作体制。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子虚赋》《上林赋》)针对“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86)班固《汉书》,第2547页。的夸饰,假“亡是公”以为天子代言“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87)班固《汉书》,第2547页。,故该四海以极天子上林苑,批判诸侯畋猎僭礼越制之举;所谓“古者天子之礼,莫重于郊”(88)董仲舒著、苏舆撰、锺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14页。,周代郊祀之制,《仪礼》无文,真正记录天子郊祀之礼的作品首为西汉大赋与“郊祀之歌”,大赋体制显然更为详实,如扬雄《甘泉赋》因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作以讽(89)班固《汉书》,第3522页。,《河东赋》因“祭后土”作以劝(90)班固《汉书》,第3535页。;至京都赋起,因尊帝都明君统以彰天子威仪、帝国雄风,“朝会”“郊祀”“明堂”“藉田”“大射”“畋猎”“大傩”诸礼仪礼事广备而概举,其间穿插地理形势、宫殿建制、京都规划、文教礼仪、风俗民情等描写,构成汉大赋特定的创作典范。例如张衡《东京赋》,或谓“通篇大旨皆就‘礼’字发挥”,“特拈‘礼’字,此赋中主意”(91)赵俊玲辑《文选汇评》,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65、71页。。其言“观礼”云:
于是观礼,礼举仪具。经始勿亟,成之不日。……乃营三宫,布教颁常。……于是孟春元日,群后旁戾。百僚师师,于斯胥洎。藩国奉聘,要荒来质。具惟帝臣,献琛执贽。当觐乎殿下者,盖数万以二。……天子乃以三揖之礼礼之。穆穆焉,皇皇焉,济济焉,将将焉,信天下之壮观也。……及将祀天郊,报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为虔。肃肃之仪尽,穆穆之礼殚。然后以献精诚,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及至农祥晨正,土膏脉起。乘銮辂而驾苍龙,介驭间以剡耜。躬三推于天田,修帝籍之千亩。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文德既昭,武节是宣。三农之隙,曜威中原。岁惟仲冬,大阅西园。……尔乃卒岁大傩,殴除群厉。……于是阴阳交和,庶物时育。卜徵考祥,终然允淑。(92)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05-127页。
明堂、辟雍、灵台三宫乃永平制度之盛举,为观礼区域,赋家由营构发语,尔后行文以时间为叙,自元日至卒岁,依次分写朝会、郊祀、明堂、藉田、大射、养老、大阅、大傩、巡狩、省耕等十大典礼。每一典礼又叙及礼事,如因朝会而及询政、燕享、纳谏、招贤、庶政诸事,如郊祀一节含郊望、明堂、宗庙三事而带及车服、戎卫、乐舞、牲物等。观礼铺象以张皇大汉气象,其中蕴涵着颂帝德的思想,故观礼后归之于“德”:“是以论其迁邑易京,则同规乎殷盤,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9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27页。汉大赋对帝国礼制的模写,虽有京都、畋猎、郊祀等诸多面向,但论其指归,仍统聚于“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94)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5、8页。的大汉中心论与万邦协和思想。
其三,汉代礼乐制度下的“以礼防情”思想。配合大一统思想与“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国家政略,在汉代董仲舒建构起一整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正定名分为主要内容的名教体系。在这一体系下,董仲舒以阴阳之学进一步改造儒家的“以礼节情”,开启汉代“以礼防情”的礼乐观,如《对贤良策》云:“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95)班固《汉书》,第2515-2516页。董仲舒以情等欲,将个人的意志、价值观自觉地纳进国家统一形态中,以重整秩序、恢宏法度。尔后班固、王充等人皆有阐论,如《白虎通义》说“性情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学以治性,虑以变情”(96)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81、254页。;《论衡·本性篇》说“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答佞篇》说“君子则以礼防情,以义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则无祸”(97)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2、517页。,或“治性变情”,或“以礼防情”,思理相同。汉代到宣、成时期,针对乐府“郑声尤甚”问题,曾试图以倡扬雅颂古乐的太乐系来节制楚乐新声,但收效甚微,而最终在哀帝朝诏罢乐府。赋家献赋所体现出来的“淫声”与“雅乐”的创作思想矛盾、“欲讽反劝”与“象德缀淫”的批评冲突,又无不与汉代制礼作乐,尊奉儒家礼乐思想相关(98)许结《汉赋造作与乐制关系考论》,《文史》2005年第4辑,第25-47页。。
三 文本书写的喻乐赞礼
楚汉辞赋的“赋乐”与“赋礼”,与礼乐制度的变迁相关,然反制于文本的书写,又显现出赋写礼与乐的创作差异。刘熙载《艺概·赋概》本于赋源于诗的观念,论诗、乐、赋有云:“乐章无非诗,诗不皆乐;赋无非诗,诗不皆赋。故乐章,诗之宫商者也;赋,诗之铺张者也。”(99)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第412页。如果说“楚辞-汉乐府-诸诗体”一线以声、乐、情为体征,那么“楚辞-汉赋-诸赋体”一线就以诵、礼、辞为体征。结合前述从汉代礼乐制度的角度理解“感于哀乐”的乐府歌诗与“体物写志”的汉代辞赋的演变现象,可以说是文学在制度干预下寻觅出的契合文体自身发展的不同路径,倘以本体的创作而论,又可回归到书写的不同取径,或可谓之“喻乐”与“赞礼”。
礼乐为教,《汉书·礼乐志》将其归于“四政”,即“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并进一步探讨其功用:“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故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此礼乐之本也。”(100)班固《汉书》,第1028-1029页。其中“治内”与“修外”的区分,在楚汉辞赋的创作中,又有了超出《诗》源思想的文本的意义。由此来看从楚辞到汉赋的创作文本,又呈现出三种转变。
一是由娱神到娱人。以《九歌》为例,其颂赞的神灵有天、地、人三类,如天神有上皇(太乙)、日神(东君)、云神(云君)、司命(大司命、少司命)、风伯(飞廉)、雨神(蓱号)、日御(羲和)、月御(望舒);地神有山神(山鬼)、水神(如湘水之神湘君、湘夫人)等;人神有祝融、颛顼、高辛、轩辕、伏羲、女娲以及厉神(殇鬼)等。而在其他篇章中,如《离骚》中诸神多排列描述,均突出展示了《楚辞》文本中“神像”的聚合。其中的描写,也充满了魅惑与神奇,如《离骚》“求宓妃之所在”一段“求女”描绘,清人吴世尚《楚辞疏》视为梦境,以为“耿吾既得此中正”是入梦之始,“焉能忍与此终古”是出梦之终,以为“此千古第一写梦之极笔也”(101)游国恩《离骚纂义》,游国恩著、游宝谅编《游国恩楚辞论著集》第一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47页。。英人霍克思则认为这段“游历”,属于“宗教仪式化的旅行”,其“铺陈总是暗含着巫术指称事物的痕迹”(102)霍克思《求宓妃之所在》,尹锡康、周发祥主编《楚辞资料海外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页。。所谓“梦境”与“巫术”,都与其娱神以讥世的创作指向有关,内多歌舞之乐的涵蕴。至于“二湘”的心态刻画,以及《少司命》中的“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至兮水扬波”(103)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72-73页。的游弋、“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104)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73页。的思念,无不充斥着以“乐”以“娱”神的情愫。与之不同,汉代骋辞大赋虽然也有对神灵的书写,如《甘泉赋》写礼祀“太一”之神,但其献赋对象主要是皇帝(人),所以“娱人”(其中包括讽颂)为创作的第一要素。从文本形式来看,汉大赋多假托人物构篇,但其虚构的人物均有实际的指向,如“子虚”为“楚使臣”,“乌有”为“齐使臣”,而“亡是公”为“天子使臣”;而从文本内涵来看,又均为“天子礼”的书写,其中“礼”的规范与赞述,恰是赋家建言“天子听政”的两个方面。但赋用的切入点却是娱人,这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记述相如献赋过程及“三惊汉主”最为典型:
上读《子虚赋》而善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请为天子游猎赋……奏之天子,天子大悦。……(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105)司马迁《史记》,第3002-3063页。
汉武帝的惊、悦与飘然,关键在赋家所述的天子之事,与其“赞礼”切切相关。而对应楚辞中多“喻乐”以娱神,又导向于刘熙载《赋概》所说的骚赋的“声情”与“辞情”的区分。
二是由声情到辞术。楚辞固然以擅“辞”称名,但在文本书写间更多的是个人抒发,以声情动人,而具有内感的特征。如《离骚》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106)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12页。,刘献廷释云:“露则譬诸君子之泪,岂肯轻坠?此在其本性则然,到得时事伤心,即铁石为怀,于焉有泪矣。”(107)游国恩《离骚纂义》,第107页。此以物性喻声情。又如《云中君》“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108)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59页。,王夫之评释云:“神不可以久留,则去后之思,劳心益切……或自写其忠爱之恻悱,亦有意存焉。”(109)王夫之《楚辞通释》,《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47-248页。此以神性喻声情。王逸《九歌章句叙》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110)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55页。其云“歌乐鼓舞”与“怀忧苦毒”,也是一种典型的“声情”呈现。汉大赋书写天子礼仪,如“游猎”“郊祀”等,兼有讽、颂之义,所以往往委曲其辞,见彰文术。如其“讽”,由于赋家一方面有强烈的经世致用之心,一方面又身处言语侍从即“倡优蓄之”的境遇,所以成文多因讽谏而取譬,因取譬而多华词。班固《白虎通》陈“五谏”,首彰“讽谏”,所谓“讽谏者,智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陈立《疏证》引扬雄《甘泉赋序》“奏《甘泉赋》以讽”及《文选》李善注“不敢正言谓之讽”以显其旨(111)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235页。,深明赋家辞术之要。汉赋的“曲终奏雅”,也是一种辞术,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描写游猎盛况后旨归俭德:“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菟之获,则仁者不由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112)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378页。所指“万乘之所侈”,乃以讽谏使之“醒悟”,是曲终奏雅之法,但其“奏雅”也是赋文对“礼仪”铺写后对“礼义”的汲取,又反证“辞术”是因缘于“礼事”而施展的。由此,我们再看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比较“骚”与“赋”之阅读感受的一段话语:
《骚》览之,须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嘘唏;又三复之,涕泪俱下,情事欲绝。赋览之,初如张乐洞庭,褰帷锦官,耳目摇眩;已徐阅之,如文锦千尺,丝理秩然;歌乱甫毕,肃然敛容;掩卷之余,彷徨追赏。(113)王世贞著,陆洁栋、周明初批注《艺苑卮言》,第13页。
其中“情事欲绝”与“丝理秩然”的对比,既是楚辞与汉赋文本的差异,更是“乐”肇“声情”与“礼”成“辞术”的区别。
三是由忧政到敷政。如前所述,楚辞产生于礼乐崩坏,而汉赋倡导“大汉继周”,是对礼乐制度的归复,这亦如《汉书·艺文志》“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而贤人失志之赋作”(114)班固《汉书》,第1756页。与《两都赋序》“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故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的记述。缘此,萧统在《文选序》中说明别录“骚”为一体之意云:
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115)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页。
将“君匪从流,臣进逆耳”视为“骚人之文”成立的前提,副以“怀沙之志”与“憔悴之容”,正是其忧政的反映。而读《离骚》如“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116)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21-22页。一段描写,针对的是君王淫佚荒政,而宣泄其忧心之愤情。汉代赋家也忧心于天子淫佚荒政,但笔法更多彰显于对政教的铺写。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假托“亡是公”之口的说辞:
“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117)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361-378页。
又李尤《函谷关赋》论汉代礼德观云:
大汉承弊以建德,革厥旧而运修。准令宜以就制,因兹势以立基,盖可以诘非司邪,括执喉咽。季末荒戍,堕阙有年,天闵群黎,命我圣君,稽符皇乾,孔适河文,中兴再受,二祖同勋。永平承绪,钦明奉循,上罗三关,下列九门,会万国之玉帛,徕百蛮之贡琛。(118)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46页。
因其非个性化的“忧政”而是政教化的“敷政”,于是又可衔接《国语·周语》所言的“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119)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12页。一段话语,而构成汉赋“大汉继周”的礼德联系。甚或追溯周人有关“赋”的运用,即《诗·大雅·烝民》“明命使赋”“赋政于外”(120)朱熹集撰、赵长征点校《诗集传》,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24页。与《商颂·长发》“敷政优优,百禄是遒”(121)朱熹集撰、赵长征点校《诗集传》,第373页。诸说法,参照郑玄《烝民》诗笺“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纳王命者,时之所宜,复于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顺其意,如王口喉舌亲所言也”(122)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 968页。,汉代赋家秉持王言以叙礼,与此渊承所系。可以说,忧政之“心”喻以“乐”,铺政之“志”寄于“礼”,也是楚汉辞赋“赋乐”与“赋礼”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视点。
四 余论
汉魏代变,中原板荡,赋体文学便随之演化,从创作上看,其转变在小品化的抒情赋、咏物赋的兴盛,从理论上看,又可视作两汉献赋制度“寖坏”的结果。这一转向有两点值得申说。
其一,赋家身份由宫廷言语侍从转向文士。与两汉赋家政治献赋为主体的创作不同,魏晋以后文士自作赋的主体性情感得到张扬。如曹植《愍志赋》《离思赋》《释思赋》《洛神赋》、阮籍《首阳山赋》、向秀《思旧赋》等无不有感而作,王粲则“独自善于辞赋”(123)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02页。,张华亦“著《鹪鹩赋》以自寄”(124)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69页。,不遑备举。“缘情制礼”思想的复起与重塑,为魏晋玄学与礼学双修、同构(125)按:此一时期玄学家往往深通礼制,礼学家亦往往兼注三玄。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06-344页。,成为门阀制度的思想基石,映射出魏晋不同于两汉的新的社会文化思潮与士人行为准则。此于赋体创作,又出现两大显征。
首先,拟骚创作的回潮。建安赋家有文献可征者多达三十余家,辞赋作品百六十余篇,就数量、成就两面论,当以曹植(五十一篇)、王粲(二十五篇)二人为胜。曹植自言因“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126)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896页。,遂作《洛神赋》,丁晏《曹集铨评》评谓:“王既不用,自伤同姓见放,与屈子同悲,乃为《九愁》《九咏》《远游》等篇,以拟楚骚;又拟宋玉之辞为《洛神赋》,托之宓妃神女,寄心君王,犹屈子之志也。……为古今诗人之冠,灵均以后一人而已。”(127)曹植撰、丁晏纂《曹集铨评》,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第216页。王粲《登楼赋》则以“情真语至,使人读之堪为泪下”(128)浦铣著,何新文、路成文校证《历代赋话校证:附复小斋赋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页。的登览情怀,被推为“魏之赋极此矣”(129)祝尧《古赋辩体》,《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78页。,刘熙载《艺概·赋概》谓“建安名家之赋,气格遒上,意绪绵邈;骚人清深,此种尚延一线。后世不问意格若何,但于辞上争辩,赋与骚始异道矣。楚辞风骨高,西汉赋气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汉而复于楚辞者”(130)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第435页。,堪称的评。
其次,“象”退“兴”起的手法变移。汉大赋对帝国典礼的敷陈展现主要是通过对物象、事象的描绘来完成,体物以呈象成为赋体批评的第一要义。汉大赋的“口语”(诵)性与“玮字”法使其语言形式大量运用双声叠韵的“连绵词”及形声词、叠字等“体状”手法,且善于在“设色”原理下化静态为动态以加强语言文字所呈现物象的可视化效果(131)许结《汉赋“象体”论》,《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第167-175页。。魏晋辞赋的抒情性、小品化特征则将大赋铺陈的“象体”手法代之以诗歌的比兴手法,并与楚骚声貌符契,隐然为六朝赋的诗化导其源流。就咏物一端,魏晋咏物赋非如汉大赋“该四海而言之”而多为“一物一咏”的短篇小制,故曹植《与杨德祖书》批评陈琳仿汉赋“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词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者也”(132)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27页。。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曾详辨汉赋鸿裁与建安短制之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乃就赋类对举;“图画天地,品类群生”与“拟诸形容”“象其物宜”乃就赋法对举;“体国经野,义尚光大”与“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乃就赋貌对举;“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与“触兴致情,因变取会”乃就赋制对举。(13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35页。
其二,赋体文学出现了文体意义上的批评转向。因汉宫廷大赋的衰退,赋体“讽、颂”功用论批评随之淡退,代之而起的是魏晋赋体“体物浏亮”的本体论批评,含括着“诗”“赋”二体的辨体分途以及文士倾心于赋体“摘句”批评的丽辞性、技巧性与声律化两面。前者至曹丕《典论·论文》尚以“诗赋欲丽”并称,及陆机《文赋》则有“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之别,刘勰《文心雕龙》分设《诠赋》《明诗》二篇,就其“性质”“作用”加以阐辨(134)郭绍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0-87页。。至此基本上完成了先秦到齐梁基于因文类范畴的不断衍扩而体类,再由此勘进于体貌、体性之诗文明体理论的建构。后者如《世说新语》载孙兴公作《天台赋》以示范荣期而有“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13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7页。的群体性认知,刘勰《文心雕龙》更以互文见义的谋篇形制在《丽辞》《通变》诸篇中聚焦“丽辞”“丽句”的赋体“摘句”批评(136)许结《赋体句法论》,《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期,第165-174页。。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魏晋以抒情赋、咏物赋为主流,但仍存在部分拟大赋如《三都赋》等的创作,这类创作与汉家献赋的供悦对象在帝王不同,魏晋赋家作赋更多的是士族间的褒贬,如《三都赋》为世所重在于皇甫谧的褒举,袁宏《东征赋》中有关个人功德之表彰的故事,其脱离朝廷的个性化创作特征已然明显。由批评反观创作,魏晋赋的“赋乐”源自个性化的“诗心”,是对汉赋“赋礼”的改变,以及对楚骚情绪的承接并开辟的新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