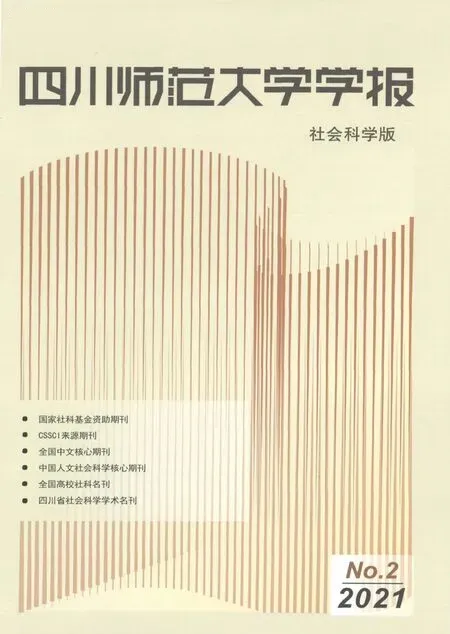康德论统觉的同一性
罗 喜
统觉的同一性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演绎”中具有核心地位,正如亨利希(D. Henrich)指出的:“康德几乎在所有表达演绎核心思想的地方都提及了自我意识的同一性这一形式特征。”(1)Dieter Henrich, “Die Identität des Subjekts in der transzendentalen Deduktion,” in Kant: Analysen-Probleme-Kritik, ed. Hariolf Oberer & Gerhard Seel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1988), 51.统觉的同一性之重要性尤其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B版演绎的第一部分和A版“自上演绎”(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的论证中。这两个论证的具体进程虽然不同,但其出发点都是统觉的同一性。那么,统觉的同一性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同一性?为什么它能够关联到范畴化综合(kategoriale Synthesis)?回答这两个问题对于理解康德的先验演绎是极为重要的。
针对以上问题,研究者们已经给出了多种解释。例如,强调自我意识的“能动作用”及其与“对象意识之间的矛盾关系”(3)邓晓芒、杨祖陶《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的解释,将范畴理解为“自我意识之自我同一性的开显方式或展现方式”(4)黄裕生《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页。的存在论解释,将统觉看作“思维的形式”(5)唐红光《康德统觉理论的两个维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2页。的解释,把统觉的自我视为“现象的思维着的自我”(6)Patricia Kitcher, “Kant’s Real Self,” in Self and Nature in Kant’s Philosophy, ed. Allen W. Woo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121.的功能主义解释,等等。在当代语言分析哲学传统中,自斯特劳森(P. F. Strawson)以来兴起了一种对康德统觉理论的“自我归属”(self-ascription)解释(7)P. F. Strawson, The Bounds of Sense: An Essa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London: Methuen, 1966), 93.。该解释认为,自我意识(统觉)根本上体现在主体把表象归于自身,即体现在不同表象的自我归属活动中。并且,由于一切表象都能被视为“我的表象”,自我就意识到了自己在不同表象中是同一个主体。“我的表象是‘我的’”这一陈述虽然在逻辑上为真,但背后却隐藏着表象自我归属的“无标准性”(criterionless)(8)P. F. Strawson, The Bounds of Sense: An Essa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164.和“能够避免误认的错误”(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9)Gareth Evans, The Varieties of Reference, ed. John McDowe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15.这两条原则。
本文认为,斯特劳森提出的自我归属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康德自我意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推进,但由于其经验主义的基本立场,斯特劳森也不可避免地将康德哲学过度经验化了。与斯特劳森诉诸经验主体和身体的做法相反,笔者立足于康德的先验哲学并试图论证统觉的同一性在表象的自我归属中是一种逻辑的同一性,而且,只有从该逻辑的同一性才能推演出范畴化先天综合的必然性。
一 表象的自我归属及其解释局限
表象(Vorstellung)作为“内心的变状”(1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14页。只能存在于认识主体中。借用当代术语,表象亦可被称之为“心灵状态”(mental state)(11)Patricia Kitcher, “Kant on Self-Identity,”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91, no.1 (January 1982): 53.。形象地说,表象就是当我们对物或事态进行设想时在脑海中所呈现出来的内在图画。从表象主义理论看,“内在表象是对外在对象的表示”(12)Ernst Tugendhat,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sprachanalytische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6), 86.。在弱意义上,表象可以是简单的知觉片段;在强意义上,它则可以是复合的认知状态。为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等级阶梯”(1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74页。中将一般表象视为种(Gattung),从属于其下的有感觉、知觉、直观、概念、理念等。
认识主体作为表象的承载者同时也是表象的拥有者。进一步说,与动物具有表象不同,自我对表象的占有具备一个自反思(self-reflexive)的层面,即自我能够把表象当作“我的表象”,从而自我在诸表象中反思到自身。或者说,由于自我把表象归于自身,自我就意识到了主体与表象之间的占有关系。假如一个主体不能把他获得的表象看作“我的”,那么该表象或许在他内心中存在并发挥某些影响,但不具有认识论的地位(14)康德在《反思录》中指出了这一点,参见: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1 (Berlin: De Gruyter, 1900), 52。。这类表象因而就只是无意识的表象。相反,包含于经验知识中的表象必须是有意识的表象,因为它们发挥着认识的功能。此类有意识的表象必须是自反思的表象,即能够被归于同一主体的表象。没有这种自反思或自我归属,任何知识就是不可能的。
康德认识到了上述主体与表象的反思关系之重要性。例如,他在B版演绎开篇就指出:“‘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因为否则的话,某种完全不可能被思考的东西就会在我里面被表象出来,而这就等于说,这表象要么就是不可能的,要么至少对于我来说就是无。”(1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89页。这表明,表象存在于主体中这一事实,还必须提升为该主体能够把表象思考为“我的”,即能够进行反思和表象的自我归属。这是认识得以发生的一个根本环节。事实上,康德在“先验演绎”的进程中也多次提及表象自我归属的核心思想。例如,他在A版演绎中写道:“因为只有通过我把一切知觉都归属于一个(本源统觉的)意识,我才能对于一切知觉说:我意识到了它们。”(1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28页。在B版演绎中,他又写道:“在任何一个给予的直观里,我的一切表象必须服从这个条件,惟有在这个条件之下我才能把这些表象作为我的表象归于同一的自己。”(1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93页。此外,他在“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中也指出:“我们只把我们所意识到的那种东西归入我们的同一的自己。”(1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321页。我们通过这些陈述可以看到,康德想要强调认识包含一个自反思的层面,即主体能够意识到不同的表象都是“我的表象”。在此,自我意识正是通过表象的自我归属而得以表现出来。然而不得不承认,康德并没有深入展开表象的自我归属理论。更确切地说,他未能揭示“我的表象是‘我的’”这个似乎极其普通的分析命题所具有的语义学内涵,也并未给这种第一人称的权威提供详细论证。在过去50年的康德研究中,以斯特劳森为代表的“分析的康德主义”侧重于从自我归属的视角来阐释康德关于自我意识的思想。
所谓“分析的康德主义”(Analytic Kantianism),是指在当代英美哲学中(尤其自斯特劳森以来)通过语言分析的方法来阐发康德哲学的一种趋势或不严格意义上的学派(19)其他典型代表人物有:Jonathan Bennett, Gareth Evans, Wilfrid Sellars, John Mcdowell, Quassim Cassam等。。与传统欧陆(尤其是德国)风格中重视文本考证、强调思想的历史发展与内在逻辑结构不同(20)如Hans Vaihinger, Eric Adicks, Dieter Henrich, Heiner F. Klemme等。,分析的风格突出具体问题、侧重给出论证并彰显语言分析在哲学问题解答中的作用。例如,分析的康德主义者在解释康德时突出强调自我归属问题,并把它与当代关于人格同一性、第一人称视角以及自我知识的讨论联系起来。下面笔者将简要说明该学派中“无标准的自我归属”(criterionless self-ascription)理论,其主要代表是斯特劳森,其追随者有埃文斯(G. Evans)和卡萨姆(Q. Cassam)。
在斯特劳森看来,“我”这个人称代词指涉一个主体,不同表象能够归属于该主体并被看作“我的表象”。在这些不同表象中,自我能够知道自己是同一个主体。但是,自我却不是一个可以交互主体地再认识的对象,因为“我”这个表达还没有用于指示一个在物理时空中的个体。所以,自我在不同表象中是同一的,但这种同一性是“无标准的”,即在不同主体间是不可通达的。这种无标准的自我归属是一个自明的事实。的确,斯特劳森的阐释将康德的自我意识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正如上面所引的那些文本已经表明的,康德的论述确实已经暗含了该阐释的可能性。在纯粹自我意识中,自我并不是一个在时空中可以反复再认的个体,但这个自我仍然能够在不同表象中保持为同一个主体。这是康德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洞见,同时也要归功于斯特劳森独具慧眼的揭示。对此,斯特劳森指出:“毫不夸张地说,康德认识到了这一真理,从而他对主体的处理远远超过了休谟。”(21)P. F. Strawson, The Bounds of Sense, 165.
斯特劳森对康德的阐释,确实推进了我们对自我问题的理解。但与此同时,他也不满足于康德的理论,作为哲学家,他想要比康德走得更远。为此,斯特劳森指责康德完全忽视了“经验主体的经验性概念”(22)P. F. Strawson, The Bounds of Sense, 169.,即人的身体也必须作为自我归属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我”这个表达在不涉及身体时完全是非指称性的,即不指示对象。在表象的自我归属中,主体的同一性要是可能的,那么不同表象所依赖的主体就必须是一个在经验中可证实的主体,所以必须诉诸人的身体。这是因为,只有通过人的身体才能区分不同的主体。也就是说,表象被归属的主体必须是“一个在世界中可以被直观到的对象”(23)P. F. Strawson, The Bounds of Sense, 106.,因而必须是“诸多有形客体中的一个客体”,即“众人中的一人”(24)P. F. Strawson, The Bounds of Sense, 102.。由此,斯特劳森将作为外感官对象的人的身体视为“主体同一性的经验上可以运用的标准”(25)P. F. Strawson, The Bounds of Sense, 106.。如果没有这个标准,没有作为经验指涉的身体,对自我同一性的意识就会是不可能的。斯特劳森认为,康德没有触及到这一点,即没有看到人的身体也理应成为判定主体同一性的一个标准,这是他哲学的缺陷。
“无标准的自我归属”后来被埃文斯批判性地发展成了“能够避免误认的错误”理论。埃文斯主张:“不理解心灵谓词的自我归属,就不能完全理解自我认同。”(26)Gareth Evans, The Varieties of Reference, 205.但是,因误认而导致的错误,只有通过物理属性或物理状态的自我归属才能得以避免,也就是说,必须诉诸定位在空间中的身体(27)Gareth Evans, The Varieties of Reference, 224.。因此,身体在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埃文斯的这种思想,显然可以看作是一种对自我意识的物理主义解释。此外,斯特劳森的学生卡萨姆在解释康德的自我同一性理论时(28)Quassim Cassam, Self and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8.,也突出强调了作为外感官对象的人的身体必须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在笔者看来,把身体作为标准纳入到康德的自我归属理论,这是对康德的过度解释。具有身体的主体,即时空中的人,是一个经验主体。把康德统觉理论中的自我解读或发展为一个这样的经验主体,这是与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构想不相容的。在此可以给出如下三个理由:第一,康德的先验自我并不是一个能够在时空中被直观到的对象,也不是一个在内感官中通过内省而能够被把握到的自我,否则,自我就完全是经验性的、偶然的和变化的,就是一个纯粹心理的产物,就不能充当认识的先验条件;第二,在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中,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在自我这里就会消失,因为先验的自我已经被当成了在经验界的现象的自我,本体的自我就完全被根除了;第三,经验自我所具有的同一性,尽管——正如斯特劳森及其追随者所希望的——可以在时空中交互主体地再认,但这远远不是康德所要求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同一性,即一个内容上空乏的自我在一切表象中无一例外地所保持的同一性。
由此推论,在康德哲学体系内,表象的自我归属理论也应当有其限度。笔者主张,对康德而言,在纯粹自我意识中,号数上同一的自我只是逻辑的主体,而不是经验实在的主体;自我同一性也必须保持为无标准的、逻辑的同一性,而不能转换成有标准的、实在的同一性。下一部分,笔者将从三个层次来论证统觉的同一性在表象的自我归属中要限定为逻辑的同一性。
二 统觉的逻辑同一性的三个层次
按照斯特劳森式的解释,不同表象被归属于的自我必定是一个实在的主体,其同一性也必定只是一种经验性的同一性。与此相反,在论及表象的自我归属时,康德所意指的是一个逻辑的自我,即在一切表象中无一例外地保持不变的非实在的主体;它是思想得以可能的逻辑条件,其同一性也只是一种逻辑的同一性,即无内容的、形式的持续性。该解释可以得到很多文本的支持: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演绎”中,康德谈到了“持存常住的自我”(2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29页。;在“谬误推理”中,他将先验自我称之为“思维的那个持久不变的逻辑主词”(3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311页。,并把自我的同一性明确地描述为“逻辑上的同一性”(3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320页。;在《实用人类学》中,他把“作为思维主体的自我(在逻辑学里)”叫作“单纯反思的自我”(32)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7, 134.;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自我被康德刻画为“统觉的普遍相关项”(33)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4, 542.;在生前未发表的《论柏林皇家科学院1791年悬赏征求答案的问题:形而上学自布莱尼茨和沃尔夫时代以来在德国取得了哪些真正进展?》中,康德把统觉的主体确切地称之为“逻辑的自我”(34)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20, 270.。这些文本证据足以表明,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体系内,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即“先验主体”(3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91页。,是一个不具有实在性的而只能在思维中被预设的逻辑的自我,其同一性也只是在概念中呈现的逻辑的同一性。
康德的纯粹自我意识或先验统觉,并不是一个在时间中发生的、当下的心理状态,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意识。其特殊性在于,这种意识不是一个真实的事态,不具有任何感觉经验的成分,不包含任何杂多内容。实际上,它就是对逻辑的自我的智性意识,或者用康德自己的语言讲,它是“一个思维主体的自动性的某种单纯智性的表象”(3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05页。。认识主体在他的不同表象中意识到他是同一个主体,这就涉及到了统觉的同一性。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这种同一性不是一种实在的同一性,而应当理解为逻辑的同一性。下面笔者将通过区分三个层次来论证这一点。
第一,从思想得以可能的逻辑条件看,思想的形成只能依赖于一个主体,即把不同表象联结成一个思想的自我。不同表象必须能够被无一例外地归属于这个号数上同一的自我。因为,不可能会在任何地方存在着一些表象,却没有一个自我;不可能会在任何地方有一个思想,却没有一个承载者。所以,毋庸置疑,不同表象要能被带到一起并联结成一个复合的思想,那么它们就必须依存于一个共同的主体(3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311页。。换句话说,这个主体在那些表象中必然要是不可分的、号数上同一的。因而,一个同一的逻辑主体是思想得以可能的逻辑要求。对此,康德指出:“统觉的我、因而在每次思维中的我是一个单数,它不能被分解为多数主体。”(3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93页。将表象自我归属的主体理解为思想的逻辑主体,该观点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个谬误推理”(3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312页。中提供了充分的论证,在此不再赘述。
第二,从反思意识的视角看,在表象的自我归属中,或者说,当自我在不同表象中意识到自己是同一个主体时,自我在执行一种反思活动,即自我意识到了自己与表象之间的占有关系,因为自我能够把它们全都称之为“我的表象”。在此,自我既是反思的主体,也是被反思到的客体;自我既是归属活动的实施者,也是表象被归属的承载者。由于在上一层次中已经表明,自我在表象的归属中是一个逻辑的主体,所以,在反思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也只是对自我的逻辑同一性的意识。表象依赖主体和主体反思到表象的归属,这仅仅涉及概念的层面,只是在进行主体与表象之间关系的逻辑分析,因而主体还并不意味着一个真实存在的实在主体。此外,康德也强调,自我的反思活动是“在一个意识中”(4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90页。进行的。与上述“在一个主体中”相比,这里又更进了一个层次。这也就意味着,主体只有在一个意识整体中才能综合不同的表象,单个表象的归属活动也必须被统一到一个意识中。康德在B版演绎中多次强调了这种在一个意识整体中对不同表象的联结(4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89、90、92、93、96页。。
第三,从逻辑语义学(logic-semantic)的角度看,主体能够从第一人称视角来描述自己的内心状态以及通过联结表象而产生的思想内容。在此,“我”作为思维者并不指涉一个实在的主体。也就是说,在表象的自我归属中,“我”这个表述的使用只具有逻辑语义学的功能,借用当代的术语,它只是一个根本指称(essential indexical),并不能像其他描述性(descriptive)概念一样指示一个具体的实在属性。“我”作为思想得以可能的逻辑条件仅仅是在思想中保持逻辑的同一性。任何思想,总是蕴含着一个思维着的自我能够把它看作“我的思想”,因为该思想就是这个自我有意识的心灵活动的产物。从而,“我”这个表达总是能够被添加到一切表象和思想之上。例如,对于任何一个思想p,它都总是蕴含了我们能说“我思考p”。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表象的自我归属只有通过第一人称代词“我”(当然也包括其宾格和所有格形式)的使用才能实现。康德自己并未从语言学的角度展开关于“我”这个表达的使用的理论,但他的一些论述已经暗示了这一点。例如他指出:“‘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4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89页。;“我思”“只是用于把一切思维作为属于意识的东西来引述”(4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88页。。此外,他也强调:“‘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代词’。”(44)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4, 542.它既不表示直观,也不表示概念,而只是“意识的单纯形式”(4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332页。。总而言之,“我”这个表述在一般思维中并不指示一个实在的同一的对象(4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93页。。
以上三个层次的分析足以表明,斯特劳森式的将身体视为同一性的判定标准的自我归属理论并不适用于康德,因为身体视角的加入会把康德意义上的先验自我变成一个经验上实在的自我。这显然是康德自己所不愿意的。相反,在康德自己的哲学体系内,先验统觉的自我是逻辑的自我,自我在一切表象和思想中所具有的只是逻辑的同一性。但是,康德自己也并不仅仅停留于此,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指出表象的自我归属或统觉的逻辑同一性要以某些先天条件为前提。
三 统觉的逻辑同一性与先天综合的规范性
假如我们遵从斯特劳森对康德自我归属学说的“发展”,即认为身体构成了判定自我同一性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康德在“先验演绎”中对先天综合的必然性所做的很多论证工作就会是多余的。因为,身体已经保证了自我的同一性可以被交互主体地再认,自我所具有的表象是否以一种先天的方式发生关联,就会是完全无所谓的。但对于康德,情况恰恰不是这样。众所周知,在B版演绎第一步中,康德的论证战略是从统觉的同一性推演出先天综合的必然性,并进一步确定这种综合就是依照范畴的综合,即范畴化的综合,从而证明范畴对于现象具有客观有效性。据此,如果笔者在上一部分的解释是对的,那么,康德提出自我归属和统觉的同一性的论证企图就可以理解为如下主张:统觉的逻辑同一性和先天综合之间具有一种条件关系,具体言之,前者只有通过后者才是可能的。笔者认为,只有将统觉的同一性理解为逻辑的同一性,我们才能从中推导出先天综合的必然性。
用康德自己的语言讲,以上观点可表述为如下核心论题:“统觉的分析的统一只有在统觉的某一种综合的统一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4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90页。在此,统觉的分析统一性是指自我在不同表象中意识到自己是同一个主体,这是由于自我能够把每一个表象都称之为“我的表象”。换言之,同一个自我处于不同心灵状态中,或者说,自我的同一性分析蕴含在每一个“我的表象”中。所以,统觉的分析统一性也可以等同于统觉的同一性(48)本文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统觉的分析统一性”“统觉的同一性”和“对自我同一性的意识”三个术语,对此的详细说明可参见:Xi Luo, Aspekte des Selbstbewusstseins bei Kant: Identitaät, Eineheit und Existenz (Stuttgart: J.B. Metzler, 2019), 103。。相应地,统觉的综合统一性也应当理解为,自我在一个意识中把所予的表象带到一起并以某种方式联结起来。因而,综合统一性根本上就在于表象被看作是在主体的一个唯一意识中相互联结着的,即它们处在一个统一整体中并具有某种秩序。对此,决定性的当然就是由内心自发地所执行的综合活动。因为根据康德的观点,表象的杂多内容虽然能通过感性而被给予,但“一般杂多的联结决不能通过感官进到我们里面来”(4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87页。。这是康德的一个重要发现:感官不能综合,表象的杂多在被给予时总是分散的,联结只能由内心主动地去完成,因而该联结也可以叫作“主体的自动性的一个行动”(5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88页。。康德非常重视这种认识过程中内心在表象之间建立起统一关系的综合活动,而且他强调,这种综合必须是有意识地进行的:“直观中被给予的杂多的统觉,它的无一例外的同一性包含诸表象的一个综合、且只有通过对这一综合的意识才有可能。”(5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90页。更进一步说,康德真正想指出的不是日常意义上表象的联想或回忆,即不是单纯主观的经验性综合,而是一种独立于经验而进行的表象的联结,即先天综合。康德认为,统觉的同一性必须建立在这种先天综合之上。也就是说,表象的自我归属或对自我同一性的意识,只有当主体意识到由他自己所执行的先天综合时才是可能的。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个主张如何能够得到论证?
在当代研究文献中,盖耶尔(P. Guyer)持一种消极态度,他认为康德并未给以上论题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盖耶尔主张,康德确信我们对于统觉的同一性具有先天知识,这是成问题的(52)Paul Guyer, Kant and the Claims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40.。因为这是基于一种混淆,即错误地合并了意识与自我意识这两个概念,且毫无根据地断言“意识就是自我意识”(53)Paul Guyer, “Kant on Apperception and ‘A Priori’ Synthesi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7, no.3 (July 1980): 210.。由此,从统觉的同一性就推不出“心灵能把秩序强加给自然”(54)Paul Guyer, “Kant on Apperception and ‘A Priori’ Synthesi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7, no.3 (July 1980): 207.的先天综合活动。盖耶尔这种悲观的解释已经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批评(55)Karl Ameriks, “Kant and Guyer on Apperception,”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65, no.2 (Summer 1983): 175-186.。与此相反,阿里森(H. E. Allison)提供了一种较为乐观的解释,他认为综合可以视作“活动本身”或“活动的产物”(56)Henry E. 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69.。假如理解为前者,则康德的论题“统觉的同一性需要对综合的意识”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并非任何时候都意识到我们自己内心的联结活动,而且康德有时也主张,想象力的综合是无意识地进行的。但假如理解为后者,康德的论题就是不成问题的。这是由于,意识到思维A表象的自我与思维B表象的自我是同一的,这“显然要求A与B在一起的意识”(57)Henry E. 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170.。与阿里森不同,笔者在此尝试提供另一种解释,即突出逻辑的同一对于先天规范性的要求。
正如上一部分的论证已经表明的,统觉的同一性是一种逻辑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在不同表象中保持不变的那个自我,仅仅是作为思想可能性条件的逻辑的自我,而并不是作为经验对象的实在的个体。这样一个抽象的自我之所以能够在不同表象中意识到自身是一个同一的主体,是因为自我按照一些普遍的、交互主体的有效的方式来联结这些表象,即自我是在有意识地进行一种按照先天规则的综合,这可称之为“受规则支配的先天综合”(rule-governed synthesis a priori)或依照范畴的综合(范畴化的综合)。正是这种对每一个认识主体都客观有效的先天规范性,才保证了自我的同样普遍有效的逻辑同一性。下面笔者将依据康德的文本进行论证。
众所周知,对所予杂多的综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在最弱的意义上,我们可以任意联结两个表象,如“飞”和“马”。在稍强的意义上,我们可以通过习惯性的联想来联结两个表象,如“睹物思人”之类。但在康德看来,这些都只是经验性的综合,它们并不能保证具有先天确定性的统觉的同一性,因为该确定性具有普遍必然性和交互主体有效性的要求。康德已经多次指出这一点:“伴随着各种不同表象的经验性的意识本身是分散的,与主体的同一性没有关系”(5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90页。,“对意识本身的意识,按照我们状态的规定来说,在内部知觉中仅仅是经验性的,是随时可以变化的,它在内部诸现象的这一流变中不可能给出任何持存常住的自身,而通常被称之为内感官,或者经验性的统觉”(5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19页。。不同于此两者,在最强的意义上,两个表象的联结能先天地进行,即不依赖于经验性地给予的内容纯粹按照一些固定的方式来联结表象。康德真正要主张的就是这样一种“先天的综合”(6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26页。,并且他断言,“我意识到同一的自己”只有通过我意识到“一个先天必然的综合”(6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91页。才是可能的。
在康德“先验演绎”的全部论述中,能够支撑以上论题的莫过于A版演绎中最晦涩而又备受关注的一段文字:
如果内心不记得自己行动的同一性的话——这种行动使领会(这种领会是经验性的)的一切综合都服从某种先验的统一性,并首次使领会按照先天规则关联起来成为可能——那么,内心就会不可能在其表象的杂多中而且是先天地思维自己的同一性了。(6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20页。
在此,康德的要点是,在不同表象中“先天地思维自己的同一性”预设了意识到自己在加工这些被给予的表象时的“行动的同一性”。正如阿里森所指出的,康德这里要强调的是“对综合行动意识的必然性”(63)Henry E. 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170.。在此,最关键的问题显然在于如何理解“行动的同一性”。初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表述。首先,不同主体的心灵活动,当然在号数上不是同一个。其次,即便同一个主体的心灵活动,也总是在时间中流逝的,怎么会是同一的呢?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阿里森主张,我们应当将其理解为“一个思想行动的必然统一性”(64)Henry E. 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171.。卡尔(W. Carl)则认为,在该语境中单数的“行动”指的是“判断活动”(65)Xi Luo, Aspekte des Selbstbewusstseins bei Kant: Identitaät, Eineheit und Existenz, 160.。笔者认为,前一种解释太含糊,而后一种解释又太牵强,所以在此试图提出一种温和的解释(66)关于该关键文本的详细讨论可参见:Dieter Henrich, Identität und Objektivitä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Kants transzendentale Deduktion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76), 101。。
为了理解康德的术语,我们有必要回到上述引文所处的语境。康德在引入先验统觉作为“纯粹的、本源的和不变的意识”(6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20页。之后立即就强调,如果被给予的表象能够处于这样一个意识之下,要获得一种先天的统一性,那么这些表象之间的综合就不能是任意的,也不能是单纯经验性的,而必须“按照法则”(6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20页。来进行。而且,康德也提及了心灵在综合表象时的“机能的同一性”(6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20页。。这就是说,表象之间的联结要依照一些恒定的方式(如判断的十二种逻辑机能)来进行,而先天法则或先天概念正是这些方式的表达。所以,无论被给予的杂多是什么,无论哪一个主体去执行心灵的联结活动,都不会影响到这些固定的联结方式;刚好相反,对表象的联结必须任何时候都按照这些同一的机能或恒定的法则来进行,否则就不能产生知识。从而,康德的术语“行动的同一性”与其说是指存在着一个号数上同一的心灵活动,而毋宁说是指,任何行动,即综合活动或最终意义上的判断,都要遵循相同的先天规则,都要受到这些先天规则的支配。据此,认识过程中对杂多表象的综合活动,就要理解为规范性的活动。
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在规范性的意义上来理解先天综合,那么康德的论题就是有道理的。因为,对统觉的逻辑同一性而言,同一的自我只是作为思想可能性的形式条件,这是对于一切认识主体都普遍有效的。于是,自我对表象所进行的综合,也必须是一种普遍有效的综合,即按照先天规范来进行的综合。所以,逻辑的同一性就必须以范畴化的综合为条件。具体来说,一个自我在不同的表象中意识到自己是同一个主体,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了由他所联结起来的表象不再是互不相干的表象,而是在一个整体中统一地结合着的表象,结合的方式就是那些先天规则,即范畴。自我既执行综合活动,也自发地为这种活动提供规范;自我在自己规范性活动的产物中意识到了同一的自身。由此可见,正是范畴的运用才保证了统觉的同一性。
四 结语
康德的统觉学说对于人类认识可能性的说明具有重要贡献。表象的杂多内容作为知识的材料是通过感性而被动地给予的,但它们还必须由知性统一到主体的一个意识中去。这种统一的综合活动,就是受规则支配的先天综合或范畴化的综合,认识主体借此才能够在表象之间建立起知识所要求的普遍必然性。正是基于主体所进行的综合活动及其意识,主体才能够在自己的思想或不同表象中去辨认出同一的自身。也就是说,自我能够进行表象的自我归属以及借此而意识到自己的同一性,必须以运用范畴为条件。本文认为,斯特劳森通过强调自我归属来解释康德的自我意识理论是康德研究中的一个重大推进。但与斯特劳森的身体主义的经验论立场相反,笔者主张,统觉的同一性应理解为逻辑的同一性,而且只有从这种逻辑的同一性才能推演出先天综合的必然性。最后,我们可以援引康德对统觉的认识论地位的强调作为结束:统觉原理“是我们一般思维的绝对第一的综合原理”(7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