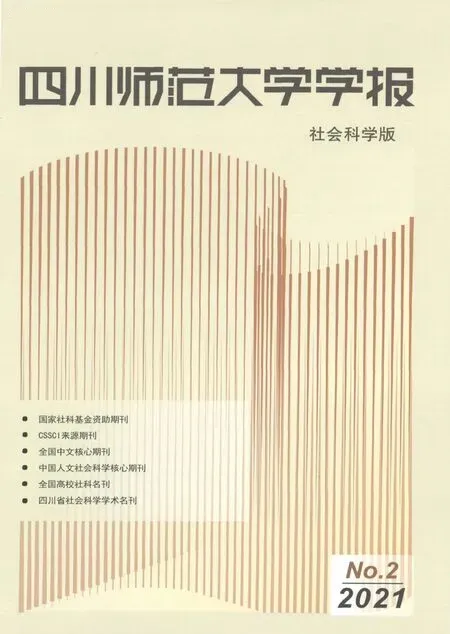论普通法视域下法条竞合的演进与启示
——兼论中国语境下的路径选择
付 恒
一 普通法系视域下法条竞合现象的存在性
在大陆法系中关于法条竞合的理论著述丰富,但在普通法系国家,几乎难觅法条竞合著述的踪影,似乎在英美刑法的教科书中也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当然更遑论对法条竞合类型的精细化研究。根据普通法系的特点,通过学理上的通说思维大致可以得出两个主要论断:一是认为普通法系因刑法典的阙如,故而没有具体罪名的法条规定,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所谓的法条竞合现象;二是认为普通法系国家在秉承先例原则的前提下,以经验为逻辑起点,以追求实用主义为价值目标,因大多数情形下已有先例和经验可循,司法上并不迫切需要专门研究一行为触犯数法条的适用问题,以至于在普通法系下缺失了法条竞合、想象竞合等与罪数相关的基本概念。
上述论断似乎在普通法系的语境下一语中的地揭示出了问题的根源,然而普通法系下究竟有无法条竞合现象?在对此问题揭示之前尚须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代表普通法系的英美刑法究竟有没有刑法典?刑事单行法规?抑或刑法法条?如若有,当然就存在法条竞合的可能性;第二,如若没有,英美法系判断一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个标准无论是理论上的犯罪构成抑或实践中的判例规则是否也存在重合的可能性?如若存在这个标准,当然也就存在法条竞合的盖然性,只是行法条竞合之实,冠之以其他称谓而已。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须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英美刑法的立法流变历程做理论上的寻踪与梳理。
二 英美关于法条竞合的立法与司法概况
(一)英国有关法条竞合的立法与司法概况
英国刑法的渊源由普通法和制定法两部分构成,其中普通法是英国刑法最主要的法律渊源,制定法则是英国刑法的另一个重要法律渊源。普通法滥觞于人们的长期习惯,并通过各级法院法官的判决和裁定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制定法则是把普通法加以整理、修订和充实,主要由国王批准的上议院和下议院正式通过的法案构成。现今英国大部分罪名几乎都是由制定法创设而成,也有部分制定法是议会将普通法的原则用条文加以细化规定而成。制定法的主要功能是对普通法的原则进行说明,也可以对普通法中某些阙如进行补正。这种功能就决定了它并不像大陆刑法典一样,在刑法总则的规定下制定统一的分则体系,而是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而产生数量众多而杂乱的规定(1)赵秉志、党剑军编译《英国刑法的新走向——法典化》,《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67页。。
自16世纪伊始,英国学者便倾心于法典编纂理论的研究并付诸司法实践。在Jeremy Bentham提出系统的法典编纂理论之前,英国刑事法律界在尝试着将制定法和案例上的某些内容做法典化的努力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法典编纂的经验。但正如美国学者Gunther A. Weiss所指出:“到目前为止,法律学者一直关注欧洲大陆法典化的历史,而有关法典化在普通法系中的相关作用仍然不甚明确。”(2)Gunther A.Weisst,“The enchantment of codification in the common-law world”,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5,no.2 (Summer 2000) : 437.直至19世纪,英国刑法改革出现了去“不成文”法传统转而走向法典化的趋势。此举引发了推动改革的法典编纂派与以法官、律师为主流的保守派之间的争论与博弈。改革派在推动法典化的进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例如,英国在1981年编纂完成了《英国刑法汇编》,但直至1989年4月,英国法典编纂委员会才公布了《关于〈英国刑法典〉的最终报告》和《刑法典草案》。在强大的普通法传统的抵制下,法典化努力最终功亏一篑。正如曾任英国刑法改革委员会主席的Brook大法官所言:“倡导刑法法典化的改革者没有找到务实、可行的法典化方法:在于其主张法典化的观点还没有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社会民众没有感觉到现行刑法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必要性;在于社会民众很难接触到刑法的基本部分……”(3)何荣功《英国刑法的法典化改革之路述评》,《中国审判》2013年第1期,第73页。英国刑法法典化运动虽然功败垂成,但从19世纪开始的刑法法典化改革对英国刑法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普通法不断吸收大陆法系成文法之精义而得以行稳致远。
英国以判例法为主,刑事法典化起步较晚,加之缺乏成文法文化传统的底蕴,并且由于英国没有明确规定构成要件的概念,导致其制定法在法条竞合问题上缺乏直接规定(4)赵秉志、党剑军编译《英国刑法的新走向——法典化》,《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68页。。这体现在无论是刑事制定法上的具体犯罪规定还是普通法上的隐形犯罪规定,均通过不同的差异化的具体案例判决将每种犯罪类型予以个别化处理,而非抽象的归纳构成要件。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大陆法系中探讨各个犯罪构成之间究竟是否存在竞合的理论,在英国刑事法制体系的构架下近乎成为多余。应当注意的是,由于刑事制定法是英国刑法的另一个重要法律渊源,它不仅可以对判例的原则进行说明,也可以对判例中某些阙如进行补正,所以制定法中存在着很多关于罪名的内涵和外延的具体规定。有鉴于此,英国为数众多的不同刑事制定法中当然也就存在着罪名之间发生竞合的可能性,从而产生法条竞合的司法适用问题。
面对一行为触犯数罪的司法处理,英国刑事法律界特别强调对危害结果的关注,不区分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严格奉行有罪必罚的原则。在普通法系中,形式上的数罪(如法条竞合)均被认为是实质上的数罪,对各罪所判处的刑罚必须进行严格相加。毋庸讳言的是,这种做法会直接导致刑罚过分严厉而失去均衡性。自20世纪50年代伊始,吸收原则(同时执行原则)和限制加重原则开始被广泛吸纳采用(5)任彦君《数罪并罚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3页。。例如《英国刑法汇编》中规定了一行为触犯数罪的并罚方法——同时执行制度。所谓同时执行是指罪犯的数个判决在相同时间和地点同时执行,其执行效果相当于大陆法系的吸收原则,但是在理论上又不同于吸收(6)吴平《数罪并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以同时执行为例,犯罪嫌疑人使用故意损坏财产的方式实施盗窃,因盗窃罪被判处5年有期监禁,因损害财产罪被判处1年有期监禁。当盗窃罪被判处5年有期监禁执行完毕之时,损害财产罪被判处的1年有期监禁相当于在4年前已经执行完毕。从适用效果上看,这种并罚方法与大陆法系的并科原则近乎一致,但其判决确立的数个宣告刑是彼此独立的并且按照判决顺序依次执行。质言之,英国刑法对于一行为触犯数罪的处理模式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对触犯的罪名分别处刑;二是依次执行各罪所判处刑罚,但刑期并科。通过刑期并科的量刑手段来纠偏因认定一行为触犯数罪而被并罚的不公正结果,从而实现罪刑均衡的价值目标。
(二)美国关于法条竞合的立法与司法概况
与英国处理法条竞合问题的模式相比较,美国不仅有犯罪类型个别化的法典化尝试,也有普通法上的类型化经典判例,同时还在法典中对该问题的处理做出了专门具体的规定。成文法在美国法律体系中作为重要的法律渊源,其地位和分量足以与判例法平分秋色。尤其是在联邦刑事立法方面,刑事单行法规几乎构成了刑法渊源的绝大部分。
美国刑法的法典化运动滥觞于1790年国会颁布的《治罪法》。此后,大量单行刑法及附属刑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879年,美国国会任命专门委员会校订和编纂刑事法典。1909年,《编纂、修正、改订联邦刑事法规的法律》正式颁布,共计14章536条。但该法典并无总则的规定,且各个章节之间留有很多空白法条,以便于后来增补。1926年,美国正式制定《联邦法典》(UnitedStatesCode);1948年,国会通过修正、法典化及实施有效法律的法令,创制了《联邦法典》第十八主题犯罪及刑事程序(7)李仲民《美国联邦刑法法典化述评》,《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7页。。该刑法典被定义为“法律的系统收集,归纳或修订”(8)Julie R.O’Sullivan,“The federal criminal code is a disgrace: Obstruction statutes as case study,”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96, no. 2 (Winter 2006) : 643.,其目的在于加强各个州之间刑事立法的统一性。但法典条文的章节“按照字母流排序排列、零散而没有逻辑”(9)Ronald L. Gainer,“Federal criminal code reform: Past and future”, 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 2, no. 1 (April 1998): 92-93.,对个罪的定义冗长而不明确。“1971年1月7日,国家联邦刑法改革委员会向总统和国会提交了关于全面修订实体联邦刑法的提案。这项工作是在国会授权的基础上开始的,旨在改善刑法典的体系”(10)John F.Dobbyn,“A proposal for changing the jurisdictional provisions of the new federal criminal code,” Cornell Law review 57, no. 2 (January 1972) : 1.。《联邦法典》虽经历多次修订,但其基本面并无太大变化。《联邦法典》“这些缺陷不能修复或通过增加新法规补救,因为它们是根本性的”(11)Robert H. Joost, “Federal criminal code reform: Is it possible?”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 1, no. 1 (April 1997): 195.转引自:李仲民《美国联邦刑法法典化述评》,《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13页。。
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立法及判例数量呈现几何级数量的膨胀,由于联邦刑法太过细化,加之理论上不完整,缺乏实践的操作性,已令司法者无所适从。1962年美国法学会编撰并公布的《模范刑法典》,被誉为美国近代刑法法典化的里程碑。回顾美国的刑法法典化进程,“《模范刑法典》不是第一个或最具有雄心的刑法编撰,但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刑法法典化编撰尝试”(12)Paul H.Robinson,Markus D. Dubber,“The America model penal code: A brief overview,” New Criminal Law Review 10, no. 3 (Summer 2007) : 320.。
源于普通法系传统的影响,美国刑事司法理论中也没有构建法条竞合的相关概念。当在判例中出现了一行为触犯数罪的客观现象而危及“禁止双重危险原则”(double jeopardy)之时,现代美国刑法理论与实务都采取了相对的变通措施,对大陆法系法条竞合类型中的包容关系予以了立法承认,并将此类情形全部作为一罪加以处理。《模范刑法典》首次在第1.07条中专门做出了具体规定,并将其称之为“当一行为超过一个罪行时的起诉方法”(Method of Prosecution When Conduct Constitutes More Than One Offense)。尤其在第1.07条第一款和第四款中更是详细规定了一行为构成“数罪”处理的一般原则与特殊例外规则,以实现有罪必罚原则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平衡(13)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Model Penal Code,1962-05-24.。双重危险原则作为美国宪法的重要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禁止多项起诉和多重处罚同样的罪行”(14)Carissa Byrne Hessick & F.Andrew Hessick,“Double Jeopardy As A Limit On Punishment,” Cornell Law Review 97, no. 3 (November 2011): 46.,其义理在《模范刑法典》第1.07条到1.11条的规定中从不同的方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
一般原则规定当被告人实施一行为而触犯数个罪名之时,对于所犯各个罪名均可予以追诉。特殊例外规则规定了当同一行为触犯数罪时,不得做两个以上的有罪认定的五种情形。(1)一罪被他罪所吸收的。第1.07条第四款规定了存在以下三种情况时,犯罪被吸收:“a.被指控的一罪成立的全部或部分事实已被包含在他罪之中;b.被指控的基本犯罪吸收该种罪的未遂或教唆;c.被指控的某一罪名对于同一人、同一财产或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损害较轻,或者可责性比较轻,那么损害和可责性较重的吸收较轻的。”(2)一罪仅为他罪的共谋或其他预备行为。(3)如果被告人只有一个相同行为时,为确定数罪的实行,需要认定不同的事实。(4)存在一般与特殊关系的情况。(5)某持续性行为被规定为犯罪,并且持续行为未被中断的。(15)美国法学会《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刘仁文、王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页。第一种情形和第四种情形大致分别对应大陆法系法条竞合理论中的吸收关系类型和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类型。第1.07节的规定充分说明,美国刑法体系中虽然没有法条竞合的相关概念,但并非不存在法条竞合的客观现象并对如何处断提出了独特的适用原则与方法。
三 普通法系法条竞合处置方案的评析与启示
概言之,笼统地认为普通法系对法条竞合的相关问题研究毫无建树是不符合实际的,认为对于一行为触犯数法条实行过于苛严的有罪必罚原则也是有失偏颇的。毕竟不同的法系之间,同样面临着如何实现法条竞合犯罪刑均衡的共同任务。因此,总结、提炼与反思普通法系下的法条竞合处置方案,或能使我国的法条竞合理论与司法实践得以借力滋养而绽现异域新花。
(一)借鉴普通法系的“找法”路径
普通法系借助于先例制度和陪审制度,针对法条竞合个案的路径导向值得大陆法系学习和借鉴。事实上,法条竞合理论建立的目的无非是要解决一行为触犯数个法条应当如何适用来达到罪刑均衡的目的,说到底是要解决如何在实践中“找法”的问题。大陆法系是在承认法条之间存在竞合的前提下,在对法条竞合现象分类的基础上,运用形式逻辑学和刑法解释学的方法,提出针对不同类型的法条竞合采取不同的司法适用原则的方法来实现罪刑相适应。普通法系则绕开错综复杂的法条而另辟蹊径,其主要着力点并非放在法律逻辑以及解释技术层面,而主要是通过对实体和程序双重维度的技术设计来“找法”,以实现个案正义。
一方面是普通法系在实体法层面通过先例的适用来回避抽象繁杂的法律条文解释。与大陆法系的司法体制不同,普通法系国家实行先例制度。在这种制度模式的架构下,法官在审判案件之时,必须以先前的判例作为指导,有效地避免了抽象繁琐的法律条文分析,让裁判者的思维更多地集中于案件的事实、证据的认定以及程序是否正当等相关问题,而非拘泥在法条应当如何分析、如何适用的语境下考虑问题。“它使法院在一个法律问题每次重新提出时就重新考察该问题的作法成为不必要”(16)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1页。,从而缩短了法条竞合个案的处理过程。同时在思维模式上则更多地侧重于通过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使得案件的判决结果符合罪刑均衡的理念。
另一方面,对于“找法”涉及的实体和程序问题,普通法系通常采用杂糅的方式进行合并规定。通过这样的技术处理,涉及相关问题的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便相对集中,较大陆法系中实体法、程序法分别规定的找法路径更为简洁明了。例如,《模范刑法典》1.07条第一款主要是从实体上规定一行为触犯数罪的处理原则;第二款规定了对数罪分开进行审理的程序性限制;第三款规定了法庭启动分开审理数罪的权限;第四款规定一罪吸收他罪的三种具体情况;第五款规定法庭是否有义务对被吸收的犯罪向陪审团提出具体的指控。(17)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Model Penal Code,1962-05-24.由此可见,第一款和第四款主要涉及实体问题,第二、三、五款主要涉及程序性问题。处理一行为触犯数罪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均在同一条文中予以全部规定,尽显普通法系简约、高效之风范。
另外,在制度的设计上,陪审团制度的设计理念与制度安排,巧妙地将草根阶层的“常识、常情、常理”融入到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之中,有效地化解了精英阶层与草根群众在“找法”路径上的价值评判差异。此种设计之精髓在于力图避免出现大陆法系学者在自行构造的理论经纬中违背“常识、常情、常理”所做出的刑法解释与司法处断。因为“出于解决纠纷的需要,司法必须要考虑民众的伦理性需求和惯常性行为方式,必须以更贴近民众生活的方式来运作”(18)李拥军《当代中国法律对亲属的调整:文本与实践的背反及统合》,《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4期,第71页。,而陪审团制度在进行犯罪事实的认定上,无疑是一种以普通大众的生活经验为基础,以满足人伦、人情、人性需求为出发点,以合理的价值考量为终极目标的独特司法运作方式。
(二)吸纳其对有罪必罚原则的“纠偏”技术
对于普通法系通常采取的对同一行为构成两个以上犯罪的“有罪必罚”原则,不能一味地加以批判和否定。所谓“有罪必罚”原则是指当一个行为触犯两个以上法条规定的罪名时,普通法系坚持以行为触犯的法条为标准确定基本的罪数,并且不设上限的原则。这一点显著区别于大陆法系在罪数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换个角度思考,至少普通法系这种在定罪问题上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这不仅反映了其对犯罪认定的谨慎态度,也彰显了其法治精神的基本理念。“有罪必罚”实质上是应然层面的法则,普通法系对这一原则的恪守,更是体现了对应然原则的遵循。在实然层面上,虽然被告因同一行为可能构成两项以上的犯罪时,被告可能会因每项罪名而被起诉,但事实上可能并非会判处构成多项罪名,或者即使判处了多项罪名也可以通过刑法典中的吸收原则或者同时执行制度加以矫正而达到罪刑均衡的目的。
从罪名的角度看,美国《模范刑法典》通过1.07节中规定了不得重复处罚的五种情形来避免对一行为触犯数罪名的过度认定。例如,被告的客观行为符合上述五种情形,那么被告虽然在理论上会被指控多项罪名,但事实上多项指控的罪名会被某一项指控的罪名所吸收而仅构成一罪。多项指控的进行体现了对法治原则的尊重,吸收原则的执行实现了对避免“双重危险”原则的恪守。通过对“有罪必罚原则”和“吸收原则”的贯彻,实现了法治精神与罪刑均衡的协调与统一。
从刑罚的角度看,英、美两国解决法条竞合问题的“同时执行”制度成功地化解了有罪必罚原则在罪数认定问题上可能导致的罪刑失衡。由于《模范刑法典》中并非一一涵盖了法条竞合的全部类型,当出现一行为触犯数罪的行为不属于五种吸收情形而被认定为数罪时,必须对每一个罪的刑罚悉数执行,这样的做法则显得过于苛严。普通法系独树一帜的同时执行制度,即是从刑罚的角度来纠正对罪名过度评价而造成的刑罚失衡。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作用,从而消解法条竞合被裁定为数罪所带来的重复评价和罪刑不相适应的问题。它的适用标准是同一行为,即针对于同一个行为的判决才能适用同时执行制度。如果基于同一行为的数罪判断,连续执行则构成“双重处罚的危险”,这是英美立法明令禁止的。于是按照同时执行的方法便可以取得按照大陆法系相关理论处断近乎相同的效果。另外,作为判断同一行为的依据,普通法系从理论上提出了“同样的证据”、“同样的处理”、“同一立法目的”等标准。“同一立法目的”标准与大陆法系在判断法条竞合上的法益标准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保护法益就是立法目的(19)李贵方《自由刑比较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
(三)吸收其最大限度消解竞合的解释技术
在刑事立法和刑法解释技术上,普通法系在易于混淆的罪名设置上,通过澄清罪名的内涵与外延,最大可能地消解法条之间发生竞合的可能性,这种技术路径值得大陆法系反思与借鉴(20)饶景、蔡鹤《英美刑法中的法条竞合》,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师大·西部法治论坛》2017年2期,第45页。。在罪名的设置上,普通法系大多采用了“互斥论”的基本立场,即在罪名的内涵释义上将容易发生法条竞合现象的罪名之间解释为对立关系。尤其是概括的罪名之下多采用对立关系的模式设立关系模糊的个罪,从而避免了各个罪名之间是否发生竞合的判断。例如,“英美普通法和制定法把杀人罪(criminal homicide)分为谋杀(murder)和非预谋杀人(manslaughter)两大类”(21)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为了防止谋杀罪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联罪名之间的竞合,通过对立模式的学理解释将谋杀罪又分为:蓄意谋杀罪(intent-to-kill murder)、故意重伤谋杀罪(intent-to-do-serious-bodily-injury murder)、极端轻率谋杀罪(depraved-heart murder)、重罪-谋杀罪(felony-murder)、拘捕谋杀罪(resisting-lawful-arrest murder)(22)对于谋杀罪的类型分类,在美国并没有统一的立法模式或理论学说,这里采用了美国大多数学者承认的分类标准。。将非预谋杀人罪(manslaughter)分为非预谋故意杀人(voluntary manslaughter,如激情杀人)和过失杀人(voluntary manslaughter)(23)Emily Finch & Stefan Fafinski, English Legal System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7), 93-113.。又如,在美国的刑法理论和实践中,通过区分财物交易过程中所有权是否转移来划分以欺骗方式实施的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域,在这类型的案件中“盗窃罪的控方要求证明在起诉状中指控的盗窃是以何种形式实施的。因此,如果起诉状指控偷盗罪,控方就不能获得侵占罪或诈骗罪的裁判”(24)德雷斯勒《美国刑法精解》,王秀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9页。。
四 我国现行制度的症结
(一)《刑法》总则中缺失法条竞合和想象竞合的原则性条款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竞合(罪数)论的体系建构可谓‘五花八门’,当属刑法知识体系中最‘杂乱’的一章。究其原委,除了竞合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包括德式竞合论抑或日式罪数论之模式选择上的博弈)原因,我国刑法长期缺乏竞合(罪数)问题的总则性规定(即无法可依)亦不无关系。”(25)王彦强《“从一重处断”竞合条款的理解与适用——兼谈我国竞合(罪数)体系的构建》,《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6期,第98页。毋庸讳言,与德日体系的立法不同,我国《刑法》总则中缺乏有关竞合问题处理原则的一般性条款,只是在分则个别个罪条文中规定了部分竞合关系的处置条款(26)例如,刑法中提示可能存在法条竞合的注意性规定“本法另有规定,依照规定”;提示可能存在想象竞合的语词“有前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某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本处之所以表述可能存在想象竞合,这是因为在交叉关系的法条竞合、吸收犯以及牵连犯等处断的一罪中,同样适用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但这些碎片式的规定由于缺乏统一的原则指导,常常会出现相互抵牾的情形而让实务界无所适从。
例如,行为人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过程中,以暴力抗拒执法检查,在《刑法》不同的条文规定中处遇迥异。《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式抗拒缉私的,以走私犯罪与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但是在第三百一十八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和第三百四十七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又将“暴力抗拒检查”的行为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相同的行为却没有得到相同的处遇,竞合问题在刑法典规定中的冲突可见一斑。
某甲利用信用卡诈骗4000元的行为,在司法实务的处断过程中似乎既符合信用卡诈骗罪,又符合普通诈骗罪的行为类型,属于法条竞合的属种关系类型。司法人员往往会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普通诈骗罪“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提示,排除普通诈骗罪的司法适用,仅适用特别法条的信用卡诈骗罪。而问题在于甲没有达到信用卡诈骗罪的入罪数量标准,应当作无罪处理。按照法条竞合的提示性语词,却得出了似乎在构成普通诈骗罪的前提下的无罪结论,这也颇令实务界感到无所适从。为了突破这一困境,《刑法修正案(九)》对分则相关竞合条款进行了系统性调适,大体形成了“从一重处断”条款、“从特别规定”条款和“数罪并罚”条款三种类型主导的局面。但由于《刑法》总则中关于竞合问题的原则性规定阙如,在实践中仍旧会出现个案处理中的巨大分歧。普通法系通过明确“有罪必罚原则”和“吸收原则”的内涵,并在实践中加以严格贯彻,实现了在处理法条竞合犯问题上,法治精神与罪刑均衡的协调与统一。在现行制度的架构下,若能从竞合处置条款中归纳法条竞合、想象竞合的一般性处置原则,则能够为“一行为触犯数罪”问题的处理,提供相关明确的法律适用原则。
(二)刑事指导案例缺失相关法条竞合的典型案例
在成文法传统占统治地位的大陆法系,案例同样是刑法学研究的基础。刑法理论中绝大多数真问题的发现都是围绕着具体鲜活的案例而展开的。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机关也高度重视对刑法典型案例的归纳和总结,注重类型化案例的示范效应。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正式建立。作为我国司法实践的一种有益尝试,案例指导制度已经实施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共计颁布了139个指导案例,其中刑事指导案例22个(截止到2020年2月17日)(27)《刑事指导性案例》,北大法律信息网,2020年2月17日访问,http://www.pkulaw.com/case/。,这些指导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正在被广泛运用,发挥着参照、示范、规范、监督等重要作用。
但是当下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也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目前刑事指导案例的数量较少,覆盖范围也非常有限,特别是22个刑事指导案例难以涵盖刑事司法实践的典型法律难题,更缺少关于疑难竞合问题的典型案例,这就不能对实践中如何处理交叉竞合、属种关系竞合以及整体法与部分法的竞合起到典型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已经颁布的刑事指导性案例存在部分案例指导力与说服力不强的问题。多数案例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在重申司法解释或者是回应社会公众关切的热点问题,缺乏对案例中蕴含的法理和规则做进一步的抽象和解释。在英美法系,先例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司法指导作用,除了其本身具有法律效力之外(28)在案例的效力上,英美法系的先例制度与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具有不同的内涵。英美法系中的判例具有法律效力,所有的既定判例就是法的渊源。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是在继承大陆法系成文法传统的基础上,运用典型案例解释现行法律、指导法院审判活动,从而维护司法统一的司法改革举措。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自身没有法律效力,仅仅只是适用成文法律而已。指导性案例在我国显然不属于法律渊源,当然法院判决也就不会“造法”,但可以为成文法的运用提供丰富的案例素材。,还表现为在辨法析理上尤为透彻,特别是能够给予后案法官充分的法律指导与启迪。特别是一些影响深远的法学理论以及里程碑式的结论往往都是通过先例判决来对既定规则进行补充和突破(29)例如,美国第五宪法修正案虽然规定了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但这仅仅是一种原则性的规定,在具体适用中当如何启动或者受限并未加以明确规定。通过1965年的格里芬诉加利福尼亚州案(Griffin v. California)的判决结果,对这一修正案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衍生出即使被告人没有提出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仍然应当受到该权利的保护的规则。参见:Griffin v. California, 380 U.S. 609, 615(1965)。。事实上,“案例指导制度的首要功能是创制司法规则,因为只有司法规则才能为此后审理相同或者相似案件提供参照”(30)陈兴良《刑法指导案例裁判要点功能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第6页。。
(三)竞合问题的处断常缺乏“常识、常情、常理”
“司法审判的进路在于从案情出发,从事理出发,诉诸常识常理常情,从事理切入讲求法理,公正裁判以达至解决纠纷之目的”(31)魏俊斌、帅佳《法与不法:比较法视野下的德国判例与“于欢案”一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53页。。但作为指导司法实践的竞合处断理论却存在着偏离“常识、常情、常理”的倾向。例如,有学者主张想象竞合犯“其本质是危害行为的竞合,其同一的自然行为蕴含了多个具有刑法意义的行为。因此,以多个犯罪构成分别评价想象竞合犯,其实是以多个犯罪构成分别评价其所竞合的多个行为。可见,从想象竞合犯的本质观之,也不存在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问题”(32)庄劲《犯罪竞合:罪数分析的结构与体系》,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因此,对于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应当数罪并罚。从专业视角关照,由于同一自然行为蕴含了多个刑法意义的行为,侵犯了多个法益,因此数罪并罚似乎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但从大众的视角来审视,草根阶层深信行为人明明只有一个行为,却要被数次评价,遭到数次处罚,明显有悖于“常识、常情、常理”。至于学者所谓的被处罚的一行为是“多个具有刑法意义的行为”,在大众看来只是学者自娱自乐的概念游戏,对于民众而言是难以理解的。正因为精英阶层与草根群众在对待个案正义上的价值评判差异,才导致了近年来诸如“辱母案”“昆山案”等争议判决的出现。事实上“在刑法领域,也要以生活经验为基础制定法律与解释法律,付出经验之外,作合理的价值判断”(33)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如何解决此种冲突?如何在竞合问题的处断上融入更多的“常识、常情、常理”?吸纳普通法系下的陪审制度之精髓,立足于本土资源的司法制度考量,人民陪审员制度无疑是有效化解冲突的选择路径。“作为一种旨在彰显司法民主与权力制衡的制度,陪审制度设立的初衷即在于通过陪审形式,让普通民众直接参与到司法审判的进程中来,并在此一进程中通过参与案件审理、独立提出案件处理意见等方式,强化审判权运行的社会监督和制约,实现民众政治意愿的充分表达”(34)步洋洋《中国式陪审制度的溯源与重构》,《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5期,第91页。。其本质不在于业内人士的职业支持,而在于草根阶层观点的融入,以便形成不同价值观念与知识谱系、思维模式的碰撞,凸显个案处断过程中草根路线与精英思维的博弈与平衡。
五 中国语境下法条竞合的制度路径选择
(一)刑法典总则中增补“一行为触犯数罪”处理原则的修正案
当一行为触犯数罪名时,可能构成想象竞合也可能构成法条竞合。当一行为真实地构成数罪时符合想象竞合;当表面上触犯数罪名,但仅适用一法条便可以对其不法内涵予以充分评价时则构成法条竞合。对于想象竞合,无论是《德国刑法典》还是《日本刑法典》都在总则中做出了原则性规定,而对于不符合想象竞合规定的一行为触犯数罪名的情况,德、日则仅在理论上对其不同的类型应当如何适用刑罚分别加以探讨。例如,《德国刑法典》总则第三章第三节“触犯数法规的量刑”之第五十二条对“一行为触犯数罪”进行了原则性规定。该规定指出,行为单数触犯数个刑法法规,或者数次触犯同一刑法法规,系想象竞合(Idealkonkurrenz)。前者称为同类想象竞合,后者称为异类想象竞合。对于想象竞合犯,采用结合原则(Kombinationsprinzip)科刑(35)《德国刑法典》,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对于因各法条本身存在的交叉、包容关系而导致表象上触犯数个刑法条文,但事实上只能适用其中一个法条的假性竞合,亦即法条竞合(Gesetzeskonkurrenz),《德国刑法典》并未加以明确规定。德国刑事法学理论认为法条竞合在本质上是犯罪单数,因此并不存在竞合问题。《日本刑法典》在总则中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一行为同时触犯两个以上罪名的是想象竞合犯。对于想象竞合犯,应当按照其最重的刑罚处断。在《日本刑法典》中也同样没有关于法条竞合的概括性规定,致使对该问题的处理模式与德国如出一辙,仅在学理解释和司法判例中予以探讨(36)《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5页。。这看似雷同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真问题”,即:为什么德、日均不在总则条款中对法条竞合的构成要件与处断原则加以规定而仅规定想象竞合的要件与处断原则呢?一是简化问题的需要。当一行为触犯数罪名时,要么是想象竞合要么是法条竞合。当总则性条款对想象竞合做出了要件规定后,一行为触犯数罪不属于想象竞合当然则归属于法条竞合,总则自然没有必要再对法条竞合做出同样类似的规定。加之法条竞合的类型复杂,不可能在总则性规定中进行详细列举与阐释。虽然美国在《模范刑法典》中对法条竞合做出了相关具体规定,但也仅涉及到了吸收关系与属种关系两种类型。二是强调想象竞合的处断不能按照普通一罪的处理模式。前文已述,法条竞合的本质是犯罪单数,实质上仅有一个法条得以适用,是假性竞合。对此按照一罪处罚即可,而无需在总则中予以强调。想象竞合的本质是犯罪复数,实质上符合两个以上的法条,是真实的竞合。对此必须在总则条款中做提示性规定,强调其不能按照普通一罪处罚的原则来进行。
想象竞合的构成要件和处理原则可以借鉴德日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刑法体系的特点,在《刑法》总则中予以明确规定。考虑到法条竞合的类型较为复杂且理论上争议较大,可以对其不作具体规定,但可以吸纳美国《模范刑法典》的经验,对于法条竞合的构成要件和处理原则在《刑法》总则中予以统一规定,以防止在个罪中分别规定所造成的抵牾。例如,前文所述某甲利用信用卡诈骗4000元的案例,若总则中对法条竞合做出了上述规定,那么我们可以在司法上明确该行为必须在表面上触犯数个法条,而只有一个法条可以对其不法予以充分评价。依据第二百六十六条普通诈骗罪“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提示,说明该行为根本不符合普通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依据信用卡诈骗的入罪数额标准也达不到相关要求。由于该行为没有触犯数个法条,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竞合问题,对其仅能按照违法行为处理而非犯罪行为处理。
(二)增补类型化的法条竞合案例,完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选取社会关注度高、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具有典型性的法条竞合疑难案例予以发布,特别是当前社会热点中涉及的交叉竞合、属种关系竞合以及整体法与部分法竞合的三种代表性案例。通过对三种法条竞合类型典型案例判决来进行辨法析理,回应社会诉求,指导司法实践。例如,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崛起,快递行业中有关侵犯财产的犯罪频繁发生。特别是对于快递行业员工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侵犯客户财物行为所导致的竞合罪名当如何进行认定,是当前刑事司法实务应当正面回应的问题。那么此类犯罪行为究竟是论盗窃罪?侵占罪?抑或职务侵占罪?围绕上述竞合问题,就可以通过典型案例的裁判要点进行释法析理,澄清三罪之间的竞合关系并给出司法处断结论。唯其如此,方能达到释疑解惑、正本清源之目的。
其次,要充分发挥刑法指导案例裁判要点的多重功能,从而满足对于特殊刑事案件的公平正义要求。梳理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22个刑法指导案例,不难发现裁判要点已经渐入刑事理论与司法实务的视域,成为司法规则的荷载主体,秉承着该类典型案例的义理精华。未来的案例指导制度改革,要进一步加大对裁判要点的学理剖析,更加充分发挥其司法规则的创制功能(与司法解释相比较而言,刑事指导案例能够更为细致、具体地创制类型化规则)、条文含义的释义功能(通过规则的细化对刑事法律规定本身进行解释与厘定,明确法律条文的具体含义)以及理解冲突中的释疑功能(通过类型化案例的辨法析理解决法律条文理解与适用中的冲突)(37)陈兴良《刑法指导案例裁判要点功能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第6页。。
最后,指导案例的裁判要点优化,一方面要在对类型化案例的案件事由、争议焦点、定罪与量刑依据的高度提炼上下功夫;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将高度凝练的裁判要点和关键词通过多种网络平台予以公开发布,以实现快捷、高效、准确的检索。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对典型案例的知晓程度,还可以借助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力量充分挖掘典型案例的价值与功能,同时法官也可以通过阅读简明扼要的裁判要点节省“找法”的时间,从而大大提高司法效率。
(三)构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本土化进路
从两大法系来看,现代陪审制度主要表现为以英美法系为代表的陪审团制度和以大陆法系为代表的参审制度两种模式。20世纪末,大陆法系的参审制度呈现出了吸收、借鉴、融合英美法系陪审制的趋势。这种趋势一方面表现为新引入陪审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以方兴未艾之势,在大陆法系的传统领域内蔓延。例如,“1995年,西班牙颁布《陪审团法》,开始采用英国式的陪审团制度;2009年,日本开始实施《关于裁判员参加刑事审判的法律》,在制度层面正式确立兼具大陆法系参审制度与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特征的‘裁判员制度’。2017年11月,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公布了《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草案)》,实现由形式监督的‘观审员’到实质参审的‘参审员’之转变”(38)步洋洋《中国式陪审制度的溯源与重构》,《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5期,第89页。。但在这种融合的进程中,部分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两种制度在体系与价值上激烈的碰撞,最终导致回归单一模式。例如,基于对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在司法上的区分困难,德国试图移植陪审制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并回归到了参审制。事实上,日本虽然引进了陪审制但也没有区分裁判员与法官在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上的职权差异,而是强调在此过程中,应当融入裁判员的社会经验与社会知识,防止法律职业精英们忽视一般国民社会经验的技术专断。因此两种模式的交融,既必须立足于各国的历史经验与法律文化传统,又必须符合国内刑法语境,满足司法民主的诉求。
一方面,在我国现行司法体系下构建以“事实审”和“法律审”彻底分离为基础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不仅不具备可操作性,且只会给司法实务徒增困扰。例如,在审理涉嫌“猥亵儿童罪”的庭审过程中,按照“事实审”和“法律审”相分离的模式,陪审员在庭审中需要对是否存在猥亵儿童这一事实问题进行认定。但是否是儿童的判定不单纯是一个事实问题,还涉及到法律的评价和判断,是否属于猥亵行为也涉及到经验法则的评价而不是单纯的事实判断。从司法实际运行的经验来看,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总是纠缠在一起,往往难以分割。因此判断“儿童”是否遭受被告人实施的“猥亵”行为侵害,必须在整体上加以评价,而不能在庭审中机械地加以分割。因此,现行陪审制度需要的是“事实审”和“法律审”的相对分离,而不是绝对分离,更需要的是职业法官与陪审员之间的协商信任与通力合作而非相互制约。2018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将七人合议庭中的人民陪审员权限限缩为事实问题认定上的决定权,法律问题上的保留建议权(39)2018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二十一条和二十二条分别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三人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人民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与法官共同表决;对法律适用,可以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这一规定正是对“事实审”和“法律审”相对分离的立法肯定,或许对于司法判决的民意基础和社会效果会更加有利。
另一方面,在人民陪审员的选任上,借鉴英美法系中对陪审员“无知美德”的要求,复归人民陪审员本有的平民视角,保留陪审员作为一般国民的社会经验与社会知识,避免“专业化”导向下的“被法官化”现象。在现阶段,首先,要逐步废除关于陪审员岗前、定期、日常法律职业培训之规定。删除关于陪审员选任的学历资格要求,明确规定在法院所辖区域内,凡是具备选民资格且未被剥夺政治权利,能够正常表达的公民均可被选为人民陪审员。其次,为凸显人民陪审员作为“草根”阶层代表的广泛性,应当充分吸收社会不同民族、年龄、性别、行业的人员参加陪审工作。尤其要在广大农村地区吸收农民参加与农民有关的陪审案件,在城市社区探索将陪审引入的途径和方式,建立社区人民陪审员制度。最后,将随机抽取陪审员的程序上升为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刚性要求,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违反该程序的否定性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