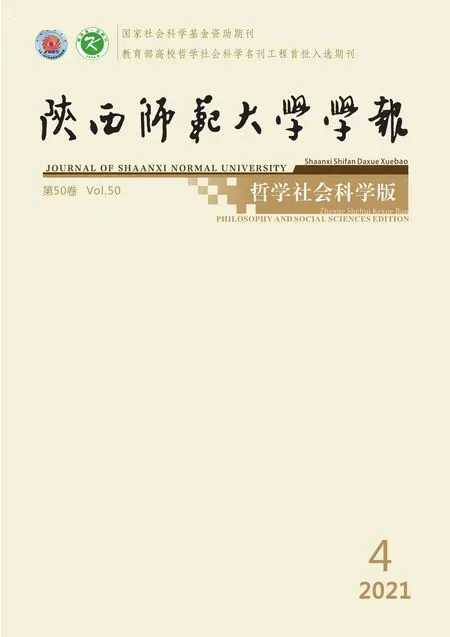黎锦熙对汉语方言分区理论的重大贡献
乔全生, 谷少华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语言科学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119)
黎锦熙先生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其学术研究涉及领域颇广,著述立论甚丰,对传承与发展汉语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长期以来,语言学界对黎锦熙汉语语法尤其是对句本位语法评述较多。称其《新著国语文法》为奠基之作、开创之作[1]1。然而,关于黎锦熙对汉语方言分区理论的贡献却鲜有报道,即使有所引述,也是寥寥数语,且数处提法尚需补正。如王福堂[2]53-54、李小凡[3]25在谈到黎锦熙对汉语方言的分区时,只提到“十二系”,未提及“四区”。黎锦熙完整的分区提法应当是“四区十二系”。此外,王、李两书中的引用标注为1934年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然而,翻检《国语运动史纲》全书(1)同时翻阅了《国语运动史纲》1934版及2011版,本文页码为2011版。,我们并未发现书中对汉语方言十二系分区的具体论述。在“文字声韵变迁考订表”中只有“方言四区”,即北方官话区、南方官话区、苏浙语区、闽粤语区4个名目[4]336。
因此,首先有必要搞清黎锦熙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著作、时间及其提法。经查,发现黎锦熙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最早论述的出处是1924年《新著国语教学法》初版第5章《标准语与“语法”——语言》第2节“因地制宜的话法教学”(汉语方言分区略)。在该书中,黎锦熙将汉语方言分为四区十二系,现摘录黎锦熙有关论述并整理如下[5]82-88:
(1)北方官话区域——可依河流再分为三系: 第一,河北系,直隶、山西(但太原一带土语较多)、东三省、山东的北部(登莱半岛土语也很多,但可属这系)、河南的河北道属之。第二,河南系,河南中部开封一带、山东的南部、江苏安徽的淮北一带属之。第三,河西系,陕西甘肃连带新疆属之。
(2)南方官话区域——又可依水道分为四系:第一,江淮系,江苏的江北一带(但东边要除开北岸的南通,西边要添加南岸的镇江和南京)、安徽的中部芜湖安庆一带及江西的九江属之。第二,江汉系,河南的南部和湖北等处属之。第三,江湖系,湖南的东部、湖北的东南一角、江西的西南南部属之(这系中的土语,也很复杂,惟江西的赣州语较为普通)。四,金沙系,范围很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的西北部、湖南的西部属之。
(3)苏浙一带——又可依流域分为二系:第一,太湖系,江苏的苏常沪海两道、浙江浙西的钱塘道(即旧杭嘉湖三府;但杭州和附近的话,要另属于南方官话,似近乎江湖系)和浙东的宁绍等处属之。第二,浙源系,浙江上流的金华道(即旧金严衢三府)、溯源而上安徽的徽州宁国等处和江西的饶州广信等处属之。
(4)东南滨海区域——又可依流域分为三系:第一,瓯海系,浙江的永嘉道(即旧温处台三府)、福建的福宁等处属之。第二,闽海系,福建的闽江流域、南及漳厦和广东的潮汕一带属之(福州和厦门汕头的语音本不同,但还可以归总作一个系统;例如潮汕一带的话即名“福佬话”,一作“福漏话”)。第三,粤海系,广东的大部分和广西的东部属之。
10年后,四区的名目出现在《国语运动史纲》(1934)中,此时已改为较为明晰的“北方官话区、南方官话区、苏浙语区、闽粤语区。”
除此之外,黎锦熙还有多种论著涉及汉语方言,如《京音入声字谱》(1923)、《方言风谣志》(1940)、《论全国方言研究调查之重要及其工作计划》(1941)、《地方志中“方言风谣志”之编查法》(1941)、《论方音书》(1942)。最可贵的是,黎锦熙用这些范式编撰了《同官县志》(1944)、《洛川县志》(1944)、《宜川县志》(1944)中的“方言谣谚”。
可见,黎锦熙对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尤其对汉语方言分区理论研究也多有奠基之劳、开创之功。本文将从以下3个方面论述黎锦熙对汉语方言分区理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一、 以四区统领十二系方式命名的准确性与层次性
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历史,似可追溯至扬雄《方言》。若论近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目前有学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学者是章太炎、黎锦熙[2]53-54;[3]25。章太炎、黎锦熙的分区被认为是“汉语方言分区的开端”[2]25。实际上,最早的两位学者并不是章太炎、黎锦熙,而是章太炎、刘师培。黎锦熙并不属于最早的学者,而是其后的学者。1900年,章太炎在《訄书》中将汉语方言分为十区,稍后又在《检论·方言》(1915)中改订成9种。而刘师培则在1905年《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把汉语方言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南音、北音及界乎南北之间者3种。第二层次具体为:
大抵北方语言河西为一种,则陕甘是也。河北为一种,则山西、直隶、安徽北境是也。界乎南北之间者,则淮南为一种,则江苏、安徽之中部及湖北东境是也。汉南为一种,则湖北中部、西部及四川东部是也。南方语言则分五种,金陵以东为一种,则江苏南境、浙江东北境是也。金陵以西为一种,则安徽、南京及江西北部是也。湘赣之间为一种,则湖南全省及江西南境是也。推之闽广各为一种,广西、云、贵为一种。[6]161
刘师培分区说比章太炎1900年的十区说只晚了5年,比1915年的九区说还早了10年,可以说章、刘二说几乎处在同一时期,然而,目前可见到的汉语方言分区中均漏收刘师培的汉语方言分区说。因此,在此有必要将刘师培的方言分区说列出并与章太炎的方言分区稍做比较。现将章太炎分区也摘述如下:
河之朔,暨于北塞,东傅海,直隶、山西,南得彰德、 卫辉、怀庆,为一种。纽切不具,亢而鲜入,唐虞及虏之遗音也。陕西为一种。明彻平正,甘肃肖之,不与关东同。 唯开封以西,却上。汝宁、南阳,今曰河南,故荆、豫错壤也;及江之中,湖北、湖南、江西为一种。武昌、汉阳尤啴缓,当宛平二言。福建、广东各为一种。漳、泉、惠、潮又相軵也,不足论。开封而东,山东曹、沇、沂,至江、淮间,大略似朔方,而具四声,为一种。江南苏州、松江、 太仓、常州,浙江湖州、嘉兴、杭州、宁波、绍兴,为一种。宾海下湿,而内多渠浍湖沼,故声濡弱。东南之地,独徽州、宁国处高原,为一种。厥附属者,浙江衢州、金华、严州,江西广信、饶州也。浙江温、处、台附属于福建,而从福宁。福建之汀,附属于江西,而从赣……四川上下与秦、楚接,而云南、贵州、广西三部,最为僻左,然音皆大类湖北,为一种。滇、黔则沐英以兵力略定,胁从中原,故其余波播于广西。湖南之沅州,亦与贵州同音。江宁在江南,杭州在浙江,其督抚治所,音与他府县稍异,用晋宋尝徙都,然弗能大变也。[7]496-497
可以看出,章太炎、刘师培对汉语方言的分区同中有异:相同的是:(1)具体分区上都主张将闽、广各为一种;(2)分区边线都是以省、区、府行政范围为大致边界。不同的是:(1)章太炎认为,陕西方言为一种;刘师培则将陕甘合为一种;(2)章太炎将彰德、卫辉、怀庆与直隶、山西划为一种;刘师培则将安徽北境与直隶、山西归为一种;(3)章太炎将四川与云南、贵州、广西划为一种;刘师培则将四川东部同湖北中西部划为一种;(4)章太炎将湖北同湖南、江西列为一种;而刘师培却将湖南、江西南境列一种,而江西北部却同安徽、南京列为一种。结合后来李荣先生的汉语方言分区,发现章、刘的汉语方言分区各有千秋,都有可取之处,如彰德、卫辉、怀庆府等豫北方言,属晋方言区,章太炎将其与山西方言列为一种,这一点比较可信,而且章太炎文中有关社会历史原因的分析也较为符合史实,后续分区中也多有借鉴;而刘师培在给汉语方言分区时,首先区分南北差异,这一点比起章太炎的十区说,显示出一定的层次性。
由于受时代局限,章太炎、刘师培汉语分区说稍嫌粗略。如刘师培在为汉语方言分区时,只描述了各类方言通行的区域范围,没有说明部分方言的语音特点和形成原因,分区的范围描述也不精致,比如以金陵东西为界的提法。章太炎虽然简单说明了部分方言的语音特点和形成原因,但由于并未给方言分区命名,因此,也缺乏一定的准确性与层次性。正如王福堂在评价章氏分区时指出:“方音差异由水土不同造成的看法则出于传统,缺乏科学性。”[2]54这些评价都是中肯的。
在此基础上,再来看黎锦熙将汉语方言分为四区十二系的特点(2)在章、刘分区说提出之后,还有胡以鲁1912年的十区说。因胡以鲁大都沿袭其师章氏的观点,故本文从略。。黎锦熙四区十二系的分区方法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准确性。李荣[8]曾指出,汉语方言分区有6种命名方法,包括:用市县地区名、旧郡府州名、山河湖泊命名、省区之别名或简称加方位词、省市区的别名和新旧地名的首字联合等。章太炎、刘师培基本上选择了省市区的别名、别名加方位词或简称加方位词、旧郡府州名等形式为汉语方言分区命名。黎锦熙则选择了以四区统领十二系的方式为汉语方言分区命名。这种分区方式不仅指出了各方言分区的具体政区范围,还首创以江河湖海的方式命名,以江河湖海所经流域为汉语方言分界,简单易辨,且具有一定的准确性与概括性。众所周知,江、河、湖、海作为地理屏障,会阻断交通,阻隔社会交往,这就较容易形成方言分歧,如长江下游的开阔江面就将现代吴语和官话分隔于大江南北;再如汉水流域就不同程度地保留有中原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湘语、赣语等多种语言成分[9]。因此,相比章、刘二位单纯以省、府范围划分,黎锦熙四区十二系说充分考虑了江河湖海在汉语分区时的阻隔与沟通,具有明显的准确性与概括性。
(2) 层次性。20世纪80年代,李荣主持编制《中国语言地图集》时提出“方言分区要有一套合适的名目,包括层次的名目与方言的名目”,并指出汉语方言区划最多分为5个层次,分别是大区—区—片—小片—点,其中区、片和点是最基本的[8]。黎锦熙首先将汉语方言分为四区,分别是北方官话、南方官话、苏浙一带、东南滨海区域,然后又以这四区统领十二系,再以河流、水道、流域分别统领数省域的州府辖区,显得层次井然。这与李荣提出的汉语方言五个层次说理念一致,都颇为注重汉语方言分区的层次。这也充分说明黎锦熙分区方法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与科学性。当然,刘师培率先关注到汉语方言的南北差异,但经过与刘师培比较,容易发现黎锦熙1924年的分区不仅有所因袭刘先生观点,重点还有诸多突破,如不单单分为南北差异,同时还关注到苏浙一带、东南滨海区域与南方官话彼此的不同。同时,黎锦熙虽然注意到了闽北与闽南的差异,但他把福建的闽江流域、南及漳厦和广东的潮汕一带归为闽海系(约为后来的闽语区)。这一分区方法与后来丁邦新[10]、李荣[8]关于闽语的分区思路基本一致,都是先将闽语作为一个大区处理,在下一级分区时,再作区域内南北差异处理。
二、 以中古入声今读作为汉语方言分区标准的前瞻性与科学性
随着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方言资料日益丰富,汉语方言的分区标准也就成为汉语方言学家讨论的共同话题。不同的分区标准代表着不同学者对汉语方言的不同看法。有的方言学者希望用单一标准将缤纷复杂的汉语方言区分开,如李方桂(1937)曾提出以中古全浊塞音和塞擦音声母的演变作为现代汉语方言分区的标准[11],也有学者主张用多项标准,如王福堂[2]58-65,当然,也有学者主张“以多项标准立区、单一标准划界”[12]。然而,截至目前,随着各方言区材料的日渐丰富,方言边界的日渐明朗,各方言分区标准的争议却越来越大。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汉语方言分区也有可谓成功的先例,如李荣对汉语官话次方言的划分[13]。
众所周知,李荣依据入声的今读情况将晋方言从北方官话中划分出来,列为一级方言区,并进一步依据中古入声字今声调归派情况将官话分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八大官话区。但李荣将入声作为分区标准的理论源泉又是什么?文中并未提到,正如李荣说:
一九五六年我还不敢说,上述古入声演变的七种方式可以作为官话方言分区的依据。经过一九五七年开始的汉语方言普查,看到的方言资料渐渐多了,我才有那种想法[8]。
至于李荣看到的方言资料是否包括黎锦熙的论著,已不得而知,但从黎锦熙的著作中,我们看到有关现代汉语方言分区中入声韵与入声调的较早论述。现摘述如下:
东南半壁,北起淮阳,南浙而包举苏浙瓯闽,讫于奥海,方音虽千差万别,却都有明显的入声;他们说话,有时上去两声不能辨别,惟独入声是他们的语言之神,假使一旦缺了入声,便简直地不能过日子。溯江而上,赣江湘江两流域语言最杂,时而入声了然,时而入声消失。(例如湘江下游语音很相近的区域有数县,而长沙、湘潭则入声了然,似京音的上声;湘阴、益阳则入声消失,与其本地的去声无异)讫于阳、夏,便成中心。东则皖、宁隶与淮、扬,为有入声的南方官话,不过,他们的入声只近于苏浙的‘短促急收藏’,用罗马字母拼音时,常以‘h’【按:今国语罗马字用‘q’】煞尾;而不同于闽粤的‘带声之韵’,可以与收音于‘ng’‘n’‘m’的字相对配,而成字尾的‘k’‘t’‘p’。阳、夏以西,统括荆、襄、辰、沅以及川、滇、黔、桂,大体上为无入声的南方官话,其入声大都一律并入阳平;然而对于北方官话之把入声各字分配于阴平、阳平、上、去各声,也就大感其不便[4]157-158。
以上述论显示,不同区域的入声不同,或韵或调。根据入声这一标准,汉语方言似乎可以分为不同区域,如派入四声的北方官话;以“h”煞尾的南方官话中皖、宁隶、淮、扬等地,归入阳平的荆、襄、辰、沅、川、滇、黔、桂等地;离不了入声的“东南半壁”;“短促急收藏”的苏浙方言;“带声之韵”的闽粤方言;时有时无的赣江、湘江。可见,黎锦熙不仅注意到了皖、宁隶、淮、扬等地的入声塞音韵尾明显不同于东南半壁闽粤、苏浙地区,也注意到了阳、夏以西(统括荆、襄、辰、沅以及川、滇、黔、桂)等地入声调的归派不同于其他北方官话。虽然,李小凡指出,黎锦熙的分区并未说明依据的什么标准[3]25,但是,我们从上段论述中可以看出不同方言区域入声的差异。这段文字最早出现在1923年,黎锦熙四区十二系的提出是在1924年,他完全有条件借鉴自己1923年的成果,而且他提出在以四区十二系方言分区推广“国语”教学的时候,在每一区、系中都提到了声调要“因地制宜”,如[5]82-88:
(1) 北方官话三系:“可以按照北京的教学法、读法、话法,不必分离。无论说话、读书,都用普通的词类语句、标准的国音、北京的语调。”
(2) 南方官话四系:“要用普通词句和国音,但四声和词调、语调就可不必拘泥……不妨随时用国音矫正他们说话的字音,渐渐地模仿标准的声调——在这四系区域内的习惯读音,惟有江湖系地跨湘江、赣江两流域,因为数百年来,族姓转徙,最为频繁;又比江淮、江汉两系的区域,山地较多;交通不便,所以土语土音,实在复杂得很……至于金沙系的区域……语言倒很纯正而普通,与江汉系、河西系很是接近;不过声调异于北方官话罢了。”
(3) 苏浙和东南滨海五系:“教学读法时,要用喷涂后的词句;但事势上,若过于困难,暂时可不必一定依著国音……然而这种读法之外,必须另加语法时间,完全依著国音和北京的声调,教学国音。平常说话,自然不能就把土语方音彻底改变,但须使儿童能操两种语言:一种是本地习用的方言,一种是统一标准的国语。”
因此,黎锦熙四区十二系的汉语方言分区不可能没有考虑入声调的情况。丁邦新也曾提到,先生们在讨论汉语方言时提到个别方言的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自然也就是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10]166-167。虽然利用入声这单一标准受到了许多学者的争议,如丁邦新[10]、王福堂[2]、王临惠[12],但放在20世纪初,方言资料相对短缺的时候,能作出如此考虑,不能不说是一大贡献。
虽然黎锦熙这个考虑是在认定“国语”时提及的,并且也未明确标明将入声作为汉语方言分区的标准,但他从入声调的归派、入声韵的保留角度来考虑“国语”的认定,并关注到了汉语方言中入声的差异,这种想法确实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最起码,可以说是黎锦熙根据入声这一标准,从许多方言里排除了诸多方言定为“国语”的可能。这与后来李荣用古入声今声调归派为官话分区标准的“想法”不谋而合,共存共现。
自黎锦熙关注到入声在汉语方言演变中的差异后,后续诸多学者在为汉语方言分区时也多会选择入声作为分区标准,如1936年王力在《中国音韵学》中用一组音韵标准将汉语方言分为五大系,这组音韵标准就有入声韵尾情况、声调的种类(3)1956年后改为《汉语音韵学》。[14]377-382;丁邦新以古塞音韵尾-p、-t、-k的演变作为早期历史性条件来区分大方言区,以古入声(调)的演变作为晚期历史性条件来区分次方言区,这二者也都是汉语方言分区的普遍性条件[10]。结合上文李荣为汉语官话方言分区的成功经验。这些似乎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在四区十二系分法中,黎锦熙充分考虑汉语方言中的入声差异,并有所考虑入声在汉语方言分区中的作用,确实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科学性。
黎锦熙在说明北方官话区域时,提到河北系中的直隶、山西,特别指出了“太原一带土语较多”,指明山西腹地方言的特殊性。直到50年后,李荣从官话中将以“太原一带土语”为代表的“晋语”分立出来。黎锦熙50年前的提法不无体现出前瞻性。
三、 汉语方言分区服务于北京标准音规范与推广的全局性与开创性
近代汉语方言的分区工作似乎一直伴随着汉语标准语的规范而出现,如20世纪初的“国语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有胡以鲁、黎锦熙。胡以鲁于1912年在《国语学草创》中将汉语方言分为10种(4)本文《国语学草创》使用的是1923年版本。,虽然他同他的老师章太炎一样,都因没有为这10种汉语方言命名而有一定的局限性[15],但他却首要明确了这次汉语方言分区的目的:“故兹所取,惟略得统一于国语之下方言,即内范略同,外范之差亦得推量源委者。”[16]92-93并进一步提出:“于是保守者谓为地方精粹之所存,且表彰思想惟方言最为适切,则不如各保其自然。以言表彰思想之适切,诚莫方言若。然是在闭关之世老死不相往来则可也。世界交通以国家社会为单位。统一教育尤宜以统一国语为先务。”[16]94,也即胡以鲁主张汉语方言分区应统一于国语之下,并为国语统一服务,但如何实现“国语”统一,却并未给出明确方案。
黎锦熙与胡以鲁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工作都是源于20世纪初“国语”的认定与推广。然而,黎锦熙却与胡以鲁有所不同。黎锦熙主张通过“国语”教学,推广国语,主要方法在于结合方言特征,因地制宜。如黎锦熙在推广“国语”语法教学的时候指出,南方官话江湖系、江淮系、江汉系的土语较为复杂,在“国语”教学时可不必拘泥,而像苏浙一带、东南滨海区域方言更是可以让土语与国语共存。这一点更能表明黎锦熙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目的:统一“国语”不是为了消灭方言,而是为逐步实现汉语的规范化;汉语方言分区的目的也不单单是为了统一“国语”,而是为了弄清汉语方言差异,认定“国语”,并进一步针对性地实现“国语”的推广。可以说在当时,黎锦熙在国语教学法上的这一理念极具全局性与开创性。
到了建国初期,在各地党、政、文教部门的具体领导下,开展了以每县为一个调查点的汉语普查工作,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汉语方言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各省(自治区)着手编写了一些概括全省(自治区)汉语方言面貌的作品——《xx省(自治区)汉语方言概况》。直至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方言音韵的研究资料异常丰富,研究方法日益多样,研究成果斐然可观[17]。无疑,这些成果都切实地加强了普通话工作的推广。黄家教、詹伯慧、陈世民就曾说过,“一句话,科学的方言分区能使各地人民清楚地了解自己方言的亲属。同时,从语言研究的需要来说,科学的方言分区还会有利于咱们掌握各地方言的特点,从而因势利导地促使各地方言向共同语集中,早日实现汉语规范化这一伟大理想”[18]。由此可见,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历来与汉语标准语的规范统一密不可分。换而言之,科学汉语方言分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标准音的推广,并逐步实现汉语的规范化,而教学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之一。
然而,在20世纪初的“国语”运动中,到底以何种语音为汉语“国语”标准音进行教学,时人争议还是较大的,争议的焦点是南方方言中浊音与入声在“国语”中的存废问题。胡以鲁说到,“标准语标准音者,欲统一国语认定特定之语词语法,特定之读音,为一般用语之准也。”[16]91-92因此,他认为应该以湖北官话为标准语,理由是:
湖北之音,古夏声也,未尝直接北患之激变,常作南音之代表。颜氏家训谓南方言杂吴楚,北方言杂建朔,固也。然吴楚当晋时已同化于中国,非建比也(陵堃氏之说)。况夏口之音由来扩张其势力,为他言他音所纷乱者少。所谓江汉之音,春秋时已见扩张之轮廓,至吴晋弓朋张益著,晋室东迁,遂与中原翕合为一大势力。尔来北音激变,湖北独然屹然保障江左。南北朝之南部,宋之南迁,中原音流入于南,夏口实保障之。北方激变,闽粤沿海块杂,中心其在斯乎。此理论也,实际亦如是。十方言之中,自闽粤吴越等沿海外,大抵皆略与湖北近,以其比较上纯粹而中和也。交通上又为吾国之中心,其发达正方兴而未艾。故以之导用于国中,似较京语为利便。云贵之事可鉴也。[16]98
然而,黎锦熙并不这么认为,他指出:
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语言中之一种;也不就把这几百年来小说戏曲所传播的‘官话’视为满足,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平的方言。北平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这也是自然的趋势,用不着强迫的:因为交通上、文化上、学艺上、政治上,向来都是把北平地方作中枢,而标准的语言照例必和这几项事情有关系,然后内容能丰富,可以兼采八方荟萃的方言和外来语,可以加入通俗成语和古词类;然后形式能完善,可以具有论理上精密的组织,可以添加艺术上优美的色彩。这仿佛是一种理想的语言,但北平的方言,因环境和时代的关系,实已具有这种自然的趋势,所以采定北平语为标准国语,比较地可算资格相当。(原文‘京’,今改‘平’)[4]16
这段表述说明:黎锦熙主张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国语”进行推广,因为他认为北京语音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与优势。国语运动大家劳乃宣曾提出国语统一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方言统四”(京、宁、苏、闽广),第二步“国语统四”。黎锦熙直接将两步走策略改为一步走,即直接选择“自然的语言中一种”——北平方言作为国语标准语并加以推广。因此,黎锦熙在为汉语方言分区的同时,也将北京语音从纷繁复杂的汉语方言中给选取出来,定为“国音”,并“主张径把很爽快干脆的北京声调为标准”加以普及与推广[4]156,也即“京音京调”的推广,这恐怕在“国语运动”中首屈一指。实际上,从“国语”标准音选择北京语音再到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可延续式推广,这一事实业亦证明:黎锦熙在“国语运动”时期以北京音作为共同语标准音的选择极具全局性与开创性。
综上所述,虽然黎锦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进行推广是为了“国语”的统一规范,但是正是这一目的,才促成了“四区十二系”的汉语方言分区法;也正是这一目的,才促使建国之后的汉语方言分区工作紧紧秉承为汉语规范化而服务的目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黎锦熙选择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并加以推广也多具有奠基之劳、开创之功,如果说没有“国语”标准音教育推广这一目的,也不会有日渐丰富的汉语方言分区理论。
本文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成果,曾在2021年3月20日汉中举办的纪念黎锦熙先生诞辰130周年暨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上报告,感谢与会的马庆株、王远新等专家的点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