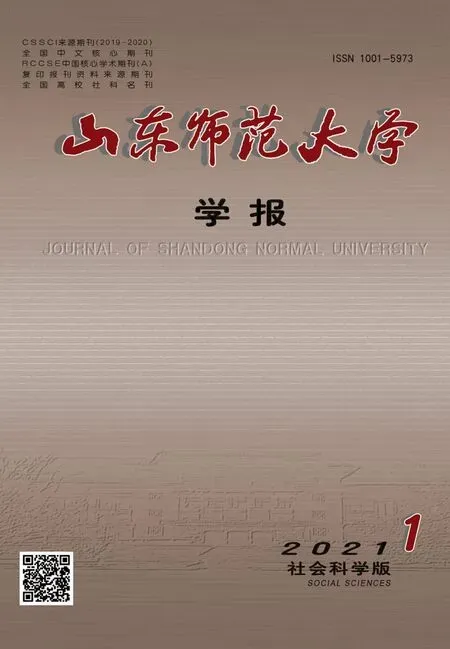李攀龙的结盟意识与文学权力复归郎署*①
薛 泉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
明朝嘉靖后期的主流文风转向,李攀龙的发轫之功不可磨灭。目前,这一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多维度、立体化态势,成果也较为丰硕。然而,却鲜有研究者从李攀龙结盟意识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文学权力复归郎署的探析来揭示这一问题。这不仅制约了李攀龙研究的深入,也阻碍了对明代文学发展演化的深层次体认和整体性把握。因而,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文所谓的结盟意识,主要是指行为主体对结盟目的、结盟方式、结盟策略、文学主张的体认,以及盟主、盟员间的认同(包括自我认同与相互认同)、盟员的归属感等心理过程的总和。文学结盟可以在盟主的号令下,有组织、有计划地整合群体力量,强力推行某一文学主张,制造文学震撼效应和文学景观,赢得文学话语权。嘉靖后期的文学权力(1)文学权力的内涵较为复杂,因行文所限,这里不展开论析。本文所谓的文学权力,主要指文学话语权,即掌控文学舆论、引导文学风向以及文学影响的一种特殊文化权力。鉴于此,二者在文中时而互用。复归郎署,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李攀龙的结盟意识。
一、自觉的结盟意识与盟主地位的确立
无论何种形式的结盟,都需要有强烈结盟意识的领袖人物,需要有盟主的引领,这在李攀龙身上表现得较为突出。李攀龙多次以“吾党”相标榜,便是较明显的表征之一。他所谓的“党”,主要指文学主张相同或相近者缔结成的联盟,即文社或文学流派。李攀龙的结盟意识,首先表现为一种居高临下的主盟意识。初识王世贞时,他便约之道:“仆愿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与左氏、司马千载而比肩。生岂有意哉?”(2)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92页。其敢为人先、主盟文坛的强烈意图显露无遗。《与王元美》则直接宣称:“惟是不佞敢谓与足下狎主齐盟哉!”(3)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28页。“狎主齐盟”一语,源于《左传》。《左传·昭公元年》:“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主齐盟,其又可壹乎?”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4)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一、卷三十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18、1219页。意谓诸侯之势,时有强弱,更相主盟,强者为尊。李攀龙援引此语,其主盟意识之强烈,毋需多言。在《戏为绝谢茂秦书》中,他当仁不让地宣称:“我与元美狎主二三兄弟之盟久矣。”(5)李攀龙撰、李伯齐点校:《李攀龙集》(卷二十五),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第560页。至于“四海而一人焉,是比肩而至也,何有于我也”(6)李攀龙:《送宗子相序》,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01页。一类的话语,表面上看似谦让,实则骨子里蕴涵着浓烈的主盟意识。
李攀龙主盟意识的终极目标是主盟一代文坛。为此,自信与自负,必不可缺少,至少他以为如此。从其“少年多时时言余”“故五百年一名世出”“故能为献吉辈者,乃能不为献吉辈者乎”(7)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92页。之类的自白中不难领略。他还“尝慨然称少陵氏没千余年,李、何廓而未化,天乎!属何人哉”(8)王世贞:《明诗评》(一),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3册),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2002页。,本意显然在于“属”己。极端的自信、自负,多易于滑向狂妄,《寄元美》称:“寥落文章事……微吾竟长夜。”(9)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1页。出言如此,可谓狂妄至极,无怪乎朱彝尊以“妄人”(10)朱彝尊著、姚祖恩编、黄君坦校点:《静志居诗话》(卷十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81页。称之。李攀龙本人于此也有清醒的意识,《与许殿卿》:“夫好比文角艺者出于妬,妬出于不自信。龙也其妄自信,奚啻先告子不动心?”(11)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二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00页。或许他以为,这正是成为盟主必须具备的。
欲主盟文坛,需要物色一批忠实的羽翼追随自己左右。李攀龙深知其难度之大,尤其是在短时间内使他人舍其所学而从己,可谓“日莫(暮)途远”。况且,那些已有成就者,又“奚肯苦其心志于不可必致者乎”。(12)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92页。尽管如此,他还是潜心笼络一己钟意之人选,以及有意向其靠拢的名士。嘉靖二十六年(1547),授刑部广东司主事后,他利用“曹务闲寂,遂大肆力于文词”,并广“交一时胜流”(13)殷士儋:《嘉议大夫河南按察使李公墓志铭》,《金舆山房稿》(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783页。,有意识地物色人选。王世贞、徐中行二人很快入其法眼。作为名家“胜流”的王世贞,由李先芳得知李攀龙的志向,慕名造访;于稠人广众中,李攀龙便“心知”王已心向于己,并与之相约“狎主齐盟”。他抑制不住内心喜悦,对王世贞道:“今乃得一当生”。(14)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92页。徐中行“以进士初官刑曹,即有能诗声”(15)俞允文:《青萝馆诗序》,《仲蔚先生集》(卷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35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98页。,李攀龙也颇为青睐之,并很快地网罗其于麾下。他曾非常得意地对徐中行说:“吴越一撮土,乃有两生奉一不佞。”(16)李攀龙:《与徐子与》,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21页。两生,即王世贞、徐中行。经其奋勉,王世贞、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吴国伦等人,“皆先后缔交”。(17)王世懋:《徐方伯子与传》,《王奉常集·文部》(卷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59页。
物色羽翼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李攀龙博得加盟者认同、并被奉为盟主的过程。较早加盟的王世贞对他甚为推崇。初入文坛时,王世贞自称,只服膺李攀龙一人:“记初操觚时,所推先唯一于鳞(李攀龙)。”(18)王世贞:《吴瑞穀文集序》,《弇州山人续稿》(卷五十三),《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7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74页。他最伏膺李之诗:“仆生平所伏膺,文则伯玉,诗则于鳞。”(19)王世贞:《潘景升》,《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八十二),《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9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208页。他以为,李“之于诗,志在超乘,其游吾侪间,矫矫牛耳矣”(20)王世贞:《海岳灵秀集序》,《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6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554页。,还诚服其“能称说古昔”,故“以牛耳归之”(21)王世贞:《书李于鳞集后》,《弇州山人读书后》(卷四),《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9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556页。。王氏还称,其“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也是在与李“始定交”后。(22)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68页。王世贞对李攀龙的推崇,甚至到了顶礼膜拜之地步:“世贞二十余,遂谬为五七言声律。从西曹见于鳞,大悔,悉烧弃之。”(23)王世贞:《上御史大夫南充王公》,《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三),《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84页。悉焚旧稿,意味着对自己先前诗歌创作的自我否定,也是对李攀龙高度认同的表征。之所以奉李攀龙为盟主,除诚服其文学造诣,还与知恩图报有关。王世贞曾言于汪道昆:
平生知我者三,始则于鳞……余何能修古,夫夫摈之相之,趋则让趋,步则让步,左提右挈,相与狎主齐盟,则于鳞之为也。(24)汪道昆:《祭王长公文》,汪道昆著,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卷八十三),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707-1708页。
王世贞以为,因有李攀龙的提携与奖掖,自己才能在“修古”路上有所斩获,才有幸“相与狎主齐盟”。由心生感激而奉之为盟主,自在情理之中。
在王世贞看来,其他加盟者也同样视李攀龙为盟主。万历四年(1576),王世贞序徐中行之《青萝馆诗集》称:
记不佞初识子与(中行)时,子与业已壮,有游大人名,而一旦见于鳞而悦之,尽弃其学而学焉。即有搆,而亡近于建安、三谢、开元、大历弗出也,出而亡当于于鳞之首肯弗存也。(25)徐中行著、王群栗点校:《徐中行集·青萝馆诗》(卷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84页。
与王世贞一样,在结识李攀龙后,徐中行也“尽弃其学”而从之。其诗文的存留,也以能否为李攀龙“首肯”为准绳。由此,徐中行显然已视李攀龙为盟主。其他的加盟者,也大抵如此。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载:
其(于鳞)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誉、不佞世贞及吴舍人国伦、宗考功臣,相与切劘千古之事,于鳞咸弟蓄之;为社会时,有所赋咏,人人意自得,最后于鳞出片语,则人人自失也。(26)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49-850页。
在凸显李攀龙“咸弟蓄之”的同时,双方地位之悬殊,也展露无遗。“于鳞出片语,则人人自失”,意谓包括王世贞在内的加盟者,皆甘拜下风,奉李为盟主。
那么,王世贞的论断,是否出于其为李攀龙推毂,而心生感激的虚美之辞呢?从当时所引发的广泛共鸣观之,答案应是否定的。王世懋《徐方伯子与传》载,李、王“方力为古诗文自振”时,徐中行至,“大悦其说”,遂与之“缔交”。(27)王世懋:《王奉常集·文部》(卷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59页。又,隆庆四年(1570)冬,汪道昆撰《青萝馆诗集序》称:“子与严事于鳞、元美,直将尸而祝之。”(28)徐中行著、王群栗点校:《徐中行集·青萝馆诗》(卷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82页。尸祝,即祭祀时主读祝文者,这里借指盟主。汪道昆为徐中行所撰墓志铭称:“于鳞以修古先鸣,盖与元美为桴鼓”,“子与相得甚欢,恨相知晚也。”(29)汪道昆:《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徐公墓志铭》,汪道昆著,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卷五十一),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071页。“桴鼓”,鼓槌与鼓。语本之《韩非子·功名》:“至治之国,君若桴,臣若鼓。”(30)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52页。以“桴鼓”称喻李攀龙与王世贞同气相应,而徐中行自愿追随左右,奉李为盟主。其实,徐中行本人早已坦言,《五子诗·李郎中攀龙》有曰:“众星何历历,周环随北辰。遂令同心者,周旋若一身。”(31)宗臣:《宗子相集》(附录),中国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496页。以众星之拱北辰,喻诸子与李攀龙之关系,盟员与盟主身份之定位,清晰可见。徐中行《重刻李沧溟先生集序》又称:
比讲业阙下,王元美与余辈推之坛坫之上,听其执言惟谨,文自西京以下,诗自天宝以下不齿,同盟视若金匮罔渝。(32)徐中行著、王群栗点校:《徐中行集·天目先生集》(卷十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46页。
“听其执言惟谨”,视其文学观念“若金匮罔渝”,表明李攀龙已成为公认的盟主。这也并非徐氏一家之言,当时入盟者,多有如此表白。万历十二年(1584 ),张佳胤撰《天目集序》:“自嘉靖文事兴,于鳞称盟主。”(33)徐中行著、王群栗点校:《徐中行集》(卷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页。上文提到的汪道昆,又何尝不如此!其《李于鳞》:“足下主盟当代,仆犹外裔。”(34)汪道昆著,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卷九十七),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980页。自陕西归居济南后,李攀龙的声望益隆,盟主地位愈加稳固,“自时厥后,操海内文章之柄垂二十年”(3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28页。,他已由一个流派的盟主,发展成为当时的文坛宗主。
如徐中行所言,李攀龙能成为盟主,与他和王世贞等人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隆庆四年(1570)秋,陈有守撰《青萝馆诗序》,也言及于此:“弘德时李献吉、何仲默相叹,大雅久已不作,伊余其力追挽之。天挺李于鳞、王元美,嘉靖中倡廓古风,持鞭弭雄视中原。徐子与前茅后劲。”(36)徐中行著、王群栗点校:《徐中行集·青萝馆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79页。钱谦益则更看重王世贞:“(李攀龙)宦郎署五六年,倡五子、七子之社,吴郡王元美以名家胜流,羽翼而鼓吹之,其声益大噪”(3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28页。。李攀龙对此也不讳言,他向徐中行坦言道:“吴越一撮土,乃有两生奉一不佞,并立中原,比肩千载,图盛事者邪?”事实上,李攀龙能成为一代盟主,是诸子共同拥戴的结果。这从徐中行“众星何历历,周环随北辰”的诗句中不难理会。宗臣誓与诸子“共励斯盟”(38)宗臣:《报张范中》,《宗子相先生集》(卷十九),《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28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201页。,也透出些许这方面的讯息。
作为盟主,李攀龙虽为人孤高,但很注重培养后继盟主,这是其主盟意识的延伸。他深知,要使自己的文学主张发扬光大,必须后继有人。结交之初,他就颇看好王世贞,视之为“吾党后贤”(39)李攀龙:《与徐子与》,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13页。,欲与其“狎主齐盟”,并大力提携之。王世贞于此也心领神会,称李攀龙于己“趋则让趋,步则让步,左提右挈,相与狎主齐盟”。在过世之前,李攀龙就已视之为二号盟主:“我与元美狎主二三兄弟之盟久矣。”王世贞也自觉当之无愧,在《王氏金虎集序》中,他自诩道: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徐国伦等人,“咸慷慨自信于海内,亡所许可,独称吾二人者千古耳”。(40)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十一),《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4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176页。这不能不说,李攀龙的结盟意识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开放性。
二、狭隘、偏激的文学主张及严苛的行为规范的推出
李攀龙的主盟意识及其盟主地位的确立,主要凭借的是重申前七子郎署文学旗帜。《明史·文苑一》称,至嘉靖时,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41)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07页。。不仅如此,李攀龙还奉李梦阳、何景明为宗,且“于本朝独推李梦阳”(42)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78页。,甚至以不与李氏等生于同时而遗憾。汪道昆曾追忆道:“于鳞谓余:‘吾党亟称献吉,恨不与诸君子同时。不自意结伍从之,取前茅以进,幸也。’”(43)汪道昆:《青萝馆诗集序》,汪道昆著,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卷二十一),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459页。“吾党”,表明重申前七子的文学主张,不只是李攀龙个人的心声,也是汪道昆与其他盟员的共同心愿。其实,徐中行所谓“文自西京以下,诗自天宝以下不齿,同盟视若金匮罔渝”,已道明于此。这也是李攀龙与诸子相约“狎主齐盟”、结盟立派的文学主张,但较之前七子,更显狭隘、严苛,也更为偏激。
时间断限上,前七子强调的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尤其是李梦阳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到了李攀龙那里,时段变得更短。殷士儋为其所撰墓志铭称之:“盖文自西汉以下,诗自天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也。”(44)殷士儋:《嘉议大夫河南按察使李公墓志铭》,《金舆山房稿》(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782-783页。钱谦益转引殷之语,稍事改易谓:“高自夸许,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污我毫素也。”(4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28页。在此,“两汉”已缩短成“西汉”,“盛唐”改缩为“天宝”。王世贞于此极为认许,干脆称:“李于鳞文,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46)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63页。他还特别声明,自己在结识李攀龙后,才“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徐中行“遂取旧草,悉焚之,而自是诗非开元而上,文非东、西京而上,毋述”(47)王世贞:《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天目徐公墓碑》,《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三十四),《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8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307页。,也发生在结交李攀龙之后。从中可见李攀龙对诸子影响之深远。
宗法对象与风格上,李、何等虽主要以盛唐为宗,且定格于李、杜等大家,但于盛唐诸家,还各有师取。宋征舆即云:“何、李刻意少陵,迪功独宗太白,神到之作,自能成一家言。”(48)上海文献丛书编委会编:《皇明诗选》(卷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5-66页。李攀龙等人则集中指向模拟杜甫,即使同宗杜甫,其过分注重“规仿”技法,造成“神理不存”,又甚于李、何。(49)鲁九皋:《诗学源流考》,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58页。廖可斌也指出,“前七子也最崇盛唐,但于盛唐各家中还各有所师,后七子则集中于学杜甫”,即便是同宗杜,后七子只学其“骨力风格”,“连任何变体、变格都排除在外,只学一体,只守一格,严重的重复雷同就成为必然结果了”(50)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27页。,洵为不易之论。
技法追求上,李攀龙主张,为文作诗应墨守前人陈规,不越绳墨。嘉靖三十六年(1557),李攀龙序王维桢《存笥稿》,称之“为文章其用心,宁属辞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于绳墨”(51)王维桢:《槐野先生存笥稿》(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34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页。。这何尝不是其心迹的外露!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李攀龙的为文技法。李攀龙认为,为诗作文须讲技法,“不以规矩,不能方圆”,古人已“法则森如”,后人意欲标新立异,已无可能,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损”。当下之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学习、模仿而已,能做到“摭其华而裁其衷,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52)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十三),《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4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301页。,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这直接启迪了王世贞:“文繁而法,且有委,吾得其人曰李于鳞。”(53)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63页。
在对待宋元诗文的态度上,李攀龙极为排斥,认为文自西汉以下、诗自天宝以下尚不足论,更无论宋元诗文。就诗歌而言,他认为,“诗歌自西京逮于唐大历,代有降而体不沿,格有变而才各至”(54)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十三),《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4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301页。,其后的诗作“格以代降”,一代不如一代,自然不必效法。如李、何一样,李攀龙所以贬抑宋诗,还因其言理不言情。不过,李攀龙批判的对象更明确、更有针对性。他曾点名批评道:“晋江、毗陵二三君子……持论太过,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胜相掩。”(55)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91页。此论主要针对王慎中、唐顺之等唐宋派诸子而发。
文学主张须经宣传与践行方可能实现其期望值。除直接宣传与写作外,李攀龙还借助选本这一媒介增强宣传效果。《古今诗删》为李攀龙“取其独见而裁之”(56)王世贞:《古今诗删序》,《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七),《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4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135页。的选本,是其文学主张的宣言与践行。是选凡三十四卷,一至九卷为古诗,十至二十二卷为唐诗,二十三至三十四卷为明诗,宋诗则阙如。四库馆臣释之曰:“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5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17页。以明诗直承唐诗,不选宋元诗,进一步突显出李攀龙诗学主张的严苛。
总体上看,李攀龙的文学主张,在时间断限、宗法对象与风格选择、技法追求、排斥宋元诗文等方面,较李梦阳、何景明等愈发严苛、偏激。宋征舆就指出,何、李“不若嘉靖时七子同境也”(58)上海文献丛书编委会编:《皇明诗选》(卷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6页。。尽管如此,李攀龙的这一主张还是得到了加盟者的一致认同,且内化为共识,成为金科玉律:“文自西京以下,诗自天宝以下不齿,同盟视若金匮罔渝”。
需要说明的是,李、何的文学主张也很严格,但只是未能很好地落实。尤其是流派成员相对自由,可发表不同的见解,如何、李之争。这从内部消解了流派的凝聚力,从而分化出不同诗学倾向与文学流派。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李攀龙因此杜绝加盟者发出不同的声音。确如廖可斌先生所言:
前七子复古派也正因为持论不十分严格,从而分化出六朝初唐派与中唐派,并最终导致了复古运动的自我泯灭。后七子复古派作家鉴于这一教训,持论更严,趋向更专一,然而又因此走进了题材、体裁、风格更加狭窄单一的死胡同。李攀龙在复古派阵营内像一个专横的家长,稍持不同意见的成员,如谢榛,都要受到严厉处罚。(59)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26-327页。
谢榛受到严厉处罚,是李攀龙在同盟内部推行严格行为规范的必然结果。为保证文学主张的严格落实,李攀龙对加盟者之要求相当苛刻,严格规范其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王世贞加盟之初,就被告诫,要与吴中派保持适当的距离。王世贞《明诗评》记之曰:
于鳞顾折节与余好,居恒相勉,戒吾子自爱,吴人屈指高誉,达书不及子,子故非其中人也,予愧而谢之。(60)王世贞:《明诗评》(一),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3册),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2002页。
由于对王世贞寄予厚望,而王又来自吴中,李攀龙不能不有所顾虑。他担心王世贞与吴中文人走得太近,不利于其文学主张的推行。同时,也是在婉转地提醒他,加盟后要尽快脱却吴地文风。实际上,这是要求加盟者不得有他涉,要“绝他游好”而“一意行其说”。尽管如此,却博得了多数加盟者的认可,并自觉付诸行动,这从王世贞“愧而谢之”可略见一斑。王世懋更感触良深:“诸君子既刻厉相责课,务在绝他游好,一意行其说。即流辈有时名者,视之蔑如也。”(61)王世懋:《徐方伯子与传》,《王奉常集·文部》(卷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59页。为了一意推行李攀龙之说,“诸君子”连时流名贤都不放在眼里。
若有人不守规范,可能会引发不愉快,甚至影响到自己在同盟中的地位。吴国伦的排名一度落在徐中行之后,就缘于此。王世懋就告之曰:“以足下有境外交,遂使子与得跻而上。”(62)王世懋:《与吴明卿》,《王奉常集·文部》(卷三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27页。对于李攀龙既不加深究,又不听解释,就认定自己有“境外交”,吴国伦很有怨言,他觉得李文多厚于情。(63)吴国伦:《复王敬美书》,《甔甀洞稿》(卷五十二),中国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2424-2426页。吴被认定有“境外交”,尚不止此次,其读《艺苑卮言》,发出“厚与吴中诸词家,而独遗一峻伯,故得微讽”(64)吴国伦:《报元美书》,《甔甀洞稿》(卷五十一),中国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2352页。之慨叹,就惹怒了李攀龙。后者援引王世贞之言,批驳道:“邵武(吴国伦)近稿辄不振,至乃阿党峻伯,以畔正始,岂其才之罪乎?”(65)李攀龙:《与徐子与》,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21页。吴则反驳道:“乃于鳞谓之党峻伯,君子亦党乎?”(66)吴国伦:《报元美书》,《甔甀洞稿》(卷五十一),中国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2352页。峻伯,即吴维岳,起初与李攀龙同社,后改学唐宋派,李大为不悦,以此结怨,且难以释怀,尽管吴氏后来主动寻求和解。(67)据王世贞《吴峻伯先生集序》,嘉靖三十七年(1558),吴维岳调任山东提学副使,此时李攀龙正辞官居家济南,吴自动造访,李却称病不复见。王世贞周旋其间,李言于王曰:“夫是膏肓者,有一毗陵在,而我之奈何?为我谢吴君,何渠能舍所学而从我。”吴维岳却不以为然,曰:“必是古而非今,谁肯为今者,且我曹何赖焉,我且衷之。”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五十一),《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7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46页。可见,诚如吴国伦所言,在李攀龙心目中,文学的分量已远在友情之上。
其实,在结盟之初,李攀龙就已表现得非常刻薄,并因此与李先芳产生摩擦。李先芳选录宋元诗,与王、李抹杀宋、元诸家诗的主张有异,引发李攀龙不满,并多次向人诉说泄愤。《与王元美》:“先是,得寄许殿卿者盈牍……李伯承走示新刻十本,寻为读之,推意就辞,未合而战,遂劣长驱,沾沾自爱也。”(68)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27页。《与徐子与》:“向约李伯承暮春者,我二人于日观之上赋相遇也。其人嫋嫋自爱,终恐三舍引避,安能顾草庐?”(69)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15页。李攀龙推定,李先芳不仅已背弃盟约,还“沾沾自爱”“嫋嫋自爱”。这是他断然难忍的,与徐中行的另一通书札,他愈发出言不逊:“日茂秦寄诗见怀,及伯承所贻新刻,并多出入,畔我族类。”(70)李攀龙:《与徐子与》,李攀龙著、包敬第标校:《沧溟先生集》(卷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14页。本为社友,因选诗观念之差异,就出语如此不近人情。谢榛被摒弃,踢出“五子”行列,也是因此。
可以说,李攀龙文学主张的严苛与行为规范的排他性,在一定时期内最大限度地维系着流派的纯粹与统一。但也必须清楚,任何一个社团或文学流派,其内部成员既要在创作上有意识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性,又要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二者不可或缺,还应尽量追求完美的遇合。若忽视或缺少前者,“则是环境对个体失去价值”,会失去维系社团或流派核心利益的内在动力,以致自我消解社团或流派的建构;若忽略或缺少后者,“个体使自己极度地等同于某一群体时,他便失去了自身的价值”(71)[美]奥尔波特:《人格:正常与反常》引沃纳·沃尔夫语,[美]马斯洛等著、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人本主义心理学译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92页。,就会泯灭创作个性,缺乏独创性。这也是李攀龙及后七子未能摆脱前七子命运的重要因素。
三、结盟意识与文学权力复归郎署
李攀龙之所以要以重揭李、何文学旗帜,结盟立派,作为主盟文坛的策略,除钦慕之情外,更重要的是其窥破文风转捩的契机。由于前七子及其末流的拟古不化,导致文坛陈陈相因、剿袭拟摹之风盛行,郎署文学权力大量流失。嘉靖初年,六朝派、中晚唐派、唐宋派乘势而兴,文坛呈现出“诸调杂兴”(72)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45页。的格局。为清除文弊,扭转文风,重振唐音汉响,李攀龙不失时机地重申前七子的文学主张,聚合同道,结盟立派。李攀龙等人一再提及的“盟”,即其组建起的文学社团。文社起初以“五子”的名义亮相文坛;后又以“七子”称之,是为后七子。
“五子”结盟后,名动京城主流文学圈。隆庆五年(1571),徐中行在滇闻李攀龙讣讯时,尚称:“先朝艺苑定宗盟,五子风流满汉京。”(73)徐中行:《滇南闻于鳞讣哭之四首》其一,徐中行著、王群栗点校:《徐中行集·天目先生集》(卷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欧大任《祭李于鳞文》也称:“李君挺起,独亢文宗。原本词骚,扬扢风雅。登坛齐盟,西揖作者。天目维徐,吴郡维王。广陵之宗,南海之梁。五子一时,天衢騕褭。”(74)欧大任:《欧虞部集·文集》(卷十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17页。不久,这种影响迅速由京师漫及全国。万历三十一年(1603),李维桢序吴国伦《甔甀洞续稿》称:“自先生与五子中兴,而趋向一归于正,天下翕然从风,非西京以下、大历以上,盻睐唇吻所不及。”(75)吴国伦:《甔甀洞续稿》(卷首),《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26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7-8页。这实表明,经李攀龙等人的努力,“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京以下”不齿,已成为文坛主流,前七子郎署文人散失的文权又归于郎署。对此,后七子郎署文人还有更明晰的表述。汪道昆《翏翏集序》言:
大方家有言,当世之诗盛矣,顾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不佞既然且疑,尝测其涘。(76)俞安期:《翏翏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页。
“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其潜台词即为文权在郎署。“大方家”,指王世贞。汪道昆《王弇州》即称:“当世斯文,下不在山林,上不在台阁。尝闻长公有是言矣。”(77)汪道昆著,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卷一百○四),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2163页。“长公”,即王世贞。汪道昆初闻王氏此言,“既然且疑”,后以为然,《送胡元瑞东归记》曰:“当世作者斌斌矣,顾上不在台省下不在山林。斯元美畴昔之言于余,心若有当也。”(78)汪道昆著,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卷七十七),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587页。“作者斌斌”,则标明当时郎署文学已蔚为大观。“心若有当”,标明汪道昆已经认同此说。俞安期《愍知》诗小序,论调也相类之:
自丁丑纳交,余始识搦管耳。秇林之业,方勺一蠡,公则知余进未可量,发醯鸡之覆,示解牛之全,命以十年业成相证。甫五年,余先以近业寄公,则已鼓掌大快,遍赞交知,称为速化。是时,弇州王公与公论文,慨我明斯道,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79)俞安期:《翏翏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2-13页。
丁丑,即万历五年(1577),俞安期与汪道昆“纳交”,在后者鼓励下,文艺大进;至万历十年(1582)年,已甚有成就。据此,王世贞发表“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的时间,当不晚于万历十年。
关于文学权力复归郎署,除后七子外,时人也多是认可的。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陈懿典《郭张虚诗稿序》云:
永陵中,李历城、王娄东六七人执牛耳,而号海内,海内靡然向风。当其时,分宜秉重,自以为作者。所推毂毗陵、晋江,皆一时名流,而竟不能夺王、李六七人之气,而拔其帜。(80)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二百七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835页。
“不能夺王、李六七人之气,而拔其帜”,说明后七子郎署文人已真正成为文权操控者。万历三十三年(1605),王图撰《槐野先生存笥稿序》亦云:
盖尝考览国初时台阁文体,类尚明析畅达,而其为诗亦冲夷俊美,颇借途宋人。而士大夫不在馆阁及布衣之雄,率乞灵秦、汉人口吻,与词林争胜。考其所作,大都刻画皮貌,剽窃影响,竞相涂抹,渐入支离,即所称海内七子,非不高自夸诩,然自历下、瑯琊而外,孰能为词坛执牛耳者。(81)王维桢:《槐野先生存笥稿》(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3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页。
“士大夫不在馆阁及布衣之雄”,即谓文权在郎署。王世贞、李攀龙等以“文必先秦、两汉”为策略,与馆阁争雄,虽不免流于“刻画皮貌,剽窃影响,竞相涂抹,渐入支离”,但“为词坛执牛耳者”,依然当之无愧。天启二年(1622)进士黄道周《〈姚文毅公集〉序》所言也大致如此:“方嘉靖之初年,议臣鸷起,文章之道,散于曹僚,王弇州、李历下为之归墟。”(82)黄道周撰、翟奎凤等整理:《黄道周集》(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873页。当时于慎行对“今世言文章者,多谓此道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说,虽不以为然,谓之“此何说也”(83)于慎行:《海岳山房存稿序》,郭造卿:《海岳山房存稿》(卷首),《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56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135页。,但也从反面透露出,文归郎署已为多数时人所接受。
“嘉靖之初年”是“文章之道,散于曹僚”之时,非李、王“为之归墟”之时,即文学权力尚未复归后七子郎署文人。后七子中,李攀龙最早进士登第,时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王世贞继之,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他们结盟立派崛起于文坛,尚需时日;二人为文章之“归墟”,当在此以后。李攀龙倡为五子诗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84)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628页。,可视作“五子中兴”的起点,故文权复归于后七子郎署文人应在此后。陈继儒《上王凤洲》称“国朝二百年以来,文章之权,先生擅之”(85)王心湛校勘:《陈眉公全集》,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第193页。,以此断限,当时值嘉、隆之际。四库馆臣也如是说:
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于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坫。(8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30页。
显然,正德、嘉靖之间,就李梦阳、何景明而言;嘉靖、隆庆之间,就李攀龙、王世贞而论。“夺长沙之坛坫”,标志着当时主流文风已经由“诸调杂兴”,重新趋于“文自西京以下,诗自天宝以下不齿”,文权已为李攀龙、王世贞为核心的后七子郎署文人所把控,即明代主流文学权力复归于郎署。
四、余论
强调李攀龙的结盟意识,并不等于否认后七子其他郎署文人结盟意识的存在,更不否认其结盟意识也有不同程度的主盟意识。王世贞的主盟意识,并不亚于李攀龙,不过碍于后者的巨大影响力,他多有意识地克抑。即便如此,有时二人也难免因此产生摩擦。嘉靖三十八年(1559)正月某日,王世贞客于李攀龙家中,李“因酒踞”,谓王世贞曰:“夫天地偶,而物无孤美者,人亦然,孔氏之世乃不有左丘乎?”王世贞“瞪目直视之,不答”。李攀龙意识到自己出言不妥,遽言道:“吾失言。吾失言。向者言老聃耳。”(87)王世贞:《书与于鳞论诗事》,《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十七),《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4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245页。王世贞《艺苑卮言》于此也有记录,但言语稍异:“于鳞一日酒间,顾余而笑曰:‘世固无无偶者,有仲尼,则必有左丘明。’余不答,第目摄之,遽曰:‘吾误矣。有仲尼,则必有老聃耳。’其自任诞如此。”(88)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64页。表面上看是为凸显李攀龙之“任诞”,实则是王抗议李以孔子自居,而把自己比作为孔子《春秋》作传的左丘明。“向者言老聃耳”,是王世贞认许的,其欲与李攀龙并驾齐驱之意,不自“是日”起,由其“相与狎主齐盟”的言论,即不难得知。吴国伦被李攀龙认定有“境外交”,也有这方面的因素。李维桢“海内荐绅、布衣、学士羔雁玄纁,不东走弇州,则西走甔甀矣”(89)李维桢:《河南左参政吴公舒恭人墓志铭》,《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31页。之语就道出了实情。这一说法,也为一些后人所认同。钱谦益称:“海内噉名之士,不东走弇山,则西走下雉。”(90)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33页。《明史》本传也称,吴氏“归田后声名籍甚,求名之士,不东走太仓,则西走兴国”。(91)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79页。当然,李攀龙以外的后七子郎署文人的结盟意识,更多地还是犹如宗臣,甘愿奉李攀龙为盟主,欲与诸子“共励斯盟”。
本文所以集中凸显李攀龙的主盟意识,主要因其萌发时间早于其他后七子郎署文人,而且程度相对更强烈。在此意识的支配下,他率先将志同道合者集结于自己周围,并在他们的辅助下,结社立派,激发出显著的群体效应,引领了当时主流文风,促成文学权力复归郎署。就此而言,李攀龙不仅为后七子之盟主,也是名副其实的一代文坛宗主。当然,文权复归郎署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李攀龙的结盟意识仅为其一,其作用主要在于导夫先路。李攀龙过世后,郎署文学能风靡文坛至万历年间,主要凭借其培养的第二代盟主王世贞及其他盟员的实力。因此,不可过分夸大李攀龙结盟意识的作用。同时,也应看到,李攀龙推出的文学主张,较之李、何等人更加狭隘、偏激,因而难免重蹈前者覆辙。尽管后来王世贞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调整,但为时已晚,故只能无奈地慨叹道:“(文权)今当复归台阁矣!”(92)王世贞:《答郭太史美命》,《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九十八),《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9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374页。与王世贞同时的刘凤,也看到了问题的本质:“然议者谓伤于袭哉。其所铸词,必范之古,是矣。然途辙尺寸,一将循其故步,是犹且不可,而况抵掌谈说,若优笑之为乎?”(93)刘凤:《送魏季朗序》,《刘子威集》(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1-32页。“范古”没错,反对六朝绮靡也没错,错就错在“循其故步”上。从这一角度说,李攀龙尽管煞费苦心,但也未能为明代文学的发展寻觅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尽管如此,从宏观上看,李攀龙结盟意识下的文权复归郎署,是明代文学权力流转的重要一环。明代主流文学之权力,先由馆阁移至以李、何为中心的郎署,后又逐渐分化、流失,导致嘉靖初的“诸调杂兴”,六朝派、中晚唐派、唐宋派顺势而生,流弊也随之而来。为补纠文弊,李攀龙首发其难,重申李、何文学主张,结盟立派,扭转了文风,促成文学权力复归郎署;因其开创的后七子派及其末流的学古不善,重蹈前者覆辙,万历中后期文学权力又由郎署开始外流,流向山林、市井,对促成晚明文学的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94)薛泉:《儒、商互动与晚明郎署文学权力之下降》,《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万历年间所谓的文权“复归台阁”,也与此甚有关联。因此,以李攀龙的结盟意识为观照中心,可为考察明后期文学生态环境、文学发展演化提供一个别样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