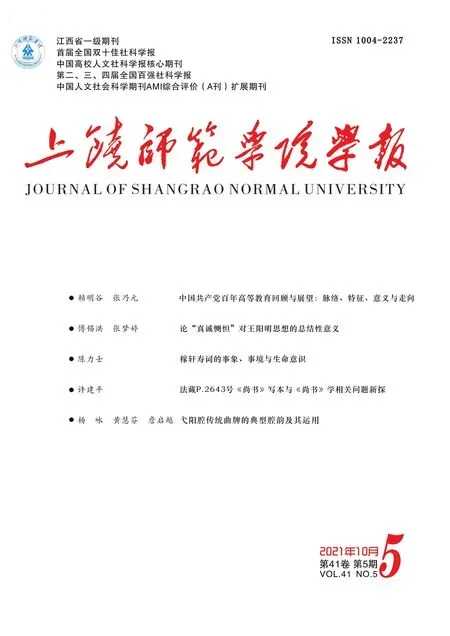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综述
周迎霞,牟玉华
(上饶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 上饶334001)
我国关于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名实之辩”。但到1950年才有学者罗常培先生自觉地把语言和文化成系统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形成著作——«语言与文化»[1]。然而,罗常培先生为中国语言学开辟的新路,此后三十余年,竟无人继踵。直到1980年代中期,陈建民、游汝杰和周振鹤等学者才踏上这条路并首次提出建立“文化语言学”的构想。从此,文化语言学迅速发展,为中国语言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邢福义先生在«文化语言学»中对21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状况作了非常详细的分析[2]75—99,因此,本文对这段时期的研究不再赘述,而是从学科理论研究和专题研究两个维度分析并梳理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以期尽量客观地呈现出该阶段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状况及主要特点。
一、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语言学主要研究成果
(一)学科理论研究
学科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对学科性质、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研究。21世纪以前,学科内部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21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文化语言学学科理论的探索仍在继续。
申小龙在«汉语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再次提出“汉语的人文性”理论以及从人文角度研究汉语的必要性,认为“汉语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形式格局的一致性”[3],并探索了汉语语法、汉字等方面的人文性。申氏把文化语言学定性为语言学本体学科。
张公瑾和丁石庆在«文化语言学教程»中从“理论与方法”和“研究与应用”两大部分对文化语言学进行了系统性阐述。但实际上该著作在理论上延续了张公瑾先生20世纪90年代所提出的观点,即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方面主张“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而且对象不是一两种语言,而是尽量多的不同类型的语言”[4],并坚持将浑沌学作为文化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并给出了多个具体应用案例。
就学科性质来说,苏新春认为对文化语言学学科性质的看法会因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理解及语言的文化意义研究的角度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具体地说,从语言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看,文化语言学是关系学科;从研究目的看,文化语言学是阐释性学科;从是否承袭现有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与成果来研究语言学与其他人文学科间的联系或语言学本身看,文化语言学可以是交叉性学科或本体学科[5]1—3,5。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专著«文化语言学教程»中还专门开辟一个章节,围绕“学科研究方法”这一讨论热点进行论述。在对前人的工作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思考的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期解决文化语言学研究方法缺乏操作性、难以定量、主观性强、不易确切把握等常受人诟病的问题[5]224-252。笔者认为这一工作对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和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刘静认为,“文化语言学是汉语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学科”“着重研究汉语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研究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及其互动关系”[6]。她侧重从具体内容及事实本身探索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所采用的一些研究方法具有一定创新意义。
纪玉华介绍了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理论的构建思路,指出了中西文化语言学的不同之处,认为“文化语言学的出现在美国对人类学和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来说是一个量变大于质变的发展,而中国的文化语言学对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发展却具有质变的性质,可以说是西方语言人类学和中国的文化学相结合的结果”[7]。
赵明从多角度对21世纪初十余年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主要成果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他认为就学科性质而言,文化语言学是交叉学科,而不是本体学科;就研究对象而言,文化语言学应从文化背景出发,在考察语言的文化性质与文化价值的同时兼顾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文化语言学应加强对比和量化两种研究方法,通过量化研究得出可靠结论,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语言的个性及人类语言的共性。同时,文化语言学还应确立学科研究的重点和突破点,加强学科成果转化和不同学科间的沟通[8]。该文虽然所列论著较少,但在不长的篇幅中讨论的大都是文化语言学界的悬而未决的难题,提出的观点鲜明而独到,值得细读。
21世纪以来,虽然学者们在学科理论方面有一定的探索和反思,但总的来看,学科理论研究少且缺乏创新性。
(二)专题研究
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内涵,早在学科成立之初,学界就存在争论,至今仍无定论。不过,中国文化语言学主要从事语言与文化研究,这是一个浅显的共识。但从事语言与文化研究却并非文化语言学所独有。为尽可能地从海量文献中区分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核心成果,笔者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将从事语言与文化的研究粗略分为以下三类:(1)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化研究,包括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2)汉语语言文化与其他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比如跨文化交际研究、外语/对外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的语言文化研究、翻译中的语言文化研究等;(3)他国语言与文化研究,例如俄语语言文化学、日语文化语言学、越南语文化语言学,等等。显然,就当前理论建设情况来看,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主体对应的是第一类。因此,本文仅从词汇及其语义、语法、语音、方言、专名等五个方面对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而暂不涉及其他两类研究成果。
1.词汇及其语义与文化
“语言,主要是它的词汇,是人类编织文化世界的丝线;从语言棱镜,主要是它的词汇系统中,可以观察到文化物质层次的种种景象”[2]110。可见,词汇与文化的研究在文化语言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词汇与文化的研究离不开对词义的探查,因此,学者们常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研究[2]85。
21世纪以前文化语言学领域关于词汇及其语义与文化的研究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进入21世纪以来,这方面的论著依然异彩纷呈,主要又可分为两小类。一类是从词汇及其语义出发,探寻其反映出的不同时期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物质、制度、精神等层次的文化,透过词语及其语义演化过程中蕴涵的文化意义或文化理据去探索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概貌。这一类研究属于文化与语言的关联类研究,走的是“关系派”的路子。例如,钱进以汉语成语和俗语为研究对象,分析并归纳了成语、俗语所反映出的性别差异现象,并探寻形成此类现象的文化根源[9]。苏新春在«文化语言学教程»第四章从单个词语、类别词等来探求其中蕴含的文化[5]75—113。值得一提的是,成语与文化的联系颇受学者们关注。例如,莫彭龄对成语与文化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成语是语言文化的精华,是语言文化的“活化石”和“全息块”,它蕴含着更典型、更系统、更丰富的文化,因此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成语的文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比较研究等三个方面对成语文化研究做出初步探讨[10]。其专著«汉语成语与汉文化»[11]也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另一类是从文化的视角去探索词语的产生、构造、语义的产生及演化等词汇及语义学理论,走的是“本体论派”的路子。例如,贺国伟认为社会人文因素是词语产生和定型的主素之一,并结合实例探求汉语词语产生和发展的文化理据,丰富词汇学理论中的文化因素[12]。又如,周一农在«词汇的文化蕴涵»中用轻松幽默的笔调,结合哲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从文化视角对生活中遇到的词语现象进行深刻的剖析,对词语中蕴含的文化作了新颖的解读,向人们展示了词汇与文化研究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方法[13]。再如,张再红“将文化模式理论和认知语义学理论结合起来对文化语义学进行研究”,试图“建立文化语义分析的文化与认知统一的理论框架”[14]。
2.语法与文化
上世纪末,以申小龙为主要代表的学者努力将汉语语法研究与汉民族思维和文化心理特点联系起来,创新了汉语语法理论。
21世纪初,申小龙系统性地阐释了一种“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贯通起来,将汉语语法的共时平面和历时平面结合起来,将句法的结构分析与结构的使用频率结合起来,将汉语语法分析与中国哲学、文学等其他文化现象的分析结合起来”[15]的新的汉语语法学研究范式。近年来,申小龙从文化视角对中西方语法(尤其是句法)进行了大量对比分析,指出中西语法差异[16],并提出“在文化认同中以汉语本位重建汉语句型理论”[17]的观点。
笔者认为,文化语言学领域中,语法的研究历来不是研究热点,但却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从长远来看,申小龙等学者在语法理论方面的创新性研究对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语音与文化
早期关于语音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较少,以史有为的“文化语音学”观点最具特色。
进入21世纪后,关于语音与文化的研究成果依然不多,其中史有为的研究较为突出。他在早期工作基础上,通过对多种语言的调查,发现“带调音节与单音节语、语法手段、句首指称词地位等类型”等因素有明显的相关性。而且,在被调查的诸多语言中,汉语是“最突出而典型的一种”。因此,他认为“带调音节是解释汉语的一个出发点,具有控制性,值得格外重视”[18]。
语音与文化的具体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谐音与文化方面。根据笔者统计,2000年后,知网中这方面的文献有近170篇。这些研究不外乎两大类:一是透过文化看谐音,包括谐音现象成因、谐音表义、谐音修辞、谐音禁忌、谐音在广告语及网络语言中的应用等;二是透过谐音看文化,包括利用谐音反映民族文化内涵、民族审美心理、习俗、禁忌与崇拜等社会文化心理。于全有和李现乐就从“汉文化对谐音的影响研究、谐音对汉文化的影响研究”两方面对前人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提出“发掘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的谐音文化现象与材料,探讨富有时代气息的新的谐音现象与材料所体现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内涵”[19]的主张。
运用Epidata 3.1对数据进行双录入,采用SPSS 20.0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采用x2检验进行组件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除谐音与文化的研究外,语音与文化方面也出现了其他值得关注的研究点。例如,董晓敏从社会文化和语言本身两个角度考察了汉语外来词音节语素化现象,指出外来词音节语素化构词将会成为汉语词汇系统中的一种新的构词方法[20]。
总的来说,语音与文化的研究偏少,且较为集中于谐音与文化这一方面。4.方言与文化
严格意义上讲,作为汉语的一部分,汉语方言与文化研究跟汉语普通话与文化研究并无本质差别。方言学者游汝杰是最早提出建立文化语言学的学者之一,汉语方言与文化的研究从文化语言学学科建立之初就受到重视,研究成果丰硕。
21世纪以来有关汉语方言与文化的研究热度依旧不减,知网上的相关论文多达2 000余篇。有从宏观的角度进行探讨的,也有从具体的某种方言进行研究的。前者如李如龙的«关于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该文认为若要研究方言,必须关注地域文化;要了解地域文化,可以通过方言这条捷径,文章就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视角,应着重发掘哪些方面的语言事实以及考察哪些方面的文化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21]。后者如唐七元的«从粤语的语音特点看粤语区的谐音文化»,该文通过实例证明了粤语区的谐音文化跟粤方言的语音特点紧密相关,从后者出发,可以基本断定前者的分布区域和流播路线,从而体现了方言与地域文化一致性的特点以及方言研究和地域文化研究相互结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22]。此类论著还有«徽州方言词汇与民俗文化研究»[23]、«鄂东方言词汇与地域文化研究»[24]、«绍兴方言语音特征与越地语言文化»[25]等。此外,曹志耘主编的«中国语言文化典藏»利用多媒体、数据库和网络技术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包括地方名物、民俗活动、口彩禁忌、俗语谚语、民间文艺等)进行保存和展示[26]。这些成果将对文化语言学研究(尤其是方言与文化研究)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5.专名与文化
专名是反映特定对象的词语。因此,关于专名与文化的研究本该放在“词汇、词义与文化”专题之下,但因为专名的内容丰富,能够反映特定的社会文化,且专名与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颇丰,因此,学界内通常专门辟出一个专题对其进行综述。
21世纪以来,专名研究依然保有较高的热度,其成果主要可分为以下几个小类。
(1)人名与文化
«中国人名文化»从历时角度探讨了中国人名符号的发展演变,具体解析了中国古代的多名制度现象[27]。«语言与姓名文化:东亚人名地名族名探源»探讨了不同地区、民族以及东南亚相邻国家的人名、地名和族名[28]。«汉语人名文化放谈»通过分析大量古今人名故事,介绍了汉语人名文化等内容[29]。
(2)地名与文化
目前,该方面有大量以具体的省、市、乡镇等地名为研究对象,探索地名所反映出的特色文化的研究成果。例如:«姑苏地名文化原本考»一文借助古籍,考证了“姑苏”地名的来源,论述了其名所反映的文化内涵[30]。又如,«吉林省地名文化研究»[31]、«寿县地名文化透析»[32]、«南京地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33]分别从吉林省、寿县和南京市的地名为研究对象探寻其反映出的文化。此外,也有从宏观角度探讨地名与文化的研究成果。例如,«汉语地名的文化特征»从汉语地名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心理文化三方面揭示汉语地名的文化特征,发掘积淀在汉语地名中的文化内容以及隐含在其中的文化特质[34]。
(3)店名与文化
21世纪以来,店名与文化的研究既保留了对传统店铺名称与文化的探究,又出现了向楼盘名与文化、商标名与文化、品牌名与文化等方向扩展的趋势。任志萍从语言和文化两个角度对网络上获取的1 000个中餐馆店名进行分析,找出了中餐馆店名的命名特点及从中折射出的饮食文化特色[35]。吕津从多个角度对杭州215个楼盘名进行分析,认为楼盘名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一座城市的特质和都市社会文化的变迁[36]。邓红莲从语音、词汇和修辞等方面研究了服装类商标命名的特点,并重点考查了服装商标名称的命名理据,指出“文化和商标名称语言互为表里”“服装类商标语言是文化的一个载体,二者互相影响而又共同发展”[37]。
(4)数词与文化
上世纪末,«数里乾坤»是该领域的上乘佳作。该书从多个方面深入探讨、阐释常用数词的文化含义,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有文化气息的数字世界[38]。
近年来,学者们依旧沿着前人开辟的路子,从各自的视角对汉语数词的文化意蕴进行解读。例如,舒志武讨论了数词“三”的产生及其特点,并分析其文化意义[39]。曹成龙考察了数词“一”的文化涵义[40]。陈烁等分析了数词“四”和“七”的文化意义的古今流变[41]。周媛发表了多篇论文,分别解读了数词“三”的传统文化内涵[42],数词“七”的传统文化意蕴[43],以及数词“四”与“八”灵物崇拜的古今文化认知差异[44]。总的来说,该方面研究数量可观,但新意和深度不足。
二、现阶段中国文化语言学发展特点
本文重点从学科理论建设和专题研究两个维度梳理中国文化语言学21世纪以来的发展现状,受篇幅限制,仅介绍了部分代表性成果,还有许多有价值的成果无法一一列举。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分析,结合知网平台文献统计结果,笔者发现现阶段中国文化语言学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理论研究匮乏
自中国文化语言学形成到21世纪伊始的短短十余年间,学科内已出版了百余部著作,发表了近千篇论文。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勃发时期,而通过前文的相关统计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21世纪以来,关于学科理论的研究明显减少,甚至呈现出“匮乏”的状态。
这一点也可以从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现状及对待文化语言学的态度得到印证。我们通过知网统计发现,在第二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等领域发表的研究语言与文化的论文数量比文化语言学领域对语言与文化的本体研究的论文数量多一个数量级。回顾上世纪末,文化语言学对第二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等领域的语言与文化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当前这些领域的大部分研究都已不再提及文化语言学。这说明文化语言学理论发展的速度已远远跟不上其在相关学科中的应用需求,反映了中国文化语言学的衰微,而衰微的根本原因便是学科理论建设的不足。
(二)学科内部争论缓和
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呈现百家争鸣之势,形成了中国文化语言学“三大流派”——关系论派、本体论派和社会学派。各流派对学科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激烈的争论推动了学科发展。但是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学科内部呈现出争论缓和的局面,究其原因应是学科理论研究匮乏。另外,各流派不再像上个世纪那样热衷于确立统一的学科理论体系,甚至可以说对统一学科理论避而不谈,而是大量深入到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的具体事实中去,这也是造成学科内部争论缓和的一个原因。笔者认为,在学科建设尚未成熟之际,离开百家争鸣,学科发展容易陷入停滞状态,因此这种缓和是学科发展缺乏活力的信号。
(三)专题研究多而不均
中国文化语言学专题研究目前主要包括词汇、语法、语音、方言、专名等几方面。其中,词汇、方言、专名这三个方面历来是文化语言学研究热点,经过三十余年发展,走在了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最前沿。例如,21世纪以来,词汇与文化方面既有透过文化对语言本体展开的研究,又有对语言与文化关联的研究,而且涉及的词汇与文化类别更细、范围更广,甚至还出现了诸如文化语义学、国俗语义学等分支。类似的,如前文所述,新世纪的方言与文化研究、专名与文化研究也在上世纪研究的基础上向细化、深化和全面化发展。
比之这几方面,语音和语法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则不够丰富。有人将这两个专题式微的原因归结为二者与文化的关联性不强。本文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语言的语音、语法和词汇这三个子系统当中,人类主要靠词汇来编织文化世界,因此,从语言,主要是它的词汇系统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文化的各个层次[2]110。而且,相比于语音和语法,词汇最敏感,演变最快,最能反映社会的变化。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语言与文化»一书也提到“文化的变迁对语音的影响不像语义那样多”[45]。另一方面,现有的主流语言学理论,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语法)、形式主义语言学(形式主义语法)等已根深蒂固,被学界广泛接受,而这些主流语言学理论与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和理论方法等差异较大。前者重形式,侧重于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而后者重人文,侧重于用人文的方法研究。因此,文化语言学的诸多观点可能都与现有的主流理论(包括语法学、语音学)格格不入。虽然,目前有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从人文的角度重新审视汉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要突破现有的主流语法理论体系,提出较为成熟系统的新理论、新观点并非易事。
(四)少数民族文化语言学缓慢兴起
20世纪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与汉文化上,很少关注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但实际上,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是中国文化语言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张公瑾先生所说,“通过民族语言研究各民族文化,不仅能加深对各种语言的文化属性的认识,而且对揭示各民族文化史上的未知现象,重塑少数民族文化的整体面貌,了解各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都有重要意义”[46]。
令人欣喜的是,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尤以藏语、壮语为甚,蒙古语、满语、维吾尔语、土家语次之。
藏语研究方面,«藏语文化语言学发凡»联系藏族历史与文化研究藏语言,不仅填补了藏语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空白,而且从16个方面开展藏族语言文化专题研究,对藏语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7]。周晶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通过量化藏语中有关“茶”的词汇,利用“‘茶’的文化语言学价值,分析茶在藏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原因以及‘茶’在近代西藏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和政治意义”[48]。崔军民通过对藏语亲属称谓系统的研究,离析出其背后蕴藏的“小家庭”制的组织形式、母系社会的影响、“等距离”的传统观念等文化内涵[49],并指出“只有充分认识藏语言的文化价值,才能下大力气克服藏语‘母语危机’的问题”[50]。
壮语与文化研究方面,壮学理论开拓者潘其旭先生再开壮族文化语言学研究之先河,发表了三篇壮语文化语言学系列论文,提出“壮语与汉语不是同源关系”“壮语所属侗台语文化集团的语言系统,其独立起源而非孤立发展,不应属汉藏语系‘谱系树’上的‘语族’、‘语支’”[51],“壮族和泰族同源异流”[52]等重要观点。此外,覃凤余也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较为系统地从语言文化角度展开对壮语地名的研究,不仅发表了系列论文,还出版了专著«壮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该书从壮语地名的内涵、特点及词汇系统等角度构建了壮语地名理论架构,并从壮语地名的分类、壮语地名命名法的特点、壮语地名中的壮语与汉语、壮语地名汉壮对译的对音价值、壮语地名中的汉语借词等角度开展了专题研究[53]。何思源采用分析与综合、静态与动态、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对麽经布洛陀进行文化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不但对麽经壮字、词汇和语法等进行了详细分析,还试图从麽经语言中挖掘出壮民族的精神内核[54]。
蒙古语与文化的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例如,曹道巴特尔“采用系统科学浑沌学理论与方法,从蒙汉历史接触出发,考察中国蒙古族语言文化在自然地理、人文社会大环境中的整体性变化,利用考古、传说、文献依据,分析蒙古族语言文化的产生,通过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变迁与语言文化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中国蒙古族语言文化的变迁。通过蒙古语语音、语法、词汇演变分析,探求汉语言文化对蒙古族语言文化的影响和作用”[55]。图拉从文化语言学角度研究蒙古国和中国边境地区的蒙古人,以及俄罗斯布里亚特人传统的奶制品和肉制品的相关名词术语,明确其区别和关系,并通过这些名词术语了解蒙古传统文化和思维定势[56]。
此外,近一二十年来,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逐年增多。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覆盖的少数民族语言总数量已有近二十种,包括维吾尔族、满族、土家族、彝族、侗族、土族、布依族、傣族、白族、羌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其中,藏语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壮语文化语言学也有系统性的专题研究成果;蒙古语、满语、维吾尔语、土家语研究成果数量也初具规模;其他民族语言文化研究也正经历从萌芽到兴起的良性发展阶段。虽然少数民族文化语言学涉及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看似零散,但若将其综合在一起却似异军突起,已发展成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重要分支。它的兴起,一方面为本民族的语言研究开拓了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古往今来中国的少数民族与汉族联系密切,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对汉语文化语言学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三、结语
本文在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成果的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现阶段中国文化语言学存在“理论研究匮乏”“学科内部争论缓和”“专题研究多而不均”和“少数民族文化语言学缓慢兴起”四个主要特点。
“理论研究匮乏”是近年来中国文化语言学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也是学科内部争论缓和的部分原因。造成学科内部争论缓和的另一个原因是研究者刻意回避对学科理论的统一。“专题研究多而不均”从根本上来看反映的也是学科理论的欠缺。对词汇语义、方言、专名等而言,从词汇,包括方言中的词汇和专名入手,比较容易观察到文化的各个层面,而且目前常见的研究范式是以主流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或挖掘语言的文化内涵,或从文化的角度对语言现象加以阐释。这种范式对理论创新的要求不高,所以容易出成果。而从语音和语法去观察文化远不如从词汇观察那么直观,而且,语音和文化及语法与文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与主流语言学(包括语法学、语音学)理论格格不入,故当前颇受冷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研究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尚未受重视,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中还未找到合适位置。另外,虽然本文未从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等其他学科应用角度展开分析,但通过知网简单搜索统计即可发现,从学科外部环境来看,文化语言学当前的理论体系已远无法满足其他学科的应用发展需求。
综上分析,本文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成果数量虽比较可观,但当前理论体系存在框架性缺陷,已有理论体系既无法很好地支撑汉语与文化的传统的核心专题研究,也没有很好地包容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更满足不了其他学科的应用需求。因此,中国文化语言学各流派形成统一认识,并科学构建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是当前亟需解决的决定该学科未来走向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