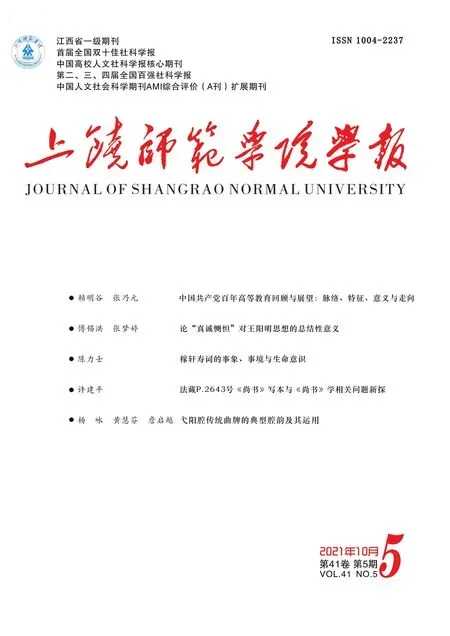论“真诚恻怛”对王阳明思想的总结性意义
傅锡洪,张梦婷
(1.中山大学 博雅学院,广东 广州510275;2.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510275)
王阳明去世前不久提出了“真诚恻怛”概念,在弟子中以及当代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一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渊源有自的,其中“恻怛”最早出自«礼记·问丧»:“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懑、气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动体、安心、下气也。”[1]两汉学者在论丧之际经常提到恻怛之心。宋代时,李觏最早提出了“诚心恻怛”[2]的说法。朱子用得较多的是“至诚恻怛”,或者与之类似的“至诚恳切”,如他对«论语»“殷有三仁焉”作了这样的解释:“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于至诚恻怛之意,故不咈乎爱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3]183此说是对谢上蔡之说的继承,朱子提到:“谢子说‘三仁’云:‘三子之行,同出于至诚恻怛之意。’此说甚好。”[4]1128而他解释“笃志”的含义的时候则提到了“至诚恳切”,其含义与“至诚恻怛”是相同的:“笃志,只是至诚恳切以求之,不是理会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泛泛地外面去博学,更无恳切之志,反看这里,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顽麻不仁底死汉了,那得仁!”[4]1204他对“恻隐”的含义的解释,实际上也可看作是对“恻怛”的解释:“恻隐是伤痛之切。盖仁,本只有慈爱,缘见孺子入井,所以伤痛之切。”[4]383由此可知,“至诚恻怛”即至诚痛切,实际上就是发自内心的对他者的不容已的同感。与之相反的是“硬心肠”,朱子把“硬心肠”视为“至诚恻怛”的反面:“试自看一个物坚硬如顽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试自看温和柔软时如何,此所以‘孝悌为仁之本’。若如顽石,更下种不得。俗说‘硬心肠’,可以见。硬心肠,如何可以与他说话!”[4]115
王阳明去世前提出“真诚恻怛”[5]95或与之类似的“诚爱恻怛之心”[5]1091、“仁爱恻怛之诚”[5]1068,正是以上述思想资源(尤其是朱子的说法)为基础,又进一步在自身良知学说的框架中对其含义作了独特而深入的阐释,由此,“真诚恻怛”构成阳明思想不可或缺的内在环节。
最早注意到“真诚恻怛”这类说法在阳明学中重要性的人,应当是阳明弟子陈明水。他对阳明家书中的“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作了如下评论:“云‘诚爱恻怛之心即是致良知’,此晚年所以告门人者,仅见一二于全集中,至为紧要。”[5]1094王龙溪在总结阳明思想演变轨迹时,提到“真切是本体”[6],而真切可以展开为真诚痛切,因而可以视为“真诚恻怛”的简化形式以及初步表达。
现代也有不少学者对“真诚恻怛”十分重视。如牟宗三先生以下所说的“精诚恻怛”就是“真诚恻怛”:“良知之内容亦不只是光板的、作用的明觉,而是羞恶、辞让、是非、恻隐全在内的心体之全,故阳明总言‘良知之天理’,亦总言‘精诚恻怛’之本心。这也是既是理,也是情,也是心。”[7]113牟先生并不局限于阳明而谈“真诚恻怛”,而是将其视为整个儒家思想的特色。他将康德与儒家进行对比时特别强调了儒家之重视“真诚恻怛”,认为这是儒家优胜于康德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关键,他评论康德说:“可惜他一间未达、一层未透(自由为一隔绝之预定、设准,其本身之必然性不可理解,是一本质的关键),‘道德的形上学’不能出现,而只完成了一个‘道德的神学’。拨开这‘一间’,打通那一层隔,是要靠那精诚的道德意识所贯注的原始而通透的直悟的,亦即靠那具体清澈精诚恻怛之圆而神的浑全襟怀,这是儒圣的德慧生命之所开发。西方自始即无这种生命。以步步分解建构的方式而达至康德的造诣,亦算不易了。”[7]158
笔者也曾对阳明“真诚恻怛”思想作了初步探讨①可参看傅锡洪:«论阳明学中的“真诚恻怛”:思想渊源、工夫内涵及当代意义»,«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怛”:论王阳明的“哲学遗言”»,«原道»2021年第4期。。总体而言,虽然学界已经注意到“真诚恻怛”在阳明思想中的重要性,然而这一概念内涵之丰富与深刻,还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可以说,“真诚恻怛”分别是本体与工夫、动力与准则、勉然与自然的统一。三重统一的“真诚恻怛”堪称阳明思想的精要表达,对阳明思想具有总结性的意义。耿宁先生将其称为阳明的“哲学遗言”[8]305,可谓良有以也。
一、本体与工夫的统一
“真诚恻怛”意味着本体与工夫的统一。阳明去世前必欲提出“真诚恻怛”并将其提至本体高度的根本原因,乃是以此揭示本体所蕴含的足以推动工夫的动力和引导工夫的准则,从而实现本体与工夫的统一。
阳明认为,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5]95。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只是”的表达。在别处谈及心体时,阳明更多使用“……是心之本体”这一表达方式,这一方式仅仅是单纯对本体及其状态作出描述。相较而言,阳明在规定良知概念的关键命题——“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5]126时,则采取了“只是”这一形式。“只是”这一独特表述,是在对良知本体作出界定。同样地,此处阳明也是用“真诚恻怛”界定而非描述良知本体。“只是”表明“真诚恻怛”便可穷尽良知的内涵。正因为真诚恻怛足以表达良知的内涵,所以阳明所说的无论“良知之真诚恻怛”,还是“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5]95,都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表述形式。而这种同义反复的表达,在阳明处也并非孤例,如他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5]51此处“良知之天理”便在语法上类似于“良知之真诚恻怛”。“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既是致此良知,也是致此“真诚恻怛”,两者所指相同,言及其一则得其二,因而下文引阳明语,只说“真诚恻怛之本体”便已足够,因为,不说“良知之本体”而“良知之本体”之义已经蕴含其中。
其次,整句话简而言之是说良知“便是他本体”。这里不是说良知本体是良知本体,那样的话就成了无意义的同意反复,而是说发用层面的良知同时也是本体,亦即良知是即发用而为本体的。本体不在发用之外别为一物,而发用直接就已经是本体了。正因为良知是即发用而为本体,所以“真诚恻怛”也是即发用而为本体,同时兼有了发用和本体的双重含义。质言之,“真诚恻怛”绾结了阳明学中的发用与本体,而将它们统一起来。
和本体与发用这一对概念类似的,是本体与工夫这一对概念。刘蕺山对阳明思想有“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9]7的著名评论,这一评论应当是符合阳明思想实情的。体和用指本体和发用。发用是相对于本体而言的,指本体的表现。工夫是从主体有意识的、自觉的行为的角度来说的。在阳明学中,由于工夫的发动和施行受到本体或多或少的指引和推动,故也应属于发用的领域。因此,在本体、发用和工夫三个概念中,关键是如何界定本体的含义。然而,阳明不仅从本体的角度来界定发用和工夫的含义,还非常注重从发用和工夫的角度反过来界定本体的含义。如果说他对体用关系的理解“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5]36是对本体与发用含义的相互界定,那么«稽山承语»所载四句话就是对本体与工夫含义的相互界定。这四句话中,“合着本体,方是工夫”是以本体界定工夫,而“做工夫的,便是本体”“做得工夫,方是本体”以及“做得功夫,方见本体”则是以工夫界定本体①朱得之编«稽山承语»,转引自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第628页。。由上述四句里的中间两句可知,工夫的具体推动者和实施者(即“做工夫的”)便是所谓本体(即“便是本体”);并且唯有能推动和实施工夫的(即“做得工夫”),才称得上是本体(即“方是本体”)。由此,工夫之所以为工夫,是因为它符合了本体的要求;而本体之所以为本体,则是因为它推动了工夫的完成,两者是相互界定的关系。“真诚恻怛”和良知一样,可以把本体和发用,或者本体和工夫统一起来,这是我们说“真诚恻怛”在阳明学中具有总结性意义的原因之一。
至于“真诚恻怛”何以就能统一本体与工夫,其实也并不难理解。因为工夫的最重要要素,是推动工夫的动力和工夫所要完成的目标,而所要完成的目标又具体落实为所当依循的准则,或说符合工夫的准则也就符合了工夫的目标,所以我们可说本体即是工夫得以完成的动力和准则。良知在阳明看来当然是工夫得以完成的动力和准则,因而可以称为本体。他又将“真诚恻怛”称为本体,其意无非是说,和良知一样,“真诚恻怛”也是工夫得以完成的动力和准则。正是在作为工夫得以完成的动力和准则的意义上,“真诚恻怛”实现了本体和工夫的统一。
事实上,阳明正是为了强调本体在工夫中的重要性,才提及“真诚恻怛”,并认为“真诚恻怛”便是本体,蕴含了做工夫所需要的动力和准则。而工夫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私欲的阻碍,私欲问题是阳明始终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由此可说“真诚恻怛”之动力和准则主要针对的便是私欲的障碍。只有充分理解私欲问题是阳明始终如一的问题关切,才能真正理解他提出“真诚恻怛”并将其提到本体高度的目的。
为了理解何以“真诚恻怛”就能提供克除私欲所需的动力和准则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比阳明其他工夫指点语,以及考察作为私欲突出表现形式的知而不行问题。
正如刘蕺山所概括的,在阳明龙场悟道以后,体现其思想宗旨和指点学者做工夫思路的主要用语,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9]183。促使阳明提出这些主张的,便是有关私欲的问题。“去人欲而存天理”作为工夫指点语的好处,在于直接点出了去除私欲这一课题,问题则在于,它不仅没有说明私欲问题的突出表现形式,也没有说明人们能做到这一工夫的动力究竟何在。
私欲问题的表现,不仅有良知被遮蔽而全然不知,更有明知私欲萌动却又无力克制亦即知而不行。由于良知自知自觉,即便受到一定程度的遮蔽,也能一反便得,所以知而不行相较于全然不知可谓是更为普遍而困难的问题。«传习录»卷下载门人以下说法,将这一知而不行问题一语道出:“私意萌时,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5]140“知行合一”这一指点语的好处,便是直面了作为私欲突出表现形式的知而不行问题,其问题则和上一指点语类似,没有明确说明人们能做到这一工夫的动力究竟何在。虽然经过仔细推敲可知“知行合一”这一表述中的“知”并非通常理解的知识,而不外乎就是良知,但毕竟这一含义可以说是比较隐晦的。
相较之下,“致良知”的优越性,就在于指点出良知这一做工夫的动力和准则。也正因为致良知之于工夫有如此作用,所以可以说正德十五年(1520)左右致良知学说的正式提出,标志着阳明的思想以及教法已臻成熟。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良知”点出了做工夫的动力和准则,学者仍然被知而不行的问题困扰。事实上这一问题广泛而持久的存在,正是阳明在去世前几年提出“真诚恻怛”的一个重要背景。
只要我们承认阳明的学说并非无的放矢,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他在叙述自己观点之际提及的以下问题,不仅仅是假设,而是更多地反映了实情。他在论述«大学»工夫条目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以下问题:“然知得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做去”,他也意识到这一不能致知的问题会导致“善虽知好,不能着实好了;恶虽知恶,不能着实恶了”亦即不能诚意的后果[5]135-136。阳明认为不能诚意是不能致知亦即不能致良知造成的。
阳明原本认为致良知工夫极为简易,可是何以他已指点出这一简易工夫,却仍然不能促使人们将对是非的认识贯彻于行动之中而做到致知呢?这当然不是致良知学说本身的问题,而是人们未真实用功的缘故。如果我们追溯人们未真实用功以至于知而不行在认识论上的原因,就会发现人们对良知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其偏差主要体现在,将阳明用以诠释良知的是非之心,单纯理解为知是知非的知识而已,没有真正在工夫中诉诸良知。而如果良知的含义仅止于在认识层面分清孰是孰非,亦即良知如果仅仅是不导出行动的静观而已的话,那么,它不足以保证人们知之必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事实上,良知在被阳明提出之际,就不仅是一般理解的知是知非的意思,因为他所谓知是知非的良知,是足以突破私欲遮蔽的本然之知,是足以保证知行合一的。在某些地方,如著名的四句教中有“知善知恶是良知”一语,如果人们断章取义,不将其后“为善去恶”之“格物”当作是良知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的话[5]133,就难免会片面地以为良知仅仅是对善恶、是非的认识而已了。对晚年的阳明来说,如何诠释出良知足以保证知行合一的固有能力,就成为一项不容回避的课题,其以“真诚恻怛”,以及与之近似的一体之仁来诠释良知的含义,正是围绕这一课题展开的主要工作。“真诚恻怛”和一体之仁,都是为了指点出良知本体蕴含的克除私欲,从而化知为行的动力而提出的概念。
二、动力与准则的统一
“真诚恻怛”意味着动力与准则的统一。本体包含的动力与准则并非相互外在的关系,准则是内在于动力之中的,动力的自我调节就形成了准则。准则内在于动力,动力已是准则,正是“心即理”这一命题所欲表达的观点。
阳明工夫论中的动力问题,已经受到学者重视。耿宁先生在讨论立志问题时指出:“他(引者按:指阳明)所关心的是伦理力量的一种‘动力学’。”耿宁先生将这种动力学称为“伦理动力学”。他概括的阳明工夫的四种动力中,除了立志以外,另外三种实即他的三种意义上的良知[8]252,255。黄勇先生则以“动力之知”来解释阳明的良知概念,从而凸显出良知表示准则之外作为动力的面向[10]。吴震先生在«传习录»第五条有关“好恶”问题的点评中也指出:“这里所强调的‘好’(hào)和‘恶’(wù),喻指良知的判断能力,同时也是指良知的道德动力。在阳明看来,良知就是一种直接的源自本心的道德动力,而不是一种静态的有关是非善恶的知识而已。”[11]43
良知即是动力,那么准则又在何处呢?我们可以参看阳明关于良知的如下论述。他在«大学问»中解释“至善”含义之后,也用至善诠释了良知的含义:“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5]1067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从“其灵昭不昧者”以后的内容可以看出,良知之发用便是其本体,本体事实上不在发用之外。良知之发用与其本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良知即体即用这一点正是我们在上文便已触及的问题。
阳明这段话不仅阐明了良知既是体也是用,更表明良知具有至善的本质特征。良知之“良”既可表示价值上的好、善的意思,也可表示天所赋予、人所固有的意思。而且正因为是天所赋予、人所固有,所以才使其价值上善的性质具有了至善的内涵。至善包含善以及善是固有的这两层含义。这两层含义可以分别对应于完成工夫所需的准则和动力。也就是说,善构成做工夫的准则,有此准则,工夫便有了克除私欲的清晰目标;而善是固有的亦即不假后天人为的,则意味着良知自有将此善实现出来的动力,此善实际上是内在于此动力中的。
阳明的这段话论及了良知内含的准则:“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以无星之称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5]66以下说法则论及了良知内涵的动力:“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5]7实际上,以恻隐之心来规定良知的内涵,也体现了阳明体不离用、即用见体的思路。本体在做工夫中的作用,正是借由这种本体与发用合一的关系才得以具体发挥出来的。
阳明以“真诚恻怛”来界定良知,则意味着“真诚恻怛”也是内含着准则的动力,能有助于克服私欲,从而完成工夫。他说,良知“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5]96。“轻重厚薄”即是亲亲、仁民、爱物之类的等级与层次。“毫发不容增减”则意味着这样的等级与层次是不容违反的准则。这些准则并非是外在的、强加于人的,阳明指出,这些准则内在于良知的“发见流行处”,是良知在发用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良知的动力可以因应具体的情境进行自我限定和调节,从而避免出现过与不及的偏差,由此达到的状态就构成了人所应当遵循的准则。由此,准则是内在于良知的动力中的,动力与准则是统一的。由于良知即是“真诚恻怛”,因此也可以说,“真诚恻怛”的动力中蕴含着准则。“真诚恻怛”意味着动力与准则的统一,这是我们说“真诚恻怛”在阳明学中具有总结性意义的原因之二。
“真诚恻怛”是好恶之动力与善恶之准则的统一。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先生曾经提及“真诚恻怛”与好恶的内在关联:“因良知并非冷彻之感知,而是与好恶之情一体的温血之知觉,故而阳明又称良知之体为真诚恻怛。”[12]前已述及,阳明将是非之心解释成好恶。对事物的好恶不同于静观,它带有强烈的意志性,必然引发相应的行为。阳明以好恶解释是非之心,意图之一也正在于揭示是非之心蕴含的导向行动的能力。不过,以导向行动的好恶诠释良知,难免让人产生疑问,即阳明何以保证其所说的好恶是好善恶恶的呢,亦即此好恶之动力何以是内含准则的动力呢?事实上,阳明此处说的好恶,是在本然状态的意义上来说的,亦即其所指乃是未受私欲遮蔽的本然好恶,或者说真己之好恶。良知之准则内在于动力。这一点在好恶上的表现就是,本然好恶不仅是好善恶恶的,甚至于,善恶的标准本身就是由本然好恶所好恶出来的,而非在此本然好恶之前已经先行地存在着好恶的标准,如阳明说:“好字原是好字,恶字原是恶字”[9]585,前一“好”与“恶”是形容词,后一“好”与“恶”则是动词。好恶不仅关乎意志,也关乎情感。正是一体之痛感使人的好恶更接近或达到本然状态。或者说,正因为有了一体之痛感,人才能放下对自我的执着,而顺从真好恶、真是非。由此,以好恶来诠释良知,就不仅展示了良知化知为行的力量,而且其所知所行也是符合善的标准和要求的。唯其如此,动力才是内含准则的动力,而好恶才是完成工夫所必须的本体。也惟其如此,冈田武彦所说的“温血之知觉”才不至于沦为单纯的感性情欲,而同时包含了良知的准则。唐君毅先生如下说法同时考虑到了好恶之动力和善恶之准则,可以说比较全面揭示了“真诚恻怛”之本体的内涵及其作用,他说:“人若能真诚恻怛,以致其知善知恶之良知,而诚其好善恶恶之意,以成其为善去恶之行,则善日以长,而恶日以消。”[13]
准则内在于动力,准则即理,动力来自心,因而此处实际上涉及了“心即理”命题。由此也可说,“真诚恻怛”与通常称为阳明学“第一命题”的“心即理”存在着内在关联。
进一步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说,具有普遍性的“真诚恻怛”之本体因应具体情境而成为准则,同时体现了具体普遍性的精神,而具体普遍性可以说是宋明儒学的核心关怀、根本旨趣①相关论述可参看:傅锡洪«从“无极而太极”到“天理自然”:周程授受关系新论»,«哲学研究»2021年第5期。。具体普遍性在阳明学中也有体现,如吴震先生指出:“他(引者按:指阳明)注意到儒家的‘仁爱’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爱,而是一种具体的普遍之爱。一方面,仁爱要从家庭人伦的‘孝悌’做起,这就是具体之爱;另一方面,又通过渐次扩充的过程,实现对天下所有的‘民’和‘物’的仁爱,这就使得仁爱具有了普遍性。总之,仁之爱具有具体普遍性之特征,仁既是‘生生不息’之根本,也体现了‘万物一体’的精神。”[11]141在上述关于“真诚恻怛”之本体的论述中,“只是一个”代表了普遍性,“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则是普遍性在具体情境中的落实。
因为准则内在于动力之中,所以关键还在于动力,而此动力即是一体之痛感。在“真诚恻怛”一语中,此一体之痛感即由“恻怛”表达出来。阳明对此一体之痛感有丰富的论述,如:“才有一毫非礼萌动,便如刀割,如针刺,忍耐不过,必须去了刀,拔了针,这才是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5]41又如:“故凡慕富贵,忧贫贱,欣戚得丧,爱憎取舍之类,皆足以蔽吾聪明睿知之体,而窒吾渊泉时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尘沙,聪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郁逆,将必速去之为快,而何能忍于时刻乎?”[5]235陈立胜先生指出:“王阳明之良知固然是一普遍的是非之心,但此是非之心依然与‘真诚恻怛’绾结在一起,一体相关的生命之实感仍然是通过痛感体验乃呈现,以致有‘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之论说。”[14]牟宗三先生则还进一步谈到了痛感的平复:“此种醒悟亦是其本心所透示之痛切之感,亦可以说是其本心之惊蛰、震动所振起之波浪。由其所振起之波浪反而肯认其自己、操存其自己,亦即自觉其自己,使其自己归于其正位以呈现其主宰之用,此即是‘求其放心’,使放失之心复位。放失之心一旦复位,则由惊蛰、震动所振起之波浪即复消融于此本心中而归于平平,此时即唯是本心之坦然与沛然,溥博渊泉而时出之。”[15]放失之心的复位,即意味着动力中所蕴含的准则得以实现。
三、勉然与自然的统一
“真诚恻怛”意味着勉然与自然的统一。“真诚恻怛”既可理解为以真诚工夫呈露恻怛之仁,即勉然的工夫;也可理解为以恻怛之力维护真诚状态,即自然的工夫。工夫由勉然提升至自然,构成一个完整的为学进路。
先秦儒学即已有对人所处的层次、阶段的区分。处在不同层次、阶段的人应该适用不同的工夫,工夫存在勉然和自然的区别。«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3]31孟子则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朱子解释孟子此章说:“这章是两截工夫。‘反身而诚’,盖知之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乐。‘强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恁把捉勉强去,少间到纯熟处,便是仁。”[4]1436朱子也注意到并承认工夫可以分为两层,在这一点上他与阳明是相同的。只是他不以此作为自身工夫论的基本框架,朱子工夫论的基本框架是«大学»的八条目以及伴随八条目的居敬。在上述引文中,他将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纳入自身以«大学»格物致知为优先的工夫论中来把握,就是明证。达到了物格知至,意念便可以自然循理①严格说,按照朱子对诚意工夫的理解,物格知至以后并非就可以完全自然循理,在此“自然”与“勉强”只是相对言之。因为他认为诚意仍然费一番工夫,只是其费力程度无法与漫长而艰苦的格物致知工夫相提并论而已。,否则的话就只能勉强使意念符合理的要求。由此可知,工夫的关键在八条目开端的格物致知,并进而由格物致知层层推及其后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朱子主张的是八目工夫,而阳明则以两层工夫作为自身工夫论的基本框架。
阳明倡导两层工夫,相关论述可以说俯拾皆是。两层指的是自然与勉然。我们可以借孟子所说“反身而诚”与“求仁”,以及«中庸»所说“诚”与“诚之”来分析其两层工夫的内涵。首先,关于自然工夫。“反身而诚”指的是意识不必费力便可以直接达到与本体一致的状态,其含义与«中庸»所说“诚”是一样的。本体的基本内涵则是仁或者说一体之仁。仁之本体直接充实于意识并主导意识和行动,这就是自然工夫。质言之,自然工夫就是以本体固有的恻怛之力维护真诚状态。其次,关于勉然工夫。“求仁”即是努力排除纷扰的意念的干扰,达到仁之本体能够主导意识和行动的状态,其含义与«中庸»所说“诚之”是一样的。“诚之”即是努力达到诚的状态,即努力达到仁之本体主导意识和行动的状态。质言之,勉然工夫即是借助真诚工夫呈露恻怛之仁。由此可知,借助真诚工夫呈露恻怛之仁和借助恻怛之力维护真诚状态两个层次实际上都为“真诚恻怛”一语所涵盖,而这两个层次分别是勉然工夫和自然工夫,因此可以说,“真诚恻怛”意味着勉然与自然的统一。“真诚恻怛”意味着勉然与自然的统一,这是我们说“真诚恻怛”在阳明学中具有总结性意义的原因之三。
阳明关于两层工夫的论述可以印证我们的以上分析。他说:“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5]7“更无私意障碍”则无需费力,“充其恻隐之心”即是使恻隐之心主导意识和行动,进而体现于事事物物之中。这就是自然工夫,就是借助恻怛之力维护真诚状态。与之不同,“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不能单纯凭借本体固有的恻怛之力,而还“须用致知格物之功”,即还有必要借助后天的真诚工夫,去除私欲的障碍,恢复本体对意识和行动的主导。这就是勉然工夫,就是借助真诚工夫呈露恻怛之仁。阳明以下所说“率性”和“修道”,也分别对应于自然和勉然的工夫:“率性是诚者事,所谓‘自诚明,谓之性’也。修道是诚之者事,所谓‘自明诚,谓之教’也。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圣人以下,未能率性,于道未免有过不及,故须修道。”[5]43以下文字中所引孔子“发愤忘食”表达了诉诸后天努力的意思,而之所以能“乐以忘忧”则是因为借助了先天固有的本体:“‘发愤忘食’是圣人之志,如此真无有已时;‘乐以忘忧’是圣人之道,如此真无有戚时。恐不必云得不得也。”[5]109
王阳明与薛侃的问答也表达了两层工夫。“侃问:‘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语,管闲事。’先生曰:‘初学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于工夫上又发病。’”[5]30“一心在痛上”突出了初学阶段真诚工夫的重要性,并且此真诚工夫指向的正是恻怛之痛切感受;“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则突出了本体固有的能力,在较高阶段所应做的就是让这种能力自然发用。一些版本的«传习录»有陆澄所录的与薛侃提问语完全相同的一段话,表明薛侃所问正是阳明平时说过的话。“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便是勉然工夫,阳明将其视为适合于初学阶段的为学工夫。阳明引«孟子»“出入无时,莫知其乡”的目的是要说明,心体所发之念指向何方,是无法预知的。因为心体总是以其当下出于自身的好善恶恶之念的方式来运作,而每个当下的情形是变化的、无法预知的,心体所发的好恶也就是变化的、无法预知的。正因如此,在达到了较高阶段以后,如果仍然刻意、执着地“死死守着”,那就会引发阻碍心体自然发用的弊病。由此也可见,唯有无所勉强的自然工夫才是适用于较高阶段的为学工夫。
达到较高阶段并不容易,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应该切实做勉然工夫。这就是阳明为什么经常以“真切”来要求学者的原因。“真切”实即“真诚恻怛”的简化形式,主要表达了以真诚工夫呈露恻怛之仁的意思。较高阶段本体充分呈露,工夫可以自然开展,这是长期真切做工夫以后随顺而来的结果,如他所说:“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5]31
以下说法虽未直接提到“真切”,但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5]18“何思何虑”的意思是,不必刻意思虑而思虑都能合理①此为阳明中年时期的看法。从他晚年的书信可以看出,他后来把“何思何虑”理解为“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由此“何思何虑”即可涵盖勉然和自然的工夫,而不再仅仅是自然的工夫,其言曰:“‘何思何虑’正是工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王阳明全集»,第66页)。初学阶段不能适用“何思何虑”的自然工夫,在此阶段省察克治是不可或缺的。阳明将此工夫称为“思诚”,亦即前述的“诚之”。“端拱”原意是指正坐拱手、无为而治,在此则表示自然工夫。之所以工夫实施起来可以自然而然、不必费力,是因为获得了本体的充分支撑。本体可以给工夫以充分的支撑,则是长期努力省察克治的结果。由此可知,对大多数人来说,工夫的关键在于初学阶段的勉然工夫。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勉然工夫并非没有本体的指引和推动,那样的话工夫和本体就脱节了。即便处在被遮蔽的状态,本体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引和推动了工夫。正如阳明所说,普通人也有良知,只是人们忽略了它而已:“‘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旧看何等玄妙,今看来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聪,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智,圣人只是一能之尔。能处正是良知,众人不能,只是个不致知,何等明白简易!”[5]124此良知正可在初学时对工夫起到一定的推动和指引作用。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提到“真诚恻怛”之后,阳明还讲到了生知安行、学知力行和困知勉行,看似有三层工夫,其言曰:“区区曾有生知、学知、困知之说,颇已明白,无可疑者。盖尽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说存心、养性、事天,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养性、事天’者,虽未到得尽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里做个求到尽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5]97实则三层可以归结为两层。阳明在解释中间一层“存心、养性、事天”的工夫亦即“学知力行”的工夫时说,“必存之既久,不待于存而自无不存”[5]49,这其实就是从勉然到自然的提升。“存之既久”仍然是勉然工夫,而“不待于存而自无不存”则已经是自然的工夫了。由此可以看出,“学知力行”介于勉然和自然之间,是两者的过渡阶段,而不是说在两层工夫之外另有第三层工夫。因此,阳明在此处对工夫的三层区分,不足以挑战我们用两层工夫论来概括阳明的工夫论。
四、结语
诚如陈明水所说,«王阳明全集»谈到“真诚恻怛”及其类似表述的地方并不多。这很大程度上与阳明出征广西回程途中溘然长逝有关。他关于“真诚恻怛”的思想因此未能得到充分展开,这无疑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不过仅从现在留下的论述出发,结合阳明的整体思想,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总结出“真诚恻怛”在阳明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它统一了本体与工夫、动力与准则、勉然与自然,是对阳明思想的总结。之所以说是总结,不仅因为其被提出的时间在阳明去世前夕,更是因为它所涉及的这三个方面正好回应了本体与工夫这组宋明儒学的关键概念。对阳明来说,动力与准则构成了本体的内涵,勉然与自然构成了工夫层次和阶段的划分,而本体与工夫两者则是相互界定、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整个宋明儒学来看,上述三个统一与其他儒者的思想相比有同有异,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阳明思想的特色。以下我们首先从动力与准则的统一说起。
首先,动力与准则的统一。这可以说是理学和心学共享的主张。朱子认为性或者理是本体,而阳明则进一步认为,直接发自性的情,或者说良知也是本体。这是双方在何为本体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抛开这一点暂且不论,双方对本体的内涵的理解却有一致之处。不仅阳明认为本体内含动力和准则,其实朱子也认同这一观点。朱子说:“动处是心,动底是性。”后者是说性的能动性,从中可以看出性所具有的不容已的动力,性不是无所作为的。朱子又说:“盖主宰运用底便是心,性便是会恁地做底理。”[4]88,89“恁地做”表明性的能动性是有特定方向的,其方向实际上就是仁义礼智,而仁义礼智即构成了人行动的准则。由此可见,尽管对本体之所指有不同主张,但朱王在本体是内含准则的动力这一点上却持一致的看法。
其次,本体与工夫的统一。这一主张很大程度上使心学区别于理学。朱子认为在已经达到物格知至之后,使意念与本体一致的诚意工夫可以相对轻松容易地实现,在此之后的工夫基本上可以说是本体工夫。不过在达到物格知至之前,诚意工夫则并非本体工夫,而主要诉诸的是后天努力。朱子认为,诚意工夫除了诉诸后天努力以外,还可以诉诸格物(或说穷理)和居敬。而无论格物还是居敬,也都不能称为本体工夫。格物的过程是漫长而艰苦的,其主要依赖后天努力是自不待言的。居敬是使心保持不昏昧的状态,或者说私欲产生便被意识到并加以克除的状态。在此不排除作为性的自然发露的本心的存在,只是朱子认为本心的发用时断时续,不足凭借。居敬就其本质而言,主要凭借的是后天努力。就此而言,朱子固然不否认性可以自然发用,但在达到物格知至之前,却并不凭借作为本体的性。由此可知,他主张的工夫就不能说是本体工夫。这不同于阳明,阳明虽然强调后天努力在初学阶段的作用,但并不否认本体的发用,不排除发挥本体的作用,并且认为后天努力的目标恰恰是要使本体的作用真正得以落实。由此可见,初学阶段的工夫仍然可以称为本体工夫,尽管不是完全出于本体的工夫亦即严格的本体工夫,而只是部分出于本体的工夫亦即广义的本体工夫而已。若不论工夫熟后的状态,可以说心学和理学倡导的工夫具有是否为本体工夫的区别。
最后,勉然与自然的统一。这一主张使阳明的主张区别于明道、象山等心学一系的其他思想家。明道主张“不须防检,不须穷索”[16],象山主张“深山有宝,无心于宝者得之”[17],这些主张强调的都是自然工夫。之所以能做到自然,是因为完全凭借了本体。自然的内涵不仅是以自然的方式达到意识与本体的一致,而且是以自然的方式体悟本体①对此可参看:傅锡洪«“严滩四句”本意考»,«哲学与文化»2020年第7期。。勉然不仅无助于彻底达到意识与本体的一致,而且也会妨碍人们体悟到本体。阳明则认为大多数人没有办法从自然悟入,工夫只能从勉然入手。这是他和明道、象山的差别之处。
总而言之,动力与准则的统一是理学与心学共享的观念;本体与工夫的统一主要是心学内部共享的观念;勉然与自然则主要是阳明的特色。“真诚恻怛”体现了三重统一,足以作为阳明思想的总结,值得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