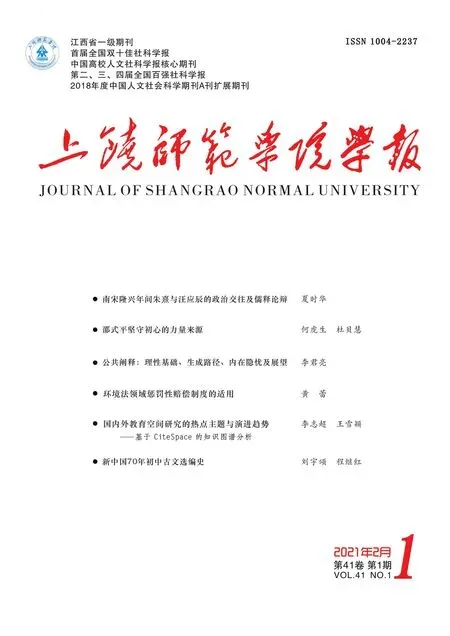公共阐释:理性基础、生成路径、内在隐忧及展望
李君亮
(海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 海口570228)
2017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在《学术研究》上发表《公共阐释论纲》一文,标志着具有当代中国阐释话语主权的公共阐释理论作为哲学诠释学的一个中国分支诞生了。这是一次世界(西方)话语体系背景下中国学者构建具有中国话语主权的哲学学说的重大尝试,是一次现象级意义上的学术事件。公共阐释这一基本概念提出之后,得到了诸多著名学者的积极响应,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反响,包括哈贝马斯、约翰·汤普森、迈克·费瑟斯通等当代国际上著名的思想家都密切关注着公共阐释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对公共阐释理论的提出给予了积极肯定的评价。目前,学界已经就公共阐释理论的一些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做出了许多有益的研究。本文将对这些研究取得的成果做一扼要评述,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公共阐释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一、公共阐释的概念生成及内涵
“阐释”还是“诠释”?
在“阐”“诠”之辨中,张江教授认为,“阐”与“诠”各有极为深厚的哲学和历史渊源,在他看来,“‘阐’之公开性、公共性,其向外、向显、向明,以及坚持对话、协商之基本诉求,闪耀着当代阐释学前沿之光。”而“‘诠’之实、之细、之全与证,其面向事物本身,坚守由训而义与意,散发着民族求实精神之光。”他认为,“中国古代的阐释路线,一条重训诂之‘诠’,一条重意旨之‘阐’。”这样,“阐”和“诠”“各有其长,互容互合”。我们“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假以对照、选择、确义,由概念起,而范畴、而命题、而图式,以至体系,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可建立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1]因此,虽然张江教授倾向于使用“阐”字命名他倡立的公共阐释理论,但是根据其“阐”“诠”辨义,实际上公共阐释之“阐”兼具“阐”“诠”二者之义。
在提出公共阐释这一基本概念之前,张江教授首先对西方文艺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从20世纪初开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表现出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等四大特征。场外征用即“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建构自己的体系,模仿、移植、挪用,成为当代文论生成发展的基本动力,改变了当代文论的基本走向”[2]。主观预设即“批评者的主观意向在前,预定明确立场,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非逻辑证明即“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基本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逻辑谬误,所得结论失去依据”。混乱的认识路径即“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既定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这就使得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从总体上倾向于“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3]这样一种强制阐释。
通过对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强制阐释传统的深刻反思与系统批判,张江教授提出建构以人类公共理性为基础的公共阐释这一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由此,阐释学由解构经由中国阐释进路发展到了建构的阶段,并正在实现阐释学由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的理论转向。
与反理性、反基础、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强制阐释不同,公共阐释中,“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4]。在对强制阐释展开反思与批判基础上建构的公共阐释具有整体性[5]、理性、澄明性、公度性、建构性、超越性、反思性等基本特征[4]。张江教授认为,公共阐释理论的建构之所以可能,就在于阐释活动的主体不是单独的人,而是社会的人,是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是此在之共同存在,因此是“集体意义上的人”,其言说也是借助公共语言向他人和同他人的共享之言说。由此之故,个体阐释绝非私人的,其理解与接受为公共理性所约束,人类的共在决定个体阐述的公共基础、集体经验构造个体阐释的原初形态、语言的公共性确立个体阐释的开放意义、阐释生成的确定语境要求个体阐释是可共享的阐释[4]。
二、公共理性:公共阐释的基础何以可能?
张江教授提出,公共阐释是“有效阐释”。公共阐释之所以可能,也即是说,公共阐释的有效性基础——在张江教授看来——在于阐释的公共理性:阐释是一种公共行为,阐释是一种理性活动。公共性和理性,这就是公共阐释之所以可能的根基。那么,公共性和理性何以能成为根基造就公共阐释?
公共阐释之所以可能,根基在于“阐释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4]。通过对“阐”字的文字考古学释义,张江教授指出,“阐”字有诸多可从语源上证明其公共性之义项[1]。正是基于“阐”字本身在语源上的公共性之义,有学者认为,“公共性在公共阐释论中是元理论问题”[6]。从“公共阐释”这一概念看来,该概念由“公共”和“阐释”这两个基本词语组成。在与哈贝马斯的对话中,张江教授指出,正是由于“阐释”之“阐”本身就能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绽放出“公共性”,因此,阐释本身就蕴含着公共性的理解,故张江教授将本就有悠久传统的中国阐释学在现代化的生成中释义为“公共阐释”,并提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中国公共阐释理论[7]。这样,公共阐释就其自身语源而言就已具备了公共性这一根基,故此笔者认为,“公共”并不是对“阐释”的限定,而是对阐释之公共性的强调。
公共阐释的公共性根基不仅从语源上就植根于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即使站在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从西方人类理解与解释的思想历程来看,张政文认为,自古希腊肇始的认识的普遍性在20世纪遵从理性原则的哲人坚守下,也为公共阐释的构建提供了理性之维和公共性之基,并造就了公共阐释的理性原则、共享性原则与知识性原则[8]。并且,站在西方思想传统的视角看,公共阐释的公共性正是源于自古希腊以来就追求认识的普遍性与确定性这一西方传统。
公共性根植于阐释的语源内蕴和人类认识的确定性与普遍性追求之中,与此同时,公共性也为公共阐释的生成提供空间和场域。张江教授说:“阐释的公共性一定是从个人阐释、个体阐释开始的。”[9]那么,从个人阐释、个体阐释开始的阐释公共性如何孕生并最终造成个体阐释上升为公共阐释? 张伟认为,公共空间孕育与接纳个体阐释,并且正是在公共空间中,个体生成的阐释行为衍化为阐释活动的一般体例,进而为公共阐释的生成提供场域。而理性则对阐释行为具备着决定性意义,正是经由理性逻辑的启迪、遴选、整合与表达,使得对文本意义的体悟能生成到阐释这一阶段,进而使公共阐释成为可能[10]。这也就是说,公共性为公共阐释的生成提供了空间场域,理性则是公共阐释生成的逻辑路径。
阐释总是阐释者的阐释,因此,只有从阐释主体本身进一步考察其阐释活动,才能更好地揭示阐释的公共性,进而辩护公共阐释的有效性基础。基于对阐释主体的考察,张冰从人的心理结构、人的社会存在和阐释的语言系统三个维度探讨了阐释公共性的生成。从人的心理结构看,理性和观念的共享性以及人的感受甚至非理性层面的可分享性都可以表征阐释的公共性;从人的社会存在看,阐释者作为社会存在的先在传统和个体自我的历史性为阐释的公共性提供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维度;从语言系统看,阐释者阐释的语言系统由于其自身的公共规则和蕴含的传统维度确保了阐释的公共性并为阐释的公共性带来新的生机[11]。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张冰对阐释公共性生成的三个维度理解为:从阐释主体来看,人的社会性生成了阐释的公共性;从阐释工具来看,语言的公共性、普遍性生成了阐释的公共性;从阐释过程来看,理性活动的公共性生成了阐释的公共性。
张江教授批评强制阐释是一种背离文本而从既定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所做的符合阐释者主观意图的任意阐释与主观阐释[3],这样的阐释当然缺乏客观性。公共阐释则是基于文本而对文本所做的具有“普遍的历史前提”的客观阐释,因此,公共阐释具有客观性。张盾认为,真正具有说服力的阐释都是自由的、即携带着创造性理解的阐释,但这种“自由的创造”必须是“正确的”,其正确性就来自阐释的公共性与客观性。而阐释的客观性就在于阐释的公共性[12],因此,公共性保证的客观性也就为公共阐释自由创造的正确性和说服力提供了基础。
傅永军、杨东东基于程序主义的视角补充提出了公共阐释有效性建立的充分性要求,他们认为,只有将有效性基础建立在充分性和理性这两个基本要求之上,公共阐释才能成为具有合理的可公度性、反思性和建构性的阐释模式[13]。
无论是张江教授提出的公共性、理性,还是其他学者补充的客观性、充分性,这都为公共阐释提供了公共理性这一有效性基础的合理辩护。但是,公共性也好,理性也罢,只有上升为公共理性,它们才能成为公共阐释的有效性基础。那么,公共性和理性是如何上升为公共理性而成为公共阐释的根基?
张文喜认为,只有根据奠基于唯物史观的阐释学原则,深入理解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将公共性置于与人民性的联系中[14],公共阐释才成为可能。李潇潇从公共理性的存在证成视角肯定了张文喜的这一观点,并且进一步指出,只有将公共性置于与人民性的联系中,公共性才能在存在中证成理性的公共性,并进而上升为公共理性,从而为公共阐释奠定根基[15]。这样,基于唯物史观的人民性阐释学原则,我们就有可能为公共阐释找到一条从公共性到理性的公共性再到公共理性的牢固根基。
我们又如何从理性上升到公共理性从而为公共阐释的有效性基础辩护? 陈海在《阐释的“公共性”何以可能?》一文中指出,理性是有限的,个体理性可能是混沌的,个体理性要达到清晰的公共理性更要经历无数艰难,与此同时,公共理性还必须面对当代资本、阶层和新媒介技术的巨大挑战,这样,阐释的“公共性”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超越认知,进入审美以及超越个人现实界,进入公共虚拟场,我们还是可以期望它的实现[16]。
三、公共阐释的生成路径
公共理性为公共阐释提供了有效性基础,那么,公共阐释如何在公共理性这一根基上生成与绽放?
路径一:从“理”“性”之义的历史溯源中构建公共阐释的基本构架
既然公共阐释的有效性根基在于公共理性,那么厘清“理性”之义的词源涵义,当有助于历史地建构起公共阐释的“理性”之基。基于此,张江教授在《“理”“性”辨》一文中分别就“理”和“性”从东西方两条路径做了词(字)源考古。从文字学的视角看,张江认为,“理”在中国古代表现为实践理性,是实践智慧的直观表达,“性”在中国古代重在伦理之性,彰显的是人类自觉的道德追求;在西方,理性表达的是理论理性,“理”乃是理论智慧的逻辑表达。“东方实践智慧与西方理论理性之互补,相鉴相融之中,集合起阐释的全部价值与意义,在无限反思之长河中,趋向真理性认识。”[17]这样,当代中国公共阐释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就可以在弘扬中国古代文化与哲学传统、借鉴西方哲学及理性方法中构建起来。
路径二:从个体阐释经由社会阐释通达公共阐释
任何阐释首先是阐释者的个体活动,是作为阐释者的个体阐释。但是,人的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又总是社会性的,是在纷繁勾连的社会关系中展开的活动,因此,也正是在人的社会性活动中,阐释者的阐释活动在纷繁勾连的社会关系中获得他者的阅读、理解、接受、传播,并沿此路径最终上升为公共阐释。范玉刚教授就认为:“阐释之发生乃源自主体的阐释愿望,更确切地说是主体间的互阐互释。因而,从个体性阐释走向公共阐释,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必然。”[18]范教授只是认为在学理上主体间的互阐互释使得个体阐释最后走向公共阐释,其实,主体间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那样,也是在人的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因此,也正是在主体间的交往实践中的互阐互释,个体阐释走向了公共阐释,这样,通过主体间的互阐互释,个体阐释走向公共阐释就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而且也是阐释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进路。
阐释从阐释者的个体阐释活动开始,因此,张江教授认为,个体阐释是公共阐释的源头和基础[19]。但是,个体阐释本身无法直接通达公共阐释,从个体阐释到公共阐释之间有一个中介,那就是社会阐释[20]。在约翰·汤普森看来,由于西方社会阐释的公共领域这个阐释活动生成与展开的空间是由不同形式的权力所塑造的,是结构化的空间,因此,在这样一种由不同形式的权力所塑造的结构化中间中生成与展开的阐释活动就是社会阐释[20]。社会阐释作为个体阐释通达公共阐释的中介是多元的、碎片的、对立的、冲突的,只要再次经过过滤的、理性的、有序的阐释,社会阐释就会最终过渡到公共阐释。因此,张江教授提出:“在个体阐释当中有一种社会阐释,社会阐释以后有一种公共阐释。”[20]从个体阐释经由社会阐释通达公共阐释,这就是公共阐释生成的一条基本路径。
路径三:从观点、方法、氛围出发通向公共阐释
江守义认为,在公共阐释活动中:“阐释者总要针对阐释对象的某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且总是要从某个角度用某种方法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同时,这些观点和看法要经过同行的评议和时间的检验,才有可能被学界接受,成为公共阐释。”[21]基于此,他提出从观点、方法、氛围出发形成公共阐释提供观点、提炼方法、营造氛围的路径。首先,阐释活动总是阐释者针对阐释对象展开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这种活动的展开过程中,阐释者首先必须提供自己的私人观点,并通过在“阐释与对象、对象与接受、接受与接受之间”形成共通性,阐释者的私人观点在公共视域中成为可理解被接受的观点,并由此通向公共阐释。其次,阐释活动中阐释者不仅提供自己的观点,也需要提炼方法,当阐释者在阐释活动中提炼的阐释方法被证明为可行的方法并在阐释活动中得到广泛的使用时,这样的方法也就是具有了公共性的阐释方法,这样的阐释方法运用下的阐释活动也就会成为一种公共阐释活动。再次,通过让某种阐释观点或方法形成自己的时代性或地域性、凝聚阐释的指导性方向、树立新的价值观或文艺观,从而营造公共阐释生成所需的公共视域氛围,为公共阐释提供讨论的空间,形成通向公共阐释的生成路径[21]。
路径四:构建共在的阐释共同体生成与实现公共阐释
张江教授指出,人类的共在决定了个体阐释的公共基础。在这一论断基础上,李永新提出了构建共在的阐释共同体以生成与实现公共阐释这一途径[22]。在李永新看来,阐释共同体是公共阐释形成与实施的基本要件,对于公共阐释的生成以及在公共阐释论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地位和意义。阐释共同体是一个具体的共在,是充满生命力的有机体,其内部既存在着权威,也能够相互默认一致。由于共在的阐释共同体其成员共同参与阐释活动从而形成一个共享的阐释空间,阐释共同体自身的历史演进使得其构成和成员能够与发展着的世界形成共契关系,并且阐释共同体通过创造平等交流的环境而使其成员通过合理交往达成共识,这样,通过构建共在的阐释共同体就能够生成与实现具有共享、共契、共识特点的公共阐释[22]。
四、公共阐释的内在隐忧
公共阐释理论为陷入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泥沼的西方阐释学找到了一条希望之路,也为中国古代阐释学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了可行的现实路径。但是,建立在公共理性根基之上的公共阐释也存在着一些内在的隐忧。
公共阐释的有效基础之一在于阐释是一种理性活动。但是,正如韩东晖所担忧的,阐释学面临的难题,就是既要限制纯粹理性的过度膨胀,同时又不陷入相对主义的沼泽[23]。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反理性的主张固然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相悖逆,也搅乱了人类的认识与思想走向,但是它们对于理性弱点的反思和对理性僭越的批判却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于纯粹理性过度膨胀的警惕。按照张江教授的公共阐释理论假设,公共阐释可以有效防止相对主义,但如何保证其能够有效避免纯粹理性的过度膨胀? 虽然韩东晖指出,公共性与规范性的实质性结合可以使公共阐释将公共性讲道理、讲真话的精神和力量充分展示出来,但是,公共性与规范性的实质性结合本身却是建立在公共阐释的公共理性活动这一根基之上的。可是,在公共空间这一场域中,理性如何保证对自身的约束而不至于使阐释成为一种强权意志的理性工具?
谭安奎则在《公共理性与阐释的公共性问题》一文中表达了对公共阐释以客观性自居从而走向专断阐释的担忧。尤其是对于历史、政治文本这样的文本对象的阐释,阐释活动鲜明地表现为约翰·汤普森所说的象征性权力,它是对公共权力、政治法律制度运作与实施的判断、理解、解释与宣传,而公共权力、法律等本身的强制性特征极有可能导致我们在基于公共理性的阐释活动中“以认知客观性的名义,或者以公共性的可接受的名义,强行达到某种一致性或确定性”。这样,“相对于公共阐释论所批判的那种强制阐释,这有可能是导向了另一种形式的强制阐释”[24]。李潇潇也提出,要谨防公共阐释在对公共性的普遍性与客观性的理解基础之上以真理自居,从而造成公共阐释在批评西方强制阐释之际自身却沦为专断的阐释。为此,李潇潇认为,公共阐释就必须从认识论层面继续展开探索与研究,找到与自己相融的真理观,避免自己在以真理自居之际沦为本是自身批判对象的专断阐释[15]。
在与张江教授的对话中,约翰·汤普森指出,阐释是一种象征性权力,这样,阐释活动就不仅仅是社会的和公共的,而且是与冲突、利益等交织在一起的[20]。当以公共权力和政治法律制度为文本对象的公共阐释在社会生活中与冲突、利益等交织在一起,我们就确实非常有必要警惕公共阐释的权力寻租了。或许正是出于对公共阐释寻租权力的担忧,约翰·汤普森说,“阐释学不是用来将权力或者权力结构合法化的,而是要更为激进,向权力提出挑战”[20]。汤普森的这一主张或许真的如其所言过于激进,但是,即使是对公共权力和政治法律制度做出辩护性阐释,公共阐释也需要做到在置人民性于公共性和客观性的阐释语境中展开反思性的辩护阐释。
哈贝马斯则在与张江的对话中以德国历史上的宗教势力和纳粹政府为例异常隐晦地表达了公共阐释可能会毒害国家的政治文化的担忧。在哈贝马斯看来,以公共权力和政治法律制度为文本对象展开的公共阐释,或许会导致“只要一种文化占统治地位”,同时还有可能会造成“集体否认重要事实”的事件发生,若如此,则“可能毒化政治文化”,对于公共阐释理论的框架构建和未来发展,“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重视和关注的”[7]。
如果公共阐释是以公共权力和政治法律制度为文本对象的辩护性阐释活动,这样的阐释活动则就既是一种公共行为,也同时是一种意识形态行为,基于此,沈江平、孟桢提出了公共阐释过度意识形态化的担忧[25]。在沈、孟二人看来,阐释活动的展开总是以一定的平台、空间为依托,公共阐释活动得以展开的公共平台、公共空间等场域都是在社会中酝酿和构建的,这样,公共阐释活动依靠的公共平台、公共空间就必然带有所属社会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此同时,作为公共阐释对象的文本本身和文本表达依托的语言也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这样,公共阐释活动也就必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活动。在公共阐释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活动中,不排除异于公共理性的阐释行为存在,从而造成公共阐释的过度意识形态化。沈、孟二人提出,要避免公共阐释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就“要协调文本和阐释之间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建立个体阐释的公共约束机制,尊重文本的‘相对独立性’,保持文本与阐释者之间的有效对话”[25]。
五、展望
反理性、反基础、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强制阐释导致了真理的放逐、价值的失落和历史的碎裂[26],当代人类精神无依的浮萍状态呼唤新的文艺理论范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江教授提出了公共阐释理论。在新时代语境下,公共阐释论的提出也深度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27]的深切要求与殷切期望。李潇潇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为公共阐释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与条件,将公共性与人民性紧密相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本身就是公共阐释[15]。可见,无论从理论研究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中,公共阐释理论的生成与发展都有深厚的土壤。
目前,公共阐释理论只是具备了一个粗略的理论框架和雏形,我们对这一理论的理解有待深入、阐释有待拓展、传播有待扩张、接受有待普及。要成为一个深刻且有广泛影响的理论体系,公共阐释论仍有许多理论难题需要解决,诸如:
第一,“阐释”还是“诠释”? 在江怡看来,张江教授对于“阐”之植根于深厚中国传统哲学和历史渊源的阐发是以“字本位”为特征的中国文字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传统讨论的主要内容一样,“阐释”对意义的解释也需要遵守解释主体介入和解释文本独立这两大基本原则。张江教授的“阐释”语境生成于对文本展开的文学诠释,而西方诠释学在由神学解释学向哲学诠释学演进的过程中则已经从文本诠释突破和上升到思想阐释。如果说对于文本的文学诠释聚焦于文本的心理意义,那么哲学阐释就必须超越语言去把握文本之外的意义。文本诠释也好,思想阐释也罢,在江怡看来,这不过是通向真理的不同道路[28]。但是,作为有别于“强制阐释”的“公共阐释”,其“阐释”之公共性的获得不仅在于“阐”之“字本位”的哲学传统和历史渊源,还需要更进一步地从阐释对象、阐释方法、阐释过程、阐释意义等方面去夯实其公共性之基础。因此,就概念而言,“公共阐释”的“阐释”之内涵有待进一步明晰和阐发。
第二,与西方诠释学一样,公共阐释也必须是一个理解、解释和应用的过程。虽然理解、解释和应用三者相互作用,但解释和应用实际上也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的理解过程。理解的标准是达到真、善、美这三者的和谐统一[29]。那么,在真善美统一的理解标准规范下,公共阐释如何才能有别于并超越于强制阐释? 公共阐释如何实现真善美统一的理解标准规范下之“非强制”的自我辩护?
第三,公共性指谓的是阐述的空间场域,理性指谓的是主体阐释的思维状态,二者如何契合成就公共理性? 或者如何保证在公共空间的表达为理性的表达进而上升为公共理性? 又或者如何使得理性在公共空间中得以表达并上升为公共理性?
第四,公共理性到底是如何消解个体理性或个人非理性或公共非理性而成为公共阐释的有效性根基的? 或者说,公共理性是如何生成为公共阐释的有效性根基的?
第五,个体理性如何在公共空间的表达中经社会理性上升为公共理性? 上升路径是怎样的或者说有哪些? 非理性在这种上升路径中有什么样的作用或者是如何被消解的?
第六,公共阐释的本体论基础是什么? 如果是作为共在的人类或人类的共在,那么,人首先是作为个体的人,然后才是社会共在的人,人的个体性如何在公共阐释的本体奠基中不被敉灭?
第七,公共阐释的认识论基础是什么? 也即是李潇潇所说的,与公共阐释相融的真理观如何生成?
只有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概念上明晰、逻辑上自洽、理论上完备的公共阐释理论体系才可能真正构建起来。
——关于海德格尔的“那托普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