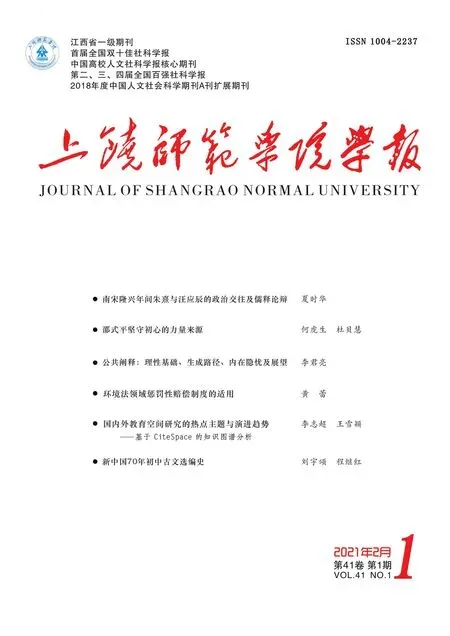南宋隆兴年间朱熹与汪应辰的政治交往及儒释论辩
夏时华
(上饶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上饶334001)
汪应辰(1118—1176),字圣锡,信州府玉山县(今上饶市玉山县)人,自幼聪慧过人,绍兴五年(1135)17岁中进士第一,后因反对秦桧议和而遭贬谪达17年之久。秦桧死后,汪应辰遂受重用,勤政有为,刚正清廉,颇有名望,官至吏部尚书,卒谥文定公,人称玉山先生。汪应辰系朱熹从表叔,他十分赏识朱熹的学识和才能,多次举荐朱熹,甚至在朝廷授予他敷文阁待制时荐举朱熹自代,可见俩人情谊之深厚。
绍兴三十一年(1161)五月,金主完颜亮即位,再次入侵南宋。九月,便以号称百万兵马,分四路大举南下。南宋朝廷围绕着与金是战还是和进行激烈争议。金军南下,宋军不战而溃,一个月左右金兵进抵长江北岸。十一月初,虞允文以参谋军事身份担负起指挥责任,在采石渡大败金兵。采石渡江失败后,完颜亮被部将射杀,金军北归。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孝宗即位,决意北伐。隆兴元年(1163)四月,孝宗下达北伐诏令。由于宋孝宗和刚被起用的张浚对这场北伐战争都缺乏必要准备,加上前线将领李显忠和邵宏渊不和,相互之间缺乏配合,所以符离一战,宋军溃败。符离之败沉重打击了宋孝宗北伐雄心,他开始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此后主战派人士陆续被排挤出朝廷,以汤思退、钱端礼为首的主和派得势。宋金双方于隆兴二年(1164)冬签订和约,史称“隆兴和议”。
隆兴北伐与和议期间(1163—1164),朱熹和汪应辰都反和主战,密切关注和战局势进展,政治交往频繁,并就儒释、苏学邪正问题进行论辩。目前为止,前人对于朱熹和汪应辰的交游有所涉略①对于朱熹和汪应辰交游有所涉略的研究主要有:沈莹莹《汪应辰师友交游渊源略论及汪氏著作流传情况》(北京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日本伊原弘《宋代知识分子的基层社会——以汪应辰的交流系为中心》(李华瑞编《宋史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第456页);邹挺超《朱熹的交往关系研究》(厦门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刘佩芝《朱熹同汪应辰的交游与交锋——以〈文定集〉为中心考察》(《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9辑,第179—186页)等。,但对于隆兴年间朱熹与汪应辰的政治交往和儒释论辩似乎缺少专门论述。为此,笔者拟以南宋隆兴北伐与和议为背景,对朱熹与汪应辰在这一期间的政治交往及儒释论辩状况进行探述,以窥当时他们的思想交流及相互影响。
一、隆兴年间朱熹与汪应辰的政治交往
(一) 隆兴北伐期间的政治交往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面对金军大肆南侵,宋高宗宣告退位。宋孝宗即位,诏求直言。这时朱熹在老师李侗的影响下,正由恬淡退守转向关注现实。八月,在李侗指点下,朱熹第一次向朝廷上书,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要求宋孝宗摒弃佛老,以儒学为正学;第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痛斥对金讲和之说,要求宋孝宗及早制定主战计划;第三,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本原之地即朝廷,对其须作好整顿[1]卷11《壬午应诏封事》,577。
这年十月,汪应辰出知福州,在建安与表侄朱熹首次相会,一见如故,叹其足为远器。之后汪应辰立即请朱熹来福州帮忙。在朱熹帮助下,汪应辰实施更革,废除苛政。但对于盐法问题,汪应辰未采纳朱熹意见。汪应辰在给宰相陈康伯的信中对此事作了解释:“惟是卖盐一事,顷岁承乏,见帅司财用窘迫殊甚,尝谋于郑少嘉、朱元晦、陈季若,惟元晦以谓宁可作穷知州,不可与民争利,而少嘉、季若则以为可,故于三人中从二人之言。”[2]卷16《上陈丞相》,176可见,朱熹在盐法问题上是站在不与民争利的立场上来考虑的,而汪应辰等人考虑更多的则是如何解决当时福州帅司财用窘迫问题,故未采纳朱熹意见。然而朱熹还是对汪应辰的为政作了高度评价:“停卖僧田,烦扰顿息,为利不赀。追还拣兵官,亦甚快舆论,……侍郎以忠恕之心,行简易之政,简策所载甚无越此二者。”[3]189
隆兴元年(1163)正月,宋孝宗任命主战派张浚为枢密使兼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锐意北伐的态度渐趋明朗。三月,朝廷召朱熹赴行在临安。朱熹此次被召主要是出于汪应辰的两次极力荐举。先是汪应辰得知官员傅钅共即将致仕,因而他致书吏部侍郎陈俊卿,力荐朱熹,希望能帮朱熹补缺谋职:“乞辟差元晦,敢望同凌丈见宰执言之,如许得的确,方敢申上也。”[2]卷14《与吏部陈侍郎》,143后 又 致 书 陈 俊 卿,荐 举 朱熹:“朱迪功熹,进修日新,殊未可量也,不知朝廷有以处之否。”[2]卷14《与吏部陈侍郎》,143其中“宰执”是指宰相陈康伯,可见朱熹此次被召应是汪应辰、陈俊卿、陈康伯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年春,汪应辰邀请朱熹来福州,正值落职福州的将领刘宝准备前往江淮前线。汪应辰和朱熹一同送他赴任,议论北伐用兵问题。汪应辰问刘宝:“今太尉去时如何?”刘宝回答说:“与金人战时,第一阵决胜;第二阵未可知;第三阵杀他不去矣! 盖此中只有些精锐在前,彼敌不得,他顽不动;第三四阵已困于彼矣。”汪应辰感叹道:“刘大将如此说了,却如何!”[4]卷130,3767刘宝的回答使汪应辰和朱熹对于即将开始的北伐平添了几分忧虑。
面对北伐,宋孝宗却是摇摆不定,一面要北伐,一面又重新起用一贯主和的近习龙大渊、曾觌。龙、曾两人恃宠弄权,排斥许多主战官员,一时间朝中乌烟瘴气。对此汪应辰非常担忧,致书朱熹告知朝廷主战人士遭受打击的情况:“谏省二公论龙大渊、曾觌未报闲,却各除知阁,仍兼旧职。金给事、周舍人相继论其不可,中批语甚峻,二人皆待罪。有旨无罪可待。刘谏除工侍,而张真甫以待制知会稽”[2]卷15《与朱元晦》,154。朱熹从信中得知朝廷此状,于是决定在四月上辞状,不赴临安。朱、汪俩人在闽常读邸报,继续密切关注北伐局势。
隆兴元年(1163)五月符离一战,宋军大溃败。符离之败重挫宋孝宗北伐雄心,使其在和战之间更加摇摆不定。此后朝廷主战派人物陆续遭排挤,以秦桧的党徒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又得势。朱熹则在给友人魏元履的信中十分中肯地分析了隆兴北伐失败原因:一是宋孝宗、张浚缺乏充分谋划和准备,盲目用兵;二是主将李显忠与邵宏渊相争不和,贻误战机,以及士兵骄惰,缺乏战斗力;三是朝廷忽战忽和,摇摆不定[3]193。通过隆兴北伐失败,朱熹看到当时国家之忧不在边境,且在朝廷自身。
(二) 隆兴北伐失败后的政治交往
隆兴元年(1163)七月,汪应辰除敷文阁待制,他举荐朱熹自代:“伏睹左迪功郎监南岳庙朱熹,志尚宏远,学识纯正,…… 举以代臣,实允公议。”[2]卷6《除敷文阁待制举朱熹自代状》,44在汪 应 辰、陈 俊 卿、陈康伯等人再次荐举下,朱熹被宋孝宗召赴行在临安入奏登对。可能是受“国家之忧且在朝廷”思想的影响,朱熹一改过去一再辞免应诏的态度,并再次在老师李侗的指点下精心准备奏札,慨然赴临安登对。这年十一月六日,在垂拱殿里,宋孝宗召见了朱熹。朱熹面奏三札,直接针对现实的对金和战问题:第一札,再次批评直指宋孝宗沉湎佛老,希望宋孝宗“是以意诚心正而身修,至于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亦举而措之耳”[1]卷13《垂拱奏札一》,632;第二札,分析了朝中主和、主战、主守三家之论,以三纲五常来论证宋金的不共戴天之仇以及抗金用兵的正义性,进而提出收复中原方略;第三札,朱熹指出纪纲未立,希望宋孝宗内修政事[1]卷13《垂拱奏札一》,637。
当时汪应辰写信给朱熹,期望他此次登对有所作为:“窃计诚心正论,从容献纳,所以开悟上意者多矣。”[2]卷15《与朱元晦》,153并愿得知登对详情,可见汪应辰等友人对朱熹登对也充满希望。然而当时举朝处于议和与佞佛的氛围之中,朱熹如此郑重其事,结果却只得武学博士一闲职,且在家待阙四年,不能有所作为,可见朱熹期待继续北伐的愿望受挫极深。但汪应辰在给喻居中的信中还是高度评价朱熹在临安登对时的反和主战抗争:“朱元晦以召命再下,诸公迫之方行。既对,力排众议,其他皆人所难言者。”[2]卷16《与喻居中》,176面奏受挫后,十二月初朱熹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张浚身上,希望他能重整旗鼓继续北伐,并向张浚呈献分兵进取中原大计,然而张浚只是答以“某只受一方之命, 此事恐不能主之”[4]卷110,3276,这使得朱熹感到张浚志大才疏,北伐希望渺茫。
由于南宋议和使节受辱而归以及议和条件苛刻,在和战问题上摇摆不定的宋孝宗又一次倾向主战,于隆兴元年(1163)十二月底,重新起用张浚,任其为右相,再都督江淮军马。这又让汪应辰和朱熹再次燃起了北伐收复中原的希望。汪应辰于隆兴二年(1164)初写信邀请朱熹到福州会面,商讨和战问题及研讨学问:“魏公(即张浚)再往淮上,其意必有不可得而闻者。……窃闻朱元晦他日必再到延平,倘因而下顾,莫大之幸。”[2]卷15《与朱元晦》,154接到来信,朱熹于二月初在延平祭吊老师李侗之后,到福州和汪应辰相见,待了整整一个月。后来汪应辰在与吕叔潜的信中回顾称赞:“朱元晦到此,一月而归。其学问精进,所养益厚,所谓日新而未见其止也。”但也对当时江淮局势表示担忧:“魏公再相,虽出独断,不知能行其志否? 种种似未免俯就,虽古人有之,亦已难矣。两月之间,并未见其施设,必有所甚重者,徒令善类瞻仰而已。”[2]卷15《与吕叔潜》,158此后不久,汪应辰又写信告诉朱熹,两淮前线张浚仍受主和派牵制,难以有所作为:“魏公与水军统制魏尚复官,言者以为不可乃止。遣王、钱两侍郎抚谕两淮,仍措置,他无所闻。”[2]卷15《与朱元晦》,154其 中“言 者”指 主 和 派,“王、钱”分指王之望、钱端礼,系当时主和派主要人士。
随着两淮局势恶化,汪应辰再次邀请朱熹来福州商讨和战问题:“谨遣听使令,自此数日,以待来临。”[2]卷15《与朱元晦》,154并告诉朱熹当时主和派王之望、龙大渊、洪适等人想方设法促使宋孝宗罢免张浚的情况。宋孝宗在主和派的蛊惑下,终于下诏罢江淮都督府,张浚于四月二十四罢相离朝。至此,张浚这面主战旗帜彻底倒下。朱熹、汪应辰虽然在福州再次会见,但无奈他们北伐恢复中原的希望也再次随之破灭。
面对当时无奈的局势,汪应辰也赞成自治。早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汪应辰在奏议中就提出:“为国者不当问敌人之盛衰,顾吾自治何如尔。”[2]卷2《应诏陈言兵食事宜》,10后来汪应辰又上《论御戎以自治为上策》,提出和、战、守三者皆末和自治为本的思想[2]卷7《论御戎以自治为上策》,64。朱熹自福州归后,致书汪应辰,毫不留情地批评其自治思想,认为其所谓自治动摇了北伐收复中原的主张:“今欲以讲和为名,而修自治之实,恐非夫子正名为先之意。内外心迹判为两途,虽使幸而成功,亦儒者之所讳也。……必以摇动为虑,则所谓自治者,其惟闭关固圉,寇至而战,去不穷追,庶可以省息劳费,蓄锐待时乎? 以此自治,与夫因机亟决、电扫风驰者固不同,然犹同归于是。”[5]卷30《答汪尚书二》,1297
汪应辰在隆兴二年(1164)五月改除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入朝奏事。七月,汪应辰由福州北上经由崇安同朱熹又一次相见,主要是与朱熹商讨入对事宜。之后,汪应辰前往临安。朱熹又给汪应辰写信,陈述自己在和战问题上的看法:一是主张修德与修力兼举,治夷狄之道与攻夷狄之道并用;二是希望汪应辰劝导宋孝宗致力于正心诚意、诚身明善,消除主和的太上皇赵构与主战的宋孝宗之间的所谓两宫异论,以图北伐大计[5]卷30《答汪尚书三》,1299;三是对汪应辰此次入朝应对寄予厚望,希望汪应辰能担当重任,借此入对机会能“诚身几谏以冀感悟”开启宋孝宗,改变局势[5]卷30《答汪尚书三》,1297。
然而,主战派在张浚被罢免后早已群龙无首,主和派首领汤思退大权在握,于七月将江淮的布防重镇撤戍,王之望除参知政事,并任魏杞等为金国通问使,继续向金妥协求和,至此朝中议和大局已定。鉴于此,汪应辰自感无奈,已难以改变局势,不得不将朝中议和大势已定的情况写信告诉朱熹:“某到阙下,留旬日,两得入对,……行止非人所能,良以自叹也。敌遣使请和,朝廷亦欲报之,闻海、泗皆已撤戍矣。”[2]卷15《与朱元晦》,156
隆兴二年(1164)冬,南宋王朝不得不再次同金签订屈辱和约,史称“隆兴和议”。就在隆兴和议签订之后一个多月,宋孝宗忽又诏命朱熹赴临安供所谓武学博士的虚职。朱熹本来要待阙四年,这次却在隆兴和议刚成的背景下提前供职,使他有所疑虑。汪应辰写信给朱熹,提出了劝其前往临安一行的几点理由:一是丞相陈康伯“尝作书相招,又以堂贴促行”;二是要无愧于道:“元晦当一来,似无可疑。若既到之后,或有未安,又在我矣。要之,自处既尽,然后可无愧于道也。愿以此道为准,不必过为疑虑。”[2]卷15《与朱元晦》,156
接汪应辰来信,为无愧于道,为争取仅存的一丝北伐希望,朱熹决意再赴临安抗辩。然而一入临安,朱熹就感受到当时朝廷上下沉沦于隆兴和议后苟且偷安的浓烈氛围。对此,朱熹自感一人抗辩难起作用,不愿在朝供职,只得再次请祠,愤而归闽。同时,朱熹投书吏部侍郎陈俊卿,非常愤慨地驳斥了主和派钱端礼之徒为和议粉饰太平而炮制的“议和”之说、“独断”之说、“国是”之说等三大谬论[5]卷24《与陈侍郎书》,1207。自临安归闽后,朱熹为好友魏元履《戊午谠议》作序,对屈辱的绍兴和议与隆兴和议作了深刻总结,指出绍兴和议与隆兴和议的前后因果联系,揭露秦桧之罪“唱邪谋以误国”以喻指主和派汤思退、钱端礼之徒,正是他们的奸谋使得当时“人伦不明,人心不正”“三纲未能复振,万事未能复理”[6]。因此,朱熹决意潜研理学以明人伦、正人心、复振三纲,使万事复理,从根本上挽救国家衰颓之势。而这时汪应辰也已在四川担任制置使、知成都府,又开始他的一段“外王”历程。
上述可见,隆兴年间宋孝宗对于和战问题举棋不定,朝廷主战、主和两派政治力量的相互博弈,使得隆兴北伐与和议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漩流。朱熹和汪应辰都反和主战,密切关注和战局势进展,围绕和战问题的政治交往也随着这一政治漩流而起伏不定。隆兴北伐前朱、汪反和主战,对于北伐既期待又有所担忧;隆兴北伐失败后,朱、汪俩人仍继续努力抗争,并寄希望于宋孝宗能够重整旗鼓北伐。然而宋孝宗最终倾向主和,主和派得势,主战力量遭到彻底打击排挤,1164年底隆兴和约签订,从而朱、汪俩人主战北伐收复中原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期间朱、汪俩人围绕和战问题的政治交往密切,数度音书会晤,相互砥砺前行。
二、隆兴年间朱熹和汪应辰的儒释论辩
宋孝宗隆兴北伐与和议期间,朱熹和汪应辰俩人还就与当时和战现实有关的儒释邪正问题展开系列论辩,这又成为他们当时政治交往和思想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
朱熹从隆兴北伐失败中看到,当时国家之忧不在边境而在朝廷,在于以宋孝宗为首的朝廷上下沉溺佛学、君心不正、纲纪不振。因此,朱熹在应诏封事、面奏登对中两次批评宋孝宗沉迷佛学,期望宋孝宗能摒弃佛学,致力于正心诚意,诚身明善,肃振朝廷纲纪,以图北伐大计。鉴于此,朱熹决意对佛学进行批判清算以正儒学,而这一批判正是从他与汪应辰的儒释论辩开始的。汪应辰曾学佛于张九成和看话禅师宗杲,朱熹对此批评指出:“张无垢(即张九成)参杲老(即宗杲),汪玉山被他引去,后来亦好佛。”[4]卷126《释氏》,3856隆兴元年(1163)宗杲去世时,汪应辰远在福州也写下祭文哀悼他。汪应辰的好佛也成为朱熹批判佛学的一个重要诱因。
隆兴元年朱熹将罗从彦《龟山语录》寄给汪应辰,汪应辰回信对《龟山语录》中一些“可疑者”即语涉佛学之处问朱熹。朱熹在信里表示对《龟山语录》中杨时杂引佛学之说表示不满:“以此知异学决不可与圣学同年而语也明矣。”他认为杨时引用佛老之说还只是一种语言表达上的借用,“然恐此类皆是借彼以 明 此, 非 实 以 为 此 之 理 即 彼 之 说也”[5]卷30《答汪尚书一》,1292。俩人由此拉开了儒释邪正问题的论辩。
朱熹与汪应辰在福州的两次相见和在崇安的一次相见,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即是“儒释邪正之辨”。隆兴二年(1164)五月,朱熹在给汪应辰的信中首先对自己早年误入好佛和后来逃禅归儒的历程作了深刻的自我检讨:“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其始盖未尝一日不往来于心也。以为俟卒究吾说而后求之,未为甚晚耳,非敢遽绌绝之也。”[5]卷30《答汪尚书二》,1295同时朱熹在信中还对理学前辈好佛问题作了评论:
然则前辈于释氏未能忘怀者,其心之所安盖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则岂易以□□口舌争哉? 窃谓但当益进吾学,以求所安之是非,则彼之所以不安于吾儒之学,而必求诸释氏然后安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
上蔡所云止观之说,恐亦是借彼修行之目,以明吾进学之事。若曰彼之参请,犹吾所谓致知,彼之止观,犹吾所谓克己也。……胡文定所以取楞严、圆觉,亦恐是谓于其术中犹有可取者,非以为吾儒当取之以资己学也。[5]卷30《答汪尚书二》,1296
可以看出,朱熹虽然温和地批判了包括汪应辰在内的好佛士大夫们的三道同源说,但他实际上还是以开放态度对待理学前辈们好佛的问题。朱熹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对待佛学的几条原则:一是可以借佛学来说明儒学,但不是儒佛同道;二是佛学中有儒学可取的成分,但不是儒佛相成,这从大体上说具有反佛学的意义[3]225。但同时朱熹又向汪应辰表示:“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此言诚有味者。故熹于释学虽所未安,然未尝敢公言诋之。”[5]卷30《答汪尚书二》,1296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了朱熹自己反佛态度上不够坚决。
隆兴二年(1164)十月,朱熹在给汪应辰的信中又用二程的格物说批判了其老师张九成、吕本中等前辈读书讲义失于太高,企图走捷径而迷惑于佛学顿悟之说:“大抵近世言道学者,失于太高,读书讲义,率常以径易超绝、不历阶梯为快,而于其间曲折精微正好玩索处例皆忽略厌弃,以为卑近琐屑,不足留情。以故虽或多闻博识之士,其于天下之义理,亦不能无所未尽。理既未尽,而胸中不能无疑,乃不复反求诸近,顾惑于异端之说,益推而置诸冥漠不可测知之域,兀然终日,味无义之语,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 不 知 物 必 格 而 后 明, 伦 必 察 而 后尽。”[5]卷30《答汪尚书三》,1297朱熹进而强调必须专致儒学,循下学上达之序而躬行力究,宁拙毋巧,从容潜玩,才能众理洞然,才能立吾儒之本而明鉴佛老之诐淫邪遁。朱熹信中表示,“每以儒释邪正之辨为说,冀或有助万分”[5]卷30《答汪尚书三》,1298,委婉地希望有助于汪应辰勉而进之,专致儒学,能摆脱佛学影响。
隆兴二年(1164)冬,汪应辰赴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而蜀中正好是苏学流行之地。当时宋孝宗与朝廷士大夫也崇尚苏学,沾染好谈佛老习气。因此,朱熹同汪应辰的儒释论辩很快又扩大到对苏学邪正之辨上。当时理学家们大多攻击王安石之学,但对苏学多加崇护。事实上苏轼、苏辙等人也取用佛老思想,这与汪应辰老师张九成、吕本中等人以儒兼佛有着同样的思想路径。因此,朱熹与汪应辰的苏学邪正之辩实际上还是儒释邪正问题的论辩。
当时汪应辰认为苏轼与欧阳修、司马光同样高致,不能将苏学与王学混为一谈同贬。对此,朱熹分别加以辩驳。首先,朱熹指出欧阳修、司马光坚守圣贤之高致,非王安石、苏轼所能比:“盖司马、欧阳之学,其于圣贤之高致,固非末学所敢议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旧,特恐有所未尽耳。至于王氏、苏氏,则皆以佛老为圣人,既不纯乎儒者之学矣。”[5]卷30《答汪尚书四》,1299其次,针对汪应辰所讲的苏学不可与王学混为一谈,朱熹认为苏学与王学殊途同归,都以佛老为圣人,不客气地指责汪应辰所讲“乃浅陋辞不别白、指不分明之过”,并对之进行了详细的辩驳:
而王氏支离穿凿,尤无义味,至于甚者,几类俳优。本不足以惑众,徒以一时取合人主,假利势以行之,至于已甚,故特为诸老先生之所诽诋。……至若苏氏之言,高者出入有无而曲成义理,下者指陈利害而切近人情。……然语道学则迷大本,论事实则尚权谋,炫浮华,忘本实,贵通达,贱名检,此其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亦岂尽出王氏之下也哉? 但其身与其徒皆不甚得志于时,无利势以辅之,故其说虽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尽见,故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论。[5]卷30《答汪尚书四》,1300
最后,朱熹表示自己极言至此,恐汪应辰未以为然,希望他“胡不取熹前所陈者数书之说而观之也。以阁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据正道以黜异端”[5]卷30《答汪尚书四》,1300。
汪应辰来信认为苏轼早年曾力辟禅学,晚年是“凡释氏之说,尽欲以智虑臆度,以文字解说,如论成佛难易而引孟子仁义不可胜用”[2]卷15《与朱元晦》,155;苏辙也曾先后作《传灯录解》《老子解》,是要和会儒释老三家为一,苏氏的好佛老不过是“习气之弊,窃以为无邪心”[2]卷15《与朱元晦》,155。朱熹则指出,苏轼早年辟禅学,“岂能明天人之蕴、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诞浮虚之说,而反之正哉? 如《大悲阁》、《中和院记》之属,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据彼之外以攻其内,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叶而疑本根,亦安得不为之诎哉?”[5]卷30《答汪尚书五》,1302
针对汪应辰所讲的苏氏好佛老乃习气之弊而无邪心,朱熹则反驳指出:
熹窃谓学以知道为本,知道则学纯而心正,见于行事、发于言语,亦无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学不纯,而设心造事,遂流入于邪。……苏氏之学虽与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为是则均焉。学不知道,其心固无所取,则以为正,又自以为是而肆言之,其不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祸而已。其穿凿附会之巧,如来教所称论成佛、说老子之属,盖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谓汤武篡弑,而盛称荀彧,以为圣人之徒。凡若此类,皆逞其私邪,无复忌惮,不在王氏之下。[5]卷30《答汪尚书五》,1303
乾道元年(1165)春,汪应辰在回信中又用“文章之妙”为苏氏辩护,指出虽然朱熹“示论苏氏之学,疵病非一”,然而“今世人诵习,但取其文章之妙而已,初不于此求道也,则其舛谬抵牾似可置之。……蜀士甚盛,大率以三苏为师,亦止是学其文章步骤”[2]卷15《与朱元晦》,155。朱 熹 对 此 作 出 回 应 并 批 驳 指出:“夫学者之求道,固不于苏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则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 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5]卷30《答汪尚书六》,1305
至此,朱熹与汪应辰这番儒释邪正之辩告一段落。其实同一期间朱熹也先后与罗博文、江元适、李伯谏、程洵等人进行了儒释邪正论辩,然而较为突出的还是与汪应辰的论辩。正是通过这番论辩,朱熹对于儒释邪正问题的看法日益明晰,在此基础上完成著作《杂学辨》,既对自己早年误入佛老的自我检讨,又对当时朝野上下浸淫的佛老之风进行了有力批判,为其后来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迈出坚实一步。同时通过这番论辩,汪应辰也逐渐接受了朱熹的批评,辟佛归儒,后来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高度评价汪应辰:“其骨鲠极似横浦(即张九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似紫微(即吕本中),而未尝佞佛,粹然为醇儒。”[7]
上述可见,儒释邪正论辩在朱、汪当时政治交往和思想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思想交流及相互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
三、结语
南宋隆兴北伐与和议期间,朝廷围绕着和战问题大体形成三派:一是主战派,以张浚为首,主张立即北伐用兵,收复中原;二是主守自治派,以宰相史浩、陈康伯等为首,他们既反对向金屈膝投降,也反对冒险对金用兵,主张以守自治,在国家物力、军力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再行北伐;三是主和投降派,以汤思退、龙大渊、钱端礼等为首,主张对金妥协求和。
如前所述,朱熹力挺主战派,主张北伐用兵收复中原。其实,朱熹主战思想与其家学影响密切相关。其父朱松(1097—1143)生在国破家艰之秋。担任尤溪县尉时,正遭遇靖康之变,朱松忧国忡忡,累上奏折,力抗和议,提出恢复中原之策。南渡后绍兴八年(1138)四月,秦桧复相,专主议和。朱松同样上疏抗论和议,主张抗金,因此触怒得罪权相秦桧,后被贬出任知饶州,而朱松不赴以示抗议,弃官隐居,遂不复起。可见朱松主战恢复中原之志始终不变。在父亲去世后,朱熹遵嘱迁居福建崇安五夫里,依靠父亲好友刘子羽(1097—1146)。刘子羽系抗金名臣,遇事果断,刚直不阿,以抗金恢复失地为己任,这同样给朱熹以深刻的影响[8]。
汪应辰也主战,与朱熹一起密切关注北伐局势进展情况,商讨和战问题,交流思想,但汪应辰更多接近于当时史浩和陈康伯的思想,主张自治,强调自治为本,修治朝政,精练军队,积蓄国家财力军力,作长期充分准备,再行北伐,这与真正的主战派并无两样。显然,汪应辰他们所强调的主守自治思想,与当时主和派汤思退、钱端礼等以自治为名而行求和投降之实有着本质区别。就当时南宋国力和局势来讲,与朱熹主张修治朝政和用兵北伐同时并举的观点相比较而言,汪应辰的这一思想无疑更为稳健。二十多年后,朱熹在淳熙十五年(1188)上《戊申封事》,一改往日一意主战北伐的思想,明显转向对主守自治的认同:“臣窃观今日天下之势,如人之有重病……。今日之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1]卷11《戊申封事》,548
隆兴北伐与和议期间,朱熹和汪应辰都反和主战,围绕和战问题的政治交往也随着宋孝宗对于和战问题的摇摆而起伏不定。他们主战北伐收复中原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着1164年底隆兴和约签订而破灭。但朱、汪俩人忧国忧民的政治努力并未因北伐希望破灭而停止,所不同的是,朱熹决意潜研理学,开始新一段“内圣”政治努力,企图从根本上挽救国家衰颓之势;汪应辰担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则开始他的新一段“外王”政治努力。
朱熹从隆兴北伐符离之败中看到,当时国家之忧在于朝廷上下沉溺佛学而儒学不正、君心不正、朝纲不振。因此,朱熹决心对佛学进行批判清算以正儒学,然而这一批判正是从他与汪应辰的儒释邪正问题之辩开始的。通过与汪应辰的系列论辩,朱熹很快完成了著作《杂学辨》,在进行自我检讨的同时,有力地对当时朝野上下浸淫的佛老之风进行了批判,从而为其后来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迈出坚实一步。通过与朱熹的这番论辩,汪应辰也逐渐接受了朱熹的批评,辟佛归儒,被后人誉为醇儒。可见,朱、汪俩人就儒释邪正问题的论辩对于他们的思想交流及相互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
表亲关系只是隆兴年间朱熹与汪应辰开启政治交往的一个引子,真正促使他们在隆兴北伐与和议这一政治漩流中相互砥砺前行、交往密切的是俩人共同的反和主战政治立场及忧国忧民博大情怀。尽管在如何看待自治、儒释邪正问题上的见解有所不同,但并不影响他们结为莫逆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