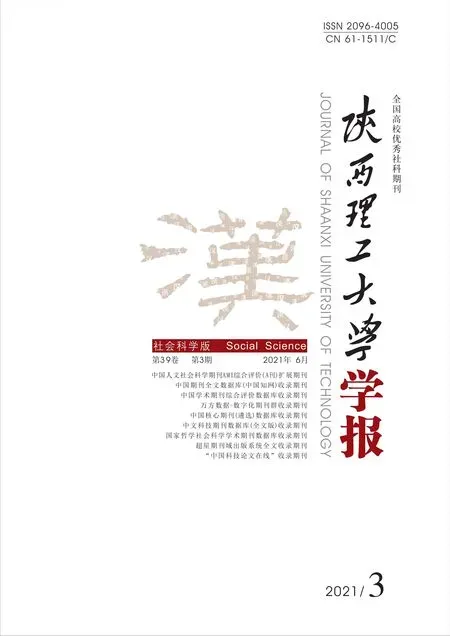由《书经讲义》看朝鲜王朝正祖君臣治《书》之特点
许 松, 程兴丽
(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尚书〉学文献集成·朝鲜卷》是由扬州大学钱宗武教授主编、钱宗武及其团队整理的一套关于朝鲜学者用汉文撰写的《尚书》学文献的集成性著述,该书以韩国成均馆大学编印的《韩国经学数据集成》中《尚书》部分为底本,通过录文、点读及校勘,全方位且系统地将这些材料整理成册,并于每一部分内容之前撰写提要,概述作者生平、文献内容及主要特点,为阅读者及研究者作提纲挈领式的导读工作。该书共收录《尚书》学著作33部,单篇文章104篇,诗歌23首,涵盖了大约从公元14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朝鲜学者研究《尚书》的相关文献,对于朝鲜《尚书》学乃至域外《尚书》学、汉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料。此外,钱宗武教授及其团队寝馈《尚书》有年,钱宗武教授为《尚书》学研究专家,其团队成员皆为目前学界《尚书》研究的后进,较强的专业性使得他们在点校之时更能准确地把握经文的思想脉络,在撰写提要时更能精准地透视朝鲜经学研究的本质及思想面貌,于我们现下学界《尚书》学史、经学史以及域外汉学等研究极具文献价值。
《〈尚书〉学文献集成·朝鲜卷》第十二册《书经讲义》乃朝鲜第二十二代国王正祖所著。正祖在位时期极力推进科举制度的改革,以达到毓养人才的目的,所以正祖躬临课试,形式主要是正祖问、文臣答,而《书经讲义》所收录的就是正祖关涉《尚书》的提问及文臣的答辩。《书经讲义》较好地折射了正祖时期朝鲜官方学术关于《尚书》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显著特点,对于我们了解朝鲜《尚书》学乃至经学研究的概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笃信孔子删次《尚书》之说
我国经学研究中关于孔子与《尚书》之关系历来有两种观点:孔子序《书》说、孔子删《书》说,此两说于《书经讲义》中皆有表现。
孔子序《书》说产生较早,而所谓“序”又有分歧,其一为编次之义,其二为序跋之义。孔子编次《尚书》说始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1]1935-1936马迁仅言孔子“序《书传》”,又说孔子编次唐虞至秦缪之际之事。此外,《史记·三代世表》亦言:“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1]487显然,《史记》所言“序”与“次”对言,非序言之序,乃编次之义。对此,清·崔适于其《史记探源》中言:“序乃次序之序,非序跋之序也。”[2]12
而另一种孔子序《书》说则最早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3]1706是班固认为,《尚书》一书乃孔子编纂,共百篇,并为其作序。《书经讲义》中时有论及孔子编次《尚书》之说者:
论及《吕刑》篇时正祖言:“《吕刑》一篇之中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敬是钦恤之意,哀敬折狱则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矣;中则无过不及之谓,用刑过则枉罹者有矣,不及则幸免者有矣。刑必贵于中,篇中所以丁宁致意屡言而不已者也,虽穆王之言而实为至论,孔子之取之,其以是欤?”[4]361正祖认为《吕刑》篇虽言狱讼之事,然独拈“敬”“中”二字,意在告诫官员治狱应有哀敬之心,如此方可洽于民心;量刑必持中正之法,如此乃能无有冤狱。正祖提问的核心点在于孔子之所以取《吕刑》以入《尚书》之原因。对此,书九对曰:“任刑之大本在敬与中,用心以敬爲主,用法以中爲主,而敬又中之本也,穆王赎刑,先儒盛斥其非,至譬于鬻狱,然一篇所言眷眷乎哀敬中正之道,犹不失前圣心法,宜夫子之录之也。”[4]362书九全然肯定了正祖的观点,认为夫子之所以录《吕刑》入《尚书》实乃由于《吕刑》言治狱特出“敬”与“中”,且进一步阐述了二者之关系,即“敬又中之本”,此实为至论,且符合前圣之心法。正祖君臣围绕《吕刑》核心主旨之探讨,屡言孔子录之,则显然承认孔子编纂《尚书》之功。言内言外皆对于孔子序《书》一说十分认可,不存丝毫疑惑。
论及《秦誓》正祖曰:“二《誓》之系《书》末,议论不一,或以为鲁则取其周礼犹在,秦则取其悔过自责;或以爲鲁则取其详于自治如王者之兵,或以爲秦则誓中多格言,不以人而废,恐皆未必然,惟当以杨龟山之说为正欤?”[4]365正祖此问乃《费誓》《秦誓》之所以系于《尚书》之缘由,此乃学界一大公案,众说纷纭。正祖虽未明言,然字里行间皆透露出孔子序编《尚书》,将《费誓》《秦誓》置于《书》末之意。东观对:“二《誓》之系《书》,辨说盈庭,而皆未得夫子本意,惟杨龟山所谓‘帝王诰命于是绝也’者最为正当,盖《周书》之有二《誓》,如《夏书》之有《胤征》,以见诸侯之事可以继天子之事也。”[4]365东观正面回答正祖之疑问,虽关于二《誓》置于《尚书》之末之缘由的讨论辩说盈庭,然杨龟山之说当为的论,因“帝王诰命于是绝”,故存鲁侯伯禽之《费誓》、秦穆公之《秦誓》,有以诸侯之事继天子之事之意,此乃正合夫子本心,故夫子存之,系于《尚书》之末。是正祖君臣一致坚信孔子序录《尚书》。关于《费誓》《秦誓》之录于《尚书》尚有一条问答见《总经》,论之甚详,正祖曰:
《周书》终于《文侯之命》,而附之以《费誓》《秦誓》者,吕东莱以为“犹《诗》之录《商颂》《鲁颂》也”,然商于周在三恪之列,则固不当比论于戎秦、鲁用天子礼乐云尔,则《诗》可有颂,而《书》不可录誓也。后儒以其解不得,或谓佐王征讨,或谓夫子逆知天下之将并于秦而录之,是皆臆说也。近世儒者有云《甘誓》天子之事也,《胤征》诸侯之事也,并存之见诸侯之事可以继天子也;《费誓》《秦誓》之存亦犹是也,此又有不然者,《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曰“予钦承天子威命”,则乃天子事,而非诸侯事也。《费誓》《秦誓》曷尝有此数句乎?夫《诗》《书》皆为夫子之所定,则其删、其录必皆有精义存焉,此不可不讲明之。[4]375-376
《文侯之命序》:“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孔传云:“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立而东迁洛邑,晋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锡命焉。”[5]799故正祖言《周书》终于《文侯之命》。而于《文侯之命》后又缀以《费誓》《秦誓》者,则聚讼难一。正祖不同意吕东莱所谓“犹《诗》之录《商颂》《鲁颂》”之论调,亦不赞同“夫子逆知天下之将并于秦而录之”之臆说。按《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序《书》,上纪唐虞,下至秦缪,然这种编次,很显然暗示了秦继周统,是受了秦统一天下期间正统观念的影响。孔子生于春秋末季,下距秦统一天下二百余年,因此在孔子的观念之中,秦尚属西戎,非为正统。此外,孔子也绝对不会预知二百年后秦统一诸侯,称帝天下,因此夫子绝不至于将其编次于《尚书》之末。正祖所言“后儒以其解不得,或谓佐王征讨,或谓夫子逆知天下之将并于秦而录之,是皆臆说也”,寔为的论。或许孔子如《史记》所言,编次其所看到的《尚书》篇目,然《秦誓》列入《尚书》必不为孔子所为。此外,正祖对于将《费誓》《秦誓》系于《周书》之末比拟于《胤征》系于《夏书》之末之说亦有疑问,认为《胤征》虽为诸侯征伐之事,然胤侯乃奉王命徂征,且经文中明言“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胤侯承王命徂征”“予钦承天子威命”,可见《胤征》实乃天子之事,而非诸侯之事。然观《费誓》《秦誓》经文,略无是语,纯然为诸侯之事,则孔子删、录《尚书》,为何独留《费誓》《秦誓》于《周书》之末?据此,师辙对曰:“鲁、秦二《誓》之附录,论者多端,或谓有征讨之備,或谓有悔过之戒,或谓补王道,或谓示王伯升降之会,率皆不足取信。朱子尝谓二誓亦皆有说不行晓不得者,臣何敢强辨?”[4]376师辙言之甚简,特举朱子所言“说不行晓不得”以证无以考据孔子录二《誓》之精义所在。纵观此条问答,依然为正祖君臣围绕《尚书》具体篇目以探讨孔子序录《书》之精义而展开,然正祖除了尊信孔子序录《尚书》之外,又提出了孔子删《书》之说。关涉孔子删《书》之说,《经史讲义·书》中尚有论议:
正祖问:“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周平王忘乃父之雠,而《尚书》取《文侯之命》,何也?《春秋》,夫子之所作,《尚书》,夫子之所删定,而圣人之意彼此不同,何欤?”
东观对:夫子志在东周,故伤东迁之后无复有天子之权,特载此篇以明礼乐征伐之自天子出而已,其义与《春秋》褒贬之书本自不同矣。[4]362
此条乃正祖与东观论《文侯之命》之大旨及孔子录其于《尚书》之由。正祖认定《尚书》乃孔子所删定,《春秋》为孔子所整理,又孔子于《春秋》大褒齐襄公复仇之举,故对孔子存《文侯之命》于《尚书》颇有疑问。东观则认为,虽孔子于《春秋》《尚书》之成书有功,然作书之目的自不相同,《春秋》旨在寄寓褒贬、维护周礼,而《尚书》则特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故载录《文侯之命》篇。正祖此处特别强调孔子删定《尚书》之说,而东观亦未予以置喙,且二者论述的侧重点在于《文侯之命》之宏旨,于孔子删《书》之态度似有不确。
《经史讲义·总经·书》尚有一则论及孔子删《书》之说:
删《书》之说,其果有征耶?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其可为世法者百十二篇,是其说出于《纬书》,固不足取信,而《汉·艺文志》古今文外,又有《周书》七十一篇,刘向以为孔子所论百篇之余,溯计唐、虞、夏、商之逸篇,又当为百余篇,则其取舍删正之责非圣人不能任,而观书周室删其善者之说,不可谓无所稽欤?《左传·定四年》祝佗告苌弘,其言鲁也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其言卫也曰“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其言晋也曰“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则《伯禽之命》也、《康诰》也、《唐诰》也,即《周书》之三篇,而孔子只录其一篇,删其二篇,何欤?若谓见逸于孔子之前,则祝佗之先于孔子不过十数年,祝佗之所及见而孔子乃不及见,岂有是理?且伯禽之命即鲁始封之诰命耳,掌之太史、藏之宗庙,将与天球、《河图》共其传,而历世未几,文莫征焉,则所谓鲁秉周礼者,又何以称焉?
廷凤对:朱子以《集传》属蔡氏,而更不说夫删几篇存几篇,《纬书》之说无所稽矣。至于伯禽之封鲁,在周公负成王之时,叔虞之封唐,在成王戏桐叶之时,未必有诰命之作,则祝佗之说,安知非出于夸张乎?[4]378-379
孔子删《书》说最早见于《尚书纬》:“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5]12显然,纬书直接将《史记》所言孔子序《书》之说改将成为了孔子删《书》之说。后来有尊用其说者,如后出伪书序:“(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5]11正祖此处所谓孔子删《书》之说,显然与《尚书纬》所载绝无二致,是其亦见《书纬》,然正祖云其“固不足取信”,是其对《书纬》之态度可见一斑。然正祖所怀疑者乃《书纬》所载孔子将原有之三千二百四十篇之书删减为百十二篇,而非孔子删《书》之行为本身。故下面正祖连续有两问:其一,《汉志》所载《周书》七十一篇,刘向谓其为孔子所论百篇之余。按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言《周书》七十一篇乃为《书》类文献,后世称其为“逸周书”。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听从李斯建议,禁民间藏书,将《诗》《书》全都搜归秘府,为博士所掌,在此期间,《尚书》被整理成编。在整理过程中,删余的部分也流传了下来,即为《汉志》之《周书》。其二,据《左传·定公四年》载,有“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之伯禽之命、“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之康诰、“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之唐诰,为何孔子独取《康诰》录之于《尚书》,而舍其二篇。言外之意,正祖坚信《尚书》乃孔子删定而成,然对于《书纬》所载删存之篇数及孔子删减之精义仍有疑惑。至于正祖臣廷凤所答,亦可见其义。廷凤首先认定《纬书》之说纯属无稽。朱熹未有《尚书》撰述,即使朱熹弟子蔡沈所作之《书集传》亦未明言孔子删存篇数,故此乃《书》学一大疑案,难以断定。至于《左传》所载祝佗之所谓“伯禽之命”“唐诰”,亦缺少史料依据,难以聚信,故不可以此推溯孔子删《书》之精义。
显然,正祖尊信《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孔子序《书》之说,如其在论及《尧典》时曰:“人有恒言,必曰尧舜,盖以一元文明之会,居天地亭午之运,风气始开,人文始备,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4]9此外,正祖君臣对于孔子删《书》之说亦坚信不疑,然对于仅仅出自《书纬》的孔子所删存之篇目以及无据可依的孔子删《书》之精义所在却抱有怀疑态度。正祖生于1752年,卒于1800年,正处于中国清朝乾隆、嘉庆之间,然当时中国学界早有人对孔子删《书》之说提出批驳,如康熙年间朱彝尊于其《书论》云:“《周官》外史氏掌三皇五帝之书,达书名于四方。郑氏谓若《尧典》《禹贡》达此名使知之。盖书之名既达矣,又虑其久而昧其义也,乃命大行人九岁则谕书名。然则,百篇之《书》皆掌之外史,而谕之行人,非孔子所得而芟夷翦截黜除之也。”[6]687由此可见,正祖时期的朝鲜王朝似未较多地关注当时中国学者于孔子删《书》问题之见解,起码于正祖之《经史讲义》中难有确据。
二、言及辨伪
西晋永嘉之乱后今文三家《书》全部亡逸,至东晋梅赜献上伪书,伪书与郑玄之《书》具行于东晋,然郑学渐衰,而伪书兴盛,直至唐孔颖达据伪书作《尚书正义》,郑学遂湮灭无闻,仅剩伪孔著为功令,一枝独秀,为官学与私学尊信不疑。直至宋代才渐有人对东晋伪书之可信度提出疑问,朱熹着重从文字难易和辞气方面辨伪,“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7]1978元吴澄大体亦遵从朱熹的方法,着重分析今、古文辞气之不同,到明代梅鷟开始将考据纳入辨伪体系之中,著有《尚书谱》和《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崛起河朔,义据通深,辨析毫芒,终是通过考据将伪孔传定为伪书。
《经史讲义·书》中亦有涉及辨伪之问答:
篇题:“伏生二十八篇,本无《泰誓》,武帝时伪《泰誓》出,与伏生今文《书》合,至晋孔壁古文《书》行而伪《泰誓》始废”云,而今按伪《泰誓》实是伏生原本,刘向、马、郑之徒虽云《泰誓》后得,而在伏生当时早已盛行,故董仲舒《对策》、太史公《史记》皆载其文。非但此也,《儒林传》分明说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且伏生自作《大传》直用其语,如云“八百诸侯俱至孟津,有白鱼入王舟”云云,则其不可诿以后来所得,亦明矣。从来论今古文者,古文则自朱子以下世多疑信之论,至吴澄、郝敬则直以为伪书,至于今文未闻有疑之者,而独伪《泰誓》一篇,诸儒之说不同,何也?
履健对:《书序》曰:“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纔二十余篇。”又汉时孔臧曰“时人惟闻《尚书》二十八篇”,与班固独得二十九篇之说不同矣。伪《泰誓》虽出于武帝末,而其中“八百诸侯会于孟津,白鱼入王舟,有火流于王屋化为乌”等说已盛行于伏生之前,故汉初娄敬之说高祖也已用此说,伏生《大传》亦用之,董仲舒、司马迁亦用之,盖其说必有见于古书者而然也。至于伪《泰誓》不过撺掇此等句语,合其伪文而并为一篇也,且《孟子》《春秋》《国语》等书多用古文《泰誓》句语,而伪《泰誓》皆无其说,诸儒之作一大疑案亦以此也。[4]52-53
按:此条正祖君臣所论乃《泰誓》版本。《泰誓》版本本就繁复杂乱,学者历来颇多争论。大体而言,《泰誓》有三个版本,其一为先秦真古本,先秦典籍多次引及《泰誓》篇名及其经文。其二为武帝河内本,此本得之于武帝太始年间,献上之后即合伏生所传今文立为官学,是为今文《泰誓》本,即此条论述中正祖所谓“伪《泰誓》”是也。其三为东晋伪孔传本,此本为东晋梅赜所献,分为上中下三篇,所述为武王伐纣之事。此条材料中,正祖君臣所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为伏生本《尚书》是否有《泰誓》。关于伏生本之二十九篇的构成,学界历来争论不一,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其一,清代江声、龚自珍、俞正燮、皮锡瑞、王先谦、当代台湾学者程元敏等认为,所谓二十九篇是分《顾命》出《康王之诰》。其二,刘起釪则认为二十九之数乃是汉武帝将后来《泰誓》加进去之故。其三,明梅鷟、清朱彝尊、陈寿祺等一致断定二十九篇为二十八篇经文加一篇序而成。此三家虽说法不一,然伏生本无《泰誓》却是学界共识。然正祖却坚信伏生本二十九篇之中即有此本《泰誓》,直言伏生《尚书大传》中即引用到了此《泰誓》“八百诸侯俱至孟津,有白鱼入王舟”之语,由此以证此本《泰誓》实为伏生本《尚书》二十九篇之一,非汉武帝时才从民间搜得。对此,履健所对倒是甚为中肯,颇具见地。他认为所谓“八百诸侯会于孟津,白鱼入王舟,有火流于王屋化为乌”的说法并非最早见于伏生本《尚书》,而是早在伏生之前就见载于典籍,故伏生、董仲舒、司马迁等人得见且用之,故其坚定地认为所谓“伪《泰誓》”乃武帝时从民间搜得,而非伏生本《尚书》所本有。此外,武帝河内本《泰誓》乃将早已见于古书记载的“八百诸侯会于孟津,白鱼入王舟,有火流于王屋化为乌”等语搜辑并纳入其中。而至于为何未将同样见之于《孟子》《春秋》《国语》等典籍的《泰誓》原文置于其《泰誓》篇中,则完全不得而知。履健寥寥数语,基本上将先秦真古文本与武帝河内本《泰誓》之渊源交代清楚了,即见之于《孟子》《春秋》《国语》等典籍的《泰誓》经文文句实为先秦真古文本,而武帝时期所献上之《泰誓》并未将这些文句辑佚留存,故马融《书序》曰:“《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王肃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经。”[5]399而等到梅赜本《泰誓》献上之后,孔颖达直接将武帝河内本《泰誓》名为“伪《泰誓》”。
此外,正祖尚提到了中国《尚书》学辨伪历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如宋代朱熹、元代吴澄、郝静,简单言及他们对古文《尚书》的怀疑。然纵观正祖之言,其对《尚书》版本的辨伪考据着实有些不着要点,他直言武帝河内本《泰誓》为伪,却对于东晋梅赜本《泰誓》乃至整本《尚书》之真伪未置一词,甚至对朱熹等人的辨伪成就也未作任何评价。而履健之回答也仅谈及武帝河内本《泰誓》的来源,而对朱熹、吴澄等人的辨伪亦避而不谈。如前所论,东晋梅赜本《尚书》辨伪于康熙年间的阎若璩之《尚书古文疏证》已尘埃落定,晚出古书至此完全定案为伪书,晚于阎若璩的正祖君臣按说应该涉猎知晓,然于此条问答中却丝毫未有表现。
遍检《经史讲义》,言及辨伪者仅此一例,但仍可窥见朝鲜《书》学研究同样关注古文辨伪工作,据《韩国经学资料集成·书经篇》目录,朝鲜王朝尚有多位学者专注于《书》学辨伪,如金正喜《尚书今古文辨》、李源祚《伪古文十六言辨》、李震相《尚书今古文辨》等。然此时虽关注辨伪,但并未一意将后出古文摒除在外,就正祖《经史讲义》而言,其所涉篇目遍及今文与古文。
三、以理释经,多言体用
正祖君臣讲经多受我国宋学之影响,在疏通经文时动辄言蔡沈《书集传》,且多引及有宋一代学者之说,如程子、苏轼、林之奇等,此外,正祖君臣在讲经时亦多援理入经,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以宋儒多言之“体用”思想来解经。如正祖君臣论及《舜典》:
自乐而言,则教是一事;自学而言,则乐是一事。而今曰“典乐教胄子”,则乐专在于教,学专在于乐也。然则成均教子弟之外,大司乐更无所事,而博依杂服不当并列于操缦耶?
履健对:直、温、宽、栗,乐之体也;诗、歌、声、律,乐之用也;神人以和,乐之功效也。此段兼乐之体、用、功效而言,不专主于教之一事也,学之者亦当以养其中和之性为本,岂但声音律吕为哉?若论设教之次序,则《诗》《礼》为先,未有不学博依杂服而能学操缦也。[4]15-16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5]106正祖所问乃夔作为司乐教授胄子的重点及根本目的何在,是否“学专在于乐”?且特别化用《礼记·学记》之文“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8]1057-1058对典乐之重要性提出了疑问。其实典乐之目的并非在于声音律吕本身,而是通过声音律吕陶养性情,恰如伪孔传所言:“以歌诗蹈之舞之,教长国子中、和、祗、庸、孝、友。”[5]106对此,履健依据宋儒常言之“体用”予以回答。履健认为“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实乃乐之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乃乐之用,故司乐乃是通过律吕的表现形式而真正达到陶冶胄子中和之性的目的,此所谓中和之性即为“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此处履健所谓乐之体即为乐之性,由用而达体,乐与诗、礼并行不悖,故“博依杂服而能学操缦也”。
在我国“体用”概念虽然由魏晋时期的王弼提出,然体用思想早在先秦即有肇端,如《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王肃曰:“水之性润万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5]453是王肃认为润下、炎上为水、火之性。孔颖达疏“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之传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为器有须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销铸以为器也。”“土上所为,故为土性。”[5]453是孔颖达亦认为曲直、从革、稼穑乃木、金、土之性。此外,孔颖达亦云:“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为卤。卤为乃咸。……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从其发见。指其体则称‘曰’,致其类即言‘作’。”[5]453显然,《尚书》此处原文既没有言“体”,亦未言“用”,但却包含着鲜明的“体—性—用”之概念。直到集两宋儒学之大成的朱子,更是将体用概念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内涵,不仅对我国后世体用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朝鲜的经学中也可见鲜明的朱子体用思想的渗透,正祖《经史讲义》中就多有体现,最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体用无定、体用一源。
五声之三分加减,六律之还相为宫,自有自然之度数、节族,为乐者,以人声求合于律吕,而非律吕有待于人声,故《益稷》之谟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以出纳五言。”而今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则是将以诗为本,而声律皆为由是而生,则何其与《益稷》所载相径庭也?[4]16
正祖认为,按照客观逻辑,为乐应当以人声和于律吕,而非律吕和于人声,《益稷》篇之据“六律五声八音,以出纳五言”乃人声和于律吕,是为正,而《舜典》篇之“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乃声律和于诗,是为非。祖承之答同样依据体用思想而展开。他说:“自其作乐而言之,律为体而声为用,自其言志而言之,诗为体而律为用也。《益稷》所论,必欲审乐而知政,故本于律吕,终之以出纳五言。《舜典》所论,盖欲教胄而成德,故主于诗歌,勉之以协和声律。然则乐律、人声,互为体用,而其于养性育材咸有功效,两篇旨意恐无径庭也。”[4]16祖承此处显然深受朱熹“体用无定”思想之影响。《朱子全书》载:
童问:“上蔡云‘礼乐异用而同体’,是心为体,敬和为用。集注又云,敬为体,和为用,其不同何也?”曰:“自心而言,则心为体,敬和为用;以敬对和而言,则敬为体,和为用。大抵体用无尽时,只管恁地移将去。如自南而视北,则北为北,南为南;移向北立,则北中又自有南北。体用无定,这处体用在这里,那处体用在那里。这道理尽无穷,四方八面无不是,千头万绪相贯串。”[9]766
此段材料乃朱熹与其弟子就谢上蔡“礼乐异用而同体”观点的探讨,朱熹明确地提出了“体用无定”的思想,他说“自心而言,则心为体,敬和为用;以敬对和而言,则敬为体,和为用。”显然,体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基于不同的视角,则会有不同的体用关系。此观点深为正祖大臣祖承所认可,并运用到了其对于《尚书》的解读中。他认为乐律、人声是互为体用的,《益稷》所论是从作乐的角度而言,重在审乐知政,故而律为体而声为用,然《舜典》所论乃从言志的立场而言,重在教胄成德,故诗为体而律为用。由此可见,两篇所论之主旨并不相悖。
除了受朱熹“体用无定”思想影响之外,正祖君臣在用体用思想阐释经文的时候亦体现出了朱子“体用一源”思想之影响:
“初一曰五行”,五行不言用者,何也?《蔡传》以为无适而非用,恐似泛然。此盖以五行之体言,故不言用也。五行之序有三:水、火、木、金、土,初生之序也;木、火、土、金、水,相生之序也;金、木、水、火、土,相克之序也。初生之序即五行之体也,相生相克即五行之用也,五行畴以初生之序言之,则此言其体也,言体而用在其中矣,如是看,未知如何?
书九对:天地生成五行之体,相生相克五行之用,举体该用,诚如圣教,然此乃五行自然之体用,非容人为于其间也。盖贯通乎三才之间,皆五行之气,故播之四时则为五纪,具于人身则为五事,以至八政、三德以下诸畴,莫非五行之所推,而敬、农、协、建、乂、明、念、向、威九者,人君之所以为用也,九用备而五行各顺其理矣。然则五行虽不言用,人君所以用五行者,实不外乎此,故曰“无适而非用”,不独以“五行”二字已包自然之体用而遂为略之也。[4]297-298
按:此则正祖君臣所论为《洪范》之“初一曰五行”为何不下“用”字。《洪范》:“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由二到九均下“用”字,独五行不下,则何欤?蔡沈《书集传》认为“无适而非用”,正祖认为此解难免泛泛。根据后文言及的五行之序:水、火、木、金、土,孔颖达疏云:“《易系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数也。如此则阳无匹,阴无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于是阴阳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谓之成数也。”[5]452故《洪范》乃以生成之序言五行,正祖亦深为认可,言此乃五行初生之序,初生之序乃五行之体,言体则用在其中,故不需再下“用”字。书九亦深以为然,直言“举体该用”。此处正祖之“言体而用在其中”、书九之“举体该用”皆受朱子“体用一源”思想之影响。
宋人关于“体用一源”思想的论述最早始于程颐,然到朱子之时,进一步将此思想系统化:“若夫所谓体用一源者,程子之言盖已密矣。其曰‘体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联,而万象昭然已具也。其曰‘显微无间’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则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为一源也。言事则先显而后微,盖即事而理之体可见,是所以为无间也。然则所谓‘一源’者,是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哉?况既曰‘体立而后用行’,则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矣。”[9]78显然,朱子认为“体用一源”侧重于言“至微之理”,在于强调理体象用,理中有象,故朱子说“言理则先体而后用”“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此处所谓“先体后用”之先后并非时间顺序,盖应为逻辑关系,故“先体后用”意即“举体而用之理已具”,与“举体该用”同一意指。显然,正祖与书九皆受朱熹思想的启发。除此之外,书九尚言五行不言“用”非但以五行本身为天地之理,举体而用在其中,尚且因为五行以下言“用”之各畴,均为五行之用于人君的具体表现,故“五行虽不言用,人君所以用五行者,实不外乎此”。
钱宗武先生曾谈到域外《尚书》学文献亟待整理之缘由及意义:“这类文献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以经典为载体的,经典的域外传译是文化传播最为有效的手段和可行的方法,是不同民族相互了解的基础。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诸国均藏有《尚书》文献资料。对这些文献资料的集成,有利于研究东亚东南亚文化圈的共同性与特殊性,进而在文化战略上把握与东亚东南亚诸国交流的策略,增进了解互信。”[10]42-53故而,钱宗武及其团队耗时多年,终使《〈尚书〉学文献集成·朝鲜卷》付梓发行,此书于我们探求朝鲜《尚书》学研究的概况与面貌意义重大。就《书经讲义》而言,其作为朝鲜正祖时期官讲《尚书》的代表性著作,直接折射了当时官方学术体系《尚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及主要特点:他们相对认可孔子删减、整理、编次《尚书》之说,且认定这种行为寄寓了夫子的微言大义,然在他们的辩答之中却丝毫未见中国明清时期对孔子删《书》说之批评;他们关注辨伪,然辨伪的角度、方法却不及中国丰富得当,甚有隔靴搔痒之感,他们仅简单言及宋元朱熹、吴澄等人的辨伪工作,且并未过多置喙,而对于早于正祖的阎若璩的辨伪观点干脆一言未及;他们多受宋代理学尤其是朱子思想的影响,于《尚书》讲论中多言体用,甚至直接继承朱子的体用思想。显然,正祖朝虽处于我国乾隆、嘉庆年间,然其《尚书》学更多地受到宋代及之前学术的影响,而很少受我国明清时期学术熏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