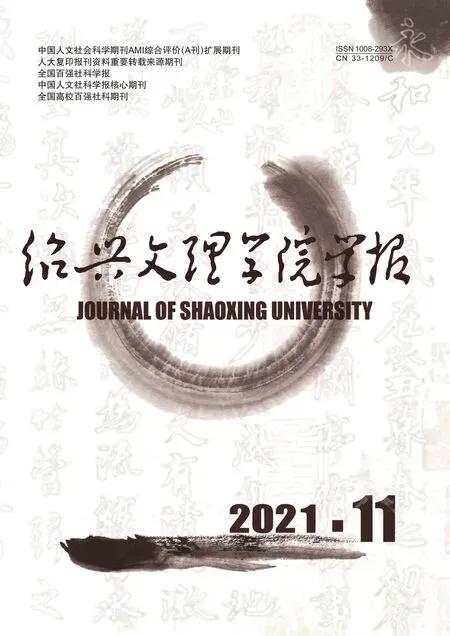国家的内部关系、权力与治理
——麦金农女性主义国家理论的三重维度
方环非 胡惠秀
(1.绍兴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2.宁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一、引言
国家一词往往会让人们想到它的阶级本质,其性别属性却鲜少被理论家提及,这是因为国家总是被默认为性别中立,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似乎也不例外。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女性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由于受到来自全球化市场的压力,国家要削减“不必要的”功能。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正面临着“结构调整”计划,第一世界的妇女正目睹着国家服务和职能的私有化不断升级。在被自动化替代的过程中,女性由于承担大量低水平、重复性的工作,因而必定会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与此同时,国家监管正以复杂而微妙的方式渗透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女性被排挤在国家权力之外,或者至多处于边缘地位[1]。在这种背景下,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A. Mac kinnon)的国家研究可能会提供一些线索,它让我们了解女性在选择与国家打交道时所面临的困境本质,理顺性别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帮助我们找到一种走出这些困境的方法。与此同时,麦金农的女性主义国家理论是一种真正从性别角度来探讨国家属性的国家理论,这使得它丰富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关于国家理论的性别本质的论述。
关于国家理论,麦金农没有系统的论述和明确的表达,她大多时候是在批评和指责自由主义和左派的国家理论。通过批判性地追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两性不平等的根源,以及对国家理论相关问题(1)比如国家、法律对女性而言究竟是什么,法律对国家、男性权力及其自身的合法化起着怎样的作用,国家的权力在社会中源自何处,性别政治中国家的角色是什么以及国家、法律是否能够为女性的地位采取积极的行动等。的补充回答,麦金农形成了以国家的内部关系、权力和治理三重维度为核心论点的女性主义国家理论。三重维度的批判之间具有逻辑递进的关系:国家社会中两性不平等的持久性表明国家内部关系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矛盾,由此揭露出两性之间的权力来源及分配问题,进而暴露国家的本质及治理问题。简而言之,麦金农的女性主义国家理论是以性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女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国家在调和两性关系中的角色,从而试图创建一个包含所有女性经历和女性经验在内的关于女性压迫和社会变革的国家理论。
二、国家内部关系
国家的内部关系涉及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诸如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国家与集体以及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关系等等。通过性别视角审视国家内部关系后,麦金农指出,国家、社会和性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国家、社会是由性构建的,同时性又被国家与社会所构建[2]4。为了进一步揭露国家的性别本质,在理解国家、社会与性的关系的基础上,麦金农继续审视国家、法律与男性和女性的关系。麦金农指出,国家、社会和法律在对待两性问题上存在一种同谋的关系。国家和法律均为男性利益的代表,由此造成女性在国家和法律中的从属地位。
(一)国家、社会与性的关系
“性之于女性主义,恰如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大多是自己的,又大多被剥夺。”[2]3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基本上是由人们在生产和制造生活必需品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的。然而,在麦金农看来,恰如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对女性主义来说,性被社会所构建,同时也构建社会。“性是一个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性别的社会关系被创造、组建、表现并被确定下来,把我们所知的社会存在创造为男性和女性,而男女两性的关系又创造了社会。”[2]4换句话说,男女两性的划分奠定了社会关系整体的基础。因此,麦金农所指的“性”是从整个人类社会的结构与秩序层面来加以审视,正是两性关系创造了社会。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性被社会所建构呢?
在麦金农看来,国家和社会之间是一种同谋的关系,正是这种同谋决定了性成其所是。在两性社会中,国家虽然具有“普遍性”的外观,实际上被男性这个统治阶级所操纵,只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3],是部分社会阶层也即男性特殊利益的代表,不可能真正反映全社会的普遍利益。也就是说,在性别的视角下,国家是男性化的,它通过剥夺女性的性欲来行使男性权力。国家已经被完善成为社会的镜子[2]296。社会决定国家,国家及其权力反映社会。具体来看,国家是社会权力的一种制度,它反映并强化着既存的社会权力形式。在一个男性主宰的社会中,国家成为一种男性的制度,其相应的行为与意识形态均是如此。当然,尽管国家有时似乎是中立的,保护着两性的特殊利益,但其本质上由男性操纵,国家已然将男性的性统治和女性的性服从制度化。这就决定了性理论必然包含多劳少得的关系,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服从的关系,一些人操纵而其他人被操纵的关系。综上所述,国家和社会是一种同谋关系,他们共同构建了性,这种同谋关系尤其体现在对待两性问题的立场上。
(二)国家、法律和男性的关系
国家是男性统治女性的工具,并维护男性利益。而法律作为国家的同谋,则是把国家统治与维护男性利益的方式制度化的手段。更形象地说,法律是使男性权力合法化的外衣,是男性霸权和男性利益的保护伞。法律作为国家话语的成文规则,代表着国家,所以法律不仅是男性统治女性的社会反映,而且它也在用男性的方法来进行统治。简而言之,法律作为权力的话语,以国家的形式记录社会,并在社会之上记录国家。
国家的本质是男性的。也就是说,国家是男性化的,国家在法律和社会的关系中采取男性权力的立场。因此,代表着国家的法律,自然也在用男性认识和对待女性的方式来认识和对待女性。在麦金农看来,所有的知识和经验都有性别,所谓客观的观点就是指法律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麦金农进一步指出,男性统治或许是历史上最普遍深入的和最顽强的权力系统,因为它“在形而上学上近乎完美”[4]。因此,在男性至上的情况下,法律就是男性的观点。这也说明,国家不只是阶级权力的反映和工具,国家更是男性利益的反映,国家支持男性群体的利益[2]271。与此同时,女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是因为国家被假定为政治,而是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法律将男性权力制度化。换言之,男性权力带有系统性,它就是政权。一方面,国家政权掌握在男性手中,男性是统治阶级,女性是被统治阶级。另一方面,麦金农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国家事实上被男性控制并潜在地为男性利益服务,但她反复强调国家从本质上依然是具有男性化特征,因为国家看待和处理性别问题的基本视角来自于男性与世界的关系。因此,即使在性别平等的法律中,人本质上也意指男人。国家通过强调中立性的价值并在法律中假设中立性的存在,掩饰了男权制度的动态性。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只要进行主观发言,她们就会被重视中立的法律制度边缘化。
(三)国家、法律和女性的关系
国家、法律存在合谋的关系还体现在它们各自与女性的关系上。关于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中,法律都被视为“社会的精神”[2]228。具体地说,在自由主义理论中,法律代表“无实体的理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法律是“物质利益的反映”[2]228-229。于前者而言,国家是中立的仲裁者,法律可以作为一种可供女性利用的工具。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家则是统治和压迫的工具,法律成为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这就导致两种理论在看待国家关于女性解放问题上截然不同的态度。正如麦金农所认为的那样,自由主义建议将国家和法律作为促进女性平等的主要工具,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放弃国家作为变革的舞台,并将国家代表女性使用法律视为注定要失败的理想主义。总之,在他们那里,国家以及随之而生的法律,要么无所不能、要么一无所有。由此看来,女性主义对国家的姿态在关于女性地位的中心问题上已被分裂[2]229。尽管麦金农认为上述两种情况都不令人满意,但她并没有就国家在女性解放问题上进行明确地表态,而是意识到女性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联系,即女性的地位与国家正相关。
在国家和女性的关系问题上,国家是构建女性作为从属这一身份之上,最初的国家行为是从男性统治的立场看待女性,接下来的行为也是用这种方式看待女性[2]244。国家在其形式、动力、与社会关系的特殊政策上,体现并服务于男性的利益。在麦金农看来,国家的文化力量决定了男人或女人的意义。女性被训练成女性化的形象,也就是柔弱和顺从;她们已经学会认同母性和教养,因此她们觉得这是本能。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语言可以让我们看到性别不平等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它被如此广泛地传播,以至于成为“事物本来的样子”,文化霸权得以实现。与此同时,国家的私有财产以及一夫一妻制贬低了家务劳动的价值,因而贬低了女性,由于女性的劳动在社会中被贬低,女性在家中自然也被剥夺了权力。如此看来,“国家通过体现和确保现有的男性在各个层面对女性的控制来保护男性权力”[2]241。因此,如果说国家是男性权力的寄生虫,那么女性就是寄生虫的寄生虫。
麦金农对国家内部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女性在国家、社会和法律中的两性不平等关系,它们构成一个等级关系。同时,两性存在的等级关系与权力的来源和分配又息息相关,而国家的内部关系反映并体现着国家的权力关系。
三、国家的权力
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关于权力及其分配不平等的理论。它们提供了关于社会分配模式的解释,即这种分配何以在内部是合理的,却是不公平的。麦金农揭示了国家权力来源于对女性性行为的剥夺,是男性形式的权力。在权力分配上,男性是权力的主体,女性是权力的客体。在权力运行上,国家权力按照男性的形式在运作,并且在权力运行中将女性客观化、合法化。为了打破这种两性权力看似合理实则不公平的局面,改变男性权力在国家中的运行规则,麦金农提出了意识觉醒的女性主义方法。
(一)国家的权力来源
国家所拥有的权力的来源是任何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麦金农的理论明确了这一点,即国家理论建立在国家拥有权力的假设之上,而不是把国家看作是权力循环网络中的一个交叉点。她认为,男性权力是在国家之外形成的,并通过国家来传递。换言之,国家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为其他地方构成的男性权力服务的工具。在麦金农的理论中,性所扮演的角色与马克思主义中劳动所扮演的角色相似。人们通过这种活动成为他们自己。阶级是它的结构,产品是它的成果,资本是劳动的凝结形式,并控制它的问题[2]3。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她这样描述对性的有组织的征用:“异性性行为是它的社会结构,欲望是它的内在动力,社会性别和家庭是它的凝结形式,性别角色是概括人的社会角色而成的性质,生育是结果,并控制性的问题。”[2]4她接着解释了男性统治的物质基础正是源于这种根本上的剥削关系。“有组织地征用一些人为他人的利益而工作,这定义了一个阶级,工人;有组织地征用一些人的性为他人所用,这也定义了性别,女性。”[5]恰如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所有权所产生的权力的描述,生产资料所有权反过来又使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力能够被征用。马克思的权力主要是经济权力,就像麦金农的“权力本身”是性权力一样[6]。
不过,要充分理解麦金农阐述的国家理论,必须从她对权力本身的分析入手。根据麦金农的描述,对女性性行为的剥夺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国家不是男性权力的起源,相反,“国家,部分地通过法律,将男性权力制度化”[7]645,正如马克思主义中的国家将经济权力制度化为“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麦金农进一步指出,国家权力是男性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创造的权力,是男性形式的权力。用她自己的话说:“男性权力就是国家制度化的权力,它是强制的、合法的、认识论的,它就是政权。”[2]245因此,体现在法律中的国家权力,与遍及社会的男性对女性的权力被组织为国家权力一样,同时作为男性权力贯穿于整个社会而存在。
(二)国家的权力分配
国家的权力来源和权力分配紧密联系在一起。权力的存在必然涉及分配问题,而权力分配又存在主体与客体之分。事实上,麦金农注意到两性的不平等不仅与权力来源有关,其背后更是一个权力配置问题。她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组成部分与女性主义的类比结合建立了女性在权力分配中的从属理论:劳动—性;无产阶级—女性;资产阶级—男性;商品—女性;生产—再生产等。从类比中可看出,麦金农将国家社会划分为两个性别,即男性和女性,这种划分奠定了社会关系整体的基础。不难看出,对麦金农而言,国家、社会是一个性别等级化的社会,权力结构影响着等级关系中主体与客体之分。
在权力等级结构中,男性控制女性,是权力的主体,拥有更多的权力和资源。女性则被排除在权力结构之外,成为男性压迫、剥削和统治的对象。一方面,男性的权力是自我实施的,它无所不在而又看似不在,是弥散性的。在男性那里,整个世界成为他们头脑所能发明的任何形式。男性以自我自称之,认为独立于自身世界之外的所有事物都是对象。女性与商品、动物没有什么不同。像商品的价值一样,女性的需求也有着类似的遭遇:使其仿佛是客体自身的属性,仿佛是自发的和固有的,仿佛是独立于产生它的社会关系,不受需求它的暴力所控制[2]170。另一方面,女性的无权既是外在强加的,也是深深内在化的[2]10。麦金农认为,女性这个性别完全被性化:“女性的意思是女性特质,这意味着对男子的吸引力,也即性的吸引力,即男性意义上的性的可用性。”[2]151换句话说,女性作为性客体传达这样的观点,女性的天性就是满足男性的性要求。女性在思想上的依赖促使她们去遵守男性为其创造的标准。这也意味着,在男性之为人的意义上,女性实际上不是完全的人。仅仅作为一个女性或许意味着很少能处于一个与男性十分近似的位置,而是观念中比人低一等的任何事物[2]196。换句话说,男性高于女性的权力位置是男性自我定义为男性,女性自我定义为女性,男性定义女性为女性。这两个方面彰显了男性优于女性的物种歧视主义的痕迹。
(三)男性权力的运行
作为男人和女人的社会角色,他们之所以涉及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存在权力的主客之分,根源在于国家权力,确切地说,是男性权力的运行方式。正是男性权力的运行方式造成男性对女性有权力,而女性对男性没有权力,甚至女性的无权也被合法化。
在麦金农看来,男性有权和女性无权、男性的统治地位与女性的从属地位的根源在于社会建构。麦金农像大多数女性主义者一样,从根本上把性视为男性权力的主要社会领域。麦金农认为,性作为男性权力的社会构建意味着由男性定义,被强加于女性,并构成了性别的意义。她甚至进一步推论,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经成为理性的同义词。一旦男人把女人看作性的对象,这将被视为一个客观决定的真理。如果任何男性的假设都有其理性、客观真理的概念基础,那么对女性的客观化就会变得合法化并持续下去。尤其是当性别不平等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时,它被广泛地传播,最终成为“事物本来的样子”。文化霸权由此得以实现,女性自然也就成了不平等霸权的产物,所谓女性平等,事实上从未存在过。
在麦金农看来,由于主宰社会运行的男性化权力以及女性的客观化都被合法化,使得女性个体很难觉察到自身的从属地位。然而女性的无力感来自于女性对性别的内在体验,这也是最首要的物化体验,由此获得一些外在的表达与强化。在此基础上,麦金农提出意识觉醒的方法。通过女性对性别物化的日常体验的交流与反思,来解释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性别支配,并以此来瓦解主宰社会运行的男性化权力。也即从个人的微观体验及其看待世界与自身的方式出发来改造宏观世界的运行规则[8]。
四、国家的治理
国家的权力分配反映国家治理基础和结构,而国家治理本质上是运用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国家是治理的主体,因此,国家的角色和职能在国家治理中是一个核心问题。在对治理问题的讨论中,麦金农的着眼点放在国家的角色及宣称的客观性基础上。国家的角色是男性的,其宣称的客观性并非是中立性,而是男性立场的普遍化。同时,国家的相对自治根本不存在,女性寻求国家改变两性的不平等是不可能的。
(一)国家的角色
根据麦金农的描述,男性权力源于对女性性行为的剥夺,由此造成男性对女性的权力。尽管国家不是男性权力的起源,但是国家在部分意义上通过法律,将男性权力制度化。因此,国家也不能成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中立仲裁者。“我认为,在女性主义的意义上,国家是男性的。法律看待和对待女人的方式就像男人看待和对待女人一样。自由主义国家通过其合法化的规范、与社会的关系和实质性的政策,强制性和权威性地按照男性这一性别的利益构成社会秩序。”[2]233
从这个角度分析,国家将永远是制度化的男性权力心甘情愿的仆人。它的行动将不可避免地服务于男性主导地位,维护和巩固男性权力。不过,国家有时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会包容两性间的社会冲突。这并不是说国家有时会处于中立地位,而是国家似中立。在表面中立的庇佑下,国家对男性利益的保护成为合法化的官方政策[2]317。女性的从属地位正是男性通过国家机器在产品和社会控制过程中形成。因此,麦金农批评国家的角色是男性的,是男性利益的代表,在国家层面上的改变对妇女解放的价值有限。这是因为国家所掌握的权力来自于国家之外,因此要终结男性统治,就需要对这种权力的基础进行变革。也就是说,国家层面上的改变不能改变男性权力根源上的剥削关系。麦金农认为这种关系指的是对女性性欲的剥夺。当然也许有可能在国家内部产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不会影响男性主导地位的整体结构。不过有一些学者指出,像国家这样的抽象概念“太单一、太不具体,无法在解决那些必须是女性主义者最迫切关注的、多样而具体的场所方面发挥太大作用”[9]。对此,麦金农强调政府结构在女性生活中的中心地位,而却需要在理论上更丰富地描述政府在调解两性关系中的作用。这样看来,麦金农在某种程度上又赋予国家以一定的客观性。
(二)国家治理基础:客观性
假如按性别划分,国家至少是由一半男性人口和一半女性人口组成。如果只把男性立场或者仅仅把女性立场称为客观性立场,这样不可避免会形成一种男性至上或女性至上的国家,都不是真正的客观性表现。因此,客观性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对于实现两性平等至关重要。
麦金农的国家理论超越了假定国家为人们的集体利益而行动。她分析了国家统治的过程,并从认识论的立场出发,论证了国家从男性权力的角度看待世界。她认为国家不仅仅是为了男性主导地位的利益而行动,而且被认为至少包括法律机构等在内的国家机构的客观方法,这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男性治理形式——客观性。在麦金农看来,客观性在实践中意味着男性的观点被认为是未经干预的真理,不过这种国家宣称的所谓客观性实际上是男权的谎言。
当掌权的男人说保持客观性的时候,其实是说他拥有权力,他们的立场即事实。大多时候,男性会有一种相互之间的认同,而且彼此之间最为认同的恰恰就是,“他们即国家”。也就是说,国家治理基础的“客观性”表现在,有权力说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真实的这样一些人的领域。由此,客观性便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掌权人的规范,而这个规范自始至终都是男性的观点。这里男性的观点被认为是无观点的观点,把男性观点的特殊性说成普遍性,把其暴力当作同意来执行,把其权威当作参与,把其霸权当作秩序的范式,把其控制当作合法性的定义[2]160。相反,女性的世界观对于掌权者来说,不仅仅无关紧要,甚至是不存在、不真实的,是无形的。因此,可以看出,客观性也即“性别中立”乃是建立在否认性别不平等的基础之上。
(三)国家并非相对自治
为了说明国家“性别中立”的谎言,麦金农提出了国家并不是相对自治的观点。在麦金农看来,国家不是当权者手中的一个简单工具,它被视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因为它被迫在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职能之间做出选择或妥协。尽管麦金农承认,国家运用的客观主义认识论,确保法律在最大程度地坚持其自身的公平理想的同时,将最大地增进现有的权力分配[2]235。并且国家在履行意识形态功能的同时,也在代表男性主导地位进行更直接的利益干预。然而在任何地方,国家似乎没有任何能力选择让女性受益,并且(无论多么微小)国家的利益似乎都与男性权力有关。国家推崇的法治和(男)人治乃一回事,是不可分割的,同时具有正式和非正式的界限,正式地被限定,而非正式则没有[2]245。也就是说,通过法律体现的国家权力,与遍及社会的男性对女性的权力被组织为国家权力一样,都作为男性权力在社会中存在。麦金农本人强烈反对“国家可以是其他任何东西,却不是男性权力的整体表现”的有关说法。她给出的理由是,“无论这个自由的国家在阶级上多么自治,它都不能在性别上自治”[7]658。男性的权力带有系统性和强制性,是合法的,也就是国家政权。
从这一说法来看,麦金农似乎排除国家具有任何形式的相对自治的可能性。尽管如此,麦金农却似乎并不认同近代女性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即国家行为的相对自治模式已经无法维持。她们认为,国家太矛盾、分散、不连贯、不稳定,以致于无法把它解释成是出于对任何总体目标的追求,又不能把国家理解为相对单一的实体。国家是一个变革的过程或舞台[10]。麦金农承认,国家确实作为一个舞台出现,但在这个舞台上,根本的女性主义变革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发生根本的改变。由此看来,麦金农似乎对国家出现任何女性主义的可能性感到悲观。她甚至认为,不符合男性直接利益的国家干预是不存在的,而符合女性利益的国家行动更不可能存在。
五、麦金农的国家理论何如
最近二三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作品涉及国家问题(2)参见C.Pateman.The Sexual Contrac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M.Sawer.Reclaiming the State:Feminism,Liberalism and Social Liberalism.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1994,40(1);W.Brown States of Injury:Power and Freedom in Late Modemit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等。,其中麦金农的女性主义国家理论可能最为著名,也最具争议。当麦金农将国家愿景描述为女性主义国家时,问题随之而来:女性主义是否真的需要国家理论?麦金农的女性主义国家理论是否仅仅是抽象的政治概念?她要实现的两性平等是否是关于国家的乌托邦?
显然,关于国家的女性主义理论既可能,也必要。女性主义需要国家理论,但它并非是一种僵化的,以生理器官为中心定义边界的国家理论。麦金农的女性主义国家理论显然指对国家的批评,而不是颂扬[11]。它在性质上是明确的女性主义,是对男性统治的挑战,也是对女性政治、社会地位的争取。然而,麦金农的女性主义国家理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关于国家女性主义的乌托邦。不管是从国家内部关系,还是从国家的权力和国家治理来看,麦金农的女性主义国家理论都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且存在诸多矛盾之处。比如,为什么将女性被压迫的事实归因于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制国家是合理的。事实上当她持有这样的立场时,恰恰忽略了男女之间的自然差别(3)事实上,麦金农将性(sexuality)与社会性别(gender)混合一谈,且将它们与“女性”这一范畴等同起来。然而麦金农自己则补充道,她交替使用“性”和“性别”这两个术语,不是真得对它们应该造成的生理/社会区别感兴趣。。这显然与她批评其他学者把男女的自然差别的客观性作为男女不平等的合理性的基础或根据相矛盾。就国家权力和国家治理问题来看,麦金农的国家理论缺乏任何关于如何结束男性统治的明确描述,她也没有说明女性主义者应该如何或为什么把国家视为激进主义的舞台。这里的矛盾之处就在于国家为什么可以既是男性利益的代表又是女性和社会变革的舞台。
如果麦金农的女性主义国家理论是一种女性主义的解放愿景,她就需要对国家在推翻男性统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描述,思考国家是否有可能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或者它是否必然会成为真正变革的反对者?我们会有一天面对女性主义国家的迷人幽灵吗?还是女性主义革命根本就是要废除国家?再有,女性主义和其他人是否真的需要一个国家理论,在这种国家理论中,男女生理差别是否可以被忽视,或者说男女差异及其导致的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和认可等。然而麦金农显然缺少对诸如此类问题以及那些批评她的理论的人,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理论回应。尽管如此,麦金农的女性主义国家理论从两性关系上对国家关于性别本质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一度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阶级本质的理论,摈弃了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或阶级斗争论,揭露了社会中更根本、更持久的问题,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除此之外,麦金农以女性主义视角看待国家的现实问题,既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新发展、新变化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认清女性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的现实困境,对于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