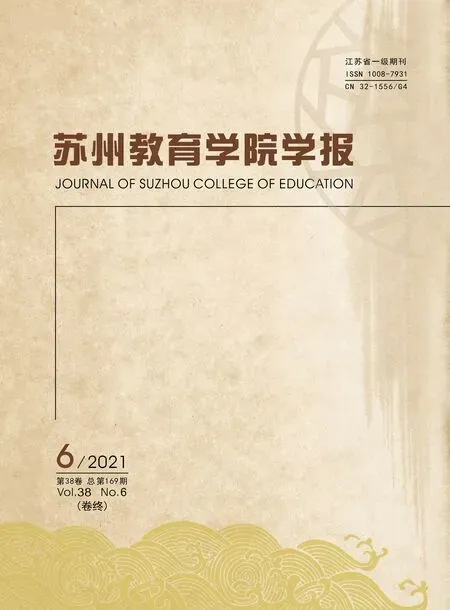明清易代之际文人画家艺术观念研究
——以王时敏为例
马文真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历史上的遗民文人画家多出现于元、明、清朝代更迭之际。作为亡国之民,他们通常有两个选择—出仕新朝或退隐不仕,前者被称为“贰臣”,被认为人格品行有损,违背了儒家传统思想中不仕二主的明节,这类人中不乏善诗画的文人精英,如吴伟业、龚鼎孳、钱谦益、梁清标等;后者则拒绝归降新朝,成为不仕的归隐文人。而王时敏却并不属于以上两类,他在明朝时出仕为官,满清入关后,虽归降清廷却并未出仕,此后的言行中亦饱含对故国的思念与归隐山林之愿,迎降的失节行为成了他一生的污点。与之情况类似的还有王鉴,明朝覆灭后,王鉴并未完全放弃入仕的念头,仍以游历为名实则意谋青云之路,后谋官未成,遂彻底放弃出仕之愿。考察这一类文人群体的代表,他们在政治立场、绘画创作风格、艺术思想上有着一致性。
一、艺术理念之“画家正脉”
明末清初,文坛、画坛乱象丛生,出现了种种不良风气,“盖明之末年,士大夫多喜著书,而竞尚狂禅,以潦草脱略为高尚,不复以精审为事”[1]。儒家文人士大夫应有的严谨精神和天下为公的社会责任感早已消失不见。在这易代鼎革之际,出身于书香门第、受教于孔孟之道的王时敏,肩负起了拨乱反正、整振画坛风气的责任。
“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江南太仓人,明大学士锡爵孙。以荫官至太常寺少卿。时敏系出高门,文采早著。鼎革后,家居不出,奖掖后进,名德为时所重。明季画学,董其昌有开继之功,时敏少时亲炙,得其真传。”[2]王时敏对清初画坛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他引领了主流的审美价值取向,继承了董其昌的正统绘画思想,力图重振正统之风。董其昌极为注重“师古”的重要性,在其绘画理论与艺术实践中多有体现,如“如柳则赵千里,松则马和之,枯树则李成,此千古不易。虽复变之,不离本源。岂有舍古法而独创者乎”[3],“学书不从临古入,必堕恶道”[4]632,“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4]680……无不在强调师法古人、以古为师的重要性。董其昌深谙儒家之道,认同儒家美学的价值观,王时敏跟随其学习,受其教导,继承了他的理论思想,推崇师法古人,承继先贤之道,坚守中国传统绘画的正统源流与脉络,重整时弊以正画坛之风。王时敏在《西庐题跋》中提出:“盖因渊思兼得神解,于古人同鼻孔出气,下笔自然契合,无待规摹。”[5]在学习古人的过程中,如果能做到领悟古人气息,得古人神韵,便可达到“下笔自然契合,无待规摹”的造诣。
王时敏还将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论”加以完善、扩展、延伸,并把“南宗画”与“文人画”的概念整合成“画家正脉”,一个“正”字不仅是对绘画艺术的重塑,同时也契合了儒家思想之正统地位。他在《西庐画跋》中言:“书画之道,以时代为盛衰,故钟、王妙迹,历世罕逮,董、巨逸轨,后学竞宗,固山川毓秀,亦一时风气使然也。唐宋以后,画家正脉自元季四大家、赵承旨外,吾吴沈、文、唐、仇以暨董文敏,虽用笔各殊,皆刻意师古,实同鼻孔出气。迩来画道衰熸,古法渐湮。人多自出新意,谬种流传,遂至衰诡,不可救挽。乃有石谷起而振之,凡唐宋元诸名家,无不摹仿逼肖,偶一点染,展卷即古色苍然。毋论位置、蹊径,宛然古人,而笔墨神韵,一一寻真。且仿某家,则全是某家,不杂一他笔。使非题款,虽善鉴者不能辨。此尤前此未有,即沈、文诸公亦所不及者也。余尝谓石谷惜生稍晚,不及遇文敏公,使公见之,不知如何击节叹赏,石谷亦自恨无缘,时为惘惘。”[6]12王时敏强调的“画家正脉”,比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内涵更为广阔,提倡承袭古法,其中不仅包含“南宗”的文人画家,同时也归纳了部分“北宗”画家。被董其昌贬义归为“北宗”的赵令穰、赵伯驹,王时敏却把他们归入“画家正脉”,重新整理了画家的传承脉络。王时敏“画家正脉”之论不仅开启了清初画坛的新气象,也为画坛正统之路的延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对后来的王原祁、吴历、恽南田等画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艺术风格的承袭与形成
王时敏承袭“董巨”①南唐画家董源与五代、宋画家巨然并称“董巨”。、“元四家”②指元代山水画的四位代表画家,一说为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一说为吴镇、黄公望、王蒙、倪瓒。、董其昌一脉,深受他们的绘画思想的影响,一生追摹黄公望画作,其在《西庐画跋》中言:“元季四大家皆宗董、巨,秾纤淡远,各极其致,惟子久神明变化,不拘拘守其师法。每见其布景用笔,于浑厚中仍饶逋峭,苍莽中转见娟妍。纤细而气益闳,填塞而境愈廓,意味无穷。”[6]17他又在《清晖堂同人尺牍汇存》中言:“弟一生规抚痴翁,访求真迹,无虑廿有余本,惟长卷最不易得。如《沙碛图》不过盈尺,《溪山雨意卷》长不满五尺耳,已为稀世之珍。前见吾兄所临《富春图卷》,长二丈余,观其点置,峰峦林木,溪桥村落,苍深潇洒,逸气飞翔。与平时畦径洗脱略尽,一峰墨迹至此神矣,化矣,天下之能事毕矣。弟研弄笔墨五十余年,所见一峰真本当以此为第一,恨曩时未及搜罗,幸吾兄相过即为我临此长卷,以补缺事,弟虽衰残,犹欲时置案间,一日三摩挲,略得其百分之一二也。”[7]在王时敏的画学理论中多处可见其对黄公望的推崇,他对黄公望画作的临习孜孜不倦,极力追摹,更是将其作为终身学习的对象。至于在追摹前人作品的过程中,王时敏为何会作出这样的艺术风格的选择,这是需要我们着重讨论的一个问题。高居翰认为:“长久以来,在中国的画评中,绘画风格与画家的社会地位一直被相提并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末,也就是11世纪到12世纪初期间,当其时,画家出身贵族或身为文人官僚者,其社会地位往往被用来引证说明其人绘画的特质。换句话说,一旦风格的选择成为重要的课题,而且,从传统中创新或撷取风格,为的乃是配合画评的品味、教条与个人的好恶,而不是为了能够有效地创造出传统标准所认为的较出色的意象或画作时,则此种画风不离画家社会地位的观念,便油然而生了。而画家在这种比传统更为广阔的考虑下所做出的风格选择,着实更能显露出画家本人的特性。”[8]长久以来,学界在对画家绘画风格的品评上一直无法脱离画家自身的社会身份与地位,画家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政治身份与其绘画特质和风格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而在明末清初的特殊社会政治环境中,王时敏在绘画风格上作出的选择更能显示出个人的特性。因此,我们可以从王时敏的生平经历、所处环境与社会身份等方面入手,分析其艺术风格的承袭与形成。
王时敏的祖父王锡爵于万历年间担任首辅,在祖上的荫庇下,王时敏年纪轻轻便顺利进入仕途,23岁就官至太常寺的尚宝丞,位列禁廷侍从,历经万历、天启、泰昌、崇祯四朝。在晚明黑暗的政治环境和激烈的党派斗争中,其显贵的出身注定了他无法置身事外。明亡前数年,王时敏卷入了复社的党争,最后以失败引退告终,从此消失于政治舞台。1644年,清军入关,易代鼎革之际,王时敏作为深谙官场的文人,在混乱的政治环境中,作出了最有利于自己与家族的选择,成功地进行了身份转化,成为世人所称的“遗民”,既拒绝南明政权的征召,又无意侍奉新朝。王时敏虽未入仕,但却悉心培养子孙,鼓励他们积极入仕举业,他为保家族延续可谓是百般经营,其子孙也不负所望,子王揆、王掞,孙王原祁皆中进士,延续了世家大族的门风,使得入清后的太原王氏依旧显赫。政治上的退隐也促使王时敏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绘画事业中。王时敏少年时期便跟随董其昌学习,受其教诲,而这期间正是董其昌受黄公望影响最深之时,因此,在董其昌的教诲下,王时敏也深受黄公望的影响。早年生活环境稳定之时,王时敏临习董其昌所摹宋元名家画稿,仍存董其昌笔意,董其昌去世后,局势动荡不稳,生活环境的不稳定促使王时敏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放在绘画上,他临习黄公望画作的勤奋程度令人惊叹。程国赋、吴肖丹认为:“王时敏甲申(1644)前后画风不变的意义,从知人论画的角度看,作为一个温柔敦厚的儒者,在易代之际勉力延续家族血脉、产业、门风,其家族又幸而能渡过劫难,稳定的画风正是他‘独际其难’、维持安稳心态的如实反映……”[9]王时敏绘画风格的稳定与其易代鼎革之际求安稳的心理是分不开的,而黄公望画作中平稳悠然的特点,显然能够符合历经局势混乱、朝代更迭后退隐在野的王时敏的心理和其遗民画家的社会身份。
商勇指出,王鉴在明亡后,无意在新朝攀高结贵,逢人就要借亡赵遗民赵孟頫的作品来体现自己的遗民心态,“赵孟頫在宋亡以后,隐于吴兴,不得已入仕新朝之后,妄图以一个政治上被征服者成为文化上的征服者,他的追求古意的艺术思想,正是以坚持发扬汉民族绘画传统为己任的”[10]。这样看来,或可认为王时敏也是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其与赵孟頫的身份、所处环境确实有相似之处—都是前朝遗民,面临的也都是异族统治。结合王时敏开城迎降的行为来看,其个人与家族也是在顺应形势,属于清廷统治下的顺民,虽个人未出仕,但从其悉心培养、鼓励子孙出仕为官的举动可以看出,其并未放弃家族继续走政治道路的想法,意欲发挥文人世家的作用,力求在新朝占据一席之地。王时敏家族的顺应时势,或多或少地也影响了其在文化艺术表现上的风格与特点,他展现出的绘画风格与理论,多少都有迎合清王朝统治者的倾向,日本学者新藤武弘提出:“‘四王’所继承的并非董其昌那种给山水画带来革命的变化的画风,在清康熙时代的强大政治影响所形成的传统文化要成为正统的倾向之下,元代绘画尤其是黄公望悠然自得的风格更契合于‘四王’们的气质。”[11]不同于一些隐居遗民画家的画中流露出的伤感、萧瑟气息,王时敏的画中展现着中正平和之气,包含着更为明确的儒家美学思想,这与他所持的政治立场是分不开的,他本人虽未出仕清廷,但他在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迎合新朝的倾向。清初,统治者大力推崇程朱理学,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文学艺术领域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影响,体现为儒家美学思想的兴起。王时敏在不断地“仿古”“摹古”中体现出逐渐内化了的儒家精神与美学思想,正契合了当时清王朝所推崇的理学思想在文艺领域的要求,其带领的“四王”画派能够受到清廷统治者的青睐并逐步占据正统地位是必然的。在追崇黄公望的过程中,王时敏也并非全是以再现黄公望的艺术风格为目的,或者说并非全然的“复古主义”,与其主要的追摹对象黄公望相比,其绘画更凸显了中正平和的特点,正如卢辅圣在谈及王时敏时指出的:“他在继承董其昌绘画思想的前提下,开始有意识地将董氏有禅学气息的风格修正为符合儒学审美理想的风格。对最主要的师法对象黄公望图式的运用,由此芟除了荒率超迈的成份,而发扬其平正中和的一面……”[12]王时敏有意摒除黄公望画中荒率超逸之气,代之以更为中正平和的气息,不断向儒家审美思想靠拢,与清初画坛所需的正统之气相契合。
三、结语
明清朝代更迭之际,复杂的社会背景与政治环境无疑对这一时期的画家群体造成了影响,他们的生存环境、人生观、所属的政治立场与其在艺术风格和理念上的呈现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王时敏作为特殊时期的特殊文人群体中的一员,既非出仕新朝的贰臣,亦非严格意义上的遗民。因此,通过分析其生平经历、社会环境来窥探他的绘画风格和艺术理念,我们以期更清晰地理解他的艺术理论及艺术成就,也希望能够给今后研究此类文人画家的学者以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