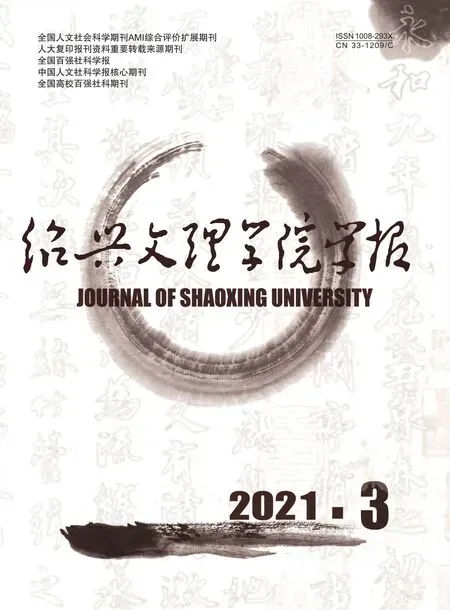不应失落的崇高
——世纪之交中国当代文学崇高缺失之思考
张冬秀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崇高既是重要的美学范畴,也是备受关注的文学命题。作为美学范畴,从古罗马的朗吉弩斯开始,众多西方思想家如朗吉弩斯、康德、席勒等都基于各自的时代精神与哲学思想对崇高进行过理论阐述。朗吉弩斯将崇高视为伟大心灵的回声;康德认为崇高是一种以理性为根基的道德感,能引起“惊叹或崇敬”的情感;席勒认为崇高是人对环境的超越;利奥塔则认为崇高是对不可表现性的呈现,以不确定性为核心。可以说,作为美学范畴的崇高,其内涵在不断地扩展,但其核心意义多与道德感、自豪感或强大精神力量有关。同时,从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人们在讨论崇高时多将其与文学结合,力图以文学呈现崇高,以崇高升华文学。朗吉弩斯的崇高就是“庄严伟大的思想、慷慨激昂的热情、构想辞格的藻饰、高雅的措词以及尊严和高雅的结构”[1],是一种文学风格,席勒则将激情的讽刺诗与崇高联系在一起,哈罗德·布鲁姆更是将崇高作为文学经典的美学标准。这不仅是因为文学有着对崇高的追求,更是因为崇高赋予了优秀文学作品超越的精神境界。
当崇高与文学结合时,崇高赋予优秀文学作品在内在精神、外在行为及语言形式等方面超越一般性文学文本的特质:从内在看,崇高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源于作者伟大的灵魂和高尚的人格,也源于能使读者达到更高精神境界的作品本身,这是理性对当下有限性的超越,指向善与美的价值取向,并带来文化的启迪与精神的提升;从外在看,崇高源于一种强大的实践力量。这种实践源于文学作品中剧烈的矛盾冲突,伴随着激情,经历艰难的精神抉择,并指向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实践行为;从语言形式看,具有崇高美的文学作品具有严肃的语言、高雅的修辞,严谨的结构。崇高的文学能为读者注入精神力量,使读者产生对美好生活、高尚人格的追求与渴望。文学的崇高精神也是评价一个时代审美健康与否的标准。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不仅要记录时代的巨变,更应呈现时代的精神风貌。传递崇高精神、塑造崇高审美形象,这不是时代强加于文学的写作任务,而应是文学的应尽之责。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出现了“躲避崇高”、消解崇高的现象。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新世纪文学创作中,并成为新世纪文学创作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重构属于新世纪新时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崇高”成为当前文学必须面对的任务。
一、世纪之交中国当代文学崇高缺失的表现
作为一个时间范畴,本文所称的“世纪之交”指1990年代中期至2014年这段时间。在这个阶段,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明显地出现了崇高缺位,无论是王蒙的理论倡导,还是新历史主义、新现实主义思潮,私人写作、欲望写作、底层写作……一系列在世纪之交相继出现的文学思潮、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都表现出对崇高的“躲避”,甚至是对崇高的消解。
(一)缺乏基于文学自觉,能激发崇高情感的作品
文学具有审美功能,文学活动具有审美无功利性。它可以摈弃外部环境因素,以自身为目的,使人进入无现实目的的纯粹精神世界。文学也具有文化功能。它总是传递和呈现着一个国家、民族、时代的文化品格与精神面貌,并借此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影响。崇高作为通常情况下被颂扬的精神境界,能带来人性的升华和实践的超越,其所具有的精神引领及情感激励作用,自然不应被排除在文学话语之外。
由于缺乏对文学功能与文学价值的自觉与反思,世纪之交的一些作家往往倾向于将传递崇高精神、激发崇高情感规避于文学创作之外。对宏大叙事的排斥,对英雄形象的消解,使虚无的历史、原初的生存、隐秘的私情、残酷的现实占据文坛,甚至形成一股股接踵而至的文学思潮。在世纪之交,莫言、阿来、北村、刘震云等作家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将历史的发展归结为虚无的宿命,用原初的生存欲望取代人类精神上的崇高追求;刘醒龙、谈歌、关仁山等受新现实主义思潮影响的作家虽聚焦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却站在道德、伦理的立场专注于展示丑恶,“分享艰难”,从而放弃了文学对崇高的追求;而以陈染、林白、卫慧、棉棉为代表的一系列个人化写作虽实现了个人话语的表达,但也以隐秘生活的公开和私人情感的宣泄满足了读者的窥视欲。伴随着互联网技术普及而崛起的网络文学更因其传播媒介的大众化,带有明显的通俗文学特质。玄幻、穿越、宫斗、盗墓的写作模式完全放逐了文学的崇高精神,而是以点击率、阅读量作为创作的内驱力。于是,在世纪之交的当代文坛,我们看到了现实的无情、男女的滥情、人与人的虚情假意,读到了寡淡、烦躁、阴郁、冷漠、挫败和悲情……却很少看到虽败犹荣的抗争、直面困境的勇气、净化灵魂的激情。这里有苦难没有悲壮,有平庸没有高尚,有技巧的新颖却没有精神的脱俗。这些都使当代文学离崇高品格越来越远。
(二)缺乏基于主体自觉,具有感召力的崇高形象
崇高的产生离不开主体自觉。这既是实践自觉,也是精神自觉。一方面崇高“产生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客观实践和斗争中”[2],这种实践自觉使人能在冲突与困境面前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另一方面崇高的“最根本诉求”,“是人能够在言语和情感上超越人生”[3]2。这种精神自觉使人能超越世俗,进入一种精神自由,以至获得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超人品质”。而在文学作品中,具有崇高品格的人物形象往往在实践与精神层面呈现出主体自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中国作家的主体意识逐渐被唤醒。他们开始摆脱政治的羁绊,“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4],在实践与精神层面寻求主体地位。但从80年代后期开始,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坛很快就出现了消解主体价值,否定主体精神,解构主流价值体系的倾向,以至有学者指出先锋文学之后“‘大写的人’已经萎缩”[5]。在这种环境下,当代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缺乏那些带有主体自觉且具有精神感召力的崇高形象。世纪之交的当代文坛有母亲“上官鲁氏”(莫言《丰乳肥臀》),有父亲“许三观”(余华《许三观卖血记》),有革命者“秀米”(格非《人面桃花》),有都市新移民“富萍”(王安忆《富萍》),有底层打工者“老乌”(王十月《无碑》),有沉浸于私人生活的少女“倪拗拗”(陈染《私人生活》)……这些形象虽不能囊括世纪之交当代文学的全部形象,但他们或是充满原始蛮力,或是张扬个性自我,或是承受生活重压。这些形象带给人的有苦难,有压抑,有卑微,有凄楚……而唯独缺乏精神上的崇高。在这些作品中,人性的阴暗面被无限放大,人生的无意义被过分强化,读者不仅很难看到人物在矛盾冲突面前的实践自觉,也体会不到人物精神中的超越性品质。缺乏真正具有主体自觉的、拥有崇高品格的人物形象,这不仅弱化了中国文学应有的启蒙功能,也拉低了当代文学的整体品质。
(三)缺乏基于审美自觉,坚守崇高品质的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是对既有文学作品、作家及文学现象的分析、阐释与评价,也对文艺发展提供一种理论引导。它首先是一种审美批评,要求批评者从审美思维进入文学研究,而不是将文学当作证明某种理论的工具。同时,文学批评与创作一样都是向美、向善的,这使它不管应用何种理论最终都以实现对美的追求作为最终目标。
世纪之交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着明显的审美缺失与正向价值引导不足的现象。一方面对西方理论的趋之若鹜带来了大量的强制阐释,使当代文学批评失去了审美自主性。在解构主义、生态批评、文化研究等理论的影响下,文学批评者广泛地从阶级、性别、殖民、生态等非审美视阈进行文学研究,他们在挖掘作家潜意识、文本隐性寓意的同时也使文学沦为各种思想理论传播的工具;另一方面受市场化、商业化的影响,面对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文学大众化甚至庸俗化,一些文学批评者失去了职业操守。他们不是以“具有崇高风骨”[6]的文学批评引领创作,而是加入了媚俗的行列。“‘躲避崇高’已非个别现象,反而成了某种时尚,放纵欲望、淡漠理想、娱乐至死的风气日渐乖张。”[7]于是,伴随着文学批评审美意识缺失,以及对崇高品质的漠视,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崇高缺失的情况愈演愈烈。
(四)缺少基于文化自觉,具有时代特质的崇高诠释
作为一个源于西方的美学范畴,有关崇高美的研究往往带有西方色彩。剧烈的矛盾冲突,艰难的精神抉择,主动献身的精神倾向,这些精神特质使崇高与西方悲剧美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却没有崇高或悲剧的美学范畴。无论是孔子的“尽善尽美”还是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抑或司空图《诗品》中有关“雄浑”“豪放”“劲健”“悲慨”“流动”等审美特征的描述,其与西方美学的崇高虽有相似,但在本质上存在差别。因此,中国文学在书写崇高、表现崇高精神时必然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崇高美的表现形式。但在世纪之交,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却缺少这种文化自觉,更缺少对中国崇高美的有效表现。
在中国当代,崇高美往往与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有直接联系,其内涵与表现形式并未出现突破与变化。相比之下,西方对崇高美的研究历时千年而不衰,崇高美并没有固化为某种特定的文学风格,也没有被理性主义所颠覆,更没有被现代主义思潮下的荒诞、滑稽、丑等范畴所淹没,或被后现代主义彻底解构。这既反映出崇高美自身的坚挺与存在价值,又反映出西方对崇高美研究的持续。而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新的社会环境却并没有催生出对于崇高美的新认识。缺少对崇高美的现代诠释,无法从新的时代精神出发赋予崇高美以新品质,这也使新世纪中国在崇高美的表现上停滞不前。
二、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崇高缺失的原因
世纪之交,中国当代文学崇高美的缺失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这其中有文艺政策及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
(一)特殊时期文艺政策的影响
1949年至1976年期间,中国当代文学处于“高度组织化”、高度政治化的阶段。此时,作家创作无不受到时代政治的影响,各时期的文艺政策成为文艺创作的直接导向。从20世纪50年代对“两结合”文艺创作手法的提倡,到60年代对“三突出”文艺创作原则的贯彻,当代文学史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一批讲求运笔“升华”,站在时代“制高点”的作家,产生了一批有着“光辉”,能“照亮人间”[8]的作品,更出现了大量“高大全”形象。这些人物虽然充满革命激情,展现出“英雄”似的高尚情操,但这却是特定语境下的“崇高”,也就是王蒙在90年代所要“躲避”的“崇高”,是一种“伪崇高”,因为这些“英雄们”所要创造的历史是“朝着乌托邦未来发展的神话史诗”[3]193,他们坚持的信仰不过是“一种极端和激进情绪下的政治‘幻影’”[9]。作家对这种“崇高”精神的展现更带有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在此类表现“高大全”形象的作品中,“崇高”产生的复杂环境被简单化处理为二元对立的冲突与矛盾,“崇高”精神生成的真实心理过程简化为“革命热情”,“崇高”所具有的精神力量更是被“神化”。在特定文艺政策的规约下,一些作家对“崇高精神”的传递,对“崇高形象”的塑造,“严重败坏了人们的胃口”[7],并带来了人们对“崇高”的排斥与不信任,而此后“对它的清算和反思符合文学发展的需要”[7]。也正是这种“清算”与“反思”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崇高缺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人道主义、主体性等“话语资源”的影响下,虽然一些作家如王蒙、宗璞、丛维熙等在进行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的过程中,力图重塑文学的崇高形象,但更多年轻作家既要让以往全能的“崇高形象”走下神坛,更要从根本上否定崇高精神的存在。他们将崇高与主流、正统或政治意图联系起来,认为“崇高形象”意味着又一次盲目的英雄崇拜。于是,他们以大胆的形式实验取代传统的形象塑造,意在使文学摆脱以往政治的束缚;他们以对个人生活、个体价值的珍视与对自我内心情绪的表达,使主流价值体系在这里失效。在对前一阶段文艺的反叛中,这些作家虽然摧毁了旧有文化体系中的“伪崇高”,消解了长期束缚中国作家的政治因素,也在反对“伪崇高”的同时否定了崇高美与人之崇高精神的真实存在,带来了一种反崇高的倾向。
(二)世纪之交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促进了文化转型。“大众文化的兴起和迅速扩张,成为当代社会文化转型的标志性事件。”[10]大众文化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文化格局,以往一体化道德追求与理想主义的文化氛围被“个人性的多元文化格局”[11]325取代。正如李泽厚所言,“大众文化不考虑文化批判,……但这种态度却反而能改变一些东西,这就是……对正统体制、对政教合一的中心体制的有效的侵略和解构”[12]。然而,这种“侵略和解构”在清除意识形态遮蔽的同时,也会消解一切精神性的存在,包括对崇高的消解。因为崇高作为一种强大精神力量和实践力量,总是带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在社会的任何发展阶段,它都是主流意识形态推崇的精神品质。于是,崇高“顺理成章”地成了大众文化嘲讽、调侃、狂欢的对象。
世纪之交,市场经济及大众文化对“自由”的追求,虽然“消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一元性规范”[11]325,使个人的主体价值得以确立,但对个体的过度关注,导致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对立,甚至使社会文化心理呈现出个人主义的倾向。而中国文学的崇高精神往往与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紧密相连,带有明显的集体主义精神向度,这也使崇高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学躲避的对象。
此外,大众文化服务于市民阶层,秉持着世俗化的价值取向,这也成为世纪之交许多中国作家的审美追求。世俗化的价值取向使作家们表现出对平凡人生存方式的认同。他们开始以平常心记录平凡人的生活,描写平凡人的卑微与渺小,展现日常生活中的辛酸与苦难。许多作家有意地“回避深刻”,他们不再塑造那些伟大的历史创造者与践行人,也不再表现人类精神深处对于崇高与神圣的向往与追求。于是,传统审美活动应有的对崇高美的追求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被世俗化审美追求所取代,这也就造成了世纪之交中国当代文学崇高的缺失。
(三)现代工业社会使崇高精神缺少了社会语境
世纪之交中国当代文学崇高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现代化工业大生产创造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消费世界。它不仅使人们摆脱了物质匮乏的生活状态,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化大生产下的生活是一种高度同质化的生活。它以生活资料的丰裕掩盖了生活方式的高度程式化、重复化、同质化特征。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多数时间人们都是以相同的节奏按部就班地学习、工作和生活。他们吃相似的食物,有相近的作息时间,在相似的钢筋水泥、车水马龙间奔波。于是,无论在社会生活领域,还是在私人生活领域,能激发崇高精神的外部条件都变得匮乏。文学表现生活,这种外在生活环境的变化使崇高成为世纪之交当代文学中的“稀缺品”。同时,在这种同质化的生活中,剧烈的矛盾冲突极少出现,艰难的精神抉择更是罕见。人们沉浸于现有的生活状况中,进而忘却了自身的精神需求,成为了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而身处在现代生活中的中国作家也不免被这种同质化的生活所驯化,并渐渐丧失了发掘崇高精神、展现崇高之美的能力。
三、重建新时代中国文学崇高需要思考的问题
重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崇高精神要求作家与批评家从审美取向、文学观念与时代内涵等方面思考新时代中国文学崇高精神的特质,以便在创作中予以表现。
(一)中国式崇高的审美取向
崇高作为美学范畴源于西方,中国虽有类似的美学理念,但因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历史背景的不同,中西方对崇高美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崇高精神,必须明确中西方对崇高在审美取向上的差别。
首先,在审美取向上,西方崇高美强调悲剧的对抗性,中国崇高美追求诗意的和谐性。在西方,天人对抗、主客二分的文化形态使其崇高美带有明显的对抗性特征。西方从朗吉弩斯的时代,人们就将崇高视为一种庄重、浑厚的风格,崇高带有对异己力量的压抑、排斥、震撼,是有浓厚悲剧色彩的对抗与批判精神。在中国,一方面传统的天人合一、主客融合的文化形态使中国古人更追求浑然天成的大美,这是虽宏大但却不具有对抗力、不带有恐惧感的壮美;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持人情性”的诗学传统与温柔敦厚的美学追求,使中国传统文化更追求雅致、秀婉、柔和的优美。因此,西方对崇高的推崇与中国对壮美、优美的追求,使得中国文学的崇高精神在审美取向上就不同于西方美学范畴的崇高。这种崇高是以壮美为追求,以优美为常态的美学形态。
其次,西方中世纪以来,以希伯来宗教理想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西方的崇高往往带有一种基督教文化特有的拯救意识和博爱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仁”“礼”“忠恕”都是对人社会行为的规范。“崇高之位,忧重责深”,正说明中国文化中的崇高更多指向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此外,中国近代以来审美文化中的崇高带有启蒙性功能诉求。在近代中国,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首次介绍了康德及叔本华美学思想中对“优美”与“壮美”的比较,而“壮美”的译法后来逐步落实为“崇高”。从梁启超倡导“三界革命”,大力赞扬西方诗歌“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预借西方文学之“崇高”精神和雄浑之气,“激发国民之勇气,以养国魂”,到王国维对西方文豪歌德与席勒赞扬“呜呼!活国民之思潮、新邦家之命运者,其文学乎”,再到鲁迅对“摩罗”诗人的推崇,称他们“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人心,绵延至于无已”。可以说,在中国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变中,先贤们不仅看到了中西方文学在审美取向上差异,更希冀用西方文学之崇高唤醒和重铸国民之精神。这种对于崇高的推崇,使得中国文学的崇高精神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审美取向,更带有以崇高而“新民”,以崇高而“立人”的启蒙性诉求。
因此,明确中国文化视阈下崇高的独特性,理解中国式崇高独具的源于天人合一的壮美气魄,源于忧患意识的社会使命感,以及其启民智、振民魂的启蒙功能,作家才能在创作中更有效地传递属于新时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崇高。
(二)现阶段崇高的时代特质
从审美特征看,崇高美指向善与美的正义感,具有超越自然人性的强大精神力量。正是这种特质使崇高能带给人心灵震撼和精神洗礼。一段历史时期,作家过分强调崇高的超越性特质,缺乏对基于时代特征的崇高的理解。这不仅造成了文学对崇高的“神化”,也带来了人们对当代文学中崇高美的疏离。因此,重塑新时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崇高,需要从当下入手,赋予崇高以新的时代特质。
一方面,以往中国作家将崇高与集体主义相连。他们在塑造一系列大无畏英雄形象的同时,也将自然人性与日常生活排斥于崇高之外。因此,重塑中国文学的崇高,要不断丰富对崇高的体认。文学中的崇高并非与自然人性完全隔离,它生发于自然人性,更是自然人性的最高阶段。另一方面,以往中国当代文学对崇高精神的表现或与国家命运相连,或与民族存亡相关,往往生发于“危难时刻”“危急关头”。但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重塑中国文学的崇高,需要扩展崇高的表现领域,从现实生活入手。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13]。在新时代,崇高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崇高形象也可能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新时代中国作家笔下的崇高形象可以是传统意义上有着丰功伟绩、为民族大业流血牺牲的英雄人物,也可以是在时代进程中践行着各自理想,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强大精神力量的普通人。
(三)新时代崇高的文学诉求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文学与崇高始终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不只是以文学表现崇高,借文学塑造崇高形象的问题,其背后隐藏着时代政治与审美体验之间的关系[3]6。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作家往往以文学之崇高精神服务于时代政治,借审美体验解决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此时,文学诉求服从于社会需要和国家意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文学的审美意识重新觉醒。对个人审美体验的重视使文学自身的诉求强于社会需要,作家又借消解正统价值中的崇高来摆脱时代政治、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可以说,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崇高缺失一定程度上源于文学与崇高的分离。崇高在很长一段时期并未真正成为文学的自身需要,而是文学创作的手段或文学表现的工具。因此,重构中国当代文学的崇高,作家有必要思考新世纪、新时代中国文学的精神诉求,明确文学与崇高的关系,处理好文学自身与时代和社会需要的关系。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特别强调,作家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13]。可以说,新时代的崇高不仅源于人类的精神需要,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诉求,它绝非外部因素强加于文学的责任,而是文学的核心价值所在。新时代作家在重构文学崇高精神时,既应从人性、人类的角度展现人之为人所具有的崇高精神,更应在摈弃“伪崇高”的同时让人感受到崇高所带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四、结语
新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必须正视文学崇高缺失的问题,认识到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文学在崇高情感表达、崇高形象塑造、崇高美自觉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并从历史和现实等方面寻找崇高缺失的原因。发现中国式崇高的审美特质,探求新世纪崇高的时代特征,明确新时代崇高的文学诉求,是当下重建中国文学崇高时不能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