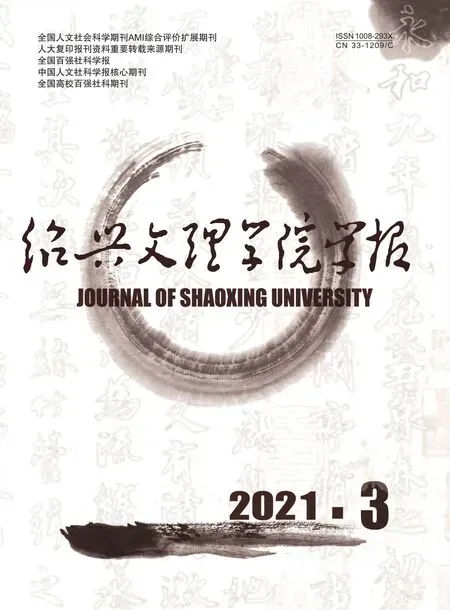蔡仲光与毛奇龄交游考论
汪 胜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毛奇龄早年与蔡仲光、包秉德、沈禹锡并称“萧山四友”,彼此视若兄弟,且“皆博洽群籍,雅善文章”[1],才学相当。毛奇龄曾数度流亡,遍交文友,继又以近花甲之龄应举出山,最后著书授徒,名满天下,其余三人则因隐居而湮没不闻。尤其蔡仲光之博学被推为萧山第一,不仅毛奇龄对他甚为推崇,屈大均也在《怀浙东毛君》一诗中直言“萧山才子推毛蔡”[2],将其与毛奇龄并举。蔡毛二人早年相识,交谊甚厚,奇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实师事仲光。二人的交游可待深入探察,以补萧山文坛研究之重要一隅。
一、明亡前、明亡之初蔡仲光与毛奇龄的交游
蔡仲光长毛奇龄十岁,仲光自言两人“家相去里许,相近,自少至长相敬爱……及处闾党,垒块不平之气无一不相闻也”[3]298,又说自己“兄事大千(毛万龄)而弟畜大可(毛奇龄)”[3]293。毛奇龄亦曾云“少与包二秉德、蔡五十一仲光、沈七禹锡为乡游,道古论文,视若兄弟”[4]2581。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
蔡仲光与毛奇龄在学问上早有交集。毛奇龄《何毅庵墓志铭》记载:“予时薄理学,以为徒事论辨,非躬行,无益,乃与仲兄锡龄、同邑蔡仲光、始宁徐咸清、山阴张杉穷《易》《诗》《尚书》《论语》《孟子》及三《礼》《春秋三传》。”[5]彼时为1643年,毛奇龄21岁,他觉察到理学的空疏无益,对理学产生怀疑,转而与蔡仲光等人研读古书,求索真理于经书根本,以图解蔽。其时蔡仲光31岁,在学问上已小有所成,其在经学上的造诣,更是得到了包括毛奇龄在内的萧山诸士人的认可、推崇(1)毛奇龄在《四书索解》《四书改错》等书中,曾数次标榜蔡仲光的经学观点。。蔡鹤《跋〈谦斋遗集〉》云:“里中西河氏,始有小毛生之称。公(蔡仲光)与之订忘年交,而毛实师事之。”[3]158并非虚言。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陷京师,崇祯帝自缢殉国,明亡。闻此消息,士林震动,蔡仲光、毛奇龄等人哭于孔庙达三日。之后,蔡仲光与毛奇龄、包秉德、沈禹锡窜身萧山城南山读书,时称“四友”[4]1723,其时蔡仲光约32岁,毛奇龄约22岁。他们所读的是“南北唐五代辽金元史”等书。四人隐居读史,除了有避乱的考量,与前文所述因怀疑理学而读经书一样,是属于遭遇危机而求解于书,他们“试图从对史书的研读中找出明亡清兴的奥秘”[6]33。
明代知识分子素以气节著称,除了忠烈,遗民甚至一些贰臣都不乏刚强不屈的一面。胡春丽《毛奇龄交游考略》就提及:“顺治年间,毛奇龄入杭州登楼社,与社中诸子集会切磋。有魏耕、祁班孙、李文达、丁澎、陆圻、查继佐、宋实颖、来蕃等。他们以结诗社为幌子,秘密进行反清复明活动。”[7]翻检丁克振《迂庵改存草》卷首所录登楼社68人姓名,蔡仲光也在列。有诗文证据表明,蔡仲光与社中不少人有直接交往(2)具体为姚宗典、顾有孝、王廷璧、徐白、朱士稚、徐芳声、魏耕、归庄、葛芝、蒋平阶、祁班孙、姜廷梧、毛奇龄、单隆周、李达、来蕃,计16人。,其中毛奇龄、徐芳声、单隆周、祁班孙、蒋平阶都是他的至交,李文达则是他关系亲密的表弟。以此而言,蔡仲光很可能与毛奇龄志同道合地秘密参加过抗清活动。
毛奇龄好辩,论人谋事又有不加善言的情况,曾多次开罪于人,至于流亡他乡。毛奇龄40岁时,被仇家诬陷杀害营兵。蔡仲光获知官府缉拿的消息,连夜告知毛奇龄出奔(3)事件始末详参毛奇龄《西河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8册影印萧山城东书留草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5页。。奇龄出走渡河后,作《渡河寄大敬、徽之、宪臣,并呈张五杉、张七梧、姜十七廷梧、丁五克振、吴二卿祯、顾大有孝》诗,表达了对蔡仲光等人的深切怀念,倾诉了自己出走经历的艰难以及有乡不得归的悲苦,字里行间颇含声泪。蔡仲光事后则有《送王彦(五首)》记之,其中“怜君不识路,梁苑至如何”[3]475及“黄河苇一渡,白帻泪千行”[3]475语,颇可见其感同身受与深重的挂念。康熙十年(1671),毛奇龄读蔡仲光《送王彦》诗,云:“蔡子伯作《送王彦》五首。彦,即予也……辛亥十月,读《子伯集》,因拭泪书此。”[6]204蔡仲光事后作诗,情感仍不免奔涌,毛奇龄数年之后读诗,仍不免感慨落泪,其中辛酸苦楚,其中深情厚谊,不可见乎?
二、清政权巩固时期蔡仲光与毛奇龄的交游
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毛奇龄参加了博学鸿词科考试,列二等十九名,五月,毛奇龄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官,以57岁之龄正式出仕清廷[6]225-236。蔡仲光则依旧隐居不出。康熙二十年(1681),清廷诏征天下山林隐逸之士,汤斌、施闰章向大学士冯溥举荐了蔡仲光,冯又派萧山县令姚文熊亲自登门邀请,但蔡仲光拒绝了朝廷的延揽[8]。
以毛奇龄授翰林院检讨为界,蔡仲光与毛奇龄的身份变得截然不同,他们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微妙变化?
一方面,因出处不同而形成的矛盾客观存在。毛奇龄入京后,蔡仲光就数致书信表达劝诫之意,并催促毛奇龄南返,如其《寄毛大可书》所云:“前数有书致足下,其中所言大抵皆语足下归耳。足下方始以博学鸿儒致身检讨,犹未及半载也,而仲光有书辄劝其归。”[3]314蔡仲光的这封书信写于康熙十七年(1678)冬,可见毛奇龄出仕尚不足半年,友人劝归的手书就接踵而至了。蔡仲光《又寄大可》“而足下重自矜持,不妄交一人,则足下贤也”[3]317句及《五月八日寄大可书》“瑜易指瑕,名因召毁”[3]319句都不无暗示毛奇龄勿出仕清廷之意。毛奇龄对此频切之事也有记录,称他在京时:“大敬(蔡仲光)则惟恐某有他意,急作书戒勉,仿佛山巨源之措词者。”[4]315蔡仲光用语几近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让毛奇龄深为不快,他辩解道:“某原揣今年告归,而益都老师过爱之切,为聘一贫家女为后嗣计,是以羁绊不果。”[4]315推之以盛情难却,实际只是不甚积极地对蔡仲光的书信做一回应罢了。
另一方面,二人途辙虽殊,但他们的友谊无疑还是保持着的。毛奇龄北上去京,蔡仲光对身处权力中心的好友甚为关切,出于奇龄因出语不当而被迫害的深刻记忆,仲光希望他谨慎处事。在《又寄大可》文中,仲光就叮嘱道:“足下在仕宦之途,凡文章、议论、书札皆宜审谨过于平日,毋使仇怨讥讪之人得持片语以为衅端。”[3]318毛奇龄早年坎坷,如今正在得意之时,蔡仲光却多道安危之语,此非实心实意的至友不能为之。此外,奇龄在京,蔡仲光还曾托他为其售卖藏画,并嘱托毛奇龄“慎无言仲光卖画也”[3]321。仲光卖画补贴家用的窘态,不为外人言而只与奇龄道,可见他们彼时的私交仍然不错。
蔡仲光不仅自己与毛奇龄保持着私下联系,还充当了众多故旧与毛奇龄交流的中间人,其“石舟辈知足下应酬之繁,苦于修答,故有札皆入仲光简中以行,今汇以奉上”[3]319语,即反映了这种情形。而由《又寄大可》所记“足下内君仲春之初遣价邀仲光语,欲倩仲光作书劝足下多购畜妾以图允孕,因为誓言,其情甚挚,似有所悔”[3]321来看,蔡仲光还曾充当毛奇龄及其内兄的信息传递者与矛盾调解人。再如其《寄大可书》中所说:“旧有足下(毛奇龄)手书,中有《长安杂诗》一帙……《长安杂诗》在吾邑观写殆遍,三月间又以转付大鸿,传入郡城去矣。”[3]320可见毛奇龄寄给蔡仲光的私人书信,出现了被邑人广泛阅览的情况。毛奇龄的作品借由蔡仲光之手,俨然成了萧山在野士人了解京师、清廷动向的一个窗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蔡仲光本人虽不出仕,却数次向毛奇龄推荐后进。其中包括仲光女婿王坛、族裔蔡德辉,以及杨子长、来立公、来子厚、王以宁等人。蔡仲光寄毛奇龄的11篇书信中,有6篇主要是向毛奇龄推荐后进,所占数量超过半数。
在清政权巩固的过程中,贰臣充当了庙堂与江湖交流的枢纽。由蔡仲光“易斋相公过听足下之言,亲书名字于柱对间,又复赐以所刻之集”[3]316语可知,毛奇龄既得大学士冯溥赏识,便向他推荐了好友蔡仲光,仲光因此得到了清廷中枢的关注。在《与赵明府书》中,毛奇龄又为乡里好友作了宣传:“蔡仲光字大敬,张杉字南士,皆笃行君子。大敬近著论若干篇,成一家之书,要其鸿论伟裁,致足可传也。足下知之乎?”[4]200奇龄在接援故友一事上可谓不遗余力。而从更广大的范围来看,我们可以说,正由于毛奇龄等贰臣对蔡仲光等遗民的大力推举,一大批草野之人才进入了朝廷的视野。
蔡仲光、毛奇龄在文化方面的合作,及蔡仲光对清廷抵触感的大大减弱,反映出清廷借助贰臣以广泛推行的文化笼络政策的成功。蔡仲光《寄大可书》记:“近又连接手教,获睹史馆中所作诸传,磊落豪迈之中而构造严密,愈见笔舌精丽,虽承谕不敢轻以示人。”[3]320毛奇龄以《明史》纂修官身份之便,将诸翰林撰写的《明史》草稿给蔡仲光阅览,表明二人在编修《明史》一事上有所交流。实际上,蔡仲光还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参与了《明史》的修撰。笔者关注到,《明史》中的《何孝子传》实际上就是蔡仲光所写《何孝子竞传》的精缩版(4)(清)黄钰修《(乾隆)萧山县志》:“按《明史》列传,孝子复仇事止举其大略,考蔡仲光撰《何孝子传》,前后事迹纤悉具备。”。蔡震甲《录〈谦斋集〉志首》云“后于《县志》中得读《魏文靖公》《何孝子》二传,汪洋浩瀚,情事曲尽,此即《明史》中二传所本”[3]160,明确指出《明史·何孝子传》本于蔡仲光《何孝子竞传》。蔡仲光在《书魏文靖公传后》中还详细回忆了作传始末:“毛甡谓予:‘萧山历明且三百年,而有贤者二,一魏文靖公,一何孝子。魏有传而不详,何无传,子盍为斯二传者?’予自以才不能过此子,且年老善病,辞不为也。及甡访求魏、何后世,得其遗迹犹未尽泯,甡又博稽他书构此二传,成以示予,予读而叹其文之妙丽。虽然,仲光固孝子,外氏之云仍也,敢谢不敏而忘先人之旧泽哉?遂复即甡所裒聚之书,更益搜罗,因而斟酌时势,补甡不足,成此二传以识仲光夙昔向往之意。”[3]375-376其时毛奇龄应该正在编修《明史》,邀请好友蔡仲光为萧山乡贤作传,以充馆阁。仲光起先虽推辞,但他最终还是颇具决心、毅力地投身到了传记的写作当中,在毛奇龄所收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访求遗珍,补毛奇龄之不足,写成了两篇完备、详细的人物传。结合前文蔡震甲之语,可知蔡仲光最终完成的《魏文靖公传》《何孝子传》得到了毛奇龄的认可,经过改编后被纳入到了《明史》当中。
不难看出,尚未完全消去遗民情结的蔡仲光,对堂而皇之地参与清廷组织的修《明史》一事仍有顾忌,从而选择了一种曲折的参与方式:推辞不为,并又在毛奇龄完成基本书籍查找,构出二传后主动动笔。如此一来,《明史》二传的主要奠基人当是作为纂修官的毛奇龄,而不是明遗民蔡仲光了,他所写的只不过是非官方的魏、何二传罢了,至于后来蔡仲光撰写的史传被采入《明史》,蔡仲光是没有理由受到指摘的。这是蔡仲光的一种策略。若真如其所言,认为自己才力不敌毛奇龄,又老病缠身,无力作传,后来又为何能写出完备、详细,且令毛奇龄为之罢笔的魏、何二传?老病实在是遗民拒绝合作的一种极常见托词,才不如人也是文人推托的惯用修饰。那促使蔡仲光最终选择撰稿的理由是什么呢?从《书魏文靖公传后》这段话来看,有两点:其一,是好友毛奇龄邀请他作传,且毛已将作传付诸行动;其二,是蔡仲光不敢“忘先人之旧泽”,要作传表达对萧山名臣魏骥、高外祖父孝子何竞的“夙昔向往之意”,借作传存“忠”“孝”“仁”“义”之文化。第一点是不可轻视的诱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第二点。存经、存史、存文化的责任感,对蔡仲光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蔡仲光选择间接参与《明史》的修撰,又将自己的经学诸疏悉数付于毛奇龄,都是其崇高文化责任感的表现。
三、毛奇龄、蔡仲光的诗学倾向与萧山诗坛
以上所述蔡、毛二人的交游,真实地展现了易代士人的生存、心灵状态。而他们之间的文学互动,更具考察价值,以他们为中心,我们可以一窥其时萧山诗坛的诗风。
蔡仲光有《毛西河〈濑中集〉序》记毛奇龄诗作之存续,并论毛奇龄之诗:
大可未归,而旧诗藏于家者十亡六七,于是其从子阿连辈,急搜平时所遗者并远游诸作请予删辑,予因诵其诗,高秀闲远,参差瑰丽,望之无涯,按之有绪,如晴江沦涟,孤舟摇曳,目极川原,致兼凫藻,而□风儵起,激势汹涌,鱼龙怪状,乘涛蜒蜿,浩浩浤浤,不可端倪,不遯于轨而不穷于轨,非得天下之名山大川,贤豪长者以澹其怀,畅其情,扬其气,穷其变,开其愁,则亦何足以至此?[3]298
毛奇龄的诗歌是才子式的,既有高远之境,又有瑰丽之辞,有静有动,有正有奇。这种才子之诗,又得阅历之助,毛奇龄从40岁开始出奔流亡,至50余岁方归,此间他游览天下胜迹,遍交海内名朋,切磋琢磨于方家,毛奇龄诗由此才、力兼具,能体物浏亮,且在常法之上有逸出的部分。蔡仲光曾评毛奇龄赋云:“西河赋大约度取江淹,而江无其形,似思规庾信,而庾逊其宕曳。”[4]2138此与上评出于同源,可以互释。江淹、庾信都历仕数朝。江淹辞赋具有悲慨劲健之气,又在古意中流出一股清丽之韵,而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晚年则融合了丽靡、浑灏的南北文风,二人作品都显示出兼具“正”“奇”两种范式的特点。诗评、赋评气脉贯通,可见仲光评奇龄作品的用心及其一贯的立场。赋评“宕曳”一词,尤得神韵,是为才力所得之奇。毛奇龄似具有一种创新的特质,好立异,有想法,正如他提出“以经解经”的新治学方法,将“性情”由表现对象变为表现本身[10],又标立“诗无成法,只自言其志,而歌咏出之”[4]829的观点,与“正”相比,其“奇”无疑更为夺人眼目。关于其“奇”,蔡仲光又有评:
大约大可以奇,大千以正,大可之诗以无法胜者也,而大千则斤斤自信,守其法不少变。
夫无法者,非纵脱于法之外也,神彩横溢,法不足以尽之。此如李将军广之行军,不击刁斗,不治簿书,而天下无不畏其略者也。然在边陲遇勍敌之人,身为所围,则出军士,令为圜陈外向,斯岂真无法哉?盖法寓于人,人自便之中见其佚乐,忘其节制,不知其兵行甚锐,其势之盘旋如车轮之转于广野,辐转而毂不敝,其部伍固未尝乱也。特其离合背向之端杳渺无涯,其规橅隐于风雨骤至之内,人自怯其勇敢耳。[3]293
在《毛大千诗序》中,蔡仲光将毛万龄视为“正”的代表,而毛奇龄则是“奇”之典型。毛万龄诗为有法之诗,心追手摹三唐诸诗人,法古人之法,轨辙分明。而毛奇龄之无法,不是“脱于法”,而是“逸于法”,神思合于常规逻辑,并又超之。如飞将之行军,虽自在而无处不“法”,人但见其“杳渺无涯”“风雨骤至”的表象,不知其背后的“离合背向”与“规模”,便感到“奇”。在这一层面上,“奇”其实与“高超”大致可划一等号。
以上诸语,对我们了解毛奇龄俊逸遒丽的诗歌风貌,以及蔡仲光论诗之格局颇有帮助。而毛奇龄评蔡仲光诗“豹变具文质,龙神解行藏”[4]3269,也向我们揭示了蔡仲光诗歌文质兼备的面貌。
毛奇龄、蔡仲光有关诗歌体裁的论述非常值得注意,其中可见以毛、蔡为代表的萧山诗坛自有其诗体、诗风倾向,其诗体选择还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且看以下两则材料:
西河曰:“少与包二先生、沈七、蔡子伯相约为古诗,予倡言诗以五古为主,若幸成集,古诗必多于近诗,五字诗必多于七字诗。暨酬应稍烦,便乖前语,始知诗格升降皆时为之。子伯尝言:‘宋元间人每选唐人绝句、唐人三体诗、唐律诗、杜律诗,并无古体。’予欲专选一唐五古诗行世而究不可得,则其意概可知耳。”[3]418
惟诗则欲各取其所长合为一集,往欲得乐府如大敬,拟梁陈以后诗如吴汉槎,七字诗如梅村,七律如药园、禹峰、南士,五字长律如杜陵生者以为善本,而皆未有定,斯佩诗倘幸而终存,是亦五言之选也。[4]529-530
包括毛奇龄、蔡仲光在内的萧山四友早年一同投身古诗创作,毛奇龄尤重五古,且又对蔡仲光的乐府诗推崇备至,体现出明显的复古特点。以体裁而言,振起一代诗风的陈子昂,即是以五言古诗《感遇》三十八首开有唐复古运动之先河,而明代的前后七子、陈子龙摹古最明显的诗歌体裁也是古乐府和五古(5)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与先后七子的创作一样,陈子龙诗中摹拟蹊径最明显的是古乐府和五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02页)。古乐府和五古能够很好地展现汉魏古风。另外,毛奇龄对五言古诗的钟爱,还有审美上的考量,胡应麟《诗薮》云:“四言简质,句短而调为舒;七言浮靡,文繁而声易杂;折繁简之衷,居文质之要,盖莫尚于五言。”[10]五言更易造出文质兼美的效果。在《大敬生日和南士作》中,毛奇龄曾褒美蔡仲光诗“豹变具文质,龙神解行藏”[4]3269,为文质彬彬的君子之诗,又在《偶存序》中推崇“体质才气无不具”[4]919之作,便逗漏了他本人的此种审美倾向。这种观点很可能承于持复古主张的云间派,陈子龙《佩月堂诗稿序》有云:“盖词非意则无所动荡而盼倩不生;意非词则无所附丽而姿制不立。……故二者不可偏至也。”[11]这便着重强调了文质兼备的重要性。而蔡仲光现存的124首乐府诗,其中不乏《短歌行》《于阗采花》《将进酒》《会吟行》等既有内容又不乏炼字的作品,毛奇龄之推崇实非无据,蔡仲光的这种自觉创作,当也受到了复古思想的陶染。
复古思想影响的印痕,在诗歌主张上表现为宗唐、崇汉魏、尚六朝三点。其一,毛奇龄《何生洛仙北游集序》云:“人能为唐诗而后可以为宋元之诗,如衣冠然……顾能为唐诗者,必不为宋元之诗,如琴瑟然。搏拊咏叹,已通神明,而欲偶降为街衢巷陌之音,以为娱乐,则流汗被地。而世人不知,则以为弦匏无异声、钟釜无异鸣而已。”[4]754言内外无不宗唐而抑宋。在《毛大千诗序》中,蔡仲光也将拟议三唐,取法陈子昂、杜甫等人的毛万龄诗视为“正”,承认唐诗一脉的主流地位[3]293。宗唐主张在萧山一带是被普遍接受的,毛奇龄“吾乡为诗者不数家,特地僻而风略,时习沿染,皆所不及。故其为诗者皆一以三唐为断。而一入长安,反惊心于时之所为宋元诗者”[4]754语,即可证此情形。其二,毛奇龄重五古,推扬蔡仲光乐府,蔡仲光本人多有上佳的乐府作品,都是承继汉魏之风的体现,屈大均读罢蔡仲光作品感叹褒扬道:“仲光乃汉魏间人也!”[3]154汉魏诗风颇得奉重。其三,屈大均《怀浙东毛君》有“萧山才子推毛蔡,可惜风流出处分……宫体只今谁绝艳,六朝人在定怜君”[2]681语,对毛奇龄在宫体诗方面的造诣作了高度肯定,六朝宫体是毛奇龄着力经营的诗体之一;蔡仲光评萧山徐芳声《寿王自牧》文时,则有“徽兄文大约铸六朝之俊丽,句琢字炼”[3]406语,六朝之风在其眼中亦属褒词。“正因为特别重视诗歌的文采,陈子龙等便非常推崇以文采斐然见长的六朝诗文,这是复古运动第三次高潮的一个重要特点”[12]388,毛奇龄、蔡仲光的以上倾向,和引领明末复古风潮的陈子龙若合符契。
毛奇龄与陈子龙联系密切,陈子龙任绍兴府推官时曾评毛奇龄文为“才子之文”。已有研究者探明,毛奇龄的创作主张受到陈子龙的直接影响,蒋寅先生即在《清初钱塘诗人和毛奇龄的诗学倾向》一文中作出了毛奇龄“少好宋元人诗,继而步趋竟陵,追摹后七子,到最终皈依于云间派麾下,他的诗学经历了一个由喜好宋元转向宗尚唐人的过程,其中决定性的影响来自云间派”[9]162的判断。实际上,不止毛奇龄,西泠十子乃至包括萧山文人在内的杭绍地区文人都受到了明代第三次复古运动高潮的强烈波及,这种波及主要又是来自云间派、陈子龙[12]366,392。
最后,再来关注材料中毛奇龄原欲为古诗,而迫于时人皆作近体,不得不转向近体诗创作一事,这其实是全国推崇宋诗风气在萧山产生一定影响的反映。即使萧山诗坛宗唐的文学壁垒甚坚,也无法做到与外部环境完全隔绝。蔡仲光所谓“宋元间人每选唐人绝句、唐人三体诗、唐律诗、杜律诗,并无古体”[3]418语,其实也侧面告诉我们,在唐人之外,宋元人在诗歌领域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与浙西一江之隔的浙东,此时在黄宗羲、吕留良和吴之振的倡导下,正高举宋诗大旗,不可能不对萧山产生影响。萧山位于钱塘江南岸,处于浙西与浙东的交汇处,同时受到了两地风气的熏染。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蒋寅先生所说,“谈到钱塘诗人的诗学,不能不提到毛奇龄,他虽不列名于西泠十子中,但与毛际可、毛先舒并称‘浙中三毛’,论诗倾向也与钱塘诗人一致”[9]162,以毛奇龄为代表的萧山诗坛,其诗歌宗尚还是与浙西更为接近。方象瑛《柴虎臣先生传》论柴绍炳诗及杭州诗风时曾说:“其诗一洗俗陋,气格声律以汉魏三唐为宗,当时效之,号西陵体。至今杭人言诗,无阑入宋元者。近虽稍稍习为宋诗,然操唐音者十之七八,流风余韵固尚在也。”[13]将此移为萧山诗坛风气之评,也大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