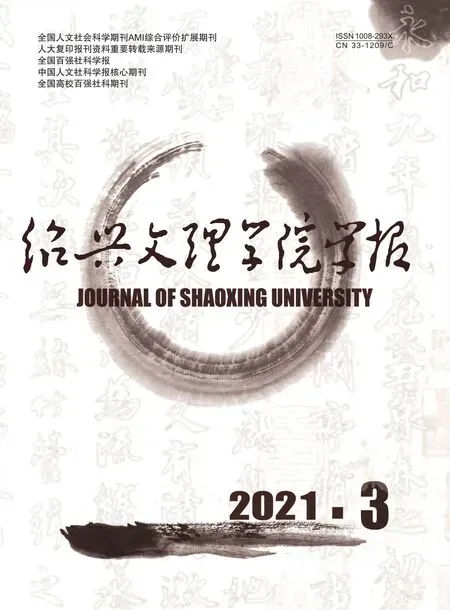晚唐敦煌文化中的江南元素及越州文士的贡献
杨宝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安史之乱爆发,原驻守于西北地区的部分唐军精锐被调往中原,边备顿显空虚。吐蕃趁机大举东进,蚕食鲸吞河陇等地。敦煌虽是河西地区陷蕃最晚的一州,却也在长达六七十年的时间里沦为吐蕃占领区。吐蕃统治者在这里强制推行了一系列吐蕃化措施,使自西汉建郡后即代代相传的敦煌汉文化遭到了异常严重的破坏。直到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汉族豪杰张议潮趁吐蕃内乱之机,率领敦煌民众推翻吐蕃统治。但受当时控制着河西东部等地的吐蕃阻隔,奉土归唐的张议潮与唐廷取得正式联系已迟至大中五年(851);是年,唐廷在敦煌设立归义军并任命张议潮为首任节度使,此后直至唐朝灭亡,敦煌均由张氏管理,此即敦煌的晚唐时期。
晚唐是敦煌历史上非常特殊且重要的时段,不但在政治、经济方面具有拨乱反正的转折意义,社会文化方面更承担了重建与复兴汉文化的历史使命。通过对现存晚唐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特别是敦煌文书等的剖析,可知晚唐敦煌文化的大致情形,而近年学界方才注意到晚唐敦煌文化与其他历史时期迥异的一大特色,即:晚唐敦煌文化中存在着一些相当明显的江南元素。这一现象实在令人寻味:在与中原内地阻隔了近百年之后的特殊时期,江南元素为什么会呈现于遥远的西北?晚唐时期的敦煌与江南缘何发生了如此紧密的联系?学界的相关研究应做出怎样的响应与调整?
本文即拟在列举介绍晚唐敦煌文化中江南元素的基础上,通过对江南元素传入缘由,尤其是对具体传播者所处时空背景、个人经历与才学贡献等方面的分析,尝试探讨上述问题。
一、晚唐敦煌文化中的江南元素
关于晚唐敦煌文化中的江南元素,以前学界鲜有关注,但近年的研究表明,此类例证颇多,且随着研究逐步深入,还在不断增加。以下试分类举例说明。
其一,某些创作于晚唐时期敦煌地区的文学作品系以江南人的口吻写成。如,英藏敦煌文书S.5644v《方角书一首》的前两句为“江南远客跧,翘思未得还”,末两句为“訄逼那堪说,鲸灭静阳关”[1]250,显然,该诗作者是一位不得已滞留于敦煌而思念江南故乡的文士。参酌该卷正面《净名经关中释抄》成书与传入敦煌的时间分别为中唐和晚唐、《方角书一首》抄写者——怀庆为晚唐敦煌本地人等资料,可将该诗的创作与抄写时间推定为晚唐时期[2]。再如,由多件英藏和法藏敦煌文书(S.6161A+S.3329+S.11564+S.6161B+S.6973+P.2762)拼合而成的《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抄本之卷背所存19首诗(以下简称“《张淮深碑》抄件卷背诗”)的作者亦自称为江南人,如其中《皈(?)夜于灯下感梦》一诗中有言“可□江南子,因循北海头”[3]122,作者自称“江南子”;名为《又》的第十一首诗末两句为“从此便应皈省闼,失途江客与格(?)携”[4]111,[5]45,作者自称“江客”,这些称谓与《方角书一首》的“江南远客”韵味有别却内涵相合,而这些诗的写作时间,据同卷同作者《“夫”字为首尾》一诗中“当今圣主回銮驾,逆贼黄巢已就诛”[3]121等语,亦可确定为晚唐时期[6]。
其二,某些可映射当时敦煌语音的著述中有不少南方语音的印迹,表明作者应为江南人。如,分类收集敦煌等地民间常用词汇的注音小词典《俗务要名林》(P.5001、P.5579、S.617、P.2609)即是典型例证。于此,敦煌语言文字研究专家黄征先生等多有论述,其中陈璟慧《敦煌写本〈俗务要名林〉研究》的表述颇为清晰:“虽不可确知其编者的姓氏,但我们仍可从卷中记载的语言、注文中窥见编者的一些情况。如‘工匠部’的‘界,锯木,音介’,‘界’作此音此义,今吴语存之。又如‘谷部’的‘籼’读若似,今吴语亦存之。卷中记录南方音者多处。又有‘饮食部’之‘糫饼’条,其注谓:‘寒具也,北人作之,上音还’;‘火部’之‘爇’条,注谓:‘北人呼燃也,而杜反。’北人云云,可说明编者确系南人。”[7]6
其三,一些敦煌文书中出现了主要流传于江南的典实,还有一些文书记述的是江南史事。如,全赖敦煌文书才得以流传的非常著名的五言组诗《敦煌廿咏》中的第七首《水精堂咏》(P.2748v、P.3929、S.6167v、P.3870)中“可则弃胡塞,终归还帝乡”[3]68所言乃是淮南裨将谭可则于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被吐蕃俘虏,至唐敬宗宝历二年(826)方逃归长安一事。此事在唐代流传并不广,史籍中也鲜有记述,以致曾有多位研究《敦煌廿咏》的学者都因不知其事而误将这组诗的创作时间推论为吐蕃占领敦煌之前,唯独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据此典故及P.3870卷末题记“咸通十二年十一月廿日学生刘文端写记。读书索文□”[8]41,十分准确地“把《敦煌廿咏》的写作年代推定在大中二年到咸通十二年这二十四年间”[9]236。关于谭可则事迹的最翔实可靠的记述出自唐人赵璘《因话录》卷四,谓:“元和十五年,淮南裨将谭可则,因防边为吐蕃所掠。……凡在蕃六年,及归,诣阙自陈,敕付神策军前驰(1)原书注:“驰误,应作驱。”使。未及进用,为军中沙汰,因配在浙东,止得散将而已,竟无官。开成四年,余于越州遇之,见其步履不快,云于蕃中走时冻损足。”[10]96-97是知谭可则逃归后很快即被遣往浙东,至唐文宗开成四年(839)犹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其经历遂在当地流传。《敦煌廿咏》的作者能十分贴切地将谭可则写入诗中,自当是熟悉越州时事之人[11]。再如,法藏敦煌文书P.3303v抄存了有关东传中国的印度制糖技法的最早最详尽记述,其内容涵括以下几个方面:(1)印度所产甘蔗的种类与各品类的特性功用;(2)熬制沙糖的具体方法;(3)制作煞割令(石蜜)的具体方法;(4)甘蔗的形貌(以沙州高昌糜子作比)及种植方法。众所周知,甘蔗的生长需要大量的水,干燥少雨的西陲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皆不适于种植甘蔗,自然也不是蔗糖生产加工地,无论古今,甘蔗都主要种植于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且唐代时传入中国的印度制糖法也主要应用于江南地区,记载此事最详的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四《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即谓印度石蜜匠到唐朝后,唐太宗很快就敕令他们“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12]120,遣送他们去越州的原因是越州等地盛产甘蔗,有利于就近制糖,而印度石蜜匠到达后,天竺甘蔗和蔗糖制作技艺自然也就为越州人所熟知[13]。
其四,晚唐时期的敦煌出现了江南地区盛行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如传道授业类型的寺学。以前学界利用敦煌文书中保留的大量学郎题记,已考出晚唐时期的敦煌地区曾建有多所以启迪童蒙为教学目的的寺学,近年又发现当时该地还存在着以向青年学子传道授业为主旨的寺学。英藏敦煌文书S.5448《敦煌录》记:“郡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木阴森,中有小堡,上设廊殿,具体而微。先有沙倅张球,已迈从心,寓止于此。虽非博学,亦甚苦心。盖经乱年多,习业人少,遂集后进,以阐大猷。天不慭遗,民受其赐。”[14]94-95文中明确记载了该寺学的兴办目的是“以阐大猷”,即传授治国理政大道,而非培训童蒙。再结合该寺学所用教材,尤其是执教者张球的经历、抱负等,更可确知该寺学非属蒙学[15]。然而,根据前辈学者严耕望、张弓先生等的权威研究,传道授业这一类型的寺学原本主要流行于中原特别是江南地区。如张弓先生即曾遍查传世文献,在其名著《汉唐佛寺文化史》之《辅世篇·寺学》中将盛行这一类型寺学的地区归纳为“三吴·两浙”“庐浔·楚衡·荆襄”“沂兖·淮扬”“罗浮·蜀中·闽莆”“终南·京畿”“嵩山·都畿”“中条山”等七大区[16],其地无陇右河西而以江南居多。
相关的例证还有,限于篇幅,此不赘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上所举例证大多为近几年才从地域文化研究角度揭出,牵涉的问题相当多,却皆使晚唐敦煌文化中的江南元素凸显了出来,那么这些江南元素是如何进入敦煌的呢?
二、江南元素传入敦煌的缘由及越州文士的贡献
上举各例证有一共同特点:这些江南元素的带入者既饱受江南与中原文化熏陶,又十分熟悉敦煌及其周边地区情况。显然,在敦煌与江南之间架起桥梁的文化使者在两地都曾长期生活过。
可是,以往学者在敦煌与外界往来顺畅的各历史时期都没有找到有姓名可考的外来人在敦煌长期居留,或敦煌人在江南生活后又返归敦煌的证据,难道至刚刚经历了长期封闭的晚唐竟会出现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吗?要知道,自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至851年归义军建立的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敦煌与中原之间的交往尚且严重受阻,遑论江南,并且,不仅在此期间敦煌与中原、江南几无人员往来,就是敦煌已经归唐的张氏归义军初期,中原与江南文士也鲜至敦煌——近百年阻隔已使中原特别是江南人士更容易视边陲敦煌为异域绝地,不会随意前往,更别说永久定居了。就总体大势而言,情况确实如此,因而晚唐敦煌文化中的诸多江南元素以前并未引起相关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甚至被误置于其他时期,如前揭《方角书一首》的作者即曾被怀疑是唐前期西来的无名戍卒。
不过,非常时期确有可能出现非常之人与非常之事。以下试简要论证。
(一)晚唐时曾有来自越州的江南文士在敦煌长期居留
英藏敦煌文书S.2059《〈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以下简称“S.2059《序》”)为一件抄经序,作者开篇即自称:“□□□(越)州山阴县人张俅……”[17]608
文中的州名虽残,但很容易补出。考我国古籍中记载的山阴县凡两指(2)旧本《旧唐书》卷193《列女传》“邹待征妻薄氏”条记“待征,大历中为常州山阴县尉”(《太平御览》卷440所记略同),似乎除下文所述两处外,常州还有一个山阴县,其实该处的“山阴”为“江阴”之误,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中已有说明,详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48、5152页。:一处地属今浙江绍兴,秦时始设,因处会稽山之北而得名,为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东汉时为会稽郡首县,隋代废入会稽县,唐复置,并为越州首县,南宋和明清时为绍兴府首县;另一处的故城在今山西省山阴县西南,系金时改辽的河阴县而成,后又升为忠州,元时并入金城,后复置,明清时皆属山西大同府。S.2059《序》作于晚唐,故文中的山阴县非越州山阴莫属。
至于“张俅”一名,除该卷外,在法藏敦煌文书P.2568《南阳张延绶别传》等中也曾出现过,另外,在其他敦煌文书或敦煌古碑铭中还常见到“张景俅”“张景球”“张球”等署名方式,学界早已考出这四个名字指代的是同一人,因“张球”一名的出现频率最高,故一般情况下以“张球”称之。为避免混乱,本文行文亦如是,但直接引录敦煌文书或敦煌古碑铭时则遵从原文用字。张球是敦煌学者一般都会有所知闻的著名人物,因为敦煌文书和敦煌古碑铭中留存有大量他撰写的作品,仅署名作品就有20来件,据之可知他是活跃于晚唐时期敦煌地区的政坛高官与著名文人。只不过以前学界因未研及S.2059《序》而不知道他来自越州,一直误认为他是敦煌本地人,S.2059《序》的揭出[18]为学界带来了他出生于江南越州的明确无误的证据。
其实,张球不仅出生于浙江东道的越州,亦成长于会稽地区,对该地非常熟悉。近年笔者已从前文提到的《张淮深碑》抄件卷背诗中,发掘出了一些有关张球早年在越州生活情况的记述[19],如据其中追忆年少时故乡风物的“镜湖莲沼何时摘”[3]121等诗句可推考出张球曾居于镜湖附近。
据S.2059《序》及自咸通初年至五代初期张球撰写的众多作品可知,张球成年后曾游历灵武等地,于张议潮奉土归唐后来到河西,然后一直任职和生活于敦煌,长期在归义军政权中担任要职,参与过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位高权重,官至节度判官掌书记(3)例如,在今藏敦煌市博物馆的《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中,张球即署“节度判官权掌书记朝议郎兼御史中丞赐绯鱼袋南阳张景俅撰”。又如,在P.2913v《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南阳张府君墓志铭》中,张球的题署为“节度掌书记兼御史中丞柱国赐绯鱼袋张景球撰”。,总揽藩镇文辞之责,可参与甚至影响枢要之事。致仕后,张球又在敦煌兴学授徒,奉佛抄经。他相当长寿,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BD10902(L1031)《金刚经》后题记“辛未年(911)七月廿日,八十八老人手写流通”[20]220等可知,张球出生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至少活到了88岁[21],亦即在敦煌生活了半个世纪,依常理,他当是终老于敦煌。张球一生交游广阔,兴趣广泛,故对久居之地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的人与事也非常关注和了解。
(二)越州人张球将江南文化传入晚唐时期的敦煌
上文的概略介绍已勾勒出了张球生平的大致轮廓,证明晚唐时确有一位越州文人远赴敦煌任职并定居。应予特别说明的是,张球是今知唯一一位曾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长期居留并于此地创作了大量作品的外来人。揆诸其经历、抱负、才智,及张氏归义军时期的诸般敦煌史事,本文第一部分所举例证皆可一一得到合理解释:前文所举那些以江南人口吻写成的文学作品正是出自张球之手,这一时段的敦煌文书中出现的南方语音乃是张球故乡的吴越方音,文书中引用或记述的江南典实史事是张球年轻时在家乡亲耳所闻与亲眼所见,传道授业类型寺学在敦煌的兴办正是张球晚年于异地他乡模仿故里前贤往哲的结果……总而言之,前文所举晚唐敦煌文化中的江南元素正是由越州人张球带入。
根据敦煌文书中存留的数量相当可观的张球作品可知,张球乃是一位能文之士,这应当是他能将江南文化注入敦煌的根本原因之一。张球一生勤于和长于撰述,且创作期格外长,9世纪下半叶尤其活跃。就藏经洞所存撰作于敦煌本地的文书而言,张球是留存著述最多的作者,除上面已提到过的20来种署名作品外,今从已佚失作者姓名的敦煌文书中新查考出的他的作品更多,仅目前笔者已考证出或掌握了查考线索的即有数十种。另外,张球改编的他人作品和编集的时人文集也不少,关于前者的典型例证即是张球曾将唐人李若立所编类书《籯金》删改为《略出籯金》(P.2537)。张球的作品不仅数量多,涉及的领域也相当广,宗教、民俗、科技、语言、文学、历史等等,时有关联,可以映射其所居或所经之地的多方面风貌状况,研究价值非常高。仅以后两类为例,敦煌文书中保留的张球撰作的诗、文、传、赞等文学作品题材广泛,用典颇多,寓意深邃,并且这些作品均仅存于敦煌文书而不见于传世文献,是对晚唐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补充,至于其作品的史料价值则更是无法估量。张球曾参与过敦煌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了张氏归义军兴盛衰败的全过程,他以江南文人的特殊视角洞悉透视权力场中的人与事,其作品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归义军政治史中的一些重要信息,为学者追寻当时的某些重大事件,尤其是各政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提供了宝贵线索。透过他的曲笔直书,可以辨析当日敦煌史事的许多细节隐秘与根源、影响,极有益于对晚唐及五代初期的敦煌地区史的解读与深入研究。因而,张球作品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可以从多角度多侧面进行深入剖析与研究。本文仅聚焦于相关文书透露的晚唐敦煌文化中的江南元素,据以追根溯源,觅寻其传入者与来源地,从而锁定了越州山阴人张球。
张球西来,正值敦煌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这位儒释兼通、学养深厚的越州文士遂因应时势所需,成为了将中原与江南文化传播至曾长期与外界隔绝的敦煌的重要使者。
越州位于唐朝东境,紧邻大海,敦煌偏处西部边陲,被沙漠戈壁包围,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尤其是动荡离乱的晚唐,两地之间原本遥不可及,但却因张球西来而交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士成就了一段特殊而重要的文化交流佳话,这自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研究讯息,足以给我们多方面的启迪。以目前各界均分外重视的丝路研究为例,它提示我们于相关专项与专题研究已各有所获的当下,或可拓宽研究视角,细化研究论题,更深入细致地探寻丝绸之路的分支路径与作用、影响,展开或加强诸如各历史时期各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与文化交融和敦煌等丝路重要节点地区的文化来源、组成与发展演变,以及唐五代时期江南文化的传播方式与代表人物等相关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