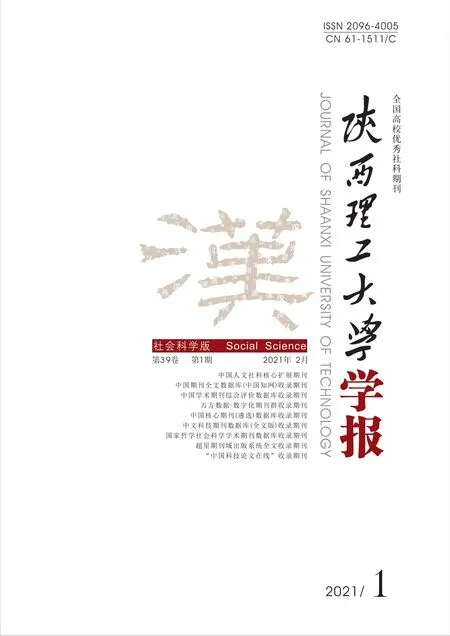论《水葬》的自然书写
冯 玉 文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王蓬《水葬》中的自然世界不但供给人们生存所需的必要物质,还令人们在其中学习、感受、淬炼、领悟、提升,更处处展示出自然与人的息息相通,以及自然对人生活和生命的介入、引领,自然往往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灵魂导师。如果把20世纪90年代起王蓬运笔于石门栈道、蜀道、丝绸之路看作是一次作家向学者的“位移”[1]94,那么,这次“位移”中始终坚定不移的成分即是王蓬对自然世界的倾情书写。王蓬不愧是“追慕自然美的山野作家”[1]41,《水葬》中,王蓬既描绘自然景物,又塑造自然人物,更弘扬自然神性。
一、 自然景:《水葬》的场域
王蓬《水葬》中的自然景色描写触目皆是,不仅仅是对文本人物、情节等起到烘托渲染的作用,以其强烈的象征暗示等功能使故事呈现出意蕴深远的诗化美,更预设和推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自然景色也由此成为《水葬》的场域。
早有学者关注王蓬的自然景色书写。作家王汶石在致王蓬的信中对此有非常中肯且比较全面的评价:王蓬是“以雄浑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秦岭的大自然景色,那茂密的原始森林,那直耸云天的山峰,那深不可测的峡谷,那神秘莫测的山峰雾气,那挂在陡峭山坡上的巴掌大的田块,那孤零零的守号人的窝棚,那林中的阳光,那皎洁的月亮,那风声,雨声,狼嗥,犬吠声,那三五人家的茅舍,鸡群,白色的炊烟,和那无边无垠的绿色,青色。”并且王蓬的“景色描写是很漂亮的,有层次,有深度,绚丽多彩,幻化无穷,既是油画,又是水墨画,表现出了秦岭的雄伟,姿色和魅力”[1]32。著名文学评论家王愚认为:“王蓬的作品,在揭示人物感情世界的起伏变化时,总少不了关于农村自然风光的描绘,而这种描绘渗透着人物的感情,衬托着人物的感情,和人物的思绪交融在一起,使他的作品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1]67两位学者的确都抓住了王蓬景色描写的实质特征。此外不能忽略的是:王蓬的自然景物描写蕴含着象征暗示等特征,这使景物描写超越了烘托渲染等基本功能,而成为故事演进的重要推动力量。正如《水葬》第一章开篇就有景物描写:“初秋,一个空气沉闷、烦躁不安的黄昏。太阳还没下山,就被大团密集的乌云吞没。一阵强劲的下山风扑来,古栈河道腾起云头般的烟尘,草屑败叶刮上天空,公鸡惊鸣着飞上屋顶,群狗翘着尾巴在镇街乱吠。风助云威,云趁风势,气势汹汹铺展开去,转瞬天昏地暗,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雨腥味、血腥味和辛辣的苦艾蒿味。”[2]4这样的景色与一场残酷血腥的杀戮极其相衬,同时,作品人物和读者都被置于不安恐怖的氛围中。作者也以此暗示即将展开的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不平凡故事。而乌云蔽日、鸡犬不宁这一时一地的自然景色,又象征着一个暗无天日、毫无秩序可言的乱世:在这样不可理喻的世界里,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出乎意料的事情。小说刚一开始便悬念骤起,令读者紧张又充满期待。
文中还以自然景物来推进人物关系的发展,从而使人物关系的变化显得从容自然。比如少女翠翠和少年何一鸣猎鹿的自然景物描写:“河滩笼罩着乳白色的晨雾,起伏的山峦在雾霭中若隐若现,四下里一片寂静,唯独从丛林深处淌出的一条溪流潺潺作响”[2]9,暗示情窦初开的翠翠和何一鸣朦胧纯净的感情。两个人又“看到的是一公一母两只鹿……并排踱到溪水边喝水……他们喝着清澈的溪水,不时扬起脑瓜,互相舔着嘴唇,那只公鹿后来又动情的嗅闻起母鹿的尾部”[2]17。此处,少男少女两个人与雌雄两匹鹿,相映成画,相较成诗。成年后的翠翠和任义成彼此喜欢,但是任义成一直为自己的道义伦理束缚,两个人的情感也一直没有大幅度进展。当一起上山采板栗时,任义成看到的景色是:“一株株碗口粗细,躯干挺拔,枝杈分开,叶片绿中染黄,一簇簇裹着板栗的刺球挂满枝头,随着一阵阵秋风扫过,刺壳炸裂,那颗粒饱满、色泽鲜润的板栗便如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孩子蹦跳出来,落在地上。”[2]71板栗成熟象征着两个人的感情也渐趋成熟;暗示收获板栗的同时,也将收获爱情。果然,任义成坚守的道德法则开始动摇,两个人的关系很快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水葬》自然景物的四季更迭也和主人公的命运起伏相应和。何一鸣被迫害独居野外的小土地庙时,因为居所“海拔较低,地形开阔,能及早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先是向阳山坡出现淡淡的鹅黄,阳光有了热力,照在水汽氤氲的山坡,峭拔的山崖开出几只妖娆的山桃花;接着漫山遍野的野花争相开放,二月兰、白头翁、紫叶苏、野蔷薇……最后是杜鹃,也叫映山红,整个河谷无处不有,映得山也红了,水也红了。”[2]313这一派姹紫嫣红、朝气蓬勃的春景,暗示何一鸣落魄的生活将有所改变。自然界有春夏秋冬的轮回,同样,人类的生命和生存都如同自然界一样,经历了严冬的考验,必然迎来春暖花开。在这里,自然与人成为世界上并行的具有同构意味的生命体。由此,“自然在作家笔下不再仅仅是作为渲染气氛、烘托情绪、暗示背景、反衬人物品格、折射人物心境以及借以抒情咏志的道具而被描写,它已经作为一种‘人化的自然’而具有了存在价值、精神、灵魂、生命意义和美学意义。”[3]
在自然景物描写上,诚然如李青石所说:“王蓬的环境意识首先表现在对祖国秀美山川的赞美……描绘了祖国各地山川的美好,歌颂了造物主神奇的造化,以期唤醒人们热爱美好、热爱大自然的意识。王蓬把他的环境意识自然的融入描绘大自然的笔墨中。”[1]169-170此外,更不能否认王蓬长期与大自然朝夕相处的日久生情。那些因“久在樊笼里”偶尔走出都市乐享自然景色的人们,会因为新奇而获得赏玩的乐趣;但王蓬是在自然中长养、磨砺了18年[1]337-338,对自然居然没有审美疲劳后的漠视,可见是因为谙熟而热爱。此外,王蓬对自然的热爱肯定有天性的因素,俄国文学中盛行以对待自然的态度来衡量人的品格,认为亲近自然和土地的人才会有善良质朴的心,如雅各武莱夫的《农夫》就展示农夫对敌人的大爱。至于落笔成文,更显现出王蓬对色彩、光影、层次、线条、声音等绘画和音乐技法的把握,而动静结合,景随心移,心随景动则使作品既充满了生活实感,给读者现场感,又有无穷的想象空间。总体看,王蓬《水葬》中具有象征暗示功能的自然书写,使自然景物与作者,与作品中人物,甚至是与读者的精神都息息相通。由此,自然景物成为了情节发展、人物情感和作家创作心理动因的具象呈现,为作品增添了有声有色又意蕴深远的魅力。
二、 自然人:《水葬》的灵魂
文明社会的喧嚣浮躁、尔虞我诈,使对现世失望乃至绝望的人们不断探寻解脱到彼岸世界的法门。人们早就认识到:人类源于自然,最终归于自然,所以《红楼梦》中有“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4]876之论,也就是说,无论生命历程惨淡或辉煌,最终总会归于尘土。由此,自然就成为人们浮生梦醒后向往的乐园:自然能够让人性得到自由舒展,情感得以尽情抒发,生命价值也得到体现。回归自然成为人们的企望:不只是身体“复得返自然”,更是心灵向自然的皈依,也就是由被驯化的社会人变成具有野生动物特征的自然人。
聂震宁说王蓬笔下的“秦岭与秦岭深处的女子是一致的色彩斑斓、温柔敦厚;他的汉水与汉水边的女子是一致的舒缓明净,催红生绿”[1]80,的确,王蓬《水葬》的主人公,尤其是女性,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大多带有自然界生灵的特征,这使人物们表现出与自然山水浑然一体的美丽而野性,蛮荒又灵动。《水葬》中“人与自然的一体性,正是王蓬逐渐达到的文学境界”[1]81。这些“与自然一体”的人们,是《水葬》的灵魂。
《水葬》着力塑造的女子不但与自然山水一致,少有文明教化的痕迹,自然而然地成长、自在自为地生活,而且具有自然界动物才拥有的“野性”:首先是“这里的女子,见着陌路生客,并不回避,问路搭话,落落大方。”[2]29还有“流浪生涯中长大的翠翠到将军驿时,才十一二岁,扎两条羊角小辫,穿着母亲改小的衣裳,脸庞带黑,眼神机警,简直像只野山羊,顽皮英勇,充满野性。”[2]79更有长成大姑娘的丫头“肤色黧黑,野性十足,没进过学堂,没经过人事,但与山林、鸡猪之类打交道,有股泼辣的劲儿,并不知羞怯。”[2]149可见,作者赞美的是女性的自然动物性,也就是未经人世熏染的自然性。小说还写到任义成想捉住翠翠的手一节:“但刚伸出手,翠翠已像小牝鹿般蹦开了,笑嘻嘻地顽皮地站在他面前。”[2]73又谈到翠翠的女儿小凤“眼睛黑亮亮的,恰如崖上滴下的泉水,无一丝杂染,无一丝纤尘,水汪汪清澈;脸庞像枝带露的栀子花,嫩白娇艳;小嘴巴翘翘的,犹如小山雀嘴一般灵巧……”[2]236无论是“野山羊”的幼年翠翠还是“小牝鹿”的少女翠翠,一成不变的是都具有与自然界动物一样的“野性”;而翠翠的女儿小凤更是自然的精灵,无论是“泉水”“栀子花”还是“小山雀”,无一不来自自然。自然野性是王蓬对女子的最高褒奖,反面形象的女子如蓝金娥则无此殊荣。正如鲁迅所说:“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蛮野如蕾,文明如实”[5]78,想获得文明的果实,就必须从未经人类污染的自然中寻找“蛮野”的花蕾,而将花蕾比拟为年轻女性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
《水葬》男女两性的爱意生成也是以自然、野性作为标尺。蓝明堂第一次看到翠翠就被深深吸引,乃至神魂颠倒,就是因为翠翠“眸子水汪汪的有神,脸庞桃花一般粉嫩,抬头看他,毫无羞怯,天然带股野性”[2]47。何一鸣与翠翠少年时互生好感,但是翠翠屈就于麻二,何一鸣又远走他乡求学,两人天各一方,在学校“何一鸣也曾因新鲜对女生关注,后来就不由自主拿她们与翠翠相比,这一比就看出毛病,她们或太矜持或太扭捏或太一本正经,怎么也没法和鲜活自然又带野性的翠翠相比”[2]228。反过来,女人看男人同样以“自然”“野性”作为审美标准:翠翠的母亲对何镇长的觊觎心知肚明——何镇长“目光表现出欣赏和赞许,但是又很隐蔽……母亲读懂了那隐藏在目光中的东西。她讨厌这种竭力掩饰的目光,远不如乡野男人们那饿狼般的贪婪劲儿来得痛快”[2]82。可见,在相爱对象的选择上,无论男女,标准统一,都展现出对自然、野性的呼唤。
甚至人物的日常生活也没有文明社会正常人类应有的规划和规则,而是具有动物自然生存的特征。任义成“虽讲成了家,但多年流浪惯了,不积不攒不存不余”;妻子桂桂“不懂得治家理财、用度过日”;他们的“四个小子整日野马一般,光着脊梁在河滩摸鱼捉蟹,浑身晒得黝黑。冬天落雪日棉袄穿不上身,几个孩子都冻得嘴脸乌青,青鼻泡长流,却从不生病,就是能吃”[2]189。这整个家庭都给人缺少人间烟火的感觉。对待婚姻之外的性关系,也少有人世间法则道德的规范:“山区男女在这方面并不计较。男人外出也常和别家女人寻欢作乐。回家真碰上自己女人与野汉子欢娱,倒会寻个借口走开,绝不为此撕破脸面,颇有种超然物外的大家风范。”[2]133这不只是超然物外,是已经完全超然于人世之外了。
《水葬》中,不但人类拥有动物性,而且在人与动物的对比中,凸显了动物的优势,善良的人与动物更达到了物我无间的境地。经历了世态炎凉、人心不古的翠翠认为:“尽管女人家放牛,上高爬低,夜间添草并不轻松,但能避开众人,省却口舌是非。这年月,宁与畜生打交道,不敢和人多往来。”[2]254而何一鸣在收养了小熊后,“抚摸那黑黝黝的毛皮,晃来晃去的小脑瓜,从未做过父亲的何一鸣突然冒出个念头,像给儿子取名字一样把它叫黑子。不知不觉间何一鸣的生活起了变化,多了一种牵挂,一种思念。”[2]312这里展示的是作为社会人的艰难和回归自然后获得的慰藉与安宁。沈从文说:“对于一切自然景物的素朴,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彼此生命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6]120。而王蓬本身就是“秦岭汉水的赤子”和“自然的精灵”[1]80,所以他能够和沈从文一样,将人类自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懂得尊重、爱戴自然中的一切,也就能领会人与自然的共生和共存。
人类历史中,当人们无法在残酷的现实中立足时,人性就常常会趋向原始自然的动物形态,这是现实中的虚无感、漂浮感造成的。无论是佛教的“轮回”还是基督教的“宿命”,也无论是西天圣境还是天堂乐园,都是人们拟想的灵魂皈依之所。《水葬》人物中动物性的凸显,是因为“人性的要求成了判断人的思想行为的最基本依据,人的思想行为已经不再依照某种固定不变的伦理规定进行判断,而是依照是否符合人性的需要来判断……”[7]79王蓬《水葬》的自然性人物就是如此。并不是作家们真正想回归原始的动物形态和生存状态,只是面临人类文明崩塌的现实表现出的无所适从而已,也就是西方文学中艾略特的荒原感。作家们摆脱现实的努力表现为或回眸过去,或展望未来,二者共同点是都需要理清文化发展的脉络才能得偿夙愿。回归原始、寻源问道,目的不只是缓解现世的创痛,更在于重塑文明的期许。
三、 自然神:《水葬》的正气
王蓬说:“人类社会运转了几千年,自有其惩恶扬善的基本规律……”[2]338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当然是善良者的共同愿望。文明缺失的人世,充满了残忍和丑恶,尔虞我诈中常常是善者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善者不具备作恶的心理力量,又常常缺少反抗恶者的操作能力,更不可能和恶者同流合污,于是不能从苦海中自救,只能向外界求救。当现实的人类世界找不到救援力量的时候,就只能向精神世界求索:各种图腾崇拜和宗教由此诞生,自然神教也由此而来。“自然神教是一种崇拜和敬畏自然,奉自然为上帝,动物为神灵的古老宗教。”[8]王蓬并不信奉自然神教,但自然神教对自然和动物的敬畏和崇拜却正与王蓬《水葬》呈现的自然灵性相吻合:《水葬》中的自然景物、动物一度占据主场,成为“惩恶扬善”的审判者,成为迷途人类的灵魂向导。
《水葬》中波谲云诡的政治运动中,人心惶惶的各种乱象中,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情感纠葛中,自然神常常成为主宰。对于代表恶者一方的阴险狡诈的蓝明堂,自然给予他的是惩罚。他的妻儿惨死于自然界突发的洪水,他从此孑然一身、一无所有。“多年苦思冥想的东西,在多少个深夜安慰过他那颗悲凉孤寂的心,眼看如同快要蒸熟的馍馍,即将到吃到嘴的时候,仿佛上帝专门惩罚他似的,给他安排了这场家破人亡的灾难。他最初听到噩耗的一瞬,脊背上像被人猛砸了一拳,浑身一阵冰凉。一种强烈的失落和悲痛过后,心底里便猛然冒出了那奇怪的念头:莫非命运有意对他考验和捉弄?有一瞬间,连他自己也惶惑,依稀觉得这场灾难是对他心底那些罪恶念头的打击。只有想到这一层的时候,他才真正浑身瘫软,双眼发黑。”[2]204虽然已经感受到自然的审判,但蓝明堂又再次心生恶念,正当此时,“咔嚓!一声巨响,惊得他魂都飞掉,距他不远的一棵脸盆粗细的核桃树被雷电劈为两截,枝叶浓密的树冠像水田中的一束稻草被强劲的山风卷起来,又轻飘飘地扔在山坡”[2]205。这是自然神再次向恶人发出的警告。最后,蓝明堂两手空空、孤苦伶仃地离去,他的所有努力谋划都化为乌有。
对于善良正直的人们,大自然尽自己的所能给予现实的和精神的援助。何一鸣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生活逐渐走向落魄,真正改变何一鸣生活轨迹、扭转何一鸣悲观思想的,正是一只来自大自然的小熊,何一鸣为其取名黑子——这是自然神派来拯救何一鸣的使者。因为日间劳苦,夜间酣睡,何一鸣“梦见古栈河水猛涨,自己在水中挣扎,猛然惊醒,却是黑子正朝自己脸上撒尿,腥臭难闻。他一下跳起来,点燃松明火把,把小土地庙照得雪亮,看着凌乱不堪,如同狗窝兽穴的蜗居之地,大受刺激:未必我何一鸣真成了禽兽!”[2]313何一鸣就此振作起来,以致看到的景象都令他耳目一新。“彩霞艳丽,一轮红日跃上山岗,清楚地窥见往日破败的小土地庙,陡然显出人家过日子的模样时,竟然惊讶地躲进了云层,但又忍不住要看个究竟,豁然一跳,把万道金辉洒向巍峨大山,滔滔河水。天地间骤然一亮,山峦青翠,绿叶如洗,夜露晃如珍珠,云彩宛若轻纱。清风徐来,沁人肺腑。何一鸣简直有些傻眼,仿佛第一次看清山野的面目。他激动得鼻子发酸,心灵中隐隐感应到一种天地的召唤,一种从未察觉的力气在体内慢慢的凝聚,他只想对着起伏的群山痛快地猛喊一阵,来宣泄宛若波浪冲击抽打着心堤的感情的潮水……”[2]313
值得注意的是:心境的改变是因为环境的改变,而环境的改变是因为来自自然界的小熊随处便溺的动物性的刺激,这便强调了自然对人的决定作用、引导功能。至此,何一鸣的思想境界也得到极大程度的提升:“思路豁然开阔,不再受一种经典、一种主义和学说的束缚,而浩瀚宇宙,悠悠岁月,茫茫人寰,上下五千年地思索开去:欧洲中世纪禁欲主义的漫漫长夜,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黑奴制度,二次大战中血腥的虐犹……人类历史长河似乎总有许多灾难绝非个人意志力量可以逆转,而任何一点小小的清醒与成熟,也不知要以多少人的牺牲做代价!”[2]314把个人的荣辱置于世界、历史、全人类的坐标中进行考量,自然得出了令人豁达乐观的结论。站在现实的地狱的门口,感受的是切肤之痛;而如果将思想放眼远方,就会将个人的苦痛淡化。王蓬也有过和何一鸣同样的感受:田间劳作时,曾从蚂蚁“井然有序”“其乐陶陶”的生活突然被“贸然一脚”“毁于一旦”中获得启发,“在茫茫宇宙,人类不也渺小如同蚂蚁,若遇天崩地裂,洪荒瘟疫,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中国‘文革’的暴行,人不也如同蚂蚁般无奈!于是也就遇事洞达,随遇而安,遇着祸事也沉着稳定,心里有些底了。”[1]340这也就是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所讲:“作者的个性渗入书中主角的,也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因为作者大都需要与主角多少有点认同。”[9]4何一鸣这一人物形象,显然承载着王蓬现实生活中对于自然界的认知、对于人生命运的哲学思索。
来自自然界的小熊黑子给予何一鸣的不只是精神的导航,更有现实生活的巨大改观。黑子大闹将军驿之后,何一鸣和黑子的生存环境彻底改善——不但没人再敢打黑子的主意,而且对何一鸣也敬畏有加,“镇街男女感叹:‘也该让人家过两天伸展日子了!’”[2]322此后,何一鸣事业有成,和翠翠两个少年时代就开始互相爱慕的中年男女,历尽劫难后也终成眷属。
“人要维持自己功利性的世俗存在,心理平衡是一个先决条件”[10]62。任何一部作品,都或多或少维持着作家的心理平衡:作品是作家的白日梦,现实中无法实现又希望实现的都可以在作品中得以实现;作品又是作家的避难所,现实中无法治愈的精神创痛都可以在作品中得到平复和治疗。《水葬》中,自然神既是《水葬》这一白日梦实现的根基,也是《水葬》这一避难所奉献的饱含温情和抚慰的灵药,更是《水葬》人物、作者和读者的精神烛照。
综上所述,王蓬《水葬》的自然书写既有以人作为主体的自然景物描写,也有同为主体的人与自然同构,更有以自然为主体的自然神崇拜。沈从文曾感叹人类的“一部分生命,就完全消失在对于一些自然的皈依中。这种由复杂转简单的情感,很可能是一切生物在生命和谐时所同具的,且必然是比较高级文化所不能少的,人若保有这种情感时,即可产生伟大的宗教,或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艺术品”[6]120。《水葬》正是这样的艺术品。当然,《水葬》的自然书写还有悠远的回响:相对于个体生命的渺小和短暂,人类族群整体的发展伟大而恒久。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凝眸于历史尘埃落定的某个瞬间,人类会愧悔对自然界有意或无意的作恶:《水葬》埋葬的不只是将军驿和它的故事,更埋葬了辉煌的古栈道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水葬》不只是苦难民族发展的史诗,更是被毁灭的人类文明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