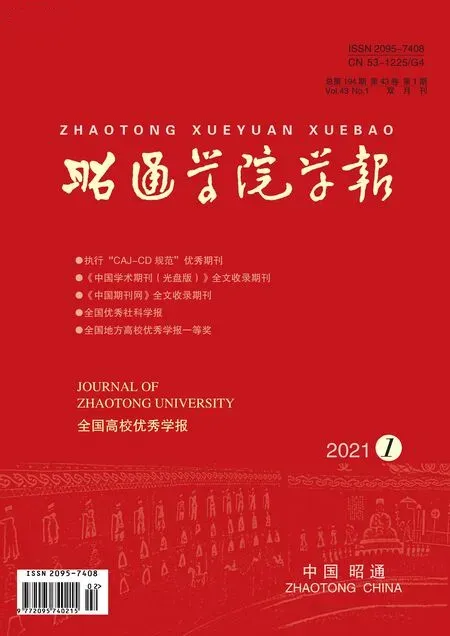死于幻想?或是死于清醒?
——论《蝴蝶君》伽里玛之死
周利均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蝴蝶君》(M.Butterfly)是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1957-)的代表作之一,其灵感一部分来源于一个真实的事件:法国外交官伯纳德·布希科(Bernard Boursicot)与一个中国京剧演员时佩璞(Shi Peipu)坠入爱河,并保持了近20年的恋爱关系,而后来证明这个女演员不仅是个间谍还是个男人[1]。另一部分来源于普契尼(Giacomo Puccini) 歌剧《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的故事情节。1988年,《蝴蝶君》首演于华盛顿特区国立剧院,而后在百老汇的尤金·奥尼尔剧院公演,获得巨大的成功,黄哲伦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托尼奖最佳戏剧奖的亚裔剧作家[2]。《时代》周刊称誉他为自阿瑟·米勒之后在美国的公众生活中第一个重要的剧作家。
伽里玛的死因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第一,东方主义话语批判[3]。第二,精神分析[4]。第三,女性主义[5]。第四,福柯的权力话语[6]。关于伽里玛的死因分析,都极具说服力。但笔者通过文本细读,注意到一些以往研究忽视的文本细节,因此本文将从东方主义话语理论出发,对伽里玛的死因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本文的研究基于以下三个疑问:第一,伽里玛说宋丽玲是一个完美的女人,剧中为何没有关于宋丽玲完美东方女性的身体、外貌描写?第二,为何伽里玛从不叫宋丽玲的名字,而只叫她“蝴蝶”?第三,为什么伽里玛没有在幻想破灭——宋丽玲脱下衣服,显示出男性特征的时候自杀?反而是在法国的监狱中表演了《蝴蝶夫人》之后自杀?因此笔者认为,伽里玛关于东方的幻想只是拉开了他死亡的序幕,清醒的认识到东西方将对方他者化不可为才是造成他生命落幕的根本原因。
一、“最完美的女人”——迷恋不存在的“蝴蝶”
作为一个男性,伽里玛显然在西方社会中的没有得到他所认为的“男性权力”——主宰女性,让女性为他倾倒。在伽里玛小时候,他被一致认为是个“最不可能被邀请去参加聚会的人”[7]4。长大以后的第一次性体验,也是女性主宰着一切,伽里玛呈现着一种“被强奸”的状态。而后,他的婚姻,也是出于“满足于在事业阶梯上的快速跃升”[7]16,而与比他年纪稍大的海尔佳结婚,因为她父亲是驻澳大利亚大使。但是,正如伽里玛所言,“我们,既不英俊,也不勇敢,又没什么权力,然而就像平克顿,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相信自己应该得到一只蝴蝶。”[7]10西方的男性总是幻想着继续平克顿与乔乔桑的“凄美爱情”,试图“捉住一只蝴蝶,用铁钉将它钉住。”[8]56
所以,当伽里玛在中国第一次看到舞台上宋丽玲着蝴蝶夫人装扮,表演着《蝴蝶夫人》中的殉情一幕时,就认为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蝴蝶”,“我要把她抱到我的怀里——她是多么柔弱,甚至,我都可以保护她,把她带回家,纵容她,娇惯她,直到她露出笑容。”[7]26此后,在宋丽玲的“精心布置”下,他们相爱,并且同居。伽里玛在这段关系中得到了莫大的满足感与幸福感,认为自己被“最完美的女人爱着”。然而,剧中为何没有关于这个 “完美的女人”的身体、外貌描写?
显而易见的是,伽里玛忽视了宋丽玲“活生生的身体”。罗兰·巴特曾在他的自传中说,我和你不同,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和你不同。”[9]3这是尼采哲学一个通俗而形象的说法。换言之,人的根本性差异铭写在身体之上。在尼采以前,人们总是将自身分成两个部分,分成意识和身体,而且意识总是人的决定要素,身体不过是意识和精神活动的一个令人烦恼的障碍。然而,从尼采开始,身体成为个人的决定性基础,人是身体的存在。[9]1因而,我通过身体认识我自己的世界,世界也通过那个我的统一身体而认识了我。
剧中对宋丽玲的直接身体描写少之又少,意味着宋丽玲的特殊性极其不明显,存在性也有待质疑。宋丽玲的身体是“不在场的”“消失的”,她的身体以三种方式存在于剧中:第一,身着他人外衣,以他人的身份存在;第二,运用“二元对立”手法,以描写他人身体的方式,暗示她的身体;第三,通过类比,以她的身体“像谁”,来表现她的身体。
首先,一开始伽里玛见到的宋丽玲不是“他/她”本人,而是扮演 “蝴蝶夫人”,唱着意大利语的一个“东西方结合体”,此时,这个身着和服,唱着意大利歌剧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宋丽玲,她穿着他人的外衣,甚至说着他人的语言。然而,就在这样的外表下,伽里玛就认为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蝴蝶”,这样的一个东方女人她娇小脆弱,需要来自西方的呵护。
其次,在宋丽玲的《蝴蝶夫人》谢幕以后,她主动结识伽里玛,他们谈论起《蝴蝶夫人》这个歌剧,伽里玛说到,“我……我的意思是,我一直是看那些身形巨大的女人演出这部歌剧的,她们的化妆糟糕透了。”[7]16伽里玛在对宋丽玲的恭维与赞美中,将西方女性与东方女性的身体进行一个“非此即彼”的对比,通过直接描写西方女性“身材巨大”,暗示东方女性身材娇小。“它们(东方)总是与欧洲的同类物相对称,然而却处于绝对的劣势。”[11]92换言之,东方是什么,不是因为它本质是什么,而是因为西方不是什么。宋丽玲的身体也处于这样的西方/东方的二元对立中,她的身体通过与西方女性的对比被描述出来,因而,伽里玛看见的宋丽玲的身形也不是她真正的样子,而是对比出来的。
再次,宋丽玲的身体像是一条能指链,永远在滑动、漂移、循环,却永远不可能指向一个“终极所指”——宋丽玲自己的身体。法国大使图伦将宋丽玲比作“莲花一样的女人”[7]46,而对西方女子则是直接的身体描写,如“面色苍白的、大腿粗大的白种女人”[7]22。伽里玛也同样将身着黑色睡袍、优雅的宋丽玲比作黄柳霜(Anna May Wong,第一位美籍华人好莱坞影星。)“她优雅地穿着一件二十年代的黑色的睡袍,她站在门口。看起来就像黄柳霜。”[7]27宋丽玲可以像“纤弱的莲花”“像黄柳霜”,就是不能是她自己。后来,在法庭上,宋丽玲脱下假发,和服,而伽里玛爬向假发、和服,嘴里喊着 “蝴蝶,蝴蝶”。由此可见,伽里玛爱的是那个穿着和服、戴着假发的“蝴蝶夫人”,而不是宋丽玲本人。
东方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他者想象”。宋丽玲的伪装,伽里玛的幻想共同构建了这个“最完美的东方女人”。“东方人首先是东方人,其次才是具体的人。”[10]294因而,伽里玛忽视了宋丽玲这个“活生生的身体”,幻想并且迷恋上了一个在身体上并不存在的“完美女人”——宋丽玲。正如凯瑟琳所言,“宋丽玲创造了一个关于身体的谎言,而伽里玛爱上的正是这个‘谎言’,而不是谎言之下宋丽玲真正的肉身。”[6]正是这个虚假的肉身为伽里玛的死亡埋下了伏笔。
二、“东方幻影”——命名一只东方“蝴蝶”
和宋丽玲的身体一起“消失的”还有她的名字。伽里玛行使了西方对东方的“命名权”,将宋丽玲这个名字抹去,用其他代词来指代她,或者甚至重新将其命名为“蝴蝶”。正如萨义德所言,在“白种人”和东方学的领域里,“只有白种人才可以论说东方,正如只有‘白种人’才可以命名有色人种或非白色人种一样。”[10]290
“名字”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称呼的语言符号,是个体被赋予的初始标签。它指向现实世界中某个以此命名的实体,从该“名字”使用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中获得自身的意义[11]。《白虎通·姓名》中也说,“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纪、尊事人者也。”[12]所以,名字是承载了些许期盼并反映一定意识形态的指称代号。因而,伽里玛给宋丽玲命名为“蝴蝶”这一行为也代表了他对宋丽玲的期许,同时也反映了他的东方主义思想。
在伽里玛与宋丽玲初相识时,宋丽玲自我介绍,说了自己的名字——宋丽玲。然而他忽视了这个名字,以“这个中国女歌唱家,这个不情愿的蝴蝶”[7]20来指代宋丽玲,而后向观众说话时,无数次用是“她”来指代宋丽玲,或者称之为“这朵小花”。而后,当他获得晋升时,他叩开宋丽玲的门,唯一一次称呼她为“宋小姐”,宋丽玲第一次拥有了姓氏,但是他/她也不是宋“小姐”,是宋“先生”。当伽里玛向宋丽玲求爱时,说的是“你是我的蝴蝶吗?”[7]39而不是,“你愿意作我的爱人吗?”伽里玛在“命名”“驯服”宋丽玲时,还在装模作样地“征求”她的同意,一遍又一遍地询问,要求宋丽玲自己承认是他的蝴蝶。仿佛在宋丽玲说出“我是你的蝴蝶”[7]40的时候,她也心甘情愿的接受了自己的新名字、新身份,而不是被迫拥有一个新名字。此后,伽里玛开始称呼宋丽玲为“我的小蝴蝶”“我可怜的小宝贝”“蝴蝶”。
“蝴蝶”是一个拥有多重意义的名字。首先,蝴蝶是一种象征性昆虫,有时代表着美丽,有时代表着幸福易逝。[13]132有时象征着纤弱美丽的年轻女子。同时,“蝴蝶”是《蝴蝶夫人》里15 岁的日本艺伎的名称,是美国军官平克顿的日本妻子。平克顿将“乔乔桑(意思是,蝴蝶小姐)译成英语,称呼她为“蝴蝶(Butterfly)”,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她重新命名了。“蝴蝶”是被西方人钉在针尖上的“蝴蝶”,是神秘、软弱、卑微、臣服于西方的所有东方女子的“名字”。伽里玛也效仿了平克顿,命名宋丽玲为“蝴蝶”。被命名为“蝴蝶”的宋丽玲,在失去她名字的同时,也失去了独立性,是一个必须依附于西方男子的柔弱女性,她被强行塑造成伽里玛的“物品”。
宋丽玲,作为一个西方眼中的“他者”,男性眼中的“他者”,在她失去“身体”的同时,也失去了她的“名字”,无论怎样,她都不是真正的自己。伽里玛通过宋丽玲的“他者”身份——“东方女性”,建构了自己“此者”身份——“西方男性”。 “完美女人”只是一个东方幻影,因此,他的爱情注定是“泡沫”,当宋丽玲脱下和服做“宋先生”时,伽里玛也认识到“你(宋丽玲)向我展现了你真实的自我,而我所爱的就是谎言。”[7]87而此时,伽里玛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三、“镜子中的蝴蝶夫人”——死于清醒
经过法庭审判后,宋丽玲被遣送回国,伽里玛则被关进了法国巴黎的一个监狱。他一夜一夜地独自坐在牢房里,将他与宋丽玲的故事在脑海里一遍遍上演,“我总是搜寻一个新的结尾,一个可以使我重新获得尊严的结局,在这个结局里,她终于回到了我的怀抱。”[7]4由此可见,脱下衣服后的宋丽玲并没有使伽里玛真正的幻灭、绝望,而是依然沉浸在他自己编织的“梦境”里。如果,伽里玛没有自杀,那么他的梦境就可以永远继续下去。然而,事实是,在最后一场里,他选择了自杀,为什么?
是因为伽里玛已经清醒了,认识到了宋丽玲只是被他的幻想“加工”后的宋丽玲,那个他爱着的东方女子,是他眼中的“他者”。而事实上,他才是宋丽玲眼中的“他者”,她/他一直以爱的名义“控制他”,让他为中国提供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军事情报。过度的幻想只是徒劳,“今天晚上,我认识到我的寻找结束了。自始至终,我都在错误的地方寻找我所要的东西。”[7]91。宋丽玲脱下假发与和服的时候,伽里玛的“蝴蝶”就已经死去了,所以幻想里再无“蝴蝶”。通过无数个夜晚的幻想,以及演绎歌剧《蝴蝶夫人》后,伽里玛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个“女人”,是“他者”。“公开地,我还是继续否认宋丽玲是个男人……但是,独自一人的时候,在我的牢房,我早已正视了事实。”[7]92伽里玛说“关于东方,我有个幻影……女人们愿意为男人的爱牺牲她们自己。即使这个男人的爱完全没有价值”,而他也说,“我的错误是简单的和不容置疑的——我爱的那个男人是个无赖,一个没有教养的人。他只配在后面踢他一脚,而我却给了他……我所有的爱。”[7]91在这里,伽里玛眼中的宋丽玲是个“既不英勇,也不勇敢”并且“试图抓住一只蝴蝶”的“男人”,而伽里玛则是那只被捉住的“蝴蝶”,是个被男人征服的“女人”。伽里玛也通过镜子意识到,“直到我在镜子中看到,看到的只是……一个女人。”[7]92而后来他的自杀也效仿了蝴蝶夫人,一个为了爱人而付出所有一切的女人。蝴蝶夫人为平克顿放弃了她的宗教、人民、孩子,最后甚至是她的生命,非常符合“东方女人为西方男人放弃一切”的模式。
清醒之后的伽里玛也意识到,自己与“蝴蝶夫人”乔乔桑是一样的,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者”。乔乔桑是西方人眼中的“他者”,是东方的“蝴蝶夫人”,而自己是东方人眼中的“他者”,是西方的“蝴蝶夫人”。因此,在第三幕第3 场之后,他穿上了和服,化了妆,戴上了“蝴蝶”的假发,从一开始扮演的平克顿变成了“蝴蝶夫人”。说着乔乔桑的台词“死于忠贞比活着……带着耻辱活着要好”[7]92,模仿着日本式的切腹自杀,以蝴蝶夫人的外形死去,以一个女人的形象死去。“我的名字叫瑞内·伽里玛——同样作为蝴蝶夫人而广为人知。”[7]93正是这样清醒的认知让他真正的绝望,进而选择肉体的死亡。
四、结语
一名法国外交官和一名中国京剧表演者相爱,共同生活了二十年后,发现他对自己的爱人什么也不了解,甚至不知道他的性别真相。乍一看来,荒唐可笑。但是在一个沟通仅涉及表面,偏见横行的世界上,这个故事并不荒唐。伽里玛固守着他的“西方神话”、“东方神话”、“男人的神话”、“女人的神话”,不仅忽视了宋丽玲“活生生的身体”,也忽视了她身体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甚至把带着自己意愿的名字强加于她的身上。爱情的破裂没有让他绝望自杀,而是在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是“女人”也是“他者”时,结束自己的生命。无论是《蝴蝶夫人》乔乔桑的自杀,还是《蝴蝶君》伽里玛的自杀,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将对方他者化,视对方等而下之,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