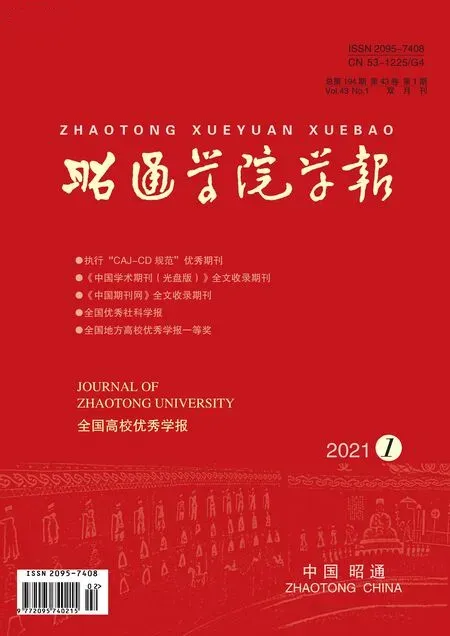小说之虚与互文之实
——关于解读《香菱学诗》的几点异议
胡 辉,宋宁刚
(1.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临沧 677099;2.西安财经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一、引言
香菱是《红楼梦》全书所有女子中率先登场,最后谢幕的重要女性形象,她“根基不让迎、探,容貌不让凤、秦,端雅不让、钗,风流不让湘、黛,贤惠不让袭、平”[1]523;香菱学诗是香菱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志在诗篇,不为境遇所困,又非寻常所能及”[2]234,亦是《红楼梦》的经典片段之一;自香菱学诗进入中学语文教材后, 这一人物更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令人遗憾的是“‘香菱学诗’的片断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后,对这一文本的多种解读,总显得很不到位。这种不到位,一方面是由于材料本身的片段性质,其生硬划出的边界,使得解读难以深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解读者自身的狭隘视野,使得解读流于机械。”[3]118
由是,如何理解、赏析这一片段,笔者不揣浅陋,将香菱、黛玉等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对中国古代真实存在过的诗人如王维、李白、陆游等人诗文的评价,视作“文本与其他文本,文本及其身份、意义、主体以及社会历史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关系和过程”[4]67作简要阐发,认为虽然像林黛玉这样的小说人物是虚构的,但是她对艺术的品鉴力却是真实的,从虚构的小说人物口里说出的对诗艺的创作与品鉴,符合实际,同时提出几点异议,以期对香菱学诗的研究有所补阙。为讨论方便,笔者先从原文段落和相关分析起笔。①
二、香菱学诗细读
《香菱学诗》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的《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滥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截取下来的一节,略加删改后,更名为《香菱学诗》,课文题目系编者添加,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文字内容基本没有改动,却因“一题三做”[2]289,成为展现作者慧心和写作技巧的重要回目,亦是《红楼梦》最有感染力的篇章之一。
话说薛蟠外出经商,香菱有机会跟宝钗一起住进大观园,她一进院,见过众人之后,吃过晚饭…便往潇湘馆中来找黛玉学诗,且说在潇湘馆,经过黛玉的一番教诲,并领了“吟月”题目之后——
香菱听了,喜的拿回诗来,又苦思一回,作两句诗;又舍不得杜诗,又读两首。如此茶饭无心,坐卧不定。宝钗道:“何苦自寻烦恼!都是颦儿引的你,我和他算账去。你本来呆头呆脑的,再添上这个,越发弄成个呆子了。”香菱笑道:“好姑娘,别混我。”一面说,一面作了一首,先与宝钗看。宝钗看了,笑道:“这个不好,不是这个作法。你别怕臊,只管拿了给他瞧去,看他是怎么说。”(P524)
最初,“喜的拿回诗来,又苦思一回作两句诗,又舍不得杜诗,又读两首;如此茶饭无心,坐卧不定。”在宝钗看来,仿佛一个“呆子”。结果,黛玉的评语是“意思却有,只是措词不雅;皆因你看的诗少,被他缚住了。把这首丢开,再作一首,只管放开胆子去作。”(P524)
香菱听了,默默的回来,越性连房也不入,只在池边树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抠土。来往的人都诧异。李纨、宝钗、探春、宝玉等听得此信,都远远的站在山坡上瞧看他笑。只见他皱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宝钗笑道:“这个人定是疯了。昨夜嘟嘟哝哝,直闹到五更天才睡下,没一顿饭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听见他起来了,忙忙碌碌梳了头,就找颦儿去。一回来了,呆了一天,作了一首又不好,这会子自然另作呢。”(P524-525)
第二次,当她诌了一首拿去,只见香菱兴兴头头的,又往黛玉那边来了,黛玉给了评语之后,“香菱听了,默默的回来,越性连房也不入,只在池边树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抠土,来往的人都诧异”(P524-525),而在宝钗看来,香菱仿佛要“疯了”。这一次,黛玉的评价是:“自然算难为他了,只是还不好。这一首过于穿凿了,还得另作。”(P525)
宝钗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个‘色’字倒还使得。你看句句倒像是月色。这也罢了,原是诗从胡说来。再迟几天就好了。”香菱自为这首妙绝,听如此说,自己又扫了兴,不肯丢开手,便要思索起来。因见他姊妹们说笑,便自己走到阶前竹下闲步,挖心搜胆的,耳不傍听,目不别视。一时探春隔窗笑说道:“菱姑娘,你闲闲罢。”香菱怔怔答道:“‘闲’字是十五删的,你错了韵了。”众人听了,不觉大笑起来。宝钗道:“可真诗魔了。都是颦儿引的他!”(P525)
又另作一首,被黛玉称为“过于穿凿,还得另作”。而“香菱自为这首妙绝,听如此说,自己扫了兴,不肯丢开手,便要思索起来。因见姐妹们说笑,便自己走至阶下竹前,挖心搜胆的,耳不旁听,目不别视”。这次被宝钗称作“可真(是)诗魔了”。众人看香菱像是着了魔一般,想拉她到四姑娘房里,引她“瞧瞧画儿”,叫她“醒一醒”,可效果并不理想。
香菱满心中正是想诗。至晚间,对灯出了一回神。至三更以后,上床卧下,两眼鳏鳏,直到五更,方才朦胧睡着了。一时天亮,宝钗醒了,听了一听,他安稳睡了,心下想:“他翻腾了一夜,不知可作成了?这会子乏了,且别叫他。”正想着,只听香菱从梦中笑道:“可是有了。难道这一首还不好?”宝钗听了,又是可叹,又是可笑,连忙唤醒了他,问他:“得了什么?你这诚心,都通了仙了。学不成诗,还弄出病来呢。”一面说,一面起来梳洗了,会同姊妹往贾母处来。原来香菱苦志学诗,精血诚聚,日间做不出,忽于梦中得了八句,梳洗已毕,便忙写出,来到沁芳亭……(P526)
第四次,被送到惜春房里的香菱,“满心中正是想诗,至晚间,对灯出了一回神。至三更以后,上床卧下,两眼鳏鳏,直到五更,方才朦胧睡着了。”(P526)结果梦里得了一首,获得了宝钗的一句:“你这诚心,都通了仙了。”(P526)香菱这次也是豁出去了,不管众人说笑她,迎上去笑着说:“你们看这首。若使得,我就还学;要还不好,我就死了这作诗的心了。”(P527)结果众人看了笑道:“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语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社里一定请你了。”(P527)
香菱学诗的桥段到此为止。这个故事横跨了《红楼梦》第四十八回后半段,至第四十九回开头。之所以如此,因为章回小说,要留下一个“尾巴”到下一回,即所谓“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稍稍总结一下香菱学作诗的几次表现,似乎可以这么说:一般的中学教学设计,会将重点放在(1)香菱学诗三次的不同;(2)香菱学诗的方法和精神;(3)“香菱学诗”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如果细读课文(或小说第四十八回后半部分)……似乎也真是如此。
三、香菱学诗的几点异议
有论者指出,《红楼梦》常被认为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不仅是因为“小说反映的文化生活面极为广阔、生动而具体”,而且“对其所反映的对象,常在小说的内部,就有一种理论化的自我阐释”:比如借“香菱学诗”一节,让黛玉与香菱讨论诗歌鉴赏和创作的理论,除了“让小说中的人物阐释一些原理”,也“使行为本身,在形象化的感性之外,获得一种理性的洞见”。[5]175-176有鉴于此,笔者就之前课堂很少涉及的,但实际上却是引导学生深度思考的,课堂内外需要关心的问题,提出几点异议。
(一)高超还是刻意
如前所说,课本的教案样板,也是按照香菱在学习写诗过程中的几次不同反应来引导学生,留意、对比曹雪芹“高超”的写作技巧。只是,从上述看,这种“写作技巧”(如果能称作“技巧”的话)真的高超吗?笔者的感受却相反,不是高超,而是刻意。
尤其写香菱第一次拿了诗给黛玉看,被黛玉批评了之后,“默默的回来,越性连房也不入,只在池边树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抠土。来往的人都诧异”(P524-525),以及最后一次,香菱满心是诗,直到五更方才蒙胧睡去,最后在梦里得了一首诗,并且喜不自禁地说梦话:“可是有了,难道这一首还不好?”(P526)的情形,都显得太刻意,甚至有些流于俗套了。②
钱钟书《七缀集》中有一篇文章叫《林纾的翻译》,在这篇文章中钱钟书批评林纾在翻译时由于自己添油加醋,导致“太戏”,而借用李贽评点《琵琶记》第八折《考试》批语说:
“太戏!不像!”“戏则戏矣,倒须似真,若真反不妨似戏也。”林纾的改笔过火得仿佛插科打诨,正所谓“太戏!不像”了。[6]84
笔者这才感觉找到了知音,或说找到了有力的佐证和壅塞心中想说而未能说出的话。中国古语说,“无巧不成书”,“巧”有多种,或说多个层面。上述的“戏”或“巧”,太直露,也太取巧,“作”的痕迹过重了,给人的感觉就不是真实、可信,而是刻意和造作。
这个问题,在关于《红楼梦》的阅读和研究(更不用说作为一篇中学课文的学习)中,似乎未见被提及。难道这是因为面对巨著,我们就少了评断的勇气?
(二)轻前(学品诗)重后(学写诗)
如论者所言,《红楼梦》有鲜明的“文备众体”的特征,其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叙事与抒情的统一”。这一特点落实在语体中,就是“韵散交错”,即“在散文叙事过程中夹杂了诗词曲韵文创作”。[7]108这就引出与前说相关的一个问题:“香菱学诗”一节中,香菱的几次不同表现和反应,自然可以成为课文学习的要点,但“‘香菱学诗’作为《红楼梦》的一个片段,其特殊性在于,并不直接以诗歌见长,而是带着诗话的属性,也许可以叫作‘诗话小说’”[8]39,更准确地说,是以小说的形式,品藻诗词,谈诗论艺。香菱之“学诗”,实际上分为学读诗(品诗)和学写诗两个部分。而作为课文的《香菱学诗》,却过于侧重后半段(学写诗),而轻视前半段(学品诗),即使重视后半段。
另外,似乎也未见有细究:香菱三次学作诗,第一次所作怎么就“不好”(宝钗语),或者“意思却有,只是措词不雅”(黛玉语)?第二次所作,又哪里显得“过于穿凿”(黛玉语),“不像吟月,倒像是吟月色”(宝钗语)?而第三次所作,又是如何像众人所说,“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了?作为语(言)文(学)的学习,这样的品类赏析,本不该缺位。
此外,又何妨将学习和研讨的重点,放在前半段,尤其是“黛玉论诗”(或曰“学诗次第”)和“香菱谈诗”上来呢?毕竟“香菱学诗”一开始,讲香菱住进了大观园,到潇湘馆中来,想要跟黛玉学习作诗如此这般:
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虚’的,实的对‘实’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得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主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香菱道:“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瑒、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极聪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P521-522)
这段所包含的信息量极大,可讨论的内容也是十足丰富。比如:如何看待这里,黛玉作为小说人物所讲的话?只是当作戏言,轻易打发过去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对这里所讲多打几个问号。比方说,如何看待黛玉所讲的作诗(评诗)的标准:起、承、转、合,平仄虚实,以及“奇句”?“平声对仄声,虚的对‘虚’的”,我们不难理解、把握;“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等等,这些论诗之语,又当如何看待?
凡此种种,笔者内心也有自己的结论,但问题比结论更重要,毕竟,结论可能有很多种,可能会过时,但问题却永远存在,而只有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才能对整个《红楼梦》的研究有所增益。
(三)学诗的次第
张平仁先生指出:“曹雪芹诗论的核心思想通过香菱学诗一节举重若轻地拈了出来,完全合乎传统诗论的混整感悟思路及主流诗论主张”,尤其香菱对王维诗歌的解读,“较历代论家有更形象、具体、深入之处,其对无理而妙的强调与理解可补前代诗论之缺”。《红楼梦》作者深厚的诗学素养,也于此可见一斑。[9]222如果我们认同这些观点,那么关于学诗的次第问题,也随之而来。
比如,为什么不可学香菱所说的陆游诗?为什么要先看王维五律,再读杜甫七律,再次读李白七绝,此后再读陶、应、谢、阮、庾、鲍等人的诗?是否有道理?在何种意义上有道理?为什么黛玉强调,学作诗要有王维、杜甫、李白三个人“做底子”?并且对每个人,强调的重点都不相同:对王维强调是五言律,对杜甫强调的是七言律,对李白则强调是七绝?这样的强调和侧重有无道理?有何道理?这些道理又说明了什么(比如从文学史角度来讲的文体发展问题,以及创作论角度的学习问题,以及黛玉的古诗造诣及其趣味等等)?
当然,实际上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且不说笔者难以胜任,就是今天的中学语文老师,乃至大学中文系的老师们,能经得起这些问题之研讨的,恐怕也不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上述问题不重要,或不值得探讨。恰恰相反,正因为其困难,牵涉的问题极广(有关创作论、作家论、作品论等多个方面),意味丰富而又深长,才值得花费心力去研讨。
值得注意的是香菱读完了王维的诗,来还书时,和黛玉有一番关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对话:
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见香菱笑吟吟的送了书来,又要换杜律。黛玉笑道:“共记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红圈选的,我尽读了。”黛玉道:“可领略了些滋味没有?”香菱笑道:“领略了些滋味,不知可是不是,说与你听听。”黛玉笑道:“正要讲究讨论,方能长进。你且说来我听听。”香菱笑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这话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从何处见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似的。还有:‘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这‘馀’字合‘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儿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正说着,宝玉和探春也来了,也都入坐听他讲诗。宝玉笑道:“既是这样,也不用看诗。会心处不在多。听你说了这两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黛玉笑道:“你说他这‘上孤烟’好,你还不知他这一句还是套了前人的来。我给你这一句瞧瞧,更比这个淡而现成。”说着,便把陶渊明的“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翻了出来,递与香菱。香菱瞧了,点头叹赏,笑道:“原来‘上’字是从‘依依’两个字上化出来的。”宝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讲。越发倒学杂了。你就作起来,必是好的。”(P522-523)
这番衡文谈艺的文字,不该成为语文、乃至文学学习的重点,甚至作为文学研习与教学的样板?作为语文和文学的研习,应如何处理读(书)与写(作)的关系?又当如何看待这里,宝玉说的“会心处”,以及后面宝钗说的“原来诗从胡说来”?这些话有无道理?若有,是何道理?类似问题,都不应轻易放过。
也许是因为自己喜欢讨论这些问题而又是老师的缘故,看到这里黛玉面对一个丫鬟,如此平心静气、耐心十足,循循善诱地提问(先问:“共记得多少首?”又问:“可领略了些滋味没有?”之后鼓励香菱说:“正要讲究讨论,方能长进。”),引导香菱说出自己的见解,心里竟有几分感动。想想后面:香菱第一次作了诗,宝钗看到时说:“这个不好,不是这个作法。”而黛玉却说:“意思却有,只是措辞不雅……”两相对照,就更觉感动。
黛玉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眼光?什么时候说起话来这么温和、善意,充满对初学者的宽待与鼓励?从她对香菱所说的话中,不难看出,林黛玉的确是喜欢诗文的,也有极高的天分。甚至可以说,只是在谈论诗文的时候,她才会显得格外认真而耐心,放下了自己尖刻的一面——因为这时,她才充分地发挥出自己的才情与价值,她的生命的灵光也得到充分的展现。某种程度上说,这时候的黛玉是更讨人喜欢的。我们甚至会觉得,整天待在大观园里慵懒无聊、没有正事可做,真是太浪费黛玉的青春、天才和生命。要是她生在另一个时代——比如近代或者现代,做个女子学院什么的诗词老师,相信不仅会非常称职,还会因其才情吸引和影响不少学生。这份工作会改变一些她的性格,也未可知。这听起像是题外话,在课堂上却未必不可以讨论。
就以上引文,如果再往民俗学上拓展一下,还可以问:香菱说,“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两句,“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似的”,应作何解?这个比喻恰切吗?香菱能这么说,必是熟悉橄榄的。橄榄是生在中国南方的,香菱又能从哪里知道橄榄?且对其稔熟到顺口就会提起?
从香菱学诗时的投入,“兴兴头头”以至有些“风魔”,我们可以看出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比如:性情、热心、积极、投入,听老师的话(她说:“既这样,好姑娘,你就把这书给我拿出来,我带回去夜里念几首也是好的。”小说中还记述:“香菱拿了诗,回至蘅芜苑中,诸事不顾,只向灯下一首一首的读起来。宝钗连催他数次睡觉,他也不睡。”),谦虚,有灵性(虽然不及黛玉),等等。还有:为什么黛玉说香菱是“极聪明伶俐的人”,而宝钗却说她“呆头呆脑”?想想黛玉的心性和眼光,是她看错了啊?抑或,她这么说只是为了安慰和鼓励香菱啊?无论如何,黛玉这样评价别人,在整部《红楼梦》里都是很少见的;她和几乎同样聪明的宝钗(比如第三十七回和第三十八回,黛玉、宝钗、宝玉等吟咏诗为乐,宝钗和黛玉就旗鼓相当),对香菱的评价差别如此之大,细想之下,更显得意味深长。
对于香菱作诗时的几次不同表现,宝钗每次都有不同的、递进的说法:“呆子”“疯了”“诗魔”“通了仙了”,与香菱的投入相比,宝钗显得冷静得多,也现实得多。看到香菱茶饭无心,坐卧不定,她说:“何苦自寻烦恼?都是颦儿引的你,我和他算账去。”“算账”不见得为真,但是认为香菱不必如此“苦辛”,却是不假。从宝钗对诗和文学的态度,也不难看出她是怎样一个人,以及她和宝、黛有何不同。
四、香菱学诗的棱镜效应
香菱学诗“以传神之笔和幽默诙谐的风格,表现出了这位神醉于诗的青春女性的独特的精神风貌”[10],但是,将不到四千字的“香菱学诗”(或“慕雅女雅集苦吟诗”)放在整部《红楼梦》中来看,只有半回的篇幅,不过两百四十分之一,或者一百六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将“香菱学诗”一节放在整部小说里来看,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未尝不是通过香菱“让宝玉、黛玉、宝钗等疏疏落落地展开错位观感”。[8]42在香菱学诗的过程中,黛玉、宝钗和宝玉的反应都有具体而微妙的差异。就此来说,香菱就像是一面棱镜,折射着黛、宝、钗三人相近或不同的心性、气质与倾向。
比如香菱来给黛玉还书时,黛玉启发她讲一讲自己的读诗心得,宝玉说:“会心处不在多,听你说了这两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P523),又说:“不用再讲。越发倒学杂了。你就作起来,必是好的。”(P523)听起来就跟黛玉很是会心、相契。
香菱第二回作诗,“在池边树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时,宝钗、宝玉等人都远远地瞧着她笑。宝钗说:“这个人定是疯了!”说了一通香菱的痴事,宝玉跟着发了一通议论:“这正是‘地灵人杰’……”结果,宝钗听了,笑道:“你能够像他这苦心就好了;学什么有个不成的吗?”小说接着写了四个字:“宝玉不答。”宝玉为什么不答?因为宝玉被宝钗㨃得很不痛快,不知说什么好,也扫兴得无心说什么。能想象黛玉会这么说宝玉吗?只有宝钗这样有正统思想的女子才会这么说。
说到心性气质(也即性情),将宝钗这个虚构的小说人物与为写作而生的卡夫卡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或许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不伦不类。卡夫卡曾在日记里写道:“在生活中不能生气勃勃地对付生活的那种人需要用一只手把他的绝望稍稍挡在命运之上——这将是远远不够的,但他用另一只手可以将他在废墟下之所见记录下来,因为他之所见异于并多于其他人。他毕竟在有生之年已是死了的啊,而同时又是幸存者。这里的先决条件是,他不需要将双手和超过他所拥有的力量全部用来同绝望斗争。”[11]641不同于卡夫卡将自己看作是作为一个“死了的人”而幸存着,宝钗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活着,并且要好好地活着的人。他们对人生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取向。对比他们对人生的态度之差异,探寻这些差异的深层原因,也应当是语文(语言文学)讨论的题中之义。
五、结语
詹丹老师也曾提醒,“香菱学诗”一节,应放在《红楼梦》的大文本背景中去理解和认识,如果这一节的“复杂意义从文本的具体语境中被抽取出来”,不仅会抹煞经典文学的深刻内涵,也会模糊“人们对当下现实本该有的清醒认识”。因此,当“倡导一种类似从‘香菱学诗’说开去的方法,努力揭示文本片断与整体语境间的断裂,并在藉文本内部的断裂中,思考文本与现实的断裂”。[3]132本文以上所讨论的,虽然只是我们阅读“香菱学诗”的一点感想,却同样期待,不仅将这一节的内容回置到《红楼梦》的文本母体重去理解,甚至应该放在诸如中国诗论史、古典诗歌创作论等更大的问题域中去讨论。
此外,也有理由相信,这一节、乃至整部《红楼梦》中还有许多未曾经深论的问题,有待有心的读者能够深入地去开掘、研索,庶几才对得起伟大的文学作品,亦推动红学研究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也是我们不惮浅陋,抛砖引玉,撰写本文的目的之一。
注释:
① 本文所引《红楼梦》内容皆出自:(清)曹雪芹,(清)高鹗著;俞平伯校;启功注.红楼梦(全两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随文标注页码。
② 本文第二作者宋宁刚老师在关于孙犁的《荷花淀》和茹志鹃的《百合花》的比较文章中,也谈到过这一点,限于篇幅和选题缘故,本文不展开论述,详参宋宁刚、陈敢:《战争原野上的艺术鲜花——在战争文学背景下对<荷花淀>与<百合花>的考察》,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