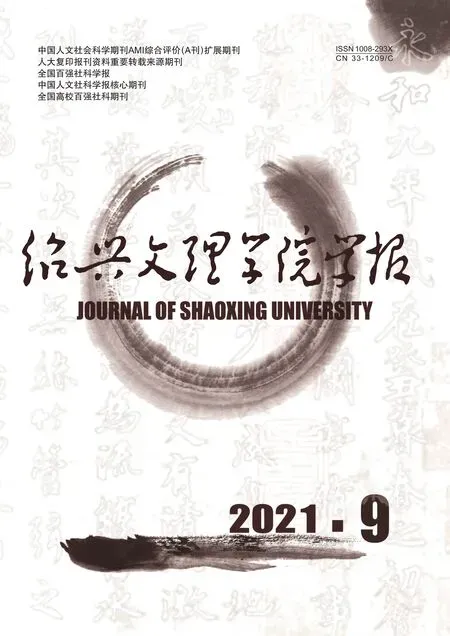《儒林外史》与“重复”
吴新苗
(中国戏曲学院 戏文系,北京 100073)
在当代西方文论中,“重复”是一个重要概念,以“重复”理论著名的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小说和重复》中说:“无论什么样的读者,他们对小说那样的大部头作品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得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识别作品中那些重复出现的现象,并进而理解这些现象衍生的意义。”[1]1按照米勒的观点,小说中“重复”大概有这样三类:“(1)细小处的重复,如语词、修辞格、外观、内心情态,等等。(2)一部作品中事件和场景的重复,规模比(1)大;(3)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上的重复,这种重复超越单个文本的界限,与文学史的广阔领域相衔接、交叉。”(1)参见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关于米勒“重复”概念的讨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页。
“重复出现的现象”在《儒林外史》中非常常见,构成小说文本的重要特征。本文借鉴米勒关于小说“重复”分类、“重复”与意义生成的相关理论,探讨《儒林外史》中的“重复”现象及其衍生意义。
一、细节重复:风俗写真与人物塑造
细节重复是指在文本中某些“词语”,外观、动作与心理描写等细节的重复。《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2)《儒林外史》的引文俱依据张慧剑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下同,不再出注。:
五河的风俗:说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着嘴笑;说起前几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里笑;说那个人会做诗赋古文,他就眉毛都会笑。问五河县有甚么山川风景,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有甚么出产希奇之物,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那个有品望,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德行,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才情,是专会奉承彭乡绅。却另外有一件事,人也还怕:是同徽州方家做亲家;还有一件事,人也还亲热:就是大捧的银子拿出来买田。[2]547
这一段“盘空硬语”是小说中语言艺术最精彩的华章之一,“五河”“笑”“奉承”“彭乡绅”四个关键词语不断重复,反映了五河县恶劣的势利风俗。紧接着这段文字后出现的几个人物唐二棒槌兄弟、姚五爷、成老爹,但凡开口,非“彭”即“方”,盖因为彭家老四在京为官有权势、方家做盐商有钱,所以“彭“方”就成了“势利”的代名词,成为这些势利者最为羡慕、巴结的对象。“彭”“方”不仅仅是这些人常挂在口头的“词语”,还成为支配他们日常生活的逻辑。小说写到季苇萧替杜慎卿带书信给虞华轩,因为是从厉知府处来,众人觉得从厉知府处来的人首先肯定会去拜访彭、方两家,而且如果拜访了彭、方就不会再来拜访虞华轩,按照这个神奇的逻辑,他们一致判定来人是个骗子,此人“一定不是季苇萧”。百口同声、无处不在的“彭”“方”形成语言的网络和现实生活的逻辑,决定了五河县人的思维和行动。
以“词语”的重复来写风俗人情,是《儒林外史》惯用笔法,其实在楔子中就已经确定了这种书写模式。王冕在郊外看到胖子、瘦子、胡子三位野餐,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危老先生回来了”!此后不长的聚谈中,每句都出现朝廷大员“危老先生”的徽号,评点者云“不料其开口便俗,却是先生著书本意”“非大老不开口,是此书行派”“开口就是一尊大神佛”[3]3,皆注意到非“大老”不开口是本书交谈体例之一,尚未揭示出此类词语的重复是小说揭示势利风俗的基本模式。这些类似的谈话方式,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本身也构成了一种重复,以表明这已经是社会上习以为常的现象,风俗之恶劣乃天下滔滔者皆是,普遍到人们“不觉其非”的程度。
细节重复不仅对描写社会风俗起到重要作用,还是塑造人物形象的“点睛”之笔。《儒林外史》非写一人一事,而是塑造了世俗社会芸芸众生的群像,不少人物倏忽而来、匆匆而去,却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这就得益于作者有意识地使用词语、外观、动作的重复,以简约凝练的白描达到“传神写照”的艺术效果。两处写韦四爷一副大白胡子和哈哈大笑的神态足以见其豪爽的个性,一遍遍擦铜炉表现出杨执中之“呆”,马二游西湖对美景毫无会心,却一次次寻吃食,让人看到其“庸腐”,多次写牛浦之“偷看”以表现此人之“下作”,都是很好的例证。尤其对那些出场不多的次要人物,作者更倾向于用词语重复的方式来强调人物某个方面的特性,以经济的笔墨勾勒出人物的剪影。
小说中写了几位由小商小贩阶层跻身文士群体的人物,景兰江和郭铁笔是其中代表(他们在祭泰伯祠时都是“司帛”),这也是作者用“重复”笔法塑造人物形象的典型例证。涉及景兰江的重复词语有“头巾店”“读诗”“赵雪斋”。出场时,他在杭州豆腐桥大街的金刚寺前开了一家“头巾店”,或许是因为卖“头巾”与文人接触多的缘故,沾染了一些风雅,爱读爱写诗词。匡超人看到他在饭店、船上都看书,“书上圈的花花绿绿,是些甚么诗词之类”(多少年后再出场时他还是伏在书店的柜台上“看诗”);他告诉匡超人各地印的诗选都有自己的作品,以杭州名士自诩。杭州诗坛最著名的诗人“赵雪斋”则成为他常常挂在口头的“一尊大神佛”,但与五河县人说“彭”“方”的势利见识不同,景兰江是打心眼里把“高据诗坛”的赵雪斋当作自己的偶像、人生目标。作家在写景兰江时不断重复“读诗”“赵雪斋”这些词语,塑造了一个“好名”的小人物形象。在他周围那些市民阶层的熟人看来,景兰江就是一个笑话,尤其为一心逐利的潘三所不齿。潘三嘲笑他在“头巾店”里一边刷头巾一边吟诗惹得左邻右舍都笑,讥讽他本来有两千两银子的本钱,“一顿诗做得精光”,“而今折了本钱,只借这做诗为由,遇着人就借银子,人听见他都怕”[2]231。景兰江名声最盛时是参加西湖诗会(这是小说中有名的一次诗文会,多少年后还常常被人提起),可就在这高光时刻,因为归来途中同行的支剑峰被逮而大扫其兴。或许是从支剑峰事件有所感悟,就像当年的蘧公孙在“人头会”后的心境一样,“把这做名的心也看淡了”(第十三回)。景兰江到南京后很少参加文人活动,一次名士聚会时杜少卿问为何不见景兰江,蘧公孙道:“他又在三山街开了个头巾店做生意。”(第三十四回)景兰江的人生兜了一圈,又转回原点,关键是从曾经也那么好“名”的蘧公孙口中道出景兰江最后的归宿,这也颇耐人寻味。同样耐人寻味的是,讥笑景兰江的逐利之徒潘三最终身陷囹圄。人生啊,名乎?利乎?
郭铁笔是开“刻图书”店的,在述及此人时,“刻图书”及其作品“图书”(印章)常常被重复,以加深读者对这个出场次数较少人物的印象。在小说描述的名士群体中,他的人生是最务实的。第二十一回写牛浦“走到吉祥寺门口一个刻图书的郭铁笔店里柜外”,这是郭铁笔第一次出场,后来到了扬州,辛东之介绍“这位是芜湖郭铁笔先生,镌的图书最妙”,然后又到了南京,“报恩寺门口租了一间房,开图书店”,描绘出郭铁笔由芜湖至扬州、南京的游走线路。他算一个文化人,从事的职业更需进入文化圈,获得主流的认可方能有个人的发展,因此他常用自己刻印的图章作为结交上流人士的见面礼。第三十回写他拿着“两方图书”去见杜慎卿,说了很多仰慕、奉承的话。黄评“铁笔之外,只奉承是本事,然也自居名士,想别无它能”,总觉得有些苛评。齐评“法聪口角,何地无之”[3]370,却包含着一种理解的同情。这番奉承话听起来的确有些肉麻,但郭铁笔绝非无耻之辈,观其劝牛浦不应欺侮舅舅时说“尊卑长幼,自然之理”,可知是一个颇通情达理的人。那么,他的那番奉承话,也只不过是世俗中司空见惯的常谈罢了,从杜慎卿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的话中,看到郭铁笔这番奉承起到了效果。后来郭铁笔也拿着“图书”拜见杜少卿,杜少卿回拜了,并邀请他参加河房雅集,最终也参加了泰伯祭祀大典,此后就不再见他的踪影。事实上,这种叙述表示郭铁笔已经成功进入了南京的文人圈,其图书店应该开得比较兴旺。郭铁笔人生境界当然谈不上有多高妙,颇似一个勤勤恳恳谋划生路的商人兼艺术从业者,但这个人物的“务实性”却丰富了我们对《儒林外史》中文人群体的认知。
众所周知,外观(外貌)描写是刻画人物形象重要方法,小说中“外观的重复”比起一般简单的外貌描写,衍生出更多的意义。读者对周进、范进出场时的“外观”应该比较熟悉,其中就有重复性因素。第二回,众人看进到屋里的周进:
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2]21
第三回范进出场时“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着一顶破毡帽”、破衣衫。“毡帽”是旧时贫苦阶层所戴的帽子,他俩都是读书人,但还未进学,所以没有资格戴代表文士阶层的“方巾”(3)《明史》卷六十七《舆服志》:“儒士、生员、监生巾服:洪武三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四方平定巾,即“方巾”。。而刚进学的梅三相公则获得戴“方巾”的资格,因此顶着“新方巾”笑傲小友周进。在周范二进的外观重复中,我们看到最底层八股文士可悲的境遇。日后当周进“绯袍金带,何等辉煌”地看着范进时,正是心中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唤起同情心,看三遍烂文字也要找到提拔范进的理由。其实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复,与周进外观最重要的重复是倪老爹,第二十五回,鲍文卿看那人时:
头戴破毡帽,身穿一件破黑绸直裰,脚下一双烂红鞋,花白胡须。[2]300
倪老爹与周进的毡帽、衣服、鞋子,甚至连胡须都一模一样的款式,所不同的是周进的帽子、衣服、鞋都是“旧”的,而倪老爹的则都是“破”“烂”的。(周进外观多写了一句“右袖和坐处都破了”,自然是周进长期坐着写字导致的,而倪老爹已经不做笔墨生涯了,因此没有衣袖等处的描写,作者在此等细微处见出人物的生活,笔法妙入毫巅)这两个人出场相隔二十三回,外观描写如此高度重复,同时一“旧”一“破”的细微差异暗示他们人生结局的天壤之别,在这些似乎无关紧要处都体现出吴敬梓的艺术匠心,令人叹为观止。但我们要知道,倪老爹早年间比起周进要算人生赢家,他20岁就进了学,带了37年的“方巾”,可此后场屋困顿,越来越穷困潦倒,到卖儿卖女的地步,他的方巾变成了“破毡帽”。周进戴到快60岁时的旧毡帽却一朝换成了方巾,接着“绯袍金带”。两人走的都是读“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的八股人生,但八股衡文无定准(所谓“唯愿文章中诗官”),在命运的拨弄下,才有了倪老爹和周进两人前后迥异的人生变局。小说通过这段精心设置的外观重复,引导人们对两位八股文士命运进行对比,要表达的不正是开篇词作“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的意思吗?回头再看两个人迥异的人生命运,不难体会到吴敬梓寄托了多么深沉的人生喟叹和对文人命运的深切同情。
黄富民说世人往往不能读懂《儒林外史》,因为小说“纯用白描,其品第人物之意,则令人于淡处求得之,鲁莽及本系《儒林外史》中人直无从索解”[4]689。这些细节重复似是漫不经心,淡淡着笔,其实皆有深意,对于理解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作者写作意图有着重要意义。
二、事件、场景重复:或显或隐的表达策略
长篇小说一般都会出现众多人物,有纷繁复杂的情节,表现具有一定广度和容量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中本身就存在着大量重复事件和场景,生老病死、恋爱婚姻、围炉聚谈、分别、重逢、过访等,小说中自然会形成这些情节场景的重复。但小说中有些事件、场景的重复是自然性质的,每个事件、场景只有自身的意义;有些被重复的事件、场景不仅具有自身的意义,还因为重复而生成更丰富的意义,后者才是“有意味的”重复。这种有意味的重复事件和场景,在《儒林外史》中有两处最值得注意。
(一)临终遗言
《儒林外史》汇集了各类人的声音,代表着各自的立场,反映各自的生活逻辑和价值取向。翟买办拿着县令的请帖去请王冕,王冕不愿意去,说除非因为犯了事老爷拿帖子传,那就不得不去;翟买办无法理解这个逻辑:“票子传着倒要去,帖子请着倒不去?”蘧公孙说做制艺是俗事,以为“向才女说这样的话是极雅”的,却惹得妻子愁眉泪眼感叹“岂不误我终身”。杜少卿父亲为官清廉“敦孝弟,劝农桑”,高翰林则嘲笑“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
作者让各类人纷纷登场,众声喧哗,表达不同生活意见。“临终遗言”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意见”,家族长者在临终时告诫晚辈该如何做人这样的场景在小说中不断重复。
第一回写王冕母亲去世遗言:“作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著我的坟墓,不要出去作官。”第十七回写匡太公给匡超人的遗言:“……第二的侥幸进了一个学,将来读读书,会上进一层也不可知,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日子略过的顺利些,就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万不可贪图富贵,攀高结贵……”第三十二回写娄焕文临别前给杜少卿的遗言(娄焕文病重离开杜少卿,这也可以算临终遗言):“……银钱也是小事,我死之后,你父子两人事事学你令先尊的德行,德行若好,就没有饭吃也不妨……你眼里又没有官长,又没有本家,这本地方也难住,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业来……“第四十回写萧昊轩给萧云仙的遗言:“我在一日,是我的事;我死后,就都是你的事了。总之,为人以忠孝为本,其余都是末事。”
估计没有哪一部小说这么一次次重复“临终遗言”的场景。细看这几处的遗言,并不完全相同,王冕母亲一再强调“不要出去做官”,匡太公不明确反对“(功名)上进一层”,但“到底是身外之物”,还是以“孝弟”德行为本;娄焕文则强调“德行”同时希望杜少卿“做出些事业来”,至萧昊轩就说“以忠孝为本”,所谓“忠”当然需入仕为官,追求事功。很明显,作者通过这些长者遗言所表达的“文行出处”,其实是有变化的,自娄焕文遗言开始,儒家积极入世君子弘毅的精神越来越强烈。正如商伟先生的判断:吴敬梓在《儒林外史》历时20年的创作过程中留下了“他人生和思想历程的痕迹,包括成长、成熟、重新定位和自我否定”[5]6。他同时又指出吴敬梓是认识了虞博士的原型吴培源之后,才开始有了在小说中加入祭祀泰伯祠(这是小说中的一件很重要的事业)的情节想法。从小说自身的逻辑来看,祭祀泰伯祠与以匡超人为代表的士子阶层的堕落有关。
以上重复出现的“临终遗言”叙事中,只有匡超人彻底违背了父亲的“遗言”,堕落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名利之徒。在父亲一番遗训之前,马二先生对他早有过洗脑,“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第十五回)马二先生这一番言论,在前几回里已经对蘧公孙宣教了一番,总之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追求功名富贵,就是要“做官”。不过平心而论,马二这番话也不过是科举社会的老生常谈,而且以“显亲扬名”的大孝为出发点在当时来说也没有什么大错,正如评者说“马二先生逢人教诲,谆谆不倦,自是热肠一片。莫以其头巾气而少之也。”[3]202匡超人事实上一度接受了马二先生的教诲,在大柳庄边读书、做生意,边侍奉卧床的老父,纯然一个孝子,一个奋进勤勉的少年,所以他完全按照马二的话去做也不会面临道德危机。(4)第十七回卧评总评:“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不至斗然变为势利心之人。”也是这个意见。见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问题出在他到了杭州之后,在与斗方诗人聚会时听到景兰江的一番高论,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前面说到,景兰江就是一个求“名”的典型人物,这次聚会上他高谈赵雪斋与黄进士谁的人生更成功——“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正是这番话,匡超人听得“才知道天下还有这一种道理”(第十七回),从此思想发生转变,开始说谎、吹牛。“求名”之心方盛,又有潘三一番教诲,“二相公,你在客边要做些有想头的事”,又生“逐利”之心。这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听到了四种不同的人生观,这些人生训诫的场面在他身上一次次重复,导致他在众声喧哗中迷失了自己。
众声喧哗意味着政教的缺失和窳败,其结果是道德失范,人性堕落。所以,如何重建道德秩序,挽回人心?未尝不是写完匡超人、牛浦故事后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换句话说,或许现实中吴敬梓是因为和吴培源结识,才开始谋划整修、祭祀泰伯祠,但也存在一种可能,是吴敬梓因为小说创作带来的困惑而与朋友交谈时促成了关于泰伯祠的计划。总之,吴敬梓小说创作的内在逻辑需要一次祭祀“助一助政教”,需要一次更大范围的更庄重的“临终遗言”的宣讲,泰伯的“让”德(“三以天下让”,让名让位,就是让功名富贵)是再好不过的“遗训”。是的,泰伯祠祭祀是另一次“临终遗言”的重复,所以小说中贤与不肖者都得以与会,让日渐沉沦的士林再次感受“礼”的熏陶,听见先祖的遗训,这就是吴敬梓的劝世之心,是他写泰伯祭祀的根本原因。
但是祭祀泰伯的事业,其效果又如何?正如经历了萧云仙的一番兵农、事功的颓然收场一样,泰伯祠很快破败。作者两次重复写泰伯祠的历史现场,至第五十五回市井奇人和邻居老爹来到泰伯祠,看到的更是破败不堪的景象,两人黯然神伤,登上雨花台绝顶:“望着隔江的山色,岚翠鲜明,那江中来往的船只,帆樯历历可数;那一轮红日,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夕阳无限,重修政教、“礼乐兵农”的理想也似夕阳一样,渐渐销匿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这时小说已接近尾声,喧哗的众声也渐渐远去,奇人荆元的声音却无比清越:
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2]638
临终遗言(包括祭祀泰伯祠)场景的重复,反映出吴敬梓对“出处”问题的思考,小说经历了一场积极入世的“兵农、事功”之后,又回归到隐士王冕、奇人荆元那里,这才是吴敬梓精神的最终归宿。
(二)才子佳人
受明清之际时代风气的影响,才子佳人小说盛行于世,《红楼梦》批评此类作品“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至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才子佳人故事的流行当然是现实中“才子佳人”思想观念文学化、理想化的产物。对于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儒林外史》可以不写才子佳人故事,但不能不写抱有“才子佳人”观念的文人;对于一部表达“意见”的小说,《儒林外史》对此类文人更应该有几笔“写照”。
小说写蘧、鲁婚姻的故事多少带有对“才子佳人”反讽的意味,蘧公孙要做才子名士,以为谈谈诗词歌赋定会赢得小姐的欢心,没想到鲁小姐这位才女却只认八股文,他们那场闹剧般的婚礼早已宣告了“才子佳人”理想的破产。才子佳人小说、戏曲中很多女主角是妓女,女主才色双绝,关键对才子还要深情款款,常常能赏识才子于风尘之际。第五十四回写从事占卜的丁言志要做名士,带着所有积蓄到妓院找聘娘谈诗,聘娘道:“我们本院的规矩,诗句是不白看的,先要拿出花钱来再看。”丁言志在腰里摸了半天,摸出二十个铜钱来,放在花梨桌上。聘娘大笑道:“你这个钱,只好送给仪征丰家巷的捞毛的,不要玷污了我的桌子!快些收了回去买烧饼吃罢!”这个故事中“才”与“情”都被消解掉了,变得那么不堪,无疑也是对才子佳人故事最辛辣的反讽。
小说还塑造了一个最为典型的具有“才子佳人”思想的季苇萧,按照第一部分所谈以“词语重复”的方式去认识人物形象,能索解到吴敬梓对这个人物的设定,“才子佳人”就是挂在他嘴边的重复词语。他在扬州停妻再娶,新房挂的对联是“清风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并对老姑爷说:“我们风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会合,一房两房,何足为奇!”[2]336自命风流可见一斑。他听杜慎卿说娶妾乃是无可奈何之举,颇为不解:“才子佳人,正宜及时行乐,先生怎反如此说?”又劝杜少卿纳妾,“何不娶一个标致如君,又有才情的,才子佳人,及时行乐?”[2]356此人颇像一本行走的才子佳人小说,到处宣扬这套自诩风流、及时行乐的人生观。
明清之际,才子佳人叙事和社会上才子佳人心理又有一些新的变化,那就是“才子佳人”中的男女之情,部分的发展为男男之情,男风甚行,并将其包装成风流文人“我辈钟情”的另一种模式。
第二十九回插入了一个有些莫名其妙的故事,那便是龙三大闹僧官,这个故事无头无尾,乍一看,搞不清楚作者写这个故事的用意何在。文中写僧官请客的那天,“那个人”龙三来了,头戴“纸剪的凤冠,身穿蓝布女褂,白布单裙,脚底下大底花鞋”——一身妇人打扮,还口口声声自称是僧官的太太。但僧官对他却不敢发火,搞得非常狼狈,黄小田评道:“说不出来的苦,又不敢说硬话,窘状如见。”[2]357小说对龙三和僧官到底什么关系,没有做任何交代。商伟分析这个插曲时说:“这似乎揭露了——尽管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他们之间隐秘的性关系,僧官拼命不让龙三说话只是加深了我们的怀疑。”[5]247并对这段故事的叙事手法进行了精彩的分析。但是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貌似无头无尾的影射“男风”的闹剧?
实际上这是为接下来杜慎卿故事做的铺垫。从时间上来说,紧接着这场闹剧的就是杜慎卿出场,有关杜慎卿的故事最为核心的三个情节分别是“江郡纳姬”“访友神乐观”“高会莫愁湖”(这三个情节直接构成回目的标题,通过“词语重复”强调了其重要性),其中“访友神乐观”又恰好是写杜慎卿的好“男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龙三的闹剧与“访友神乐观”的谐剧构成了重复。
作者通过很多细节暗示杜慎卿在众名士中的特殊性,比如他出场时穿的直裰是“莺背色的”,即那种浅黄中带微绿的双色,小说中其他的直裰全是单色,宝蓝、黑色、酱色等;还有他顾影徘徊的情态,吃块板鸭就呕吐起来的作态,所以韦四爷说他有些“姑娘气”。杜慎卿自己酒后吐露心曲,更是大谈“鄂君绣被”,称赞汉哀帝与董贤是“独得情之正”,感叹自己“缘悭分浅,遇不着一个知己”[2]357。季苇萧发觉此人已经着魔,所以才将五十来岁的老道士来霞士说成是一个美少年,骗杜慎卿去结交,闹了一场笑话。这样看来,杜慎卿说“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并非故作矫情之论,他可能真不喜欢女人。好男风,在明清士子中非常普遍,尤其是狎玩男旦更成为社会时尚,陈维崧与男旦徐紫云的情爱故事广为人知,受到众多文人的羡慕,见诸当时人的歌咏,对清代好男风的风气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杜慎卿的原型吴檠就曾经收藏过徐紫云的小照,并表达了对那段风流韵事的倾慕之情(5)其在收藏的《九青小照》上题写序跋和诗一首,对画中云郎做了描写,赞“洵尤物也”,并追慕陈维崧“风流放达,仿佛晋人之遗”“漫道钟情我辈痴,可怜作达文人态”。见张次溪辑《九青图咏》,《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998、999页。。不仅如此,莫愁湖高会排定“梨园榜”,这也是清末狎优文人最为热衷的行为,杜少卿评选“梨园榜”,可算清末各种评花谱、菊榜的先声了。所以,事实上写杜慎卿的三个情节,都是正面表现和侧面渲染他这种异样风流的。
关于男风还有一次叙事,出现在第四十二回,汤大爷去男旦葛来官家。这里也透漏出相隔如许之久的故事之间的隐秘联系,葛来官就是杜慎卿梨园榜中的第二名。故事写得同样比较隐晦,只有一句写两人对饮,“葛来官吃了几杯酒,红红的脸,在灯烛影里,擎着那纤纤玉手,只管劝汤大爷吃酒”。正在这时,外面一片嚷声,原来仆人大脚三把两人吃的螃蟹壳倒在了邻居周医生家门口,葛来官出门来还未开口,便招来周医生劈头盖脸的谩骂:“该把螃蟹壳倒在你门口,为甚么送在我家来?难道你上头两只眼睛也撑大了。”[2]501这场男性密友的聚会显得如此难堪,看不到一点旖旎风流的情致。
男风在明清时期如此盛行,很多文人都带有这样的癖好,《儒林外史》不能不写,但作者又不愿一贯干净的文词稍染邪污,所以对三个涉及男风的故事用了三种不同的手法:第一个实有其事,但无头无尾,是一闹剧;第二个杜慎卿实有其“情”,但事则虚渺,是一谐剧;第三个稍涉实际,却被邻居骂退,更加不尴不尬。吴敬梓的态度也就隐含其中了。
三、文本之间的重复:“风雅颂”与小说内在结构
关于《儒林外史》的结构,一直是众说纷纭的焦点话题。20世纪末,张锦池总结百年来《儒林外史》的结构研究有四大提法:“连环短篇说”“功名富贵说”“时间顺序说”“单体多彩说”。作者综合以上几家观点,又提出“时间顺序”暗线、“功名富贵”明线、“连环短篇”为情节结构外在特征的“纪传性结构形态”,这可算第五种[6]。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还在不断拓展,出现八股文法式结构、地域板块结构等多种。按照米勒重复理论的说法,“在各种情形下,都有这样一些重复,它们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这些因素包括:作者的精神或他的生活,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心理、社会或历史的真实情形,其他作家的其他作品,取自神话或传说中的过去的种种主题,作品中人物或他们祖先意味深长的往事,全书开场前的种种事件”[1]3。因此影响一部作品结构的因素是多样的,而且很可能是复合性的影响。比如说《儒林外史》的结构既受到史传文学的影响,《水浒传》等小说的影响,也受到吴敬梓根据自己现实生活不断调整写作内容和主旨所带来的影响等,当然也包括作者学术研究以及生成的其他文本的影响(这里指的是他的《诗经》研究及成果《文木山房诗说》)。
明清士子科举考试除了需要写八股文,还需专攻一经。吴敬梓专攻《诗经》,“少治《毛诗》”[7]141,“晚年说诗更鲜匹”[8]134,撰成《诗说》应是中晚年的事,在《儒林外史》创作时代已基本完成。他将自己研究《诗经》的宗旨和几则说《诗》的意见在《儒林外史》中发表出来,因此,《诗说》与《儒林外史》本身就形成了重复、互文的关系,其意义在于,首先通过“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晋诸贤所能笼络”(6)吴敬梓《尚书私学序》本是对江昱治《尚书》的评价,也是他自己的治经宗旨,《儒林外史》曾明确表白。见李汉秋、项东升《吴敬梓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18页。的“宗旨”,形容八股文士的孤陋、毫无学问根底,从而融入小说讽刺儒林学风的创作主旨;其次通过将《七子之母》《女曰鸡鸣》《溱洧》的解读写进小说,与小说相关情节主旨产生互文关系,比如《女曰鸡鸣》中表达“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的“修身、齐家”思想,与小说中庄绍光夫妇在玄武湖边优游岁月的情节相“重复”,生活态度和具体人物形象得到相互印证;再次,《诗说》中有些篇章,如《子衿》《简兮》等篇虽然没有出现在小说中,但其精神内涵深深契入了小说的主旨表达中。这不仅表明吴敬梓对《诗经》研究颇有心得也非常自信,更表明对《诗经》的理解和接受已融进了吴敬梓的生命意识和思想观念中,这无疑对《儒林外史》的内在结构形成深刻影响(7)因为对《诗经》的理解和接受融入个人生命意识和思想观念,吴敬梓的其他著作也受到深刻影响,比如词作“婉而多讽“(黄河《文本山房集序》,见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版,第137页);从不写“燕游花月,分题角胜”多应酬之作,所作“大抵皆纪事言怀,登临吊古、述往思来,百端交集,苟无关系者不作焉“(李本宣《文木山房集序》,见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版,第138页),郑志良新发现的《后新乐府》及已亡佚《乐府新题六篇》皆表明《诗经》对其诗作的影响。。
“风雅颂”“变风变雅”“美刺”是《诗经》及诗经学中至关重要的总论性理论问题,也是《毛诗》“以政教说诗”精神的核心所在,在这个根本层面,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时心系政教的宗旨与之相一致,从而形成了小说“风雅颂”式的内在结构。
“风”是采自民间的里巷歌谣,“雅者,正也”,是“中原正声”(8)梁启超说:“依我看,《小大雅》所合的音乐,当时谓之正声,故名曰《雅》……然则正声为什么叫做‘雅’呢?‘雅’与‘夏’古字相通……雅音即夏音,犹言中原正声云尔。”(《释四诗名义》)转引自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类似后代说戏曲中的“花雅”,既是从音乐角度来区分,也与内容的雅俗有一定关系。《诗大序》中说由于王道衰微、政教失范、礼义荒废,所以有了“变风变雅”,于是就有了“美刺”之分。关于何者为“正”、何者为“变”,汉儒常以国次、世次划分,文王成周时代制作礼乐,所以当时的风雅是“正”;后来世风浇薄,就成了变风变雅。吴敬梓在《诗说》中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吸纳前人一些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当据一诗而各言其孰为正,孰为变;不当以国次、世次拘也”,直接将正变的划分与每首诗具体内容联系起来,“可美者为正,可刺者为变”[9]491。“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大序》),是庙堂祭祀的乐舞,其内容是赞美、歌颂祖先的功德,自然就不会有正变、也不会有美刺之分,纯然是“美”。
《儒林外史》在文化意蕴层面(即其内在结构)与“风雅颂”是一致的,“风”来自民间,表现民间风俗人情,小说中大量涉及社会风俗的部分是“风”;代表“雅正”文化传统的文人群体的故事,就是“雅”。“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同样是吴敬梓认识当时社会、开始《儒林外史》写作的思想基础,因此,在小说中“风”“雅”两部分的笔法也是有美有刺的。比如“风”的部分,汶上镇、南海县、五河县的风俗写真,就基本用“刺”;写秦老爹、邹吉甫、匡太公、牛太公、卜太公、娄文焕、祁太公、甘露僧这些淳朴忠厚的长者以及他们之间或对别人真实无伪的温情,用“美”。作者在写“风”时,通过美刺强烈对比,实现“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的主旨追求。“雅”的部分,同样有正有变,有美有刺,如对士林中的各种追名逐利、道德沦丧现象用“刺”,对文人的诗意情怀、儒家风范用“美”。“颂”乃“美盛德之形容”,体现于小说对“礼乐兵农”理想及其实践者的描写中。
正如《诗说》中一再强调的“见美刺,以裨政教”[9]486,小说中的美刺也是为了回归儒家伦理道德和淳朴自然的社会风俗而服务的,体现了《诗谱序》“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温柔敦厚的诗人之旨。是出于公心而非私愤,“所忧于人心者深,彰阐之权,无假于万一,始于是书焉发之,以当木铎之振,非苟焉愤世嫉俗而已”[10]279,这也正是鲁迅所云“秉持公心,指擿时弊”同时将其与那些谴责小说区别开来的原因,儒家理想主义的“美刺”精神铸成了小说独特的文化品格。
“风雅颂”构成小说内在结构,同时也赋予小说叙事结构的基本框架。自第二回至第八回,主要写山东汶上、广东南海和高要等城镇的风俗民情,是“风”(虽然也出现了周范二进,但主要写他们未中科举时的乡间故事,张静斋、严家兄弟的故事回目中标明“乡绅”,主要也是写乡间风俗的)。自第八回下半段(代表名士的“斗方”一词首次出现)至第三十五回,是“雅”,主要是写文人群体的故事。其中也有小雅、大雅之别,以论其品格。其中第二十八回以前是“小雅”,以山人、斗方名士为主,“刺”多于“美”;第二十八回后季苇萧、杜慎卿先后出场,开始入“大雅”,表现的人物风貌和笔法都越来越雅正。第三十六回虞育德出场,至第四十回萧云仙故事的结束,书写“礼乐兵农”理想及其实践者的风貌,是“颂”。
第四十回以后皆是余波,余波又重复使用了“风雅颂”的叙事结构框架。大致说来,第四十回从沈琼枝的故事开始,是“风”;第四十八回自王玉辉的故事开始,至第五十四回是“雅”,写文人群体为主;第五十五回,“颂”。余波中“风雅颂”的重复,其中颇有深意:风俗越来越糟糕,雅部最后写丁言志找妓女评诗被羞辱斯文扫地,文脉断绝矣。最后的“颂”,赞美的是市井奇人,他们追求在个性自适的生活中聊以卒岁,重兴儒家礼乐的理想与那轮落日一样慢慢远去。
《诗说》有云:“窃意《小雅》中有近于风者,《周南》中有近于《雅》者,《豳》诗则风雅颂而有之,或古之太师聆音而知其孰为《风》,孰为《雅》,非章句之士拘于卷轴之谓也。”[9]487这也非常适用于对《儒林外史》“风雅颂”叙事结构的认识,在大体主干清晰的情况下,风、雅、颂三部分的叙事互有交叉、掺杂,这又使得作为浅层叙事结构框架的“风雅颂”,重新回到文化意蕴和内在结构之中,这个内在结构却是稳定的。正如吴敬梓说古之太师能聆音而知《风》《雅》一样,《儒林外史》内在的“风雅颂”旋律,也需要我们认真聆听。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花费的心血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从那些精心设计的细节、事件的重复中,或许我们得以窥见一二,同时,更令我们感叹其创作方法之新颖独特,艺术匠心之神龙莫测。去发现更多的文本内部的重复,文本之间的重复,为我们深入理解这部伟大作品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和视角,揭示出作品本身更为多元和复杂的面相。“文学的特征和它的奇妙之处在于,每部作品所具有的震撼读者心灵的魅力,这些都意味着文学能连续不断地打破批评家预备套在它头上的种种程式和理论。”[1]5《儒林外史》正是这样一部经典之作,因此也提供给人们多重阐释的可能,总是让人常读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