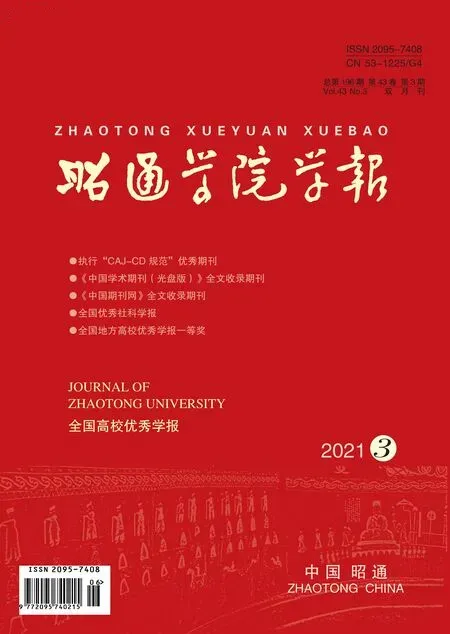孙世祥《神史》和杨恩智《普家河边》对比研究
吕 叶
(昭通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
孙世祥和杨恩智都是昭通本土的作家,一个60年代末出生于昭通巧家,一个七十年代末出生于昭通昭阳区。他们将笔端付诸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滇东北,对这片土地上贫困乡村的人和事进行了抒写和思考。
巧家县荞麦地发拉村属于高寒地带,孙世祥就出于这里一个普通而贫穷的农民家庭,2001年10月因肝硬化在昆明去世,时年32岁。生命戛然而止,他文学成就上不可预知的光芒以悲剧的形式搁浅了。但是他短暂生命中留下的那些他原本打算用很多年时光去打磨和修改的小说、诗歌等手稿,却“粗糙”地具有了特别的文学价值,那是孙世祥对现实的真实呈现,那是他生命的血和泪,那是一个时代滇东北某些地方苦难的缩影,那也是给予我们深刻思考,灵魂被撞疼的现实。所以他被称为“以命相搏的写作者”,这些在他手稿似的长篇小说《神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孙世祥在《神史》这部书中,引用了村里老人的一句话“昭通以前不叫昭通,叫乌蒙,‘既乌且蒙’,清朝的时候才更名昭通”。[1]而《神史》这本书就写了诸多既乌且蒙的事情。
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因素,这些身陷贫困的南京“大明帝国”的后裔们,祖祖辈辈靠放牧牛羊和种植洋芋、荞麦为生。相对闭塞的环境让他们从语言、习俗等方面保留着“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痕迹。这样的环境造就了孙世祥的孤傲、痛苦、绝望以及中国文人自古所拥有的心怀天下的赤诚。只是,他的命运和书中的主人公相似,一个又一个希望的升起、然悲剧又接踵而至,直到生命的逝去。
书中的主人公是孙天主。这个名字是作者最后改的。开始主人公叫孙福贵,代表着父母热切的期望,识得些许文字尤其是读了武则天的传记以后,他觉得武则天一个女人敢“则天”,而他一个男人却只是追求荣华富贵,他觉得这名字配不上他的宏伟理想,于是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孙天俦”(与天做朋友,虽然后来他的老师几乎没有人把它读对)。名字体现了他的人生追求,但是现实重重的打在他的脸上、心上。他所在家乡的贫穷就像深夜借着月光还在山上干活的“父亲”的铁锄挖在石头上那般的清冷和让人心疼。离开贫瘠的土地成了孙天俦奋斗的目标。后来不负众望考取了师范学校,那份荣光刹那间照亮了这个家庭。但是因为贫穷在学校里他经常挨饿,到处周借饭票,图书馆是他逃避饥饿的精神家园“去图书馆的路,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走”;后来师范毕业如愿当了乡村教师,虽然个人和家庭收入得到了一些改变,但是学校的不平事,学生的不争气,同事的鼠目寸光和欺凌侮辱、殴打,导致他远走广州、流浪街头,最后辗转反则凭借才华在昆明的报社谋得一职。但是天意弄人,因为弟弟中专录取被人冒名顶替,最后他只能天天“蹲守”省政府,“守得云开见月明”为弟弟争取了再上中专的机会。在农村的父母对他经济上的依靠,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的学费,尤其是他采访的稿件纵使主编读了都看得痛哭流涕但是依然被压下无法发表。这些“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再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不愿意向命运低头,他不愿意苟且于现实,他不愿意和天做朋友,他要做天的主人,于是,他把名字改成了孙天主。老天确实龙眼一开,他拼尽全力通过了第一届国家公务员的考试,顺利地抵达了首都。孙世祥没有实现的理想他通过他书中的主人公来帮他实现了。写到书中这个章节的时候,孙世祥的心灵是不是得到了一丝安慰?但是他知道理想终归太丰满,现实太骨感,所以孙天主的命运最后成了劫难。他在春节回乡的探亲的时候,因为村人的嫉妒,因为那些曾经欺负伤害他的人的害怕,嫉妒的火焰让村子里面第一个开得起车的司机头昏眼花,车开下了悬崖。一车人,一个村年轻的生命群体,无数个家庭的希望和牵挂,还有孙天主那经天纬地的抱负,戛然而止,万声叹息。更具讽刺的是人物的命运伴随着主人公名字的更改而起伏:孙富贵——孙天俦——孙天主,他的命运不是像名字那样变得更“伟岸”了,而是和名字相反被现实戳得更伤了。所以,掩卷思余,内心是深深的悲痛、压抑,是“落得大地一片白茫茫的”感慨,是书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既乌且蒙的无力感和无助感。
“以文学的、审美的方式反映正在发生的新时代,对作家来说,是个极大的考验。同时,火热的现实和身临其境的生活体验提供了大量崭新的文学素材,这些第一手资料是时代与生活的馈赠”[2]是的,作为一个作家同时也是扶贫干部,杨恩智的《普家河边》和孙世祥的《神史》一对比,时代差距感一目了然。毕竟“扶贫文学”几个字已经彰显了国家的政策。有了政策的扶持和倾斜,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才有无数的可能。《普家河边》这本书人物出场和这个村落大事小物都和扶贫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这是一个和孙世祥的《神史》不能同日而语的时代。“既乌且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时代的机遇给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照顾”,让他们看见了生活的期许和曙光。
《普家河边》以张德伟到医院病房看望扶贫干部李仁芬为开端,叙述了李仁芬在驻村工作的过程中由于道路颠簸,差点流产。顺着这个思路开启了张德伟为了让李仁芬安心静养,代替她下乡驻村扶贫的事情。文章难能可贵的是张德伟面对一地鸡毛的“家务”,艰难开口告诉妻子陈晓宇这个决定时,她没有大气凛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说“支持”,而是像极了人间烟火气息的我们:“星期五批复下来,星期一就要去报到,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这是你一个人的事情阿?为啥不和我商量,你想当官想疯了?”;“陈晓宇伸手抓起儿子说‘早点认得,还不如流掉的好。现在生了,你倒好,一溜烟走了,丢给我一个人。你说我咋带?你去也行,我们各负责一个,随你选’”。[3]真真实实的几句话倒出了二胎时代没有多余的钱请保姆,也没有老人帮忙带孩子的诸多无奈和万般辛苦。同时,也道出了多少扶贫干部在家庭和扶贫攻坚任务双重挤压下的不容易。但是,总得有人流汗、流泪、付出辛苦,才能换来万千人的幸福。这些付出平凡而坚韧。
终归是工作所需,责任使然,最后,张德伟还是以扶贫队长的身份火速进驻到了普家河。然后随着他工作的开展,通过作者的叙述,普家河作为中国扶贫点的一个缩影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普家河一些地段竟然还没有自来水,单寻找水源这个过程就翻山越岭,“那山蜿蜒着,像是断开的一座一座,又像是连着的一座,起伏着一直往后向上连绵而去”。水利局来搭建水管引来水源的艰难可想而知,何况上山的路还是狭窄的泥土路。另外,普家河可以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是稻谷、玉米、洋芋这些,但是生活在滇东北这块土地上的人清楚,这些农作物不仅产量不高而且市场价格低廉。所以普家河的主要经济支柱是烤烟种植。撇开文章涉及到的那些合同和现实的“黑幕”外,种植烤烟,尤其是产量高种植面积广的人家,收入确实比其他种植农户好得多。但是烤烟这种“敏感脆弱”植物几乎属于“望天吃饭”系列。如果不幸,一场冰雹足以把经济支柱烤烟打成灰烬。“百元户”变成“万元户”,还是“万元户”变成“百元户”除了取决于辛苦的农事付出还要看老天爷是否高兴。“一场白雨下来,一家人五六万七八万的损失,我们忙死忙活的,一场白雨,都白忙活了,一夜回到解放前”。[3]这些环境因素也为后面的异地搬迁奠定了基础。环境的艰辛在孙世祥的《神史》里面也异常凸显,因为发拉那片只能种荞麦,蔓菁,洋芋的土地,锄头下去挖在石头上的金属声和寒冷的气候让人绝望,以至于后来很多人逃离到思茅去开垦荒地寻求生存。而普家河,他们环境的艰难在政策的扶持下有了庇护和盼头,异地搬迁工程直接让他们的生活跨了一大步。
“精准扶贫是物质脱贫和精神扶助一起抓。不仅要解决物质贫困,也要解决导致物质贫困的思想文化根源,从而进行精神、文化扶贫。”[4]显而易见,物质和精神的贫穷不仅在《神史》中存在,在《普家河边》也比比皆是。普家河贫穷的显著因素之一就是环境。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有些人出生就在罗马”。正因为环境使然所以国家才提出了异地搬迁的扶贫政策,它也是《普家河》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作为政策的体现,它必然要在作品中进行阐释,书写政策落实的情况,遇见的阻力和扶贫的意义。但是这本书如果只是仅仅停留于此,那么它体现的无非就是政治的宣传品。这本书的文学价值和亮点海在于书中涉及到的人性问题。胡适说过“愚昧是一切落后的根源”。所以扶贫先扶“愚”。国家这些年来的政策一直在向教育倾斜。比如孩子是否上学这个问题,在今天的我们尤其是大城市的孩子而言是个没有必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它仿佛就是每个人生命的必经过程。但是,农村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农村,失学、辍学却依然严重。“控辍保学”成了国家新时期脱贫攻坚的一个重要政策,被大力宣扬和提倡。文化的匮乏,交通的闭塞,经济的落后,那些可怜又可叹的人们的眼神,还有那些吃了没有文化的亏却依然让“悲剧”重演的人们,触目惊心。所以可以想象张伟德和耿世兵等村干部去村子里面劝失学儿童重回校园的艰难。因为那些辍学孩子的父母没有意识到辍学也许会误了孩子一生。因为有些孩子怕学习,不喜欢学习,还有些人因为家庭贫苦甚至就因为贪恋成人世界打工短期可以换来金钱的诱惑,他们选择了辍学。小小年纪,远走他乡打工谋生,甚至还有些十多岁已为人父为人母了。他们不知道现在不吃一些学习的苦,可能后半生将吃更多的苦,将为今天的选择买单。那些我们在教室里说的诗和远方、精神家园,在普家河不仅贫瘠而且荒芜,甚至对于他们而言完全是天上月海底星,遥不可及。
而最可怕的是与经济和文化落后伴随而来的是愚昧,人性的沦丧。普家河村“招姑爷”上门的侯万发的行径体现了人性的沦丧和卑劣。他上门之前,自己已有两个姑娘和一个儿子,自己“单身”上门娶了已经去世的冯正伟的老婆。这种凑合的婚姻拉开了高家16岁女儿的人生悲剧。他不仅娶了高氏,还把高家女儿强奸了。“强奸了还不说,后来狗日的一直占着,只要有媒人来说冯正伟家那个姑娘,狗日的咋整都要把人家整走掉,甚至直接回绝说不给”很多次“侯万林还带着小姑娘到乡街子的小诊所去打胎”。这样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的事情竟然是高氏知道的。“开始那婆娘也闹过,但是她一闹,就被侯往死里打。打了不说,还把菜刀架在脖子上,扬言说只要她敢跟别人说,就要把她砍掉,还要把她那两个儿子也砍掉。被这样一威胁,那婆娘二话都不敢吭一声了”。[5]高家婆娘可能想找个伴侣为她挡风避雨,没有想到后来生活中的狂风暴雨就来自这个人,不仅毁灭了她婚姻的幸福更糟蹋了她亲生女儿的人生悲剧,若干年后,侯万发还把这个姑娘给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村子里面的人未尝没有心疼过那个女孩,未尝没有诅咒过侯万发那样的畜生,但是毕竟是别人家的事情,谁愿意多管闲事惹火上身?他们甚至很多年都没有报案的意识。而这些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对于当事人和她身边的很多人而言,或许麻木了。因为她亲生的母亲都妥协了何况其他人?生活的一地鸡毛压得他们无暇顾及其他的人生要义。在他们看来,这些无非是庸常人生的一次又一次经历,是命运的安排,是生活的日常。他们也从不不觉得一个无耻的人可能毁了另外一个人人生无数的可能。当把这一切归属于命运,无可逃避的命运时,就显得多么的麻木和残忍。
艰难的生存环境,小农经济根深蒂固的影响,知识文化的落后,不仅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更影响了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式。比如控辍保学,那些辍学的家长只一句话:“只要你劝得来就尽管去劝,我是无法的”,那些辍学的孩子说:“我就是不想上学,我要打工去了”;还有当村干部动员一些村民先搬到政府兴建的安置房时,张德伟说:“这些人还不是得寸进尺的。你拿个手指头给他,他恨不得连你手拐子都含了。有人还跟我说,是不是搬出去,一家人还给一个门市?你说咋可能嘛?他们也怪想得出来”;当村子里面修路的时候“不占着自己的呢,巴不得把路修成飞机场,一占着自己的呢,又巴不得让那路就像原来那肠子样”“更让人受不了的是,竟然有人听说要修路后,连夜连晚地在那种本来就撑出路面来的圈边砌了厕所,甚至砌了房子,还栽了树”。[3]“他不无忧虑地指出对扶贫利益的争夺已经改变了乡村百姓原本淳朴的人性人情,造成村民关系和乡村社会风气的恶化,造成了村庄的失衡,更为严峻、也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围绕扶贫利益引发的乡村生活风波和新的社会矛盾让精准扶贫陷入尴尬境地”。[5]而这种对利益争夺的失衡,在《神史》中更是比比皆是。资源的匮乏,经济水平、文化的滞后,常年困守闭塞村寨,眼界狭隘,促使这个群体可怜可悲也可叹,“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可以很好地形容某些村民的状态。但是人是自然环境导致的产物,又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环境不同自然人的境遇不同。国家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从输血到造血,到现在的异地搬迁,就是了解到改造有些贫瘠的自然环境之艰难,要付出极大代价,何不换个环境以相同的代价却可以极大地提高和改进这些人的生活,尤其是对他们下一代再下一代的影响更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意义,何乐而不为呢?我们期盼的除了脱贫致富,不是还更希望带来文明的进步和人性美好的期许吗?
《神史》和《普家河边》都深刻地阐释了人性,揭示了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但是,两本书的不同在于,《神史》的悲剧意蕴和对人性刻骨的描写让人痛彻心扉,“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作品中的人和事残酷地烙在了读者的脑海,压抑、愤懑、甚至绝望。作品看不到希望,这不符合我们习惯的对人间美好的期许,也不符合我们大团圆结局的传统模式。虽然它的自传体写实性质让你觉得如果不是作者早逝,它极大可能会是一部很经典的文学作品。很多作家书写底层,代表底层,而孙世祥,他就是底层,浸淫得太久,所以他对底层写得极其透彻,以至于书中的人和事掩卷之余还历历在目。而《普家河边》本身就是以扶贫文学的方式呈现的。它彰显的是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在贫困地区的实施情况,展现的是扶贫干部在这个过程的辛劳和付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村民在政策扶持下享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政策照顾和倾斜。尽管作品里面依然淋漓尽致地书写了普家河自然环境的落后,人们思维的局限,眼界的狭隘,人性的沦丧、贪欲和不思进取,当然还有淳朴。但是更多的是政策扶持给继续留守普家河的村民带来的发展变化,给异地搬迁的村民带来的对新生活的向往。虽然,结尾的时候作者没有理想化的大张旗鼓地去描绘“沸腾”,因为他知道“政策的外在力量与农民内生力量的结合才是实现脱贫的必由之路。”[4]但是那灯火通明的安置房和之前寂静也寂寞的山村一对比,你就能感受到那满满的希望所在。而这“希望”是《神史》写作的时代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