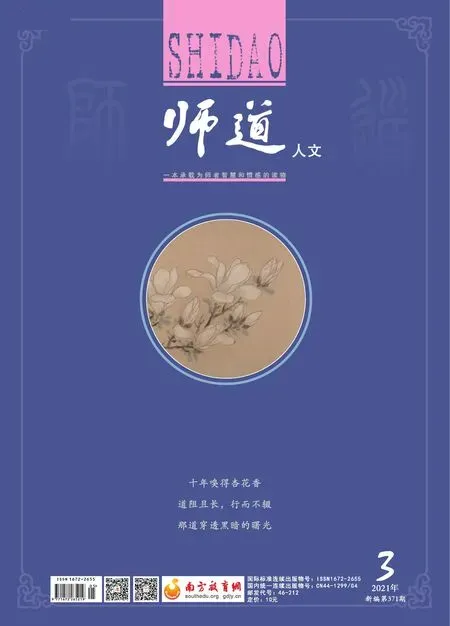做一个自生长的老师
刘娟娟
2009 年夏天, 我在珠海谋了一份教职, 成为一名中学教师。
7 月, 我独自拉着行李从成都来到这个滨海小城。 犹记得踏出车门的一瞬间, 生机勃勃的热烈扑面而来……转眼, 三千多个日夜如涤荡不息的海水, 倏忽而逝。
守一方讲台, 与一群青春少年相伴, 教书的日子既不会跌宕起伏, 也没有高光时刻, 似乎乏善可陈。 用 “平淡” 一词来形容, 真是再贴切妥当不过。
但细细咂摸平淡, 其间也有不易觉察的滋味, 也能听见拔节的声响。 从女孩到女人, 从迷茫困惑到主动承担, 从生涩仓皇到随心自适, 更自信、 更勇毅, 那个居住在身体里的灵魂悄然生长。 就如满园春草, 虽不见其长, 却日有所增。
相比于十年前的卑怯, 我更爱此刻拥有自生长能量的自己。
精心雕琢, 不荒废宝贵的自己
每次想起自己入职时上的 “第一课” 都感慨不已。
当时, 我刚入职一个多月。 上级教研部门要到学校调研, 作为新入职的教师, 我的课是首推。 接到通知后, 看着还懵懵懂懂没有一点儿教师模样的我, 同备课组的老师不禁为我捏了一把汗。 趁我不在办公室, 他们竟商量着要给我来一次“变形记”。
师父和我选定好文章后, 便塞给我一堆备课资料, 叮嘱我务必要认真研读教材, 认真备课; 还不忘叮嘱我一句, 别搞砸了, 一定要珍惜亮相的机会。 经过两天的日思夜想, 更多的其实是 “东拼西凑”,我拿出一份自己还算满意的教学设计给师父看, 心想总算准备停当,可以喘口气了。 哪知真正的历练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两天, 同备课组的老师拉着我去上课。 我在前面讲课,她们拿着本子在后面埋头笔记, 这种被全方位观摩的感觉, 现在想起来依然心有余悸。 下课了, 她们将课堂上呈现出的不足逐一记下来,细细讲给我听, 甚至演示给我看。然后再换一个班级上课, 如此往复, 我竟将整个年级的班级上了个遍。 初为人师的我木讷、 生涩、 笨拙, 如同演员, 在讲台上反复NG着自己的脚本。
那时, 同事们真是用心良苦。她们帮我记录下来的问题既有文本解读、 活动设计这一类的大问题,也有用什么样的语调提问和点评这样的小问题, 甚至具体到课堂上站立的角度、 看向学生的眼神、 伸向学生的手势这一类的细节。
当时不甚理解, 觉得课堂上的言谈举止这些无非都是小事, 实在无须这样费心雕琢, 出于对前辈的敬意, 还是一一受教。 但现在回想起来, 却常常感动不已, 非常感谢自己初登讲台的这 “第一课”, 无意间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打上底色。
后来, 有一次, 我接到执教《儒林外史》 课前导读课的任务。因为是面向全区的公开课, 我格外精心, 用了一个多月时间细读原著, 阅读了大量研究资料, 最后拿出了一份自己的教学设计。 教研员看了教案后, 却说匠心太重, 灵气不足, 顾虑太多, 没有了自己的个性。 她语重心长地告诫我: 做语文老师需要打破桎梏, 充分展现自己的原创力; 不能老师做久了, 就被格式化没了自己的个性。
后来, 那节课我彻底 “任性”了一次, 没有时间限制, 没有课堂形式的桎梏, 随心所欲地带着学生享受阅读的乐趣。 原来不一定要墨守成规, 不一定要因循守旧, 不一定要刻意表演, 自由随性才是课堂最好的节奏。 一节不凡的课, 我经受了一次思想震荡。
我真是足够幸运, 有这寻常却又宝贵的两课: 一节课教会我严谨自持, 一节课启迪我释放个性, 不拘一格。 细细想来, 每一天在课堂上的站立, 既可以沦为一场庸常,也可以升华为对自己的一次雕琢,心头对课堂便多了一份敬意; 只有足够精心, 才算不荒废宝贵的自己。
用书写为自己悄悄唱一首歌
说到写文章, 我对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杂志社的编辑心怀感激。
一天午后, 我忽然接到一通陌生电话, 原来, 是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杂志要刊用我的文章。 我激动不已, 原本以为投出的文章早已石沉大海, 哪知竟意外地收到了回音。 对于一个入职不久的老师, 这真是莫大的鼓励。
隔着电话, 杂志社的梁主编先是对文章的内容提了一些修改建议, 末了竟还帮我列出了一些文稿的规范, 诸如字体、 字号、 行距这一类的小问题, 仔细叮嘱我以后投稿前务必把这些小细节做到位。 虽然只是只言片语的提醒, 但在此后的写作中我对这些细节都会格外留心, 最终内化成自己的一种书写习惯。
此前我虽也常写一些教学手记, 但多是随心而为, 也只敢偷偷地投稿, 并未想过有朝一日竟能发表, 更不用说是在核心期刊上。 尽管只是一篇篇幅不长的教学观察,但这从0 到1 的跨越, 对我的专业成长却给予了莫大鼓舞, 更重要的是培植出行动的自信。 古人云:“世上事有难易乎? 为之, 则难者亦易也; 不为, 则易者亦难矣。”诚不欺我。
自信是一种心理机制, 会迁移与延续, 产生积极的连锁反应。 后来我将集体备课中出现的问题写成文章, 竟然也发表在了核心期刊上; 将工作中切实面对的问题整理后, 在市教研中心的课题申报中立了项。 写作让我慢慢多了一重观察和审视的视角, 也多了思考和整合的思维习惯。 自然也因此在看似繁琐无味的工作中发现了几分别样乐趣。
我也慢慢开始从最初级的书写开始, 写自己的教育观察, 班级故事, 学生成长手记, 凡有随想感悟, 皆以文记之。 起初不在意, 时日久了, 写作不经意间竟成了一种自我慰藉的方式。
有人借由写作超越庸常, 有人借由写作言说荒诞, 有人借由写作直面虚无, 写作于每个人的意义不尽相同。 但毋庸置疑, 写作是一种高级的精神生活, 使人不至于彻底匍匐于尘俗; 在书写中直面自我,强健自己的意志, 聚敛自我生长的勇气和能量。
在每个未拂晓的清晨, 我端坐于书桌前, 等待着天光大亮, 借由这份宁静开启一日的尘世之旅。 笔下的文字能够被人看见自然是好事, 更多时候我愿将它当作悄悄清唱给自己的歌。 一路轻吟低唱, 随心自适, 乐亦无穷矣!
对成长永远保有一份敬意
钱理群教授在 《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 中写道: “生命是美丽的, 培育生命的教育更是美丽的。活着, 真难, 真好。 孩子的成长,真难, 真好。 教育学生并和学生一起成长的老师, 真难, 真好!” 与孩子一起成长, 也许是一个教师职业成长的最大动力。
说到 “学生观” 这个话题, 我想起十年前曾经历过的一次投诉。对此我一直铭记于心。
临近中考, 我为同学们安排座位。 出于未经审慎的私心与偏见,我将几个学业落后、 升学无望的孩子集中安排在了教室后方。 未曾想到的是, 第二日全班同学拒绝自己的新位置, 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抗拒我的不公和粗暴。
那一天, 校长把我约到办公室, 我当即泪如雨下: 为什么我如此用心良苦却不被理解……那位温和的校长只是在一旁默默看着, 任我流泪, 任我哭诉。 经此一事, 我心中也经受了一次地震和断裂, 自己惯性思维中以为的 “爱” 与“好”, 多半只是蒙昧与偏见。 如果没有这次断裂, 我也许还会在后来的日子里为自己的 “良苦用心” 傲慢自得。
对于这次不光彩的小事, 我一直埋在心里轻易不再提及, 怯懦地怕暴露自己曾经的稚气与卑劣; 但却无法否认它的真实存在。 记忆太过长久深切, 以至于它无形间影响着我的学生观: 不自矜, 不功利,平和抱持, 把孩子当作一个鲜活生动的人, 对成长永远保有一份敬意。
后来,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痴迷于儿童心理学著作的阅读, 重新学习去认识儿童。 也因此, 面对这群青春少年成长中的困境、 挣扎, 我常默默提醒自己警惕成人惯性式的冷漠, 多一份尊重与理解。
马克思·范梅南说: “教育学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 一个真正的教师总会怀着一种莫大的热情去参与孩子的成长。 在不长的教育生涯中, 我留心于对学生个体成长的观察和记录, 也许和十年前心头经历的那次地震有莫大的关系。 如果要说这份 “迷恋” 对自己最大的益处, 大概就是在看似繁琐无力、虚浮功利的日常间埋下欣喜的伏笔, 还有给自己的内心贮蓄源源不断的轻灵力量。
那群孩子毕业后, 我们偶尔还会见面, 听他们聊自己读书时的糗事和工作中的困惑。 有一次, 听闻他们要组建自己的互助小组, 心中不禁感叹, 这样真好!
向不设限的人生致敬
我不仅迷恋学生的成长, 也迷恋自己的成长。
我从不把教书育人当作是对孩子们的牺牲与奉献, 因为我知道自己才是那个最大的受益者。 我不仅仅只是在完成一份劳作, 更是借由倾心于一业打磨历练自己, 开拓精神的边域。
曾经那个将教案详细列出每一句话才有底气上讲台的我, 现在可以自信地将自己的课堂公开给所有人听; 曾经那个会因为比赛失利而懊悔自责的我, 现在会对自己说没关系, 你已经尽力, 下次继续加油; 曾经那个讲课声音低微细弱的我, 现在可以不在意外界的目光随意歌唱; 曾经那个常常暗自神伤似乎永远走不出青春期的我, 现在却也可以随性而为自信自得; 甚至,曾经跑500 米就会气喘吁吁的我,现在却已经做好了去跑马拉松的准备……
30 岁以前, 为赋新词强说愁,哀叹自己如暮春的花, 要纷飞凋零; 30 岁以后才发现, 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不知道终将抵达何方,但人生辽阔无边, 一路前行总有新的风景。
每一日沉没在日常琐碎间、 劳作间。 然而我相信, 劳作是对我的馈赠, 是心灵的磨刀石。 热爱工作,在劳作中忘我投入, 谋一份心灵的安宁, 创造人生的可能和坚实。 善意、 信任、 严谨、 洒脱、 勇气、 执着、 沉思……这些闪亮的词时常浮现, 它们累聚着, 滋养和鼓舞我,为我积蓄活力与自生长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