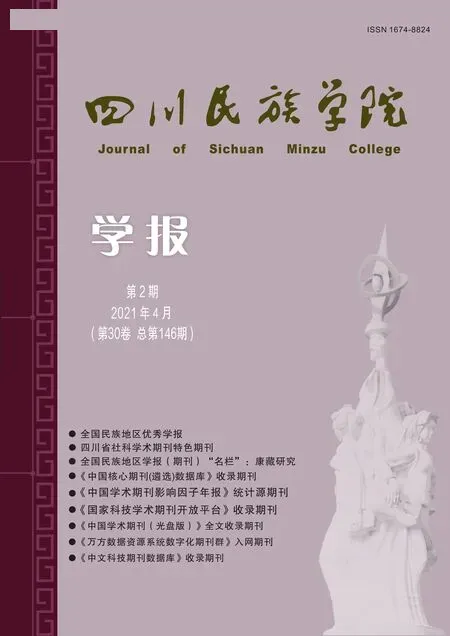国内《格萨尔》史诗传播研究综述
郑敏芳 崔红叶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 咸阳 712082)
被誉为东方“伊利亚特”的格萨(斯)尔史诗,既是族群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多民族民间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见证。格萨(斯)尔在多民族中传播,不仅是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各民族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的生动见证[1]。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要重视《格萨(斯)尔》史诗(1)1. 2011年,习近平参观西藏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图片和实物时,看到藏戏、史诗《格萨尔王》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他就充分肯定了对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工作。(习近平率中央代表团参观西藏和平解放60年成就展[EB/OL].[2011-07-18].https://www.chinanews.com/gn/3191069.shtml)2.2014年10月14日,习近平在《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全文)[EB/OL].[2014-10-15].http://culture.people.com.cn/c22219-25842812.html)3. 2018年3月20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中,习近平再次谈到“中国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EB/OL]. [2018-03-2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c_1122566452.htm)4.2019年7月15日,习近平在赤峰考察调研时,同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亲切交谈。(这件事,在习近平心中有多重[EB/OL].[2019-08-19].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c_1124894941.htm)的保护与传承。传播能够架起文化遗产与公众世代对话、交流的桥梁,所有与遗产价值有关的变化也都需要借助于某种传播手段来传递[2]2,因此,传播研究也是“格萨尔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当前,以“格萨尔传播”为主题的研究已有诸多成果出现,但依然存在一些研究的盲点和短板,本文在盘点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拟就国内《格萨尔》史诗传播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研究热点
美国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哈罗德·拉斯韦尔于1948年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who)、说什么(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说、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即“5W模式”[3]。十年后,布雷多克在《“拉斯韦尔公式”的扩展》一文中又增加了两个W,即:“在什么情况下(in which circumstance)、为了什么目的(in which aim)”,构成“7W模式”[4]。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格萨尔》,其传播除了具备“7W模式”中的各要素外,还有其独特的要素,即:“在什么地方(where)”“以何种面貌(in which form)” 、表现出“什么特征(what characteristics)”。但国内的《格萨尔》传播研究并不是对上述传播要素均做了探讨,而是只关注其中的某几个要素,研究热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播者研究
“7W模式”中的“who”指的是传播者。《格萨尔》说唱艺人既是史诗的创造者也是史诗的传播者,说唱艺人研究是史诗传播研究中关注最多的课题。国内史诗的传播者研究以陶阳的《琶杰的诗歌艺术》拉开序幕,此后格勒、杨恩洪、降边嘉措、旺秋、斯钦孟和等二十多位学者都对这一课题做了研究并发表成果。其中,杨恩洪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既有对艺人群体的宏观研究,也有对具有代表性的藏族、蒙古族、土族民间艺人的个案研究,她首次将艺人分为神授艺人、吟诵艺人、掘藏艺人、学识艺人( 听别人说学而识得的)、圆光艺人五个类别[5]。于静和王景迁在专著《〈格萨尔〉史诗当代传播研究》中沿袭了她的这一分类。此外,杨恩洪还试图探讨艺人的“神授”之谜。对这“神授”之谜做了探讨的学者还有何天慧、角巴东主、徐国琼、阎振中、顿珠和高宁等。降边嘉措、角巴东主等主要对说唱艺人这一群体进行了宏观研究。谈士杰关注的是青海省的艺人的说唱情况,向波探访了土族的说唱艺人,格日勒扎布概览了蒙古族的说唱艺人。甲央齐珍、陶阳、格来、旺秋、热噶和王国明等学者分别对艺人迪琼·巴吉、才智、琶杰、扎巴、桑珠、玉珠和王永福等做了个案研究。努木探讨了加强《格萨尔》说唱艺人工作的举措。张蕊以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了部分格萨尔说唱艺人的说唱情况。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丹曲发现了史诗的特殊传播者——寺庙。他通过对达那寺的实地调研发现,在史诗《格萨尔》的流传过程中,藏传佛教寺院及高僧大德发挥了传唱、收藏、撰写、研究、收集格萨尔文物等重要的作用[6]。
(二)传播内容研究
“7W模式”中的“what”指的是传播内容。《格萨尔》史诗传播内容指的是史诗在流传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族群、不同地区出现的不同版本。目前国内这一方面的研究多聚焦在四个方面:藏、蒙、土、普米、裕固等民族间流传的《格萨尔》史诗特征;某两个或多个民族或地区流传的史诗异同比较和关系分析;北京木刻版和某些地区或某位艺人演唱版本的异同分析;史诗传播内容的变化。齐木道吉分析了蒙文《格萨尔》的特征。杨恩洪、王兴先探讨了土族地区流传的《格萨尔王传》的内容。王军涛分析了裕固族《格萨尔》的故事类型。袁晓文和李锦详述了藏彝走廊上各民族间流传的《格萨尔》版本。乌力吉简要介绍了蒙藏《格萨尔》的异同。班马扎西将土族和藏族的《格萨尔》做了对比。李垣比较了普米族和藏族《格萨尔》的差异。王兴先分析了藏、土、裕固族中流传的《格萨尔》的不同。徐国琼的探讨了普米族《支萨·加布》与藏族《格萨尔》《昌·格萨尔》与《岭·格萨尔》及西藏的《格萨尔》与巴尔底斯坦《盖瑟尔》之间的关系。齐木道吉论述了青海《厄鲁特格斯尔》与《北京木刻本》的关系。斯钦巴图分析了青海蒙古口传《格斯尔》与北京木刻本《格斯尔》的异同。降边嘉措比较了扎巴老人说唱本与木刻本《天界篇》之间的差异。次仁平措在访谈中谈到了史诗传播内容的变化:当代新的艺人所表演的多是一些短的说唱,而传统的说唱艺人说唱的故事很长,内容十分庞杂多样,而且时间跨度大,说的内容也可能会出现前后人物不一致、故事情节衔接不连贯等问题[7]。
(三)传播方式研究
“7W模式”中的“In which channel”指的是传播方式。《格萨尔》史诗的传播方式主要体现在其传播渠道、传播工具上。《格萨尔》史诗流传千年,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学者在研究《格萨尔》史诗的传播时,都关注到其传播方式的变迁。袁爱中认为《格萨尔》史诗的传播贯穿口头传播时代、手抄本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直至网络传播时代:藏文字产生以前,史诗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民间;印刷术传入后,史诗开始借助印刷媒介传播,以“说唱”和“文本”的形式并存流传;进入电子传播、网络传播后史诗以“音视频”、艺人说唱、文本形式并存流传[8]。王治国指出,史诗的传播分为口头传承、书面文本传播和现代多元媒介传播三个阶段,其传播方式历经了从听觉主导的口头媒介经由视觉中心的印刷媒介再到综合延伸的电子媒介的变化过程[9]。此外,他还对史诗艺术改编与跨媒介传播进行二度艺术创作的可能性、可行性与运作机制进行了探讨[10];并提出传媒时代要发挥现代科技与视觉文化的优势,要想让《格萨尔》文化代代不息地传承与传播下去,就必须在史诗的传播渠道和方式上创新模式与方法,运用影视数码技术来进行《格萨尔》文化的保护与抢救[11]。张美认为虽然说唱艺人是传播主体,但因传播范围窄、传播方式形态单一、受众心理差异、“人亡歌息”等问题的出现,史诗的传播需要探寻多种途径。因此,她认为探索利用新媒体传播《格萨尔》史诗显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12]。索南措的《〈格萨尔王传〉传播方式对藏民族崇拜心理的影响》则探讨了《格萨尔王传》的传播方式对藏民族崇拜心理的影响。
(四)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既包括对译本的研究也包括对翻译理念、翻译策略、翻译活动等的研究,可以将它看作“7W模式”中的“what+ in which channel” 。翻译决定了《格萨尔》史诗以何种面貌出现在异质文化中,翻译史、翻译理念、翻译原则、已有版本的成因等都是它关注的话题。《格萨尔》的翻译研究远远晚于其翻译活动,学界普遍认为《格萨尔》在国外的翻译活动始于1771-1776年俄国旅行家帕拉莱斯将其蒙文本译为俄文本,国内的翻译活动始于什么时候,目前尚无定论[13],但普遍认为藏汉翻译的时间,始于1930年任乃强将《降伏妖魔》一章译为汉语。而对译介的研究则始于1981年,王沂暖梳理国内外《格萨尔》翻译简史[14]。此后,在宏观翻译及汉译研究方面:张积成论述了艺术性翻译原则,马进武论述了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岗·坚赞才让提出了翻译的原则及《格萨尔》翻译中不可丢失的文化层面。扎西东珠论述了《格萨尔》的文学翻译研究问题及翻译原则等。降边嘉措论述了《格萨尔》翻译面临的困难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要将《格萨尔》的翻译提高到文学翻译的高度[15]。平措提出《格萨尔》汉译,应以达意、传神、措辞通顺自然、读者反映相似等为译文标准[16]。外译研究方面的成果有:王治国探讨了《格萨尔》翻译的学科定位、英语世界《格萨尔》史诗的接受语境、翻译现象、翻译策略等,重点关注了道格拉斯·潘尼克译本、葛浩文译本和达维·尼尔译本。弋睿仙等分析了艾达·泽特林译本,对其中的 “去史诗化”现象进行了阐发。邵璐以阿来小说《格萨尔王》中佛教用语英译为例,运用文体分析法对译者认知进行探索。王景迁、拉姆卓嘎、臧学运、张宁等则从文化传播角度阐述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原则和策略。杨艳华分析了译本的质量,殷培贤探讨了英译的理路、臧学运还提及了史诗的英译史。陈琪和赵蕤梳理了《格萨尔》在日本的译介研究情况。张晓阐述了《格萨尔》译介模式构建中应该注意的因素。
(五)传播形态研究
“7W模式”中并未包括“in which form”,即传播形态,但《格萨尔》史诗的传播中体现出这一独特的传播要素。《格萨尔》史诗在流传过程中,除了口传史诗形态外,不断有新的形态出现,史诗的传播形态自然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徐国琼在《〈格萨尔〉考察纪实》中的《格萨尔唐喀与画像》中,介绍了他所见到的六种不同类型的格萨尔图像;在《别墅里的格萨尔壁画》中,介绍了在西藏昌都寺活佛希哇拉的别墅中所见到的一幅巨幅格萨尔壁画;并在《记邓柯·吉苏雅的“格萨尔神庙”》中,对格萨尔王诞生地林葱土司执政时期,修建于 1790 年的“格萨尔神庙”内的壁画作了详细的介绍。杨嘉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致力于《格 萨(斯)尔》图像文化研究,成果颇丰(2)论文有《松格嘛呢——格萨尔的寄魂城》 《石渠格萨尔文化探索之旅》 《格萨尔造型文化论纲》《格萨尔图像艺术的新开拓》《格萨尔图像的基本类型》《〈 格萨尔千幅唐卡〉绘制纪实》 《关于英雄史诗主人公岭 · 格萨尔 是否有原 的讨论》《一部展 示伟大史诗 〈 格萨尔 〉的精美画卷——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唐卡述评》。出版的专著为《琉璃刻卷 ——丹巴莫斯卡 〈格萨尔〉岭国人物石刻谱系》《雪域骄子岭·格萨(斯 )尔的故乡》《西藏格萨尔图像艺术欣赏》(上、下)。。降边嘉措等在2003年出版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唐卡》,此后索朗格列、青措、文德等及四川博物院和四川大学博物馆也加入《格萨尔》唐卡研究中来。杨勇研究了唐卡形态的格萨尔文化品牌传播及其衍生品开发。吴结评和陈历卫分析了英语世界的《格萨尔》唐卡传播与传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索南卓玛、曹娅丽致力于藏戏形态的《格萨尔》史诗研究。谭春艳论述了色达格萨尔藏戏在传承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探讨了其对当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重要意义。于静和王景迁探讨了新时代《格萨尔》的新传播形态。金石和彭敏指出《格萨尔》史诗有多种传播形态,包括文本类、影视类、曲艺类、其他衍生品类以及传统说唱类。丹珍草认为,传唱千年的《格萨尔》史诗,除了民间艺人的口头说唱和各种版本的书面文本并存外,还有格萨尔藏戏、格萨尔唐卡、格萨尔音乐、格萨尔石刻、格萨尔“朵日玛”、格萨尔漫画、格萨尔彩塑酥油花等等[17],并研究了当代格萨尔壁画“图式”表述。杨恩洪谈到了相声形态的《格萨尔》。卡先也对制作《格萨尔》动画片可行性及其意义进行了探究。甄卓英指出史诗网络传播中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六)传播区域研究
“7W模式”中也不包括“where”(传播区域)。但《格萨尔》的传播区域是《格萨尔》传播研究中的重要因素,因为传播区域研究不仅可以勾勒出《格萨尔》的传播轨迹,还可反映出《格萨尔》流传地区各民族交往交融的情况。《格萨尔》史诗由产生地向四周辐射,学界用“三个九”(3)《格萨尔》学界用“三个九”来概括其流传的广泛性。“《格萨尔》流布于中国、蒙古国、俄罗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不丹、锡金环‘世界屋脊’九个国家的藏族后裔、蒙古族和其他民族当中,以及国内四川、云南、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辽宁、新疆九个省区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普米族、纳西族、白族、傈僳族九个民族和摩梭人当中”(参见:格萨尔学刊[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161)。来概括其流传地域的广泛性。因为各地的传播情况不尽相同,因此史诗的传播地域也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课题之一。域内传播方面,杨恩洪认为,史诗的流传是以德格、邓柯为中心的青海、西藏、四川三省交界处的康区为发源地,向四周呈放射状传播,距离这一发源地越近,史诗流传则广泛,距离越远则反之[18]。此外,她也注意到新时期史诗传播环境的变化:从过去比较偏远的传统艺人说唱的环境逐渐开始城镇化,到人集中的地方[19]。谢继胜认为史诗所涉及的地区几乎全部是游牧草原地区。史诗流传在今天西藏自治区西北部和北部、四川省西南部、西部,青海全境,新疆东南边缘地带,甘肃西南部,河西走廊地区也被史诗渗透放射到蒙古地区;出境则流传到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20]。韩喜玉认为从分布的格局上看,《格萨尔》的流传有若干个点, 四条线和两个面[21]。索南措认为今天的格萨尔文化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流传区域。一是以三江源地区为主的 “核心流传区域”,另一个是后来随着文化和商业的来往,格萨尔文化逐渐辐射和流传到非牧业地区[22]。安惠娟的《近30多年来国内裕固族〈格萨尔〉研究综述》梳理了近30多年来国内裕固族《格萨尔》研究状况。王艳的《跨族群文化共存——《格萨尔》史诗的多民族传播和比较》研究了《格萨尔》史诗跨民族传播的情况,并探讨了《格萨尔》史诗多民族传播中的文化共存;姚慧的《〈格萨(斯)尔〉史诗跨民族传播的音乐建构——以扎巴老人,琶杰,王永福说唱的“霍尔之篇”为例》研究的是跨民族传播中的音乐建构。域外传播研究方面,王宏印和王治国勾勒出了《格萨尔》从藏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和蒙古族)再走向世界的翻译传播认知地图。
(七)传播特征研究
时代、地域、媒介等不同,《格萨尔》史诗的传播呈现出不同的传播特征,即“what characteristics”,学者们对这一领域也做了探讨。袁爱中和杨静分析了不同媒介形态下《格萨尔王传》史诗传播的特点。李连荣探讨了史诗在西藏南北的传播存在的差异,认为随着西藏南北生产生活模式的明显差异,演唱形式的《格萨尔》史诗只流传和分布在北部牧区地带,而南部农区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则很少有史诗的演唱形式[23]。丹曲从国内外研究现状、地理位置和地域文化等方面探讨了《格萨尔》在德格地区的传播特征。韩喜玉认为《格萨尔》传播过程中,具有与宗教信仰交织缠绕、众多遗物遗迹印证、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和学科体系以及有效利用大众媒介的传播特征[24]。张诺增尕玛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史诗《格萨尔》在海西地区的传播特征为:①地域性。其大多数风物遗迹和民间传说均与《霍岭大战》相关;②本土化。蒙藏杂居地区《格萨尔》的传播与变异,《格萨尔》传入蒙古族之后,在艺人的创作、改编下,并吸收和融入了本民族及其周边民族的民间故事,使史诗印上了本民族文化的印记;③滞后性。缺乏利用大众媒体带动格萨尔文化发展[25]。杨恩洪和次仁平措均在访谈中谈到,传统的说唱艺人一般都是到老百姓的帐篷里去说唱,现代的说唱艺人很多都是在说唱厅里给大家说唱,或者表演给观众欣赏。
(八)其他
韩喜玉阐释了藏族《格萨尔》外向传播原因,对“在什么情况下(in which circumstance)”作了初步阐释;刘新利则关注《格萨尔》史诗的传播与保护。张美分析了新媒体语境下史诗的传播效果,是唯一关注“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的研究成果。臧学运也在书评中谈到史诗的对外翻译传播及其拓展,王倩从翻译出版角度论及格萨尔的传播。
二、存在问题
虽然上述成果均从不同方面对《格萨尔》史诗的传播进行阐释,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史诗研究的发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传播目的、传播对象、传播者及传播内容研究均存在盲点。迄今,传播目的(in which aim)研究尚无成果出现。传播对象(to whom)研究方面仅有于静和王景迁提到了新时代《格萨尔》史诗受众的变化。传播者的研究局限在说唱艺人上,仅有一篇文章关注到艺人以外的传播者,而且艺人研究中缺乏对新生代艺人的研究。传播内容主要集中在关注藏、蒙、土、裕固等民族间的传播内容上,其他民族的《格萨尔》传播内容关注几近空白;现有的传播内容研究多为个案研究,缺乏对史诗现有全部版本的宏观研究。对传播效果的研究也较为匮乏,当然,传播效果本身的受制因素较多可能也是学者们很少研究这一课题的原因之一。
其次,缺乏文化环境变迁对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因素的影响的研究。史诗流传千年,文化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及当前的文化语境对史诗的传播内容及传播方式等会产生什么影响?面对这些影响,史诗何去何从?均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三,对史诗传播地域关注不均衡。关注域内传播研究的成果较多,而关注域外传播研究的较少。域内研究方面,大部分学者的关注点多集中在青海、西藏、内蒙古和藏彝走廊上,对其他地区的传播情况关注较少。《格萨尔》研究发展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格萨尔王故事》被选入大中小学课本后(4)《格萨尔王的故事》被选入S版教材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下册第二课。《格萨尔王全传》(节选)被选入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第四单元。,其传播地域远远超出原来的“三个九”地区,但目前的研究还局限在其产生地及周边,甚至对“三个九”里的一些地方的研究也不充分。而域外的传播研究,大多集中在英语国家,其他国家的传播情况只是学者们在陈述《格萨尔》的流传地域时提到一些国家和地区名,但这些国家及地区的《格萨尔》呈现什么面貌,传播方式有什么特点等,目前尚无研究。
第四,对非英语国家的史诗翻译关注不足。目前的翻译研究大多集中在《格萨尔》的汉译、英译及英语国家的接受语境等研究方面,但对于藏学研究处于世界前列的俄罗斯、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的《格萨尔》史诗的译介,除了提及早期的译介情况、几个典型的史诗研究者及其成果外,其他方面鲜少论及。
第五,传播方式、传播形态和传播特征研究视角单一。传播方式、传播形态和传播特征的研究较为成熟,但多名学者的视角基本一致,缺乏新的研究角度。
三、未来研究趋势
《格萨尔》史诗是人类口头艺术的杰出代表。虽然其传播研究还存在上述不足,但这些不足将会成为《格萨尔》未来研究的增长点。未来的《格萨尔》史诗研究将呈现以下特征:
首先,史诗传播目的研究会从无到有;传播者、传播内容研究会产生新变化;宏观研究也将问世。由于当前有关传播目的研究成果较为匮乏,未来将会有探讨史诗传播目的的成果问世。而新时代史诗传播受众的变化依然会是史诗传播研究关注的课题之一。随着史诗传播者身份的多样化,未来的史诗传播者研究可能会出现以史诗研究者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传播内容方面,藏、蒙、土、裕固等民族外的其他民族间的史诗传播也将会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史诗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必将促使以史诗现有全部版本为研究对象的宏观研究出现。
其次,文化环境的变迁对史诗传播的影响将会成为未来研究迫切需要关注的课题。文化环境的变迁是史诗传播研究中恒久弥新的课题,文化环境的变迁对史诗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文化环境的变迁对史诗传播的影响也会成为未来史诗传播研究需要关注的课题。
第三,史诗传播地域研究在原有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向周边扩展。“三个九”里的地区和国家是史诗流传较为广泛的区域,但随着史诗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史诗将会传播到更远更广阔的天地,同时“三个九”里的史诗传播也会呈现出新的特征。因此未来史诗传播地域研究方面,“三个九”依然会是研究的重点,但也会出现以“三个九”以外地域的《格萨尔》传播情况为研究对象的成果。
第四,译介研究会进一步深化。《格萨尔》史诗各语种的翻译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史诗的传播,但以往的研究中,对史诗的翻译研究关注不足。未来,西藏周边及藏学研究较为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的《格萨尔》翻译史、翻译理念、流传版本等研究也将是《格萨尔》传播研究的新增长点。
最后,传播方式、传播形态和传播特征也会出现新的研究视角。随着史诗传播研究的深入,从新的视角探讨《格萨尔》的传播方式、传播形态和传播特征将是未来这些研究的必由之路。
四、 结语
《格萨尔》史诗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史诗惩恶扬善、弘扬真善美的主题,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对人们的生活有着积极地意义。史诗的传播研究不仅能促进格萨尔学的学科发展,而且能推动藏族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虽然目前《格萨尔》史诗在国内的传播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国多家科研院所及高校学者也都勠力同心、砥砺奋进,奋战在《格萨尔》史诗研究的最前沿,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格萨尔》的传播研究必将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又会进一步促进了史诗的流传,未来《格萨尔》史诗必将“支芭盛茂满天空,根儿蔓延遍大地”,必将造福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