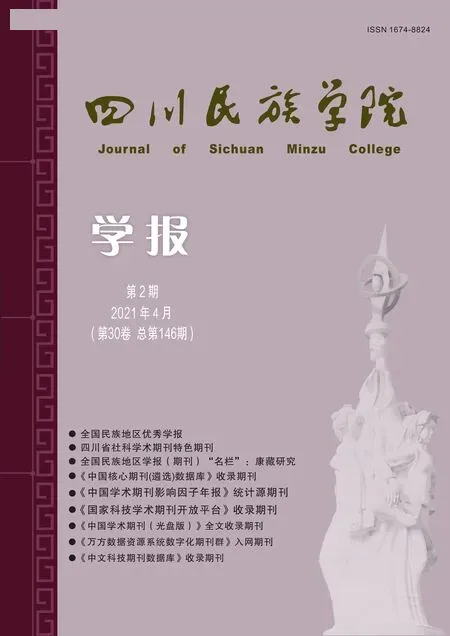试论二十世纪上半叶水族诗歌的忧患意识
——以潘一志的《浪游集》和《归农集》为例
潘光繁
(贵州省民族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04)
水族的书面文学起步较晚,1855年前后,清末水族秀才潘文秀创作的《一两五有序》成了水族书面文学的滥觞之作,潘文秀这首《一两五有序》古风诗饱含的忧患意识为水族书面文学的创作方向开辟了新的道路。二十世纪上半叶,水族诗人潘一志继承了其祖父潘文秀诗歌创作的民本思想,创作了大量诗作,他勾勒出贵州广阔的现实社会,书写了底层百姓呼声。潘一志的《浪游集》和《归农集》,是他一生中思想高度和艺术成就最高的两部诗集。“《浪游集》记写的是作者从1929年至1946年之间的生活轨迹,凸显出旧中国那一段苦难的历史。”[1]1“《归农集》则以清高的意境和忧患的意识,展示了潘一志1946年至1949年避世隐居,办农林场的苦与乐。”[1]1《浪游集》和《归农集》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水族地区现存下来的仅有的两部诗集,这两部诗集具备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成就,使得潘一志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水族文学史上代表诗人之一。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水族诗歌创作的重要诗人,潘一志以诗人的视觉,用诗歌淋漓尽致地呈现了贵州的社会现实,折射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他结合自身所见所闻,以秉笔直抒胸中块垒的吟咏方式留下大量诗作,导致他的诗歌亦诗亦史,散发出忧国忧民的传统士大夫精神,饱含着诗人深刻而又强烈的忧患意识。
一、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担忧
出生于1899年的潘一志,他的家庭是水族地区著名的教育世家。潘一志三岁时,就开始接受其祖父潘文秀的启蒙教育,后就读于由其父潘树勋开设的梅山学馆。1918年,时年十九岁的潘一志凭借深厚的旧学功底考入贵州省都匀十县合立中学(四年制文科),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22年毕业,随后开始步入社会,先后在政界、军界、教育界任职。1946 年,潘一志放弃贵州省毕节专署秘书及科长职务,到贵州省荔波县城北十五里外,一个名叫擦耳岩的大山深处隐居,并开荒种植,兴办农林场,以求自给自足。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潘一志,幼承家学,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水族地区著名的文人,耳濡目染中,从小就得到了很好的文学艺术熏陶,为日后诗歌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和文字基础。在拥有深厚旧学功底的基础之上,他又接受了长达四年的新式教育,两种教育碰撞之后,在潘一志那里得到了汇合和交融,这使得诗人在诗歌创作上,形成了意蕴悠长的艺术风格。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潘一志,历经社会各种历练之后,写出了或深沉或慷慨或激昂或悲壮的诗歌,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水族诗歌的底色注入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指的是对国家民族兴亡和人间黎民疾苦的一种持续担忧和密切关注。潘一志的《浪游集》和《归农集》,字里行间充盈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和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使得潘一志的这两部诗集,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具有了永恒的生命力。潘一志诗歌深沉的忧患意识,与他出身的家庭背景有着极深的渊源。潘一志出身于书香门第,这是一个数代都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且受儒家影响极深的水族家庭。在中国历史上,“儒学在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从内在心性、外在言行、价值观念上形成了一整套准则。”[2]儒家的人生理念,信奉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是儒家的终极目标。儒家的忧患意识,常常表现为对国家社稷前途安危的关切以及对黎民百姓生命苦痛的悲悯上,忧患意识往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高度地融为一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潘一志,内心深处产生了救世救民的人生使命感。尽管他并不是国家政权的执掌者,但这并不影响他以国家为己任的精神追求,儒家的灵魂和思想深处中最为积极的因素也正是这种积极进取、又敢于担当的精神,这是潘一志从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到的精神力量,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他思想的底色,在后来的创作中,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形成了潘一志诗歌创作的主基调。
潘一志关心国家大事,时刻关注国家的盛衰与兴亡,对祖国的热爱及其前途和命运的担忧,使得他的诗歌渗透着一股连绵不绝、强烈的爱国热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境内军阀混战,烽烟四起。1929年,滇、黔军阀战争爆发,诗人从兴仁返回贵阳的途中,时值二十五军与四十三军为争夺花江河(即贵州黔西南境内的北盘江)阵地而相互混战,又在八轮桥相持,对峙扫射。面对死伤无数、尸横遍野、腥气熏天的惨烈战场,潘一志忧心忡忡,他挥笔写下数首记叙战事场面的诗篇,其中的《过花江河》和《上关索岭》这两首七律表现出来的忧虑之情尤为激烈。国内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痛使诗人心中最为悲愤,从诗中可以看出他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深深忧虑。
过花江河
漫天烽火起干戈,踏破花江战垒多。
血染悬崖疑赤壁,腥腾浊浪拟黄河。
铁桥练断横波渡,鸟道云封叱驭过。
慢说巉岩天堑险,关津有道入牂牁。
“漫天烽火起干戈,踏破花江战垒多”,极言国内军阀混战的无休无止和规模之大、波及范围之广;“血染悬崖疑赤壁,腥腾浊浪拟黄河”,是对军阀战争场面的描写,诗人并没有直观地加以描绘,而是巧妙地以“疑赤壁”“拟黄河”来对“血染悬崖”“腥腾浊浪”进行对比,让读者读到这两句诗时,能情不自禁地想起历史上烽火连天的赤壁之战和浊浪排空的黄河之水。诗人引古入今,通过古今对比,来为读者讲述军阀混战场面的惨烈和血腥。潘一志的这首诗直接揭露了军阀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和连年混战,给黎民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诗人把矛头指向军阀,从灵魂深处迸发出激烈的抗议,充分表达了诗人的愤怒之情。这首七律具有深刻的忧国忧民思想和尖锐的批判意识,这和杜甫《兵车行》中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关索岭
快步连登造极巅,得从关岭上云间。
一声长啸惊天外,万叠层峰拜膝前。
放眼频观空宇宙,惊心犹未静烽烟。
英雄逐鹿谁先得,战垒纵横白骨悬。
潘一志的《上关索岭》,首联极力描写贵州高原呈现出来的莽莽的崇山峻岭,关岭高峰耸入云天。登高望远之后,诗人以“一声长啸惊天外,万叠层峰拜膝前”之句,让颔联道出了眼前气势恢宏之景,颇有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气势。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忧国之思即纷至沓来,“放眼频观空宇宙,惊心犹未静烽烟”;颈联则表达出诗人对内战不息导致局势动荡的无比担忧。对贵州高原壮丽景色和国内军阀混战不休进行了深刻的描绘,两相对比,作者对壮丽河山上演的内部混战,极为悲愤;作为尾联,诗人再以“英雄逐鹿谁先得,战垒纵横白骨悬”来结束全诗,这和杜甫《兵车行》中那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该是何等的相似,在情景交融和古今交汇中,这首七律的思想和艺术被诗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间散发出来的气息,无一不流淌着诗人浓厚的忧国情怀。
潘一志有着数次从军,欲求报国的经历,1933年秋,诗人在驻扎于贵州省绥阳县的国民党二十五军教导师第二营,任营部编修。这支军队的状况仍然让胸怀报国思想的潘一志感到深深的失望。“作为正规军,本该保民平安,可是为冒功邀赏,部队常乱抓百姓充匪骗赏。长官的滥杀无辜,给地方造成的戕害,胜过于杀人越货的土匪,这是潘一志所无法容忍的。”[1]59而在此前一年的1932年,中国东北全境已全部沦陷于日本之手,这时,诗人报国无门的痛苦和对国土沦陷的悲愤,相互交织,表达了他忧国忧民和感时伤怀的焦急心态,以《正安军次杂感》(其二)为例。
《正安军次杂感》(其二)
投笔从军古播州,盾头磨墨又何求。
十年校务惭尸位,千里乡思作梦游。
知己感恩谁是鲍,登楼作赋慨依刘。
不堪翘首望东北,国是萦怀系杞忧。
报国无门的失落,功业未成的悲伤,备尝辛酸的委屈,历经坎坷的磨难,凡事种种,皆萦绕于胸。此时诗人悲痛欲绝,在兵荒马乱、人人自危之时,潘一志仍抱着一颗报国的赤子之心为国家领土的沦陷而悲戚。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其二)中为国土沦陷这样写:“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二十世纪上半叶面对国土沦陷,作为诗人的潘一志也吟咏出“不堪翘首望东北,国是萦怀系杞忧”的诗句,古往今来,饱受儒家思想影响、心怀忧患意识的诗人,在面对国土沦丧之时,抱有的强烈哀恸之情,如出一辙,尽管时过境迁,今之读来,依然让人为之动容。在潘一志的古风诗《游黔灵山》中,多次出现诗人对国家前途和命运深切忧虑与关切的诗句。诸如:“渺渺兮余怀,鱼烂忧家国”“莽莽兮神州,割据势分裂”“誓拋我头颅,誓洒我热血”“不为名利争,牺牲去杀贼”“不作亡国奴,是鬼亦壮烈”“潦倒虽半生,壮志未衰歇”“为国求生存,何复太消极”等等,忧国之心,溢于言表。此外在诗人的《浪游集》中,忧国之句,亦不胜枚举。诸如:“无端倭寇犯神州,怪雨盲风无限愁”“铁血不忘期有日,与君慷慨赋同仇”(《送别》其二 七律)“横眉奋起扫愁魔,顾影中原感慨多”(《题像》七绝)“漫道长安寻乐处,萦怀家国几时休”(《南明河畔有感》七律)“匹夫原有责,天坠曾忧杞”(《感怀寄友人》古风)“漫天烽火慨夷侵,回首中原白感生”“报国几时酬壮志,重洋直渡捣东京”(《重游榕江五榕山有感》其三 七绝)“家国萦怀感,愁肠泪欲煎”“倭焰今方炽,金瓯缺未全”(《白发感》五律)“烽火惊边患,莼鲈思故乡”(《台江得胜关留别》五律)“国难正严重,努力奋前程”“此生已许国,台水可盟心”(《台江桥惜别》古风)“国事凭谁诉,江涛日夜鸣”(《都匀大桥远眺》五绝)“战火漫天前史空,黔南遍地血飞红”“只余焦土空遗憾,国破家亡感慨同”(《一九四四年冬日寇窜扰黔南五县创巨痛深 有感步陈某原韵》其一 七律)“何时厌乱天心转,举世和平庆大同”(《一九四四年冬日寇窜扰黔南五县创巨痛深 有感步陈某原韵》其二 七律)“关怀国是心如结,轸念民生志未酬”(《由榕江赴独山 船中有感》七律)以及《归农集》中的“触目田园寥落尽,伤心家国乱离频”(《步〈 寄怀〉》原韵其四 七律)“炼石徒劳终莫补,移山有志亦虚过”“翘头问天天不语,怎将壮志付蹉跎”(《又倒次前韵》七律)等等,无一不体现出诗人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深切关注与持续忧虑。
二、对黎民疾苦和遭遇的悲悯
潘一志诗歌忧患意识除了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担忧之外,其诗歌另一个的重要表现则是对黎民疾苦和遭遇的悲悯。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以民为本是儒家德治的思想基础,仁者爱人更是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核心思想。正因为“以民为本”和“仁者爱人”是儒家治国的核心价值所在,这使得古往今来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诗人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往往是一种范围广阔的天下意识,如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于谦的“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郑燮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等等。
潘一志诗歌对黎民疾苦和遭遇的悲悯,其根源除了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渊源就是他的家世背景。潘一志的祖父潘文秀本身就是一位同情底层百姓、关注民间疾苦的诗人,他著有的《松亭诗稿》,虽然已经散佚,但其写的七言古诗《一两五有序》,却成了水族书面文学的滥觞之作。“该诗用‘赋’的手法,将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以第一人称直接描绘、抒发所见、所闻、所感,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封建官府穷凶极恶地催逼赋税,水族穷苦百姓被迫卖儿鬻女、流离失所的极其黑暗的社会现实。”[3]潘文秀在诗中描绘封建时代水族底层民众的“披星戴月田亩间,手胝足胼不惰寙”和白居易在《卖炭翁》描写烧炭老人劳作场面的“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何其相似。描绘吏役凶残的诗句“开征过了十五天,吏役登门猛如虎”,这又和杜甫的“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如出一辙。面对黎民百姓“剜肉难医眼前疮,余谷变卖倒篝篓”的无奈和“更差吏役辛苦钱,哀求不许复震怒”的哀求,吏役不但不予以同情,反而变本加厉,面对饥寒交迫的穷苦黎民,凶神恶煞的吏役采取的是“铁锁套颈苦锒铛,掳去烂皮和破釜”来砸骨吸髓。“夜深晚饭儿问娘,灶里烧柴没锅煮”和“瓦缸装米无半粒,篾笼装布无一缕”以及“破壁吹来西北风,枵腹上床背伛偻”这几句,更是力透纸背,极言封建时代边地水族底层百姓被横征暴敛之后,衣食无着、饥寒交迫,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披星戴月田亩间,手胝足胼不惰寙”,换来的是“鬻子作奴女作婢,依依割爱泪如雨”的悲惨结局,最后在欲哭无泪中,悲怆地发出“有子不如无子好,无子绝粮免痛苦”的长叹!封建时代把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看得极为重要,这里却反而言之,认为无子更好,这与杜甫在《兵车行》中的“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的悲伤和无望,在思想和意境上是一致的,其道尽了底层百姓的万般凄苦,表达出诗人对黎民生活处境寄予的无限同情和无望的悲鸣。
潘一志家学渊源深厚,诗人饱受祖父、父亲的儒家文化思想教育和文学熏陶,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民本思想,潘一志诗歌也表现出忧患意识和对黎民疾苦和遭遇更多的关切和同情。在这一点上,他继承和发扬了其祖父潘文秀“以民为本”的创作思想。潘一志对黎民疾苦和遭遇抱有深切悲悯的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怨刺和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二是对民生疾苦与遭遇的悲悯。很多情况下这两者又常常融为一体,在同一首诗中,这两种感情又呈现出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情况。潘一志的诗歌常常广泛深切地反映黎民百姓在战争中的苦痛,如“遍野嗷嗷鸿雁声,流离琐尾慨民生”,表达诗人对民生艰难的忧心忡忡。面对外敌侵入,当权者不顾百姓安危,先行逃避的卑鄙行径,他写下了“敌虽猛进军孤入,官自逃亡势蹙穷”“阵地转移千里外,难民颠沛万山中”的诗句,深刻地揭露当时的当权者不顾黎民百姓死活的社会现实;看到百姓因为自然灾害和战争频发,不得不流离失所时,他发出 “水旱连灾兵燹后,田园寥落乱离中”的感慨;看到战争给黎民带来的生存艰难,他留下了“八年抗战膺艰巨,五县沦亡困益穷”“广陌连阡旧土司,贫民开垦上嵚崎”的真实写照。面对战乱频发、民生多艰的社会现实,他吟咏出“几生化着甘霖雨,解尽云霓渴望愁”的心愿等等。潘一志用诗歌对身处战乱年代的底层百姓进行持续关注,他的笔下诗句的沉痛悲吟,使得当时底层民众的斑斑血泪,得以留存。潘一志1945年写于贵州省独山专员公署的古风诗,即《荔波浩劫纪实并记》最能体现诗人以民为本的思想和他对黎民百姓疾苦和命运的悲悯。
“1944年11月,日本侵略军进犯贵州。11月27日,黔、桂两省分界处荔波一侧的黎明关被日军攻破。11月30日三都县城失守,12月2日独山、丹寨两县沦陷,12月3日荔波县城、都匀境内日军铁蹄飞扬。国民党军在独山、荔波战场作战略转移抵抗,战事颇为激烈;荔波至三都一线,无国军保卫,全由以水族为主的民间武装力量抗击日寇,战况惨烈……”[1]134。 日军在荔波境内肆虐之际,“县长陈企崇率保警队弃城而随二十七集团军司令杨森逃往邻县的榕江县城”[1]135,深处险境的潘一志,不顾个人安危,“联络进步士绅,组织民众坚壁物质,疏散市民。”[1]135诗人将日寇蹂躪故土、县长守土失责、土匪掠村烧寨、久旱无雨、蝗虫肆虐、山洪暴涨、田土淹没、荔波十万生灵转徙流离,呼天号泣,苦不堪言的惨痛景象收入诗中,使得此诗自始至终都笼罩在对守土失责者的极端愤慨,对黎民百姓惨遭蹂躏的无比悲痛的基调之中。深处战争旋涡的诗人知道故土沦陷时,心痛交加地在诗中写道:“全月三日荔城陷,噩耗传来泪欲倾。”面对荔波黎民百姓惨遭战乱之苦,诗人写下“黑烟冲天惊火起,荔民何辜竟遭此”的同情和叩问。日寇入侵,贪生怕死、守土无责的县长逃跑,而九阡水族百姓,却扛起大刀、长矛跟日寇血战,两相对比,判若云泥,于是诗人高呼“偏是民众不怕死,大刀杀敌九阡里”,对守土失责、行径恶劣的逃跑县令,诗人予以最为愤怒的抨击:“血肉换取太阳旗,县令报功恬不耻”。面对“四乡土匪复乘机”,官府却“盘踞坐大任群贼”;面对“哀鸿遍野嗷嗷鸣”,官府却“褎如充耳不关情”。极言诗人对底层黎民百姓遭遇的无比悲伤和对为政不仁者的极端愤慨。黎民百姓在战乱之后,桑梓故园已是“货物掳尽房屋毁、猪鸡杀绝塘鱼死、悬釜待炊千百户……”,在历经“兵灾匪祸”之后,只能“琐尾流离”。底层黎民百姓欲重建家园,换来的也是血泪斑斑,“筑渠戽水昼复夜,鹤形伛偻呻吟频”换来的是“蝗虫啮尽叶连茎,束手无策心孔疚”,更兼“入秋山洪复暴涨,田土淹没更无望”,最终“勤劳终岁竞成空,踯躅呼号哭天丧”。在古风《荔波浩劫纪实并序》中,面对黎民百姓的深重苦难和凄凉处境,诗人最终以“长歌一咏复三叹,长夜漫漫守达旦”来跟黎民百姓同呼吸和共患难。潘一志对黎民百姓的疾苦带有深切悲悯的情怀,并将这种情怀付诸现实,诸如:组织民众坚壁物质,疏散市民,两次为黎民百姓,告倒贪官污吏等等。虽然在现实世界中诗人并没有能力去解救底层黎民百姓的疾苦,但他总是念念不忘地去同情和悲悯他们的苦痛,并希冀他们能够平安地活下去,这种愿景在他的诗歌中,经常得到表露,诸如:“裸体乞儿不禁寒,沿街叫化强遮拦”(《毕节杂感》其二 七绝)“何故萑符遍地生,根追症结问民情”(《毕节杂感》其五 七绝)“医疮痛剜心头肉,再寄来春泪欲汪”(《毕节杂感》其九 七绝)“十日城门锁不开,却因淫雨欲为灾”(《久雨闭北门戏占》其一 七绝)等等。二十世纪上半叶,潘一志数次从军、从政、从教,其报国理想均无法得到实现,但面对百姓苦难,他吟咏出来的“几生化着甘霖雨,解尽云霓渴望愁”和“长歌一咏复三叹,长夜漫漫守达旦”等诗句,却能一直震撼着后人的灵魂。诗人的心能跨越个人的生死荣辱,自始至终对底层黎民百姓的疾苦和遭遇给予持续的关注和永恒的忧虑,其强烈的忧民意识业已超越了传统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要求 。
三、对人生挫折和苦痛的感慨
潘一志诗歌的忧患意识,还体现在对个体人生挫折和苦痛的感慨上。茫茫宇宙,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对于持久永恒的大自然而言,个体生命极为短促;而对于强大的政治和复杂的社会来说,个体生命的存在也极为脆弱。因此个体生命对生存走向的焦虑、对生命的追寻和叩问,伴随着人类社会一路走来,已是亘古不变的一个千年话题。从《浪游集》到《归农集》,潘一志诗歌中对人生挫折和苦痛的感慨,极为常见。诗人才华满腹,步入社会后,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心中怀才不遇的惆怅苦闷尤为明显。如1929年诗人流落于贵州兴仁时写的《兴仁旅次杂感》(七律三首),先看第一首。
兴仁旅次杂感(其一)
夜半孤灯未忍眠,风风雨雨奈何天。
惊心时事棋翻局,转瞬韶光箭出弦。
世味饱尝同嚼蜡,人情识透学参禅。
闲鸥莫笑穷途客,自古儒冠误少年。
历经生活磨难、事业未成的人生处境,面对军阀混战、天下动荡的社会现实,诗人的报国理想难以实现而变得惆怅满怀。诗人以“夜半孤灯未忍眠,风风雨雨奈何天”来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在悲怆感慨中,他又以“惊心时事棋翻局,转瞬韶光箭出弦”来感慨时光的飞逝,表现出吴钩空握、壮志空怀的深层忧郁与苦闷。
兴仁旅次杂感(其二)
京华冠盖气横秋,措大穷酸只罢休。
孤愤难偿甘落拓,半生漂泊复何求。
功名盖世羞屠狗,富贵还乡笑沐猴。
坐客三千谁脱颖,侯封尽属烂羊头。
古往今来,有建功立业情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文人士子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要面对的是心中理想和现实残酷的不对等,理想和现实的极大反差,于是诗歌在他们心中就成了一种悲愤的寄托,此诗表露出潘一志在山河含恨的时代背景下,独自感慨“孤愤难偿甘落拓,半生漂泊复何求”的满腹悲伤。
兴仁旅次杂感(其三)
误入尘凡廿九秋,锔天踏地自搔头。
来生祝我成顽石,莫再随波堕浊流。
历变沧桑同泡幻,可求富贵等云浮。
沙虫一例原何益,翻悔当年铸六州。
“误入尘凡廿九秋,锔天踏地自搔头”,曾经的努力和拼搏,一如浮云在沧桑的世事中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这与陆游“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衷情倾诉颇有几分相似;心中块垒无法消除之后,诗人用“来生祝我成顽石,莫再随波堕浊流”来寄托情怀,这和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又有几分相同。但从整首诗来看,潘一志忧患意识蕴涵的情感依然是诗人心中那无法排解的壮志难酬。对人生忧患的感慨,在潘一志的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当面对生离死别之时,其诗歌的透出感情尤为悲切。如《挽李君伯纯》(其一),这是一首七绝。
挽李君伯纯(其一)
达观归寄古今同,我哭先生却为公。
此后与谁谈正义,九原能否梦魂通。
潘一志以悲怆之心哭诉友人离世,其哀恸之情难以言表。“此后与谁谈正义,九原能否梦魂通”一句,道出了诗人痛失知音的无限感伤。潘一志为悼念亡妻潘媛贞所写《悼亡》诗,其中五律四首,七绝四首。先看五律中的第四首。
悼亡(其四)
医书曾涉猎,时症可追寻。
小别才周月,沉疴竟丧身。
斗升偏误我,汤药可怜君。
归来呼负负,谁是梦中人。
面对妻子突然离开人世,诗人表达出来的是深深自责,其情感真挚,尤为真切感人。再看七绝中的第四首。
悼亡(其四)
小别竟成千古恨,归来只见一家空。
艰难未了营斋葬,一片酸辛结五中。
面对天人永隔,诗人写到“小别竟成千古恨,归来只见一家空”,这与苏东坡的“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潘岳的“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又有何异?沉痛中,自是对亡妻不尽的怀念。1943年11月,潘一志长女、时年二十三岁的潘懋禧病逝于榕江国立师范学校,九个月后的1944年7月,诗人的长子潘懋祺又因病离世。潘一志对长女和长子的先后离世,表现出极大的悲伤,人生如此无常,生命易逝的忧患意识充盈其中,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苦中,诗人写下了哭女诗和哭子诗,这些诗句,内容哀婉,极尽哀伤之情。先看其《哭女诗》中的第十首。
哭女诗(其十)
荒郊矗立一孤碑,石上刊成哭女诗。
一字一声一滴泪,是诗是泪有谁知。
“1943年11月,潘志长女潘懋禧在榕江师范病殁。女儿的辞世,对潘一志的打击特别大。 ‘一字一声一滴泪’是潘一志知道女儿逝世时悲痛欲绝的真实情态。全诗体现的父爱精神在水族地区影响深远,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常有人提及。”[1]118《哭女诗》字字是泪,句句是血,诗中对女儿的追忆,以逐步推进的方式,让悲伤之情层层深入,在低沉的诗句表述中,诗人对爱女逝去的悲伤,笼罩在灰暗的情绪之中,此起彼伏地叫人肝肠寸断,读之,令人不禁怆然而泣下。
长女和长子先后离世,悲伤和无奈笼罩于潘一志的心胸,在悲伤的心境下,他以“去年冬月哭禧女,今年七月哭棋儿”起笔,然后用“屈指周年九月余,慧中秀骨夸凤雏”“望孙可慰泉下祖,蚌犹未老庆生珠”来追忆长子生前的天资禀赋;再以“呼妈呼伯声咿哑彳亍甲欲行脚交叉”“翻书认识之无字,握手执笔学投鸦”来描绘爱子生前的活泼可爱。到此,诗人笔锋开始转向,他将长子从染病到临终前的过程进行了叙述,最后用“伤心最是临危句,蜂声细说‘ 没吃了’”来表达诗人的苦涩、悲伤和无助。“四壁寂静灯路黑,荒鸡声声增怆恻”,长子于深夜死去,诗人用黑夜的漫长和鸡鸣的怆恻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荒凉和凄苦。让读者仿佛已看到肝肠寸断、痛彻肺腑、老年丧子之人立于眼前。“哭子之泪,幻化成垂挂的帘子,定眼看竟是滴滴泣血。”[1]122最后诗人仰头长问:“天心胡太忍?天道有谁知?”呼应开头,让全诗笼罩在无尽的悲伤之中。
人生挫折和遭遇,表现在潘一志诗歌创作上,那就是深沉的感慨和吟咏,潘一志对人生挫折和苦痛的感慨,汇集到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之中,融成的忧患意识极为强烈。对人生忧患意识的一咏三叹,论述在《浪游集》和《归农集》中,读此类诗作,往往让人悲怆落泪。
此外,在诗人的《归农集》中,诸如:“怕将往事说从头,转瞬年华春复秋”(《步〈寄怀〉原韵》其三 七律四首七律二首)“顾影当年伤老大,不堪残漏听晨钟”(《步〈寄怀〉原韵》其六 七律四首七律二首)“丧乱流离同一病,自伤未几复伤君”(《步〈杂感〉原韵》其三 七绝四首)“弹指沧桑几度迁,不堪回首话当年”(《有感》七绝)“世与我相违,复驾亦何益”(《邑令周绍伊强以县府秘书职务走避述怀》古风),“半百残年负负呼,功名早信命中无”(《友人寄送好橘种并颂以“不求官一品 但愿橘千头”感谢以诗》其一 七绝二首)“不解群芳争艳色,繁华春梦了无缘”(《步〈咏菊〉原韵》其一 七绝二首)“老大悲伤志未成,不堪时事再回萦”(《有劝“仍服公务以解决生计”赋此谢之》七绝)“沧桑一变一飞梭,造化频将好事磨”(《又倒次前韵》七律)“休将往事苦寻思,已悔当年觉悟迟”(《步〈感兴〉原韵》其一 七绝二首)“问君谁与易滔滔,悲悯婆心枉自劳”(《步〈感兴〉原韵》其二 七绝二首)“东隅虽逝桑榆在,壮志何曾减少时”(《步〈遣怀〉原韵》其一 七绝二首)“去年漂泊才恢复,昨日繁华又落空”(《步〈落花有感〉原韵》其一 七律二首)“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属谁家红”(《秋夜小池玩月》七绝)“繁华如梦古犹今,回首当年百感侵”(《重阳后三日赏菊》七绝)等等,无一不表达诗人对人生挫折和苦痛的喟叹和感慨。
四、结语
作为水族最为著名的史学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水族诗歌创作的重要诗人的潘一志,他有着数次从军、从政、从教的社会经历,丰富的社会阅历,使得诗人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境内战争频发,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接踵而至地发生,诗人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经历战乱的痛苦,过着空怀理想、壮志难酬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得他对国土沦陷和黎民疾苦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烽火连绵、遍地哀号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潘一志忧国忧民忧己的多重忧患意识除感慨人生之外,更多的是体现人民疾苦、反映国难深重,“潘一志的诗歌立意明确,结构严谨,在众多的诗篇中虽然流露出忧愤心情,但他愤世并不厌世,悲怨并不悲观,能激发人民敢于正视现实,从而去寻找救国之路。”[4]对生存困境进行深刻思考、对社会现实提出批判意见是忧患意识的精神内核,因此忧患意识是一种防范和预见,更是包含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以及使命感在内的理性认识。“从文化的被启蒙到文化自觉,文化身份的混杂与家国重建努力的时代背景,共同催生了以潘一志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诗人旧体诗写作的现代因子。”[5]无数人生体验和社会实践,才能形成真切的忧患意识,把忧患意识转化成积极的实践导向,让生命去突破困境,让人生去超越忧患,从而让忧患意识变成改变人生困境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
二十世纪上半叶,潘一志投身于广阔的社会实践之中,但他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并没有得到实现,于是儒家思想中的忧患意识郁结于诗人之胸,并最终在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释放。潘一志忧国忧民的思想导致了他忧患意识的形成,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他的诗歌创作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他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传承者的理想性人格;诗人亦诗亦史的诗风,将忧国、忧民、忧人生融为一体,使得其诗歌的忧患意识尤为强烈,凸显出的济世情怀和民本思想,在提倡文化自信的当下,非常值得我们去挖掘、继承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