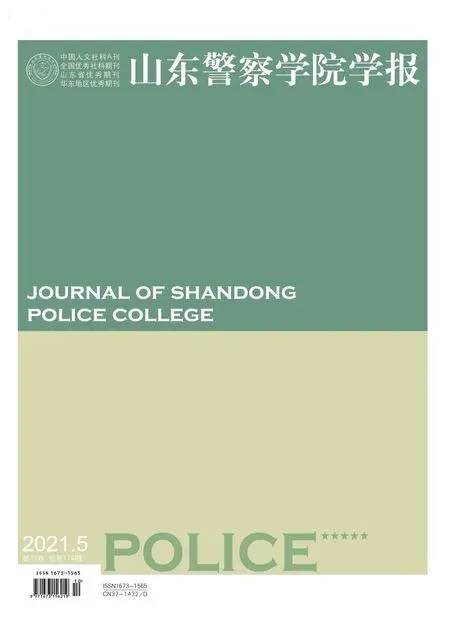渎职犯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刘德法,李沙沙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一、渎职犯罪责任要素的拨乱反正
渎职犯罪是特殊主体违反正确履职义务的行为,《刑法》第9章关于渎职犯罪的规定包括一般罪名(第397条)和特殊罪名(第398条至第419条)。其中《刑法》第397条规定了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两罪用以规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渎职行为;《刑法》第398条至第419条规定了特殊的渎职犯罪,即特定主体在特定领域所为的特定渎职行为。一般主体的渎职行为用民法、行政法或公司章程进行规制,而不构成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特殊主体,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其渎职行为的责任要素认定与普通犯罪的责任要素认定不应相同,应以渎职犯罪的保护法益为指导,正确理解各种责任要素。[1]
(一)渎职犯罪一般罪名的罪过形态
从刑法历史承袭的角度分析,1997年《刑法》第397条是由1979年《刑法》第187条修改而来的,1979年《刑法》规定的玩忽职守罪是过失犯罪,1997年《刑法》在保留玩忽职守罪的基础上新设立了滥用职权罪。目前,对玩忽职守罪的罪过形态为过失并无争议,也符合渎职犯罪的设立目的,理论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态。有学者认为,滥用职权罪应当为故意犯罪[2],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应以主观方面作为界定标准。不过,这种观点显然值得推敲,因为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两个罪名是规定在同一条文里的,规范构造并无明显差别,人为限定二者之间的区别为主观方面[3],在逻辑关系上较为片面,且没有有力的支撑依据。还有学者主张,滥用职权罪应为复合的罪过形态。[4]复合罪过又称复杂罪过,是指由于立法模糊或司法认定等问题,一个罪名可以同时由故意形态和过失形态构成。[5]这种观点同样值得商榷。就同一事实而言,故意和过失相互排斥[6],不能因为司法实践中故意心理难以查明、难以认定而模糊犯罪的主观要素,认为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皆能构成此罪。使用故意和过失两种主观心理来认定本罪,不仅有悖我国“一罪名一罪过”的常识,更会混淆本罪的认定标准,使得罪过形式的确定变得悬而不决,进而冲击刑法权威。因此,罪过形态不能同时适用双重标准。亦有学者认为,滥用职权罪仍属于过失犯罪[7],故意和复合罪过形态不符合本罪的规范构造。本文赞同此观点,但是对此观点所提出的过失内容有不同看法,笔者主张,在界定具体犯罪的主观方面时,应当结合保护法益、规范构造、价值取向进行综合研判。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滥用职权罪的保护法益应为公职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本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类主体代表国家履职,权力较大,不正确履职所造成的后果较严重,而且会损害国家机关的权威。相比之下,一般人不正确履职,社会危害性较小,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无需对其进行规制。渎职犯罪规制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正确履职而没有正确履职的行为。为了防止刑法过度泛化,刑法规定渎职行为需要造成损害后果才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的程度,才能用刑法对其进行处罚。行为人对重大损失的责任要素实为本罪重点考察的对象。
其次,按照刑法关于故意与过失区分的规范构造,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方面应为过失。通说认为,国内刑法学对罪过形态的认定基础来源于刑法总则对故意与过失的认定。[8]判断行为人的罪过形态依据行为人对结果的态度,行为人对行为的态度不影响罪过形态的认定。如果将行为人故意利用本人职权对财产或人身等方面而为的犯罪行为仍然按照滥用职权罪进行规制,不仅不能完整评价犯罪行为,更会放纵犯罪,从立法上侵蚀司法公正。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事责任要与行为人犯罪行为的严重性相符合,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这样才会使得刑法具有权威性。如果行为方式相同,因故意罪过比过失罪过的社会危害性更严重,那么刑事责任也应更严厉。例如,故意杀人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1)《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同样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起点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基本法定刑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再如交通肇事行为,如果罪过形式为过失,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行为人明知违章行为会造成人身伤亡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则应构成故意杀人罪,而不以交通肇事罪对其进行处罚。倘若行为人利用渎职行为故意引发特定结果,刑法不考虑其罪过形式,规定与过失引发特定结果相同的法定刑,就明显有悖于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再次,基于历史沿袭和立法技术的价值取向,行为构造相似,但主观方面不同的两个罪名一般分属于两个条文规定,如故意杀人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放火罪与失火罪等。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一同规定于《刑法》第397条,同一条文的罪过形式若没有特别提出,则应为同一罪过形态。(2)比如,《刑法》第398条规定的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与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行为构造相同,法条明文规定了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态。1979年《刑法》规定的渎职犯罪属于过失犯罪,但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行为人积极渎职行为难以归属到玩忽职守罪的困境,因此,1997年《刑法》增加了作为形式的渎职行为,在法条中增加了滥用职权罪。滥用职权罪是用来规制作为形式的渎职犯罪的,并不是说其罪过形态是故意。从趋利避害的角度考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仅可能故意实施滥用职权的行为,但不会故意造成“重大损失”的危害结果。
最后,如果行为人基于主观故意希望危害结果发生,其行为可适用刑法分则相应的其他罪名,以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无需以滥用职权罪论处。滥用职权罪规制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正确履行其应当履行的职权,从而引发重大损失的行为,关注的焦点是履职行为,对于危害结果,其主观心态应当为过失。如果行为人故意滥用职权造成危害结果,滥用职权罪的法定刑就不足以规制此种行为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处于同一条文,立法并未对其进行区分,罪状描述使用的是相同的语言,对构成要件和法定刑的规定也相同。考察立法本意,并无将二者主观方面进行区分的目的,更无区分的基础。另外,2012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也规定,关于重大损失及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两个罪名采用相同的标准,并未有所区分。
(二)特殊要素之主观徇私的定位
《刑法》第397条第2款规定的不是独立的罪名,而属于第1款的加重情节。《刑法》第397条第1款规定的是一般渎职犯罪的两种行为方式,第2款规定的是故意形态的渎职行为。对第397条第2款,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该款规定的是独立的罪名[9],理由是该条规定的两款内容罪过形式不同、法定刑独立。笔者认为,根据条文的描述,将其理解为第1款的加重情节较为合理,因为从法条规定和立法本意来看,行为人基于徇私的主观动机实施了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等渎职行为,罪过形态由过失变为故意,法定刑相应增加。
另外,徇私属于犯罪动机,是本罪的必备责任要素,影响犯罪的成立与否。原则上,徇私仅指徇个人私情、私利而做不合法的行为,谋取本单位私利不属于徇私。(3)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徇私舞弊型渎职犯罪的“徇私”应理解为徇个人私情、私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397条第1款的规定定罪处罚。徇私舞弊类犯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特点是基于私利或私情;而渎职致使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对重大损失持的是故意的态度,并且法定刑相应提高,足以容纳主观恶性。针对主观上未谋取私利的舞弊行为,不构成徇私舞弊类犯罪,应当依照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作为犯罪动机的主观要素,徇私不要求具有相应的客观行为。因此,行为人基于徇私(收受财物等)而为的渎职行为不能包容评价受贿罪,此类罪数形态将在下文进行详细分析。
(三)谋取个人利益与渎职犯罪的关系
谋取个人利益与渎职犯罪的认定并无关系。渎职罪的设置旨在保护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以及公民对此的信赖。[10]行为人是否因此谋取个人利益与渎职犯罪并无必然关系,渎职犯罪属于侵犯国家利益的犯罪。因此,行为人是否谋取个人利益与一般渎职犯罪的构成与否没有关系,不能因为行为人没有谋取个人利益,进而否认渎职犯罪的构成。认定渎职犯罪,应当依照渎职犯罪的规范构造进行主客观相统一的把握。职务犯罪的贪污受贿章节中,个别犯罪在构成要件上要求行为人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如受贿罪规制的是权钱交易行为,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不可收买性。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行为人未谋取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单位、集体的利益不正确履职的情形,司法机关认定重大损失结果与受贿犯罪没有关系。与此相反,个别司法机关以行为人未谋取个人利益为由否定渎职犯罪的成立是错误的。考察行为人的职务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当重点审查犯罪的保护法益,而不应片面审查行为人获利与否。行为人是否谋取个人利益与渎职犯罪并无对应关系,认定渎职犯罪应当考察行为人的履职行为。
二、渎职犯罪规范构造的回本溯源
渎职犯罪一章规制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公职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而造成一定损失的行为。按照目前学界的认定标准,应当采用客观归责理论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追责。考察行为人是否应当承担渎职犯罪的刑事责任,应当重点把握以下三点:首先,行为人应当具有特定的管理职责。管理职责是渎职犯罪成立的基础和前提。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职权、职责,则不存在渎职行为。其次,行为人实施了违反相关规定的履职不到位、不规范的行为是渎职犯罪成立的关键,即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违法行为,违反了应当正确履职的义务,因此具有非难可能性。最后,存在因果关系是渎职犯罪成立的依据,因果关系将渎职行为与损害结果相连接,使得损害结果能够归因于渎职行为。上述三个要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渎职犯罪,任何一个要件缺失就不能构成渎职犯罪。
(一)渎职犯罪的职权定性
认定渎职犯罪的前提是行为人拥有特定的职权,具有履行职责的义务。职权的定性是本罪的关键,也是区分罪与非罪的要点,更是本罪成立的主体要件。立法解释(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已经明确规定,渎职犯罪主体的认定应当依照“职责论”,即行为人是否拥有特定职权。渎职犯罪的职务仅指本人拥有的职务,即本人对国家机关职务具有行使、支配、掌握的权力,渎职犯罪仅规制行为人直接行使职权的行为,不包括通过本人职权对他人职权实施间接影响力的行为。渎职犯罪的职权内涵不同于受贿罪中的职务内涵。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受贿罪中的职务不仅包括本人职务,也包括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不仅包括本人职务直接被人收买,更包括本人职务间接被收买,即他人利用本人职务之便实施受贿行为。行为人不论是利用本人职务,还是借助本人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而利用他人职务,都影响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因为,此类犯罪会侵害大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信任感,行为人利用他人职权之便为请托人谋利而受贿,此类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严重,扩大职务的范围符合我国刑法的目的。但是,渎职犯罪需要处罚的内容是行为人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在其位,谋其职”的义务规范,渎职犯罪的职权行为实质是行为人的履职行为,不同于贪污受贿犯罪可以包容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两种犯罪规范构造的不同造成了对行为人职权规定的不同。例如,某教育局局长黄某利用本人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请求某环保部门负责人张某对某企业排污不处置,最终企业污染对附近农田造成了重大损失。考察此案例,张某不正确履职并因此造成了重大损失,毋庸置疑构成渎职犯罪。但是,黄某并未对本人职务有滥用或不用的行为,不属于渎职犯罪所要规制的范畴,不构成渎职犯罪,如果黄某收受财物则可能构成受贿罪。
认定渎职犯罪的关键即行为人违反相关规定,错误履职,表现为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表现形式为超越职权和违规履职。超越职权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未被授予的某项事项或职权的行为,即本无职权却实施该行为;违规履职是指行为人具有职权,但是违反规定处理事项,包括擅自违规履职和明知应当履职而不履职的行为。滥用职权罪的本质是行为人以积极的方式渎职,实践中常表现为作为的形式。此时,行为人对于履职行为是故意为之,即明知是滥用职权的行为而故意实施,但是对造成重大损失的结果仍属于过失,对行为的认识不影响罪过形式的认定。玩忽职守的表现形式也为两种:一是不履职,即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消极不作为;二是履职不到位,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工作懈怠,不完整履行职责。玩忽职守的本质是行为人以消极的方式渎职,实践中常表现为不作为的形式。此时,行为人对于履职行为既可能是故意懈怠不作为,也可能是过失懈怠不作为,但是对造成的重大损失结果仍属于过失。综上所述,对行为和结果的主观心理态度都不能明确区分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二者在主观心理方面存在重合关系,只有通过客观行为方面的差异才能对二者进行合理界分。
(二)渎职犯罪的归责基础
渎职犯罪的因果关系与结果归属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果关系是某种先行行为与后发事实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因果关系的认定有三种学说。其中,条件说将引起事实的所有条件都认定为因果关系的“因”;原因说认为,条件和原因应当区分,诸条件中最重要的、有力的或必须的条件才需要对结果负责,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相当因果关系说使用相当性对原因进行判断,更加符合刑法原则。条件说将所有引起危害结果的危害行为进行包容评价,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司法实践中,渎职犯罪的行为和结果往往没有直接关联,行为和结果之间不像一般犯罪那样联系密切,存在着介入因素,也常常伴随着多因一果的形式出现,采用原因说或者相当因果关系说可能会放纵渎职犯罪。另外,渎职犯罪通常会引起重大责任事故的危害结果,认定渎职犯罪的因果关系首先需要考察渎职犯罪的设立宗旨和保护法益,进而从因果关系的判断和多因一果的作用力等角度进行认定。
首先,对渎职罪的因果关系考察应当采取条件说,即在渎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只要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这种条件关系,就认为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渎职犯罪规制的是因履职行为而引发的重大损害结果,此时,重大损害结果与渎职行为往往具有间接因果关系。虽然条件说在刑法理论上广受诟病,但是对于渎职罪的因果关系论证却是一种有力的主张。由于渎职罪的危害结果和行为之间的联系较远,并且渎职罪造成人身伤亡也不用承担侵害人身权的罪名,因此条件说更适合渎职犯罪。同时,相关判例也证明了此项主张。(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批指导性案例胡宝刚、郑伶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检例第7号)。在渎职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如果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认真履行其监管职责,从而未能有效防止危害结果发生,那么应认定这些对危害结果具有“原因力”的渎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例如,蒋某某玩忽职守罪再审一案中,被告人在监管采石场的过程中,不认真履职,致使未能及时发现越界开采的情况,在发现越界开采以后也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各采石场继续非法开采,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人民法院认为其行为与越界开采之间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行为虽然不是发生危害结果的直接原因,但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渎职犯罪的刑事责任。(6)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刑再6号再审刑事判决书。
其次,渎职犯罪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往往伴随着多因一果的情况,即在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造成了一个结果的实现,行为人的渎职行为是否应当对重大损失结果负责主要判断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实践中,渎职犯罪较多出现多因一果的情况,若多因一果不能切断渎职行为与重大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则渎职行为仍需要对损害后果负责。如张某春、谈某滥用职权罪一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了对佘某坤故意伤害韦某隆等人一案未予立案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不能全部归责于被告人的辩护意见。经查,佘某坤故意伤害韦某隆、张某云案件虽在办理过程中存在被害人不配合进行鉴定、新旧警综平台未能衔接等因素,但案件不及时查处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被告人怠于履行职责,故对上述辩护意见法院不予采信,最终法院判决两被告人构成玩忽职守罪。(7)参见甘肃省山丹县人民法院(2021)甘0725刑初90号刑事判决书。
最后,多因一果的情况下,介入因素中断渎职行为与重大损失结果的因果关系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首先,介入因素需要对结果的发生存在影响力;其次,结果是由介入因素直接造成的;最后,结果的发生超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权的监管范围。只有介入因素完全符合以上三个要件才能中断渎职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其中任何一个要件不符合,则行为人的渎职行为与重大损失结果仍然存在因果关系,渎职行为仍需对结果负责。司法实践中,渎职犯罪与重大损失结果往往是间接因果关系,与重大损失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则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等其他罪名。对渎职行为之后的介入因素是否足以阻止渎职行为与损失结果的因果关系,应当严格按照以上三个条件进行判断。与此同时,在使用条件说解释渎职犯罪的因果关系时,应当采取“因果关系中断论”及“合义务的择一举动”等对其进行修正,以防止因果关系范围无限扩大。因果关系中断论是指当行为人的渎职行为还未起作用时,与此无关的后条件行为如果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则其阻断渎职行为的因果关系。
(三)重大损失和情节特别严重的判断标准
“重大损失”在渎职犯罪构成要件中处于决定罪与非罪的地位。司法实践中,行为人虽然有滥用职权的行为,但是未造成重大损失结果则可不按犯罪处理。例如,马某某滥用职权、受贿罪一案中,二审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触犯滥用职权罪,但是再审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行为人滥用职权行为情节显著轻微,相关领导滥用职权行为责任分散,并且行为没有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等损害后果,认定滥用职权罪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8)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刑终168号二审刑事判决书。损失的评价更侧重于行为所造成的后果,间接性更突出,但是,司法实践中认定间接损失容易扩大范围,所以对间接损失的认定应当进行合理限缩,下文将详细界定司法实践中认定重大损失的疑难问题。
实践中,重大损失的认定不应局限于物质性利益,非物质性利益也应被认定为重大损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司法解释规定了重大损失的范围,用以统一全国渎职犯罪定罪的具体标准。(9)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97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事实上,渎职犯罪的结果不能仅认定为财产损失,从渎职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结果来看,人身伤亡情况并不少见,更存在着对国家声誉等产生重大影响的恶性渎职事件,需要运用刑法手段予以介入和告诫。例如,罗建某、罗镜某、朱炳某、罗锦某滥用职权罪案中,被告人长期不正确履行职权,并未造成达到立案标准的财产损失,但是给周边商铺和住户的经营、生活、出行造成了极大不便,此种结果也属于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10)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批指导性案例检例第6号。
对涉案人员的财产罚没属于行政处罚,不应从造成国家经济损失中予以扣除。因为行政处罚系相关责任人员渎职犯罪既遂之后作出的,行政处罚收取了多少罚没款,收取的罚没款是否到位等事实均不影响对行为人造成的重大损失数额的认定。对渎职犯罪造成结果的判断应当讲究相对性,具体分为结果和后果。结果是直接的、必然的,后果是间接的、偶然的。符保某玩忽职守罪再审一案中,被告人辩称其违规开具的证明造成的损失不属于直接损失,其行为尚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人民法院则认为,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未按照规定履行职责,致使发生了严重违反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符保某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有关政策,未收取的费用应当认定为重大损失。(11)参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琼刑再1号再审刑事判决书。
“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具备普通犯罪构成要件为前提,即以致使重大损失结果发生为前提。如果没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虽然情节特别严重,也不能直接适用第二档刑罚定罪论处。在渎职犯罪的结果要件和加重要件的关系上,刑法学界也存在一些讨论。有的学者站在法律批评的立场上,认为现行刑法的设计存在着规范性断层现象,因为从规范文字上看,“重大损失”与“情节特别严重”并非同类标准,不能量定不同的刑罚等级。他们认为,这样的立法会引发司法机关的实践困惑,即某些渎职行为虽然“情节特别严重”但又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对其能否定罪量刑。这其实仍然是一个如何理解和解释法律的问题。如前所述,作为渎职犯罪结果要件的“重大损失”是成立该类犯罪的基本条件,如果渎职行为没有造成司法解释所列举的“重大损失”结果,自然不能立案侦查,更谈不上定罪处刑的问题。而作为该罪加重要件的“情节特别严重”当然是在“重大损失”已经形成的前提下才加以综合考虑的。对这里所谓的“情节”确实应当作广义解释,它是一个包含诸多因素的综合指数。在渎职犯罪中,一方面,其包括特别重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其还包括对行为人犯罪动机、主观恶性等因素的判断,并通过刑罚裁量的酌情选择,实现罪罚之间的真正相当和对应。所以,就整体而言,现行刑法关于渎职犯罪结果要件和加重要件的表述及其关系设计并不存在明显不当之处。实践中更需做的是,如何对其加以科学解释和通过有效发挥立法规范正向效应的作用。
三、渎职犯罪罪数问题的系统梳理
一罪和数罪的认定混乱,必然造成量刑上的畸轻畸重现象,只有正确区分罪数,才能为合理量刑提供前提条件。对罪数问题的研究,需要从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两个视角加以审查,结合渎职罪的构成要件分析其罪数形态和处罚原则,首先界定一罪与数罪,进而讨论数罪是否并罚,由此系统梳理渎职犯罪的罪数问题。
(一)渎职犯罪章节内部的罪数认定
1. 《刑法》第397条与本章内部其他罪名竞合的处理
《刑法》第9章渎职犯罪分为一般法条与特别法条,并在《刑法》第397条作出明确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由此可知,《刑法》第397条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与本章特殊渎职犯罪属于法条竞合关系,两类罪名为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首先,两者存在逻辑的包容关系,即无需借助具体案件事实,通过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就可以发现《刑法》第397条包容了特殊渎职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内容;其次,两者存在法益同一的关系,都属于渎职犯罪;最后,两者存在不法内容的包容关系,即特殊渎职犯罪都可以包容评价为一般罪名的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以《刑法》第397条为基准观察,《刑法》第398条至第419条(特殊渎职犯罪)补充了《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二者属于法条竞合关系。
因此,以上条文之间属于单纯的一罪(法条竞合),又称实质的一罪。法条竞合的适用规则包括“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和“重法优于轻法”两种,即一般情况下,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当特别法的法定刑不能全面评价行为人的不法和责任时,则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但是在渎职犯罪章节中,由于法律的特别规定,当行为人既触犯《刑法》第397条一般罪名又触犯本章第398条至第419条的特殊罪名时,只能适用特别法条优于一般法条的规则,即只能适用本章第398条至第419条的特殊罪名。即使适用特别法不能全面评价行为人的不法和责任,也不能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否则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2.《刑法》第397条内部两个罪名的罪数分析
学界讨论渎职犯罪的罪数形态往往关注本章一般罪名和特殊罪名的认定,但是并未对《刑法》第397条之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罪数形态进行严格认定区分。有学者笼统认为本条属于选择性罪名[11],使用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方式对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进行区分,行为人仅有作为形式的渎职行为,造成重大损失的,可定为滥用职权罪;仅有不作为形式的渎职行为,造成重大损失的,可定为玩忽职守罪。当行为人既有作为的渎职行为又有不作为的渎职行为,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以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按一罪论处。选择性罪名一般是立法机关在制定法或立法解释中,使用顿号进行连接的罪名[12],然而从《刑法》第397条的罪状描述上可以看出,本罪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选择性罪名。
《刑法》第397条规定的不是选择性罪名,而是并列罪名。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是互相独立的,不是一罪而是数罪。并列罪名不同于选择性罪名,在并列罪名的情况下,两种以上行为虽然规定在同一条款,但属于两个独立的罪名,如《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规定的数个并列罪名。(12)第114条【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一】: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以下有期徒刑。第115条【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二】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于类似罪名的规范构造类似,立法机关出于精简字数的考量将这些罪名使用一个罪状描述,订立于同一条文中,罪与罪之间的关系是各自独立的,不属于选择适用的范围。因此,当行为人的危害行为既触犯滥用职权罪,又触犯玩忽职守罪时,不能适用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罪,而应当独立分析是否符合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构成要件,按照两罪名的规范构造进行定罪论处。
考察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发现,虽然《刑法》第397条规定的是侵害同一法益的犯罪,但是根据其行为手段的不同形态,将其设计为两个独立的犯罪。当行为人同时触犯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时,虽然属于数罪,但是不可以数罪并罚,而应当适用吸收犯的原则进行定罪论处。吸收犯属于处断的一罪,是基于司法适用对数行为认定为一个罪名的犯罪形态。吸收犯虽然有数个行为,但是数个行为侵害的是同一法益结果,并且行为之间往往存在前后发展关系。例如,行为人仅仅消极不作为,不对违规事项进行查处,后来害怕事情败露,又采取积极作为的方式滥用职权最终引发危害结果发生。经过实质考察可以认定行为人既触犯滥用职权罪,又触犯玩忽职守罪。同一人既实施伤害行为,又实施杀人行为,由于触犯相同法益,不实行数罪并罚,而采取重行为吸收轻行为,行为人只构成故意杀人罪一罪。因此,行为人既触犯滥用职权罪又触犯玩忽职守罪时,应当适用重行为吸收轻行为。两罪的危害性相同,保护法益同一,此时作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不作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严重,因此应当适用滥用职权罪吸收玩忽职守罪,行为人构成滥用职权罪一罪。
(二)渎职犯罪与其他罪名竞合的处理
渎职犯罪本章内部的竞合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处理,而与其他章节罪名竞合应当如何处理却没有定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阻止他人犯罪的,成立不阻止犯罪的共犯还是单独成立滥用职权罪?有学者认为,如果公安人员对他人的犯罪不予阻止,则应认定为正犯。[13]还有学者指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他人犯罪,如果认定为他人犯罪的共犯,则滥用职权罪形同虚设,因而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14]以上两种学说皆有合理之处,但是,渎职犯罪的一般罪名可以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以作为形式和不作为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构成其他犯罪的帮助犯,处理情况是否应当有所差别?本文认为,对滥用职权与相关犯罪之间的关系,关键看行为人实施了几个行为,不能以行为人渎职的目的是帮助他人实施其他犯罪,就择一重罪论处。
如果行为人仅实施了一个行为——渎职行为,以此来帮助他人实施犯罪,根据法益评价标准,渎职犯罪的法益可以包容评价帮助犯,此时应当以渎职罪一罪论处。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仅实施了一个行为,同时触犯渎职犯罪和其他罪名,属于想象竞合犯。想象竞合不同于法条竞合,想象竞合可以适用行为所触犯的数个法条,原本属于数罪,但是作为科刑的一罪处理;而法条竞合只适用一个法条,其他法条被排斥适用,属于单纯的一罪。[15]两个罪名之间存在渎职犯罪可以包容评价帮助犯罪名的关系。国内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属于包容竞合的想象竞合,即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法条,两个法条的行为构造存在吸收关系,即整体法与部分法的竞合。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法只是整体法的一部分,整体法的法律评价已经包含部分法,因此,整体法是优位法,应依据整体法优于部分法的原则适用整体法,这也被称为吸收与被吸收的关系。[16]意大利学者认为,吸收标准的基础是对犯罪构成的价值判断。当一个行为触犯多个法律规定时,应适用能完全反映该现象的法律规范。[17]因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阻止他人犯罪仍然单独构成渎职犯罪,而不构成其所不阻止犯罪的共犯。例如,某公安人员不阻止他人杀人、某食品监管机关人员放纵制售伪劣食品、某海关人员放纵走私等,此时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触犯渎职犯罪,而不以相应的帮助犯对其定罪论处。因为渎职罪的构成不仅仅包括对社会造成重大财产或人身等损害结果,还包括对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造成的侵害,渎职罪可以包容评价行为人不阻止他人犯罪而构成其他犯罪的帮助犯。行为人的不作为既是滥用职权型渎职犯罪的实行行为,又是使他人犯罪更为容易的帮助行为。行为人既构成滥用职权型渎职罪的单独正犯,又构成他人犯罪的共犯(片面的帮助犯),由于只有一个行为(不作为),故成立想象竞合犯而从一重处罚,通常以滥用职权犯罪一罪论处就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渎职犯罪与其他犯罪的想象竞合因作为方式或不作为方式的不同,处理结果大相径庭。一方面,行为人只有消极不作为的渎职行为,并未积极帮助他人实施犯罪,但在客观情况下同时构成渎职犯罪的正犯和其他犯罪的帮助犯,应当以渎职犯罪一罪论处。因为渎职犯罪既可以包容评价对国家机关权威的损害,也可以包容评价对财产权、人身权、社会秩序等造成的危害结果。另一方面,如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既有消极不作为的渎职行为,还与他人事先存在通谋,甚至以投资经营人入股等方式积极参与他人的制售伪劣商品或者走私犯罪的,应以滥用职权型渎职犯罪与他人犯罪的共犯数罪并罚。因为此时行为人既有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负有阻止他人犯罪义务而不阻止的消极不作为,还实施了参与他人犯罪的积极作为行为。
司法实践中,对于不阻止他人犯罪,甚至积极参与他人犯罪的,仅认定渎职罪一罪,而没有认定他人犯罪的共犯,本文对此不敢苟同。例如,冯某某为帮助麦某某名下企业融资,伙同麦某某骗取银行票据承兑的犯罪行为与冯某某利用职务便利,违规以单位名义为麦某某个人及其名下企业的债务提供担保的犯罪行为分属两个犯罪行为,触犯两个罪名。再审法院认为,原判据此分别评价并无不当,最终认为对冯某某应数罪并罚。(13)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2019)鄂刑终197号。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渎职行为和其他犯罪行为属于两个行为,理应数罪并罚。并且在职务犯罪的认定中,应当严格限制吸收、牵连关系的处罚范围,对行为人的各个行为分别定罪论处,严惩渎职行为,树立国家机关的权威,顺应当下的刑事政策。
(三)渎职犯罪与受贿犯罪的罪数认定
《刑法》第399条第4款(14)司法工作人员贪赃枉法而犯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等罪,同时又构成受贿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而不数罪并罚。的规定不是注意规定,而是法律拟制。法律拟制不同于注意规定,法律拟制是将原本不符合某种规定的行为也按照该规定处理;注意规定的设置并不改变基本规定的内容,只是对其进行重申。法律拟制的内容并非理所当然,不能推而广之。注意规定的内容是理所当然的,可以推而广之。因此,我国《刑法》第399条第4款的规定不能广泛适用。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又从事其他渎职犯罪行为,明显符合多个犯罪构成要件,原本应该数罪并罚[18],但立法在这里特别规定按照竞合(牵连犯)的关系处理,不再数罪并罚。
除《刑法》第399条的规定之外,其他渎职犯罪与受贿犯罪在并无法律规定处罚规则的前提下,则应数罪并罚。首先,渎职犯罪与受贿犯罪之间没有包容评价的关系,二者的保护法益也不相同,虽然都是利用职务进行犯罪,但是行为构造和罪过形式均不相同,二者没有法条竞合的关系。其次,法律拟制应当按照该规定用语的客观含义进行解释。立法者设立《刑法》第399条是基于法律经济性的考虑,在特殊的司法领域,将渎职犯罪与受贿犯罪从一重论处。该规定的正当性引发激烈争论。法律拟制是法律创造性地拟定新的规则,基于本体刑法学,法律拟制不能广泛适用于所有渎职犯罪与受贿犯罪,而应严格限制该法律拟制成立的范围。最后,基于渎职犯罪和受贿犯罪属于数罪的关系,并且二者互相独立,任何一个罪名都不能完整评价行为人的渎职行为和权钱交易行为,因此,在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渎职罪和受贿罪应当数罪并罚。
行为人徇私舞弊又收受他人贿赂,则同时构成徇私舞弊类渎职犯罪与受贿罪,并且两罪之间不存在方法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应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在渎职罪的罪状描述中,有的直接将“徇私”作为基本犯的构成要件,有的则把“徇私”作为加重处罚条件。有学者主张,徇私要件可以包容评价受贿行为,当同时触犯徇私渎职犯罪与受贿罪时,应当仅认定徇私类渎职犯罪,如此方能禁止重复评价,保障人权。[19]笔者则不这样认为,在渎职犯罪的整体把握上,徇私舞弊型渎职罪中的徇私系犯罪动机,行为人徇私行为不在渎职罪评价范围之内,如构成犯罪的可由其他刑法条款进行评价;并且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主观要件,而非客观要件,作为特殊主体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客观上利用本人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则应构成渎职犯罪。综上所述,受贿罪与徇私舞弊型渎职罪之间不存在想象竞合或法条竞合的关系,行为人受贿又渎职的不成立牵连犯或吸收犯,属于实质数罪。
对于行为人实施的数个独立的危害行为,如果各行为之间并无特殊关系,一般应对数行为进行数罪并罚,这样方能对各个危害行为进行充分的否定性评价。渎职犯罪的论处应当从严密法网的立场出发进行解释,对于数个行为符合数个犯罪构成要件,并且侵犯了数个保护法益的,择一重罪论处不能完整评价行为人的行为,除法律有特殊规定以外,一般应当数罪并罚。在处理受贿牵连渎职的行为时,除《刑法》第399条第4款规定的情形以外,一般都应当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