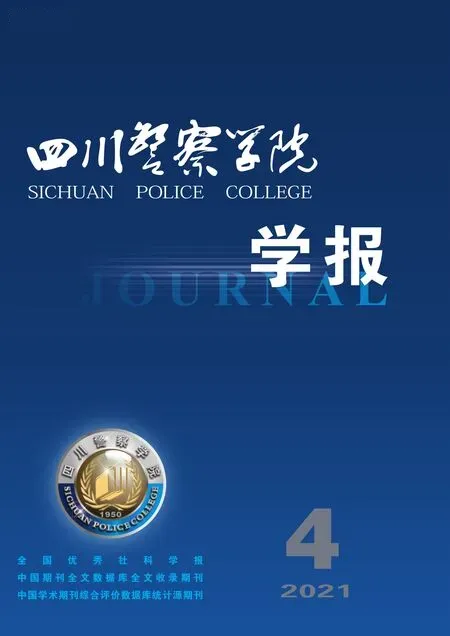犯意引诱型诱惑侦查裁判规则实证研究
毕清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福州 350108)
实践中对于那些具有常习性、隐秘性高而取证困难的特定犯罪,侦查机关有时会以“特情人员”隐匿身份使用所谓的“陷阱”或“提供机会条件”等方式抓获犯罪嫌疑人,这类侦查手段在理论上被称为诱惑侦查,并根据被诱惑对象此前是否具有犯罪倾向划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引诱型”。2018 年《刑事诉讼法》第153 条规定将诱惑侦查纳入法治化轨道。对此,理论界普遍认为该153 条的但书条款部分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实施犯意引诱型的诱惑侦查手段,但并未从整体上否定诱惑侦查手段的合法性①。据此,本文对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展开进一步分析。
“犯意引诱”一词通常被认为来源于日本,目前学界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犯意引诱的界定,如对“犯意引诱”“数量引诱”与“诱惑侦查”等相关概念的区别[1]。当然也有关注到“犯意引诱”的证明等问题,例如,台湾地区林钰雄教授认为,被告人客观上是否具有犯罪的犯罪嫌疑、主观上是否具有犯罪的意图、被告人最终的犯罪意图是否超越了引诱的界限、警察引诱的方式和强度是否对被告造成了促使其犯罪的压力是认定警察的引诱行为是否属于犯意引诱的四项标准[2]。针对同一问题,不同学者的认识存在差异:艾明认为对于“犯意引诱”的认定上,不仅要审查被引诱者,还应当审查侦查机关行为的合法性[3];田宏杰则认为被引诱者必须存在重大犯罪嫌疑是启动正当的诱惑侦查的前提,以引诱行为本身不能与犯罪意图或行为有因果关系为界限[4]116-126。就犯意引诱的法律后果而言,翟金鹏教授则认为若被告并无初始犯意,被引诱行为一般不会产生客观危害结果,故没有犯意的被引诱者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5]。由此可见,学界对“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方面入手,以合法的诱惑侦查为切入点对犯意引诱进行考察,反映出了学界较少对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进行独立观察,缺少了相关裁判规则的实证研究。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不得诱使他人犯罪”是单纯不得引诱犯罪人产生犯意,还是需要从整体上判断侦查机关的行为形态以及手段是否妥当,法律上既无明确标准,实务中对相关案件的处理也较为混乱。为此,本文拟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法院裁判过程中在认定是否存在犯罪引诱问题上的论理进行归纳总结,继而提炼出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对犯意引诱所持的标准与规则。
一、法律法规文本中的“犯意引诱”
为了打击毒品犯罪、集团犯罪等具有高隐蔽性、高程度组织化犯罪行为,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多采取了隐匿身份、诱使被侦查对象落入圈套等手段,这些特殊手段大大打击了此类特殊犯罪行为,相应的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为了规范由此涉及的问题,相关司法机关陆续出台了一些规范文件。
(一)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司法实践中对于侦查手段中的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的判断标准主要依据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相关规定。实践中,侦查机关在毒品案件侦查中多采取诱惑侦查的手段,但是无论是司法实践还是理论界都对诱惑侦查到底是国家追诉犯罪还是制造犯罪产生了极大的争论。作为传统侦查手段的补充与辅助,“采取一定诱惑手段”“提供条件或制造机会刺激犯罪发生”将诱惑侦查②[4]116-12中侦查机关是促使犯罪人犯意暴露还是使犯罪人产生犯意的问题,特情人员受到公安机关支配再去寻找卖家的行为是机会提供型犯罪还是犯意诱发型犯罪的问题抛了出来。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将犯意引诱定义为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③。对“持毒待售”“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采取特情贴靠、接洽破获的案件则认为不存在犯罪引诱。对于存在犯意引诱情节的案件,《会议纪要》规定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从轻处罚。除此之外,《会议纪要》还对“机会提供”“犯意引诱”“数量引诱”和“双套引诱”进行了识别④。
(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2018 年《刑事诉讼法》对辩护、证据、侦查等进行了大范围修改,对侦查工作影响重大而深远,为了保证公安机关正确贯彻执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公安部对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进行了相应的规定。相对于2018 年《刑事诉讼法》的153 条,2020 年修改后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71条⑤肯定了部分诱惑侦查手段的存在,但排除了“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的合法性,并且比《刑事诉讼法》153条但书“不得诱使他人犯罪”更进一步明定“诱使他人犯罪”是不得采取各种方式“促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其与2008 年《会议纪要》对“犯意引诱”的定义相符。第273 条⑥规定合法的诱惑侦查与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肯定了合法诱惑侦查收集的证据的合法性,但对“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收集的证据是否合法未做规定。
另外,厘清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与控制下交付的适用情形,须识别诱惑侦查与控制下交付。根据《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相关条款⑦,控制下交付系法定侦查措施之一,由此取得的证据并无合法性及量刑的影响。控制下交付与诱惑侦查最显著的区别是,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在案件中并非仅仅是知情者或监控者,而是有直接介入案情之中,促使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由于部分特情侦查会诱发行为人的犯意即侦查手段超过诱惑侦查的合理范围,故会对定罪量刑产生影响。
(三)“地方性”规范中的“犯意引诱”
1.四川省公检法三机关《关于贩卖毒品案件有关犯罪预备问题的意见》。2001 年四川省公检法三机关针对四川省毒品犯罪案件中禁毒侦查部门在运用诱惑侦查手段时存在的问题联合制定了《关于贩卖毒品案件有关犯罪预备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肯定了公安机关可以使用合法的诱惑侦查手段,同时第6 条规定“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中,严禁引诱犯罪”。结合该《意见》第1条和第2条的规定,使用诱惑侦查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有犯罪预备行为即“为贩卖毒品准备工具、制造条件”⑧,这是四川公检法认定毒品案件诱惑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犯意的判断标准,若符合上述条件之一,公安机关对此采取诱惑侦查手段,则就不应认定为存在犯意引诱情节,其侦查行为是合法的诱惑侦查行为。
2.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指导意见》。为进一步依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准确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广东省各级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经验以及2002年的实际情况,对毒品犯罪案件审判实践中亟须解决的若干问题提出了相关意见。其中对于特情介入的问题,该意见认为在以下两种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属于犯意引诱,应从轻处罚:(1)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无犯意;(2)特情主动提出、多次要求等手段引诱。但是存在以下几种情形,不宜认定为“犯意引诱”或“数量引诱”:(1)特情虽主动提出,但被告人对此一拍即合;(2)被告人积极实施毒品犯罪行为。
并且对于特情介入的案件中不能确定属于引诱,但难以排除引诱因素的,《意见》规定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酌情考虑,不宜对被告适用死刑的量刑标准。
3.辽宁省公检法三机关《关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辽宁省公检法三机关结合本省毒品犯罪案件实际情况,对办理毒品案件中涉及的特情引诱问题提出相关意见。首先,对存在犯意引诱与数量引诱的案件的量刑作了区分:对于具有犯意引诱的被告人,应从轻处罚,且无论毒品数量多大,都不能判处死立执;而具有数量引诱的被告人在从轻处罚时,若毒品数量标准超过死刑标准,一般情况下也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次,针对间接受特情引诱的被告人,该意见规定应对被告从轻处罚,且在达到死刑数量标准时,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另外对于是否存在特情引诱不明确的案件,侦查机关不予说明或案情存在矛盾,不能排除存在特情引诱情况的案件,量刑时应予以考虑,审慎使用死刑立即执行。最后,对非特情引诱情况作了认定,意见规定只要非特情引诱人,受侦查机关支配,所起的作用和特情一样,那么仍然应该在量刑上对被告人给予考虑。
二、审判实践中的犯意引诱
(一)研究样本情况
在“无讼案例”法律信息数据库中以“犯意引诱”为关键词,检索判决书全文中出现“犯意引诱”此词的刑事判决书为7008 篇⑨,其中贩卖毒品案件为5986 篇。以“诱惑侦查”为关键词,检索判决书全文中出现“诱惑侦查”此词的刑事判决书为325 篇,其中贩卖毒品案件为230 篇。以“犯意诱发”为关键词,检索判决书全文中出现“犯意诱发”此词的刑事判决书为25篇,其中贩卖毒品案件为10篇。由于本文需研究实务中法院对犯意引诱型侦查情节案件的处理方式,因此笔者将随机提取含有“犯意引诱”和“诱惑侦查”两词的刑事判决书300份作为样本进行分析比较。
从上述数据可知,在含有“犯意引诱”和“诱惑侦查”的案件中,由于主要是依靠关键词检索,可能存在一篇判决书中关键词重复或者几个关键词都存在的情形,只能避免显示案件是否构成犯意引诱具有很大的争议,故笔者将对这300份案件以“案件类型”“辩方抗辩理由”“公诉方提起公诉的理由”“法院裁判情况”“法院判断标准”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就案件类型而言,300 份案件中,涉及毒品类犯罪的案件有264 份,涉及非法买卖、持有、制造枪支、弹药案件有13份,涉及敲诈勒索罪的案件有5份,涉及非法经营罪的案件有3份,涉及盗窃罪的案件有3份。
(二)样本所涉及的控辩审三方情况
就辩方提起的抗辩理由而言,300 份案件中除36 份案件未提及相关关键词,其余案件都有提及“犯意引诱”“诱惑侦查”等词汇。其中,以“犯意引诱”作为抗辩理由的案件有93 份,以“诱惑侦查”作为抗辩理由的案件有111份,提及存在“特情引诱”现象的判决书有35篇,辩护人认为存在数量引诱现象的案件有43篇,辩护人提及其余类似词汇的案件46份。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案件可能存在辩护人同时主张存在“犯意引诱”“诱惑侦查”和“数量引诱”,例如在300份案件中,“犯意引诱”和“诱惑侦查”两词同时出现的判决书有12 篇,“犯意引诱”与“数量引诱”同时提及的判决书有32篇。这种现象表明辩方自身对抗辩理由的提出就是混淆的,并不能准确的定义诱惑侦查手段与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的关系。
就公诉方提起公诉的理由而言,除了对被告人以相关罪名提起公诉外,公诉人也会判断是否存在“犯意引诱”或“特情引诱”情节以提起量刑建议。在300 份案件中,以“犯意引诱”和“诱惑侦查”作为量刑情节的案件有6 件,以“数量引诱”作为量刑情节的案件有2 件,反驳辩护人提及的存在“特情引诱”和“诱惑侦查”情节的案件有4 件,其余案件均未提及诱惑侦查手段及其相关的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这些数据表明在司法实践中检方甚少对侦查机关的行为是否构成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进行判断认定,检方对此类案件多是不提及不判断的态度,从侧面反映出,实务中对涉及犯意引诱相关问题的证明责任并未完全由控方承担。
从法院裁判情况来看,300 份案件中法院明确认定存在犯意引诱情节的案件50 份,否定存在犯意引诱情节存在的案件占多数,达251份(其中一份为同案两被告不同认定),故可知审判实务中法院对辩护人及其被告提出的具有“犯意引诱”等侦查手段的意见,多是采取否定结果。
三、犯意引诱存否的裁判类型
(一)肯定存在犯意引诱的裁判情形
1.明确肯定存在犯意引诱。明确肯定存在犯意引诱,即法院正面认定侦查机关的行为属于犯意引诱。在50份认定存在犯意引诱的案件中,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明确表明存在犯意引诱情节的案件有38份,例如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何某贩卖毒品一案,法院认为“何某本没有实施贩卖毒品的主观意图,而是在公安特情人员谢某的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从而实施贩卖毒品犯罪,故本案存在犯意引诱,依法应当从轻处罚。”⑩在实际判决中,法院援引相关事实及证据认定侦查机关的行为存在犯意引诱情节的案件多属于公安机关先查获毒品,再利用被查获的毒民为特情人员接洽贩毒者佯称购毒,公安机关在约定地点当场抓捕贩毒者这类情形。由此从侧面表明法院在认定存在犯意引诱的判断因素中,“特情人员主动求购”是尤为重要,具体又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1)法院根据单独的线人主动求购即认定存在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例如,安徽省无为县人民法院审理的邰某某聚众斗殴、贩卖毒品一案中,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邰某某在起诉书指控的第3起贩卖毒品犯罪中,因诱惑侦查被公安机关查获,同时因犯意引诱使得该宗冰毒自交易一开始即不可能完成,系犯罪未遂,均依法从轻处罚。”⑪此案中法院就依据单一的特情人员主动求购的事实判定存在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
(2)法院根据侦查机关布控+特情主动求购认定存在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例如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江某某贩卖毒品一案。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指“被告人江某某的毒品犯罪行为系特情引诱,属犯意引诱。”⑫此案中公安机关抓获匡某某后,以匡某某作为侦查手段的延伸,匡某某在控制中主动与被告人联系诱使被告人贩卖毒品,侦查机关并对此展开一系列布控。法院依据此案件事实和证据判定匡某某属于侦查机关的特情人员,其行为属于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认定该情节属于犯意诱发型侦查手段。
(3)法院根据侦查机关控制+特情主动求购+毒资或所贩毒品为公安机关或特情人员安排提供此三因素判定侦查手段存在犯意引诱。例如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何昌伟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一案中⑬,特情人员王某某主动与被告人何昌伟电话联系购买毒品事宜,且王某某购买毒品的200 元毒资由公安机关提供,之后被告人何昌伟在约定地点将毒品交付给王某某时当场被公安机关抓获。又如姚敏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一案中⑭,法院经审理查明特情人员李某在向姚敏电话联系要求购毒的经过中,姚敏表明其“手中没有毒品,且没有钱拿不到毒品”,而李某却主动向姚敏汇入购买毒品的毒资。这两个案件法院最终都判定侦查机关存在犯意引诱,故可知,特情人员或侦查人员在行为上的主动界限是判断是否存在犯意引诱重要因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38 份判决书中有10 份案件法院只是单纯表明采纳辩护人或被告人的意见,并未采用相关案件事实和证据说理是如何认定存在犯意引诱的,或者法院阐述理由简略,甚至存在未引用相关事实和证据来说明被告人为何是在特情介入引诱下形成犯意,又是如何认为被告人之前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的现象,缺乏文书说理。
2.反面印证存在犯意引诱。除了上述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明确认定存在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的38 份案件外,其余12 份案件,法院在文书中均采用了“不排除存在犯意引诱情形,依法从轻”的表达。此种方式表明,法官虽未在判决书中直接明确肯定犯意引诱的存在,但从判决书的的言语表达中可以反面印证出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超过合法限度。如在豆虎东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一审判决书中,法院在判定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的侦查手段是否合法时,法官认为“本案中,证明被告人豆虎东持有毒品待售的证据不足,特情人员介入后,不排除特情引诱情形即犯意引诱情形的存在。”⑮又如潜江市人民法院审理的杨放新贩卖毒品案⑯,对于辩护人提出的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超出诱惑侦查的合法范围的辩护词,法官在结合案件事实和证据后认为“不能排除存在犯意引诱”,最后法院都对被告人的量刑予以了从轻,虽然未直接在判决书中明确认定存在犯意引诱,但依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采取了“不排除犯意引诱情形存在”的表达方式,对被告人量刑上予以了从轻,反面印证了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采取了犯意引诱型的侦查手段。
(二)否定存在犯意引诱的裁判情形
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判决文书中表明不存在犯意引诱时,要么认定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属于诱惑侦查中的机会提供型,要么直接否定存在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目前学界认为判断是否属于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应从“犯罪人表现”“引诱力度”“引诱的危险性”出发,而在实际的判决中,法官考量的因素是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被告人已持有犯罪的主观意图,主要表现为“主动电联”或“主观上积极主动”(在251份不存在犯意引诱情节的案件中占比31%)。如张某某贩卖毒品案中⑰,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三起犯罪事实存在犯意引诱情节的意见,法院认为“虽然是公安人员运用特情破获,但当时张某某主观是积极主动的,且毒品交易完毕后张某某又实施了贩卖毒品的犯罪,综合全案事实足以说明张某某已持有毒品贩卖的主观意图。”判断被告人是否已有犯罪意图,是一个综合判断因素,需要法官综合全面的评价行为人的主观态度及其行为。多数案件中,法院主要从犯罪人在行为前、被引诱时、行为后的表现着手,判断被引诱者在各个阶段的主观态度是否积极主动。
2.被告人在接到买家购买信息后在较短时间内就准备好毒品或犯罪物品,表明此前被告人即具有毒品交易倾向或犯罪倾向(在251份不存在犯意引诱情节的案件中占比9%)。在这里“较短时间”是法官进行审查判断的最重要的判断标准之一,而多长时间是“较短时间”?在吴义总贩卖毒品案中,对于吴义总在当天短短30 分钟后就准备好毒品并到达交易地点进行交易这一事实,法官认为“被告人吴义总的行为表明其案发前就存在毒品犯罪的故意和行为,发生本案并非是特情诱惑促成的,且特情仅仅要求购买90元毒品,并非引诱实施大量毒品犯罪,故本案不存在犯意引诱及数量引诱的情形。”⑱又如杨某贩卖毒品案中⑲,杨某短时间就与特情达成交易。
由此可知,“短短时间”主要表现为被告人与特情之间求购与达成交易的时间长短,应以正常一般人对短时间的判断为标准。其实此种判断因素也是从侧面在考量被告人行为、态度的积极性,被告人的行为往往表现为“随即交易”“一拍即合”“立即答应”“短短时间交易完成”等状态,其态度总体上呈现积极性。
3.被告人在实施本起犯罪前已经实施过同类型犯罪行为(在251 份不存在犯意引诱情节的案件中占比13%)。如孔龙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二审中⑳,法官的主要理由是孔龙辉在实施本起犯罪之前已实施过两次售卖毒品的行为,说明孔龙辉主观上已经具备犯意并已着手实施了犯意,故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仅是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其犯罪实施的特定条件和机会,不存在诱发无罪者犯罪的问题。又如但文洁、但元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容留他人吸食毒品一案21可以看出,犯罪人之前是否有过同类型的犯罪行为是法官判断行为人在案发前是否已具有犯罪主观意图的重要依据。
4.法院认为案件中并不存在“特情人员”或“线人”,侦查机关是依据相关“举报”或“线索”抓获被告人,故案件不存在犯意引诱情节(在251 份不存在犯意引诱情节的案件中占比12%)。此种裁判理由具有特殊性,在裁判文书中多表述为“本案是同案关系人某某为了立功,在警察控制下主动联系上家进行的毒品交易,并无特情参与,不存在特情引诱的情况。”22或“本案系公安机关根据举报人举报后布控将被告人抓获归案。”23这类型的考量因素,模糊了案件中“特情人员”“线人”的性质,否定了“特情人员”作为公安机关侦查手段延伸的存在。
5.被告人案发前已持有毒品或犯罪物品待售,侦查机关采取特情贴靠、接洽而破获的案件,不存在犯意引诱(在251份不存在犯意引诱情节的案件中占比11%),如文红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一案24。对于行为人在案发前已持有毒品待售这一因素,根据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贴靠、接洽而破获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诱,应当依法处理。实践中法官也主要依据此规定裁判案件。
实务中,若案件中存在“犯罪前已出售过毒品”+“已持有待售毒品”或者“犯罪前已有吸食毒品的行为”+“已具备出售大宗毒品的能力”几种情形的结合,裁判法官会当然认为侦查行为不构成犯意引诱。例如毛某一案中,对于辩护人提出的贩卖毒品行为系犯意引诱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被告人毛某持毒待售,并有出售记录,其主观上具有贩毒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贩毒行为,不存在犯意引诱。”25
6.不构成犯意引诱,但构成数量引诱(在251份不存在犯意引诱情节的案件中占比4%)。吉地拉鬼、雷保民贩卖毒品案、林以保、王君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等,法院都认为不存在犯意引诱,但构成数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7.无证据证实侦查机关具有犯罪引诱的行为(在251 份不存在犯意引诱情节的案件中占比9%)。如陈俊非法持有毒品一案中26,对于是否存在犯意引诱这一争论,法院以无证据证明驳回了辩护人的意见。这种无相关证据证明存在或者不存在犯意引诱的情形,法院直接裁判为不存在犯意引诱情形做法,与上文所言反面印证存在犯意引诱情形的做法是相互矛盾的。并且这里的“无证据”是指的辩护人没有证据还是公诉人没有证据?谁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在王玉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中,法官认为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中没有证据证明朱某系特情人员,且存在犯意引诱的事实,否定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可以看出本案是公诉机关承担了证明是否存在犯意引诱的举证责任。
可是在多数案件中,这里的“无证据”是指辩方及被告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侦查机关侦查行为存在犯意引诱的主张,如苏某、邓某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案。是否存在犯意引诱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谁承担?这个问题值得考究。
8.未对辩护人或被告人提出的犯意引诱的辩护意见进行说理,只是单纯的进行了否定(在251份不存在犯意引诱情节的案件中占比11%)。如陈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一案中27,法院对于辩护人提出的侦查机关存在诱惑侦查情节的意见,以“毒品犯罪在司法实践中需要采取特情介入的侦查方式,本案不存在犯意引诱情形”为由,不予采纳。
从前述被告人有无同类型犯罪前科、是否“持有待售毒品”、是否有主观积极的行为或态度等来看,这些因素都是法院在判断犯罪人是否已持有犯罪意图上进行的细分,它们都可以成为判断被告人是否已有固定犯罪的主观意图或行为的综合判断因素。从上述案件的观察可看出,目前法官在判断是否具有“犯意”时,主要聚焦在被引诱对象即被告人的行为表现上,对于侦查机关在侦查中采取的引诱事项是否具有危险性、其行为是否超过“引诱力度”等并未进行过多审查,这与理论上所存在的争议是不同的。前述判断因素中看似可与“引诱力度”挂钩的是法院对于“数量引诱”的认定。但是“数量引诱”是属于合法的机会提供型侦查手段,与“犯意引诱”是两个并行的概念,其并不能作为判断是否具有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的因素。因此,实务中对于“引诱力度”“引诱事项的危险性”的审查是缺少的,法院应当对此二者引起重视。
四、存在犯意引诱的裁判结果
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不得诱使他人犯罪”,明令禁止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采用引发他人犯意的侦查手段。法官在确认侦查机关采用了犯意引诱型的侦查手段时又将如何处理,实务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将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所获取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在300份案件中,共有24份案件中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审判中主张以犯意引诱侦查手段收集的证据为非法证据,应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如果排除此证据无法达到定罪标准,法院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但是此种主张法院甚少采纳,既存在不采纳犯意引诱和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形,又存在采纳犯意引诱的主张,但不采纳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如徐明、康山夫贩卖毒品罪一案中对于辩护人认为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不合法,存在犯意诱发的情节,其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的主张,法院并未采纳。尽管有《刑事诉讼法》第52条有关于“严禁以引诱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但由于《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的规定28,故实务中法院多数的做法就如浙江舟山普陀区法院审理的高从芳贩卖毒品案一样29,甚少有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形。
(二)将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作为被告人除罪的理由
这一观点认为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具有欺骗性、引诱性,侦查行为作为国家打击犯罪的手段实际上却促使了犯罪发生,损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故对于被采用犯意引诱侦查手段的被告人,应当运用个人排除刑罚事由,宣告无罪。此理论界的观点,除了我国台湾地区法院有判决外30,目前大陆地区尚无此种判决。虽然法院无此判决,但实践中却有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将此作为除罪的理由。例如在300份案件中,有8份案件中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主张“犯罪事实系犯意引诱不应认定为犯罪”,但是在这8 份案件中,法院都没有采纳辩护人及其被告人的意见,而是对构成犯意引诱情形的被告人量刑上予以了从轻。
(三)将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作为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情节
案件中若存在犯意诱发型侦查情节,理论界的一种观点是将此作为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在刑罚上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司法实践中,法院多依据2008年的《会议纪要》的规定对被告人依法从轻处罚。
在判决书中还存在一种情形即法院认为“虽不存在犯意引诱情节,但因特情介入,犯罪行为处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没有流入社会,应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此种观点是将特情介入+侦查机关控制相结合,认为被告人贩卖的毒品或犯罪物品不可能流向社会,不可能给社会造成危害,将此作为量刑情节对被告人予以酌情从轻处罚。在此种情形下,法院已经明确否定了犯意引诱侦查手段的存在,若又因合法的诱惑侦查或特情介入对犯罪人予以酌情从轻处罚,此种做法是否合理?2008年的《会议纪要》在第六章“特情介入案件的处理问题”最后一条的规定31和辽宁省公检法三机关《指导意见》对间接引诱的规定,似乎上述情形法官的做法是合理的。但是无论是何种情况予以量刑从轻,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这些规范性文件并不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正式的法律文件,在其适用上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
除此之外,对于有可能存在犯意引诱情节的案件,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是定既遂还是未遂,在实践中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在300份案件中,有29份案件的辩护人及其被告人都提出了存在犯意引诱,犯罪未遂的辩护意见。在曹文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中,一审法院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案件中存在犯意引诱的情节,应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从轻处罚;鉴于曹文辉在犯罪过程中被抓,系犯罪未遂,比照既遂犯减轻了处罚。检察院在二审中予以抗诉,主张案件不存在犯意引诱,其行为已既遂,原审判认定贩卖毒品未遂,系适用法律错误。在之后的审判中,二审法院否定了案件存在犯意引诱情节,并认为曹文辉已经实际着手实施犯罪,是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属犯罪未遂,最后以因特情介入,毒品未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性较小对曹文辉酌情从轻处罚。
对于存在犯意引诱情节下,法院对该犯罪行为是定既遂还是未遂,笔者在3份判决书中发现法官对此作出了未遂裁判,其余判决书均否定了辩护人关于未遂的意见。如邰某某聚众斗殴、贩卖毒品案32。
对于认定既遂的法院的裁判理由多为如“在犯意引诱不成立的前提下,吉地拉鬼已将毒品带入双方的交易现场,故应视为犯罪既遂”33“贩卖毒品的行为已进入交易环节,根据相关规定性”“对于犯罪未遂问题,通过但文洁与特情人员之间毒品交易成功,应认定为犯罪既遂”。虽然贩卖毒品罪只要完成了毒品交付的就是既遂(非法药物类犯罪,行为人只要完成了任何一个危险品的流通,就成立犯罪既遂),但由于审判实务中大多数毒品案件被告人被抓获时正处于买卖交易状态完成时或待完成时,若单纯的认为“贩卖”是购买和出卖两个行为,这样就会导致侦查机关控制被引诱者是否构成既遂或未遂的问题,即侦查人员是否允许毒品在现场交易将直接关系到犯罪的既遂、未遂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行为人以贩卖毒品目的实施了购买毒品行为或将持有的毒品带到与买方约定的地点交易的,应按既遂处理。在运用特情介入的案件中,行为人犯意形成在前,特情介入在后并且只是为行为人贩卖毒品提供一个机会和交易对象,则对此种情形,应按照行为人本来的意思和行为处理,若被告人已经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应认定为既遂。若行为人犯意是特情介入后产生的,且特情人员诱使了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其犯罪行为其实是无法构成既遂的。
目前,我国实务中对已认定为存在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的案件,最终的裁判结果都是采取2008 年《会议纪要》的做法,对被告人的量刑予以了从轻。但是笔者结合目前的实务案例分析认为,确定存在犯意引诱的法律效果方面,宜采认定被告人无罪的观点。
首先,根据刑法体系与理论,若该犯罪行为的产生是侦查机关使用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引诱、挑唆、违法制造的,那么犯罪人的行为就应属于个人排除刑罚的事由,且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其次,“犯意引诱型”侦查行为也严重侵犯了被告的权利,违背了刑法应有的人权保障以及社会保护机能,违背了刑罚的预防目的,故明确否定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才能使刑法的预防理论达到效果。
并且,实务中法官并不是仅对存在犯意引诱型侦查情形的被告人量刑上予以了从轻,在有些仅仅存在特情介入、未认定存在犯意引诱的案件的被告人也予以了从轻,理由是“鉴于特情介入,毒品未流入社会,未造成实际危害,酌情从轻。”正如其所言的“毒品未流入社会,未造成实际危害”,那么犯罪行为的产生是由于侦查机关使用引诱手段挑唆、违法制造的,且被告人在该具体案件中也并未对社会造成实际危害,那为何还要对其予以量刑呢?故笔者认为,在被引诱者刑事责任方面,若法官判决明确认定存在犯意引诱情形,被引诱行为一般不会产生客观危害结果,那么没有犯意的被引诱者就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另外,对于实施引诱的公务人员或特情人员是否构成其所引诱或帮助犯罪的共犯,法律上并没有相关规定,实务中法院也没有相关判决。若认为需要对相关的侦查人员及相关特情人员的行为予以定性,则可以刑法上的未遂教唆形态进行分析讨论,若采共犯独立说,则不可罚;若采共犯从属说,则仍具有可罚性。若构成犯罪,可对其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五、犯意引诱型侦查的规制路径
(一)以立法定义犯意引诱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处理存在诱惑侦查的案件主要依据的是最高法院印发的2008年《会议纪要》,虽《刑事诉讼法》第153 条规定了“不得引诱他人犯罪”,但始终未明确提出认定犯意引诱的规则,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同样没有对如何认定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作出解释,这也导致了在审判中法院对于犯意引诱的认定无法可依,仅依据2008 年《会议纪要》对犯意引诱的认定以及对相关法律后果作出的规定,法院在审理可能存在犯意引诱的案件时,容易对犯意引诱与诱惑侦查等概念混淆。
在前文中的概念辨析中可知诱惑侦查是当前侦查机关侦查犯罪普遍使用的一种侦查手段,存在着几种情形。日本学者田口守一认为“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或民间侦查合作者促使第三人犯罪,将其逮捕,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两类。”[6]日本学界为了区分合法的诱惑侦查和非法的诱惑侦查而对诱惑侦查进行了“两分法”,在审判实务中更是基于“两分法”将诱惑侦查中合法的情形定义为“机会提供型”,非法的情形则为“犯意引诱型”[7]。2004 年7 月12 日,日本最高法院首次针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要件作出的判决34与过去二分说的观点相比较而言,明显更倾向采纳实质的观点,即将诱惑侦查的案件分为三个类型35,由此可知,日本实务中的重要判例将“犯意引诱型”36定义为合法诱惑侦查的相反面,该犯意引诱概念清晰且有相关解释和法律规定。
反观我国,由于主要依据最高法院印发的《会议纪要》,因此审判实务中就存在着辩护人或者被告人,更甚至公诉机关和法院对于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的概念界定不清。如辩护人采用“诱惑侦查”“数量引诱”等属于合法侦查行为的概念来作为存在“引诱犯罪”的抗辩理由,并且控辩双方对此展开一系列辩论,真正需要认定审查的“犯意引诱”反而被忽略了,这就导致实务中对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的认定标准不一,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态度模糊不清。
(二)以立法确定犯意引诱的判断基准
犯意引诱定义的模糊一方面也导致了我国审判实务中对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的认定态度的模糊、混乱,并未形成如日本、美国、欧洲人权法院一样清晰的认定条件,所以在实务中无论是公诉人还是法院在否定存在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情节时所援引的理由都不一样。由于受《会议纪要》对“犯意引诱”的定义,司法机关在认定侦查机关的行为是否属于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时,将重点放在了侦查机关的行为是否引起犯罪人的“犯意”上。结合上文的实务分析也可以清晰看出,目前司法机关对此的审查主要集中在犯罪人的行为和主观表现上,缺乏对侦查机关本身行为限度的关注。
犯罪人的行为和主观表现的审查也存在单一性问题。例如在前文中,法院有单纯依据被引诱者之前存在同类型犯罪行为就认定被诱惑人已持有固定犯罪的主观意图。这存在一定偏颇。笔者认为即使被引诱者之前实施了同类型犯罪行为,也并不能肯定被引诱者对此次犯罪已存在犯意。被引诱者并不是意味着必须是没有犯罪的人,而是要求被引诱者在该具体案件中,被引诱之前没有犯意,法官重点在于审查该具体案件中犯罪人的“犯意”何时产生,这是对该具体案件中行为人主观和客观的综合判断。例如以美国的Jacobson v.United States 案37为例,法院最后判决被告主张的“引诱犯罪”的抗辩成立,主要观点就是Jacobson是不警惕的无辜者,即被告的犯意是由侦查人员的引诱行为引起的,被告人在被引诱前没有犯意。若被告人之前具有犯意,则侦查人员的行为仅仅是对不警惕的罪犯提供了不寻常的诱因或条件。从此案就可以看出,不能单纯以被引诱者之前存在同类型犯罪行为就认定被诱惑者已持有固定犯罪的主观意图。
实务中,目前我国对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的认定缺乏对侦查机关本身行为合法性的审查。结合2018 年《刑事诉讼法》第153 条但书“不得诱使他人犯罪”,对公安机关采取的“隐匿身份侦查措施”进行的限制来看,《刑事诉讼法》对公权力机关侦查活动进行了自我限制,强调了侦查行为的合法限度。因此在新修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背景下,法官再在实务中单纯依据《会议纪要》的规定,青睐主观审查的标准就有点不合时宜。毕竟“主观基准会促使犯罪挑唆问题的面向从警方行为的妥当性过度转移到行为人品格性向及前科的审查使刑法从行为罪责沦落为人格罪责。”[8]因此笔者认为可以立法,明定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的认定标准,实务可采取将“主观审查说”和“客观审查说”相结合的混合审查模式判定犯意引诱相关问题。
一要注重审视被引诱者的主观层面。在主观审查方面,要落实在该具体案件中,对被引诱者行为和主观进行审查。可以参考美国的主观审查基准,判断被告人在被引诱前是否具有犯意。第一,考量被引诱者之前是否具有类似的犯罪行为,若有,则需考察实施该类似犯罪行为的次数和与此次被引诱犯罪行为的间隔时间。第二,审查被告人被引诱之后的行为态度,这里可以参考2001年四川省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制定的《关于贩卖毒品案件有关犯罪预备问题的意见》的做法,即以被引诱者之前是否实施了犯罪预备的行为来具体判断被引诱者的“犯意”是何时形成。若被引诱者为该犯罪行为主动准备了工具、制造了条件,则该被引诱者在主观和行为上是积极主动的,就可认定在该诱惑侦查中被引诱者之前就具有犯意。另外,还应将被引诱者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是否可以主动放弃犯罪纳入考察因素。第三,将被告人实施犯罪的能力,如有无金钱购买毒品或犯罪工具、有无时间实施犯罪行为等纳入判定因素。除此之外再行考量被告人的公共评价和被告人的后续行为及言论等因素。
二要重点考察侦查行为的合法界限。在客观审查方面,需要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是否超出合法限度进行判断。第一,需要判断侦查机关采取此种侦查方式有无必要,该被引诱者是否已经具有犯罪嫌疑。若侦查机关针对被引诱者及其涉嫌的事实已经先行展开了一定的调查程序,但该调查程序无法取得侦查效果,那么此时采取特情介入的手段就是适宜的。第二,需要审查“特情”“卧底”“线人”的行为是否属于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在前述实务分析中,可以看出有些案件控方和法官否定了“特情”“卧底”“线人”是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延伸的。诱惑侦查的行使主体在我国现行的侦查体制下是法定以及特定的,且除非有必要是不得采取诱惑侦查措施的,故可以明确的知道其实施主体只能是侦查机关,而具体执行的人员可以不限于侦查人员还包括侦查机关所支配的人即侦查协助者。司法实践中侦查协助者参与诱惑侦查也确实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特情”“卧底”“线人”就是作为侦查协助者参与到侦查过程之中的。虽然有些案件中法官认为“特情”“卧底”“线人”是同案犯,是为了立功参与案件,并在判决的结果中认定为其构成立功,但是也不可否认“特情”“卧底”“线人”是作为侦查协助者参与到该案件中的,其行为就是侦查机关行为的延伸,所以法官就应该考察其行为的引诱次数、引诱力度、危险性和合法界限。第三,要审查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的方式和强度,超过了手段的正当性和强度,就构成了非法的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3]193-202。刑事侦查的目的是为了查明事实和保障人权,这意味着侦查机关的职责是发现犯罪且打击犯罪而不是主动制造犯罪,这也是诱惑侦查的应有之意即侦查机关不能因实施诱惑侦查而制造犯罪,不能使无犯意的人产生犯意,否则就失去了侦查权所应有的正当性。在具体案件中,法官应从诱饵的刺激性、引诱的次数、诱惑时间的长短、犯罪利益的诱惑性、侦查人员涉案程度等入手,审视侦查机关在案件侦查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三)明确不存在犯意引诱的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
实务中在对犯意引诱型侦查手段进行认定的过程中,存在着承担证明责任的混乱的问题。从有些案件可以看出,法官倾向于将证明责任科以控方,控方若不能提供有力证据有效证明不存在犯意引诱情形时,法官最后会采取存疑时有利于被害人原则,反面认定不存在犯意引诱情形。从有些案件的裁判理由来看,法官又倾向于将证明责任科以辩方,若辩方不能提供有力证据有效证明存在犯意引诱情形,则将承担不利的后果。这种混乱的情形导致同类型的案件最后有不同的裁判结果。
笔者认为,犯意引诱的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比较妥当。原因有二:一是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来看,虽然犯意引诱存在与否的问题严格意义上属于量刑问题,但人民检察院承担的有罪证明责任并不意味着检察院只能提供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基于客观公正的原则,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无罪或罪轻、罪重的证据都提交给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根据全案证据综合判断被告人是否有罪、无罪、罪轻或罪重;二是控方是国家公权力机关,其更易接近和查找证据证明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或特情是何时接触被引诱者,控方也更易就被引诱者在侦查人员第一次与其接触前被告人是否已具有犯罪意向举证,证明侦查人员行为是否逾越且超过合理怀疑的程度。
[注释]:
①这些研究主要有:翟金鹏,简远亚的《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行为非犯罪化问题研究》,载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28 卷第156 期,第109-114 页;万毅的《论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及其底限——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 条释评》,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199期,第164-168页。
②诱惑侦查是指国家侦查机关为了侦破某些重特大疑难案件,由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隐蔽身份,采取一定的诱惑手段,提供条件或制造机会刺激犯罪发生,借此抓获犯罪嫌疑人。
③详见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六章内容。
④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①机会提供,即对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贴靠、接洽而破获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诱,应当依法处理。②犯意引诱,即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无论涉案毒品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③双套引诱,即行为人在特情既为其安排上线又提供下线的双重引诱下实施毒品犯罪的,处刑时可予以更大幅度的从宽处罚或者依法免予刑事处罚。④数量引诱,即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标准的毒品犯罪的行为。”
⑤《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71 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侦查机关或者公安机关指定的其他人员隐匿身份实施侦查。隐匿身份实施侦查时,不得使用促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的方式诱使他人犯罪。”
⑥《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73条规定:“公安机关依照本节规定实施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⑦《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规定:“控制下交付是指在当局知情及监控下,允许货物中非法或可疑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其他毒品或替代物继续进行运送与交易,以此来查明涉及该毒品犯罪的人员,包括幕后指挥者和操作者。”
⑧四川公检法三机关《关于贩卖毒品案件有关犯罪预备问题的意见》:“犯罪嫌疑人有犯罪预备行为指:一是为贩卖毒品样品在四川省境内主动寻找毒品卖主;二是协定毒品样品在四川省境内主动寻找买主;三是为贩卖毒品,有商谈毒品种类、价格、数量、质量、交付时间、地点、方式、出示毒品样品、预付、收取定金、准备运输工具等情形的;四是其他为贩卖毒品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
⑨数据来源于“无讼案例信息数据库”,https://www.itslaw.com/home,案件搜索结果截止于2020年2月8日。
⑩资料来源于《(2014)渝二中法刑终字第00002号判决书》。
⑪《(2015)无刑初字第00133 号判决书》写道:“检察院在指控邰某某的第三起贩毒事实中,张某作为线人主动与被告人邰某某电话联系购买毒品事宜,被告人邰某某在约定地点准备交付毒品时当场被张某带领来的公安机关抓获。”
⑫《(2015)衡中法刑二终字第285 号判决书》写道:“本案中,匡某某因吸毒被抓获后,为立功愿意配合公安机关抓获贩毒人员。经过公安机关布控后,匡某某主动电联江某某佯称购毒,并约定毒品交易时间、地点,江某某同意交易。后江某某按约携带毒品偕其妻开车至毒品交易地点,将毒品交给匡某某时,被事先埋伏的公安人员当场抓获,并当场缴获毒品。”
⑬《(2017)鄂0104刑初435号判决书》写道:“法院认为本案存在犯意引诱,依法可对被告人何昌伟酌情从轻处罚。”
⑭《(2014)娄中刑一初字第33号判决书》写道:“法院认为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姚敏曾经有贩卖过毒品的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姚敏事前有贩卖毒品的犯意,本案存在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
⑮《(2017)甘12刑初8号判决书》写道:“法官认为特情引诱分为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犯意引诱指的是公安特情人员对没有犯罪故意的人进行引诱并使其产生犯罪行为,持有毒品待售的,即便特情人员介入,也不构成犯意引诱。”
⑯《(2014)鄂潜江刑初字第00145号判决书》写道:“法官认为本案中,贾某某虽交代其之前贩卖的毒品来源于被告人杨放新,但被告人杨放新对此予以否认,再无证据予以证实,且在公安机关安排贾某某联系被告人杨放新购买毒品之前,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杨放新持有毒品待售或者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
⑰资料来源于《(2014)额刑初字第21号判决书》。
⑱《(2015)湛开法刑初字第97 号判决书》写道:“本案的案件事实为2014 年10 月21 日22 时许,公安机关的特情人员“梁三”(化名)了解到被告人吴义总有贩卖毒品行为,主动电联吴义总购买毒品,并对数量、价格、交易地点进行了约定,吴义总表示同意。约30分钟后,吴义总到达交易地点被公安民警抓获。”
⑲《(2017)粤03刑终329号裁定书》写道:“特情人员11日23时求购毒品,上诉人与特情12日1时许即达成交易,短短时间,双方就毒品交易价格、地点、约定时间一拍即合,因此本案不存在犯意引诱。”
⑳资料来源于《(2018)闽0723刑初84号判决书》。
21《(2018)皖12刑初77号判决书》写道:“法院认为但文洁案发前曾两次因犯贩卖毒品最被判处刑罚,在该起毒品交易中就毒品数量、价格中起积极主动作用,因此公安机关对但文洁的侦查行为并不存在犯意引诱问题。”
22资料来源于《(2013)绵刑初字第28号判决书》。
23资料来源于《(2017)浙0382刑初637号判决书》。
24《(2016)沪0110 刑初375 号判决书》写道:“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文红安在与特情人员联系前已经持有毒品待售,且在特情人员向其购买冰毒时,未予丝毫拒绝就于特情人员进行了交易,因此文安红实施贩毒行为并非他人引诱的结果。”
25资料来源于《(2015)绍柯刑初字第67号判决书》。
26《(2018)鄂01刑初112号判决书》写道:“法院认为辩护人提交的视听资料截图形式要件缺失,证据形式不合法,亦不能证实照片中的男子与案件事实存在关联;该组照片交由江夏区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禁毒中队民警辨认,中队民警均表示该组照片中无本案线索中涉及的“特情”人员;同时××物业服务中心××、公安机关、陈俊的辩护人均出具情况说明证实,未调取到证实存在犯意引诱的相关证据。综上,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本案部分毒品存在犯意引诱。故该辩护意见与证据、事实及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27资料来源于《(2015)台椒刑初字第942号判决书》。
28《刑事诉讼法》第154条规定:“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29《(2015)舟普刑初字第179 号判决书》写道:“本案的证据是由特情侦查获取的证据,来源形式合法,可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在事实认定上不得以非法证据为由排除适用。”
30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台上字”第5000号判决文书》写道:“若行为人原本无贩卖毒品营利之意思,因调查犯罪人员之引诱或教唆始起意贩毒,即属陷害教唆,不能认已成立贩卖毒品罪。”
31 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对被告人受特情间接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参照上述原则依法处理。”
32《(2015)无刑初字第00133 号判决书》写道:“法院认为被告人邰某某在起诉书中指控的第三起贩卖毒品犯罪中,因诱惑侦查被公安机关查获,同时因“犯意引诱”使得该宗冰毒自交易一开始即不可能完成,系犯罪未遂。”
33资料来源于《(2013)三刑初字第00029号判决书》。
34《〈刑集〉第58卷5号》第333页写道:“该判决认为在没有直接被害人之药物犯罪等之侦查案件,仅以通常的侦查方法查获该项犯罪有困难之情形,将可疑为一有机会即实行犯罪之意思者作为对象,实施诱惑侦查,应解释为是基于刑诉法第107 条1 项所定的任意侦查,而予以容许。”
35日本将诱惑侦查分为三种,即依比例原则实施“以无直接被害人之药物犯罪等之侦查案件”,必要性原则实施“仅限于依通常的侦查方法查获该项犯罪有困难之情形”,而对象之被诱惑人已具有犯意而有实行犯罪之嫌疑者为限,作为任意侦查合法性的三个检验标准。
36日本学者认为犯意引诱的非法性在于对象案件的范围不限于“无直接被害人”的毒品犯罪等,且没有高度实施诱惑侦查的必要性,且被诱惑的对象无犯意而没有实行犯罪的嫌疑。
37基本案情为:警方因Jacobson 曾在成人书店以邮寄方式购买过含有男童及少男裸照的杂志,实施过同类型的犯罪行为,就锁定Jacobson为侦查目标,并长时间诱使其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