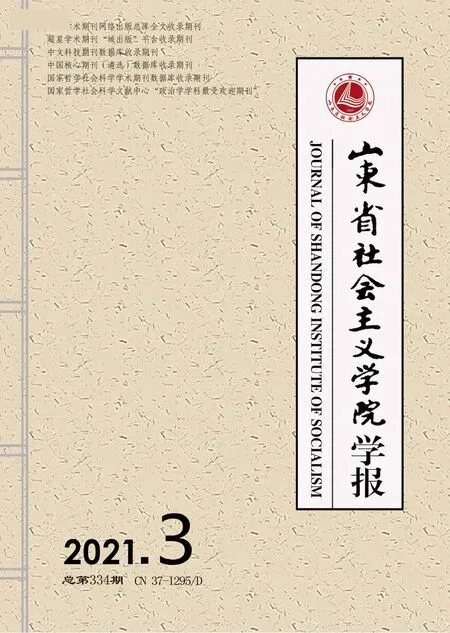《周礼》的行政制度设计及其对后世政治的影响
丁 鼎
《周礼》(又名《周官》)一书内容繁富,体例完备,结构严密,可谓体大思精。本书原来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篇。汉时《冬官司空》篇已亡佚,由于冬官司空主要掌管工程营造,所以汉儒取记载先秦手工业技术的著作《考工记》补之。
《周礼》一书通过对“六官”系统的记载和论述向读者展示了一套十分完备的社会管理系统。每一官均冠以“叙官”一节,以总括设立此官的意义、介绍此官的职掌等。对于各种官职,均是先叙其官名、爵等、员数,然后再分叙其职掌。六官的设置应该不完全是《周礼》的创造,而是渊源有自。如《尚书·牧誓》载:“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1]可见商周之际就已经有了司徒、司马、司空等职务。因此可以认为《周礼》所记述的这套六官系统及其所体现的社会管理思想,是对上古职官制度和社会管理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虽然《周礼》一书自从汉代问世后,人们即对其作者和撰作时代莫衷一是,但其记述或设计的职官制度和相应的社会管理系统却引起了当时和后世学界、政界的广泛关注,对后世历代的经学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周礼》行政制度设计的特点
《周礼》一书系统条贯,设计出一套非常完整的治国理政的职官系统。这套职官系统实际上体现了一套参酌古今而成的理想国的行政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治国理政思想。
《周礼》中六官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的首长分别是大(太)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大司空,总称六卿。《周礼》把国家的官僚机构分成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个子系统,在王的驾驭统领之下,各司其职。六官分掌王朝政务:天官冢宰掌治典,主管宫廷事务;地官大司徒掌教典,主管民政;春官大宗伯掌礼典,主管祭祀;夏官大司马掌政典,主管军务;秋官大司寇掌刑典,主管司法;冬官大司空掌事典,主管营造工程。六官又各分设数量不等的官属,形成系统的官僚机构。
朱熹曾对《周礼》六官的属性及其职掌特点做出较为简明精到的概括:“天官是正人主之身,兼统百官。地官主教民之事,大纲已具矣。春夏秋冬之官,各有所掌,如太史等官属之宗伯,盖以祝史之事用之祭祀之故;职方氏属之司马,盖司马掌封疆之政。”[2]其说甚是。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礼》是我国古代一部具有行政法雏形的著作。它构想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由王驾驭六官对王朝政务和社会生活进行治理的管理制度。这套管理体系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突出王的至尊地位
《周礼》一书设计了由六官分工合作、协同治理天下的管理体系。超然于六官之上的是君临天下的王。《周礼》一书中虽只分为六章分别论述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而无专章讲解王,但全书不厌其烦地突出显示王在朝觐、会同、祭祀、田猎等重大活动中的至尊地位,对王的车旗、冕服、礼器和乐舞等的规格做出最高等级的规定,从而突出王凌驾于六官之上的独尊地位,体现的是儒家一贯的“尊尊”思想。彭林先生通过对《周礼》六官相关记述的考察和分析将《周礼》中“王”的权力概括为如下六类:对百官的任免权、立法权、治朝权、刑狱的终裁权、主祭权、统军权。[3]其说甚是。
《周礼》在严格的等级制基础上突出显示了王的独尊地位,体现了“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六官即六大行政机构,由六卿统领,各有属佐,各有职司。而这六官及其属官不仅全直接或间接听命于王,而且全直接或间接服务于王。
《周礼》六篇不仅以天地四时经纬百官,而且六篇起首反复开宗明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①这段文字初见于贾公彦《周礼注疏》卷一《天官冢宰》(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9 页),又见于《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和《秋官司寇》各篇卷首,兹不赘注。这几句话堪称全书之总纲,其内涵就是以王为最高核心设官分职,治国理政。这可谓《周礼》顶层设计方案的宗旨所在。
(二)在朝政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特别突出礼的作用
《周礼》原名《周官》,汉代古文经学家刘歆始改称为《周礼》。刘歆的这一改动,倒也十分贴切地体现了《周礼》一书的内容特点,因为不仅《周礼》六官所涉及的“设官分职”、王邦之治、都鄙制度、“地政”构想、“教化”构想、贡赋制度等属于礼的范畴,而且夏官司马主掌的军政和秋官司寇主掌的刑狱、法制等也可归于礼的范畴。
《周礼》一书中不仅六官所涉及的政事多与礼相关,而且特设“春官宗伯”一官,专掌礼事,突出显示了作者以礼治国的价值取向。
《周礼》一书中不仅由春官宗伯专掌礼事,负责对万民的礼义教化,而且其他各官也都有对民众进行礼义教化的责任。如《周礼·天官》述“大宰”之职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4]《周礼·地官》述“大司徒”之职亦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县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乃施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5]这是说,从周历正月初一开始,一连十天由太宰和大司徒分别向诸侯国及王畿内的采邑宣布治典与教法,主要方式就是将之形成文字挂在象魏上以供民众观看。显然这里所述大宰与大司徒“布教于邦国都鄙”“乃施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等,都是对民众进行礼义教化的政务活动。
《周礼》各官中都贯穿着对民众进行礼义教化的内容,这些教化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礼仪教化、道德教化和礼法教化等等。《周礼·地官》所讲的“十二教”,是大司徒一职应当施行的十二种礼义教化的措施:“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6]
第一教“以祀礼教敬”,就是通过祭祀的礼节教民尊崇天地神和祖先;第二教“以阳礼教让”,就是通过乡射饮酒之礼教人民谦让;第三教“以阴礼教亲”,就是通过婚姻之礼教化人们相亲相爱;第四教“以乐礼教和”,就是通过礼乐教化人民和睦相处;第五教“以仪辨等”,就是通过礼仪来明辨等级秩序;第六教“以俗教安”,就是通过礼俗教育民众安居乐业;第七教“以刑教中”,就是通过刑罚教民守法(这也可以看作一种广义的礼义教化);第八教“以誓教恤”,就是用誓戒教民敬慎;第九教“以度教节”,就是用制度教民节制;第十教“以世事教能”,就是用世间技艺之事教民技能;第十一教“以贤制爵”,就是根据贤行颁授爵位;第十二教“以庸制禄”,就是根据功绩制定俸禄。
在《周礼》中其他各官都有施行礼义教化的责任,只是由于各官职掌不同,因而其施行礼义教化的面向和内容也有所差异。各种礼义教化措施的实施,其最终目的就是对全社会的人们进行人文化育,把自然的人纳入政治性伦理性轨道上来,使各等级各阶层的社会成员都能自觉遵守社会礼义规范,和平相处,共同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
(三)职官制度的设计体现了“礼法相济,礼主法辅”的社会治理思想
《周礼》虽然是一部记述我国古代礼制的典籍,但其中也记述了许多有关“法”与“刑”的内容,而且可以说是我国先秦文献中讲述“法”与“刑”内容最多的一部典籍。
《周礼·天官·大宰》曰:“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7]《周礼·秋官·大司寇》也记载:“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8]“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9]这里所谓的“刑典”与“刑象之法”虽然还不能与现代意义上的刑法典等量齐观,但把它们看作刑法典的雏形或原始的刑法典是没有问题的。
正如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晁福林先生所说:“我国上古时代的法制情况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周礼》一书中。《周礼》一书虽非周公所撰,但其内容多反映了本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面貌……《周礼》一书浸润着社会和谐发展的精神,贯彻了‘礼-法’融汇的原则,颇具古代中国特色,在古代中国法制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研究中国古代法制离不开对于《周礼》一书相关内容的探讨。中华法系的内容非常丰富,后世的律、令、格、式等方面的内容都可以在先秦时期,特别是在《周礼》一书中,找到其渊源之所在。《周礼》一书虽然涉及周代多方面的社会制度,但其核心内容则是非常系统的行政法典,既有国家构建方面的根本大法,又有关于刑事及民事方面的诸多法规和指令。先秦时期,礼、法相融,《周礼》一书偏重于以礼融法,其指向在于构建系统而和谐的社会结构形态。正如前辈专家多曾指出的,《周礼》一书对于国家结构与法制建设,虽然具有一定的理想化的倾向,但其现实性质在不少方面已为地下考古资料证明。”[10]
《周礼》中法制(刑法)内容主要集中于《秋官·大司寇》篇。现代学人对本篇中的法制(刑法)内容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当为张全民的博士论文《〈周礼〉所见法制研究(刑法篇)》和温慧辉的博士论文《〈周礼·秋官〉与周代法制研究》。
《周礼》分门别类地记述了六大系统的官职及其职掌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制、工程等各种制度。《周官》所记载的这套职官系统及其相关制度从总体说来属于礼制的范畴,其中秋官系统的职官及其职掌则主要属于法制的范畴。《周官》设计的这套职官制度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礼中有法、法中有礼,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的国家治理模式。这与孔子与先秦儒家重视礼制,主张礼主刑辅、礼法合治的政治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因此汉儒将其纳入儒家文献体系之中,并将其由本名《周官》改称为《周礼》。
《周礼》一书的结构安排和思想内容体现出礼法相济、礼主法(刑)辅的特点。在《周礼》中法是作为维护“礼教”的辅助手段而存在的。它主张在社会治理领域用礼义教化民众,用刑罚禁止民众违礼。如《周礼·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行,二曰不睦之行,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行,五曰不任之行,六曰不恤之行,七曰造言之行,八曰乱民之行。”[11]显然这是以八刑纠正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乱民等八种违礼行为。郭伟川先生指出:“礼学是儒学最重要的核心部分,故《周礼》一书显然充分地体现了儒家的礼治观念。至于治国方面,儒家历来主张礼、乐、刑、政四者并举,而以礼乐为先,但对刑法并不偏废。这一点从《周礼》中设‘秋官司寇’可知。于是,国家典章制度既立,礼制昭然,法在其中。故笔者认为,从《周礼》一书的主要内容及其体现的治国理念来看,显然是以‘礼’为主,‘法’为其辅。”[12]
在《周礼》中礼与法虽然相济相成,共同建构起一个庞大的礼制系统,但在这个礼制系统中,二者的地位不是并列相等的。在这个礼制系统中礼外无法,出礼入刑,也就是说礼是规范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根本制度,理所当然地也是指导法的根本原则。一方面,制定和执行法的依据在于礼,即礼外无法,礼是法的指导;另一方面,礼需要以法作为保障,违反了礼,就纳入法的制裁范围,法是礼的保障和必须补充。所有的规章制度都属于礼,违反了礼就是触犯了法,就应该用法来惩处。礼居于主导地位,是法的依据和总纲;法居于辅助地位,是礼的补充和保障。礼侧重于从积极层面进行规范,告诉人们行为的准则,用道德教化的方法禁恶于未然;法侧重于从消极层面对违礼行为进行制裁,通过刑罚惩处的方法纠正违法行为。
(四)创立了多官联合、协调治事的“官联”制度
所谓“官联”制度是指在处理一些国家大事时,一官不能专擅,需要会同众官联合、协调处理政务,互相佐助配合,把政事解决处理好。这项制度可视为《周礼》的创造性贡献。
“官联”制度是《周礼·天官·大宰》提出的“八法治官府”的第三法。《周礼·天官·大宰》曰:“以八灋(法)治官府:一曰官属,以举邦治。二曰官职,以辨邦治。三曰官联,以会官治。”郑玄注:“官联,谓国有大事,一官不能独共,则六官共举之。”[13]“官联”制度的作用就是让各官互相制约以避免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过分专断,其实质就是权力的分化。
“官联”是《周礼》“治官八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也是一项非常关键的政事处理规则。清儒孙诒让曾揭示“治官八法”的重要性说:“古经五篇,文繁事富,而要以大宰八法为纲领。”[14]“全经六篇,文成数万,总其大要,盖不出此八科。”[15]宫长为先生更进一步指出“官联”的重要性:“在太宰八法之中,官联一科,尤为重要,……而天官之要在八法,八法之要则在官联。”[16]由此可见“官联”制度的重要性。
大宰(冢宰)作为天官系统乃至整个六官系统的枢纽,虽然其权力制约范围非常广泛,但他并不能独揽大权、专断朝纲,因为“官联”制度会有效地限制和约束某一职官的专权。按照“官联”制度的构想,无论是在同一系统之中,还是在不同的系统之中,《周礼》各官之间都可以通过“官联”,使官员之间互相配合、依存和制约,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政事管理系统。这种使各职官之间相互监督牵制以防止舞弊的官联制度,能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各官在其他职官的制衡下正常运行。
二、《周礼》的行政制度设计对后世政治的重大影响
《周礼》一书自汉代发现以来,就成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争议的焦点。古文经学认为《周礼》是周公遗典,“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17]。今文经学则认为《周礼》是“末世渎乱不验之书, 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18]。两汉之后,关于《周礼》的成书问题,一直争议不断。宋代的胡安国、胡宏父子甚至“以为(《周礼》)是王莽令刘歆撰”[19]。不过,由于《周礼》一书记述了系统的职官制度,体现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因而对后世政治和学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得到了汉魏之后的历代王朝政府和学者的推崇和重视。后世不仅许多王朝以《周礼》为蓝本进行职官制度和行政制度设计,而且许多学者以解经为名,从《周礼》中挖掘、阐发制作之精义、圣人之微旨,甚至借阐述先王政治的微言大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后世关注《周礼》的学者中,许多都具有鲜明的通经致用的特点,他们把经典诠释和政治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关注现实问题,依照《周礼》中的理想模式对现实政治进行改革或“变法”。
(一)《周礼》六官制度对后世职官制度的影响
《周礼》设计的六官职官体系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发端于汉代、确立于隋代的“三省六部制”,其“六部”就是仿照《周礼》六官而设置的;唐代将六部定名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至清代。在隋唐之前,汉成帝置“四曹尚书”,即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尚书,是后世六部尚书之滥觞。唐杜佑《通典》记载:“汉成帝初置尚书五人,其一人为仆射,四人分为四曹。常侍曹(主公卿);二千石曹(主郡国二千石);民曹(主凡吏民上书,以人字改焉,自后历代曹部皆同);客曹(主外国夷狄)。后又置三公曹(主狱断)。”[20]汉光武帝刘秀在尚书台设三公曹、吏曹、民曹、客曹、二千石曹、中都官曹等六曹尚书,为六部前身。西晋时,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属尚书省。显然,东汉时期尚书台下所设的六曹既是《周礼》六官的仿制品,也是隋唐以后三省六部制中六部的前身。
(二)《周礼》“荒政”思想对后世政治的影响
所谓“荒政”,就是指灾荒年间由政府组织实施的救荒赈民的政策措施。换言之,“荒政”是国家政府因应灾荒而采取的救灾政策。
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灾难,例如地震、旱灾、水灾、蝗灾、瘟疫等,《周礼》是我国最早提出系统的“荒政”思想和政策的著作。《周礼·地官》述大司徒之职时对于“荒政”列出了十二条纲领:“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21]《周礼》提出的十二条“荒政”纲领,包括了国家放贷、蠲缓租税徭役、降低各种礼仪标准以节约物资消耗、祈神禳灾、严禁盗贼等灾后补救措施。《周礼》中这一系列的“荒政”措施及其观念体系对后世历代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灾荒的发生不可避免地会加剧社会动荡,激化阶级矛盾,对国家统治秩序构成严重威胁,故后世历代王朝大都在《周礼》“荒政”思想的影响下,较为重视“荒政”政策的实施,采取诸如平籴、常平仓、移民、减税、发放钱粮等措施,通过赈济灾民来维持政权统治的延续。
(三)后世以《周礼》为标榜的政治改革
《周礼》以六官为框架设计构建起一套严整完备的职官制度,而且还以这套职官制度为基础构想建立起诸如畿服制度、都鄙制度、爵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赋贡制度、军政制度、刑法制度、市贸制度等众多政治制度和礼仪制度。这些制度或来源于当时或前世实行的制度,或出于作者理想化的构想。
由于《周礼》记述的一系列制度不仅整齐完备,而且多具有理想化的色彩,因而获得后世众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青睐。汉代以后,许多王朝根据《周礼》的思想和制度进行政治实践,甚至有很多政治家根据《周礼》进行政治改革,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几场著名的根据《周礼》进行的政治改革多以悲剧或失败收场。孙诒让曾在《周礼正义·自序》中这样论述历史上几位托《周礼》进行政治改革的著名人物:“刘歆、苏绰讬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踣其祚。李林甫讬之以修《六典》而唐乱,王安石讬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乱。彼以其诡谲之心,刻覈之政,偷效于旦夕,校利于黍杪,而谬讬于古经以自文,上以诬其君,下以天下之口,不探其本而饰其末,其侥幸一试,不旋踵而溃败不可振,不其宜哉。而惩之者遂以为此经诟病,即一二闳揽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于今,是皆胶柱锲舟之见也。”[22]
孙氏认为:西汉末年刘歆辅佐王莽篡权并根据《周礼》进行政治改革而身死国灭;西魏末年苏绰辅佐宇文泰篡权并根据《周礼》进行政治改革也落得与刘歆一样的下场;唐代李林甫根据《周礼》纂修《唐六典》致使唐代政权出现危机;宋代王安石根据《周礼》进行政治改革而引发北宋政局的混乱。需要指出的是,孙氏所说并不准确:一是苏绰的结局与刘歆并不相同,他是病亡,而不是像刘歆那样被处死,而且其改革官制并未导致宇文泰政权的垮台。二是唐王朝在唐玄宗时期出现政治危机不能把责任推到李林甫纂修《唐六典》上,而且他也并没有按照《周礼》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改革。
下面我们分别考察一下王莽、宇文泰和王安石三位著名历史人物托《周礼》进行政治改革的有关情况。
1、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是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王莽是西汉末年著名的外戚和政客,凭借权术篡汉成功,建立新王朝,登上皇位。王莽在篡汉自立的过程中,得到了古文经学家刘歆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刘歆试图根据《周礼》及其他先秦经典来修改和取代西汉时期的政治制度,比如仿周公居摄政事,立五等爵封制,以六为数分城置州郡县,模仿周代井田制实行“王田制”,根据《周礼》的赊贷之法颁布五均六管法等。
王莽在改制中食古不化,控制朝政后,“议论决断,靡不据经”[23]。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24],一切政令、设施都尽可能从《周礼》中寻找依据。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他的改制大都出于空想,并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因而遭到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反对,最终失败,新王朝也随之灭亡。
2、宇文泰改革官制
西魏末年,权臣宇文泰进行官制改革。他授意汉族士人苏绰、卢辩依据《周礼》制定了一套新官制。这套新官制不采用魏晋以来的官职名号,而是仿《周礼》设立六官: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余官称号也都仿《周礼》。这套新官制并不是将秦汉官制一概废除,而是参照使用,尤其是地方官职仍然按照秦汉旧法而不变。同时,宇文泰利用改革官制之机,将地方官吏任免之权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为其子宇文觉后来篡权建立北周奠定了基础。
3、王安石变法
北宋神宗时期,宰相王安石也根据《周礼》发动了一场旨在改变北宋积贫积弱局面的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元丰变法。
王安石在变法实践中特别重视《周礼》一书。他认为《周礼》是先王制度与先王思想的主要载体,包含着丰富的制度资源和思想资源,因此把《周礼》作为其变法实践的依据。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王莽根据《周礼》进行改制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以《周礼》为指导的社会变革运动。王安石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宋神宗去世后,王安石变法也以失败而告终。
上述三个参照《周礼》对社会政治进行改革的典型事例虽然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后世依然有许多学者非常重视《周礼》,他们从通经致用的目的出发,希望能从《周礼》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方,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改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