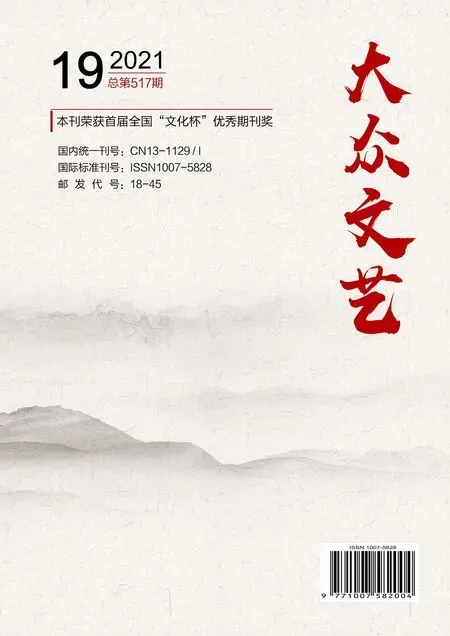现代语汇阐释传统戏曲的矛与盾
——观戏曲电影《对花枪》有感
杨建华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戏剧影视系,北京 100068)
数字时代,新一代戏曲导演在电影技巧运用上,更加大胆充分,为当代戏曲电影带来了新的个性与风貌。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与融合之中,新时期戏曲电影对传统戏曲既有突破又有丢失:在叙事形态上,剧情上升为第一位,情节整体完整的同时,程式化动作减弱,生活化形态加强;在创作风格技巧上,视觉效果增强的同时,戏剧主体却被忽略。得失之间,很多创作者及其作品就像是一手持矛一手持盾的叫卖者,随时都有可能自相矛盾。戏曲电影《对花枪》在此浪尖上也创造了新争议。
首先,浅谈《对花枪》“突破之矛”。一、行当突破。《对花枪》从本体讲,传统程式保留很好,合理创新角色行当,力求京剧老旦唱、念、做、打俱全,深化人物创造手段。审美角度看,现代人的情理需求更深入细腻,呈纵向发展。袁慧琴扮演的老旦角色,内涵相对丰富、行当特点不再单一。二、置景抽象。传统电影一般有两种置景风格:舞台记录式和实景,《对花枪》利用不规则几何图形对舞台置景进行了写意设计,很符合戏曲美学抽象虚拟的写意创作原则。把传统戏放在这么一个时尚抽象的环境中来演,既保留了戏曲原有特质,又扩大了京剧张力,颇有后现代感觉;神似郭宝昌的《春闺梦》,但多媒体数字技术与舞台抽象置景结合,视觉上更耳目一新。因此,电影《对花枪》是戏曲电影一次大胆尝试,只有通过这种新的尝试,才有可能使京剧等戏曲在新时代吸引新观众、焕发新活力,更好地流传下来。新媒体的传播力度不容忽视,也是戏曲影视创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变则通”,目前戏曲发展几乎到了博物馆艺术的阶段,必须向其他领域探索、延伸、吸收,最后再反哺本体。三、舞美基调纯粹。《对花枪》的舞美置景中,保留着舞台观演感觉的底线,最值得肯定的是黑色底调设计:1.纯黑色底屏滤掉没必要的杂质,浓缩并强调了舞台,增强舞台的纵深感;2.黑色底调给抽象的背景拓宽了观看视角,镜头又多用俯拍,给人以居高临下三面观演的视角。3.部分人物出场亮相在黑色区域,突出戏曲人物鲜明色彩,比起戏曲舞台九龙口亮相效果,这个黑色调在戏曲电影中的使用,有过之无不及,把传统戏曲的程式最大化融进了现代语汇。这一点值得借鉴,甚至可以发展为戏曲电影置景程式。
其次,反观“右手之盾”。因为大胆突破,《对花枪》获得好评如潮,甚至被誉“里程碑式”的定义。特别是《对花枪》中有一个长达23分钟多的镜头,108句唱段,只有袁慧琴一个演员表演。大家给予这个镜头以极高的评价,甚至拿它来和苏联电影史中,一部以一个长镜头贯串始终而著名的电影进行比较,声称这个23分钟的长镜头是在挑战电影极限。其实,这恰是混淆电影审美理念,忽略戏曲本体特质的评价。毕竟数字技术在戏曲中的运用仍处在尝试和摸索阶段,用“23分钟”和特技做一定的商业宣传固然可以,但市场炒作和作品质量要能力对等才可赢得最后的胜利,切不可过早孤芳自赏。很多艺术作品在创新中都会出现本体和创新相优相盾的情况,《对花枪》也不例外,值得争议的有以下几点:
一、戏曲本体与电影长镜头的矛盾
大家众口皆碑的这个长镜头,恰恰最具有争议。首先应该明确:长镜头是摄影过程从开机到关机,未间断且完整的拍摄下一个完整的戏段、表演过程或电影意念。从概念上,《对花枪》的长镜头符合这个条件。但从美学意义上讲,长镜头不等于镜头长。电影美学中的长镜头中,表现的是事物的多含义,一个长镜头的构成,至少应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戏剧元素。它有瞬间性与随意性;是以人物调度来达到蒙太奇效果的,随着人物的运动并能产生一定的纵深感和写实感。电影镜头中每一贞镜头中包含的信息量是相当大的。[1]而戏曲本身“以歌舞演故事”,它的音乐延续性与大段抒情性唱腔的特性直接决定了—戏曲电影中,镜头的长度要比一般电影长。所以说,舞台艺术对观众而言,整场就是一个“长镜头”。《对花枪》只是基于戏曲特有的音乐性,将这种观演形式延伸到电影中,和一般电影中的长镜头并不具可比性。而且,从电影剪辑角度来讲,中间的叠画与特技部分,本身就是剪辑点,并不具备电影长镜头审美所具备的时间线性前进感。其次,镜头处理方法上,1.其实没必要保留这么长的唱段。戏曲节奏本身就慢于其他戏剧表现方式,而电影播放过程中,电影时长观感要长于生活时长。《对花枪》虽然在技艺上对老旦行当进行了丰富,却忽略了老旦最大的问题就是唱腔拖沓冗长,把它搬到银幕上完全可以借助电影处理手段把节奏提上去或者对唱词进行一定的删减。虽然多媒体技术可以丰富画面,但唱腔本身节奏决定了整个影片的节奏。再美的画面,一个人自言自语二十多分钟,即使有故事在语言中,观众也会累。既然拍成电影,就要照顾到电影观众的审美习惯而不是只针对戏曲观众。2.在这个二十三分钟的唱段中, 这一个镜头有叙事、回忆、想象、抒情,不断变化的背景采用了国画、剪纸等多种传统艺术形式, 来反映四季变换,表达唱词意境。用心良苦, 有一个画面值得肯定,那是表现姜桂枝思念亲人的孤苦之情时出现的背景:深蓝的夜,几缕云、一弯月,既有视觉美感又烘托氛围,简洁、线条柔和、又贴切人物心理。但是这个长镜头里其他过于具象的画面,比如剪纸、水墨画作品,和戏曲的似与不似之间的“意境”并不融洽,有拼凑感,风格不统一难免让人跳戏,多媒体只是从表层图解人物唱词和心境。且有几个背景过于突出鲜明,虽然视觉冲击力增强,却有喧宾夺主之嫌,不但没有增强艺术感染力,反而削弱了人物表现力。戏曲是传统的,但并不是所有传统元素杂凑在一起就可以来修饰戏曲,也不是所有包含传统文化的画面杂凑在一起就真的具有传统文化内涵。重要的是如何保留本体特质下,融合的天衣无缝。3.在声音录制和灯光方面还不尽人意。数字技术营造的写意环境时虚时实、时而空旷时而狭近,但是演员脸上的布光却永远都没有变化,声音听起来也缺乏空间感。镜头讲究写实,这些细节难免是一个疏忽。
二、棱角与圆润——写意布景中的矛盾
《对花枪》布景有创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主景是抽象的几何造型,立体感强、色彩运用漂亮,感官刺激加强。黑色底调的运用,分外加强了布景的分量。“矛盾”就在这里,当人物运动在黑色区域中时,人物形象得到很大强调和突出,当人物运动到景片中时,布景就开始和演员抢戏。特别是在山路上的那两场戏,镜头还有点俯视角度,雪白的三角形景片加上一些线条的涂鸦,在黑色调衬托下,显得棱角过于鲜明硬朗,而戏曲圆润的调度和流线性的武打线条在这样的环境中则显得格格不入。这样过于坚硬的线条布景、绚丽的数字背景大大增强了“间离”感,“共鸣”感却明显降低。艺术审美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艺术审美的最高境界是共鸣与间离、情与理的双向满足。不经意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创作冲突就出现了。
三、新编与传统文本结构的矛盾
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是个优秀典范:它从当今视角出发,分别在人文、社会、人性等多个角度都占足分量,深入分析,重新阐释了曹操与杨修的关系,人物丰满、内容深刻警醒。相比之下,《对花枪》在剧本结构上,还是像传统老戏一样重点突出了老旦这个角儿。1.没有从新的人文角度阐释相关人物。2.没有从当代角度来处理问题。《对花枪》创作阵容强大,由著名京剧老旦演员袁慧琴领衔,著名京剧花脸表演艺术家李长春、京剧老生新秀张建锋联袂主演。老旦表演精彩饱满,花脸与老生的戏,却乏善可陈。文本结构局限,使剧中角色塑造好似蜻蜓点水。如:李长春扮演的程咬金,代表了某些贤明君主,最后的冲突解决办法还是寄希望于贤明君主:因程咬金定下的英明决定才得以圆满。而老生新秀张建锋所扮罗艺一角,其心理犹豫、情感转变太过仓促,仅是迫于上级命令才答应迎战。他对老太太的感情究竟是什么?两位老人心底多年的情感纠葛并未调动出来就草草圆满。甚至某些关键点,基本的表演交流都没有。比如,姜桂枝与罗艺在离散几十年后,经历重重矛盾与误会,终于在山下宣战,得以相见。这么关键与复杂的一刻,这可是几十年未见的情仇冤家,两位老人第一眼看到对方时,竟没有任何镜头节奏或者表演节奏上的处理,非常草率。情不入心、事不入理。从整体来看,《对花枪》布局谋篇略有失调。
总之,用现代语汇来阐释古典戏曲,绝不是给传统设计一件时尚外衣。尺寸拿捏之间,需要艺术创作者在综合考量上更严谨。20世纪50年代,吴祖光等艺术家拍摄戏曲片以舞台记录为主,60年代,崔嵬、陈怀皑的《杨门女将》《野猪林》等作品使北方戏曲电影有了发展,形成了具有时代感的戏曲艺术片风格。今天,高科技、多媒体迅猛发展,艺术手段得以丰富,戏曲电影电视剧的探索形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对花枪》将戏曲纪录片和戏曲艺术片两种不同的创作形式结合起来,在具有强烈舞台纪录感的同时,又给予了鲜明的时代创作特征。探索如何在保持戏曲艺术特质的前提下,用影视的手段和语汇来提升剧作的内涵、烘托戏剧情景和演员的表演这方面,《对花枪》的探索精神与方向还是值得肯定的。
英国戏剧家彼得.布鲁克在《空的空间》中谈道:“不合格是世界各种戏剧的通病、现状、和悲惨剧。一般的观众可能发现不了的问题,评论家却一定要注意到这些,要发现不合格!尖锐评论家那怒不可遏的反应是可贵的—那是要求看真正够水平的戏剧的呼声……”[2]在众多戏曲电影的创新摸索中,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创作尴尬常态多见,但是相关评论疲软。非公开场合下常能听尖锐而苛刻的批评,公共平台却多是鼓励和理解,一针见血的见报评论是少之又少,令人深思。客观评论可以促使进步,每位从事戏曲、热爱或曾经热爱戏曲的人,都有责任对此提出要求,而非手持矛盾妄图一箭双雕的叫卖者。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解与鼓励,恰恰是对戏曲失望的敏感回避,这样其实更有点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