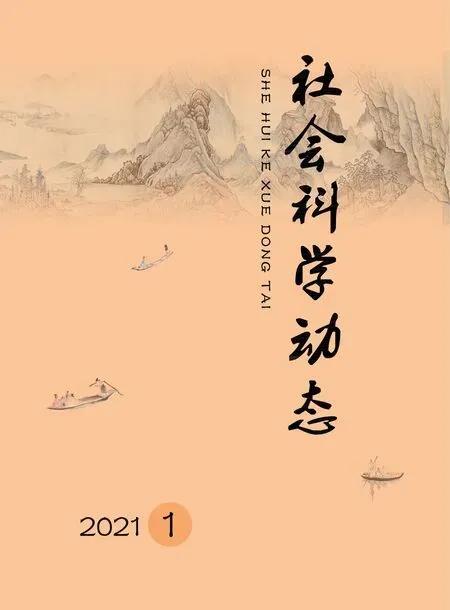五四童话中童心想象与启蒙话语的纠葛
——以叶圣陶的《稻草人》为例
刘小雪
20世纪20年代,在周作人、鲁迅等人的呼吁下,中国现代文坛掀起儿童文学热潮。本着为儿童创作的理念,叶圣陶也开始关注童话,并于1923年出版童话集《稻草人》。然而,他在创作数篇纯真的童话后,“著作情调不自觉地改变了方向”①,由孩提的梦幻迅速转向成人的悲哀。对于这一创作倾向的变化,叶圣陶也曾困惑“太不近于‘童’否”②,但其后的《牧羊儿》 《古代英雄的石像》等童话作品,现实人生的灰暗色调非但没有减少,反倒越发滞重了。《稻草人》的创作过程中,作者为何背离了赞颂童心的出发点,转而发出成人的哀叹与讥讽?应怎样看待这一童话书写?为回答上述问题,笔者认真梳理了《稻草人》的创作转向及其背后的话语逻辑。
一、《稻草人》 的儿童书写与童心能量
1921年11 月,叶圣陶抱着创作“适宜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③的想法,开启了童话的创作。到1922年6 月,他先后在《儿童世界》上共发表20 余篇童话,并在1923年以“稻草人”篇名为题合集出版。
展开童话创作时,叶圣陶在教育领域已深耕多年,可以说相当熟悉儿童心理。其童话作品不单能作小儿情态,更充溢着童心能量,“由儿童底感官可以直愬于其精神底堂奥”④。他并未采用当时流行的国王、王后、精灵等西方童话形象,而是创造性地塑造了傻子、芳儿等天真睿智的现代儿童形象,以及燕子、梧桐子等人格化的形象。郑振铎曾在《〈儿童世界〉第三卷的本志》中提出“应当本着我们的理想,种下新的形象,新的儿童生活的种子”⑤,而芳儿等儿童形象显然也蕴含了叶圣陶对于现代儿童的殷切期待:他们多自由地徜徉于大千世界,张扬着儿童主体的自我意识。
卢梭曾指出,儿童唯有脱离社会,在自然中才能成长为“不受传统束缚而率性(即按本性)发展的人”⑥。顺应本性、自然成长的儿童构想,也渗透在叶圣陶的儿童书写中。他笔下儿童的活动背景多是乡野田园。《稻草人》的23 篇童话,无一不以清新瑰丽的自然景色开篇。如《小白船》的开篇:“一条小溪是各种可爱东西的家。小红花站在那里,只是微笑,有时作很好看的舞蹈。绿草上滴了露珠,好像仙人的衣服,耀人眼睛。”⑦这般简单清新的文字,蕴含着天真的童心自是不必说,也映射了创作者对儿童烂漫情态的珍视。“可爱”的不单是自然,更是弥足珍贵的童真。叶圣陶笔下的孩子们生长于自然中,他们无一不亲近自然,在自然的美景中酣醉:在长儿的眼中,春天的花园是他向往的胜境、幻想的乐园;月下的梦中,芳儿与月亮、云儿舞蹈,将星星做成项链送给最爱的母亲;男孩、女孩乘着小白船在溪水中畅游,与动物歌唱嬉戏,好不快乐。这些儿童在梦幻的自然中驰骋身心,他们的本真与纯粹的自然在此融为一体。
自然中的儿童并非只有天真,他们也可能遭遇种种艰险:乘小白船出游的男孩、女孩,遇到乍起的风浪,好不容易驶过风浪,又到了无人的陌生旷野;再如梧桐子独自担惊受怕的旅行,在外玩耍的燕子意外受伤,等等。这些幻化的危险皆隐喻了儿童成长可能遭遇的困难,但在“童心”面前,这些艰险并无实质的阻碍作用,因为一切终会被孩子们所克服。《小白船》中的男孩面对风浪丝毫不惧,安慰女孩之余,“自己站起来,左手按帆绳的结,右手执一柄桨。很快的一个动作:左手抽结,右手的桨,撑住岸滩。帆慢慢的落下来,小白船便止住了”⑧。而面对陌生人的考验,他们俩也机智应答:
那人说,“第一个问题是鸟儿为什么要唱歌?”
“要唱给爱他们的听”,她立刻回答出来。
那人点头说,“算你回答得不错,第二个问题是:花为什么芳香?”
“芳香就是善,花是善的符号”,男孩子抢着回答。
那人拍手道,“有意思,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小白船是你们乘的?”
她举起右手,像在教室里表示能答的姿势说,“因为我们最纯洁,唯有小白船合配装载。”
那人大笑道,“我送你们回去了!”
两个孩子乐极,互相抱着,亲了一亲,便奔回小白船。⑨
这段故事中的考验情节采用典型的三段式结构,突出两个孩子的现代儿童特质——他们主动体认了儿童的纯洁、善良,尤其“我们最纯洁,唯有小白船合配装载”一句,更是传递出独有的自信与自尊。
此外,在《鲤鱼的遇险》 《芳儿的梦》等作品中,也充分展露了孩子的机智:鱼儿们依靠自己思考出逃出木桶的方法,芳儿从自然中获得了礼物的灵感。除了依靠自身的机智,这些儿童遭遇险阻时,也多受到成人或他者的庇护,如燕子得到青儿的细心救助,梧桐子被好心的姑娘捡回,又在小草的陪伴下成长为一棵大树。
叶圣陶的早期童话多效仿安徒生的创作,即运用富于诗意的浪漫想象,去写就儿童在冒险中成长的理想故事。故事中,孩子们的独自冒险、种子的飞行等只是幻化的,很快便被化解。这些情节设置显然意在消解他们探索外界的不安,为其营造温暖的成长情境。与此同时,儿童的心愿也在幻想的维度达成,他们不单得到各类人物的庇护与助力,愿望得以满足,甚至完成了自身的成长与蜕变。如乘小白船安全上岸后,男孩与女孩不由得感叹:“没有大风,就没有此刻的趣味。” “假若我们不能回答他的问题,此刻还有趣味么?”⑩可见,经历了风浪与考验的儿童们,显然相信自身能够从冒险和考验中获得成长的趣味。作者对这一成长状态的书写,显然是在幻想层面实现了顺应儿童天性发展身心的教育设想。
值得注意的是,《一粒种子》这篇童话以种子的培育隐喻了儿童的自然成长:世上唯有一颗的宝贵种子,在国王的白玉盆中、专业花匠的看护下,都没能发芽;反倒是农夫的“照常割草” “照常浇灌”令其长出了碧玉一般的芽,散发浓厚的芳香1⑪。比起功利主义的刻意培育,叶圣陶认为儿童应在平常的环境下,顺应本性接受教导,“自然”地成长起来。叶圣陶最初创作童话时,着意于书写儿童的纯真天性与自然成长,而这一书写行为的背后,蕴含着这位成人作家的“童心”梦想。所谓“童心”,即“儿童所特有的生理与心理机制”⑫。成人作家写儿童,需模拟儿童的生理与心理特质,在贴近儿童身心状态的前提下,方能刻画出富于童心的作品。叶圣陶早期童话创作基本都以天真目光观察世界,人物的童言稚语也颇得儿童喜爱。此外,这些故事多采用民间童话的圆形情节结构:儿童独自在外冒险,克服险阻,最终实现愿望,于一波三折中收获圆满结局。这一故事结构的设置,正显示出作家对儿童群体的纯真睿智等特质的深刻体认。
可以说,叶圣陶在童话书写中建构起儿童独有的幻想园地,凝聚了巨大的童心能量。尤其《傻子》 《大喉咙》 《旅行家》等涉及现实题材的童话,作者更是有意放大了童心想象的能量。《大喉咙》中,婴儿因不见了母亲,便出门质问工厂的大喉咙即大喇叭。听完婴孩的申诉,大喉咙立即答应不再叫喊,从此婴儿“含着母亲的乳头,睡得很甜蜜,小面孔上全是笑意”⑬。结尾依旧是甜蜜的,但工厂喇叭不再叫喊后,母子俩的生计便无从保证了。另一个儿童傻子的故事也颇为天真:傻子天生良善,待人真诚,却被人嘲讽为“傻子”;然而,傻子在历经不幸后,因大胆质疑国王终于得到赏识,原本嘲弄他的众人也立马改换成赞颂的腔调。不难发现,作者有意借助结尾的反转淡化傻子的悲剧,以凸显天真良善终得好报的道理。《旅行家》则塑造了旅行家这个救世主形象:他因目睹地球人争夺私利,便好心带来万能制造机,使其过上了予取予求的生活。傻子、旅行家、婴儿等人物遭到现实打击时,作家并未令其消沉,反倒挥洒童心,勾勒了美满的结局。可满足众人心愿、大喉咙停止叫喊这类幻想,只是将童心视作超越黑暗力量的象征性策略,但因违背了现实人性与物质逻辑,终究无法激起读者深层的精神启示⑭。叶圣陶的早期童话着意刻画儿童的纯真睿智,赞颂童心能量,“以为‘美’ (自然) 和‘爱’ (心和心相印的了解) 是人生的最大的意义”⑮,描摹了安徒生般“美丽的童话人生”。但他在拓宽童话的现实题材后,便不自觉地讽刺起来,尽管仍旧佯装天真,试图纾解悲苦的现实,却只营造出幼稚的空想。
二、《稻草人》 的现实批驳与成人悲哀
1922年1 月,叶圣陶在给郑振铎的信中提及:“今又呈一童话,不识嫌其太不近于童否”⑯,为新写的童话是否贴近儿童而困惑。1922年1 月至6月,他创作了《克宜的经历》 《稻草人》等10 余篇童话,这些作品一改早期的童心想象,而以亦真亦幻的笔触暴露现实人生的黑暗,并抒写了成人的悲戚。
作品仍借儿童般的无辜眼光打量世界,只是目睹的并非梦幻,而是残酷现实。一个人为寻找同情的眼泪,走遍戏院、工厂,却只看见人们廉价的笑容与麻木的面容;满心丧气之时,终于在孩子那儿捧得了满满的眼泪。“一切人失去的东西”,正是孩子眼中“仿佛明亮的珠”的泪水⑰。人性复归的希望仍旧被寄托在怀有赤子之心的孩童或成人身上,但相较于早期对儿童本体的成长、游戏的书写,作者创作发生转向后的童话作品则更多地聚焦于儿童在广阔世界中触目惊心的“发现”。如《克宜的经历》 《祥哥的胡琴》呈现了乡野儿童视角下的城市见闻。祥哥的胡琴乐声灵动自然,可城里的人们却用眼去“听”,以为祥哥衣衫褴褛,他的音乐自然也是下品。反倒是田野这片“没有围墙的音乐厅”,成就了祥哥的天籁之声,而这自然的乐曲“仿佛温柔的梦一般”⑱,慰藉了乡人的身心,使其忘却了悲哀。另一个乡野的孩子克宜,为感受“美丽而撩乱的梦”⑲进城,却借助蜻蜓的镜子“发现”了可怖的景象:表面光鲜的都市在早晨却是黑暗无光,而这里的人们无论病人、医生,穷人还是富人,未来都只剩下“瘦得只剩皮包着的骨头”,化作“脸上全没血色,灰白到足以惊怕”⑳的死人。这一乡野儿童视角下的疾病观察,在批驳都市生活的同时也保留了生存的希冀:相较于都市人的异化生存,乡村的儿童在和风绿野中成长,其生命形态更接近本真化的存在。
叶圣陶早前的童话书写将儿童抽象为纯真睿智的群体,正如他们所乘的小白船,容不得一点灰暗。但是“从来没经过可怕的事情” “不懂得怕,逃和防备”㉑的天真儿童,如何能应对现实的险恶环境?祥哥、克宜等儿童目睹了黑暗的现实,但他们仍能在自然乡野间保持纯真身心。而到《鲤鱼的遇险》等童话中,天真的儿童便被迫从可怖的现实中觉醒。《鲤鱼的遇险》中,好心的鲤鱼误以为鸬鹚是朋友,被其一口吞下,结果困在木桶里。幸免于难的鱼儿悔恨之余,更改了世代的教训:“凡是有太阳光、月光、星光照着的地方,外面看看虽然平和而美丽,实在和他们所住的那条河一样,里面可怕得同地狱一般”㉒。而木桶中的鲤鱼也开始挣扎,先觉醒的几条鱼鼓动着鱼儿们积极应对:
不要管做梦不做梦,现在身体上觉得干燥难受,有了鳍尾,又没有一点用处,总是我们的痛苦!我们该想办法,怎么可以使痛苦去了?
只要把这木的墙打破了!
只要到河里去取一点水!
只要我们大家熬着,不一定要安适,就躺在这里也不妨!
以上是许多鲤鱼们想出来的方法,他们想到了,就随口说了出来。但是统统给同伴们立刻驳回了,就是以下三句话:
身体还不能动,怎能打得破木墙?
取水固然也好,但是谁能够去取?
熬得住自然什么都不怕了,倒是躺在这里,不得水,就要干死的不好!㉓
从打破、取水到煎熬,鱼儿们试图主动顽抗,或消极等待,然而一番讨论后竟只剩下煎熬的法子。木桶犹如鲤鱼们万难突破的困境,与鲁迅的“铁屋子”的文化隐喻颇为相似。“铁屋子”中的人们,唯有少数的呐喊者叫醒了几个人,孤独地承担“无可挽救的苦楚”,而众人只能“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㉔。不同于鲁迅对国族的悲观预言,叶圣陶在童话叙事中搁置了社会文化结构的复杂争论,选择以幻想的形式打破这一困境——鱼儿们漫溢的泪水使身子潮润,甚至溢满了木桶、船舱,他们最终跳出木桶,重获自由。这一结局固然不乏童真的慰藉,但鲤鱼们也深刻领悟了自救的真谛:“我们怎能得到强盗的帮助?木的墙又怎会自然地破坏?……现在我们不至于干死,原来是我们自己救了自己。这是我们的泪呀!”㉕这类童话将现实困境与童心幻想直接对比,反倒催生了众人团结自救的革命启示,由此丰富了五四一代的文学启蒙表达。
上述故事中的童心幻想,仍被指认为相对现实的异质化力量,然而美满的结局只是表面的叙事因素,幻想叙事的内核已被置换成了人性重塑、国族未来、群众自救等成人启蒙话语。为了展示“真的人生”与“真的道理”,叶圣陶不惜将梦幻的泡沫戳破,创造了画眉鸟、快乐的人等形象。画眉鸟因不明白歌唱的意义来到民间,有着先验自我意识的她,很快便发现了车夫、歌女等“劳力者”的异化命运。当她“为自己唱歌,为发抒自己对于一切不幸东西的哀戚而唱”㉖时,不单张扬了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启发读者将同情转化为行动。而形成对照的是,快乐的人、玫瑰等人物,一味天真,最终莫不落得凄惨的结局。只因周身包裹着一层“透明且无质的幕”㉗,快乐的人觉察不到周边的“混污与颓丧”,可一旦戳破了他的薄幕,他便痛苦地死去了。《玫瑰和金鱼》中,被主人呵护的玫瑰、金鱼原本认为爱是不求回报的,没想到他们都被作为爱的礼物送出,却得不到青年、女郎的呵护,最终落得腐烂的命运。老母羊、老桑树的劝告,以及“不论什么花不论什么鱼,同样的下场,值不得人家的注意”㉘等讽刺话语,都向读者曝露了爱的本质是自私这个道理。
正如郑振铎所言,《稻草人》越到后面,“‘悲哀’分子”便越发浓厚了。长儿这个孩子听闻花园的神仙境界后,便一心渴慕进入。可每去花园外,他总遭到守门大汉的威吓,屡屡挫败的他只得幻想起来:“红的花堆得山一样高,他眼里只看见红色。忽然花笑了,默默地对他笑。从笑着的花脸上,滴下一滴一滴香甜的水。流到地面,凝成红色的香糖。”㉙一系列细腻的心理刻画,再现了儿童愿望从滋长到落空的全过程,造就童心碎裂的悲剧。在后期救赎主题的作品中,稻草人的四次“救赎”行为无疑最为绝望:只因不能言语与行动,他只能眼见虫蛾啃噬稻谷,病孩为穷苦叹气,鲫鱼困死木桶,妇人走投无路而自尽,在目睹无数悲剧后痛心倒下。“稻草人”的倒下,也喻示成人的忧患意识已过于深切,他们无法在童心幻想中得到慰藉,面对现实的悲戚则深感无力。至此,叶圣陶的童心幻梦已彻底沦为现实悲哀的寓言。
叶圣陶后期童话的幻想书写,或映射、凸显残酷现实,或指认国族的未来可能。总之,童心能量的赞颂让位于作家的忧患意识及“针砭现代中国的诸种人世相、社会相”㉚的需要。《稻草人》之后,叶圣陶的童话创作从情节结构到人物命运几乎都充满了深切的悲戚,如1924年的《牧羊儿》,牧羊娃和羊的短暂欢乐后,孩子遭遇母亲离世、羊儿被卖等厄运。
作为童话作家的叶圣陶,并非没有创作的自觉意识,他深知作品“离开美丽的童话境界太远了”,可也无奈坦言“生活在那个时代,我感受到的就是这些嘛”㉛,这或许也是他将《稻草人》这一悲剧作为故事集的名字的缘由。叶圣陶创作的自觉与无奈,正揭示了五四时期童话创作中童心想象与启蒙话语的纠葛。
三、五四童话:“童心的梦” 与 “真实的虹” 的角力
从赞颂童心转向现实批驳与成人悲哀,不仅仅是叶圣陶的童话创作路径,更是20 至30年代童话的主流倾向。当为儿童独享的童话作品中遍布成人的启蒙话语时,童话书写如何界定与评价?为此有必要回溯20年代文艺界对童话、儿童的讨论,分析五四童话的话语纠葛的实质。
五四时期,儿童作为“承载进化主体的最重要形式之一”㉜,其成长教育与文化教养受到知识分子群体的高度关注。正是在儿童与国家民族未来同构的话语背景下,“童话”以“异邦新声”的面貌参与到中国现代的文化实践中来。参照西方的儿童文学史,其儿童文学是在教育课程、政治权力与自由、幻想等话语力量的拉扯下发展起来的㉝。而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芽时期,童话创作也免不了遭遇话语力量的纠缠与对抗,尤其体现为童心幻想与启蒙话语的角力。两股话语的纠葛,表面上是写实主义与幻想精神的对立,实则是不同儿童观念的对抗。正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所言,现代意义的“儿童”是后来者重新建构或发现的“风景”㉞。无论是叶圣陶早先的童心赞颂,还是后期对儿童社会意识的强调,很难说是基于现实儿童客体的书写,而是五四知识分子对理想儿童形象的一种文学建构。
曾经高喊儿童独立的五四知识分子,在20年代逐渐分化成以鲁迅为代表的社会派和以周作人、赵景深为代表的自然派。鲁迅将儿童视为社会历史进程中“未来”的一代,必将处于“宽阔光明的地方”;而儿童幸福度日,则需要成人“肩住黑暗的闸门”㉟。然而,在现实的文化困境下,成人一代尚且需要启蒙,儿童自然也无法割裂与社会发展的现实联系。鲁迅评价爱罗先珂的童话时指出,作为“历史的人”㊱的儿童,必须在“童心的梦”中看定“真实的虹”,才“不至于是梦游者”㊲,意在要求这一群体担负起现实的苦厄以及国族的未来。基于这一现实立场,叶圣陶塑造了稻草人、鲤鱼、画眉等觉醒的儿童,使其直面“真的人生”与“真的社会”。周作人、赵景深等人则继承了卢梭的儿童观念,强调儿童的自然属性而非社会属性,主张顺应“小儿趣味”发展儿童身心。正是着眼于儿童的自然成长,叶圣陶才塑造出燕子、梧桐子、芳儿等“自然”儿童,使其在自然中徜徉,愉悦身心。其后期对于现实忧患的过度展现,则被周作人批驳为“太过教育的童话”,以为“非教训的意思”方才是理想的儿童文学,“儿童的空想与快活的嬉戏,比那些老成的文字更与儿童的世界接近了”㊳。赵景深也指出,只因太过心切,成人才创作这类教训的童话,但这只是“尽量的把饭塞了进去”㊴,而不顾儿童是否吸收。这一说法看似偏激,实则切中肯綮:鲁迅等启蒙主义者对儿童文学的现实诉求,并非源自儿童本体的呼吁,而是成人遭到社会文化的围困后而做出的妥协。出于迫切的启蒙诉求,叶圣陶创作出教训的童话,径直指出儿童的天真可笑;同时多赋予他们以“不得所爱” “不得所求”的悲剧结局,着意要使儿童迅速了悟现实,尽快成长为睿智的一代。
尽管《稻草人》创作倾向和儿童观念前后不一,但正如鲁迅所言,《稻草人》 “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㊵,尤其在发扬童心幻想上,《稻草人》称得上现代童话的开山之作。作家不单创造了天真烂漫的儿童形象,也善于运用清新自然的笔触传递启示,可谓“自然生出美妙与教训”的文字。而经由这般“童心的梦”,儿童和成人都能从中得到“慰藉”。其实,儿童、成人对童心幻想的审美接受是共通的。尤其对于力求摆脱“年少老成”的文化传统的五四文人来说,童话所隐含的童心能量是巨大的,这使他们能暂时搁置现实烦扰,在童真境界中撷取美好。此外,《稻草人》等五四童话标举儿童的独立,使“儿童”这一群体被抽象为成人不具有的纯真睿智等特质时,童心幻想不单能助力儿童成长、协调儿童身心,更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超越黑暗现实的成人梦想。《稻草人》中,克宜、祥哥、鲤鱼等形象的命运被用来指认未来的出路,在有意放大童心能量的同时,也实现了超越现实困境的成人梦想。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童话创作为知识分子“建构了一个与现实相对的想象空间”,“并与当时流行的启蒙话语、个人与国族的进化想象有着更为复杂纠葛的关系”㊶。童心幻想的所指已被置换为国族进化等启蒙话语,幻想便沦为表面的形式。并且,这类童话中过于强势的启蒙话语明显破坏了童心力量与幻想精神的传递。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童话的幻想品格始终不高,显然与萌芽时期幻想精神遭到的过度压抑有关。但在五四时期的整体文化语境下,完全搁置启蒙话语或教化观念,似乎也并不现实。如何在童话书写中平衡童心幻想与启蒙话语的关系,便成为关键问题。对此,周作人从安徒生的文字中得到启发,认为童话不单要塑造“儿童的世界”,为了达成儿童、成人的共同期待,还需塑造“融和或超越成人与儿童的世界”的“第三的世界”㊷。所谓“第三的世界”,即现实与幻想的交互之地,作家一方面借助儿童的天真目光营造“童心的美的梦”,另一方面也可融进成人的现实思考,只是不能过于真切地揭露现实的悲哀,否则便会破坏这童话的境界。就五四作家而言,他们可经由这“第三的世界”,招呼人们进入“童心的梦”,并在其中看定“真实的虹”。尽管不乏功利的现实诉求,但至少能在启蒙主义的浪潮下,保全些许童心能量,使幻想精神不至于遭到过度损害。当然,要真正发扬幻想精神,则需要文化、教育等社会制度的长期滋养,非一朝一夕之功。
结语
《稻草人》的创作转向,表面上看是现实主义与幻想精神的撕扯,实则是“自然儿童”与“社会儿童”的角力。成人作家创作儿童的童话,其作品审美品格由成人的儿童观决定。当成人顺应儿童天性,贴近儿童心理时,便能创造出赞颂童心的佳作,成人也从中受到慰藉;而作家的思想关注远离儿童群体时,便只剩教训讽刺的启蒙话语,童话精神也就荡然无存。叶圣陶的童话实践与鲁迅、周作人等人的童话讨论都启示我们:童话创作应糅合儿童与成人视野,在激荡现实的同时发挥幻想精神,以寻求启蒙话语与童心幻想的和解。但寻求二者的和解,毕竟是童话书写的理想状态。实际上,现代童话创作始终未能达成童心与教化的和解:无论是五六十年代围绕“童心论”展开的批判,还是当下对儿童本位的过度尊崇,都能看到童心幻想与成人教化两股话语势力的撕扯。就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来说,由于过度尊崇儿童本位,部分儿童文学作品尤其童话对于儿童愿望的满足甚至是不加选择的,以至于创作与宣传呈现出“商业化和娱乐化的趋势”㊸——不少作家打着为儿童的旗号,只知愉悦儿童,而不注重主题理念的煅造。比起五四一代的童话作家们,如今的童话创作者明显缺乏教化儿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回顾《稻草人》的创作转向之余,我们也需从更为开阔的历史面向来思考童心想象与启蒙话语的关系问题。
注释:
①②⑯郑振铎:《稻草人〈序〉》,见叶绍钧《稻草人》,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7页。
③㉛叶圣陶:《我和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④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民铎杂志》1921年第2卷第4期。
⑤郑振铎:《〈儿童世界〉第三卷的本志》,王泉根编:《民国儿童文学文论辑评》 (上),希望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⑥[法]让—雅克·卢梭:《爱弥儿》,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9页。
⑦⑧⑨⑩⑪⑬⑰⑱⑲⑳㉑㉒㉓㉕㉖㉗㉘㉙ 叶绍钧:《稻草人》,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1、5—6、9、10、38、82、124、165、181、185、102、107—108、110—111、113、134、210、144、152—153页。
⑫马力:《童话学通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⑭常立:《论五四时期童话理论的“个性”话语》,《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⑮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蔡元培等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页。
㉔ 鲁迅:《坟· 热风· 呐喊》,《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㉚杨宏敏、王泉根:《叶圣陶张天翼童话之比较》,《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
㉜㊶徐兰君、安德鲁·琼斯编:《儿童的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110、151页。
㉝彼得·亨特:《理解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㉞[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央编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6—167页。
㉟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6 号。
㊱蒋风、韩进:《鲁迅周作人早期儿童文学观之比较》,《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2期。
㊲鲁迅:《古籍序跋集》,《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
㊳周作人:《儿童的书》,刘绪源编《周作人论儿童文学》,海豚出版社2010年版,第186页。
㊴赵景深:《童话的讨论三》,《1913—1949 儿童文学论文选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版,第49页。
㊵鲁迅:《译文序跋集》,《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㊷周作人:《童话的讨论四附录》,《1913—1949儿童文学论文选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版,第56页。
㊸钱淑英:《关于“童心论”与“教育工具论”的再反思》,《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