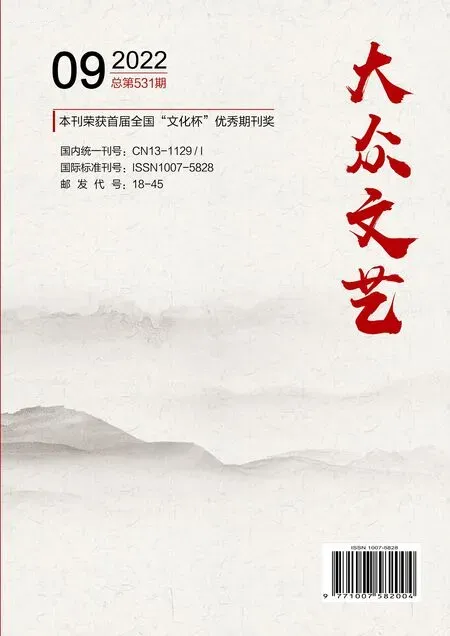嫁娶仪式下性别觉醒的时代转向
陈瑶瑶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550025)
自古以来,男娶女嫁被看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与男尊女卑和重男轻女观念有莫大的关系。父系制时代流传下来的从夫居成为一种主流的婚姻居住形式,而这一方式是影响中国乡村社会及其权力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随着近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性站起来呼吁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不断为女性的权益所奋斗。在这些女性思潮的不断传播中,近代的进步人士纷纷呼吁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但是嫁娶仪式仍然成为一种习俗流传至今。
《说文解字》中对“嫁”字的释义为“女适人也, 从女家声”,即女性离开自己的家到丈夫家居住,这一方称作婆家,而在三朝回门时便成为娘家客人。“娶”字则解释为“娶, 取妇也,从女取声”,即男子接妻子到家中,成为自家人。虽然“嫁”和“娶”都是描述婚姻活动的词语,但是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仍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虽然男女的性别地位已经逐渐趋平,但是嫁娶活动所折射出来的社会思想仍然以一种固习的形式存在着。
一、传统嫁娶习俗下的性别角色
在传统社会中,嫁娶仪式对于女性的束缚远远大于男性,因此,在讨论时会倚向女性视角。男权社会下,女性的人身权利从出生到老死都被剥夺,由男性权威掌控。而在嫁娶仪式下所表现出来的性别差异以亲属网络和家庭权威表现出来。
(一)男女双方亲属关系网络表现出来的性别差异
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社会,家族观念深深刻在每个人的意识中。在经历了神圣的一嫁一娶仪式后,女性便有了两个家——娘家和婆家,女性成为连接两个家庭的纽带。在女性出嫁后,将被冠以夫姓,孩子也会随父姓,其中孩子对父母双方亲属的称谓就呈现出差异,并形成了两套比较系统的称谓体系,即“父系亲属称谓”与“母系亲属称谓”。两套亲属称谓体系表现出人们总是在有意无意间被代代相传下来的伦理所捆绑。
周星认为早期的人类学常常把人理解为单方面的“被社会化”“文化化”,遵从风俗习惯或是硬性的制度而生活着。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人们对于亲属称谓的沿用仿佛就是在被动接受单方面的社会化,反思亲属称谓对于家庭权力关系的分配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女性在举行“嫁”的仪式后,需要在娘家与婆家之间构建起亲属关系网络,但是她所建立的外亲关系不从属于父系亲属关系,而是属于女性自身的亲属关系,因此女性的身份具有两重归属性;另一方面,女性作为外来者进入夫家,处在父系亲属关系的边缘,并逐渐被认同划归在父系亲属关系之下,同时还要遵循父系亲属制度,其身份的双重属性逐渐在小家庭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削弱。
(二)男女双方家庭地位所表现出来的性别权威差异
李银河指出婚后从夫居制度被认为是农村男权制的基础之一。通常丈夫被看作是家庭的顶梁柱,并在权利和义务上成为经营家庭的主要承担者,妻子需要听从丈夫权威。传统制度下的夫妻经营方式为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外的生活内容成为男性力量与权威象征的高度表现,“柔弱”的妇女无法完成父系社会中的重重挑战与考验,轻省便捷的家庭琐事似乎更符合女性特质。在传统的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家庭中的小事妻子常常可以做主,但大事还是得靠丈夫拿主意。而在一个联合家庭中,掌握最高权威的一家之主通常都是男性大家长,女性在家庭中仅仅处于从属地位。
夫妻的结合意味着一个小家庭的即将诞生,而要顺利使小家庭脱离原生家庭,得到独立成长,在传统社会中还会存在关键的一步,即分家。观念上,妻子在分家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因为正是这一角色的出现,使得分家变得理所当然。分家的行为是对原生家庭权力关系的划分的暗示,从属在大家长权威下的男性可以获得小家庭的最大权利来经营自己的家庭生活,如此周而复始。李霞在《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中提出女性所拥有的情感权力在家庭和生活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她认为在农村的主导文化规范中,男性是权力的正式代表,扮演着台前的主要力量,女性则以幕后的支持力量发挥影响作用。男女双方在分别掌握前台与后台权力之间彼此相互给予,但隐性的后台权力在父系权威下始终不具有正式性和规则性。
二、嫁娶仪式下性别觉醒的时代转向
虽然乡村至今还是以从夫居为主,人们始终在潜意识中将已婚的女儿看作在习俗制度上的外人。但是随着生育观念的变化,家庭以养育一个或两个子女为主,随之家庭的养儿防老功能出现弱化,女性对于原生家庭的责任更加重要与突出,父母的观念随之也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发生改变。嫁娶仪式下的社会性别观念逐渐出现新的变化,男女双方对于家庭的认知也出现新的转向。
(一)传统婚礼仪式的弱化
传统婚礼讲究“三书六礼”的形式,过程繁琐复杂。男子娶妻,要行拜堂叩首之礼,而证明女子嫁出去的一个重要仪式就是在男方家拜过祖先,与丈夫行过交拜之礼;而男子在迎接新娘时是否要对女方先祖行叩拜之礼端看各地习俗。女子所带去男方家的物品称作“嫁妆”,而男方拿到女方家的物品则唤作“彩礼”或“聘礼”,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嫁娶仪式从提亲到回门的整个过程都是对男女两性的角色归属,随之女性的生活中心转移至夫家。
随着近代思想开化后,不少人开始效仿西方婚礼,提倡去奢求简,特别是在文化知识分子中,如徐志摩与陆小曼、冰心和吴文藻等文化界、知识界的知名人物。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家门,在酒店、教堂等地举行婚礼,不再似从前那样一家迎娶一家哭送。对于“娶媳妇”、“嫁姑娘”的说法在年轻一代中逐渐没落,结婚不再成为男方的专属名词。传统拜堂仪式正渐渐地被新式婚礼所取代,这不是年轻人的“花样多”“赶潮流”。从社会性别上看,这是年轻一代在性别意识上的觉醒,男女平等不是口号而是实践,形式上的淡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女性权益的一种补偿机制。
(二)两头并重的亲属来往方式
在经历了计划生育的特殊时代之后,“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进一步对压制重男轻女的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强制性作用。以往社会中只有女儿的家庭常常通过“招赘婿”的方式来完成家庭的延续,并解决养老问题,但这种形式对于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来说显然行不通,进而出现双方家庭处在同一地位的情况。娘家与婆家对于子女的依靠是等同的,而子女对双方家庭的付出虽然各有侧重,但总体上还是趋于平衡。虽然有一部分家长不觉得小夫妻应该与老人一起过日子,但养老送终的期望仍然寄托在子女身上,而子女在父母养老上也负有伦理道德上的责任和义务。
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对其家庭地位和角色的改变发挥着积极作用,虽然已婚女性在观念上还没有得到娘家身份(自家人)的正式认同,但是在承担家庭责任和义务时也获得一定的正式资格。就如在养老议题上,传统乡村中女儿不具有给父母养老和继承家产的正式资格,但是在情理上又会默认女儿对娘家的扶持。如今的婚姻生活趋势使嫁娶仪式不再是划分娘家与婆家孰轻孰重的衡量线,在关系来往上,男女两方的亲属都得到同等对待。
三、结语
婚姻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人生议题,嫁娶仪式作为一种习俗一直在延续,少有人对其提出质疑。男女双方的结合为什么要以固定的习俗作为人生重要时刻的庆祝方式?家庭是在不断的分裂中独立成长,具有周期性。而结婚应该是两个家庭同时分裂出成员组成新家庭的过渡仪式,新家庭不归属于两方的原生家庭,并且双方关系不应具有亲疏远近,不论在观念上还是道德习俗中。嫁娶仪式对于男女双方都有一定的损害性,意识上的归属与认同应该远远重于血缘、家族关系。庆幸的是,在时代的前进过程中,旧习俗逐渐展现出新内涵。